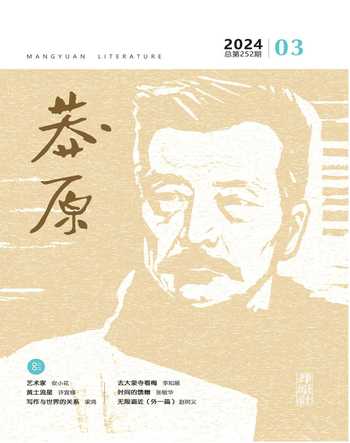与麦同长(散文)
王志荣
一
打麦场上,连耞在空中旋转、翻飞,转轴吱嘎有声,木排砰砰啪啪,重重捶打着麦秸秆,麦芒断折,颖壳迸裂,麦粒骨碌碌蹦跳着滚落。少顷,风呼啸而过,漫卷尘屑,天地一片混沌。母亲抢收麦子的身影在旋风中扭曲,摇摇晃晃,影影绰绰。不承想,母亲已离世三十年,如此亦真亦幻的场景依然穿越时空,入我梦中。猛然醒来,我赶紧去拾掇那些夹藏在时间褶皱里的生活碎片,唯恐有失。
故乡,在渝东北的偏僻乡村,山高坡陡,田少地多。稻谷占据了平坦的田,麦子只有屈身旱地,因此叫做麦地,而不是麦田。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粮食有粗粮与细粮之分,有主粮与杂粮之别。比如大米、麦子是细粮,红苕、洋芋、麻豌豆等等是粗粮。即使同类粮食,也分了等级优劣。可我时刻不敢忘记在我饥肠辘辘、食不果腹时,根本无法抵挡任何食物的诱惑。面对饥饿,粮食的等级优劣似乎毫无意义。
麦地,也是耕地的嫡系,得取个响当当的名号,既便于称呼,又能明确麦子的专属领地。农民是伟大的创造者,从不缺乏生活智慧。他们依山就势,总能给麦地配上熨帖的名号:陡峭的叫麦地坡,山湾里的叫麦地湾,岭上的叫麦地岭,山包上的叫麦地包,有坎的叫麦子坎,沟边上的叫麦子沟,低凹的叫麦子凼,稍平的叫麦子坝……
麦粒晒干,或磨面发酵蒸麦子粑;或去面坊,兑换成白面,蒸馒头;或直接调换成面条。只要是入人口腹,都是好归宿。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食物因是待客上品,我爱吃,却不能常吃。犹记儿时吃面条,总要有意无意地发出响亮的声音——嗦。用现在的礼仪标准,嗦面条似有不雅之嫌,但那时候,“嗦”是最美味的佐料,对治愈饥饿带来的恐惧感,也有超级疗效。
母亲爱麦地胜过爱自己。农闲之余,摆龙门阵,一旦提及麦地,她就兴致盎然,滔滔不绝地讲述,总是一腔自豪的语气。在柏青村这个狭小的山旮旯,母亲绝对有这个资格。贫瘠的边角地到她手里变戏法似的肥沃了,产量高了。当然,这与我传奇般的落生不无关系。据母亲讲,那时她挺着大肚子正在地里挑渣子肥,我火急火燎地要出世,差点儿就把我生在地里。乡亲们戏谑,说我是后稷转世,庄稼的保护神,也有的说我是渣子肥榨出来的,特别肥地肥庄稼。后来,跟着母亲在地里摸爬滚打,我倒感觉自己像一粒麦种,被母亲种在麦地,与麦子一同生长。麦地,成了我生命的土壤。
海子有诗言“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海子说的“你”,无疑也包括我。
二
给麦粒一个家,这是麦地存在的意义。种麦,长麦,收麦,日子漫长,过程复杂,充满辛酸。越复杂的事,越是从小开始的。人,由一只不起眼的“小蝌蚪”开启了漫漫生命之旅。麦亦然,生长也从微小的麦粒出发。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农民对气候的感知,敏锐而直接,我万分佩服。他们顺应四时节令,摸透了庄稼的脾气。母亲虽读书不多,但也算有几分灵气,通过劳动实践,亦学亦悟,掌握了许多关于气候、土地、种植的知识。比如:不能让麦苗超前拔节,否则冬天就会被冻死,但也不能太晚,否则麦苗出不了土或扎根不深,易造成幼苗死亡。她还知道,播种时,麦种之间要留足够宽的距离,麦苗出土后才有伸展胳膊腿脚的空间,规规矩矩,整齐划一,好看且好管理。
寒露过后,雨减露增,气温如高空坠落的石子,直线下降,这便进入播种小麦的最佳时节。
我家有块“飞地”在麦地坡,由于靠近山巅,是全村最陡的耕地,所以耕作极为艰难。我在边沟里目睹母亲挥锄挖地的样子,像是趴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她的姿势十分别扭,每向下挖一锄,就得向上倒推一锄,然后立刻把锄头翻转过来,用锄头箍砸碎较大的土块儿,以防土块儿乘机向坡下逃窜。挖完后,再用搂耙来回钩、推、蹚,尽量使泥土细密均匀。一些土坷垃很调皮,像被施了法,滚来滚去不变小。母亲便蹲下身子,用手将它们一坨一坨地捏碎捏细。整理完地后,她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像被胶水紧紧粘在了身上。
母亲身材并不高大,为了一家人的口粮,除了全心全意侍弄庄稼,别无他途。如今方才明白,母亲是在用肌肤与泥土亲近,是在用心与大地对话,以祈愿根正苗壮,以祈愿岁稔年丰。
地里准备就绪,就要备种了。母亲时刻关注着气温的变化,凭借经验卡播种的时间点。撒种前,麦种要经历“冰火两重天”,先温水“冲凉”,后冷水“泡澡”。待两三天后,母亲捞出一些种粒,捧在手里,凑近了仔细端详,判断是否适宜播种。原本干燥的麦粒,因为喝饱了水,皮肤变得圆润起来,饱满的小嘴唇,像要开口说话似的。她盯着看时,嘴角常常扬起,仿佛一弯新月,她像是捧着孩子,比拥着我时还温柔。
待时机成熟,就赶紧播种、覆土、浇头茬水,静待出芽。种子出芽后,开始向下扎根,向上出苗。母亲时常要到地里观察,掌握幼苗的生长状况,小心谨慎地呵护麦苗。
有年冬末春初,气温骤降,下了一场雪,我央求母亲带我去玩儿雪,母亲欣然答应。雪真大,漫天飞舞,目之所及,皆被白雪抢占了风头。菜园、竹林、山坡、麦地……万物皆被覆盖,大地如铺展的巨幅白绫。少不更事的我只顾贪玩儿好耍,看到几朵粉嫩的映山红从雪里冒出来,便急不可耐地跑去摘食,饶有兴致地咀嚼微甜带酸的花朵。母亲则缄默不语,眉头紧锁,目光聚焦在远山上被白雪覆盖的麦地,脸上露出忧郁的神情。我以为是我贪玩儿的行为引起母亲不悦,赶紧收敛,不敢继续造次。半晌,母亲紧蹙的眉头才慢慢松弛下来,她终于开口:“但愿天遂人愿,明年有个好收成。”
寒冬,漫長而严酷,是对万物的磨砺。跨越严寒,就是跨越生命中的塄坎,迎接凛冽寒风和刺骨冰雪的考验,是必经之路,绕不开,躲不过。那个年代,农民完全靠天吃饭,粮不入仓,心就发慌。每个突如其来的变故都可能会让母亲一季的辛劳付诸东流,将她的满心期望化为泡影。倒春寒,就是冬小麦的绝命杀手。俗话说“一场倒春寒,十麦九减产”,对于倒春寒,即使深谙农耕之道的老农也无法预知。一旦遭遇冻害,就可能减产甚至绝收。母亲含辛茹苦、安不忘虞,时刻为收成忧虑,但即使危机四伏,她也从未退缩。
三
春来回暖。麦苗经过一冬的历练,已大梦初醒。它开始返青,返青后继续分蘖,为拔节做准备。而我,依然青涩懵懂。
母亲对麦苗拔节有自己独特的术语,称为“起身”。至今我仍觉得这个词形象贴切,令人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场景:一位参加百米大赛的短跑选手,听到发令者的预备口令后,迅速提臀,身子前倾,眼睛注视着前方跑道,耳朵全神贯注地聆听“跑”字的发出。我仿佛听到麦苗携手拔节的呼喊,自己也长高了一截儿似的。麦苗不负众望,噌噌地疯长,拼命拔节,竭力孕穗,短短二三十天,叶、茎、穗齐头并进,能长到年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母亲喜形于色,形象地称这种现象为“抽条”。她对我说,等过几年,我也会像麦苗一样抽条,长得很高很高。可我不争气,只拔节到一米六五就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
拔节之时,稍微疏于防范,小麦就极易染上病虫害。诸如条锈病、纹枯病、白粉病、麦秆蝇、麦蜘蛛、叶蝉、黏虫、蚜虫等。蚜虫最常见,我家的稻麦、蔬菜等作物都曾感染过,因此记忆深刻。
那可恶的蚜虫,仅牙签头儿大,黑漆漆的,密密麻麻地附着在麦株上,黑压压一片如同千军万马,令人毛骨悚然。蚜虫的繁殖速度之快也让人咋舌,只要有一片叶子染上蚜虫病,很快会传染至全株,紧接着奔向下一株,直到整片地,再到另一片庄稼。如果清除不及时,它准能繁殖祖孙十八代。
母亲说,别看它个头儿小,危害却极大。它专门吸食麦株的汁液,导致麦叶卷缩,直到麦株枯死。母亲叫它“魇”,我叫它“吸血鬼”。它是麦株的梦魇,也是母親的噩梦。
一株麦苗的消亡,不像大树倾覆那么声势浩大,尽显悲壮,它往往悄无声息,不会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于母亲而言,麦株的死亡,更能令她在哀叹之余,产生对饥饿的恐慌。毕竟母亲是因家中无法养活,才被迫从云安镇过继到农村,以求一口保命的食物。可是,来到农村的母亲,依然没能摆脱食物匮乏的窘境。她饥饿难耐,必须得弄些东西往肚子里塞,以缓解腹空引发的身体疼痛。母亲讲,她吃过干红苕藤,吃过好多野菜,吃过又苦又涩的“黄棕米”(金黄色的棕树籽),吃过“观音米”(据说,吃之前还要跪拜观音,所以叫观音米,其实就是白沙泥)。她讲得泪眼婆娑,我听得阵阵心疼。万幸,她活了下来。因此,麦苗每生一片叶,每长一寸根,每结一支穗,无不牵挂着母亲的心,那是我们一家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
只有像母亲这样,经历过饥饿折磨,又曾亲手呵护种子长大的农民,才会真心为麦株的死亡而悲伤,才会真切感受到由此引发的潜在危机。
面对虫害,母亲表情凝重,但她极力克制,并不表现出焦虑和恐慌:“染病的不多,现在治还来得及。”她的语气中似有几分疏忽大意后的自责。
那时候,有杀蚜虫的农药——“六六粉”,但为了省钱,母亲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她把干烟叶和稻草灰混合在一起搅拌,加水浸泡,然后滤水喷洒在麦株上,效果出奇的好。没想到,这倒契合了后来的绿色生态理念,麦穗上不会残留农药。可是,虽然剿灭了可怕的蚜虫,那年麦子的收成依然缩了水。
天灾对庄稼的肆虐,如同风吹芦花般轻而易举。面对病虫害,庄稼同样显得弱不禁风,毫无抵抗力。它们仿若一块嫩豆腐,一捏就碎身糜躯,只能任由天灾和病虫蹂躏、吞噬。生命之脆弱有时让人难以置信,不亲身经历,永远都只会觉得那是遥远的故事。殊不知,船底一个小洞即可覆舟,千里之堤可能溃于小小的蚁穴,一只小虫足以令麦株终结生命。其实,当人被病魔缠身时,与庄稼如出一辙的脆弱,虽有这样那样的药物,但往往收效甚微,但那时候的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1989年,我刚进入初中,在学校惹是生非,结伙儿打架。母亲为劝诫我摒除恶习、远离行为不端之人而操碎了心。她用灭蚜虫的事教导我:“人养成不端的行为,就像麦株感染蚜虫,不及时治疗,麦株就枯了,就夭折了。”母亲的话好像只是说给我的耳朵听的,我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不思悔改。
那时,母亲已乳腺癌晚期。情况危急,父亲陪伴她赶赴北京治疗。除夕,母亲病中来电,由于刚做完放疗,她气息微弱,哽咽泪语:“儿啊,你……一定要……走正道。”母亲的话如麦芒刺进我心里,麦子和我都是母亲的收成,一个是生活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麦子的丰收给付出辛勤劳动的母亲带来满足,我给含辛茹苦养育我的母亲带来了什么呢?再不痛改前非,我还配做人吗?我在电话这头默默地听着,不禁泪潸潸、涕连连。那个除夕,孤单搅着担忧在我内心如麻交织,愧疚混着悔恨在我内心疯狂撕扯。最终,我幡然悔悟,迷途知返,清除了满身“蚜虫”。时过境迁,母亲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四
估计很多人没见过麦花。我庆幸在农村滚了几年泥凼,更庆幸有一位细心又懂种地的农民母亲。她像信使,引导我与麦花一次次如期相约。这也成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
二十四番花信风,每季各不同。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当熏风南来,遍地麦花始盛开。清明前后,小麦孕穗抽穗基本结束,便进入扬花时节。
此时,麦株亭亭,穗籽累累,碧叶郁郁葱葱,娉娉袅袅的样子,若豆蔻梢头,若出水芙蓉。麦地披着厚厚的绿,像大山脖子上的吊坠,像腰间的挂饰,真有“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的意境。麦地的闺女,长大了,该花上头了,该出嫁了,该灌浆了。
如果不是母亲阻止,顽皮的我,真要置身麦地,打几个滚儿,翻几个鹞子翻。如果不是母亲提醒,我也不会留意那些娇小的麦花。
麦花,实在太小,小得有些让人怜惜。我要以闻的姿势靠近它,方能一睹真容。它没有花瓣,没有萼片,仅有沙粒般大小的花蕊,依靠一根细细的花丝,附着在深绿色的颖壳上。它就这么不事张扬,像山村姑娘般羞怯、矜持。我用手轻轻一碰,麦花就粘在指头上,贴近鼻子嗅了嗅,一丝淡淡清香萦绕,缥缈而过。
麦花不仅小,而且开得急。
人们常以昙花一现形容时间之短,消失之快。然而,母亲说麦花开放多则半小时,短则仅仅三五分钟。
我问母亲:“麦花怎么不多开一会儿?”
“麦花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麦粒去生长。”母亲娓娓道来,“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麦花完成了授粉,麦穗才能长出丰实的麦粒。”
母亲的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有时,我会在麦地边呆呆地注视着麦穗,妄想研究麦花到底是如何授粉的。可我眼都望穿了,也没能够看清楚麦花是怎么绽开,怎么授粉,又怎么凋落的。只觉得一眨眼的工夫,麦穗上蓦地就多了一星黄,不经意间,又消失得了无痕迹,像一群神秘的仙子,来无影去无踪。若不是无数的麦花前赴后继地填补时间上的空隙,我可能无从知晓麦粒是从麦花开出来的。
麦花,看似开得潦潦草草,实则出落得清新脱俗。
麦花的歌颂者,古今不乏。诸如:“顿回茧馆柔桑绿,渐落峒山细麦花”(李洪),“永日屋头槐影暗,微风扇里麦花香”(范成大),“岚气回环映水光,麦花吐秀菜花黄”(李荣树)。但凡以上种种,不外乎歌颂麦花其形色味之美。然麦花之美,并非仅限于此。因它结构不完整,只保留了遗传繁衍的功能,在植物学的概念里,麦花属于“不完全花”,我甚至不忍称它为“花”,似乎应该叫“蕊”才恰当。麦花无意来世间秀姿色之美。它的美,在于用短暂的绽放赢得麦株长满穗、灌饱浆、丰满籽的结果,喘息之间就功德圆满。
记得清人袁枚有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倒觉得,麦花虽更小,不须学牡丹。我就是我,别样的焰火,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干吗要学牡丹呢?做自己不好吗?幸好麦花没有学牡丹,一味地只顾自己开得惊艳,还在枝头久久炫耀。倘若营养全被花占了去,如何能长出饱满又丰实的麦粒呢?
风,赶趟儿似的,带着些许薄凉,一股股奔跑過山野,掠过麦地。也就十日左右,整块儿地里的麦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麦花小而求实,且不谋名利,不慕虚荣,不求美色,多寄营养予麦粒;落入尘埃,也不卑微;收获的麦粒,终将馨香如故,胜于一切虚无的美。
母亲,恰如麦花,在时间轴上,不舍分秒,车轱辘转。她的身影,时而在家里闪现,时而在地里忙碌。她一生素位而行、衣褐怀宝。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朵微小的麦花。也许,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宿命。
五
小满小满,麦粒已满。
布谷声起云雀和,一夜之间麦子熟。难怪人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
麦穗,一串串,沉甸甸,金黄金黄的,鼓鼓囊囊的。
风从山谷一路歌吟至山顶,麦穗随风起伏,摇曳多姿。熬过太多辛劳,终于盼来“小满哥”,终于可以放荡地浪一波。层层麦穗在浪,片片树木在浪,群山也一起浪。母亲嘴角的新月又升起来了,像煮熟的菱角,我闻到了麦子清甜的香气,可要吃到嘴里,不知要耗费母亲多少的汗水。
收割麦子,总是在骄阳似火、烈焰炙烤的日子里。
“大太阳就是好天气。”母亲说,“麦子淋不得雨,会发霉,得与时间抢。”母亲嘴里的一个“抢”字,就是一场为了填饱肚子的战役——抢收、抢晒、抢储。
母亲头戴草帽,顶着炎炎烈日,俯身弓腰,挥舞着早已磨得锋利的镰刀,与太阳斗,与大地斗,与雨抢,与夜抢。钢铁的锋芒,飞速啃啮空心的麦秸秆,如同按弦取音,弹奏出丰收之乐,喜庆,欢腾。她左手拤麦,右手执稻草,环绕麦秸秆一周,拇指和食指捏住稻草的两头,快速旋转几圈,扭成结,然后食指略略勾起,使稻草绳露出一丝缝隙,同时拇指一顶,将稻草末端回头嵌入缝隙,这样就扎成了一把。十把再扎成一捆,一气呵成,动作十分娴熟。
我在地里捡拾掉队的麦穗,不忍母亲太过辛劳,便突发奇想:“妈妈,怎么不把镰刀把子做得长点儿?那样就不用弯腰了。”
母亲又扬起嘴角的新月,指着满地弯着腰、低着头的麦穗说:“幺儿,你看,成熟的麦穗多谦虚。我们要靠它养活,也得弯
下腰。”
背麦回家,背的是希望,累并快乐着。母亲头顶一张长方形蓝印花的枕巾,很乡土,却很智慧,可阻挡麦芒尖刺的侵袭。她把麦穗码叠在背篼上,系紧,套牢。母亲熟知省力技巧,把背篼搁在半人高的坎上,便于起步。即使如此,我也必须得上前搭把手,她才能双手撑住膝盖,吃力地站起来。五捆麦穗,很高,很重,像一座小山压在母亲瘦弱的身躯上。从背后看,她的腰极度弯曲,上半身几乎与大地平行,看不见头,只有蓝印花枕巾的角垂落下来,格外显眼。我拎着水壶,有时候刻意走在前面,想用我更矮小的身体给母亲指路。因为,路上的危险无处不在,路边有石坎,有悬崖,笔直得令人胆寒。有的路段太窄,我怕过不去,就会伸出手比一比,大声喊:“得行!得行!”母亲从不应答,她只顾专注地稳住背篼,一旦倾倒,非死即伤。我不时地回头望,只见母亲脚上那两只泛黄的解放鞋,正在艰难地向前交替移动,路上的泥土显露出被汗水浸湿的痕迹,一大滴一大滴,忽左忽右,跟着母亲的脚步,走了一趟又一趟。那么清晰,那么扎眼。
接下来,母亲还要继续完成几道工序:翻晒麦穗——用连耞打麦脱粒——用风谷车过滤草屑、瘪粒——翻晒麦粒——直到麦粒干了水分,再收装入仓。那段时间,她忙里忙外,累得骨头都快要散架了,就像那些被我拆烂的玩具。她浑身疼得夜里睡不安稳,白天就栖栖遑遑的。麦子的丰收,给家里带来不尽的喜悦。母亲的艰辛却给自己的健康埋下了无法消除的隐患。
1993年的麦收时节,麦穗再次披上了永不褪色的“黄金衣”,而母亲的钢铁镰刀,早已锈迹斑斑,孤独地挂在墙上好几年了。母亲临终前,癌细胞已扩散至大脑,连续昏迷了几天,没能留下只言片语。我一手紧紧地攥着她的手,粗糙、皲裂、沁凉;一手擦去她眼角涌出的泪,泪水滚烫,像麦芒扎在我手上,也扎在我心上。我明白,她有割舍不下的千愁万绪,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病魔吞噬掉她最后一点儿呼吸的力量而无能为力。母亲没能越过自己生命的严冬,像一朵麦花,匆匆盛开,又匆匆凋落。
现在回想,母亲弯腰捏土、割麦、背麦的姿势,多么谦逊,足以表达她对大地和麦子的至臻礼遇。那条长方形蓝印花枕巾,历历在目,多么素美!
当我在记忆的流光里,剪辑下一段过往,藏匿在表情之间,断裂的细碎动作,以及画面背后听不见的声音,像剥茧抽丝一样,一点点儿被抽拔出来。这些瞬间,隐隐夹杂着丝丝疼痛,我却难以弃舍。它们悄然鞭策着我,给我面对浇漓现实的底气,给我昂首面向未卜前路的勇气。
每过麦地,目睹躬身割麦的妇女,我总觉得恰似母亲的身影。每每此时,我就感到自己是一粒种子,与麦一同黄熟,也终将被锋利的时光之镰收割。
责任编辑 刘淑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