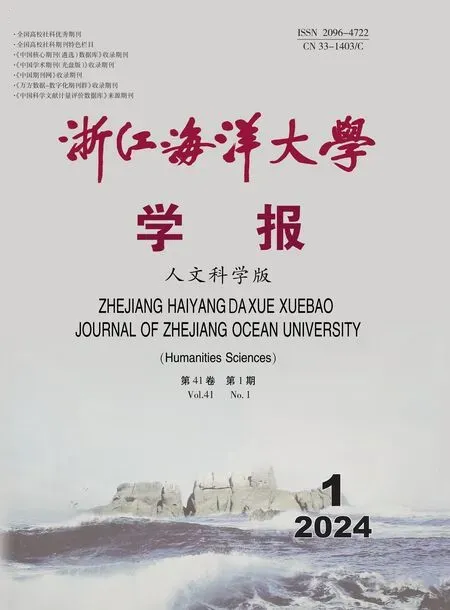从禅史编纂学意识看今本《祖堂集》的编定
徐 丹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丝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 362000)
《祖堂集》是最早在南唐保大十年(952)于泉州招庆寺编成的一部禅宗灯录,比《景德传灯录》的编定早了约五十年。最初的编者是被称为“静、筠二禅德”的两位招庆寺僧人,但具体生平不详。其书编成后不久便在中国散佚,目前保存在韩国海印寺的印板是现在所有《祖堂集》的祖本。这个版本(简称为“今本”)的正文分为二十卷,记载了禅宗自西天七佛以下至五代宋初总计246 位僧(佛)的语录、事迹,另外在卷首有署名为文僜、匡儁的两位僧人分别撰写的序。
自20 世纪初今本《祖堂集》被重新发现以来,许多学者从文献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个角度对这部书作了研究。在与本文关系密切的文献学方面,柳田圣山[1-2]最早对这部书作了系统的探讨,此后石井修道[3]、衣川贤次[4-6]等人又有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祖堂集》的研究,特别在语言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丰富,[7-8]并出现了几部质量上乘的校订本。[9-10]在西语学界也有值得关注的成果,如Paul Demi ville[11]、Christoph Anderl[12]、Laurent van Cutsem[13]等人的论著。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海印寺本的《祖堂集》并非该书最初编成时的原貌,因此厘清它的编定过程就成为研究该书的基础课题。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界一般都认可衣川贤次等人的看法,即认为《祖堂集》最初的版本只有一卷,后来经过扩充,最终在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由高丽僧人匡儁“写定”为二十卷并付梓刊行(其成果就是海印寺所藏的印板)。[14-16]这一看法的关键依据,是高丽僧人匡儁为该书所写的序言,其中提到:“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尔后十卷齐到。谨依具本,爰欲新开印版,广施流传,分为二十卷。”[9]1
笔者认为,前人的看法是对匡儁序言的误读。匡儁确实曾经将《祖堂集》分编二十卷,但他并不是高丽高宗时期的人物,其序言的写成时间也远早于今本《祖堂集》印板的开雕时间。下文将从禅史编纂学的视角出发,分两个方面对上述看法加以论证:一是从高丽后期佛书序跋与政治环境的关系,论证匡儁序言不可能写于高宗三十二年;二是从“灯录”这种题材形成发展的禅史编纂意识出发,论证匡儁序言应该写于《景德传灯录》进入朝鲜半岛之前。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了今本《祖堂集》成书的四阶段论。
一、 “匡儁序”与海印寺《祖堂集》板的开雕
今本《祖堂集》的印板确实是高丽高宗三十二年(或稍后)开雕的。它的第一卷末尾有“乙巳岁分司大藏都监雕造”一行字。所谓“乙巳岁”就是高丽高宗三十二年,当时高丽王朝为雕造《大藏经》而设立了大藏都监、分司大藏都监等机构。《祖堂集》虽然是藏外佛书,但无疑也是由分司大藏都监负责雕版的。[14]934-953因为“乙巳”年题记只存在于第一卷末尾,不排除后续各卷的雕版时间要更晚一些。
但是,匡儁分编二十卷的活动,与今本印板的开雕并无直接关联。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厘清匡儁序的写作时间。这里先节录序言如下:
1.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尔后十卷齐到。谨依具本,爰欲新开印版,广施流传,分为二十卷。以此先写七佛,次艐天竺二十七祖并诸震旦六代,代有傍正。祖位次第,并以录上。
2.随其血脉,初后联绵,佋穆之仪,有孙有嫡也。其纂成,所以群英散说,周览于眼前;诸圣异言,获瞻于卷内。
3.今以沙门释匡儁所冀:中华集者,永祛惜法之痕;此界微曹,愿学弘禅之美。
4.……(中间僧佛名录省略)……海东新开印版《祖堂集》,现其本迹者二百五十三员,并载于
二十卷内;莫知迹者,不能具录矣。[9]1-9
可能是受了文中“新开印版”这一说法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匡儁序就是为高丽“乙巳岁”这一次雕刻所写的。[10-16]然而,序言本身并没有直接的时间线索,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排除“新开印版”是另一次刊印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并没有得到任何确切证据的支持。
其实,细考匡儁序的文本,会发现它对《祖堂集》的历史定位与“乙巳年”高丽的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社会背景格格不入。从宗教背景的角度看,根据前引序言第3 段,匡儁之所以编定、刊行《祖堂集》,是希望它能充当禅宗东传的锁钥。如果禅宗能够藉由这部书的流通而从中华传到高丽,则一方面编纂这部书的中国僧人将禅法普惠东国之人,因此摆脱了自身“惜法”不传的嫌疑(“中华集者,永祛惜法之痕”),另一方面高丽的禅宗弟子们也愿意效法大德,致力于弘扬禅法的美事(“此界微曹,愿学弘禅之美”)。
问题是,在“乙巳岁”高丽雕刊《大藏经》时,禅宗已是高丽佛教的强势宗派。早从新罗末期,传统佛教各宗派即走向衰落,而新兴的禅宗逐渐发展,[17]34-35先是在高丽前期形成盛极一时的“禅门九山”,然后又由僧人知讷开创出朝鲜半岛特有的禅宗派别曹溪宗。[18]14-22913 世纪初,曹溪山修禅社第二代主持僧慧湛运用《景德传灯录》等资料编成《禅门拈颂集》一书,“采集古话凡一千一百二十五则并诸师拈颂等”;在贞祐十四年(1226)为该书所写序中,慧湛声称“本朝自祖圣会三巳后,以禅道延国祚,智论镇邻兵”。[19]可见高丽禅宗经过数百年发展之后已颇有自觉与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象一个有学养的僧人会把《祖堂集》的印行看成禅宗东传的锁钥,并赋予它“永祛惜法之痕”“愿学弘禅之美”的意义。
从政治背景的角度看,匡儁的序言还缺少了乙巳年高丽官刊佛书背后的政治紧张感。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后,蒙古军队开始向外扩张。从1218 年开始蒙古军队连年入侵高丽,并迫使高丽朝廷在高宗十九年(1232)从旧都开城迁到江华岛上,以避蒙古军锋芒。高丽显宗二年(1011)为抵御契丹入侵而发愿刊刻被高丽君臣视为国宝的《大藏经》板也被蒙古军队焚毁。在王朝生命悬于一线的紧张时刻,高丽君臣为了祈求佛祖保佑、祛退蒙古入寇,“借神通之力,使顽戎丑俗,敛踪远遁”[20],决定重新雕刻《大藏经》,并为此专门设立大藏都监、分司大藏都监。[17]149
很显然,重刻《大藏经》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一项政治行动。这在同时期分司大藏都监刊刻的其他佛书序言中有非常清楚的体现。高宗三十五年(1248)刊刻的《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事实》后有“按行卞韩道兼大藏分司”的高丽官员全光宰所作跋文:
予素信内典……岁戊申(1248),按行卞韩道兼任大藏分司……募工笔而书之,简善手而镌之。所冀我晋阳公寿增岳峙、福(畜)[蓄]渊深,塞消狼大,天扫搀枪。……庆尚晋安东道按察副使都官郎中全光宰志。[21]59
文中的“蒙寇”“狼大”指的都是入侵高丽的蒙古军队,“晋阳公”则是高丽朝廷中主持抗蒙军事行动的权臣崔怡。[22]388-393另外一部高宗三十一年刊刻的《金刚三昧经论》后有高丽人郑晏所作跋文,里面提到“氛尘永寝,朝野升平”[21]139,同样是在祈求蒙古退兵。①
分司大藏都监刊刻《祖堂集》的行为本身无疑是高丽朝廷“以佛法驱敌寇”的政治行动的一部分,但匡儁所写的序言不仅对当时高丽万分危急的政治局势丝毫无感,而且给《祖堂集》赋予了与时代不相契合的禅史意义,完全没有体现今本《祖堂集》刊刻时的历史语境。其实梁天锡已经提到,不应该把匡儁序与高丽高宗三十二年的《祖堂集》刊刻活动联系起来,[23]只可惜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其观点也未能引起重视。
二、 “匡儁序”的写成时间
如果匡儁序不是写于高宗三十二年(1245),那么它又写于什么时候?从序言透露出的禅史编纂意识来看,它应该写于“灯录”这种禅宗史书传入朝鲜半岛的初期。匡儁序言的第2 段是作者对《祖堂集》的编纂特点的概括。其中,“随其血脉,初后联绵,佋穆之仪,有孙有嫡”强调的是体裁上效法血缘家谱的特点,不仅用“血脉”一词来指称禅僧的师徒相继,而且将僧人的传承关系拟称为宗法制下区别父子、嫡庶的“昭穆之仪”。“群英散说,周览于眼前;诸圣异言,获瞻于卷内”则强调其内容具有集大成的意义。简洁地说,就是明辨谱系、集成语录这两大功能。
这样的评价,实际上与南唐泉州招庆寺僧文僜为《祖堂集》所写的序言相互呼应。根据文僜的说法,禅宗本来不立文字,但因为“中下品流”的人只能借助“机句”悟道,所以不得已而留下“半偈一言”。在文僜写序之时,禅宗大德的语录已经广为流传(“言教甚布于寰海”),但没有人按师承关系将之梳理清楚(“条贯未位于师承”),使他常有“乌马难(辩)[辨]”之虑。新编成的《祖堂集》“珠玉联环,卷舒浩瀚”,弥补了文僜的这个遗憾。[9]1虽然文僜的评价比较含蓄,但细究其“问题意识”,可以说他看重该书的也就是明辨谱系、集成语录这两点。
文僜的问题意识体现了禅宗在五代宋初日渐枝繁叶茂而带来的禅史编纂的新要求,这也正是《景德传灯录》所要解决的问题。宋景德元年(1004),“东吴”僧人道原将所编的一部禅宗史书献给宋真宗,经校定之后,由朝廷下诏收入藏经。该书初名《佛祖同参集》,被进呈给皇帝之后乃获敕定书名《景德传灯录》。[24]从道原献书的时间即可看出,它体现的正是宋代初年禅宗知识界对本宗传法历史的一种认识。[25]宋真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杨亿曾经为《佛祖同参集》作序,对该书编纂的宗旨、特点有非常精当的评价。据其所说,道原编书的目的,一是有感于当时“祖师法裔,颇论次之未详”,发愿加以厘清;二是要接续唐代僧人圭峰宗密的《禅源诸诠集》的宗旨,以编集禅僧的语录。而这部书的突出成就也正是两点:一是谱系详明,“自饮光尊者,讫法眼之嗣,因枝振叶,寻波讨源”;二是语录收集完备,“语句之对酬,机缘之契合,靡不包举,无所漏脱”。[26]
在这里,杨亿对道原《佛祖同参集》的评价与文僜、匡儁对《祖堂集》的评价如出一辙,这无疑说明在五代宋初禅宗日益枝繁叶茂的情况下,禅林知识之中存在某种共通的禅史编纂学的创新意识,这种意识推动了后来被称为“灯录”的这样一种兼有明辨谱系、集成语录这两大功能的新禅史体裁的成熟,《祖堂集》和《佛祖同参集》都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杨亿作序时应该没有看到《祖堂集》,否则他不至于将道原书的渊源追溯到一部当时已经散佚的唐代书籍。杨亿《佛祖同参集序》中已经明言,当时《禅源诸诠集》的“百卷之文不传于世”,留下的只有被称为“都序”的一小部分总序类文字。事实上,宗密《禅源诸诠集》旨在融通禅教,“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27],在撰写目的和体裁上都和“灯录”这种专在阐扬禅风的史书有根本不同。但正因如此,扬亿、文僜的两篇独立写成的序言更加体现出当时禅林知识界共通的禅史编纂学意识。
匡儁序对《祖堂集》的评价很高,几乎认为它是“当代”禅宗法脉、法音的集大成。这说明,匡儁写序时并不知道有《景德传灯录》一书。因为《景德传灯录》的篇幅达到了《祖堂集》的两倍,收录的人物范围也远远超过了《祖堂集》。笔者未能查到《景德传灯录》初传高丽的确切时间,但最晚于12 世纪已广泛流行开来,[28]高丽普照国师知讷写于明昌元年(1190)的《劝修定慧结社文》已经多次援引《景德传灯录》,[29]慧湛于13世纪初以《景德传灯录》为基础资料之一编成《禅门拈颂集》。[30]这些都远早于今本《祖堂集》的刊刻。
其实,从匡儁序中“中华集者,永祛惜法之痕;此界微曹,愿学弘禅之美”这两句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应该是在禅宗传入朝鲜半岛不久的语境下写成的,此时高丽人是否“愿学”禅宗还是一个问题。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匡儁序的内容才具有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匡儁序的写成时间应该在10 世纪后期到11 世纪中期,晚到12 世纪之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不可能写于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今本《祖堂集》开板刊刻之时。
三、今本《祖堂集》的成书过程
衣川贤次论证了今本《祖堂集》二十卷本编定的三个阶段。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是《祖堂集》一卷本,由名叫“静、筠”的两位僧人,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在泉州招庆寺编成;第二阶段是增广的十卷本,“何时期成立也不可知”;第三阶段是高丽高宗32 年“写定”的二十卷本。[14]944-949但上文已经指出,匡儁序应该写在《景德传灯录》流行于高丽以前,时间上远远早于今本《祖堂集》的刊刻,序中提到的“新开印版”指的应该是更早前的刊刻活动。因此,今本《祖堂集》的成书不是三个阶段,而是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南唐保大十年成书的一卷本,内容大致相当于今本《祖堂集》的前两卷,记载西天七佛、禅门三十三祖(包括西天二十七祖和东土六祖)事迹。[4]今本《祖堂集》文僜序就是为这个最初的一卷本而写。这部分的内容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显示其最初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编纂的。一是在第一卷、第二卷多次提到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岁”或“今壬子岁”的说法。二是它的资料运用如频繁引用《宝林传》、诸多佛经等,与后续章节不同。[23]有研究者提出《祖堂集》最初的一卷本可能还包括六祖慧能以后的禅僧。[31]因为《宝林传》本身就记载了六祖慧能的几位弟子和再传弟子,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证实。
第二阶段是南唐保大十年之后不久完成的十卷本。匡儁序说一卷本“先行此土(按:即高丽)”,然后“十卷齐到”。从这个语气来看,十卷本也是先在中国编成,然后才被带到高丽。关于十卷本编成的时间,《祖堂集》本文没有明确交代。检索全书提到的年代信息,时间最晚的除了今本第一、二卷提到的“保大十年壬子”之外,就是南唐保大九年辛亥(951),可见于今本《祖堂集》卷十二荷玉、禾山、光睦、氻潭、龙光等章。[9]543-571另外,《祖堂集》立传的禅师总计246 人,其中卒年最晚的是福先招庆省僜和尚,去世于开宝五年(972)。[14]946但《祖堂集》只记载省僜在招庆寺开堂,没有提到他的迁化以及谥号等。因此《祖堂集》十卷本应该也是在保大十年或稍后不久的时间内编成的。
第三阶段是二十卷本的初刻,即高丽释匡儁以从中国传来的十卷本为基础,重新分编为二十卷并付梓。刊刻时间与匡儁序的撰写时间大体相当,即在10 世纪后期到12 世纪前期之间。匡儁序把“齐到”的十卷本称为“具本”,也就是全本、完整的本子,说明他在分编时没有对原本内容作大的增补。梁天锡认为该书内容“十之九”为匡儁补编。[32]考虑到《祖堂集》频繁使用许多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闽浙地区的方言,相关文本只能在中国形成,[33-34]因此匡儁作大幅增补的说法难以成立。
和《景德传灯录》相比,《祖堂集》的一大特色是对一批新罗禅史的记载特别详细。有些学者认为,这部分是匡儁增补的;[34-35]但也有反对的意见。[36]可以确定的是,东国禅师各章并不完全是东国文献,至少有一部分文本是在中国形成的。特别是“梵日”章收录了梵日与齐安、药山的问答各一段,里面使用了记载中国南方口语的俗语文,如“什摩处来”“争得到这里”“作摩生寻”等。[9]756-757这两段文字无疑是在中国写成的。
第四阶段就是二十卷本的重刻,其成果就是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乙巳岁分司大藏都监雕造”,现在收藏在韩国海印寺的《祖堂集》印板。前人对这个版本的研究很多,最早是池内宏对与之直接相关的高丽《八万大藏经》的版本情况做了考证,[37-38]此后柳田圣山、衣川贤次等人都有深入探讨。在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学方面,前面引用的van Cutsem, Laurent、Christoph Anderl、梁天锡等人,以及陈耀东等[39]都有相关研究,这里不再详细转引。
今本《祖堂集》书前的“匡儁序”并不是在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高丽“分司大藏都监”开板时写成的。虽然现在无法考证确切时间,但匡儁序的文本明显符合禅宗传入高丽不久的历史语境,并且呈现出“灯录”这种禅宗史书体裁成熟早期的禅史编纂学意识。由此笔者大致可以推测,匡儁序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公元10世纪下半叶到11 世纪,最晚到12 世纪前期,而不可能写于《景德传灯录》等书已经广泛流通的13 世纪。这意味着,今本《祖堂集》的形成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在南唐保大十年(952)的泉州编成了最初的一卷本,稍后不久又在中国编成了完整十卷本,随后有高丽僧人匡儁将十卷本重新分编为二十卷并开板印行,最后则是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分司大藏都监重刻的二十卷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能支持匡儁曾经对《祖堂集》内容作大幅增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