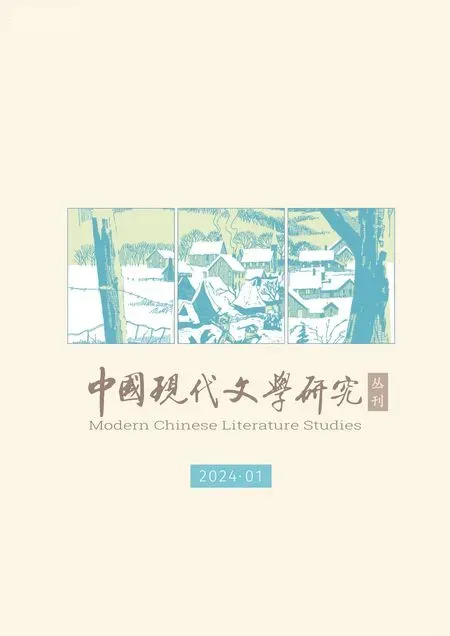勘探文体的跨文化游踪
——读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
白新宇
内容提要:张丽华新著《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以晚清民国时期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与文学创作为主线,勘探文体在跨语际旅行中的新变,打开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多重可能。文体作为文学文本与社会语境的中介因素,是形式诗学通往文化诗学的桥梁,作者对勘译作与原文,重新体认译者经验过的二者之间的语言摩擦,辅以历史的想象力,洞察表面上孤立的文学现象的内在关联,对文学史上因循的成见多有辨正。《文体协商》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向世界文学充分敞开的中国文学重构传统,锻造表达现代情感与思想的书写语言,以新的主体姿态汇入世界文学的协商对话之中。
长期以来,“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并非焦点话题,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文章的述学文体方面,不同于古典文学深厚的文体明辨传统,现代文学受到西方十八世纪以降兴起的文学观念影响,大量实用性文体被摒弃在纯文学畛域之外。文体被简单化地理解为文学内部的形式特征,一种讲授文学概论课程时便于分门别类的工具,遑论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彼此矛盾重叠,或与“文类”概念相混淆。这一局面说明现代文学文体研究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与阅读技艺要求甚高,新一代研究者需努力寻找打开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空间的钥匙。张丽华的新著《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收入作者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在晚清民国时期广义的跨文化翻译实践中重新勘探文体的游踪,激活现代文学研究中文体问题丰富的可能性,其宽广的理论视野、丝丝入扣的论述以及上下四旁牵引勾连的研究方法,值得细心体味咀嚼。
张丽华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的首部学术著作《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选择“短篇小说”这一文类,考察其文类形构的历史过程,探析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整体性文学图景不同的文学变革方式,将文类理解为历史性的交流模式或交流现象,联结文学文本与社会制度的概念。1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对象本身所包孕的丰富性导致单一的文类视角不足以发覆其内蕴,因此作者决定在新著中重新启用古典文论中的“文体”概念。从“文类”到“文体”的变化,内在地呈现出作者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的自我调整:西方的文体(style)研究旨在探索作者个体对表达方式的选择,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体”指向规范性的文章体制,作者所使用的“文体”概念更具有弹性与包容度,综括中西两种对文体的理解模式,即包含文类、语言、修辞、人物话语的表达形式等诸范畴在内的文学结构与话语类型2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01、22页。,开放而融通的文体概念为作者紧贴研究对象的考察提供方便。然而从“文类”到“文体”,作者贯穿始终的研究旨趣在于寻找介于文本与社会语境中间的变量(分析单位),这种将历史化分析内置于形式分析的追求,既能展现系统性制度因素如何自然渗入文学,又可透视微观的文学结构如何表征特定的社会文化意涵。
“文体协商”的提出受到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莫莱蒂(Franco Moretti)“形式妥协”的启发,指的是文体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后,与本土习俗风尚、制度轨范碰撞后产生的变异与创造。3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01、22页。在莫莱蒂看来,世界文学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他关注处于边缘文学系统中外来形式、本土内容、本土形式三者的“妥协”。1弗兰科·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猜想》,诗怡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协商”(negotiate)相较于“妥协”(compromise),和缓了外来与本土形式之间紧张的权力关系,以更加从容的主体姿态审视古今中西之间文体的跨文化游踪。作者尽管希望在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但其精彩的个案研究恰恰证明民族文学的文体成规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文体不可避免的改造,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反而凸显民族文学文体轨范的某种不可通约性。作者在第二章分析晚清民初与《域外小说集》中的三部短篇小说同源异译的文本时,发现与周氏兄弟的译文相比,三位译者翻译时皆不同程度调用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演义”传统资源,以适应国内读者的受容能力。吴梼据日译本“重演”显克微支《灯台卒》,其直线的时间叙事框架冲淡原作中高潮的力量,增添说书人的“声口”削弱小说的异质性;刘半农译安德烈耶夫《沉默》将阴森压抑的心理象征主义小说改造为通俗的“哀情小说”;周瘦鹃译哀禾《先驱者》较原作多所夸饰,其呈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修辞效果与演义小说并无差异,三个翻译案例显示出演义传统强大的生命力。第六章中对自由间接引语的分析则更为显豁地体现出中西文体的异质性,由于汉语中没有时态变化,经常省略人称代词或主语,叙述人物内心世界的自由间接引语很难在汉语中被原样翻译出来,作者对勘曼斯菲尔德小说AnIdealFamily与徐志摩译文《一个理想的家庭》的分析,展现出徐志摩只能通过增加语词等语义手段,翻译原著凭借语法手段达到的叙述效果。
第三章“无声的‘口语’”关注周作人早期从文言到白话的翻译文本,透视周作人理想的白话文之创生历程,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这一部分是在木山英雄与王风研究基础上的深入与推进,极具启发性。周氏兄弟留日时期深受章太炎影响,崇尚复古,晚清至五四时期,无论是写论说文章还是翻译域外小说,皆出之以文言,复古的态度如何转向文学革命的激烈主张,断裂性的文学史叙述遮蔽了内在的连续性。木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作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具体考察周氏兄弟与章太炎的思想关联,指出周氏兄弟留日时期使用古字,以文言翻译西方近代文学,在原文与译文的艰苦摩擦中形成自身内部的文体感觉,这里的“文言”亦非与白话相对的陈腐文字,而是精神卓特之士的语言表征。1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38页。木山的文章,多引而未发之处,三十余年后,王风通过分析周氏兄弟晚清民初文言文本的书写形式,即分段与标点符号的运用,揭示二人在新文化运动前已然锻造出一种“欧化”的文言,将西文章法“对译”到汉语文本,在书写系统内部,周氏兄弟的文言实践于文学革命时期被“直译”为白话,构成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主要源头。2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119~169 页。维柯认为“凡是学说(或教义)都必须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开始时开始”3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8页。,王风的研究从周氏兄弟现存最早的文章与翻译入手,找到翻译的原文,相互对勘,这相当于研究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9页。,重新体会研究对象翻译时所经验的语言摩擦,如此方能无限趋近“真了解”。近年来,宋声泉、周旻对周作人早期译作《侠女奴》《玉虫缘》《荒矶》的分析亦处于这一研究谱系。
张丽华独具匠心选择周作人1917年翻译的《古诗今译》——Theocritus牧歌作为核心文本,《古诗今译》翻译语体由文言转为白话,在周氏的翻译胜业中具有原点意义。作者循着周作人的译诗脉络对读译作与原作,发现周作人译诗的策略从依靠传统诗词曲文体成规逐渐转变为无所因循的散文体,在此过程中,熟滥的文体格套逐渐委蜕,生成的是一种新鲜而素朴的白话文体,这是汉语言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创格。这种白话文体摆脱汉语言文体轨范的同时,亦不再为原文文体风格的流失而焦虑。吴汝纶致严复的信中谈到翻译泰西文籍宜取法六朝译经,“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5吴汝纶:《答严幼陵》丁酉二月七日,《吴汝纶尺牍》,徐寿凯、施培毅校点,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99页。,周作人的译诗实践真正将此理想落到实处。作者将周作人所使用的“直致的白话文”与新文化同人互歧的白话想象做对比,认为胡适白话译诗未脱旧诗窠臼,钱玄同更加激进地追求文学书写与当下之“言”的一致性,周作人则将文学改革的思路限定在“文”的畛域内,译诗采用的“口语”是摆脱任何“今音”限制的书写语言。6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第71页。笔者此前在研读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时,发现周作人在编译Theodore W. Hunt的《文学的原理与问题》(Literature,ItsPrinciplesand Problems)过程中潜在批评了章太炎的泛文学观,但章太炎坚持区分“口说”与“文辞”,认为“策士飞箝之辩”与“宋儒语录,近人演说”全部“与文学殊途”1章氏学(章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9月2日。,实则对周作人影响深远。阅读张丽华对周作人介入文学革命所使用的白话语言的精妙分析,笔者对章太炎与周作人的深刻联系亦有进一步的认知。鲁迅为追求译文保留“原作的丰姿”,“宁可译得不顺口”2鲁迅:《“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65页。,其白话文写作始终追求“言”的及物性,主张“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3鲁迅:《人生识字糊涂始》,《鲁迅全集》第6卷,第306~307页。;周作人坚持在“文”的畛域内耕种自己的园地,特别是在对民间口语的浪漫想象消散后,我们很难找到周作人攻击文言的话。在周作人这里,“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4周作人:《国语文学谈》,《京报副刊》第394号,1926 年1月24日。,建设理想的国语文学亦不妨引入文言、方言、外来语以增强现代国语的活力。周作人的散文写作正是其理想的国语文学的创作实绩,所谓“文言”亦即“文章的言语”5药堂(周作人):《古文谈》,《华光》第1卷第4期,1939年10月28日。,在如此通透的文体观念基础上拆解文白对立,文章中文言分子的增加不能被理解为思想层面的消沉与落伍,这恰是更为开放而包容的态度,“文言”删汰基于音乐性的滥调,无妨清明思想的表达。本书第八章讨论的融合中国诗歌抒情手法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废名小说文体,以及小说语言的“不及物性”所带来的趣味6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第213页。,也唯有在周作人的语言观、文体观的延长线上才能得到呵护与欣赏,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文学的文体探索而引发的争议,周作人同样不遗余力地回护所谓“看不懂”的新文艺。第三章结尾部分由周作人翻译文体自然过渡到散文写作的文体意识,将“言”引申为翻译中的“原作”与文学表达中的情志或自我,“文”无以与“言”合一,“译作”无以及“原作”,“文章”无以完全表达“自我”,三者同构而异名,标识“文”所能抵达的限度。
从研究思路来看,本书第五章与第三章一脉相承。通过细致梳理1921年群益版《域外小说集》诞生前后的语境,对勘其与1909年东京版的差异,作者指出《域外小说集》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的时代氛围中被塑造为与林纾、严复译作对立的“直译”典范,是人为构造的历史叙述,是为争得新文学合法性的“发明”,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在作者看来,以林译小说在晚清的影响力而言,周作人一直处于其“影响的焦虑”中。作者的研究解构了稳固的文学史论断,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周氏兄弟文言翻译与林译小说的关系。
据周作人回忆,兄弟二人早年对于林纾的译作“随出随买”,直到1909年出版的科南达利《黑太子南征录》为止,购读的林译小说“大约有二三十种”1知堂(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第30期,1936年12月1日。。然而从阅读感受而言,《域外小说集》的确与林译小说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固然由于二者有长篇短制之异,但周氏兄弟翻译策略、文体想象与林纾的不同亦为重要原因,作者的结论还可再做辨析。首先,据崔文东的考察,《域外小说集》的编译主要出自鲁迅的构想2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 年第 6 期。,尽管鲁迅仅翻译三篇小说,但这三篇语言最为古奥。作者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第三章“文类如何翻译?”中将《默》与德译本对勘,发现鲁迅不惜破坏汉文习惯以贴近原文3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134页。,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相比更具弹性,常拆碎原文语序而达意,但其属词工切而雅正,其语言之古奥与朴讷均超过林译,这一点在翻译《红星佚史》时即有所体现。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明显受到林译哈葛德小说影响,翻译《匈奴奇士录》《劲草》则深受林译司各特历史小说影响,即便如此,张治发现翻译《红星佚史》时周氏兄弟便有使用古字的苗头。4张治:《〈红星佚史〉与〈金梭神女再生缘〉》,《蜗耕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红星佚史》中的歌曲基本由鲁迅以骚体翻译,而此书的林纾译本不但大量诗歌略去不译,仅存的三首译诗(见《金梭神女再生缘》上册第5页弓之歌;第19页奥德修斯之歌;下册第79页勒尸多列庚蛮族之歌)亦简单粗糙,如Laestrygon战歌周作人译成杂言体歌谣,虽不拘原诗语序,但基本完整译出原诗语义,林纾则译为五言古诗5“彼此皆同乡,汝乃以盗猖。吾军自远来,扫尔如稗糠。所向匪不克,锋锐谁能当。”参见哈葛得《金梭神女再生缘》下册,林纾、陈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79页。,归化程度更强,与原作差异较大。翻译过程中周作人下功夫研究古希腊神话,增添注释,这些行为均违逆晚清翻译文学所遵循的商业规律。其次,周氏兄弟与林纾翻译时的文体想象不同。阅读林译小说,偶见难懂的词语,经查往往来自《左传》《史记》《汉书》,作为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的所谓翻译其实发生在汉语内部,将口译者的白话翻译为文言,胎息史汉,寝馈唐宋古文的林纾将域外小说转化为可以雒诵的文章,读者被文章的魔力牵引而陶醉在紧张的故事情节中。反观周作人《域外小说集》的译文之美,取法六朝译经,骈散夹杂,并不喧宾夺主,读者读讫,故事中人物的情思依然郁结心头,难以释怀。林译小说与周作人翻译活动的离合关系,还需要用更细致的语文学功夫来论证,而《匈奴奇士录》《黄蔷薇》《炭画》这几部译作迄今未得到深入分析,足见作者的研究所触及问题之复杂,可激发学界进一步探索的动力。
第四、第六、第七章分别以《狂人日记》《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三个经典文本为中心,讨论鲁迅小说独特的诗学形式,追问现代文学何以能够表现人的内面性。本书第四章的内容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第四章即有所涉及,作者发现《狂人日记》与陈冷血1910年翻译的安德烈耶夫《心》(《思想》)具有明显互文性,二者同样分享小序与正文的文体区隔。通过对读英译、日译、中译三个版本,作者认为安德烈耶夫受尼采影响而塑造的“超人”形象被陈冷血改造为与“谈”体小说人物类似的抨击社会的“异人”。鲁迅的创造性在于折中二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具有心理深度的“异人”,也是一位活在中国现实社会的“超人”,《狂人日记》小序与正文的对立又表现在语体层面,实现在安德烈耶夫小说文体基础上的跨文化创造。此一章节推进了对鲁迅与晚清文学翻译之关系的理解,往昔被视为鲁迅戛戛独造、劈空而来的《狂人日记》,找到了形式创造的可能性来源。范伯群认为陈景韩1909年的小说《催醒术》与《狂人日记》已有部分“共识”,笔者注意到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将因鸦片瘾而败家亡身者的自叙传嵌入叙述者的叙述中,与《狂人日记》有相似之处1刘禾在《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中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使用“框式结构”叙述,使其有别于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关诗珮对此有反思性意见,参见关诗珮《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翻译语“小说”的生成及实践》,香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1~27页。,但其依然保有拟话本小说主体故事前先讲一个引子的文体结构,以及“诸公”一类叙述声口。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鲁迅读到过陈景韩的译文,但张丽华绵密的论证具有极强说服力,这种发现需要研究者深入阅读晚清小说报刊,呼吸领会一时代文风之转移,辅以必要的想象力,在实证研究止步的地方飞翔起来。
第六章的研究与此类似,鲁迅没有留下阅读徐志摩译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文字记录,但徐氏译文曾与周氏兄弟文章登载同一副刊版面,唯有在原始刊物历史现场的空气中方可捕捉同时代文学者相互激发的微观路径。作者发现《幸福的家庭》与徐志摩译《一个理想的家庭》存在多重互文性,曼斯菲尔德通过自由间接引语表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声音,与叙述者叙述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反差。由于中西语言之差异,这种文体效果被徐志摩改造为人物内心的独白,而经过徐志摩译文的媒介,鲁迅小说以直接引语的形式转达自由间接引语的文体效果1作者分析《幸福的家庭》开篇一段内心独白,认为引文第一段去掉引号和“(他)想到这里”这一提示词,就是典型的自由间接引语(第173页),此观点可以商榷。由于这一段直接引语中有“——而我,……这算什么?……”一句,去掉引号和提示词,是自由直接引语,而非自由间接引语。如果再去掉“——而我,……这算什么?……”,可以理解为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两可型。申丹认为在没有时态标志的中文中,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不同仅在于人称,若人称无法区分,则为自由直接式与自由间接两可型,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三版)第十章第四节“中国小说叙述中转述语的独特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30页。,同样与叙述者的叙述形成对比,从而讽刺脱离实际的“室内写作者”之虚妄,《幸福的家庭》形式诗学的奥秘,尽在于此。我们跟随作者的论证脚步,穿梭在曼斯菲尔德原文、徐志摩译文、鲁迅小说三者之间,竟有移步换景之趣。
作者在第七章分析《高老夫子》的双重诗学魅力:一方面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将笔触深入“高尔础”分裂的自我意识中;另一方面调用《儒林外史》的讽刺笔法描写“高干亭”卸下道具后的真实自我。作者并未停留在形式分析层面,从形式诗学进入文化诗学,结合1924年“韩杨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潮,为小说找到“今典”,高老夫子的形象亦由虚伪的腐儒转变为包裹着旧伦理的“新文化”之隐喻,小说成为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化境遇的寓言式表达。作者的分析改变了我们对《高老夫子》的认知模式,不同于《呐喊》时期配合新文化同人攻击旧礼教、旧思想,在新思想逐渐成为主潮的1925年,鲁迅批判的矛头针对轻易“转向”的新文化应声虫,因此高尔础发表呼吁整理国史的论文,并非出于对国故“骸骨的迷恋”,而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一类新思潮的“拟态”。阅读此章牵连想到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1925年高尔基在中国的声誉未若日后左翼文学兴起时那般崇高,彼时鲁迅对高尔基亦无特殊兴趣,为何让高老夫子改名高尔础?循着作者提到的“韩杨事件”,可以发现《妇女杂志》第10卷第7号1张丽华在文中引用了同期署名“起睡”的论者评论“韩杨事件”的文章《两性间一桩习见的事》。有一篇樊仲云译述的《俄国文学家高尔基的妇女观》,高尔基认为女子责任在鼓励男子去创造,而非自己创造,女子不愿了解知识本源,在艺术上无创造力,高尔基虽赞成女子从事活动,但活动范围应受限制。这种妇女观恐怕会引起鲁迅的反感,鲁迅很有可能读过此文,写作时便让主人公改名高尔础了。
第九章以鲁迅与陈寅恪为中心透视二人对小说的不同理解与想象。作者发现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既以西方注重虚构与独创的小说观串联中国小说不同的文体形态,又希望彰显各时代小说文体自身的衍变规律,依违于中西两种传统。浦江清1940年代即意识到,在过渡时代中国小说史研究难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出发,唐宋以来的笔记文学才是《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后裔,“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实则“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2浦江清:《论小说》,张耀宗编:《浦江清文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182页。,唐传奇是小说的别派旁支,批评的指向显然是鲁迅。针对鲁迅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近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界也出现检讨之声,鲁迅的观点被视为以西律中的典型例证3刘晓军:《中国小说文体古今演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233页。,对小说史研究的反思召唤中国本位立场的回归。但小说在二十世纪从“小道”跃居“文学之最上乘”,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载体,是近现代知识体系结构性变革的一环,小说史研究也是以现代视角“突入”并“筛选”整体化文学传统的关键步骤,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理据也建立在此基础上,回归本位的声音是学科成熟的表现,亦暗含消除其自身动力来源的可能。张丽华同样检讨鲁迅小说史论中的线性演进模式,但并不希望回归看似不偏不倚的本位立场,而是以陈寅恪的小说观为例,与鲁迅小说观参差对照,展现小说作为详尽摹写现实的混合性文体的魅力。陈寅恪的小说观突破单一的文类视角,小说的驳杂性为雅俗文学的交融提供试验场,他受到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的启发发掘中国诗文中摹写现实的传统,在具体的文体辨析中尊重历史实际,又不胶着或止步于此,将小说理解为“文备众体”的“结构”。由此,小说恢复其野草式的特性,在正统所欲遮蔽的缝隙中倔强生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阅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第三章“无声的‘口语’”中,作者发现周作人翻译《Theokritos牧歌第十》时,误将脚色乙(Battos)的一节情歌当作对话,推测这是由于“安特路朗将原作的人物对话与歌一律都译成了不加区别的无韵散文,以致周作人在初次翻译时,分不清是歌是话”,这首情歌“在安特路朗译本中因为分页的缘故与第二句隔开了”,导致周作人误将此视为“Bucaeus的答话”1张丽华:《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第75页。。然而笔者查阅著者所引用的Andrew Lang 编译的1880年版Theocritus,BionandMoschus:RenderedintoEnglishProse,withanIntroductionEssay,发现这首情歌并不存在因分页而隔开的情况(第55页)。这一情况出现在1889年再版本(第56~57页)以及《洛布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的TheGreekBucolic Poets一书(第133、135页),为蔼特芒士(J. M. Edmonds)译本,脚色名字旁注有表歌唱的sings,周作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Theocritus拟曲即参考蔼特芒士译本。若作者的推断符合实情,则1917年周作人翻译时的底本并非作者文中所标注的1880年初版本,国图藏有一册1896年本,据1889年再版本重印,极有可能是周作人藏书,为《古诗今译》底本。2周运:《知堂藏书聚散考》,《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01~602、470页。至于初版于1912年的TheGreekBucolicPoets,周作人所有的一册为1923年版,1924年购入3周运:《知堂藏书聚散考》,《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01~602、470页。,1917年尚未曾得见。
作为作者的“第二本书”,《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以现代文学的核心人物——周氏兄弟为中心,在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的互动中勘察中西文体的跨文化游踪,自由灵活地调用多种理论资源,通过耐心的文本对勘,几乎每一章都动摇了稳固的文学史常识,或在前人止步之处推阐尽致,阅读过程中往往伴随发现的愉悦。此书揭示出在世界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所抵达的深度与广度,细密的论述针脚昭示一种述学范式的成熟,批文入情,沿波讨源,发皇心曲,端赖于此,发覆抉微,启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