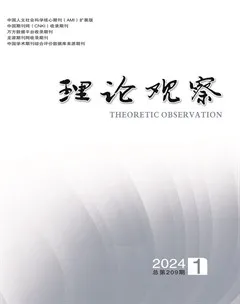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住房获得
李君甫 王树祥
摘 要:除经济资本外,还有其他个体资本影响农民工的住房获得,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住房获得的影响,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农民工的住房获得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相关研究,分析农民工获得商品住房和保障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更丰富的农民工不仅更容易获得产权住房,而且在保障房的获得上也更有优势。农民工获得商品房的机会有限,而各地的保障房更倾向于保障本地人和人才,大多数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弱势的农民工被“挤出”了住房保障范围。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住房保障;保障房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1 — 0061 — 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务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达到了17172万人。①但是这一庞大的群体一直难以有效地融入城市,进而实现市民化,实现安居乐业。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众多困境中,住房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1]。随着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长,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也开始逐渐得到关注,自2006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起,涉及农民工群体住房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期望缓解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境。然而,直到2018年,进城农民工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和租赁公租房的比例分别仅有1.6%与1.3%②,保障性住房惠及农民工的情况很少。大量的农民工仍然聚居在租金低廉、环境较差的城市边缘地带[2],生活配套和卫生设施简陋[3],农民工的住房困境依然严峻。
“安居”才能“乐业”,农民工的住房获得不仅关系到其居住状态的优劣,也是关系到其城市消费、投资以及市民化意愿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民工群体的住房获得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现行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的成效如何,已经成为关系到城镇化发展与国家民生目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在探讨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现象中指出,在人们获取住房的过程中,单位与职业性质、收入水平等经济与政治资本因素均会起到显著作用[4][5][6]。而住房获得的差异并不仅是一种建立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基础上的社会排斥,除收入水平外,诸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同样会在资源获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因素在农民工商品住房獲得上有多大的作用,是否也会影响保障性住房的获得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二、理论与假设
(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住房获得
资本可以理解为个人所持有的、可以在行动中可以得到收益的资源。边燕杰指出,资本最根本的形式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种,物质资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财富,它外在于社会行动者但为社会行动者所占有[7]。人力资本的概念摆脱了物质资产的束缚,可以理解为附着于人体的知识、技能、健康、流动与迁移等一切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则表现为基于稳定社会关系形成可以通过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为个体提供收益的社会结构资源[8]。住房在城市中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农民工的住房获得可以理解为一个获取资源收益的过程。那么在此过程中,各类资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中国城镇住房资源获得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在住房福利分配时期,农民被排除在住房分配体系之外,无法获得城镇住房。城市居民的住房获得主要取决于其单位性质与政治资本。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住房获得由再分配逻辑逐渐转向市场逻辑,住房资源获得的影响因素也逐渐多元化。人们获取住房的过程中,单位与职业性质、收入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等经济与政治资本因素会起到显著作用[4][5][6]。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个体与家庭特征、受教育程度与社交群体等人力与社会资本因素同样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住房获得[9][10],这些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均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自有住房、购房意愿以及购房融资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1]。基于增加收入、改善生存状况的人口流动也是一种人力资本[12],务工时长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人力与社会资本积累越多[19],务工5年以上的农民工购房意愿会更加强烈[13]。住房的获得经历了一个由政治与经济资本主导转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
(二)农民工的保障房获得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是我国政府进行住房市场干预,用以缓解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但不同于商品房的获得,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存在经济上的准入标准,在户籍身份、工作时长方面也有严格的限制,绝大多数份额被用来缓解当地城市居民的住房困难。截止到2017年,农民工获得住房保障的比例不足3%[14],农民工的住房困境并没有在保障房建设的推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当前农民工保障房获得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限制、建设与管理不足方面。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住房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15],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民工难以从单位福利制度和公房私有改革中获利,也难以享受福利房、廉租房与公租房等优惠政策[16][17]。农民工当前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完整[18],保障房准入和退出管理不够完善[19]、保障房的建设也存在空间失配,政策缺陷性失灵和变异性失灵等问题[20]。
同商品房一样,保障性住房更是一种稀缺资源,但保障房的获得是否也会受到个体持有资本的影响问题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仅有部分研究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指出,在保障房的准入过程中存在收入与财产更多的家庭获得保障房成功率更高的承租错位现象[21],权力寻租与信息不对称使该得到保障的人群被排斥在保障性住房之外[22]。由此看出,尽管有着具体的收入准入限制,在保障房的获得中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依然发挥着某些作用。同样在住房获得过程中发挥影响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否在保障房的获得过程中依然发挥作用,获得保障房的农民工在哪些方面具备优势,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探索。
(三)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指出了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住房的获得由政治与经济资本因素主导逐渐转向由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因素与受教育程度、社交群体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多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并从制度限制、建设与管理不足等方面指出了现有住房保障制度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以及保障房准入和退出管理不够完善等问题,为我国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回顾以往的住房获得研究,探索的往往都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城市居民产权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对于农民工群体的住房获得分析不足,也没有分析保障房获得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合理性。而经济资本对于住房获得水平的影响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探索农民工群体各类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保障房的获得机制。根据对现有文献研究,本文提出如下4个假设:
假设1: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越丰富,其在所流入城市获得产权住房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2: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越丰富,其在所流入城市获得保障房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3: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在所流入城市获得产权住房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4: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在所流入城市获得保障房的可能性越高。
三、数据与变量
我们采用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研究,该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农转居户籍、居民户籍及其他户籍的流动人口。根据研究对象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筛选,共选取了其中132555份农民工样本。
因变量:以农民工的住房获得作为因变量。根据研究需要,将住房获得属性为自购商品房、自购小产权住房、自建房的农民工定义为产权型住房获得者(除产权型保障房);将住房获得属性为自购保障性住房、政府提供公租房的农民工定义为保障性住房获得者;将住房获得属性为单位/雇主房(不包括就业场所)、租住私房——整租、租住私房——合租、借住房、其他非正规居所的农民工定义为其他住房获得者。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设置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两个方面。人力资本因素包括教育程度与务工时长(意味着经验与技能的积累)两个变量,社会资本包括是否参与党/团组织活动与主体社交关系两个变量。其中是否参与党/团组织活动变量根据农民工党/团组织活动的参与情况设置成“是”与“否”的二分变量。主体社交关系变量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情况转化而来,我们将社会交往主体为同乡(户口迁至本地)、同乡(户口仍在老家)、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来的其他地区)定义为强关系。将社会交往主体为其他本地人与其他外地人定义为弱关系,强关系意味着社会交往的范围小,弱关系意味着社会交往的范围大。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属性、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融入特征会对其住房获得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职业类别、月平均收入、流动范围、客观社会融合(社保卡持有)、主观社会融合(认可自己成为本地人)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农民工住房获得的描述性分析
(一)农民工群体的住房特征
表1是关于农民工住房获得具体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在132555份农民工样本中,产权住房获得者31416人,占比23.70%,其中主要居住于自购商品房,占比达到了71.1%。有2743位农民工获得了保障房,占比2.07%。其中有46%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内,54%购得了保障房。其他住房群体983996人,占比74.23%,主要以租住私房为主,其中整租比例为65.3%,合租比例为15.1%,其余主要居住在单位房、雇主房、借住房、就业场所等性质的住房中。根据表2可以看出,其他住房获得者尽管住房条件远远比不上产权房获得者和保障房获得者,但是他们平均每月住房支出明显高于保障房获得者,达到了711元。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也分别比产权住房获得者与保障房获得者高出了4%与10%。总体来说,当前农民工群体获得保障房的比例较低,仅有2.07%。绝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单位房、雇主房等其他性质的住房中,比商品房和保障房获得者的住房条件差得多,相比于保障房获得者住房支出更大,面临的住房困难更严重。
(二)不同住房性质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
表3是不同住房获得者的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都不高,主体为初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群体,分别占到了农民工群体的48.3%与20%。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上的农民工在产权住房与保障房的获得上更具优势,在产权住房获得者与保障房获得者中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4.5%与2.8%。务工时长代表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经验和技能的积累,也使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根据表4,产权住房获得者与保障房获得者的平均务工时长分别为8.09年与7.12年,而其他住房获得者务工时长平均只有5.98年。
(三)不同住房获得者的社会资本特征
表5是不同住房获得者的社会资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党团组织是政治性的组织,农民工的党团组织关系在来源地,参与务工地党团组织活动几乎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和机会,但是参与相关组织活动可以获得政策信息,也可以密切和正式组织的关系,获得组织支持,我们将其视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可以看出,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参与党/团组织活动的比例都很低,参与党/团组织活动的农民工占比只有3.7%。其中保障房获得者的参与党/团组织活动比例最高,达到了6.4%,而其他住房获得者参与党/团组织活動比例只有3.1%。社会交往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根据格兰诺维特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往中的弱关系在择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可以看到,产权住房获得者与保障获得房者交往的对象主要为弱关系,交往范围更广,分别达到了66.6%与64.8%。而其他住房获得者的社交对象更多的是强关系,交往范围更狭窄。
五、农民工保障房/产权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究农民工保障房/拥有产权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我们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得到了如表6所示的农民工获得保障房/产权住房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模型拟合显著性为0.000,内戈尔科R方值为0.216,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表6可以看出,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在保障房的获得上,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农民工群体与小学及以下农民工群体并无显著差异。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农民工群体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农民工群体在获得保障房方面则表现出很大优势,高中/中专、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群体获得保障房的概率分别达到了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群体的1.39倍与1.745倍;产权住房的获得与受教育程度则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产权住房。务工时长与保障房获得与产权住房的获得也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务工时长越长,获得保障房与产权住房的几率越大。
社会资本特征对于保障房与产权住房获得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参与党/团组织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获得保障房的概率达到了不参与党/团组织活动农民工群体的1.654倍。在产权住房的获得上参与党/团组织活动的农民工群体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达到了不参与党/团组织活动农民工群体的1.261倍。在主体社交关系方面,强关系代表了一种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同质性”互动,这种群体内部的交往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生活局限于单一的活动范围与单一的信息环境中,往往会阻碍其对城市的了解与认同,也阻碍了政策信息的获取和理解。而弱关系则体现了一种农民工与当地居民间的“异质性”互动,他们可以通过异质性的交往拓展社会关系,了解更丰富的政策和社会信息,进而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资源与融入城市。在城市生活中,到城市后再建构社会网的以弱关系社交为主体的农民工相比于局限于“同质性”社交的以强关系社交为主体的农民工是更具优势的[23]。在住房资源的获得上也同样体现出这一特征,弱关系社交群体相比于强关系社交群体无论在产权住房与保障房的获得上均呈现优势地位。总体来看,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处于优势的农民工群体无论在产权住房的获得还是保障房的获得上均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六、结论与讨论
一是,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处于优势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体面的产权住房与保障房。通过农民工保障房/拥有产权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及不同住房群体在住房、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征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更丰富的农民工无论是在产权住房与保障房的获得方面都显现出来明显的优势。商品房和保障房都是稀缺资源,那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较差的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无论是工作选择还是信息获得往往依赖于同质性群体,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人力资本难以脱离社会资本单独发挥作用。而那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处于优势的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学历与好职业,更适应城市文化,拥有更好的发展预期以及市民化机会。他们通过其较高的人力资本与“异质”性互动拓展了社会网络建立起新的社会资本,从而在保障房获得这一在信息不对称的竞争场域中取得了优势。而那些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群体难以获得保障住房,大多通过租赁获得住房,其住房支出也超过了保障房获得者。
二是,农民工住房保障覆盖面很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弱势的农民工难以获得住房保障。一方面,尽管大多数城市虽然已经建立了面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包括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權房等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但主要是面向本地户籍居民和人才,农民工能够获得住房保障服务的比例很小,仅有2.07%的农民工能够获得保障房,远远低于城镇户籍人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农民工住房政策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存在较大的自主行动空间[24]。而城市保障的建设是由地方财政买单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建设将动用其大量的空间与财政资源,削减发展性与公共服务型支出的同时又容易遭到本地居民的不满[25]。因此,尽管在理论上,保障房的供给面向所有存在住房困难的城市居住群体,而在实际上这种供给是有限度的,甚至是具有排斥性的[26]。在住房保障实行过程中往往通过稳定收入、缴纳社保年限等方面的条件来提高保障房的申请门槛[20],加上大部分农民工很难及时掌握相关政策信息,使得农民工保障房政策很难覆盖那些真正存在住房困难的群体。那些对城市发展具有较大预期贡献的,具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的农民工往往被纳入到住房保障体系之中,真正处于住房困境的最弱势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到住房保障。
尽管全国很多城市在农民工住房保障模式与政策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农民工住房政策缺乏顶层设计与法律保障[18],地方政府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往往不愿将财政资金投
入到经济与政绩回报性小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方面
来[27],总体上农民工群体的住房困境依然存在。与之相对,地方政府似乎更为重视解决具有推动城市发展能力的人才的住房问题。随着各城市人才争夺战的展开,各类为人才提供的保障房和住房补贴政策不断推出,甚至将申请公租房的“收入标准”置换成“学历标准”,农民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获得受到了进一步的挤压。2021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的文件,这一政策旨在解决青年人和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一些地方的保障性租赁房项目已经开始入住,期待地方政府能够加大力度,从而缓解农民工的住房困境。
〔参 考 文 献〕
[1]彭华民,唐慧慧.排斥与融入: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困境与住房保障政策[J].山东社会科学,2012(08):20-29.
[2]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J].管理世界,2005(08):48-57.
[3] Zhang Y,Zheng S,Song Y,Zhong Y.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village removal on nearby home values in Beijing[J]. Growth&Change,2016(01):9-31.
[4]刘祖云,毛小平.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12(02):94-109.
[5]毛小平.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J].社会,2014,34(02):118-139.
[6]黄建宏.住房分化:市场、再分配还是家庭结构?——基于广东、北京及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26(01):72-77.
[7]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136-146.
[8]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 邓方,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80-295.
[9]崔光灿,刘羽晞,王诤诤.城市新市民住房状况及决策影响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实证[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02):118-124.
[10]杨巧,李仙.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1):62-70.
[11]杨婷怡,叶倩,雷宏振.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与住房消费行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6):148-160.
[12]栾文敬,路红红,童玉林,吕丹娜.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综述[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2):48-54.
[13]李君甫,孫嫣源.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流动人口购房的影响——基于国家卫计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02):62-72.
[14]蔡键,包云娜,陈安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住房保障研究[J].江汉学术,2015,34(02):43-48.
[15]Lau J,Chiu C.Dual-Track Urbanization and Co-Location Travel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in New Towns in Guang—zhou, China[J].Cities,2013(30):89-97
[16]Wang Y P,Wang Y L,Wu J S. Housing Migrant Workers in Rapidly Urbanizing Region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Model in Shenzhen[J]. Housing Studies,2010(01):83-100.
[17]Wu W P,2004.Sources of Migrant Housing Disadvantage in Urban 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4(07):1285-1304.
[18]周建华,刘建江.农民工城市住房支持的政策因应[J].农村经济,2014(07):103-107.
[19]吴秀梅.新型城市化下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与对策——以南京市J园区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8,57(19):168-172.
[20]吴宾,李娟.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失灵及其矫正策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02):36-42.
[21]卢雪松.关于我国城市保障性住房准入机制的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08):209.
[22]鲁菊,孙文建.信息不对称下保障性住房准入问题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2(25):55-57.
[23]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社会学研究,2003(03):99-110.
[24]高伟.住有所居农民工住房问题实证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88.
[25]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阙如与重构[J].城市问题,2011(02):90-95.
[26]赵晔琴.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55(06):68-75.
[27]吕萍,周滔.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认识与对策研究——基于成本-效益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8(03):110-114.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