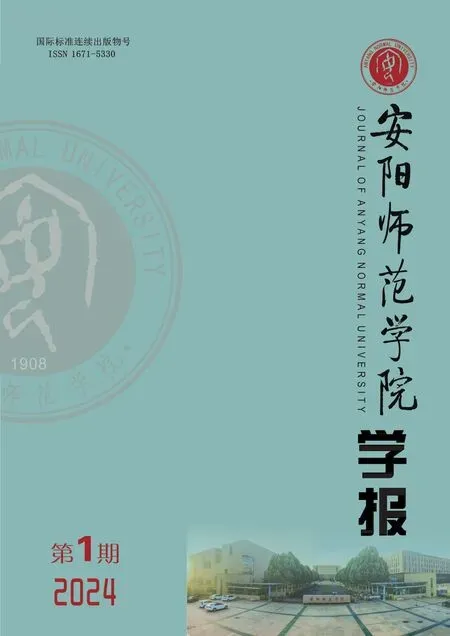宋代南北江治理研究
苏换着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宋代北江地区指沅江下游和澧水流域,包括澧、鼎、辰州及溪州等羁縻州[1](P474)。北江蛮首领为彭家,世有溪州,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1)当时溪州分为上溪州、中溪州、下溪州。文献里很少提到中溪州,一般只提上溪州、下溪州,下溪州是彭氏政权中心。,十九州皆听从指挥,谓之“誓下”。宋代南江地区指沅江中游及其支流,包括沅、靖州及诸羁糜州,皆属荆湖北路。南江蛮酋各有溪峒,其中叙、峡、中胜、元四峒属舒家,奖、锦、懿、晃四峒属田家,富、鹤、保顺、天赐、古五峒属向家[1](P474)。
宋代南北江治理既包括唐末五代以来南北江豪酋区域治理,也包括宋王朝对南北江豪酋的羁縻统治,还有宋代章惇经制南北江的历程。
一、宋代地方豪酋对南北江的治理
(一)宋代北江豪酋的地方治理
“北江蛮”由唐末五代时溪、澧等州“蛮”部发展而来[2](P55),“溪州蛮”为“北江蛮”主要组成部分[3](P159)。唐末,彭士愁为溪州刺史,据《十国春秋》之《李宏皋传》,彭氏在溪州“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立三四代,长百万夫”[4](P1018)。可知彭氏据有溪州,到彭士愁之世,已历三四代,彭氏有“胜兵万余人,春夏则营种,秋冬则暴掠”,彭氏之“胜兵”当由其族人——“土蛮”组成[3](P158)。彭氏在溪洲的军事力量在唐末就已经初露端倪,迫于其军事压力,其周边的族群与部落竞相归附。但是,彭氏占据溪洲期间,虽然也注重农业生产,但其暴力掳掠行为对周边民众的生产发展威胁极大。
以北江蛮下溪州刺史为都誓主的彭氏是北江诸蛮中最强的一部分。《大明一统志·辰州府》古迹条云:“铜柱,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会溪城对江,五代晋时,溪州刺史彭士愁纳土求盟,楚王马希范立铜柱为界,学士李皋为铭。”[3](P159)铜柱上刻满盟誓,这反映了唐末以来彭氏统治北江地区的具体情形。彭氏作为北江势力最大的一支,担负着都誓主的东道主责任,彭氏的举动关系着北江政局的稳定与否。在政权纷迭的唐末五代时期,北江溪州地区能够以盟誓制度来团结稳定周边部族,彭氏一族在宋代初期北江地区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史》记载:“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听自补置。”[5](P14178)溪州彭氏作为都誓主承担着调和北江诸蛮酋之间承袭等政治秩序的中介代理人角色,虽然名义上彭氏不过是溪州刺史,事实上却有着可以自己补置诸如押案副使及校吏等下属职官的权力。
彭氏酋帅除据有上、下溪州以外,其另一支系还据有忠彭州,彭儒猛在稳定了对下溪州的统治之后,开始向邻州兼并和扩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天圣三年(1025年)七月,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攻杀知忠彭州彭文绾[6](P2386)。彭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北江政局的局部统一,但彭氏内部却因为支系复杂,时常纷争不断,对北江以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阻碍。
北江豪酋不仅内部因争夺地盘战乱不已,还与南江豪酋勾结侵犯内地。庆历四年(1044年),夔州“土贼”田忠霸诱“下溪州蛮将内寇”,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彭仕羲“以罪绝贡献”,可能是彭仕羲参加了田忠霸的“内寇”行动[3](P163)。南北江蛮酋相互勾结内寇的同时,便拒绝向宋王朝进行朝贡,这表明羁縻政策之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式打破平衡,唐宋时期民族地区地方豪酋叛服无常,表明羁縻政策很难达到对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彭氏内部的争斗不仅在直系与支系之间,即便父子之间也有纷争,至和二年(1055年),彭仕羲和师宝父子之间就发生了争斗。据载,师宝“告其父之恶,言仕羲尝设誓下十三州,将夺其符节,并有其地,贡奉赐与悉专之,自号‘如意大王’,补置官属,谋为乱”[6](P4491)。五代晋时彭士愁可以担任都誓主来调和诸蛮酋之间的承袭纷争等诸般事宜,但到了彭仕羲时代,依然妄想做北江豪酋的都誓主,意欲自设官吏做地方霸主,首先便遭到儿子的反对,这表明宋朝正统地位得到北江蛮酋承认。唐末五代政权纷迭,需要彭氏作为都誓主来统合一方秩序,而宋王朝建立之后,随着中央政权的稳固以及中央羁縻政权在民族地区的建立,彭氏的政治权势有所压缩。此时,充当统合北江局势中介的实质调解人应该是朝廷,而彭氏意欲膨胀权力,这势必为中央王朝所不允,也会遭到北江其他蛮酋的敌视。
(二)宋代南江豪酋的地方治理
南江“诸蛮”由唐末五代“叙州蛮”等部发展而来,叙州为分辰州所置[3](P166-168)。《十国春秋》记载,后梁开平四年( 910年)十二月,“辰州蛮宋邺寇湘乡,溆州蛮潘金盛寇武冈,王(马殷)命昭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州兵五千讨之”[4](P938)。《九国志·吕师周传》载,师周“领兵破飞山蛮,斩其帅潘全盛,诸蛮悉归款”[7](P121),可见 “飞山蛮” 是由“溆州蛮之一部演化而来。
不同于北江,南江豪酋大姓众多,而每个豪族大姓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唐五代十国时,叙州大姓酋帅有张氏、昌氏、潘氏、符氏、杨氏等。唐末,马殷据湖南[3](P167),“澧州向环、辰州宋邺、溆州昌师益等尽统溪洞诸蛮来附”马殷[4](P998)。后汉乾裙三年( 950年),马希萼攻破长沙时,溆州蛮帅符彦通曾领兵随入长沙[3](P167),希萼“率群蛮破长沙,府库累世之积,皆为彦通所得。彦通由是富强,称王于溪峒间”[4](P1037)。后周广顺三年(958年),王逵得潮南之地,遣牙将王虔朗至溆州招抚符彦通,符彦通即除王号,王逵授符彦通为黔中节度使。后周显德年间,据有湖南的周行逢死,“溆州蛮杨正岩遂以十洞称徽、诚二州,或言即彦通诸部云”[4](P1037-1038)。
南江豪酋富州刺史向通汉曾大规模倒卖田地,可知向氏作为南江蛮酋,占据军政要职的同时也可能霸占大量土地。《宋会要辑稿》载,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宋真宗对宰相说:“富州刺史向通汉于辰州溆浦县,潭州益阳县广市土田,或言谋劫内地,此为次舍之备。可就命交州安抚使邵烨俟经其地,熟察情伪及图利害以闻。”[8](P378)后来,荆湖转运使就向通汉于潭州等地购买土地的传闻作了澄清,说“荆湖转运使言,富州刺史向通汉,遣人于潭州营佛事,以报朝廷任恤之意”[6](P1255),消除了宋真宗对向通汉的怀疑。
南江诸蛮酋之间经常为争夺地盘而纷争不已。据《宋史》所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5](P14181)《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熙宁六年( 1073年)二月,“富州向永晤亦欲构变,以百姓不从, 遂止。”[6](P5903)富州向氏酋帅的贪婪好战以及长期的不义之战,逐渐激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没有了百姓的支持,宋王朝对南江进一步治理的加强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宋王朝对南北江豪酋的羁縻统治
(一)宋王朝对北江豪酋的羁縻统治
宋代对北江豪酋的羁縻统治主要是通过对归顺的蛮酋授予刺史官衔来加以笼络,同时地方豪酋也有定期朝贡的义务。据载,太祖乾德元年( 963年)七月,“王师既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赟等列状求内属。乙丑,以允林为溪州刺史,洪赟为万州刺史”[6](P98)。
北宋初年,为了笼络溪州大姓酋帅,多授以虚职,并乘机将他们徙之内地,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诏溪州宜充五溪团练使,刻印以赐之。五年(967年)冬,以溪州团练使彭允足为濮州牢城都指挥使,溪州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牢城都指挥使,珍州录事参军田思晓为博州牢城都指挥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据山险,持两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5](P14173)。
北宋政权稳固之后,朝廷权威成为调和北江内部诸蛮酋势力消长的重要力量。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朝廷“诏辰州不得移部内马氏所铸铜柱。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旧三年则为州所易,望朝廷禁止。’赐敕书安抚之”[5](P14173)。由此可知,统合北江诸蛮酋势力的中介力量由唐末五代以来的都誓主彭氏让位给了北宋朝廷。是时,为继续维持溪、锦等州的现状,“辰州言溪、锦、叙、富等四州内属蛮,相率诣州,愿比内地民输租税。诏遣殿直王昭训与权沅陵县令高象元、权辰溪县令张用之分往四州仔细相度,察其民俗情伪,委得久远利便可否,乃按视管界山川地形画图来上。卒不许。”[6](P550)
宋王朝通过赐予归顺蛮酋高官厚爵来拉拢其心,而地方蛮酋也借助朝廷封爵、印信以及朝贡所得的丰厚赏赐来维持自己的地方权威。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上溪州刺史彭文庆率溪洞蛮六十二人来朝,且献方物。上顾谓文庆曰:‘尔善于统辖,益宜尽心’。又谓群蛮曰:‘自今勿复为过,犯者不赦。’各赐锦袍、银带有差”[6](P1385)。《宋会要辑稿》云:“先是,溪峒蛮或时扰边,自文庆总领,不敢为非故也。”[8](P379)虽然北江彭氏豪酋假借朝廷权威统合一方,但对于北江地区政局的稳定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羁縻之道重在以蛮制蛮,宋王朝深谙此道。借助北江豪酋彭氏的势力来平定其他部落的叛乱,并对平叛有功的彭氏大加赏赐,这对其他地区的蛮酋无疑起到了震慑与诱惑双重之功。景德二年(1005年),“辰州诸蛮攻下溪州,为其刺史彭儒猛击走之,擒酋首以献,诏赐儒猛锦袍、银带。儒猛自陈母老,愿被恩典,诏特加邑封”[5](P14175)。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夏四月,“诏忠州彭文绾自今岁赐锦袍,又赐下溪州刺史彭儒猛奖诏,以辰州言其捕获蛮寇故也”[6](P1926)。
羁縻政策并不能长久有效统治地方蛮酋,他们为争夺地盘或自相仇杀,或侵扰内地,这种叛服无常的举动朝廷也心知肚明,但羁縻政策中因俗而治的原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统治效果。朝廷了解蛮酋所在地经济生产力有限,蛮族部落性情不同于内地民众,朝廷对于进犯内地的蛮酋处罚都比较宽容,并且对叛乱后归顺的蛮酋还赏赐丰厚,以此来笼络蛮酋。《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下溪州彭儒猛与高州蛮同恶,虑延及施、黔州,寇劫居民。”[6](P2107)《宋会要辑稿》载:“其年,儒猛因顺州蛮田彦晏上状本路,自诉求归,转运使以闻。上哀怜之,特许释罪。”[8](P385)事后还对彭儒猛仍加录用,赐锦袍银带,令辰州通判刘中象与儒猛歃血为誓遣还本州,并留其子仕汉等人在今河南供职,实际上留作人质。
宋王朝对不触及朝廷实质利益的北江蛮酋内部纷争常持默认态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〇三载,天圣三年(1025年)七月,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攻杀知忠彭州彭文绾,其子儒素率其党九十二人来归,欲补儒素为复州都知兵马使[2](P2386)。宋王朝对彭儒猛兼并忠彭州置之不问,却补彭儒素为复州都知兵马使,表明宋王朝对北江地区的羁縻统治也是通过以夷制夷手段来实现的。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彭儒猛死,其子仕端知容州,以名马来献,请继袭[6](P2453),此事说明只要北江蛮酋向朝廷称臣纳贡,朝廷对于他们内部的兼并纷争往往是默许的。
如果北江豪酋的叛乱侵犯了朝廷的权威,或者威胁到了宋王朝的正统地位,宋王朝往往会以军事势力横加干涉。至和二年(1055年),彭仕羲和师宝父子之间发生了争斗,荆湖北路及辰州多次派兵征讨,皆是无果而终。于是宋仁宗遣御史朱处约前往视察,“仕羲乃自陈并无反状,其称僭号、补官属,特远人不知中国礼义而然”。到嘉祐三年(1058年),彭仕羲被荆湖北路兵马钤辖郭逵击败,乃归还所掠兵丁、械甲,率“蛮众”七百(拜)饮血就降[3](P164)。宋王朝派兵征讨彭仕羲,是因为其子告其僭号造反,侵害了朝廷在北江地区的统治权威。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朝廷对野心勃勃的蛮酋还是持宽容态度,歃血为盟、俯首称臣之后朝廷便不再予以追究。
朝贡不仅是中央与边地联系的重要纽带,也对边地与内地经贸往来、政治格局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云:“盖自咸平已来,始听溪峒二十州贡献,岁有常赐,蛮人以为利,有罪即绝之。”[6](P4077-4078)各溪洞酋帅向朝廷贡献,是维持当时中央王朝和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正常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贡献”不仅可以换取优厚的“赏赐”,还可以向朝廷请求封爵。彭仕羲要求恢复“岁贡”的目的,还在于谋取上溪州,利用朝廷赐予的权威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溪州地区给朝廷的贡品主要有丹砂、水银、虎皮、黄连、兵器、马匹等,朝贡不仅是北江蛮酋承认宋王朝正统地位的政治象征,更是调和北江与内地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马和丹砂并非溪州当地的特产,而是通过与西南诸蛮交易中获得,可见朝贡与回赐实际上成了北宋王朝与溪州之间的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促使了汉族经济文化在溪州地区的传播,使溪州地区接触到许多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从而直接剌激了溪州经济社会发展[9](P196)。
(二)宋王朝对南江豪酋的羁縻统治
宋王朝对南江豪酋的统治也是通过授予高官厚爵、丰厚赏赐来拉拢人心的。乾德三年( 965年)秋七月,五溪团练使、洽州刺史田处崇言:“先是,湖南节度使马希范以叙州谭阳县为懿州,命臣叔万盈为刺史。希范死,其弟希萼改为洽州,愿复旧名。从之,仍铸印以赐处崇。”[6](P156)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懿州刺史田汉琼、锦州刺史田汉希上言,愿两易其地,诏从之,以田汉琼为锦州刺史,田汉希为懿州刺史。奖州为田处达所据,晃州为田汉权所据,朝廷亦均授刺史[5](P14173-14174)。
宋王朝对南江蛮酋之间不涉及朝廷实质利益的纷争也持漠视态度。《宋史》载,淳化二年(991年) ,荆湖转运使曾上奏说:“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远俗,令勿问。”[5](P14174)可知朝廷起先的羁縻政策是因俗而治。对于南江豪酋向氏,宋王朝不仅授予其高官以及优厚赏赐,还允许其在中朝任职,而且令其居住在内地。这原本是质子监视制度的延伸,但对向氏而言,留居内地在朝廷任职,不仅可以观光上朝,也是其家族的荣光。《宋史》载,至道二年(996年),向通汉上言: “五溪诸州连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为辰州墙壁,障护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虽僻处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诚,因兹郊礼,特加真命。”[5](P14174)太宗诏加向通汉检校司徒进封河内侯。天禧二年(1018年)二月,知辰州钱绛言,得富州刺史向通汉状,请纳疆土,举宗赴阙[6](P2100)。《宋史》亦说:“通汉上五溪地理图,愿留京师,上嘉美之,特授通汉检校太傅、本州防御使,还赐疆士,署其子光泽等三班职名。通汉再表欲留京师,不允,乃为光泽等求内地监临,及言岁赐衣,愿使者至本任,并从之。”[5](P14177)宋王朝对南江向氏的统治为此后经制南江埋下了伏笔,诸如授予向氏检校司徒进封河内侯这样的职官,便打破了以往只对边地蛮酋授予刺史之职的范例,对向氏加封中朝官职正说明宋王朝有意对南江蛮酋进行王化治理,这为此后章惇经制南江打下了基础。
宋王朝对南江蛮酋舒氏的治理更体现了其羁縻统治中以夷制夷的策略。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知元州舒君强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宋神宗令枢密院“加等推恩”招降峡州舒氏酋帅。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峡州军牙头首向真“说谕蛮人有劳,后为蛮舒光旦等驱略并屠其家”,以抗拒宋朝的招抚[3](P170)。但是,宋朝经制南江已是大势所趋,熙宁九年(1076年)冬十月,“归明人舒光禄等与贼斗杀,获首级,夺器械,及招降人户,兼光禄等领黔江城兵数次,共杀贼五十余级,并生擒首恶。诏舒光禄与右班直,添差沅州黔江城巡检”[6](P6807)。继舒光禄归附宋朝之后,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甲午,允州蛮舒光勇先纳土而逃,今诣州自陈[6](P6925)。舒氏通过平定南江诸蛮叛乱而得到朝廷的加官赐爵,原本是宋王朝以夷制夷羁縻统治的手段。如果说北江蛮酋归顺朝廷只以刺史授予之,而对南江舒氏的职官授予便具有了朝廷经制意味在内了,诸如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等中朝职官,便是为此后经制南江做铺垫。
三、宋代章惇经制南北江
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北方对外用兵,在南方也派兵深入湘西的南北江蛮地区,打算将其改造为正式政区。由于北宋王朝的不断征剿和内部相互攻杀,熙宁初年彭师晏知下溪州时,彭氏酋帅的势力已大大削弱,北宋王朝利用彭师晏等人“穷窘”之势,对北江之地大力经略。
时王安石秉政,命章惇察访荆湖北路,经制南、北江“蛮”事。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辰州布衣张翘上书曰:“江南蛮虽有十六州……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晏孱懦,众不畏服,争斗仇杀不已,皆有内向心。近师晏尝于辰州自陈,愿以石马镇(今湖南沅陵西北)一带疆土归化,乞乘机招纳,建城寨,定税赋。”[6](P5727)宋神宗采纳了张翘的建议,命领兵压境,密行招谕。接着,又诏荆湖北路转运司,北江下溪州已纳土,其每户合纳丁身粟米自熙宁十年为始,以下溪州之地直接隶于辰州治理,但是下溪州西北广大地区仍是羁縻之地。熙宁六年( 1073年)十二月辛巳,“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构言:招谕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宴内附,录其地里四至、户口以数闻”[6](P6059)。这是宋王朝意欲经制北江的计划,但经制北江困难重重。
相比北江地区,南江地区虽然豪酋大姓众多,但势力分散,易于各个击破,对于南江的经制比较顺利。章惇以荆湖北路为根据地,溯沅江而上,用“三路兵平懿、洽、鼎三州”,于是湘西正式入宋版图,并逐步改造为辰、沅、靖三州,归荆湖北路所领[10](P358)。《元丰九域志》卷六沅州条云:“熙宁七年 (1074年) 收复溪洞黔、衡、古、显、叙、峡、中胜、富、赢、绣、允、云、洽、俄、奖、晃、波、宜十七州,即唐叙、锦、奖州地置州。”[11](P275)其中所列实为十八州。
章惇经制南、北江以后,南江和北江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局面。北江除下溪州以外,大部地区仍是彭氏等大姓酋帅据有的羁縻之地,南江地区则建立经制沅州,由中央王朝直接派遣官员治理。先以“讨荡竹滩佶伶蛮之功”任李浩“知沅州”,接着又以辰州通判谢麟知沅州,兼缘边溪洞都巡检使,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沅州进行治理。
朝廷对南江的经济治理。章惇经制南江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沅州进行治理,例如置博易场与“蛮”人交易[3](P17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载,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诏荆湖北路转运司相度沅、锦、黔江口三处置博易场与蛮交易可否以闻。后本司委知沅州谢麟相度,麟言:‘置务博买,则均平物价,招抚蛮僚,新附之人,日渐驯熟,永息边患’。又下其事三司,时章惇领三司,亦以为便。”[6](P6225)把贸易作为沟通同“蛮”人的联系以求“永息边患”的重要途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诚州杨光富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并出租赋为汉民[5](P14197)。南江蛮为朝廷出租赋,一方面体现了对国家应负的义务,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对南江民族地区的经济盘剥。
在沅州建州学。《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熙宁八年( 1075年)三月,沅州奏:“比建州学,今听读者已多,乞赐国子监书,庶一变旧俗,皆为礼义之民。”[6](P6364)从之。由此可知,建立州学是要改变“蛮”俗,使之成为“礼义”之民,宋王朝开发南江地区以后开始礼仪之教,意即从文化上改造南江蛮成为“国民”。
保护外来人户在沅州经营田土。熙宁九年(1076年)夏四月,察访荆湖南、北路蒲宗孟言:“沅州官田并山畲、园宅等荒闲甚多,闻全、永、道、邵州人户往请射,其官吏以既籍充逐处保甲,遂令遣归。况保甲本欲藉其强力督奸盗,若舍贫就富,固当从所欲。乞下诸处,如人户往沅州请田土,毋得以保甲为名勾抽。”[6](P6704)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言,这就为外来人户迁入沅州提供了条件。
免沅州“归明人”秋税。熙宁九年(1076年)冬十月,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言:“沅州新归明人户实贫乏,乞除放去年倚阁秋税。”[6](P6809)从之。“倚阁”为暂停之意,沅州“新归明人”当是归附宋朝之“蛮”人。
在沅州行屯田之法。《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及新置沅州,有屯田之法,与广西事体相类。”[6](P6247)知沅州府麟上言,本州屯田务无军士应募,请依照配罪人于河州之法,配罪人于本州牢城,神宗从之,后来又将屯田改为募人租种。元丰元年( 1078年)六月,荆湖北路转运司言:“沅州屯田务自初兴至今,所收未尝敷额。若募人租种纳课,不费官本,利害甚明。乞朝廷详酌施行。”[6](P7092-7093)神宗从其请。这些措施沟通了南江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
四、余论
整体来说,宋代南北江治理大体是通过因俗而治等羁縻政策对南北江蛮酋进行笼络,然而羁縻统治并不能长久有效统治蛮夷地区,南北江蛮酋的叛服无常影响着宋王朝政局的安稳。当南北江蛮酋叛乱撼动宋王朝正统地位的时候,朝廷便派兵镇压,并对其地实施慢性王化策略。后来章惇开发南北江,由于南北江豪酋大姓势力不同,导致南北江的开发形成了不同结局,其中溪州地区走上了土司制度的发展道路,南江地区却没有。也就是说,北宋朝廷对南北江地区的开发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开发不彻底、治理有差异的地方。另外,学术界通常把南北江开发治理混为一谈,以为南北江很难分开,实际上南北江治理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别,对其分别研究更容易区分南北江治理的差异,从而为南北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不同历程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