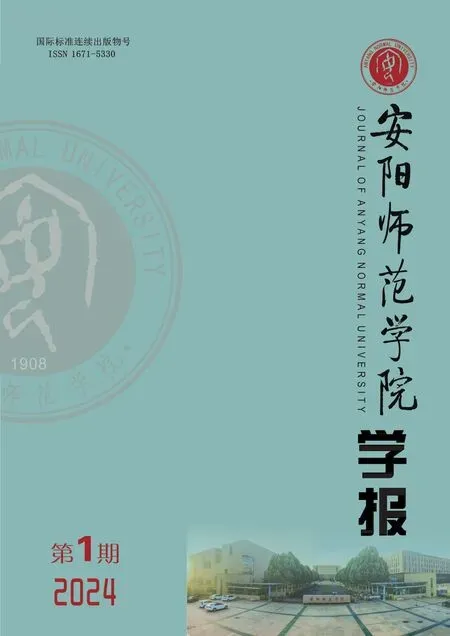论辽夏金的山岳崇拜
郭 恺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关于辽夏金的自然崇拜,如同王曾瑜先生的论断:“各民族几乎无例外地经历了原始宗教崇拜的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包括了对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湖海,以至动物、植物等的广泛崇拜。各民族以不同形式保留了此类崇拜。多神崇拜与宗教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多神崇拜往往并无专门的宗教团体或信徒。宋代祠庙往往有庙祝,‘无非假鬼神以疑众’。但庙祝们各据祠庙,并未如僧道那样组成宗教团体。多神崇拜流行于各民族社会的上层至下层,其仪式或耗资巨大,而劳民伤财,或简单朴素,而虔诚尽敬。多神崇拜往往是为祈求今世的福祉,而宗教更包括了对冥福的追求。”[1](P78)同一时代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之间,其自然崇拜的形式与内容往往是有所关联的,既有主观上疑众祈福的共性,又有客观上各自环境及发展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区别,辽夏金的山岳崇拜反映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意象塑造,汇聚成古代中国认知自然、开发自然、崇敬自然的人文精神。
一、山岳崇拜是辽夏金三朝族源圣地的象征
辽代的山岳崇拜直接反映着契丹民族依山而兴的历史,其中以契丹发祥地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都庵山、马盂山和木叶山最为典型。都庵山为契丹先祖奇首可汗降生处[2](P24),辽太祖时“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3](P8);辽太宗时“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4](P49),可见都庵山作为契丹族源圣地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马盂山、平地松林与木叶山的连线则书写了辽代影响力最深的族源神话,《辽史》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5](P445-446)尽管宋人编纂的《契丹国志》认为,契丹早期历史“远夷草昧,复无书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6](P3),但依然采用了马盂山和平地松林汇至木叶山的说法。赵国军先生认为,契丹祖源在马盂山,族源在木叶山[7](P336),在社会发展中民族属性开始强化并超越亲族属性。“白马青牛”神话的书写离不开部族迁徙前后的山川名号,这是契丹人用地理元素强调族源可信度的方式,同时这些山川也因神话的流传而不断神圣化,成为一个民族根基的象征。“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8](P397),此时的木叶山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行军前始祖神灵护佑的文化象征。
《北史》[9](P3192)《隋书》[10](P1845)《旧唐书》[11](P5290)《新唐书》[12](P6214)中称党项活动范围数千里,居于山谷之间。随着党项人不断内迁,此后正史中不再提及其依山而生,而在西夏立国后,山又被赋予了圣地的内涵。西夏文《夏圣根赞歌》中称其始祖源自“石城”“漠水”“白河”之地[13](P125),而其祖先“啰都”除了与《红史》中曼西山山神“格胡”相关外,亦有可能是借鉴了庐陵山神“山都”的传说[14](P30-41)。如《红史》[15](P23)《雅隆尊者教法史》[16](P26)《西藏王统记》[17](P13)《汉藏史籍》[18](P75)《新红史》[19](P47)《松巴佛教史》[20](P505)中,都称西夏源于曼西山(门西山、门喜山、闷日山、凉州和弭药嘎之间一山、色浦山),并有山神格胡(夏巫、毒龙、智呼、龙魔斯呼、妖龙默西)。按《红史》之说此山应位于北都和林附近,这也是元人建立西夏与北魏族源关系的一种方式。更晚的藏文史籍中此山又位于凉州或甘州多地,可知党项的族源圣山多为后世附会。不同于契丹和女真,党项人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迁徙,又有羌和鲜卑多源之争,很难使族源统合于一处具体的山。正因如此,《夏圣根赞歌》中的山河意象是超越自然实体的民族象征,只有当西夏灭国后,其具体的族源圣地才得以确立。
女真的族源圣地毫无疑问是长白山,长白山及其支脉在中国古代有“不咸山”“徒太山”“盖马大山”等称谓,至辽金时称“长白山”。作为发源地,辽时就将长白山和女真人并称,如辽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长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长来贡,乞授爵秩”[21](P170),至《金史》则更加明确了女真源流:“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22](P2)“金国之所起”[23](P2881)长白山是十分明确且历史积淀深厚的,因此并没有如辽代那般以塑造创世神话来强调,但反映的现象是一致的,就是山川已经从地理实体概念上升至民族源流的象征。长白山崇拜成为一种文化意象也是伴随着山神的塑造而逐步完善的,如《祭长白山神祝文》曰:“盖以发祥灵源,作镇东土,百神所寰,群玉之府。势王吾邦,日隆丕绪,祀典肇称,宠章时举。显显真封,岩岩祠宇,神之听之,永膺天祜。”[24](P342)
以山为族源圣地象征在中华民族发展中自古有之,黄帝在峚山“是食是飨”[25](P44),炎帝则“起于厉山”[26](P1472)。三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炎黄始祖有相当程度的认同:“辽之先,出自炎帝”[2](P24),另一说“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27](P466)。西夏文献中不仅有古代杰出人物黄帝,还有“五色帝”中的黄帝形象[28](P126-132),金代王浍则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29](P2366)。上述文献所载均是边疆多民族政权对中华文化的承袭,而山岳崇拜作为族源圣地象征即是华夏信仰中重要的寻根方式,山的恒定多产为孕育文明提供了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基础。
二、山岳崇拜是辽夏金三朝祭祀仪式的载体
陵庙作为古代中国祭祀仪式的重要场所,其建立体现着祭祀者“敬天法祖”的精神诉求。在宋人的记载中木叶山是辽太祖和辽太宗葬处,而木叶山上又建契丹始祖庙,包括奇首可汗南庙、可敦北庙、二圣并八子神像和白衣观音像等[5](P445-446),辽圣宗时“皇太后谒奇首可汗庙”[30](P135),可见始祖庙在辽代的重要地位。而木叶山作为祭祀仪式场所,同时也是祭祀对象,辽太祖、辽太宗和辽圣宗等均亲临木叶山,皇帝不能亲至则遣使祭祀或“望祠”,辽兴宗以后便多为“望祠”。辽代官方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十分正式,《辽史》中记载了历任皇帝祠木叶山的活动,除在位时间较短的辽世宗外,历代皇帝的祭祀从未间断。辽代早期,木叶山与“射鬼箭”等军事活动息息相关,从宋辽战争时辽方行军途中的活动来看,有祠天地兵神、祭旗鼓、射鬼箭和祭白马青牛等一系列仪式,祖先传说的神圣性与军仪的权威性不断融合,而木叶山始终是重要一环。辽穆宗之后,开始出现木叶山与潢水的共同祭祀,而辽景宗之后,柴册礼和再生礼等也开始与祠木叶山一并举行,此外又有“射柳枝”“唱番歌”“寄库”等习俗配合祭祀[31](P252,284)。辽代祭山仪属吉仪,“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32](P905),而传说遥辇胡剌可汗所制祭山仪又包括“西向祭祀”“树木悬牲”“绕行祭祀”“抛盏烧饭”等多个要素。辽天祚帝乾统六年(1106)“木叶山瑞云见”[33](P873),辽始行贺祥瑞仪,此外辽代又有魂归黑山的观念,学界大多认为其与乌桓赤山信仰相关。辽穆宗时祭祀黑山[34](P76,81),皇帝也曾亲至黑山狩猎。张国庆先生认为,辽代祭山习俗“纵源”来自契丹的“先源民族”乌桓,从“横源”来看,是吸收了中原汉族人的祭山文化习俗[35](P3-7),杂糅融合已经成为辽代崇山活动的必然趋势。随着辽代礼制建设的不断加深,木叶山等又承载着更多的文化内涵,祭祀正是外在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是辽代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
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于黑水建桥立敕碑:“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发)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36](P162)碑文表达了西夏仁宗祈祷诸神渴望免除水患的爱民之情,而诸神之首便是山神,反映了山对于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建桥立碑的仪式中,皇帝亲临躬祭更是凸显了朝廷对旱涝灾情的重视,祭祀对象以山神统领诸神,也是对自然万物的敬畏。诸神与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是紧密关联的整体,而山神是代表着依存根源的重要载体,正如西夏文《圣立义海》所言:“山根立地,接天合云。花草着色,远眺下方。野兽固守,诸鸟栖宿。珍宝本源,永泽不绝。”[37](P58)
女真人的崇山体现了更为明确的专属性和规范性,金朝建立后对长白山尊奉更甚,先后将其封为“兴国灵应王”(1172)和“开天弘圣帝”(1193)。对长白山和大房山的祭祀礼仪自然十分重视,作为兴王之地,朝廷对长白山封爵建庙,确定封册仪物和庙内外陈设,并颁册文,“每岁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38](P819-821)大房山作为帝陵宝地则敕封为“保陵公”(1181),礼节类如长白山。为山封号是金代崇山的一大特色,另如将静宁山(旺国崖)封为“镇安公”,将胡土白山(麻达葛山)封为“瑞圣公”等,以人格化圣山来适应中原的封祀体系。山岳崇拜的持续完善,既是金代政治建设的方向,也是古代中国礼仪不断关注民生的趋势。
辽夏金的山岳祭祀在部族习俗、消灾祷告和封爵颁文等方面可谓形色各异,但都反映出了祭祀者对广博自然的无限敬畏。“山川为天下衣食”[39](P101),朝廷借祭祀山岳来表达对属地民众的庇护,民众也将对山的依赖性转嫁到朝廷。自秦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后,“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40](P1357),这种思想无疑是三朝共同秉持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博爱包容的山岳信仰。
三、山岳崇拜是辽夏金三朝疆域认定的标识
契丹民族的兴盛始终围绕着土河与潢河二水流域,辽代的政治中心随着皇帝的“捺钵”移动。辽圣宗时“四时捺钵”成为定制,冬捺钵广平淀即在两河相汇处,其他季节的行宫也是以两河为中心向东北、西南和北部游行。因此两河流域一系列山脉成为辽代塑造圣山的对象,并不断增添新的仪式,此外作为游猎之地,辽圣宗和辽兴宗也曾亲至马盂山[41](P1060,1061)。木叶山是辽代四楼之南楼,关于木叶山的地理位置,学界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各县旗等地。之所以各家之言众多,一是由于文献记载中的矛盾难以调和,二是木叶山崇拜诞生于特定的时段,既无前承又无后继,若要从中华大地复杂的山系中循迹千年前的某一座山峰,除非文献文物多方证据充实,否则便不能妄下结论。不过这些考证共同反映出的问题是,辽代木叶山在自然实体层面并不十分突出,甚至因为其规模小或经历时间的冲刷而丧失特征,但也更衬托出木叶山在文化内涵层面上的特殊地位,即两河地区作为政治中心在古代中国疆域上开始活跃起来。此外,《辽史》称“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33](P879)宋人张舜民在《使辽录》中亦有“北塞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归此山”[42](P621)之说,直接将黑山与岱宗泰山类比,可见辽代也有如中原的五岳封祀体系。《洞天记》谓“黄帝画野分州,乃封五岳”[43](P43),所谓“画野”即是利用山岳标识疆域。木叶山之源起,黑山之魂归,此二山间便是契丹人内心的广阔疆域。
党项与契丹源于两河、兴于两河、扩于两河的情形完全不同,木叶山等无论具体在何处都是有迹可循的,而对于数次迁徙的党项来说,即便有族源圣山,也很难发展为专属的祭祀区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夏对山岳只停留在遥远模糊的追思,而是对境内之山赋予了新的尊崇。以兴庆为政治中心的西夏政权,缺乏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山,于是因势利导,以贺兰山为屏障,加帝陵处之尊,又有积雪山和焉支山等联结起河西疆域的脉络。特别是佛教“须弥山”“八山”等概念[14](P30-41),将山岳崇拜跨越到人力无法企及的层面,在自然分界的基础上又建立起坚实的心理“围墙”,以巩固这个深处内陆四面受压的疆域。依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所载,贺兰山和焉支山是西夏重要的犛牛产地,《圣立义海》又言:“冬夏降雪:番国三大山,冬夏降雪,日照不融,永积。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贺兰山尊:冬夏降雪,诸种林荫树果,芜荑药草皆有。诸种豹虎鹿獐固守,遮风蔽众。积雪大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界融,河水势长,番国灌水谷成也。焉山源上:冬夏降雪,炎夏不融。庶民耕灌寒地,大麦九月熟。羊马利养,马奶酒饮也。”[37](P58-59)李范文先生认为,若以“夏国三大山”划分,积雪山可对应祁连山;若以“番国三大山”划分,积雪山可对应岷山[37](P31-35)。西夏人特别崇尚有积雪的高山,正如西夏文谚语中所言“山中积雪者高,人中有德者尊”[44](P23)。在三大山中,贺兰山的地位较为尊贵,如西夏文《圣殿俱乐歌》所说的“宗祖庙堂之坚固,天之高处贺兰山”[45](P171),这与贺兰山地处西夏政治中心且帝王陵庙建于此关系密切。而山以安魂也体现在西夏谚语中,如“山谷鬼庙害日禳”[44](P10)。除三大山外,《圣立义海》所载的沙州圣山和天都山等也是西夏尊佛崇山的圣地,这些山岳共同构成了西夏对疆域神圣性的认定,“三大山”即是“五岳”的微缩翻版。
女真人所经历的迁徙历程明确,且深入中原腹地的程度也是最深的,特别是“长白山女真”这样的绑定早有定论,因此便具备了文化积淀优势,无需再多的穿凿附会。长白山、大房山和五岳五镇一同标识着金代广袤的疆域,中原岳镇为圣的观念在金代尤甚,混同江册文载:“盖古者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至有唐以来,遂享帝王之尊称,非直后世弥文,而崇德报功理亦有当然者。矧兹江源出于长白,经营帝乡,实相兴运,非锡以上公之号,则无以昭答神休。”[38](P821)大房山册文里亦有“仰惟岳镇古有秩序,皆载祀典,矧兹大房,礼可阙欤?”[38](P821)特别是在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和中镇霍山都进入金朝版图之后,金代的崇山活动逐步走向高潮。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所诏表明金代的山岳崇拜彻底中原化,诏曰:“礼官言:‘岳镇海渎,当以五郊迎气日祭之。’诏依典礼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东岳于泰安州、东镇于益都府、东海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渎大江于莱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岳于河南府、中镇霍山于平阳府。立秋,祭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望祭西海、西渎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岳恒山于定州、北镇医巫闾山于广宁府,望祭北海、北渎大济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明昌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淮为长源王,江为会源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46](P810)
作为新兴的内迁民族政权,辽夏金三朝以少数派面对陌生的中原文化,势必走向多元融合的道路。原始的游牧渔猎文化以及萨满宗教文化都贯穿其中,最终交汇为丰富多姿的中国山岳崇拜文化。这些民族携带着各自的文化记忆而迁徙,如清人看待天女配合生子:“魏圣武帝于山泽见天女,受命相偶。契丹祖与天女遇木叶山,生八子。”[47](P105)鲜卑和契丹等民族依山而居,自然依山而造圣,专属的神圣始祖因专属的地利而成,这是边疆民族内附后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体现。内迁后的民族大融合使山岳成为民众共同认定生活疆域的标识,至后世王朝如《大明一统志》所载,木叶山、长白山属山东布政司辽东都指挥使司,大房山属京师顺天府,马盂山属兀良哈,贺兰山属陕西布政司宁夏卫,焉支山属陕西布政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48](P1167)。三朝所崇拜的山岳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版图,是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边疆地域,扩展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
各民族对山岳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对人性的理解,如《圣立义海·山之名义》的结语:“山有神宰:山有诸宝,金银、树木、毒药,神护,成就出也。博士山名:高低宽窄,百尺之高山名成,谓习艺者博士已审也,故得名智者也。能蔽善恶:大山能隐善恶毒药,江河清浊有性,国家愚智混居。君覆于臣:豹虎离山则败,鹿獐堡中亡,智臣离心于君则得罪过也。德勤桥至:顶峰难行,勤以桥越。帝妙难言,巧智能言。山高隐秘:山高亦尘土,力增则大震。君亦闻德言则国威邦盛。”[37](P60-61)山既是蕴含广博的自然实体,也是复杂多变人心的象征,而以具象代抽象,是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便捷之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