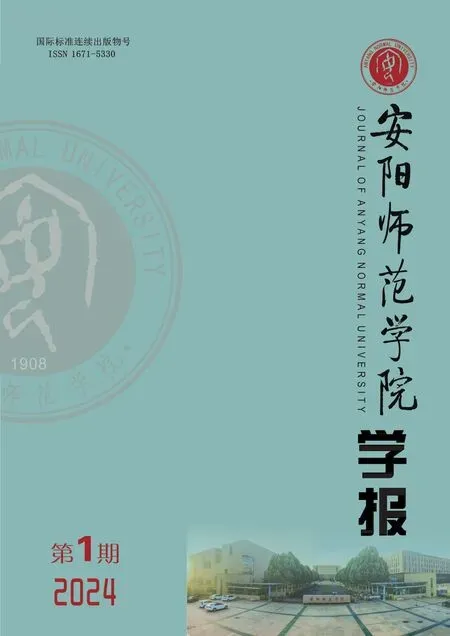西汉关中民众对秦朝的情感认同
——以司马迁为例
吴 涛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洛阳471934)
西汉王朝建立后定都关中,采取了以关中制关东的基本国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刘邦夺取天下过程中,依靠的基本力量就是关中民众。但刘邦本人又是秦王朝的终结者,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叙事中,刘邦被塑造成推翻暴秦的革命者,批评秦朝成为西汉的政治正确。而这对于关中百姓而言,显然是一种很矛盾的情结,毕竟秦是他们的故国,他们本是秦人。于是,在他们的国家认同中既接受现政权西汉王朝,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秦的留恋,这种情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着相当显著的体现。
一、关中地区对汉政权的接纳
战国七雄不同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他们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国家,虽说天下将会“定于一”是时人的共识,但战国百姓对各自所在国家也有很强烈的认同。在这一点上,秦国作为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秦人的国家认同自然也会比东方各国更为强烈。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关中秦人对秦的国家认同更是伴随着一种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西汉王朝便取代了秦王朝。
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在关中百姓的支持下,最终选择在关中定都。那么,关中百姓何以会接受一个昔日的敌人呢?
首先,西汉政权建立过程中并未对关中造成大规模破坏,关中百姓对刘邦心存好感。早在刘邦入关过程中,除蓝田战役外,并没有其他大规模的战争,“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1](P361)。而且根据“怀王之约”,率先入关的刘邦当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关中王,因而他在入关之时虽以秦为敌,但在子婴出降之后,刘邦就以关中之主自居,已经把关中视为自己的产业,他当然不会任由乱兵破坏,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刘邦的“约法三章”赢得了秦人的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1](P362)。
其次,项羽入关后的暴行更加坚定了秦人对刘邦的拥护。由于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人,项羽在入关之后,对秦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2](P315),结果“秦人大失望”[1](P365)。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2](P315)。就这样,项羽收获了满满的仇恨离开了关中。在此后三年的楚汉相争中,一次次被项羽打得大败的刘邦回到关中,都会得到关中百姓的大力支持,“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3](P2015)。楚汉相争已经不是刘邦和项羽个人之间的争斗,而成了关中子弟复仇的手段,关中百姓的大力支持,成为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
再次,在西汉政权建立后,原关中秦人的利益并未受损,以关中制关东的立国策略使得秦人成为西汉王朝依靠的中坚力量。刘邦称帝后,他最早属意的都城是洛阳,但在刘敬和张良的劝说下,刘邦决意定都关中。此后,以关中制关东成为西汉王朝的基本国策,关中地区成为最早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也是西汉王朝最为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4](P3262)早在楚汉相争时,大批秦人从军,他们成为西汉初年军功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刘邦称帝后分封为侯爵的一百多人中,关东籍将领占有很明显的优势,此外还有大批的士卒也因军功而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刘邦称帝后不久就公布了《复故田爵令》,其中规定:“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5](P54)事实上,这些中小军功者中,关中籍应当占大半(1)刘邦入关时有十万之众,去汉中时已经开始出现逃亡,之后的历次作战中,刘邦带到关中的十万人已经所剩无几。刘邦称帝时,刘邦军中虽说将领多为关东籍,但普通士兵应以关中子弟居多。。刘邦的《复故田爵令》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5](P54)秦灭六国时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主要渠道,因此,就刘邦此令中的“故爵”而言,最大的获益者也是关中百姓,关中百姓支持西汉新政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汉承秦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关中百姓对西汉政权的认同。西汉王朝基本上全面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不仅包括三公九卿、郡县制这些国家根本制度,也包括秦朝对历史合法性的论证。其他方面,如秦始皇统一后以“水德”自居,色尚黑,数用六,刘邦全盘接受了,秦朝的历法颛顼历也一直使用到汉武帝太初改历为止,文字、度量衡等也沿袭了秦制,这些举措都使得关中百姓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西汉政权。
总之,虽说西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终结者,但西汉王朝的建立得到了身为秦人后裔的关中百姓的支持,或者至少西汉政权是被关中百姓接纳了的,而这一点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所体现。司马迁祖上是秦朝名将司马错,作为秦人之后的司马家族在汉朝建立后也转而出仕新朝,司马迁本人二十多岁就出仕为郎中,后来继其父担任太史令。司马家族虽是秦人之后,但对西汉政权也是拥戴的,司马迁父子甚至认为,他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负有歌颂这个伟大时代的责任。司马谈临死之前对司马迁说道:“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6](P3295)司马迁也在解释其著述动机时称:“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6](P3299)虽说司马迁这段话是为了消除汉武帝的疑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司马迁当时的心声(2)虽说司马迁在遭遇了李陵之祸后,其撰述动机有所转变,由记录和歌颂一个伟大的时代转变为“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司马迁也并未否定西汉王朝的伟大,其“颂汉”的基本框架并未改变。。
二、西汉前期的反秦叙事
毕竟西汉王朝是建立在亡秦的废墟上,因此反秦叙事必然成为西汉前期主要的历史叙事。
在西汉王朝构建其合法性时,刘邦的反秦功绩是西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秦末群雄起兵时喊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在刘邦与郦食其的第一次见面中,反秦是他们最大的共识:“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7](P2692)刘邦入关后,也曾向关中父老宣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1](P362)刘邦称帝时,诸侯王上疏中所提及刘邦首要的功绩就是灭秦之功:“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5](P52)
在后世,刘邦灭秦之功也一再被人提及,比如汉景帝时,辕固生就以刘邦灭秦之功证明革命的合理性:“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8](P2123)
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反思中,亡秦又一再成为批判反思的对象。早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秦朝的暴政就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7](P2699)
在对秦政的反思中,贾谊的《过秦论》很具有代表性。贾谊曰:“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9](P278)
对秦政的批判最为激烈的当属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所上的《天人三策》中说:“自古以来,未有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10](P2504)秦朝的暴政体现在社会的诸多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严刑峻法,董仲舒认为:“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1](P328)在经济领域,秦朝的暴政表现就是民众负担的加重,“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12](P1137)。在社会风俗方面,秦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3)对这段史料(班固《汉书》卷五十八《董仲舒传》,第2510页),我们应当清楚的是,董仲舒批评秦朝的目的是为了述说当代,因而其言论未必反映了秦朝的真实情况,不可作为论证秦朝的直接材料来用。。
汉武帝时的谋士徐乐用“土崩”来形容秦末的局面,他说:“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13](P2805)
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叙事中,秦朝被贴上残暴的标签,人们言谈话语之间提到秦朝往往称之为“暴秦”“无道秦”,秦始皇本人更是被视为无道暴君的典型,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比如在贾山的《至言》中说,“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14](P2332)
纵观整个西汉王朝,无论是前期《公羊》学家的三统说,还是后期刘歆等人的五德终始说,秦朝的历史合法性被彻底否定。班固曾在《汉书·王莽传》结尾处说,无论秦朝还是王莽,虽然都曾经统治天下十余年,但那不过是“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15](P4194)
号称“实录”的《史记》,不仅如实记录了秦人的暴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西汉前期的反秦叙事。相对于西汉前期诸多文人言辞中的反秦仅限于情绪性宣泄,司马迁的《史记》如实记录了秦人暴政的详情。同时,司马迁本人也对秦朝二世而亡有所反思,他全文收录贾谊的《过秦论》就意味着他对贾谊观点的基本认同。
三、关中地区对秦政权的情感认同
虽说关中地区百姓对西汉政权的拥戴是真挚的,但作为秦人后裔,他们在接受反秦叙事的同时,又对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留恋等复杂感情,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早在秦末,群雄喊出“天下苦秦久矣”口号时,其实所谓的“天下”并不包括关中。首先,战国时期的混战中,秦人胜多败少,所谓“天下苦秦久矣”,假如仅仅是秦始皇称帝之后的十五年,称不上“久矣”。事实上,战国后期的百余年间,秦人基本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些战争留给东方各国百姓的是痛苦的记忆,而留给关中百姓的却是辉煌的回忆。其次,关中百姓也是秦灭六国的受益者,秦灭六国之后关中百姓以胜利者的心态看待东方各国,事实上他们也高人一等。近年来的出土材料证明,在秦朝的法律中,故秦人和新秦人的地位并不对等,所谓的故秦人是关中百姓,新秦人是原六国百姓。而且秦国的二十等爵也在秦灭六国后被推行到天下,东方各国百姓原有的爵位肯定是不会被秦人承认的。在国家统一后,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停止了,新秦人即便加入秦军,其获得军功爵位的可能性也很小。这样,有爵位的故秦人与没有爵位的新秦人之间的差距就更明显了。秦人的爵位又是与职位相关联的,没有爵位,或者说爵位不高的东方百姓出仕的几率不大,即便出仕也只能担任一些中下级的小吏。以刘邦所在的沛县为例,当地人萧何、曹参、刘邦等人,只能出任吏职,沛县县令却是秦人。萧、曹等人在密谋反秦时曾明确表示:“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1](P349)由此可知,当时关中百姓对秦王朝肯定是拥戴的,在秦末的动荡之中,关中没有发生一例反叛事件,这并非偶然。
西汉王朝建立后,作为秦人后裔的关中百姓,一方面支持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汉的反秦叙事;另一方面,作为秦人后裔,他们对秦的态度也不可能如关东百姓那样决绝,西汉一朝激烈批判秦政的言论大多出自关东人士之口,如贾谊、贾山、董仲舒、徐乐等。
身为秦人后裔的司马迁,他把对秦朝彻底的否定称之为“耳食”,他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16](P686)
第一,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功绩。在孟子眼中,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经是“无义战”了,战国时期的战争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17](P2722)。但是司马迁对秦人发动的这场持续百年的统一之战,有着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在《秦本纪》中详细罗列了秦人在秦孝公之后百余年间的一系列战争胜利,其用意不仅在于记录史实,也在于对秦人功绩的认可。再比如对秦将白起的态度,由于白起的一系列胜利是靠毫不留情地大规模屠杀完成的,白起甚至被关东人称为“人屠”,最后白起被迫自杀后,关东百姓肯定是欢呼雀跃的,而司马迁则是如实记录了秦人的态度,白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18](P2337)。至于秦灭六国的辉煌战绩,更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秦始皇的几篇刻石虽有自夸的成分,但秦灭六国的功绩却是事实,司马迁之所以详细记录这几篇刻石,显然也是认可秦始皇一统六合之功的。在司马迁的笔下,东方六国统治者的颟顸无能与秦人的积极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秦始皇和东方六国的亡国之君的对比更为鲜明。司马迁在《赵世家》中对赵国灭亡的评价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19](P1833)虽说司马迁也如实记录了东方各国的反抗,但并未给六国以同情。
第二,司马迁客观地记录了秦制所取得的成功。刘邦在入关之初曾经对关中父老说过:“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事实果真如此吗?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变法之后,“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0](P2231)。再者,由于推行郡县制,秦国已经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官僚制是秦制的基本构成。相对而言,东方各国也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也都具有了郡县制、官僚制的雏形,但秦国的变革更为彻底。那么,在秦国这一套政治体制下,其实行的是不是都是“苛法”呢?事实上,在战国的纷争中秦制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对秦法的严苛与专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就体现了他对专制的厌恶,但司马迁并非仅看到了秦制的缺陷,他也如实记录了秦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例如商鞅所设计的二十等爵制,使秦人焕发出巨大的战斗力,秦朝的客卿制,吸引了各国的杰出人才为秦所用。秦国的制度优势是秦人能在列国纷争中最后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统一的历史意义。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统一是大势所趋,他充分肯定了秦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在《魏世家》结尾处,司马迁的一段评语很能说明他的态度,“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21](P1864)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时,重点强调的也是统一,他说:“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6](P3302)正因为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所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例如,司马迁对项羽颇为欣赏,他能不以成败论英雄,把项羽列入本纪,但同时司马迁也认为,项羽任性的分封不合历史大势,成为项羽失败的关键。再如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制造了一个个冤狱。韩信在被刘邦俘获时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22](P2627)但司马迁站在统一的立场上,依然对韩信进行了批判:“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同辑),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22](P2630)促使司马迁做出这一评价的,不在于此案乃刘邦钦定,而在于司马迁对统一的执念。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对西汉王朝铲除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举措,都是持赞赏和肯定的态度,尽管这些诸侯王与西汉中央政府的矛盾冲突中,不乏“莫须有”的罪名。
第四,司马迁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在战国时期,东方各国对秦就持敌视的态度,比如鲁仲连把秦视为虎狼之国,他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23](P2461)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司马迁并不认同对秦的彻底否定,而是充分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给汉惠帝单独列本纪,反而写了《秦本纪》。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要把秦列入本纪,就是肯定其历史地位的表现,他说:“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6](P3302)这段话的重点在“昭襄业帝”,因为秦国数百年的发展奠定了秦始皇一统六合的根基。对秦始皇统一后所建立的秦朝,司马迁也认可了“五德终始”的观念,他认为秦上承周的木德而为水德,汉上承秦的水德而为土德。对汉文帝时丞相张苍认为汉应为水德这件事,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中说:“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24](P2682)司马迁本人的态度显而易见。
第五,司马迁对秦始皇本人也并非一味否定,在承认其过失的同时也肯定其功绩。如前所述,西汉建立后,秦始皇被很多人视为桀纣一样的暴君,但是司马迁却对秦始皇否定的同时也有所肯定,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不仅有贪婪、残暴的一面,也有其作为优秀政治家的一面。
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肯定,首先是其灭六国之功,此外还包括秦始皇卓越的政治能力和对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比如在秦始皇亲政之初,从容应对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的挑战,表现出高超的斗争水平。在《秦始皇本纪》中,我们还能看到秦始皇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比如他对尉缭的任用。秦始皇也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比如在灭楚过程中对老将王翦的任用。秦始皇的勤政,也是东方那些亡国之君所不能及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9](P258),常年如此不曾懈怠。
应该承认,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对秦有所肯定,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品质使然,也有其作为秦人后裔的情感因素。司马迁对秦的情感并不是孤立的个例,众多关中父老在口耳相传中也会不断重复先人曾经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中百姓对秦的情感也会逐渐淡化,例如,同样是关中人,班固在《汉书》中对秦的态度就与司马迁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