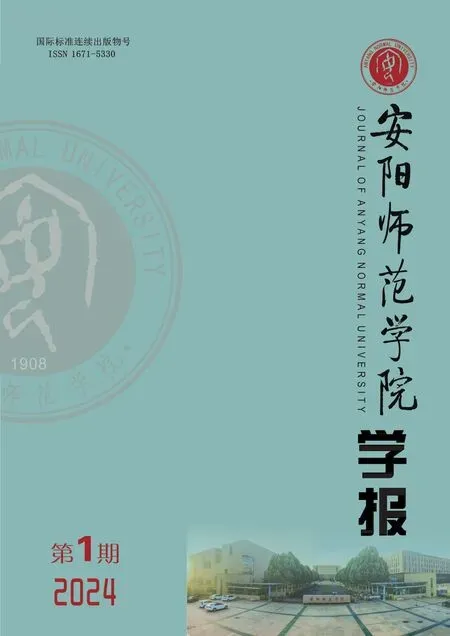君子的自居与处世
——从王弼《周易注》出发
何波宏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君子”是《周易》中重要的借喻载体与人格形象,其内涵既与先秦两汉儒学文本中的“君子”有相通之处,亦存在明显区别。在《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中,君子形象虽仍夹杂贵族色彩,但更多意指德行贵重、能力出众而又超乎常人之上并能推行圣人之道、利益家国的高尚之人,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1](P2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P52)。《周易》中的君子形象则与儒家所言君子有显著差异。首先,“君子”在《易》中虽亦可用于指称品格高尚的贤良之士,但该指称多在解说一爻或一卦中作为某种过程性论述环节出现。“君子”的品格未曾在《易》中被任何一卦独立讨论,亦不导向成贤作圣齐家治国的儒家价值观,毋宁说《易》与儒家典籍中的君子形象重合的部分多是某种为论述卦象意旨而作的必要叙述环节。其次,《易》所描绘的“君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被界定为伦理学意义的人格典范,而更多指涉在社会关系与人际网络中生存发展的具体人物。而且,不同于儒家有意弱化君子的阶级意涵,《易》中的君子形象明显具有贵族政治中上层士族的特点,如师卦“君子以容民畜众”[2](P256),谦卦“劳谦君子,万民服也”[2](P295)。最后,《易》中的君子有某种形而上的象征性,其既可指代上位之君、贤德之士,又超乎具体人物形象而用于描绘阴阳变化中万事万物的运转消长与时势变动中内在生命的自我调适。正因《易》中的君子形象存在以上复杂特征,才使王弼拥有一个不同于汉代儒教思想氛围的文本空间,进而摆脱形式化的道德训诫,并从超越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视角探讨君子的自居与处世之道。
王弼在对《易》中大量有关君子的卦象及爻辞的注解阐发里表现出其独特的君子观,并同时赋予君子形象以现实色彩与形上维度。一方面,王弼不再立足人皆有之的道德潜能谈论成为君子的可能性或君子在应然层面的道德境界,而是多将谈论对象指向魏晋现实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其代表如王弼时代的“正始名士”与紧随其后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拥有超乎常人的高贵人格与不俗的情趣眼界,又在乱世中面临艰难的生存处境,被卷入动乱的时局与复杂的政治架构。王弼既赞赏此类“君子”的高风亮节,又敏锐地觉察到不当的自我认知与生存方式可能为其带来的危险。在注释坤卦彖辞时,王弼所言“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2](P226),道出了特定情境中“君子”的生存窘态。另一方面,王弼淡化了君子一词的伦理内涵,代之以形而上的超越性,令关于君子的讨论突破德性论的藩篱,对接至周易所揭示的天地阴阳相互运作、生生不息的整体过程,以各卦所显现的抽象义理思辨与不同发展阶段论述君子的自我修养与为人处世之道。
王弼的讨论从君子的修身养性之道开始,他指出君子应涵养自身品德情操,但需时刻摈弃一己先见,承认一切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并在不同的时节与过程中顺势而为,以刚驭柔,以柔辅刚,而非固执己见、画地为牢,最终自居险境。接着,王弼探讨了君子的处世应物之道:其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P213),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君子并非逆来顺受,而应发挥自身能动性,积极有为地协调各类情状,在实践中促进良好的发展趋势并防患于未然。其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P226),君子的行动不应夹杂任何排他的主观立场,进而招致上下相争、万物失和,而应保持思想的虚空与开放,容纳一切更新中的差异性存在,谦和处下,如此方能不局限于一己之存有而通达天地万物的整体进程。其三,王弼特别提示了君子在现实社会与政治实践中的为人处事之法,即作为政治建筑的中间部分,文人士大夫在面对君主等“大人”时处于下位,而对平民百姓却是身处上位的统治者。这既要求君子保身求安,以阴顺阳,审时度势全其性命,又呼吁其以自身才能辅佐君主,保养百姓,以审慎的态度发挥自身主体性,将安邦利民的君子之道行于天下。
一、守德与顺时
王弼对君子之道的探讨首先聚焦于其自处之道,即形上层面的自我认知与生存方式。毋宁说君子如何对待天地间不尽相同的万事万变与社群中的世事人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与自身相处,如何看待自身在阴阳交替、四时更迭的宇宙整体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对世界及人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根源性探讨,在王弼看来对君子的待人接物有着举本统末的作用。
从王弼的相关注解出发,君子的自处之道由守德与顺时两部分组成。而对一己德行的呵护培育与顺应来往的差异环节二者之间并非是割裂对峙,而是互为其本、彼此转化。在《周易》中,最能彰显君子大公之德的一卦莫过于乾卦,乾卦六爻均为阳爻,代表作育群生、推行万有的天德。乾卦爻辞以龙设喻,以譬君子之德的尊贵崇高以及积极有为的强烈主动性。然而六爻皆阳的乾卦却在九五之后出现如是表达:“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2](P212)王弼注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2](P212)在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是王弼对“亢龙,有悔”的解说——“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上九是乾卦的最后一爻,从整体卦象着眼,万物各尽其极自由生长,而以上九一爻言之,其置身一卦之终,下五爻皆为阳,位居最上的上九若自恃高位以己为尊,将破坏乾卦整体的通畅与和谐,并因凸显自我而阳刚至极、缺乏通情达理的柔顺,断绝与其他各爻的往来而从整体中脱落。因此,王弼认为哪怕在至刚至健的乾卦中,都不能令自身过于煊赫而背离万事万物各不相害、彼此转化的和谐过程。且对于真正效法天德的君子,这种对一己盛德的克制乃是自然而然的,王弼将其解读为“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意焉”。
何谓“天德”?其与一般意义的“人德”有何不同?“亢龙有悔”的上九爻可象征常人对德行的理解。在其认知中,尊贵之士的德行应得到积极地颂扬与展示,引领其他无德或少德之人。正如上九爻位居众爻之上,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或是此类认知的相近表达。而在王弼周易注的语境下,如此招摇高调的道德观不仅从实践角度而言有害(亢龙有悔),而且背离德行的真实内涵。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3](P85)无论德性论者推崇的理想人格何等完备,只要其将一己价值理念视作普遍标准,产生越出自我规范他者的冲动,则非但不能促成更大的善,反而将破坏以差异为基本特征的万事万物各得其宜的自然与和谐。而“见群龙无首,吉”,乃是形容整个乾卦中表露的天德及能体会此德的君子吉利的人生处境。乾分六爻,完全由象征进取与发展的阳爻构成,而从整体卦象着眼,各爻相辅相成,分居其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中心。六爻各尽其极充分释放自身——而令其得以发育进展的天无形无象,因其不产生任何阻碍他者发育的排他性,反而将诸多差异形式源源不断地纳入自身,令其获得成立依据。如此,在天的运行下,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如群龙或潜或出,而没有任何绝对的道德标准或终极目的为其立法,此即“群龙无首”。而君子能“见”此卦象,则能“用天德”,其对自我主体性与异于自身的他者的看法也发生改变。王弼说:“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飞龙’也。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2](P213)王弼将“用九”与“见群龙无首”结合,认为“天行健”之“健”是“用形”之意,天下万物的局限性来自其“形”,万物形态各异,因此相互排斥,操心于保持自我形象的同一且意欲征服他者。但越是如此,其越无法摆脱既定形式加与其身的被动性,因而形是“物之累”。君子同样有形有质,其特殊形态带来的排他性亦有妨碍整体性认知的获取之弊。然而当君子效法天之德以“用形”时,思想视野随即改变:天无常形,而是不断以其运行促成诸有形现实的发展与浮现。作为万有之极的天在该过程中不对更新发育中的任何存在物施加控制或居于其上,也正因如此,天却令自身“无亏”而促成一切刚健之物的运行而成为事实层面的万物之首。因此,当君子放弃任何可能引发对立与排异的观念或立场时,即能效法天德,顺应不同事物的具体发展环节并更新自我,在所处时势中应机而动,与天地阴阳的变化转换保持一致,因而在保全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与天同德。王夫之在注解此卦时亦言:“君子之安其序也,必因其时。”[4](P6)而此德之所以需“守”而不可“用”,原因在于所用为“形”。德之所以需“守”,是因为此“德”来自于对乾卦中天之象的体认,需在顺时而行的同时保守此德,不因顺应各发展环节而泯灭自身主动性。德之所以不可“用”,在于以德施于物将造成主客双方的对立与紧张,而自守其德,与四时百物共生同进则最大化地实现了“自强不息”的卦义。王弼以为“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本质上皆是形容“乘变化而御大器”的过程,即守德与顺时的统一。以王弼的说法,“静专动直,不失大和”,此处“静专”即得天德于心,常存不失;“动直”即乘时而行,无有阻碍。如此方为“大和”。
二、有为与虚待
若王弼以乾卦破题,阐述君子形而上的自我认知与修养原则,则其随后便顺此话头论述了君子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境中应对人情世故,掌握待人接物的尺度并令其德行润物无声、行于世间。结合《周易》具体丰富的卦象与王弼的相关阐释,君子处世应物的原则大致可归纳为有为与虚待的结合。
若乾卦以天之无形广阔象征了君子之德在其修养实践中伴随万事万物的伸张发育周遍无碍,则坤卦即以地方正有型、轮廓鲜明的特征刻画出具体生存情境下个体生命直面的重重被动性与其主动性或不得已的随顺与收敛。从乾到坤,抽象的生存论落实为君子在具体情势中须谨慎遵行的现实之理。坤卦所象之地之所以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在王弼看来是因为地的方正之形本质为刚——天健顺刚强,却又无形无象,其德如飞龙周游无碍,而地居下处卑,六爻皆阴,然而却是方正严整、遍布各异的具体地貌而刚烈难化。因此坤卦虽为至阴,却内含纯阳之性,象征着生活于具体社会环境、历史节点中的君子不得不面对的异己之物与时运情状。王弼的注解精准地把握到了坤卦以柔行刚、阴中含阳的特征,他说:“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两雄必争,二主必危。有地之形,与刚健为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顺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马,利之不以永贞,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2](P226)自身有形的地恰如现实生活中作为有限的关系个体而待人接物的君子,而地与其上万物的相处之道即“至顺”——这并不是警惕于万物可能遭受的阻碍而顺时而行,而是为避免自身与现实中的刚强之物相克相争而自觉地收敛主见与锋芒,以开放与顺应的姿态迎合居于阳位的刚劲之物,经由其发展实现自身价值,而非身处下位却与上相争,造成“龙战于野”的局面。之所以以母马象征地之德,是因为“马,在下而行之者也,而又牝焉,顺之至也”[2](P225)。马是骑乘之物,在人之下,而母马象征阴柔,更是柔顺在下之物。在王弼看来,这是有形有象之地与万物的相处之道,它主动居于万有之下,以至大之形托举万有,始终保持自身的谦下与开放,以柔顺之道应和一切旺盛张扬的有形之物。然而这种顺应的结果却是促成地极大之形的持续,令其“永保无疆”,地亦未因处下守虚而丧失其主体性,而是因与物无争而令自身主体性一以贯之,“柔顺利贞”。这事实上揭示出君子法地而厚德载物、柔顺处下的虚待并非“柔而又圆”,而是有地本性之方刚为基础,在柔顺待时中既尊重显赫刚强之物的特性与需求,又善寻时机进取有为,令阳刚之物获得承载并在阴柔之道中开放自身,以不至过刚而折、亢龙有悔。因此,地之永贞与君子之虚待实将导向事实层面的有为——“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地因其至方至正而须柔,而若效法其柔的君子因此丧失柔中之刚,即将本末倒置,背离地的永贞之德。
柔中含刚、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实的君子之道源出坤卦,而在周易的其他卦象及王弼的注解中亦能晓见此意。泰卦卦象乾下坤上,至阳之乾在下而至阴之坤居上,既代表阴对阳的暗中作用,亦象征在上卦的柔顺之德覆盖下下卦中天道的通畅无阻,因此“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2](P276)。《老子》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太”通“泰”)。”[2](P87-88)泰卦呈现出阴阳相通、积极奋发的天道与守虚处弱的地道往来结合之时吉祥顺遂的趋向,王弼注曰:“泰者,物大通之时也。上下大通,则物失其节,故财成而辅相,以左右民也。”[2](P276)物之通源自上阴下阳的卦象,阴居上而欲下,阳在下而上涌,在君子的虚待与顺应之下有形万物不再与其为敌而“失其节”,君子因此得以与其亲近,通过主动的引导与辅佐将其导向良好的发展方向,顺应其特质而不以阳刚之道与其相争。“左右”既代表辅佐、护佑,又象征改变、影响,表面似与小人阿谀奉承之道相近,实则“内君子而外小人”,通过处下无争贴近万物,以君子之道调和纯阳之性的刚劲易折,令其通达无碍、向他者开放自身。如此,君子虽以阴柔之体虚待,却身居上位而就阳,促成诸存在物的沟通与共存,泰卦中的六五爻便正应此意:“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2](P278)按王弼的一贯解易原则,三五爻各在一爻之上,是为阳位,五更是至阳之位。而泰卦中六五上下皆为阴爻,其身居高位却以阴为体,向下方的九二爻委身倾斜,以喻君子之应物秉性柔顺、虚己待物,然而却身居高位向下影响九二之阳,实是一种恰当的有为。王弼曰:“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中行愿,不失其礼。帝乙归妹,诚合斯义。履顺居中,行愿以祉。”[2](P278)该爻以“帝乙归妹”设喻,卦象为尊贵之女下嫁,正如君子身居正位,自愿降身谦卑,以阴配阳,通过积极的行动贴合刚健而处下的九二爻,令其与君子之德相配并与在上的他者相通,避免龙战于野的冲突。
结合有为与虚待的君子既不会与他人或他物相抗,亦不会因委身于他者而削弱自身能动性,而是在二者的平衡中获得民众的仰赖与万物的归顺。此意在王弼对谦卦的注解中有充分的表述,他认为谦卦为吉卦,其卦体艮下坤上,地居山上,山本在地之上,而退居地之下,是为谦之喻。此卦中,君子因柔顺与虚待而产生的主动性与号召力得以呈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2](P295)此卦除九三外,余爻皆为阴,按王弼所言,则“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2](P591),且谦卦与履卦为独爻卦已被前代学者证实[5](P58)。因此九三为一卦之主,象征谦和的君子,而君子“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虽谦和应物,却在此卦中作为唯一的九三上位之爻存在,尊贵光明。虽在上爻之下而不可逾越侵犯,却是“君子之终”,即结合有为与虚待的君子以自身言行达成的现实效果。九三爻辞为“劳谦,君子有终,吉”,王弼注曰:“处下体之极,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众阴所宗,尊莫先焉。居谦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劳谦匪解,是以吉也。”[2](P295)
作为六爻中唯一的阳爻,九三居于下卦之阳位,承接上下诸爻,协调其关系。君子看似在虚待与谦顺中处下,却令万物万民都依赖于君子的沟通协调为其带来的阴柔之益,因此一切通顺与和谐(五处阴爻)的产生都有赖九三之位的君子。君子自愿处下而不争五之尊位,却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而为“众阴所宗”,进而“尊莫先焉”。通过谦卦的注解,王弼进一步阐明了《易》中君子的为人处事之道产生的现实效益,也令源自坤卦的虚待与有为之道有了更为完整的论述逻辑。
三、保身与行道
在探讨君子的自我认知与具体处世之道后,王弼在《周易注》中重点关注了一种现实关系,即魏晋时代身为君子的文人士大夫在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在保全自我的同时又无愧其所在的位分,并在身居下位、面对位高权重者时既能明哲保身、避免与之对立,又能以适当的方式发挥自我才能,辅佐上位者推行正道,这是学会自处与应世的君子需进一步处理的重要关系。一方面,君子对自身的认知从内在德行转向其士大夫的外在阶层地位;另一方面,普遍的交往之道聚焦至兼具文人与官僚双重身份的中国传统士人不得不面对的政治实践与君臣关系。
王弼在相关解易文本中,提出了保身与行道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居于臣位的君子虽有齐家治国之志、知是知非之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直言不讳地表达一己志向,而须明确其臣子身份,以卑顺之道保全自身。同时,作为君子还须审时度势,时机成熟方可有所行动,否则将有性命之忧。履卦警示了君子身在臣位,却贸然行事、邀功夺主带来的危险。履卦乾上兑下,五爻皆为阳,唯有六三为阴,其彖辞云:“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2](P272)全卦中六三居下卦之顶,又承接乾卦,以柔履刚,应和诸阳爻,因此得保平安。从全卦着眼,此非凶卦,然而就六三爻一爻而言,其体却凶:“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王弼注:“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志在刚健,不修(循)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顽之甚也。”[2](P273)履卦卦象凶险,五处皆阳,而唯一的阴爻却身居阳位,自身资质卑下却擅居六三,因此将如踩踏食人猛虎之尾般招致灾祸。若以卑居尊,以下犯上还因此自鸣得意,就如同视力模糊之人以为自己能辨光明,跛足之人认为自己能够行走般不智。其身在下位却觊觎九五尊位,欲凌驾于刚强之物之上,仿佛武夫在君主面前肆意妄为,终将自取灭亡。因此,若王弼对乾坤二卦的论述多从形上义理层面劝诫君子谦和顺随,其对履卦的解读则从现实后果上警示了以卑履尊、以弱犯强的不智。
与履卦的凶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师卦,师卦卦象与履卦相左,坤上坎下,五阴一阳,阳在九二,以尊贵之身居于下位,应和六五,是为吉卦。其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2](P256)师卦描绘了作为军队首领的君子领军打仗的场面,卦象所示水在地间用以比喻君子以其德行广施治理、众民归附。因此,此卦不仅展现了君子恭顺有礼、与六五之主同心同德的君臣之义,更预示良好的政治关系下君子率先垂范、引领人民的可能性。九二爻辞曰:“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王弼注:“以刚居中,而应于五,在师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宠,为师之主,无功则凶,故吉乃无咎也。行师得吉,莫善怀邦,邦怀众服,锡莫重焉,故乃得成命。”[2](P256)九二为全卦唯一的阳爻,寓意君子领兵出征,其德行贵重(体性为阳),却居于九二,甘愿置身六三之下,因此谦卑有礼。然而其居于下卦中位,以阳统阴,诸阴爻事实上为其掌握。而因其不履尊位,方能与六五相通,即居于尊位却体性阴柔缺乏刚健之气的六五委托九二统御全卦,而不担心其僭越冒犯,是以“三锡命”于君子。也就是说,只有在谨慎行事与上位者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君子才能展现积极有为的一面,如同行军得胜般以自身德行与实践智慧治理百姓,最终既赢得“邦怀众服”的声誉,又拥有君主“锡莫重焉”的信任。
因此,君子为人臣子,既须有所作为、行道于天下,又需在此过程中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等待恰当的时机与条件,避免唐突冒进、损伤自身。当然了,身为士大夫官僚的君子亦是民之父母,其在施政于民、教养百姓的过程中亦需贯彻内刚外柔的原则,在有所作为的同时顺应百姓的实际需求,以无为柔顺之道保障百姓的休养生息,潜移默化令天地之德行于万民,王弼在对临卦的注解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临卦上坤下兑,地临于泽,象征君子居于上位以德护民,而九一与九二两爻亦代表“阳转进长,阴道日消;君子日长,小人日消”[2](P311)。王弼在该处罕见地使用了“小人”一词,而“小人日消”并非君子与其相斗的结果,而是由于君子临于百姓、以德养民而令奸佞之人无从产生。临卦之象“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王弼注曰:“相临之道,莫若说顺也。不恃威制,得物之诚,故物无违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也。”[6](P255)可见,无论是对上位之君还是下位之民,君子均需谦和顺应,在接纳其真实情状的前提下协助其生存发展。君子居高临下,临的上卦却为秉柔顺之德的坤卦,因此君子永远以其言教利益百姓,如大地容纳保护万民。即便如魏晋名士不居尊位,游走庙堂江湖之间,亦能行德保民、泽被一方,是为六四爻所言“六四,至临,无咎”,王弼注:“处顺应阳,不忌刚长,而乃应之,履得其位,尽其至者也。刚胜则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2](P312)六四在六五之下,非为尊位,却以阴爻处正位,为上卦第一爻。因此,其居上而应阳爻,虽谦和柔顺、不居高处却身在正位,既有不惧刚强的品德,又有虚己应物的智慧。此即王弼通过注解周易各卦,呈现出的立体鲜活、融保身与行道于一体的君子形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弼从立足君子自身修养的守德与顺时过渡到待人接物的有为与虚待,最终详细探究了身为士人大夫的君子如何结合保身与行道的原则进行社会治理与政治实践。其思想既有超越的形上维度,又蕴含深切的现实关怀,在批判继承前代儒家思想合理因素的同时,又对周易文本加以创造性地阐发,扩充了君子之道的哲学意蕴,为后代郭象的内圣外王之学与宋明理学的相关论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