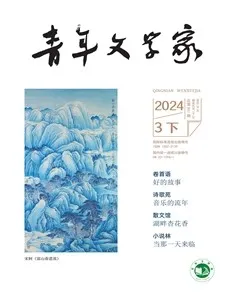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创作影视化特征研究
杨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說改编影视剧的现象非常常见。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受众广泛的娱乐方式,对其他艺术的影响日益明显,尤其是对文学创作。众多作家开始从影视作品中寻找创作灵感,影视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的挪用越来越明显。以王朔为代表的作家,在影视联姻方面表现得尤为成功,出现了著名的“王朔现象”,即王朔每部作品改编成影视剧都非常成功,这些对当代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刘震云的影视化小说创作也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以上种种都为文学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文学与影视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各具创作独特性,将影视技巧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将以刘震云的小说影视改编(即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影视改编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及渗透。
一、影视成为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
影视对文学的影响集中在小说这类体裁。小说强调叙事,这是其与影视产生联系的重要原因。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很多,日常生活经验成为文学创作素材的首选。但是,影视作品的丰富性、娱乐性同样带给作家们创作的灵感。麦家在创作小说《捕风者》时就直言不讳:“如果一定要问出处,勉强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另一个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徐则臣在北影大讲堂讲座时提出:“我在电影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写小说《北上》中有些开阔的场景时,我的脑子里有非常清晰的意识,觉得这是一个俯拍的镜头,那是长镜头,又或是正反打镜头,所以今天如果有哪个小说家敢说自己完全没有从电影中汲取养分,我觉得这是一个虚伪的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影视的喜好会因为影视作品中的一个细节或一个段落,促使作家开始创作,客观经验在这里已经被影视作品代替,成为作家灵感来源之一。
二、影视技巧运用在文学创作中
循着影视带来的灵感,作家们也看到了影视创作规律同样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来,这可以丰富文学创作的内容,并丰富文学创作的技巧,满足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要求。众多作家因为参与了影视创作,很容易就顺手将影视镜头语言直接转译成文字叙述。
首先,最简单也最明显的表现即对话的增多。在这方面,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通篇存在大量人物对话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不能不说受到了电影的影响。同时,刘震云的代表作《手机》也是先改编成电影剧本后才创作的小说。《手机》和《一腔废话》这两部作品包含了大量人物对话。这些对话的运用成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必要元素,同时也是作家有意地模拟电影场景的结果。例如,在小说《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用自杀威胁工头时就有这样一段对话:“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演得太好了。又问任保良:‘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鸡撒了一地:‘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人不用找了,就是他!”从以上内容能够看出,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这样在人物对话时将人物动作、道具直接表现的情况,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文本可以直接运用到影视剧本中。反过来更为准确地说,是他的小说受到了影视的影响,小说中使用大量的人物对话是一种影视化的叙事策略。而且,小说中的对话处理也是简洁直接,绝不拖泥带水,少写人物的表情和心理活动,以一种更加直观、直接的方式呈现了故事情节。
其次,除对话的增多外,情节的戏剧化也是小说创作影视化的明显表现。追求故事性,注意偶然与巧合来推动情节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又一明显特征。例如,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存在着大量的戏剧化的情节,这些偶然的巧合包括:严守一约定与情人伍月最后一次见面;严守一当日将手机忘在家中;从不主动联系的伍月打来电话;妻子于文娟串休在家;严守一发现手机不在身边回家侥幸拿回手机,心虚关掉手机;老家奶奶要和严守一通话;妻子联系不到严守一,联系费墨;费墨与妻子吵架,气头上说漏了嘴,打电话给严守一补救时却让于文娟接听到了;严守一继续撒谎,却赶上伍月发来了暧昧短信。一连串的失误和巧合将说谎者严守一步一步逼到绝境。
因为作家先创作了电影剧本,所以这段文字明显强调戏剧的偶然与巧合因素,影视化痕迹尤为明显。同样在《我叫刘跃进》中,也是因为刘跃进寻找自己的包,开始了一系列离奇的情节。显然,这种文本创作为后来的剧本改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样也是影视化思维对文学创作的明显影响。
再次,文学作品更加注意画面感的营造。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电影基本上是一种视觉艺术。显然,作为视觉艺术的影视依赖的是声色光影的综合表现,即图像的呈现。由于受到影视的影响,文学作品越来越注意画面感的表现。例如,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写道:“胡同底有间屋子,房门就开向胡同。墙上的石灰缝,横七竖八,抹得跟花瓜似的……”再如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中写道:“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生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天终于黑尽。”以上叙述可以直接作为影视剧本呈现的画面,由此我们能够看出,作家们重视通过文字来对画面进行表现,这些都是影视作品中的视觉性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借用。
最后,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文学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如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心理蒙太奇等手法。传统小说一般运用线性叙事方法,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故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叙事上进行了更多实验性的尝试。于是,蒙太奇就被大量地运用到了小说创作中来。作家们对这种手法越来越熟悉,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例如,刘震云小说《我叫刘跃进》,作家已经超越古代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简单的平行叙事方法,使用至少三条线索在不断地平行和交叉中展开故事,制造了足够的悬念,显得故事精彩异常。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时间线索,更多地按照空间的变换,由刘跃进、青面兽杨志、严格三人作为线索。因为小说章节均以人名命名,所以在故事展开时,按照三人的行动及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交错展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八章结束。直至侦探老邢出现之后,这种平行、交叉的故事线索才结束,回到了统一的时空中,展开下一步的叙事中。再如严歌苓,她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的频率非常高,可能在其创作中就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了改编的便利性,于是,蒙太奇技巧就在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例如,小说《陆犯焉识》中至少出现了三种蒙太奇手法。首先,平行蒙太奇的运用。小说以1954年为界,讲述了祖父入狱前后的生活,将入狱前后的两种生活状态不断地进行比较,两条线各自展开,最后又汇聚到一起,由此向人们展示了祖父在20世纪的波折命运,时代巨变以及小人物命运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其次,心理蒙太奇的运用,即按照人物的心理活动,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任意在现在与过去的时空中交替展开叙事。例如,小说先由关键物品—一块手表的来源说起,再跳到1960年手表被换成几个鸡蛋,再跳到多年前祖父对祖母的对视而引发了此后的感情纠葛,再跳到祖父在收到手表的当天故事,到此终结故事,后来继续转移到了叙事者—“我”的视角,展开了又一段联想,即关于垦荒情节的描写,同时又随机插入了几个人物,帮助完成叙事。这样的文字叙述,仿佛是一部影视剧一样,完全不受时空限制,随意地闪回或闪前,展现了主人公—祖父艰难而波折的一生。最后,隐喻蒙太奇的运用。这与象征手法运用十分相似。在小说中,隐喻蒙太奇的承载物是那块“欧米茄”手表,它承担了丰富的信息:对祖母而言,它是她爱情与幸福的见证;对于祖父而言,它就成为一个枷锁,不得已接受手表,即接受不得已的婚姻,此后这块手表也伴随着他不幸的生活,最终又戏剧性地变成祖父对祖母爱的见证。一段错位的爱情,一个时代巨变下知识分子的艰难追寻,一块手表承载了太多的内涵。
当然,影视和文学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一直存在,这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挑战,文学创作的革新是否要一直依赖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的传播是否要依赖影视?文学作品是否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如果文学创作一直强调影视化特征,作家与读者都满足于图像带来的感官刺激,缺少理性思辨,感性美学逐渐成为潮流,这样的文化现象我们是否能够面对?影视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
文学作品借助影视传播后发行量确实在增加,但是文学创作的水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视觉狂欢,让文学作品失去了独立性,尤其是快餐式阅读时代的到来,传统意义的阅读者不断减少。视觉化的写作让读者渐渐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影视化思维也影响了“读者”们的阅读习惯,即传统文学中的抒情、描写方式逐渐被他们厌弃。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每种艺术都需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影视化思維越来越被重视,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文学思维的削弱。会有一些作家用影视剧本的方式代替小说原来的创作形式,这样的做法无疑让文学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单薄、浅显。当然,进入21世纪后,我们看到传统的精英写作一直在艰难地行进。一些清醒的作家意识到了问题,试图摆脱影视化创作的弊端,执拗地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例如,莫言、苏童等诸多作家,在与第五代导演多次合作后就有了很深的感触。苏童在谈到与张艺谋合作剧本《武则天》后就提出:“这个长篇写得很臭,我不愿意谈它。我的小说从根本上排斥一种历史小说的写法,而《武则天》恰恰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它跟我希望的那种创作状态多么不一样,而且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想,不能虚构,武则天这么个人物不好去虚构她的。结果吃力不讨好,命题作文不能作,作不好。”(《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莫言也提到:“一个小说家不应该跟在导演的屁股后边,他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应该是导演来找小说家,不应该是小说家去迎合导演。”文学创作影视化现象确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常见的文化现象,且这种现象也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文学创作应始终把文学性放在首要位置,可以运用电影技巧为文学服务,提高文学创作的艺术魅力,而不是让文学创作单方面成为电影作品的垫脚石。只有注意影视与文学的互动,才能够推动影视与文学的共同进步。
本文系长春光华学院科研基金培育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现象研究”(项目编号:QNXS202301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