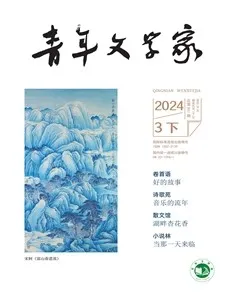探究中国现代新诗的西方诗歌传统
谭星瑶
诗人的创作离不开他们自己的传统,在我们早期的理解中,传统似乎只是指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传统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本民族的传统和向其他民族的传统借鉴的部分。对于中国现代新诗来说,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诗歌创作和西方诗歌文化都是它们起源的传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传统的作用又各不相同。一百多年前,中國第一批诗人在西方诗歌传统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他们把新诗歌视为中国新诗歌发展的机遇和路径。因此,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全面翻译和介绍西方诗人的创作和理论,并将西方诗歌的经验和理论应用到自己的诗歌中。
西方的传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大地,入乡随俗地在东方的土壤上发生了变异,有了不同的特质。现代性已经在中国发生了,而且已过百年,它以乘风破浪的势头形成了一个自觉的传统,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写作。“世界诗已进入我们,我们也进入了世界诗,的确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诗存在,这里没有纯中国诗,也没有纯西方诗,只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只有一种共通的语境。”(柏桦《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
一、哲学主题:对人与时代的思考
在西方,诗歌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是自我精神的升华,而不是诗人思想情感的现实性平面展示。诗歌不是平凡的,诗人也不是平庸的,诗歌是人类的精神追求,诗人是不断超越于自我和现实而进入另一个更完美的精神世界的人。只不过,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
诗人北岛在翻译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时,由后者诗歌中所体现出的使命感,常常联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他对西方哲学母题的继承,如曼德尔施塔姆描写但丁:“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伊里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而北岛认为,在这段话中,爱伦堡所说的其实是一种外在的命运,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或者说担当、责任。外在的命运和内在的使命之间往往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就像是一对两生花。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不可避免地是要受命运的苦的,他们必然将在某个时刻与命运作斗争,并最终引导外在的命运。
这样的使命感同样也体现在北岛的创作中,以《白日梦》为例,“住在钟里的人们/带着摆动的心脏奔走”,“风暴,我们是/迷失在航空港里的儿童/总想大哭一场”,“总是人,俯首听命于/说教、仿效、争斗/和他们的尊严”。这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心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这是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经验和感受。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地解释诗人在说什么,我们可以确认诗人是不言自明的,是个人与群体,是当下与永恒,是历史与真理。所以,诗人不仅是在表达个人的痛苦,也是在研究人类的生命。
这样的诗歌,它不再是个人对个人生存权利和人的生命的渴望和控诉,而是对现代生存的冷酷反思和哲学探究。优秀的朦胧诗人已经从批判社会和道德转向关注人类生存状况。正是像北岛这样的诗人对人类生存的“终极探索”,使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和传统的“风语者”。
二、美学传统:音乐美与节奏感
诗歌是一种被寄托了韵律的文学。北岛认为,一首诗中最难翻译的部分就是音乐,几乎不可能被完美还原,除非翻译者在别的语言中再造另一种音乐。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它具有这一特点,所以各个具体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同的。
正因为如此,北岛在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无题》时,指出了刘文飞“沉重的蜂房和娇柔的渔网”这一翻译的弊端,即把“网”译成“渔网”,刘文飞主要是为了跟着原作押尾韵,他不惜使用极其别扭的词(如“吸吮”“耕翻”)来凑韵,这在汉语诗歌翻译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却是一大忌讳。把一种语言的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诗歌,押韵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创造的其实只是汉语的内在节奏。
我们的现代诗歌也有自己的音乐之美,新格律诗的提出者和探索者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探索,而且进行了创造性的实验,形成了一种不断涌现的新格律诗风。闻一多将英诗的音尺引入诗行,形成一种“豆腐块”式均匀整齐的诗体,如《死水》每行九字四顿:“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每一段四行文字,都从视觉和听觉上完美地表达了他的“三美”原则。徐志摩以其娴熟的技巧以及和谐的发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何其芳、卞之琳则以闻一多的音阶为基础,提出了以“顿”为中心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他们通过相同数量的“停顿”形成诗行,并有规律地使用行内的奇数或偶数停顿来满足不同节奏的需要,形成了一种有节奏、和谐、结构对称的押韵诗形式,其影响延伸到后代。
三、陌生化手法
“陌生化”是施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在《艺术即手法》中指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强度,因为感觉过程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由于时常接触的是日常语言的陈词滥调,这也让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变得过时和迟钝,而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自动化”,但文学语言通过巧妙的安排和语言的技巧,将日常语言变成“未知”,更新我们的日常反应,唤醒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和世界的新鲜感。
北岛在翻译里尔克的《预感》时,特别指出了其中的陌生化手法:“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预测”和“秋天”一样,也强调了这种无知的影响。里尔克通过一面旗帜展示了诗人的愿望,而旗帜本身的孤独和孤独反映在周围:空虚、风、门、烟囱、窗户、灰尘和风暴—正是这些敏感而精确的细节延长了我们的体验过程。在这首诗中,对比是陌生化的表现形式。
我们再来看看北岛在创作中陌生化手法的应用,以《雨中纪事》中的第二部分为例,“在这里,在我/和呈现劫数的晚霞之间/是一条漂满石头的河/人影骚动着/潜入深深的水中/而升起的泡沫/威胁着没有星星的/白昼”,其中的意象,如晚霞、河流、泡沫等,就有明显的“陌生化”倾向。“陌生化”是一种针对读者的藝术手法,目的是唤醒读者一种新鲜感和陌生感。“晚霞”出现在天光渐暗的黄昏时分,预示着黑夜即将到来,这个意象既不温暖也不美丽,古往今来,它往往被视作不祥之云的代名词;河流也并不是读者熟知的生命力和清晰度的代表,而是随着落日余晖而成为恶势力的源头。诗人对河流的描述似乎带有一抹似是而非的色彩—笨重的石头能够漂浮在河流上,而人却挣扎无果、沉入河底,这显然与读者的日常意识格格不入。这种描述恰恰准确地说明了诗人意识的外部世界是颠倒无序的,有一种类似梦境的荒谬感。诗人的痛苦是因为看到了人的卑劣和黑暗本性,但他又无能为力,不能拯救他们,只能让罪恶的残余孤烟直上并伤害他人,将世界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白昼”和“星星”原本是希望的象征,但前面用了修饰语“没有”这个词,强调了诗人的绝望。《雨中纪事》的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描绘了诗人发现希望然后粉碎希望的整个过程,诗人的内心世界不断地与黑暗的外部世界对峙,但这种对峙最终退化为理想难以实现的挫败和焦虑。
四、意象的对立与悖论
对于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歌,北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拉克尔的诗歌,往往是由两组意象组成的:一组是美好或者积极正面的,一组是邪恶或者消极负面的。这两组相互对立碰撞的意象,在北岛的诗歌中转化为悖论意象—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挤压,一方面化解了现实世界的不完美,另一方面也给予了现实世界坚实的抵抗。北岛在这两个如同南北极一般的世界之间纵横航旅,同时也仿佛不甘心一般地进行了几乎绝望的抵抗。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两种对立形象是相互排斥的。北岛在否定现实的时候,又通常持有有意义的理想,通过思想实现超越,所以悖论式的情景有时出现在他的同一首诗中:“走吧/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走吧》)
在悖论的旋涡中若隐若现的悲剧色彩,也反映在北岛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星星群落中,如“风上是闪烁的星群”(《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星星,那些小小的拳头”(《四月》)等。对这些意象的分析表明,北岛诗歌中的各种星星群落虽然形式各有千秋,但是内涵大同小异,包括两个相对的主题层次:一方面,诗歌和诗人的永恒和不朽—表现在高度和上升空间的图像上,象征的是骄傲和狂欢;另一方面,这是诗人疏远、短暂和孤独的一生—以悲伤和绝望的基调描绘彗星的坠落和沉寂。星星的矛盾性的不可或缺,以及对立意象群体的混合、消解和辩证分析,凸显了诗人在现代新诗创作中,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视作了悲剧英雄的形象。在北岛的诗歌中,星星象征着诗人昂扬挺拔的意志。
五、西方诗歌的历史趋向性
与中国现代诗歌相同的一点是,西方诗歌也有大量的传统。在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宗教传统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传统)。前者如里尔克,他的诗歌虽然有意识地体现对宗教的反叛,但他的诗歌中也反复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意象,诸如上帝与撒旦、灵魂与肉体。他的女友莎洛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上帝本身一直都是里尔克诗歌的对象和主题,并且也影响了他对自己内心最隐秘的存在的态度,上帝是终极的,也是匿名的,上帝超越了所有自我意识的界限。当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系统不再心甘情愿地为“宗教艺术”提供清晰可见的意象时,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里尔克伟大的诗歌和他个人的悲剧都可以归因于如下事实:他要把自己抛向造物主,但是造物主已不再具有客观性。后者则以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为代表,对荷尔德林来说,正是诗人在公共生活中的使命,成就了古希腊文明的伟大。这两种文化渊源有时也会同时存在,如在弥尔顿的五大诗歌诉求中,“缪斯”属于古希腊罗马史诗传统,而“圣灵”“圣光”和“天堂的诗歌女神”显然属于基督教史诗传统。也就是说,单就“诗意感染力”而言,弥尔顿的史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种史诗传统的共存特征。
由此,北岛深刻地认识到,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在人生某一刻才会顿悟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个人力量的势单力薄,就像狂风与孤帆的关系一样,只有懂得利用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可感而不可知的。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者们要积极探索,要孜孜不倦地丰富这一传统。
更普遍地说,中国现代诗人所要面对的,其实是整个世界的诗歌的更新迭代、潮起潮落,而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他们不仅要满足诗歌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审美预期,还要应对20世纪各种各样的挑战。因此,当古典诗歌的影响表现在不同形式的转折中时,它也很可能同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转变和重组。有的时候,古代与现代的联系是相当隐蔽和间接的,并嵌入了其他诗歌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九叶诗派和宋诗之间,就嵌入了许多西方20世纪传统诗学的内涵。我们无法确定九叶诗派的实际成果究竟包含了多少对宋诗的高度肯定,但可以确定九叶诗派与宋诗有着某种遥远的契合和联系,这可以说是一个“被改造特征”。而类似这样的“被改造特征”,在中国现代新诗的比喻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恰如肯尼斯·雷克斯洛斯认为中国古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样,西方诗歌传统也可以为全世界的诗歌创作提供很好的借鉴。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写作绝对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在与西方诗人的对话中进行的。在这一对话中,西方诗歌的哲学传统、美学传统和历史传统等因素,跨越千山万水,被巧妙地融合在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中,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