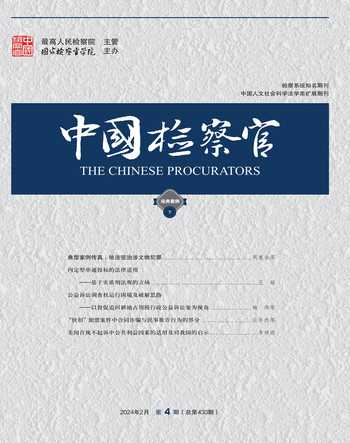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路径检视*
郑法梁 蔡雅芝
摘 要:当前,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定罪路径较为混乱。应厘清毒品与麻精药品的关系,从贩卖毒品罪的立法原意出发,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确定行为人明知是管制的麻精药品而向吸毒、贩毒人员贩卖或者被购买人用于特定犯罪活动的,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具体适用时,应对行为人对麻精药品的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是否有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是否存在非法用途等予以考量。
关键词:麻精药品 贩卖毒品罪 主观故意 非法用途
一、出售麻精药品的定罪争议
[基本案情]2021年至2022年间,张一在某省从事“泰勒宁”及多种处方药的收购、贩卖活动。张一明知“泰勒宁”系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为牟利多次从医院病人处回收“泰勒宁”,并每盒加价2元出售给张二,总计600余盒。张二在该省亦长期从事药品倒卖生意,从张一处购入“泰勒宁”后又将每盒加价5元左右出售给张三经营的药房(不具有出售资质)及其他药房。张三明知张四吸食“泰勒宁”成瘾,仍每盒加价20元左右出售给张四,总计100余盒。公安机关对张一、张二以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作撤案处理,法院审理认定张三构成贩卖毒品罪。
《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指出,部分吸毒人员因受毒品供应大幅降低影响,转而寻求其他麻精药品等替代滥用,或交叉滥用以满足毒瘾。[1]在办理涉麻精药品案件时,其定罪路径不同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案件。具体而言,传统毒品案件的定罪路径相对简单,仅需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客观上实施相关犯罪行为;而麻精药品大多具有药用属性,认定为毒品时需满足多个限定条件,对行为人主观认知有较复杂的要求,以贩卖毒品罪论处时需更为慎重。司法实践中,对于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路径未形成统一认识,在适用时仍有诸多纷争,本案中张一、张二、张三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即存在较大争议,相关问题亟待厘清。
二、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定罪路径评析
(一)出售麻精药品的三种定罪路径
当前,对于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主要存在三种定罪路径。第一种路径为限缩的认定模式,即出售麻精药品以贩卖毒品罪论处要求相关行为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一是行为人出售的麻精药品受国家规定管制;二是出售去向为吸毒或者贩毒人员;三是行为人明知所出售的药品为受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且去向是吸毒或者贩毒人员。采用此种定罪路径的代表性案例有吴某某、黄某某等非法经营案等,该案中被告人吴某某等人在未取得药品生产、销售许可的情况下,生产盐酸曲马多等药品,后多次将加工好的盐酸曲马多药片及包装盒、说明书交给多人转卖,法院未认定吴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2]该案例为进一步论证被告人的贩毒故意,还在上述三个条件外增加“获得远超正常药品经营所能获得的利润”,出售利润大小往往能反映出行为人是以药品还是毒品出售的故意,该增加條件意为兼顾麻精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条件并非必然存在,如少量、零包出售的,利润差并不明显。
第二种路径为扩张性的认定模式,即将第一种路径中的出售去向从吸毒或者贩毒人员扩张到“非法用途”。在这种定罪路径中,即使出售的麻精药品未被用于吸毒或者贩毒,只要是医疗等合法用途以外的非法用途,行为人明知而出售的,即可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第三种路径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对非法用途作出限制,即麻精药品是被用于吸食、贩卖或者实施抢劫、强奸等较明确的犯罪活动,行为人明知而出售的,可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二)三种定罪路径的证明体系差异
传统的贩毒案件证明体系的核心在于主观明知是毒品以及客观有贩卖行为,而出售麻精药品案件证明体系的核心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以及麻精药品的用途去向。不同的定罪路径中,出售麻精药品案件的证明体系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种定罪路径中,需要证明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包括认识到出售的是管制的麻精药品,且具有将麻精药品作为毒品替代品出售的意愿;客观上,麻精药品系用于吸毒或者贩毒。引申到本文案例中,就要求证明张一、张二、张三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购买者将“泰勒宁”作为毒品的替代物吸食,并且查实购买者系吸毒者或贩毒者。
第二种定罪路径中,仅需要证明行为人明知是管制的麻精药品,且具有将麻精药品作为非医疗用途出售的意愿。第三种定罪路径和第二种定罪路径基本相符,但在非法用途的证明上,需具象为吸食、贩卖、强奸、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引申到案例中,第二种路径要求证明张一、张二、张三明知他人购买“泰勒宁”并非用于医疗活动,且购买者无医疗等合法需求,第三种路径要求证明张一、张二、张三明知他人购买“泰勒宁”并非用于医疗活动,且购买者系用于吸食、贩卖或者实施抢劫、强奸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三种定罪路径的选择
根据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昆明会议纪要》),行为人符合第一种定罪路径的情形,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不存在争议。按照第一种定罪路径,本案中的张一、张二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张三构成贩卖毒品罪。但第一种定罪路径过于限缩,不能很好应对当下的毒品犯罪形势,其最明显的弊端在于只有查实吸毒人员吸食了麻精药品才能定罪,无疑放纵了一些犯罪。比如,个别类型的麻精药品吸食后无法以尿检等方法检出,此时下游买家有无用于吸毒未能查明,导致无法以毒品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第二种扩张性的定罪路径,《昆明会议纪要》既未明确反对,亦未直接支持。《昆明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中曾将第二种扩张定罪路径吸纳其中,后在正稿中又予以删除,表明该路径有较大争议。若采用第二种定罪路径,案例中张三构成贩卖毒品罪无争议,张一、张二均有可能因未妥善履行审核义务,未严格把握“泰勒宁”去向,从而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支持扩张定罪路径的主要理由为“实践中,一些行为人通过网络平台向不特定主体出售麻精药品,并冠以‘迷奸水‘催情水等称谓,仅概括知悉他人可能用于实施违法犯罪,但是不了解、不关心他人的具体行为,且向多人进行销售,确有通过贩卖毒品罪予以规制的必要性” [3]。诚然,第二种定罪路径的突破、扩张是有必要的,但若扩张幅度过大,将所有网络倒卖麻精药品的行为均以毒品犯罪定罪,可能导致错用罪名。
相较第二种定罪路径,笔者认为第三种定罪路径更为妥当,主要理由是第三种定罪路径将非法用途限定于为实施明确的、具有较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能兼顾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昆明会议纪要》涉及麻精药品的规定共有6条,其中出罪条款是为了与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条文规定保持一致;入罪条款则对非法用途作了条件限制。在传统毒品犯罪中,毒品也不一定是用于吸食,基于其他违法目的而出售的,同样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按照第三种定罪路径,本案中的张一、张二均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张三构成贩卖毒品罪。
三、出售麻精药品定罪路径的进一步释明
笔者在赞同第三种定罪路径的基础上,对该定罪路径中的核心要素作进一步释明。
(一)行为人对麻精药品的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
刑法中毒品的概念还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因此,麻精药品被认定为毒品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规定管制,二是能够使人形成瘾癖。那么,行为人对这两个要素主观上是否都要有认识,并且需要达到何种程度,就能认定明知是毒品?案例中张一就曾提出其不知道“泰勒宁”受管制,不知道“泰勒宁”能够让人成瘾,只知道在外面药店买不到,因此张一认为不能认定其明知“泰勒宁”是毒品。
瘾癖性是麻精药品的客观属性,是常人所知的常识,无须例外证明。如案例中的“泰勒宁”是作为癌症病人的常用止痛药,而止痛药不能滥用、容易成瘾系一般常识。管制性则是国家规定列管后才具有的,检察机关对行为人明知是管制药品具有证明责任,证明内容为行为人明知麻精药品受到管控,不能随意买卖。当前,我国管制目录主要有《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以及其他列管公告。如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将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种列入精神药品管理的公告》在2019年将“泰勒宁”列管,列管前“泰勒宁”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列管后“泰勒宁”只能在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具,流通受到严格控制,这是列管前后最为直接的变化。检察机关在论证时,无需要求行为人意识到具体的列管规定,只需对列管结果有概然性的认知。具体到案例中,张一经手的“泰勒宁”都是带完整包装的,包装盒上显眼之处注明系精神药品,其提到的“泰勒宁”不能随意买卖实际上就是明知受管制的供述。
當然,对于列管不久的麻精药品,在行为人是否明知管制的认定上要更为慎重。如依托咪酯于2023年10月1日起正式列管,对于行为人在列管前后连续出售的,要进一步核实行为人对管制状况、何时列管、知晓渠道等情况的认识,以免作出错误认定。
(二)以毒品替代物出售故意的认定
贩卖毒品罪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在涉麻精药品案件中,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也应包括直接追求和间接放任。实践中常有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行为人没有作为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第二种情形为行为人出售时认识到有作为毒品替代物的些许可能;第三种情形为行为人有作为毒品替代物的高度怀疑而放任出售;第四种情形为行为人确定有作为毒品替代物的直接故意。
其中,存在争议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正如案例中的张一和张三,张一在向张二出售“泰勒宁”时,知道张二是倒卖药物的,药物去向有可能流向黑市;张三在向张四出售“泰勒宁”时,前期怀疑张四短期、多次、大量购买“泰勒宁”系用于吸食。张一坚称自己没有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张三认可自己有该故意。对于第三种情形,可以认定具有贩毒故意。对于第二种情形,就不能认定贩毒故意。尽管张一多次向张二出售“泰勒宁”,未尽到审核义务,亦未排除“泰勒宁”流入毒品市场的可能。但张一的这种可能性不明显,与张三所持的高度怀疑程度上有较大差距,张一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认识尚不充分。同时,张一仅有倒卖药物从中牟利的追求故意,不能以未尽到审核义务直接推定为张一具有作为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放任故意。
涉麻精药品的毒品案件中,行为人主观必然交织着扰乱药品管理秩序的故意和以毒品替代物出售的故意。在不认罪的情况下,判断贩毒故意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他人购买用于替代毒品的认知程度,若达成高度怀疑的则可以认定。
(三)非法用途的界定
毫无疑问,将麻精药品作为毒品替代物吸食是非法用途之一。实践中在判断非法用途的对象、方法上存有偏差,如判断对象混乱不清,又有以最终去向倒推认定为非法用途等问题。具体到案例中,张一作为出售者,其始终具有倒卖药品获利的非法目的,能否就等同于非法用途?判断张二的非法用途时是站在张二、张三角度综合判断,还是要考虑张四?“泰勒宁”从张一、张二、张三层层流转,最终被吸毒人员吸食,能否认定张一、张二、张三均是非法用途?
其一,倒卖牟利的非法目的不等于非法用途,对非法用途的评判需要兼顾买卖双方。《昆明会议纪要》规定,对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未经许可生产、经营或者自救、互助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换言之,买方作为麻精药品持有者,其是否用于治疗疾病,能够反映卖方的主观故意。卖方明知买方需要麻精药品进行治疗而提供,表明卖方是出于治疗他人疾病的目的。倒卖牟利与否与麻精药品是否用于治疗疾病没有必然联系,无法推定为非法目的。否则,所有无许可经营管制的麻精药品行为人都可直接认定为非法用途,显然不妥当。
其二,在连环倒卖的情况下,需要多环节判断非法用途。在贩卖毒品罪认定中,明知是贩毒分子而贩卖管制的麻精药品同样构成贩卖毒品罪。该种情形下,为论证买方的贩毒分子身份,需对买方的下线进行考量,全维度审查行为人—贩毒分子—吸毒人员链条。如张二向张三出售“泰勒宁”,贩毒分子张三又向吸毒人员出售,只有张二明知张三是贩毒分子方可认定非法用途,张二才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若不审查张三对“泰勒宁”的处置去向,则对张二不便进行非法用途的判断。
其三,非法用途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而非客观事实的简单倒推。不是麻精药品最终流入毒品市场,就能对流转链的出售人均进行打击。如张一将“泰勒宁”出售给张二,张一无法确认张二如何使用“泰勒宁”,或是否按照约定使用“泰勒宁”,此时以最终流向是毒品市场推定张一系非法用途,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法理,不当扩大了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圈。
其四,非法用途的限制条件应为较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出售人明知麻精药品用于上述危害行为,其将麻精药品用于违法性目的的故意相对明确,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责并未超出公众认知。
本案中张三明知张四将“泰勒宁”作为毒品替代物吸食,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张一、张二明知转手的“泰勒宁”实际流向药房,但对药房私下向吸毒人员出售“泰勒宁”并不明知,故无法认定张一、张二的购买者系非法用途,二人不具有贩毒故意,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本文所称麻精药品是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四级检察官[325200]
***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325200]
[1] 参见《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国禁毒网http://www.nncc626.com/2023-06/21/c_1212236289_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2月1日。
[2] 参见林钟彪、曹东方:《吴名强、黄桂荣等非法经营案——非法生产、经营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应如何定性》,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厅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2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0页。
[3] 元明、黄卫平、肖先华:《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惩治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解读》,《人民检察》2022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