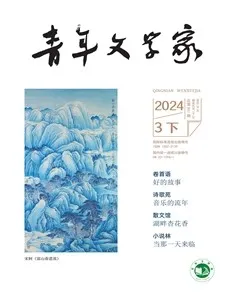种瓜南墙下
张海新
“南瓜,南瓜……”我叫着,如同在呼唤童年的小伙伴。它就像家乡的亲人一样让我念念不忘。
“三月三,南瓜、葫芦地里钻。”谷雨前后,母亲总是在南墙根点种几窝南瓜。母亲常常说,南瓜泼皮得很,种下就不用管它,等着吃就是了。
春风雨露滋养着,不几日,它们便探出嫩绿的小脑袋,沐浴在阳光里,舒展下肥嘟嘟的手脚,便憋足了劲儿,爬呀爬,爬满了土墙,成了一道翠绿的瀑布。
南瓜生命力格外旺盛。两三颗瓜子就能生长出大片大片的茎叶,缠缠绕绕,每一根细长的藤都做着去远方的梦。这时,母亲就会掐些嫩的茎叶,并说,这样才可以让南瓜长得更肥,开更多花,结更多果。鲜嫩的南瓜藤,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先撕去一层外皮,掐成一小段,带着新生的嫩芽。把南瓜藤用井水洗净,沸水里过一道,捞出,保持其翠绿的本色,再起锅烧油爆香姜末、蒜粒,放入南瓜藤翻炒,放适量盐巴,出锅便是一盘鲜嫩爽口的时令小菜。
不久,大朵大朵的南瓜花开了,攀上墙头,对着天空,鼓着腮帮子,嘀嘀嗒嗒地吹着喇叭。当太阳射出第一缕阳光,雄花就浑身披着朝露,先醒了。我跟着母亲摘公花,学着母亲的样子花瓣朝下,朝羞答答的雌花的俏脸蛋儿上扑几下粉。母亲说只有授了粉,才能结出瓜来。我觉得有趣得很,乐此不疲。
授了粉的雄花也不会丢,装满一篮子,回去做美食。母亲擅长蒸南瓜花。一朵朵洗净,沥水,拌上面粉,在笼里蒸熟,准备好蒜泥、辣椒酱、酱油、香油调成的酱汁,夹一筷子蒸南瓜花,蘸足酱料,吃一口,软糯鲜嫩,唇齿留香。后来,母亲还做炸南瓜花,一朵朵干净的南瓜花挂上面糊糊,在热油锅里炸得焦黄酥香,撒上椒盐,犹如绽放在精致的荆篮里,金灿灿的,赏心悦目。
南瓜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类的餐桌。吃过了南瓜藤、南瓜花,该吃南瓜了。瓜熟蒂落,花落处,挂着一个个光溜溜脑袋的胖娃娃,拳头大小,嫩得能掐出汁水来。骄阳似火的正午,母亲从田里归来,顺手在南墙的瓜藤上摘四五个南瓜回来。用刨丝器擦成细丝,放适量的盐,倒入面粉,搅拌成稠糊状。大火烧热油锅,用汤勺挖一勺放入,再用锅铲压扁,形成一个个圆圆的小饼子,文火慢慢煎,不停翻动,煎到两面金黄,出锅。煎好的南瓜坨,既能吃出南瓜的鲜嫩和麦香,又能吃出悠长的麻油香,真是人间绝味。我们姐弟三人,一人一大碗下肚,连呼好吃。母亲总开玩笑说:“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费油。一顿下来,一瓶香油都见底了。”我们则摸着肚皮,心满意足地傻乐个不停。
秋天,历经季节风雨的南瓜,老了。父亲把它们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母亲为了防止我们吃厌了,变着花样做南瓜:早上是南瓜稀饭,中午做南瓜饼,晚上吃蒸南瓜,还时不时更新菜系,炕南瓜芝麻饼、炸南瓜园子、晒南瓜干……最后,还把南瓜子淘洗干净,在草木灰里阴干,烘焙成焦香的南瓜子。
就这样,储存的老南瓜一直吃过冬天,到春暖花开,又要种南瓜了。
诗人红土在《像南瓜一样活着》中说:“有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活得像南瓜,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在秋天的时候躺在地里,红得像瓦。”是啊,我突然想起儿时常常对着一南墙的南瓜突发奇想:要是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南瓜,该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事啊。
此生,我已与南瓜结下情缘。循着记忆中的南瓜,隔着千山万水,我总能夢到久违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