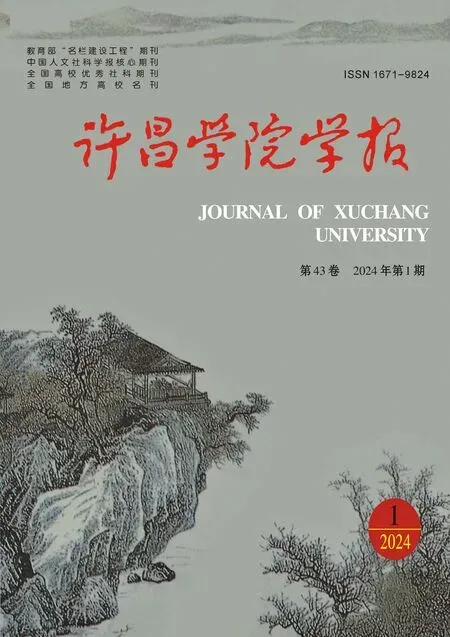曹植《远游篇》创作年代新探
夏洵若
(上海建桥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01306)
一、引言
(一)研究概述
汉魏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一生佳作甚多,尤以五言诗在文坛获得极高赞誉。他被《诗品》列为上品[1]9,被钟嵘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2]73,是唐前中古时期的“诗神”[3]127。对他后期阶段创作的“游仙诗”,历来关注甚多,不过多就诗歌主旨议论品评,对创作时间的研究甚少。关于《远游篇》的创作时间,前人亦未有定论,仅有一些学者编订各类《曹植集》时估测过时间,但尚未取得共识,且讨论也较少,值得进一步探研。
放眼前人对《远游篇》的讨论,对此诗的创作年代,基于诗歌意境语气等因素,大致将其定位在曹植人生后期,对此多无异议。只不过具体到哪段时间,尚不确切。因为曹植的“人生后期”,从兄长曹丕为魏王的延康元年(220)开始到他人生终点[4]333的太和六年(232),历时不短,跨越魏王朝文帝、明帝两代帝王,且文帝、明帝对待曹植的态度也有差别。笔者基于文本,通过分析文学家心理,考量当时历史环境,探析这首诗确切的创作时间,将诗作、诗人、历史环境三维与时间第四维结合,争取获得精准定位,逼近创作的确切时间与诗人历史上的真实心境。
(二)《远游篇》创作背景
《远游篇》是曹植的乐府创作,属于“游仙诗”范畴。传统学界对其游仙诗主旨的判断也有分歧,但大多同意是作者因政治失利而宣泄苦闷的表达。笔者对此曾做过论述,提出游仙诗中的“仙界”含有诗人对“天”向往的“通天”意识[5],这种意识在《远游篇》中也可见端倪。关于《远游篇》的主旨,学界看法较为一致,认为它抒发了诗人“思欲济世而不能”的忧伤情怀[6]121,关乎他在后期现实政治中被排挤的一番感触。然而,这首作品究竟作于何时一直未有公论,且其中蕴含的思想还需结合创作背景来做进一步分析,这就使这首诗的时间断代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有关《远游篇》创作时间的认定,多在各类《曹植集》的编纂中,编者或者在介绍此诗时顺带提一笔,或者通过目录排列做出暗示。总体来说,各家并无确论,经常各执一词。具体情况如下: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将《远游篇》列在太和时期的作品之中,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中间靠前,即太和前期[7]目录8,未解释原因;林久贵、周玉容《曹植全集》通过目录排序将《远游篇》列为太和时期作品[6]目录4;王巍《曹植集校注》将《远游篇》定为太和时期作品,且表示是曹植临终时所作[8]101;杨焄点校的《曹植集》通过目录排序将《远游篇》列在曹植晚期作品中[9]目录3,但未明确具体创作时间;余冠英选注的《三曹诗选》将《远游篇》列为后期作品,具体原因未做阐释[10]3,104;张可礼、宿美丽编选的《曹操曹丕曹植集》在目录中将《远游篇》排列在曹植诗作中的倒数第5篇[11]目录5,意指其为晚期靠后作品;黄节《曹子建诗注》将此诗列在偏后的位置[12]88,暗示为后期作品,但未说明具体时间段。另有徐公持《曹植年谱考证》认为,此诗作于“建安中后期”[13]249-250,归入一个笼统的可横跨曹植生涯前后期的时代——对应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任魏太子之际为曹植后期的说法,便属于前后期之交;依照曹丕登基为帝(220)为曹植前后期划分的界限,则属于前期阶段。但无论是根据哪一种,依据都不够,因而作者也承认:“具体年份难定,姑且于是。”[13]
以上是学界权威专家在《曹植集》编选或《曹植年谱》中的观点,皆未确定这首诗具体作于何时。古代学者亦未辨明,仅有清代朱乾谈到这首诗时说:“读曹植《五游》、《远游篇》,悲植以才高见忌,遭遇艰厄。灌均之谗,仪、丁廙受诛,安乡之贬,幸耳。……所谓‘九州不足步’,‘中州非吾家’,皆其忧患之辞也。”[9]150提及了背景事件,即黄初年间曹植兄长曹丕上位后对曹植“党羽”进行铲除,因此认为《远游篇》和黄初年间的事态有关,然而并没有直接说明此作的创作时间。朱乾的这番话有一定道理,可惜未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纵观前文引述的《曹植集》或《曹植年谱》中的相关内容,各家论述形式和逻辑大多相近,然对此问题的真正解答却并无更多价值。本文尝试分析曹植《远游篇》的真正创作时间,由此对诗中思想内涵做进一步解读。
二、《远游篇》应作于黄初时期
根据本文新解,《远游篇》实为曹植黄初年间所作,而非更早的建安或更晚的太和时期。对此,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曹植在黄初年间更为压抑
虽然同为人生后期,黄初(从曹植处境上来说,亦可包含曹丕为魏太子的建安后期)和太和时期曹植的处境是不一样的,这使得他的心理状态也有所不同。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对曹植在各个阶段的心态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分析了黄初和太和时期曹植心态上的区别[14],虽然还有不甚精准之处,如未考量曹植在太和时期因政见能得以发表而产生的振奋感。比较而言,曹植在黄初年间压抑感最重,且甚于他在建安后期父王曹操尚健在时以及太和之际曹丕已过世后,而《远游篇》给人的感受更符合这一时期曹植的心境。还有学者注意到,《远游篇》比起曹植其他游仙诗诸如《五游咏》等,情感上更为激烈愤慨[11]267。因此,诗中透露出的诗人心境,跟他黄初时期的处境是最为贴合的。太和时期,曹植固然依旧因壮志宏图不得展而忧郁,但程度已较为柔缓,还有着些许寻求突破的积极振奋,如向魏明帝表达“求自试”等(49)参见曹植《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太和年间写给魏明帝曹叡的政论文章。,不像《远游篇》表现出的压抑低迷的心境与回避现实的嘲讽口吻。
(二)黄初中后期“鄙国”意识浓烈
黄初年间,曹植因“夺位失败”遭到皇兄排挤,曹丕等候多年才取得曹魏继承人之位,心态不佳[15]40-42,故给予弟弟的政治待遇很差。纵观历史,魏王朝以苛待宗亲闻名[16],追溯其源,或许就是黄初时期曹丕定下的基调。在此期间,曹植被驱逐至藩地,远离京城政治中心,这对于自小就跟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8]前言1、拥有雄心壮志的曹植来说,自是不喜。他对当权的曹丕不敢明言,就将此种心迹婉转表露在诗文中,如在《黄初六年令》中说曹丕来到“鄙国”,言语中暗含着对曹丕的嘲讽:“今皇帝遥过鄙国,旷然大赦,与孤更始,欣笑和乐以欢孤,陨涕咨嗟以悼孤。丰赐光厚,赀重千金……”[6]121明里暗里,塑造了曹丕又哭又笑的滑稽模样;且这番话里,中心俨然是自己,说皇帝如何围着他转,而非如之前父王曹操在世时及以后皇侄当权时将自己定位为“王佐”[17]。多年来丕植二人围绕权力相争不休,曹丕作为胜者亦不够宽容大度,故要让曹植放下恩怨自是不太可能。这段时期,曹植身处险境,心灰意冷,由此萌生出在条件苛刻的藩地“画地为牢”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还要隐藏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正符合《远游篇》里“中州非我家”那种傲慢中带有讽刺的语气。而到曹叡登基后的太和时期,曹植少年时代的热血再度澎湃,从政的信心和积极性再度生起,当初的“鄙国”意识便不复存在了。
(三)与“仙道方术”的接触距黄初较近
学界有观点认为,曹植人生后期由于遭遇挫折,转而“求仙问道”[18],更进一步,认为曹植后期信奉“道教”[19],此皆存在误读。曹植自始至终都不曾信奉那些宗教,他基于自身的独立思考,秉持着某种政治哲学观念,同时吸收了一系列包括诸子百家的先秦文化和上古的“天人文化”而具有一种“通天”意识[5]。他的思想主线得儒家、道家浸润颇多,但也未完全偏向任何一家[20],他是有着属于自己“曹子哲学”的思想家(50)参见曹植《髑髅说》,此文是他哲学思想的体现,在作品中他自称“曹子”。。撰写《曹植年谱》的学者江竹虚指出,曹植的思想类似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杂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意识都能为他所理解、通融,且他兼有身为王侯的王霸之气[21]25-26。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之下,曹植拥有稳定而一贯的哲学思想和坚固信念[22],不可能因为现实的挫折而转向他早年就已看透的虚妄而人为的宗教。
早在少年贵公子时代,曹植就和方术之士有所接触。那时曹操为稳固中原政局,将方术之士召集在一起以避免发生类似于“五斗米教”的事情,顺带让他们教给曹氏家族一些养生健体的方法。曹植早年曾写过《辩道论》,提到自己追求客观真理而不信仙道,对于个别“玄妙”的事件亦不轻易下定论,表现了一种理性求知的态度。《辩道论》还含有现实的政治意图[23],是要为其父所采取的举措做合理性辩护。但后来传闻为曹植所写的《释疑论》则持“不可知论”立场,且对仙道也颇为接受,对此有学者质疑其真实性,判断其为道教中人托名曹植的伪作[15]73-76。其实,曹植的《辩道论》早就将相关问题阐释清楚,如果到晚年他别有感悟,亦不会连少年时的辩才都不复存在,仅在文中申明“结果”而不多做解释,这完全不似他一贯的理性作风。此外,由于客观原因,曹植真正接触那些方术之士仅是在早期建安时代,到了后期,莫说是方术之士,就连一般生活所需的仆从对曹植来说都大为不够了。这从他后来所写的《谏取国士息表》中即可看出,曹植在其中将仆从人手等记录在案,一一统计他们的年龄和生理状态,由此可知他在藩地的生活条件有多差。正如史学家所说:“名为藩王,实为囚徒。”[24]372他还写有《求通亲亲表》,表示“每逢四节之会,所对唯妻子”[9]241——连个门客都没有,遑论什么方术之士呢。所以说,认为曹植后期在“信仰”方面有所转变去信奉仙道,就是误解;以此推断他涉及仙界题材的所谓“求仙诗”为后期的作品,逻辑上也是错误的。如果从真实生活考察,前期建安时代曹植作为贵公子接触过当时有名的“修道中人”,出于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目的曾向他们请教过,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段更接近于黄初而非太和时期。这份记忆形成后加以调取和输出,在建安之后的黄初年间最合情理。
(四)讽刺意味区别于太和时期游仙诗
曹植在太和年间创作了大量游仙诗,但这并不表示他在其他时期不能有此类作品产生。《远游篇》和那些作于太和时期的作品意境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者是对“中州”的疆土意识。实际上,曹植一直秉持大一统思想,将整个中国视为自己的国度,心心念念吴蜀统一事业[25],眼界开阔而非局限于自己的封地。但是,当他在现实中遭受不公,极度失望愤慨时,就会透露出讽刺现实、嘲讽“当局”的言辞,这也是《远游篇》里表现出的情绪。这与他黄初后期其他文章颇有共通之处,对此可参考他的《黄初六年令》。该文顾名思义写于黄初六年,曹植在此令中先提及皇帝对他的所谓恩典:“反我旧居,袭我初服。”看似说给予自己恩典,实际上更像是划清界限,表明那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自己的;而且恩典的是“旧居”和“初服”,也并非什么大恩大德;更何况这皇帝不是别人,乃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哥哥。讽刺性不可谓没有。而后又提到这位皇帝“遥过鄙国”[17]。作为宗亲藩王固然可以如此称呼自己的藩地,但曹植的这种表述无疑是划分立场,强烈表明自己的地域意识,此与《远游篇》中“中州非我家”表达的意味如出一辙。因此从讽刺意味上看,《远游篇》很可能撰写于与《黄初六年令》同时,即黄初后期。
(五)太和期间曹植政治地位和心态不同于以往
太和年间,曹叡登基后,曹植作为皇叔长了一辈,他对皇帝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皇兄曹丕当权的时候,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面对现实积压了诸多不满。由于曹丕与曹植有过权力斗争,纵然二人有兄弟血缘关系,但在政治层面来说他们是敌对关系,且上位后曹丕对待弟弟十分苛刻,还留下苛待宗亲的政策。这种情况下,曹植身处重压之中,创作出《远游篇》那样含有控诉意味作品的概率要高得多。而在皇侄曹叡当权的太和年间,曹叡对待宗亲的策略趋于缓和[26]144,曹植作为长辈亦没必要对一位温和的晚辈在诗篇中“夹枪带棒”。而且曹植对待皇侄曹叡的态度亦比较温和,言行间欲对曹叡施加榜样作用和启迪功效[27]。因此,《远游篇》整体呈现的激愤而讽刺的意境风格,不符合曹植太和年间的心态与身份。
从政治地位上来说,太和时期的曹植作为魏明帝曹叡唯一的嫡系皇叔以及家族中富于政治远见的人物,俨然已经成为曹魏宗亲的领袖[28]。他屡次上疏奏表,发表政见,虽然没有直接进入朝廷中枢,但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亦相对受到魏明帝的尊重[29]。因此,曹植的感受与心态也不同于以往,因为政治上有了参与感,心理上自然放松平和。这与《远游篇》里呈现的对中央政权的回避感,是完全不同的。
三、《远游篇》中作者心理与黄初年间作品的对比
《远游篇》中,诗人畅想“仙道”的幻彩画面源于诗人自身的灵性化意识,体现出诗人睿智的哲思和细腻的心性。诗歌将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元素注入畅想式的“仙趣”情怀[6]123,同时又将对现实的不满和嘲讽融入其中。根据《远游篇》所体现的各类元素,将其与曹植黄初时期的其他作品对比,亦可印证此诗作于黄初时期。
(一)“远游”意象与《游仙》语句类似
曹植在黄初年间写过另一首游仙诗《游仙》,其中的“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同《远游篇》中“远游临四海”的意境十分相似。其实这类游仙诗并非表达求问仙道之意,而是现实经历的反馈,是出于对政局不满而做出的心理宣泄[30],其来源自然与黄初年间遭受皇兄曹丕及其爪牙的逼迫有关。由于现实环境的压迫,曹植幻想“远游”,也以此象征自己翱翔远行的凌云壮志。
事实上,曹植《远游篇》的创作源泉部分来自屈原的《楚辞·远游》。屈原和《楚辞》给予曹植文学灵感,曹植与屈原也有相似之处[31],二人皆遭身世之悲和理想难求之苦。“远游”一词,不仅在屈原的《远游》中出现,在曹植的《远游篇》中亦出现,在曹植的其他游仙诗中也多有类似意境,可见这一意象在曹植心中根深蒂固。这一意象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应生发于曹植对政治事业最感无望的黄初年间,而非后期情况有所好转的太和时期。
(二)“四海”出现在《赠白马王彪》中
黄初四年,曹丕当权中期,曹植和曹彰、曹彪兄弟从各自藩地前往京城拜会曹丕,然而曹彰却莫名其妙地暴毙,回去时只剩下曹植和曹彪。回归之时,二人被要求不得同行,并全程由曹丕手下监控,相当屈辱和压抑。在如此氛围下,曹植写下《赠白马王彪》,发出愤慨言辞,显示出对曹丕态度的转变。《赠白马王彪》中有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表达了曹植作为兄长对弟弟曹彪的嘱咐和教诲。而《远游篇》亦有提及“四海”这一意象的句子:“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只不过在《赠白马王彪》中这一意象的气势更为宏大,因彼时曹植仍对政治怀有坚定的信念和未能冷却的热血。而在《远游篇》中,则少了这份参与的意志,而多了许多规避式的讽刺。然而两篇诗歌所含有的愤怒情绪、基于不公现实的内心宣泄,依稀之间是一致的。
(三)“大鱼”“清歌”意象在《洛神赋》中亦曾出现
《洛神赋》是带有政治意味的作品,确定作于黄初时期。虽然学界对该赋主旨未有公论,然主流的“寄心帝王说”等均认为该赋同曹植的政治诉求有关[32],而且作者序中“有感于宋玉《神女赋》”这句话也道出了其中的政治因素。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7]344-345《洛神赋》中这段话看似描写了上古的神祇仙境,实际却夹杂了曹氏政治文学家族所喜爱的清歌音乐形式,应当暗含着曹植对昔日家族盛景和过往政治生涯的留恋之感。而《远游篇》中的“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亦具有同样的幻想场面和感情色彩。这是基于真实经历的艺术的反映,所包含的思想意识在其兄长继位后那几年里尤为显著。
(四)“鼓翼舞时风”与《鞞舞歌》有近似之处
曹植在大魏王朝创立初年曾写过一批乐府歌,为曹丕初登宝座庆贺,他将前朝歌曲改造成大魏王朝自己的“官方歌曲”,此即《鞞舞歌》。此歌原包括带着鼓合着乐进行的舞蹈,如今只剩下歌词,但仍能从中看出恢宏的气势和隆重的仪式感,以及强烈的政治意识[33]。它与《远游篇》中的“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句隐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此宏大热闹的场景,在曹植后期处于藩地的情况下已经远离,只存留于记忆和想象。但这份记忆和想象对黄初年间的曹植来说,距离更近一些。更重要的是,其中展现的政治典礼场景,更接近曹植前期以昂扬的状态深度参与政治的情形。这似乎与他在《远游篇》中所写的远离“中州”有些矛盾,但也正体现了诗人曹植的纠结矛盾心理:一方面不满于国君给他的待遇,另一方面对政治事业仍怀有热诚[10]前言18。因此《远游篇》表现出类似黄初早年《鞞舞歌》之《大魏篇》那种热闹的仪式感,又带有太和年间“超脱”的游仙诗风味,细品之下,与他晚年太和时期所作的游仙诗自是不同。
(五)“长啸”与《杂诗·西北有织妇》《美女篇》意象相似
曹植有六首《杂诗》,后世编订时不确定创作时间,其中《西北有织妇》即《杂诗(其三)》,按意象与情感分析,应为黄初年间所作,它与《远游篇》也有相似之处。《西北有织妇》这首诗借弃妇之语表达作者心声,“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表达了对夫君的思念之情,是作者求君臣和睦而不得的内心写照。而曹植写作《远游篇》的时段,正遭受曹丕苛待,眼看君臣兄弟重修旧好的机会趋于渺茫,不免怨气暗中积累,诗中嘲讽之意就多了。《远游篇》中“长啸激清歌”[11]266句,似隐约提及昔日寄心于文帝的情怀,描绘场景也类似于大魏王朝初建时的盛景,应是诗人在黄初后期对黄初早期的一种思忆。
此外,曹植另一篇有关女性的诗作《美女篇》中也有“长啸”一词出现。“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是他借用美女的形象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而《美女篇》所表达的意象和呈现的诗人愁苦之态,也符合黄初年间的作品风格。《远游篇》同样有“长啸”一词出现,只是诗人情绪比起《美女篇》来,更为激烈愤慨,有种因政治排挤而心存不甘的感觉,当为黄初晚期所作。
(六)“日月”及人生短暂意象类于《浮萍篇》
《浮萍篇》为曹植黄初年间所作,用夫妻比喻君臣,是拟“代妇体”的典范。诗中“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一句,类似于《远游篇》中的“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都是表达人间物质易于腐朽而渴慕永恒这种意识。对于《浮萍篇》的创作时间,学界没有异议,均认为是黄初年间的作品,有怀念昔日兄弟情谊,寄心于兄长,希望重修旧好之意[6]83。比较而言,《远游篇》应创作于《浮萍篇》之后,是曹植对曹丕更为失望时的表达,故有讽刺之意、排斥之感。因而同样出现的“日月”这种相似的诗句,在《远游篇》里呈现得更为激烈,在《浮萍篇》中则相对柔和。因二诗使用了类似的词语、意象,故推断是同属于黄初时期且相差不远的两篇作品。
由以上可见,《远游篇》中的词语和意境均在曹植黄初年间其他作品中出现。虽然说作家不一定仅在同一个时段使用相同词语,但从其所用的词语中毕竟可以发现些许规律。在相同的时间段,作家使用相同意识形态词语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不同的时间段。
四、对《远游篇》创作意识符合黄初后期情况的补充
以上就《远游篇》中文字和意象等符合黄初年间创作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而除了文字和意象外,在宏观或微观意识层面,作品也符合黄初尤其是黄初后期曹植创作的情况,现对此加以补充。
(一)“远游临四海”句显示该时段作者距海边封地较远
在曹植历次受封中,只有建安时期为临淄侯时封地靠海,该封地也非贫瘠之地[34]129。这是曹植早期的封地,当时曹魏实行“寄地”政策(51)《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而后又值曹丕当政,故曹植一直未能前往。《远游篇》反映的意识状态,是距离上和心理上都远离海边的一种感受,“远游临四海”,很可能暗含着因未能前往临近海边的封地而感到遗憾。这样一种心理,当事人距离事发时间较近的概率更大。而到太和时期,曹植虽然被迫多次迁徙,但在待遇上已有了很大提升[28],尤其是他来到东阿地区,此地环境优美,国用富饶,令曹植十分喜爱,他自愿将东阿鱼山作为自己身后的入土归葬之地[35]。如此看来,《远游篇》并不符合“临终前所作”的说法。
(二)“疗饥”透露出当时的生存境况
一直以来,曹植都不是注重物质生活的人,他更重视精神层面,属于以灵性和哲思为导向的精英人物[36]。他在后期遭受各种苛刻待遇时所感到的痛苦大多是精神层面的,例如政治事业不能发展,想求得君主信任而不能,至于物质层面,直到基础生存受到威胁而实在难以忍受时,他才会提及,而且这种“提及”也是带有“文艺”风格的。比如在《谏取国士息表》里,曹植将仆从和各类残疾人员做了分布统计,但也非呈现客观死板的数据,而是将其融入优美而恳切的文辞中;在《迁都赋》中,他谈及自己多年以来的坎坷颠沛生涯,通过艺术加工的手法,呈现出唯美感伤的氛围。《远游篇》也有这样的描述,曹植在诗中委婉地反映了他当时的生存境况——衣食住行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对此可以看这一句:“琼蕊可疗饥,仰首漱朝霞。”有学者认为这是对道家养生和求仙问道行为的描写,然而对擅长使用比兴象征手法的曹植来说[37]169,这不是仅在行动上的如实呈现,而是暗藏玄机的“微言”[38],即对皇兄给予他贫瘠封地使他生活艰难的文艺式讽刺。什么样的人需要“疗饥”呢?自然是食不果腹之人。这与他后来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表达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7]480这段话描述了他在封地雍丘时的窘迫境况,而这正是黄初四年以后的时期,与本文推测的《远游篇》的创作年代恰好相应。
(三)对皇兄曹丕的讽刺
《远游篇》里对帝王和政权的不满充斥全篇,是作品的核心内容。末句“万乘安足多”中的“万乘”指帝王排场,“安足多”,则表示对此不屑一顾。这种帝王排场,颇类于大魏初期魏文帝曹丕的做派——彼时曹丕代汉称帝,对树立大魏王朝形象更为讲究。而从心态上说,曹植性格敦厚,对比他小一辈的皇侄曹叡当不会做出如此浓烈的讽刺;只有与他有过权力斗争,在胜利后又对他持续打压的曹丕,才会让曹植产生这样强烈针对的欲望。曹植参与夺位之争惜败,自然受到曹丕的排斥和忌惮,而皇侄曹叡与皇叔曹植则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太和年间,曹植与皇帝的关系已然缓和,故《远游篇》里浓烈的讽刺状态不像是太和时期曹植的表现,更像是黄初中晚期的表达。
黄初早期,曹植惶恐不安之余也有过寻求政治作为的想法,如其《责躬》云:“心之云慕,怆矣其悲。天高听卑,皇肯照微。”[6]29表现出祈求皇兄垂怜照拂的心态。然而经过持续几年的政治排挤,他清醒地意识到曹丕对昔日兄弟相争之事仍耿耿于怀,根本不会让自己有所作为。因此,在黄初中晚期,曹植更可能在作品中呈露出嘲讽和不满,《远游篇》应是当时披着游仙诗外壳的一番倾吐。
五、归总
《远游篇》是曹植对曹丕幻想破灭后,内心压抑日积月累而产生的讽刺性作品。其中含有游仙诗元素,但也有强烈的政治元素,两者皆不能忽略。曹植对政治的热切、早年承袭的“天人”意识,以及因接触方士而产生的对仙道的兴趣,杂糅在一起,反映在《远游篇》中。诗歌中的“仙界”场景,与黄初早期曹魏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典礼场景近似,代表了他心中对政治事业和过往荣光的留恋。
纵观曹植一生,他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的热情,只不过在曹丕执政的黄初年间他看不到希望。而在曹叡上台后,曹植重新生起参与政治的希望,这与《远游篇》中背离政治的“反中心”意识大相径庭。而他写于太和年间的求仙诗,更偏向“仙趣”,更有超脱意识,而无浓烈的讽刺意味和沉重的压抑感。因此,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是魏文帝曹丕在位的黄初晚期,确切地说是黄初四年至七年,也就是曹植为雍丘王期间。
——兼与赵沛霖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