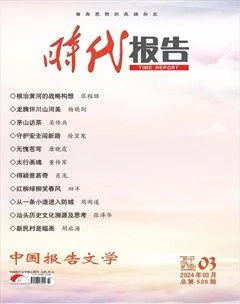从一条小道进入防城
周闻道
我承认,我这次到防城,一开始就受到一种“小道”思维的影响。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海上胡志明小道”,更主要的还是与道路的逻辑有关。因为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路,都是从小道开始的;大道能到达的地方,小道也能,而小道到达的地方,大道未必能。因此,我进一步相信,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其源头和起点都离不开小道;只有通过小道,才能够更好地进入一个地方的深处。
回到这次防城之行,其实我也清楚,从交通的角度,进入防城的选择很多,比如乘飞机,坐高铁,再辗转巴士、的士等等,甚至自驾。但这些都只能说是身体的进入,或者叫身体的在场。但这不是我这次走进的目的。我这次走进的目的是精神的在场。因此在我心里,真正的走进防城,是从小道。可以说,当知道有“海上胡志明小道”存在,我就想也许这就是天意,只有从小道进入防城了。于是,还没有从蜀地出发,我就开始想象着那小道的样子,以及头脑里储存的小道模型。
我的想象,在簕山古渔村和十万大山,都得到印证。
是的,我是从一条小道走进簕山古渔村的。走进了簕山古渔村,就走近了这里的人。古渔村是渔民在陆上的家。渔村就在海边,想来是为了方便,出海与归来,都是举足之劳。既然是古渔村,留下的显然是过去。古渔村的渔民是这里真正的土著,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以海洋为家。海洋的家,我们都不曾体验,无法想象。眼前的渔村,砖墙、矮屋、古树、旧道、雕牌,都诠释着这里的岁月沧桑。“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还要加上“一小道”。不是孔夫子的《为政》,也没有古贤士的所谓超然,就是渔民们平常的海式日子,而且可能是最理想的日子。但是,现实往往没有那么诗意,也没有那么风平浪静。
比如,京族三岛的澫尾村和江平古镇,就有与众不同的“小道”。
天空是鸟的路,陆地是人畜的路,大海江河是鱼的路,这是世间道路的逻辑。问题是,“小道”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门前的一条小路。土路、泥土、石板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路通向哪里。在澫尾村和江平古鎮就不一样了。除了这样的陆上小道,还有大海里的小道;而且,他们日常的行走,大都是在大海里的小道上,人与船行至哪里,小道就延伸到哪里。大海里的小道与陆地上的小道,哪个更难,更艰险,更风雨飘摇、来去无踪,更具有不确定性,是不言自明的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要说什么雷达,什么航海仪,甚至不要说天气预报。一切都凭经验,说出海就出海,一出海就进入了一片浩瀚的未知,命运不属于自己。海浪,台风,礁石,鲨鱼,都是未知的构成。滔天巨浪,与浪共舞,在巨浪中养殖和捕捞;沙虫、牡蛎、青蟹、文哈、对虾等海产品,都是他们的猎物:这就是京族人的日常生活。“大海啊故乡”,在别人,这也许就是一首歌,朱明英唱的;而在京族,不仅是歌,还是一部苦难史。
从小路走进大海,我看见一种危难与拯救。京族,就这样走过来。
澫尾村和江平古镇,是京族人海上生活的B面。村里有点儿冷落。一片低矮的房子,被鱼网式的小道连在一起,大小不一,造型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冷清和陈旧。当地人说,现在村民们都住进了城里的小区高楼,住在这里的并不多。但村子还在,还保留着曾经的样子,比如“草木棚屋”“高脚棚屋”“栏棚屋”“石条瓦房”,在澫尾村和江平古镇都可以看到影子。不只是海上迷幻的延伸,岛上的树林清幽,礁石嶙峋,岗楼威森,土屋幽暗,古墙浮雕,与海上的辽阔安静结合,构成了岛上生活的魔幻。
魔幻就注定了不确定,像小道上的风。不确定的东西多了,就没有了安全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京族人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生存。现实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求助于神灵。京族人的神灵就是海神——南海之神不廷胡余。为了感恩海神的庇佑,京族人专门设置了哈节和哈亭。哈节,就是专门祭祀海神的节日;哈亭,则是专门用来祭祀海神的场所。为了不厚此薄彼,每年从农历六月至八月,这里的澫尾岛、巫头岛、山心岛“京族三岛”上,都要依次有序地举行哈节。仪式是庄重而肃穆的,迎神、祭神、乡饮(入席、听哈)和送神等,每个程式都严肃认真,像模像样,不能有半点儿敷衍。
想起了京族民歌《过桥风吹》,那天防城的龙哥还给我们唱了一段。歌声里不仅有“桂花落池塘,一更来约郎”,更有“风吹醒,哪里望,梦儿短,夜真长”……
哎,“梦儿短,夜真长”。也许,这就是小道上的京族曾经的梦与现实。
古街说是街,其实就是簕山古渔村的一条小道。小道两三米宽,百多米长,一条又窄不长的青石板路,被两侧灰暗的青砖墙和老旧的木板房夹在中间。青石板路上的每一块石板,都记录着古街过往的历史。古街走到尽头,拐了一个弯,进入一小片茂密的竹林。林盘里面承接古街的,仍是一条小道,石板铺就的路面上的竹叶比脚印更多更明显。海上的惊涛骇浪,此刻凝聚成眼前的安静。不是岁月静好,而是走过了太多的沧桑,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处变不惊,心如止水。人走在这样的小道上,不管你年纪大小,经历了什么,都会很快被这种安静融化,让你的进入和走出判若两人。
可是,安静并没有因此而在京族三岛安家,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从小路进入海边,我看见一种危难与沧桑。
既然是岛,当置海里,有一片红树林却在海与陆地的交汇处。海水刚刚退潮,微风兴不起大浪,远处的海柔软而宁静。虽有点俗气,很容易令人想到诗与远方。林地遍布海水洗礼的痕迹。先还以为红树林就是由红树构成的林子,到了红树林公园,看了关于红树林的介绍,才知道红树林是个集合概念,由100多个具有相同属性的树类构成。比如白骨壤、秋茄、桐花树,都是它们的家族成员。它们在陆地与海洋之间交替、防风、消浪、促淤,净化海水和空气,创构了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既为自己,也为我们人类。与其他树不同的是,红树属于胎生植物,生长在海水与淡水、水里与陆地、潮涨与潮落、污泥与净土交织之间。于是,我在心里想,这该要有多大的韧性和生命力。因此,当岛上的主人介绍,红树的籽掉在污泥里,经过这一系列交织的炼狱,只有百分之一能够生长成树,而且红树的叶子排盐功能强,会在出汗时就会把体内的盐排出来,实现身体的生存代谢时,我心里微微一震,眼眶润润的。
就这样,从小路走进红树林,我看见一种生命的顽强与坚韧。
我是从一条小道进入十万大山的。而且,那小道不只是在十万大山蜿蜒,还延伸到了大海,与大海里的小道对接。这就把大山的命运与大海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巴士穿过大道,开到小道前,一抬腿,就进入了小道。青石板路,弯弯曲曲,被两侧茂密的丛林护住。青冈树,狭叶坡垒,大头茶,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杂树野草,构成了小道的近似原始的生态系统。顺着小道,过了一个闪悠悠的吊桥,又过了一个闪悠悠的吊桥,再过天女浴池、蝴蝶石、八角林,当看见珠江源头几个字,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神奇。沿着一条小道,一条小河,似乎须臾之间,就把一条大江走完了。
其实不然,世界上的事,哪有这么简单,何况十万大山。
前震旦系的板溪群组成,加里东运动的下陷,泥盆系至二迭系的沉积,海西运动的左江谷地进一步下陷和三迭系巨厚的沉积,最后在防城的北部形成了这一脉叫着十万大山的山。谓之“十万”,乃南壮方言“适伐”记音,意即“顶天大山”。事实上,东北起平旺乡,西南经板八、峝中延伸入越南,绵延百余公里的十万大山,峰峦叠障,峭壁悬崖,就是防城一道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大山里完整的亚热带雨林,60万亩的原始森林,1890多种植物,9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18.9万个的负氧离子,与山下不远处辽阔的海滩,和海滩上的阳光、微风、细沙、浪平、坡缓、水暖相结合,现在可能是为前来旅游、观光、度假、恋爱的人准备的;在漫长的“防”的岁月里,则是为舍生忘死、镇守边关的将士接风洗尘的。
从小路进入大山,我看见一种对家国的忠诚。
当你回望一下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就知道这里的一切隐喻。
只顾在小道上行走,忘了脚下这片叫防城的土地。为什么要以“防”命名?其实,孟夫子早就阐释过“防”与“攻”的制胜哲学。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然,人是制胜的最重要因素,但当国家衰落,人成“东亚病夫”时,城和城防就成了“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防,就是我们的一个缩影。即便生活在内地的大后方,长期远离战乱,也要家家户户筑起高高的围墙,甚至政府机关也有围墙。围墙的背后是不放心,没有安全感,而“夜不蔽户”则早已变成了理想。人不犯我,我决不犯人;人犯了我,我也以防为上,不会将防转为攻。古往今来,总是浸润着这种防的恐惧,防的屈辱,防的善良。从万里长城、山海关,到大连,再到黑河、藏南等地理名词,都是防的产物。只是,其他城市表现得更为隐忍,而防城,则是坦坦荡荡坦露自己的心扉,不求攻击,不求掠夺,只求防与安宁。
在去“北港故里”和“广西322工程”的路上,我曾对我的“小道”思维產生怀疑。这也难怪,北港路、防东路、防港路、防钦路,无不宽阔大气。大型巴士在上面行走,平稳而舒适,完全没有“小道”的感觉,就是行走在一条现代化的城市大道上,而且,这样的城市大道到处都有。比如我所在的眉山,东坡大道、三苏大道、滨江大道、岷江大道等都是这样,连几条大道旁边的西湾海湾,与我们的岷江东坡湖也差不多。
还好,我的怀疑很快被这两处的事实所破解。
两处指向同一对象,其实,它们的灵魂,就是前面说的“海上胡志明小道”。可以说,北港故里是防城的精神象征;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以防为本,以温良恭俭让为德,以邻为善,长期在小道上行走,小心翼翼惯了的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标本。
起因仍然是防。在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越南发动了战争。封锁,占领,轰炸。同样的借口,同样的旗号,同样的张牙舞爪,相隔不到十年,他们曾在北面的朝鲜战场上一败涂地,仍贼心不死。面对边境的挑衅和冲突的加剧,中国政府光明磊落,是非分明,不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斩钉截铁地庄严宣告:“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毛泽东主席也发出了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属于人民。”
“坚强后盾”“大后方”,当然不是简单的外交辞令,更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宣言,是承诺,更是行动。于是,有了中越两国政府1967年初签订的《关于战争期间使用中越两国间海上隐蔽航线和越南船舶疏散到中国港口的议定书》,有了中越两国政府1968年3月22日签订的《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于是,防城的“广西322工程”应运而生。虽然在现在看来,项目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建设内容也只有简单的港口码头、卫东船厂、江山牛头油库,但与那时全国的经济水平和积贫极穷比,与农民年收入不足百元,工人月工资十几元比,已是巨大的天文数字。
另一个天文数字,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胡志明小道”,运送到越战前线的16万吨援助物资,这是输送给巨大创伤的血液。天上有敌机绕来绕去,地上有万人大军战天斗地,海上有惊涛骇浪的怒吼,我们心中的小道,和它的家——防城港码头建设,却在一个荒岛,一片汪洋中神速推进。
1974年冬,历时20年的越南战争以西方列强的惨败而结束,终于,一条小道走出了大道。不是一般人走车行的大道,而是一个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畏困难、前赴后继的大道。更重要的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它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代表未来每一天的阳光都是新的。
兔年初冬的某一天,阳光柔软而和绚。我站在防城港竹山村大清国一号界碑处,轻轻抚摸着伤痕累累的界碑,眺望不远处的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泪流满面。这里既是中国海岸线的终点,又是中国陆上边界的起点。共和国的海陆边界线像一条小道,在这里交汇。交汇点被命名为零公里,在这里塑了一个圆球形的地理标志,与附近的界碑和地标广场相结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边关风景。阳光正好,天气和暖,冬景如春。
眼前风景的构置颇有讲究,甚至说用心良苦:界碑代表治属,圆球代表陆与海的无缝连接,地标广场代表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亘古不变。特别是地标广场的主体建筑造型颇费匠心。不知道这个主体建筑有没有正式命名,只知道它就是一尊印象派的巨作,线条清晰,轮廓分明,蓝红两个主色,代表海洋和陆地,两只紧紧握在一起的手代表友谊;手里握住的一根圆柱直指蓝天,代表力量与方向;我把它分别理解为海、陆和边界。仰头一看,就是一个大写的人,挺立在海陆天地间,两脚一柱落点,恰好构成一个立体的空间三角,很容易令人想起中学时学的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直挺挺地站在塔下照个相,最好是单人照,不要破坏了结构。人在两脚之间,刚好把紧握的手和擎天的柱联结在一起,天地海陆人和都齐了,心里很踏实。
以这里为元点,两国的界碑依次延伸,编号。单数为中国建,双数为越南建。在东兴华美达酒店的35层俯看,大道与小道交织在一起,在界河两岸缠绕蜿蜒。对岸是芒街,越南的直辖市,相当于中国的北京、上海。看上去好像我们眉山的青龙镇。都是各自的祖国,由不得自己选择。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小道就可通向大道。
我终于理解了京族的哈节。哈亭里除了祭神,还要祭哈族英雄,比如鸦片战争中的英雄,抗法战争、抗美援越中的英雄,比如杜光辉、罗顺叶、杜顺强,等等。他们用自己短暂的生命,换取了边境的长久安宁,换取了这里更多人的幸福快乐和长寿。我们到达时,恰逢这里被批准为“中国长寿之乡”。一问才知道,一个百十万人的防城港市,百岁老人达147人,人均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6岁。英雄们为国捐躯时都很小,十几二十多岁,没有子女。村里长者说,我们京族人就是他们的子女,把他们作为这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当神供奉在哈亭里,每年的哈节祭神,就祭祀他们。
这时,我才释了先前在防城港市大街大道上的怀疑。原来,我们自己要享受现代文明,就必然会与历史有一段距离。相对于历史,我们现在所见的许多东西,都是被遮蔽的;越是历史的远处深处,遮蔽越多,假相越多,时间和人,就是一切遮蔽的制造者。按照符号学的观点,一切概念都是人为的设置;只有从元初的小道走进,才能更好地走进真实和真相。
防城港的小道与大道,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西江黄金水道和“一带一路”的陆上海上通道相连,就连接了世界。世间的路很长,我们的路还长。再宽阔的路,我们的行走也只能踏着一脚。对世界的行走,最好从小路进入,就像这次我对防城的走进。
世界太大,我们的脚太小。
责任编辑/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