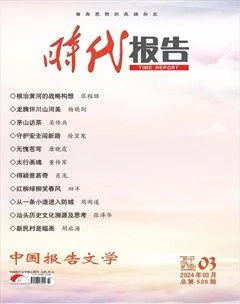星辰是这样闪烁的
张国宝 罗贤
属于他的水稻世界
我国水稻良种培育人管仁欣,他仅仅初中结业,几乎是一直在业余进行着此项科研,最后却大获成功。他的米质优异的粳稻后季稻优良品种选育成功,他培育出的“双丰系列”晚季水稻全国14个省市推广种植,累计达2332.8万亩,增产的稻谷若按彼时奉贤50万常住人口计,可以足足吃上12年……
2023年9月16日早上,我如约赶到他家。在解放新村踏上他家楼梯时,不禁极为吃惊且怀疑自己的眼睛,40年前的老公房,可谓“老破小”,楼栋之间空域狭窄,绿化稀少,破旧的楼梯踏步板裂缝如龇牙咧嘴……
1973年10月21日的《文汇报》,以《育种“专家”》为题的报道提到:“想收千斤稻,要种‘双丰号。”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对奉贤县庄行良种场管仁欣辛勤培育后季稻优良品种“双丰一号”的赞语。一天,他走进一块“农垦58”品种的稻田,仔细观察时突然发现了几个成熟早、杆子粗、穗头大、谷粒饱满的穗头,就一穗一穗地把它们剪下來放进背包里。这一年,他步行了半个月,跑了4个公社,先后收集了1000多个稻穗。接着,他在场里开会,把1000多个稻穗拿出来,请领导和职工一起鉴定。大家经过认真比较,共同鉴定了370个穗头。管仁欣将这370个穗头晒干后,一穗一穗编上号,装在纸袋里挂起来,一冬一春检查了好几次。第二年,场里成立了科技小组,试种了370个穗头稻种。从浸种、移栽一直到施肥、治虫、收割,管仁欣始终和大家战斗在一起。然后,再从370个种穗中挑中了4个优良穗系。第三年,4个小区继续实验,最后从中挑选出一个理想品系,这就是“双丰一号”。他又将“无芒沙粳”与“矮脚南特”杂交。培育出“向阳一号”至“向阳四号”,又从“向阳号”中选育出“矮早粳”;将“科睛三号”与“桂花黄”进行杂交,培育出“科花一号”早稻优良品种。还有水稻与稗草杂交、糯稻与粳稻杂交。他为此苦战整整28年。
为了更深了解并理解其中的专业知识,我购置了很多与水稻繁育相关的书籍及讲义,意通过研读与学习,让我能更深地走近他与水稻的世界。
17岁立志当育种专家
1956年,早春,东风拂扬。
傍晚时分,位于上海县(现闵行区)马桥镇吴会村西稍,颇显气派的两栋横排相距的三开间瓦房,瓦房后有一个牛棚,棚内那头壮实的水牛正大口咀嚼着草料,门口后一侧,17岁的管仁欣正手握大铡刀不停地把一捆捆稻草铡成短短的草料,棚内漾起阵阵稻草清香。
“喂,知道哇,这次苏州农校办培训班,听说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你去考吗?”村西本族的阿介,年龄与管仁欣相仿,不知何时钻进了牛棚,右手卷成个喇叭状神秘兮兮地说。
“喔,去的!去的!”管仁欣惊喜地说。
他的人生幸运又有些曲折。祖父继承了50多亩耕田,父亲又攒钱买下7亩薄田。父亲把20亩田出租,其他40亩自家耕种,父亲与母亲两人每天晚上收工回家,总是累得直不起腰,父亲笃信农民唯有伺候好庄稼才能过日子。管仁欣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奇好,担任少先队中队长。初中在马桥镇念书,每天来回要走16里路。但管仁欣学习极为认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念完初二,父亲铁了心叫他停学。然而在田地间,他仍是得力干将,耕田耙地的农活都会干,挑重担也如一个大汉子,但他的心仍充满憧憬。“我得出去干大事!”他暗自想。
管仁欣是幸运的,报名时在所属的邻松乡政府,那位40多岁的干部对登记的青年说:“农民家孩子都是靠劳动吃饭,让他们去吧!”青年爽快地给他们开了介绍信。
考试那天凌晨,管仁欣悄悄起身出门,到官路上跟阿介会合,去设在闵行镇上的县农业局考场参加考试。管仁欣发挥优异,数学是他的超强项,按照初中毕业程度出的试卷他考了近80分;另外一门科目是语文,他最近看的《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恰巧与考卷上作文命题相近。
发榜时,他名列其中,遗憾的是阿介没考中。
可父亲坚决不让他去,说:“读书读书,都读书去了谁在家里种田!”母亲虽然一直支持他念书,但在家里作不了主。管仁欣在牛棚里边流泪边铡牛草,事情闹得姐夫都过来了,姐夫是小学教师,对岳父说:“考上不容易啊,让他去吧!他个子小,干农活吃力。培训班不要书费学费,国家还发生活费。”
父亲最终同意他去念书。
管仁欣肩上背着用草绳捆紧的被子,脚上穿着大脚趾破口的鞋子去了。“我不管,我是去念书的!”他笑说。身上没一分钱,县农业局干部专门陪送他们去农校。
培训班为期3个多月,需要学习《栽培学》《植物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等8门课,老师上课速度如同灌水一般。尽管学习条件一般,课本是由老师的讲义复印装订的。可这所1907年创办的江苏省立农校,毕业的学生中有5位后来分别成为我国花卉学、果树学、家蚕育种学、蚕体病理学、昆虫学的先驱,并有多位成为农林植物学、微生物化学专家。
许是受上述大家们浸润,在写毕业总结时,管仁欣居然挥笔:“我立志成为水稻育种专家!”
曙光村里冉升理想之光
培训结束后,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到不错的工作岗位上,管仁欣在内的200名学员大多被分配到省农业厅、农业研究所,还有的被分配到其他省办农业中专担任政治教师。他和10多位同学分配到奉贤县农业局,其中一位女同学黄式申,金山县朱泾镇人,出身名门,后来与管仁欣喜结良缘,这是后话。
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要成为专家不啻天方夜谭。希冀与现实水火不容——在所属松江专区的毕业生分配会议上,原专区农业局艾局长的山东普通话声嘶力竭,极富激励:“你们中将来一定会出现一批农作物栽培专家,出现一批果树栽培专家,还有如苏联米丘林那样的果树嫁接大专家……”而苏州农校教导处主任徐国桢,1944年获金陵大学硕士学位的副教授的话如一盆冷水:“3个月的培训,对于你们今后的工作,仅仅摆了个渡,而且是个‘野渡,你们掌握的知识,只适宜在农科推广推广。”
奉贤县农业局专门设立4个農科推广站,每个站负责所属区四五个乡。当时是小乡体制,一个乡辖四五个行政村。管仁欣和贺连云、杨树林等3人被分配到南桥区推广站,推广站设在曙光村,借住在村中破旧房子里。他们都是外县人,40多岁的站长是奉贤人,性格憨厚直率。他在会上音阶拉高八度:“我们的工作就是搞好农业科技推广……”
管仁欣常常说起米丘林,“小米丘林”也是他后来在整个农业局被大家熟知的外号。
“苏联的米丘林、美国的摩尔根,他们能够成为大科学家,我为什么不行?!”他时时在鞭策自己,“不,我自学一辈子知识足够了吧!”
上班的第一个周末,站里的其他3位同事周六晚上已经回家。管仁欣周日清晨出门,乘公交车辗转劳顿5个小时,来到市区福州路上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
管仁欣要买下米丘林遗传学方面和摩尔根的细胞遗传学方面的书。米丘林成功地将北纬30度的果树嫁接到北纬50度的果树上,除此之外,他嫁接的许多果树都获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管仁欣要买下这些书,要把“野渡”变作大海上的勇敢远航。当他已经买了四五本书时,又发现《中国水稻》这部大著书非常有价值,爱不释手。可看那价格,倒吸一口气。他走出书店,在街边踯躅好一阵,咬咬牙下决心买了下来。
为了节省乘车钱用来买书,他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回家总是把每月工资中近3成交给母亲,以此资助弟弟妹妹们上学念书。
工作繁忙且艰辛。奉贤与整个市郊一样,水稻种植由过去的直接撒播谷种改变为秧苗移栽。移栽的分蘖大而产量高,可是病虫害多,防病治虫极为关键,可当时我国农药制造业落后,农药价格贵。除了水稻,棉花、三麦和油菜全都提倡合理密植,大幅度提高了产量,致使防病治虫压力极大。所以,要紧日子里他们必须天天观察所辖乡农田里的庄稼,还有水稻生长期不同的灌水厚度、棉花急需施阶段肥等等,农事上都需要他们拿出方案,由乡领导指挥实施,同时还要汇报县农业局,县农业局汇总资料上报县政府领导。
然而,奉贤的地域大多由大海冲积成陆,因而处处见河流,婉转曲折的小河,河面颇宽的中等河流,还有人工开掘的运河,而被奉贤人称为“养鱼沟”的一条条小溪,遍地都是。一次下午,他们在树浜村,观察三麦的生长情况,傍晚回来走了整整2个小时,还没有走出河流的“包围圈”,最后只能从一条水深半腰的河中涉水而过。他们还经常参加合作社的劳动。管仁欣初二停学扎实务农的一年时间,让他在干农活上成为一把好手,农民和局里领导经常表扬他。但那一次,竟差一点儿害他丢了性命。大暑天的一个下午,他们给村里一个合作社的棉花喷农药,棉株很高,直至胸口,天气十分闷热。管仁欣和两位同事喷完一桶农药后到河边配灌药液,不禁脱了衣服跳入河里去去暑气。清洌的河水凉爽舒服,可脚下河床陡然走深,足有三四米。管仁欣不会游泳,慌忙双手乱拍打河水并喊救命。不一会儿,身子往河底下沉。此时,贺连云、杨树林正游向对岸。还好被岸上碾米厂的老杨看见,奔过来跳入河里把他救了起来。
工作条件艰苦,吃饭也得来回走4里多路到乡政府食堂用餐。
如此不堪,他却说那是天堂一般的生活。白天积攒实践经验,晚上学习理论知识。
10月的一天早晨,只见他站在一块麦田里颇似“范进中举”情景。那是他迈出异想天开第一步:一个月前的星期天,他到南桥镇上自己掏钱买了嫁接用的切刀、钳子、器皿和花盆,回来把放在热被窝中保温催发了芽的数十粒小麦,以一个型号为母本,另一个型号为父本,进行嫁接。嫁接的麦苗不仅全部成活,而且一派生机勃勃。
一心钟情水稻科研事业
1957年冬季征兵开始,他积极响应局领导号召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两天后将穿上军装到部队历练。他无比渴望,那里是大展人生宏图的地方。他匆忙把自己的30多部书,还有自己订阅的《农业通讯》杂志等,打包放在一个布袋里,急急送到马桥镇上一个亲戚家,写信给父母请他们去取。然而第二天,局办公室主任来电话给他:“小管,到部队去的人员已经满额,领导决定你留下来做原来的工作。“好的!好的!”他连连答应。
然而倏然3个月过后,他又得去“流浪”——得益于他们10多位同学工作能力见长,县农业局决定改变推广站模式,为每一个乡配备一名农技员,他被分派到胡桥乡。胡桥乡还不通公路。他乘水上交通,一只响着“突突”柴油机炸声的小木机船,自南桥镇余庆桥码头出发,往西往南又往西往南,逶迤航行3个小时才到达。在乡政府,分管干部看到他不禁有所失望,“这么小年纪哇”。
他工作的地方在胡桥镇北约2里路地方的窑桥村,约三四十户人家。村长领他到了村东头一户农民家,那是一户极为殷实的人家,夫妇俩都40多岁,两个女儿,待人不无亲热亲切。村长对双方做了热情介绍,更是特地嘱咐夫妇俩,一定要为技术员搞好伙食。
工作不多久的管仁欣简直成了半个科技副乡长(该年下半年乡政制改为人民公社),对于全乡农作物的农事安排,都是由他与乡政府指定的专职植保员商量,拿出建议方案,报乡政府主管领导。肩上压重担,他得几乎每天对全乡的农作物作抽样观察,极为仔细。除此之外,还要按照局里和乡里要求,指导种植两块试验田,各两三亩,分别为水稻与棉花。农民讲究看得见摸得着,乡里领导号召做事情,可是怎么做?便带了村长与合作社的干部来观看“先走一步”的试验田,那是立竿见影的。为了种好试验田他必须付出十二分努力。棉花苗移栽时,他特地搞了一根划下等距离记号的绳子,要求社员严格按照记号栽种。水稻秧田的耕翻,深度必须是30厘米,他在现场用尺子多处测量,水田的耙田他亲自干……虽然这些日子艰苦辛劳,但他感慨自己人生收获颇多。如合作社老金社长,从互助组组长干起的,身为老党员,一心为集体的精神让他折服。在确定试验田时,老金社长就告诉他,这两块田肥力足。8月的一个晚上,滂沱大雨下了4个多小时,他担心稻田积水,撑着雨伞,打着手电筒赶到试验田,然而老金社长已经在田埂上用双手扒掉了排水口前堵塞的乱草。
“科技副乡长”干得风生水起。乡里的领导会上布置工作时常常讲“农业局的小管怎么说怎么说”,那两块试验田更不含糊,水稻与棉花单产预测比通常的高出两三成。《奉贤报》有个记者叫陈肃勤,闻讯后乘了小木机船赶来采访,拍下新闻照片又写了文字报道,发表于该报,管仁欣一夜名闻全县。快秋收时,市农业局举办农业大丰收展览,县农业局要送标本过去,选送的同志特地赶到他的试验田,拔了好几大把水稻,放河里洗干净了根须部分,欣然而去。
他没有显现春风得意。农业副乡长赶来,问:“小管,我们的试验田水稻单产报多少?”
“我测算过,亩产800斤多一些。”他说。“可人家报2000斤啊!”副乡长说。他说:“我们只能这个数。”
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他去试验田里的摘棉花,几个40岁上下的妇女叽叽喳喳地笑说:“小娟前世修来的福份呢!什么技术员寄饭,原来是村长介绍的上门女婿啊……”
管仁欣怔住。
“哪跟哪啊!”他简直手足无措。
小娟,虽身形柳条却很结实,农业劳动一把好手,小学毕业,特聪明。管仁欣在她家寄饭,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总是含着笑意,尊敬地叫他仁欣哥,管仁欣对她也如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别无他意。
那一晚上,他天快亮才入睡。第二天清晨,他急匆匆赶到已经是胡桥公社的机关,给分管的公社副书记老陈汇报了这个情况,并提出不再吃寄饭,要赶到公社食堂吃饭。陈书记同意了他的请求。
将水稻科研作出成绩
1964年2月一天,在奉贤县农业局出现一场非同寻常的谈话。
局长说:“小管,今年的粮食作物三熟制种植试验,关系明年能不能全县全面推开。砂北大队徐家村生产队的徐寿均队长很得力,各方面基础都不错。局里这次特地派你去农技领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个人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局里给予帮助解决。”
“请局长放心,我必全力以赴!”他如军人一般霍然站起身,话语铿锵。
县农业局此番尽锐出击,管仁欣一行5人,一位担任蹲点队队长,还有4位是上海农学院毕业生,另外一位则毕业于七宝农校。而此期間,分管农业的南下干部副县长侯尚进,多次骑自行车来试验田查看,尽管他是个“外行”,可总是在田头激励大家:“好!这个长势很好!那个也很好!”
10个月后,试验田结果终见分晓:面积21.435亩,平均亩产1962.4斤,其中大麦亩产304.4斤、早稻亩产843.4斤、后季稻亩产814.6斤;同比去年,比稻麦两熟亩产增62%,比绿肥田双季稻亩产增24%。并且,奉贤粮食三熟制试验种植单产居市郊之首。
彼时,以市郊350万亩粮田计算,三熟制生产若仅仅以亩产增300斤计算,一年可增产10.5亿斤,而10年可累计增产105亿斤,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由此增加2年多粮食支撑。市科委、市科协与市农业局组织市县农技员到锦江饭店撰写粮食三熟制高产经验,以此指导下年全郊区普遍种植。《上海郊区粮食一年三熟制生产经验》一书于1965年3月出版于上海科学出版社,其中汇集了郊县7位农技员撰写的成功经验,而管仁欣的文章置于7篇之首。
在砂北村种试验田是一场苦战。试验田早稻秧苗播种时,恰逢妻子生产,管仁欣为了撒播谷种顾不上去医院。因为他曾到松江参观学习陈永康的种植水稻技术,其中包括撒播谷种,回来练出功夫——每平方厘米3粒谷子,必须不多不少,这件事他必须亲自完成。他上午完成了试验田播种,下午搞杂交水稻播种,一刻也没有停歇。管仁欣从1960年搞起水稻杂交,有籼稻、粳稻和糯稻。杂交水稻播种不同品种的种籽一粒也不能混淆,他特地做了一个精致的无底篱笆筐,一个品种种籽撒播一个篱笆筐内,然后再用镊子,把那些撒播稍疏密不均的调整匀称,细致到可以说是绣花针功夫。下午直至太阳快下山才完成。管仁欣把其他事情托付给徐队长,脚上泥土还没洗净,就拔腿往县医院奔。
“农业科技工作很辛苦,与农民种田没多大区别。分配来奉贤的农学院农校的毕业生,后来大多调走去当教师什么的了。我们培训班出来的,除了其中到部队的,同样剩下不多,有多位干脆回家种田了。”他说,“也有坚持不懈的,极少。”
1959年,县里成立农业研究所,他调入。研究所置于县农场内,农场共100多亩耕田,共50多位职工。他的工作一是为农场领导提供全场农作物防病治虫方案,包括其他主要农事方面的建议;二是专职于水稻和三麦的良种科研培育。1964到1965两年他在砂北村搞三熟制,同时辟建“自留田”继续水稻三麦良种科研。
黄式申刚分配来的时候在县农业局当技术员,1958年因机关干部调整而下乡劳动,又经辗转后调江海公社信用社工作。她小个、丹凤眼,美丽的荷包嘴,智商很高。可她因神经衰弱,晚上难以入睡,导致身体虚弱,最后竟不能从单位集体宿舍走到江海公社机关食堂用餐。当时管仁欣的单位距她所在单位都在南桥镇地域上,相距仅约2里路。她便托人转告老同学管仁欣,请她帮忙从农场食堂买了饭帮她送来。不久,两人坠入爱河。半年后的1961年10月1日,他们结婚了。结婚仪式很简单,到公社机关打了结婚证,买了2斤糖果在各自单位分发了一下,然后叫上双方家人在一起吃了顿午饭。
结婚后,管仁欣更是一心扑在科研上。他为充实自己的大脑不断学习,参加县机关夜校语文班,通过学习取得高中语文单科毕业证书;市科协举办遗传学讲座,他都一次不落地赶到市科学礼堂聆听;他加入了市遗传学会、市种子学会、市作物学会、市农艺学会……他的良种培育科研一路向前。
1965下半年,县农业局成立庄行良种场,旨在为全县主要农作物做好种子提纯复壮,以减缓作物的退化。同时,全县引进的农作物新品种在此地先行试种,然后全县推广种植。整个良种场200余亩耕田,80余位职工。农业局派他去当技术员,庄行良种场一年得提供全县种子10万斤,他的责任更加重大。所幸,他在做好场长“农事参谋长”的前提下,也可名正言顺从事良种培育科研。
整个良种场技术员只有他一个,因此他的工作很忙,他每年参加生产劳动200天以上。甚至良种场的厕所脏了他都会去冲洗,场地脏了他都会去清扫。1972—1973年两年时间,他的肝炎病情严重,可医生每次开的病假条,他都没有交给领导。他常常一边劳动,一边身上虚汗直冒,但他不顾这些,病倒了也不吭一声。面黄肌廋的他自己制作个煤油炉,用于熬药与晚上烧点菜粥作夜宵。为了工作为了科研,他甚至牺牲自己的节假日。场领导经常命令他回家休息,但是他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领导心疼他,局里决定给他发放20元补助,让他用于改善营养,早日恢复身体健康,可他坚决推辞。
10多年里在庄行良种场搞水稻杂交和小麦杂交,总是从上午一直搞到中午1点,才去食堂吃饭。有几次下起雨来,为了保护好杂交水稻,他就把带来的雨衣盖上去,不顾自己身体淋湿。科研探索搞水稻和稗草杂交,为了弄清稗草的开花时间,他和3位职工4天4夜轮流值班查看,终于发现稗草开花于凌晨2点至3点。
…………
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
庄行良种场率先搞早稻尼龙培育秧苗,是一项大幅度提高早稻单产的创新。可是播种时间提早至3月中旬,而场里经济不宽裕,无力购买长筒雨鞋,他只能光脚在冰冷的水田里带领大家干活。谷子播种后,每天上午气温升高时需要打开每个尼龙棚两端放风,傍晚,又要把放风的尼龙棚两端再拉下来。此般操心活他自己干才放心,每天早晚插在水田里的双脚冻得通红。一星期后“倒春寒”,夜里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他带几个年轻人光脚站在水田里扫雪……
要开始早稻播种了,却缺少耕翻秧田的人手,他亲自开手扶拖拉机干,10多亩田精细耕翻得整整一天。场长王金发见了,急忙奔过来,连连摆手,叫喊着:“危险!你不能干!你不能干!”秧田左侧田岸数米高陡直的下坡,如果操作不慎拖拉机翻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从拖拉机座位上跳下来,双手抓着操纵柄,两脚跟着前行。“没事了!这样没事了!”他冲着场长喊道,但他这样干简直会累死。
是年秋,全场100亩水稻已经稻穗灌浆,再有一个半月左右可获丰收,他的10多个杂交水稻同样长势良好。但这两天突然稻飞虱爆发,每一亩达到数万只。那是第三代晚季水稻稻飞虱,接下来以至有第六代爆发。闹不好百亩水稻将会歉收,更何谈外供提纯复壮的种子。但目前场里没有农药了,而百畝棉花需要施的棉铃肥也得赶紧购买。上午,他擅自拉了行政干部周洪才,摇了场里那条可载重一吨的木船去庄行镇购买。老周50多岁,不太会撑篙,管仁欣叫他“顶住”,不让船首撞岸边,他自己摇船水平搭浆,令人担心的是他还不会游泳。他刚刚摇动几下木橹就打飘了,而且一个趔趄跌倒,差一点滑出船外。“不行!你这样要出大事的!”老周大叫。“什么不行,行的!你干好你的事!”他大吼。把长约4米的木橹重新接到铁榫上,又摇起来。到庄行镇水路6里长,其中主要航行于潮汐很大的巨潮港,只能逆水行舟……那天他们购了农药化肥回来,已经是晚上月上东山,但万般庆幸的是安然无恙。
翱翔在自由的水稻王国
深秋的清晨,庄行良种场庄稼地上薄薄一层水气雾,在一股微风吹拂下消逝。他习惯早起,洗漱过后,走在田埂上。眼前的百亩水稻品种为“农垦58”,那是我国从日本引进,是近些年上海市郊种植面积最多的品种,可目前已经出现退化。水稻的一个品种,优势壮盛期一般6~8年,出现退化后单产将逐渐降低。
望着稻田,他不禁沉思,脑海中竟出现了他和黄式申手拉着手,站在推开的窗子前赏景的情景。窗外院子里,那棵梨树紫红的花蕊洁白的花瓣,满枝簇拥。“农夫,我学的农学知识都还给老师啦。可我感觉,你的水稻良种培育选育与杂交两条腿走路很有价值……”黄式申说。
黄式申是有主见的,他想。然后习惯性地抬头远眺,突然回过神来,他收住将跨出的右脚,目光凝视前面。突然看到一棵异样稻穗,身影很大。他摇摇头,定睛一看,然后脱了鞋袜,快速闯入稻田。
世界的一切是动态的,人类种植的作物同样。它们通常表现为退化,但同时极个别的朝着优势方向变化,植物学上称变异分离。
“好一棵优势株啊!”他激动万分。陈永康、洪群英和洪春利,他们同样是先发现优势株,然后精心繁育,在全国多个省市推广种植,并获得高产。他仔细数了数整穗谷粒,100多粒,比通常多10余粒,并且谷粒饱满。更喜人的是已经成熟,早熟足有10天。“过了立秋收秕谷”,说的是后季稻秧苗移栽日期一定得在立秋时令之前,否则歉收乃至绝收。他又走上田埂,边行走边不断查看前面每一块稻田,场内的水稻田里有类似优势株上百棵。他顾不上吃饭,回去拿了工具,赶来走入水稻田里。他把那些优势株一穗一穗用剪刀剪下来,分开放置在一个个纸袋中封闭好,接着装入一个布袋。
赶回的路上他想,附近公社种的水稻中有这样的优势株吗?他把想法告诉王金发场长,老王很支持他。接着就有了前述《文汇报》报道的内容,他10多天跑了4个公社的水稻田。
《文汇报》报道的还有一段:“奉贤县地处东海前哨,有10多万亩盐碱地。‘双丰一号耐不耐盐碱?星火农场用‘双丰一号与其他20多只品种的水稻一起试种,这年由于盐碱地返盐严重,其他品种都渐渐枯死了,唯有‘双丰一号长得清秀挺拔,郁郁葱葱……”
成功的喜讯如春雷滚过奉贤上空。
1971年6月调来奉贤的县委书记王杰,已经注视着这场“大戏”展开——该年全县种植“双丰一号”5400亩,平均亩产729.6斤,同比增约8%。1972年全县种植4万亩,又呈现一派丰产景象,抽样测算比1970年增产10%,个别生产队亩产将达到近千斤。这位原来为我军炮兵团团长、先前作为军管会负责人调任来的领导,对此常常兴奋不已。
10月的一天,王杰书记穿着他那套没有了领章的军装,坐着那辆草绿色吉普车,在县农业局党委书记于建福陪同下,来到庄行良种场(此时已经通了公路)。在场里,他在场长的带路和介绍下,兴致勃勃地查看了全场种植的水稻与棉花。这期间,局党委书记于书记吩咐食堂同志,带了几斤“双丰一号”的谷子到附近村的碾米厂辗成大米,又到镇上买了一只小公鸡、一瓶上海“土烧酒”,搞了个简便中餐,请县委书记品尝水稻优良新品种。王杰书记破例吃了这顿中饭,席上,他连连举杯祝贺管仁欣的成功,举杯感谢良种场全体干部职工的艰辛努力。遗憾的是管仁欣恰巧不在场里。第二天,王杰书记在县委常委会上对自己此次违规吃饭做了深刻检查,并补付了中餐饭钱和粮票。
第二年秋,王杰书记再度破例。那是管仁欣再度向场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书,可因为当时管仁欣出身特殊,党支部不知如何是好,并汇报局党委。局党委于书记小心翼翼请示,“你们把材料送过来,我好好看下。如果没有其他负面情况,这样的同志不入党谁入党啊?!”王杰书记说。两个月后,管仁欣光荣加入党组织。
“又10多年里,他用杂交方法培育成功早稻籼稻品系‘771‘772‘773,又把‘773与糯稻杂交成‘1026,‘771‘772两者都具有成熟早与不自然落谷的特点,适应机械化大面积收割;选育成大麦新品种‘741‘746,两者亩产均在400斤以上,增产15%以上;选育成功油菜‘764,具有植株高大、抗病性强的特点。”县农业局资料记载。
1988年,市人事局、市科技干部局合制的一份报表显示:“双丰一号”比当时普遍种植的“农垦58”单产增产7%~18%,而且出米率高、米质优、口感好,自1972年至1983年市郊累计种植514.8万亩。1968年,他从“农垦57”中成功选育“双丰四号”比种植的“沪选19”单产增产8%~15%,比“桂花黄”单产增产12%~20%,并具有早熟、耐寒、抗病与省肥的特点,市郊种植18万亩;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山东等14个省市,自1980年至1985年每年种植300万亩(统计资料不全)。据安徽省《中国水稻品种系谱稿》资料记载,安徽省1985年种植“双丰四号”103万亩。县农业局那份资料记载,奉贤那些年外供“双丰号”系列水稻种子2000万斤。1985年管仁欣已经调至川沙工作,仍然有安徽的同志来信要求支援调拨“双丰四号”种子。
盐碱地产量基础极低,增产幅度往往奇高。笔者1989年采写的报道《奉贤农业综合开发效益巨大》中提到过:“奉城地区10个村的近万亩盐碱田,过去后季稻单产仅200~250公斤,今年平均370公斤,最高达到500公斤。”按最保守估算,彼时江、浙、沪及山东省濒海滩涂盐碱地种植水稻不下百万亩。
除了在锦江饭店撰写的那篇大作外,上海科技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种子工作手册》,29万字,他撰写良种繁育和比较试验两部分共计8万字,此书1979年2月再次出版;1975年出版的《作物育种》一书他撰写万余字;撰写农业科技方面论文和指导文章50多篇共计20万字,其中近10篇由上海市《科技杂志》发表。
1978年3月18日,管仁欣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置身于庄嚴、神圣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他作为全国3478名科技人员代表之一,前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会上,他获得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为全国获此项殊荣的1192人之一。
长达14天的与会,他激动得每个晚上久久无法入睡。会议结束后,他制订了一个更宏大的科研计划。
管仁欣,是我国农科人星空板块上一颗卓著星辰,其闪烁极为光彩动人!
(因人物要求,文内小娟大娟为化名。文中领导干部职务以事件中任职为准)。
作者简介:
张国宝,上海奉贤人,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职业农民、远洋海员(二副)、记者、企业总经理。纪实类作品《娶新郎》《秀发拂着钢枪》《狱中‘红与黑》《深蓝上的交响曲》等,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多家媒体发表作品,并获得多则奖项。
责任编辑/赵吉政
——柳州农业巡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