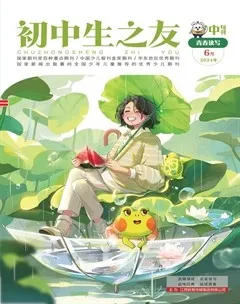延安诗湾
刘成章
延安有个极富浪漫气息的地方,叫作诗湾,竟没有一篇游记写过它。而诗湾,是极有文化价值的所在,是很值得看一看、写一写、品味一番的。
诗湾地处延河岸边,清凉山底部,创建于宋朝,后经历代承续,摩崖石刻很多,只是由于日久风化,不少已漫漶。然而,较清晰的仍有五十多处,参差错落,布满全湾。
诗和湾,一个是文学名词,一个是地理名词,本是两个毫不搭界的词儿。诗是语言的精灵,而湾,是C形之地,上面有石有土有草有花,有人的脚印、羊的蹄痕;诗印在纸上,读在口中,而湾,存在于大地上。可是延安,却把它们奇异地组合在了一起。它漾动着延安特有的风土灵气。恐怕除了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哪里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我相信,即使一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听到诗湾这样的名字,心里也会升腾起一片好奇。诗湾这个名字,即使放到全国看,也是独一无二的,是别异的,比诗还诗,是可以和响彻全国的陕北民歌相媲美的。
在距离诗湾不远的地方,一块巨石高高悬空。巨石之下,是一道凹进去的石崖,悠悠岁月,风雨剥蚀,崖上形成了天然线条,像云霞一般美丽。因此,在那巨石上,古人就刻有“宛若云霞”几字。
在诗湾之旁,有一景致叫作“水照延安”。那是一个月牙形的石钵,石钵里蓄有水,从其一角斜视,可看见对面山上的古城墙倒映在水面。石钵边竖一有趣的碑,碑上反刻着几个字,映到水里后,才变为正的,是“水照延安”四字。而其实,站在这儿,正可一览延城全貌,三川二水尽收眼底。
诗湾的下边是月儿井,左边是印月亭。月儿井是一口十余米深的六角古井。合上印月亭,透过里面的一个圆孔,可以看到月儿井里的水面。井水悠悠浮一月,有时还可看到星星。
在诗湾,镌刻于石崖上的诗,篇篇都是书法艺术,虽久经风雨剥蚀,满目沧桑,但真草篆隶,各闪其辉。假如后退几步,人们可以看到诗湾上方的山形地貌。那里有窑洞,有院落,有出墙枣枝,有伸向晴空的卫星天线,有扯长声儿正在唤猪的大妈的身影。
我再次抬头,重新凝望詩湾,凝望那高悬于半空的石头的诗页,好像望着一本刚出版的诗刊。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延安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这儿的诗情诗意诗葩,硬是超越了以前的任何年月。
那时,一张张油墨未干的《解放日报》,就从这山上飞出。著名作家丁玲就主编着此报的文艺副刊,而这些,距离诗湾只有数十米的光景。这样,在我的思维中,诗湾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就重叠了,或者,诗湾成了这个副刊上的一个显眼栏目。
就在那一时期,艾青的诗、柯仲平的诗、何其芳的诗、公木的诗、贺敬之的诗、李季的诗、戈壁舟的诗,联翩出现在延安。不过,它们与既往的旧体诗不同,这些诗散射着崭新的光芒。哦,一湾的糜谷一样的诗行,一湾的点燃火把的节奏,一湾的红旗翻卷的韵律。它们飞在天上就是鹰鹞,落在地上就是流水。它们使延安的一些崖、一些石、一些窑院、一些柳树槐树、一些吹响的梅笛或管子、一些送饭的小罐和新开的田垄,都曾一闪一亮。
可惜,这些划时代的新诗,却并没有刻在诗湾里面。我想,如果因为诗湾的地方有限,延安有的是湾,有的是石崖,可以另辟一座新的诗湾,把那些诗,还有更多的歌颂延安的优秀诗歌,都刻在上面。这无疑会成为一件文坛盛事。
(选自《中国艺术报》2022年5月13日,有删改)
- 初中生之友·中旬刊的其它文章
- 一双旧皮鞋
- 北窗古樟
- 因……
- 那些令你啼笑皆非的瞬间
- 再见,拖延君!
- 与绿色低碳有关的地道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