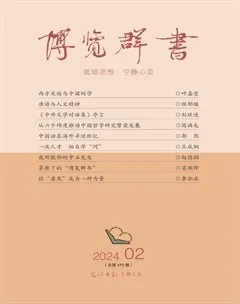数点梅花天地心
王君超
知识分子在过去被称为“读书人”,意思是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在今天的“碎片化阅读”时代,手机屏代替了图书馆,“浅阅读”代替了“慢阅读”。那么,还有多少人像过去那样信奉“开卷有益”,进而“展卷阅读”呢?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过去那那种含英咀华、细嚼慢咽的“慢读”时代,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读书是中国社会主流的阅读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是我的彼时的人生至乐,也是我人生经验中最希望分享的一个方面。
壹
古人认为,读书乃“天壤间第一快乐事也”,因此,“养性莫若修身;至乐无如读书”。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也以书喻人,视为老友。他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读书,先要有书。我小时候的阅读,是从阅读窗户纸上的旧报纸开始的。现在有人讽刺一些报纸版面过于严肃,说必须“立正读报”;岂知我的儿时,不保持“立正”的姿势,还真无法读报。当时往往是在厨房的窗户纸上看新闻,在卧室的窗户纸上看诗歌。版面分离,东拉西扯,懵懵懂懂,良多趣味。如果哪一天窗户纸被风吹破了,那就意味着:又有新的报纸可以看了!
对于一个粗通文字的孩子来说,最喜欢的恐怕还是以画为主的“小人书”。一次,班上有位同学带来一本没有封面的“匹诺曹”,旁边的小伙伴们一拥而上,凑在一起对他的长鼻子研究了半天。据拿书的小伙伴说,这是村上的一位婶婶在大城市里收购的“废品”。没想到在我们的小学,它竟成了宝贝。
大部分时候,大家是拿着卷边缺封面的书来互通有无。准备交换时,双方总爱问的一句话就是:“打不打”?“打不打”是那个时代对有武打、战争情节的“小人书”的“行话”。现在回忆一下,那些“很打”的书虽然最受欢迎,但是读后并不能引发我多少思考;反倒是那些“不打”的书,却让人历历难忘。例如,那时偶然读到一本又脏又破的画书《席方平》,主人公的遭遇竟引起了我长达几十年的心灵震撼。
除了画书,还有对门的三爷去省城探亲带回来的《故事会》。这是一本需要跳着很多生字去读的一本很“深”的书。在他的“高楼”正堂,每当我读得津津有味,他就会忽然走过来,正襟危坐地问道:“史大奈和瓦岗军打登州,用的是什么计?”
再大一点,我开始爬到家里堂屋的顶棚上“淘宝”。那里堆着先父留下的一些“古董”。被我第一批“挖”到的,是四书五经、国学读本,以及解放初编印的《政治经济学》。手持发黄的宣纸书页,凑近油灯观赏,不管能否读懂,都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这一段“青灯黄卷”的读书经历,也激发了我后来对线装书着迷,并大量收藏旧书报的习惯。
“凿壁偷光”的故事大家听过吧?那个时候经常停电,阅读主要靠油灯。喝粥、吃咸菜,在油灯下看缺页少皮儿的书,倒也没觉得什么苦,反而活得有滋有味——好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作业,也没有什么培训班和学习资料,有的只是“柳笛、知了、林场、槐花香”。
常言道:“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读初中时,我在刚从外地打工回来任教的英语教师办公室,发现一本《英语语法》,于是就软磨硬泡地借走,随后一顿狂抄。三四周内,竟全部抄完。后来上了大学,这种状况也再一次重演。那时候在图书馆看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瓦西列夫《情爱论》,读一遍、读两遍都觉得不过瘾,于是就放手来抄。读而后抄,抄而后读,那效果自非“干读”可比。至今,这两本书中的一些丽词佳句,我还能背出一二。
贰
1982年起源于上海,次年在全国呈燎原之势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是80年代大学校园的主旋律。那时候,校园的“读书热”主要表现为诗歌热、文学热、哲学热、托福热,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冲出牢笼,渴望知识的强烈意愿。从金庸、三毛、琼瑶到顾城、舒婷、汪国真;从王蒙、张贤亮、张承志、李泽厚到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托夫勒……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无所不包。与社会上的经商热、气功热、预测学热、人体科技热不同,校园的“读书热”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是元代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的名句。对于愛书人来说,不只大雪封门的冬季适合读书,一年四季都可以体验到读书的乐趣。暮春面对一树繁花,你可吟咏春之诗篇;深秋感慨黄叶飘零,你可朗诵秋之经典;盛夏沐浴荷塘月色,你可与大师神交、笔谈。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正是在如此美好的阅读享受中度过。在弥漫着月季和夜来香气息的郑大老校区,每天穿过流水淙淙的金水河,到图书馆去占座、看书;饿了就跑去食堂填饱肚子。这种“两点一线”式的校园生活模式,虽然缺了咖啡、茶肆的浪漫,但也因读书而变得丰富多彩。为了给考研者提供方便,八角楼里还专门开设了一个“长明灯”教室。如果你兴致未减,大可通宵达旦。
相比平日听课、备考和社团工作的忙碌,假期就显得较为清静。平日里那拥挤的宿舍和偌大的图书馆,似乎成了你一个人的地盘。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意思是买的书因为已经拥有而懒得去读;而借的书则因为限期归还而总会尽快读完。有一个暑假,我几乎天天泡在馆里,一口气读完了列入上世纪80年代争鸣文学书单的所有作品。那个时候正流行“读书热”,校园里到处都是书摊。在每个男生宿舍的床头,除了磁带、随身听和挂历,恐怕最常见的就是朦胧诗集、哲学原著和武侠书了。尽管这些书与普通文科的教材是脱节的,但不得不说,他们扩大了我们的阅读视野,满足了当时大学生“向外看”的需求。
叁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是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名句。实际上,从小学开始,我受的教育都就是不能“死读书”。在中学时代,老师们不止一次地晓谕大家:“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做了记者;之后又读研究生深造,毕业后再作冯妇,开始了全国性的“田野调查”。如果说求学时主打“读万卷书”,那么工作后则开始“行万里路”。那时参加的采访活动,很多也以“行”为名。比如:“西部行”“焦作行”“灾区行”……“行行重行行”,都是为了在旅行采访中获得真知。我形象地称之为“读无字之书”。
为了体验“无字之书”的妙处,很多时候我出差都不带书。原因有二:一是旅途中可以和陌生人聊聊天,多些社交体验;二是可以看看风景或者仰望星空,让大脑处于“排空”状态,以便放飞思绪,“过过电影”,让那些平日里被湮没的思想冒个泡。
长达十年的记者经历,使我的足迹印在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读“无字之书”,不仅使我领略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风土人情;而且也透彻地了解了国情民意,培养了人文关怀。记得20世纪的90年代初,我曾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深入“老少边穷”地区,曾在青海的山路上遇过险,曾在四川采访中受过伤,也曾为广西白裤瑶地区的贫困状况而伤心落泪。有一年的除夕之夜,我还冒着零下40多度的极寒气候采访地震灾区,才明白处于灾难中的人们是多么无助;我多次到港澳台地区采访、交流,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血浓于水”;应邀赴非洲办报,让我感受到了发展中世界的情感互通,“环球同此凉热”。“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些独特而真实的个人感受,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日之我”所断断无法获得的。
记得我刚读大学时,通过表哥认识了一位书法家,便请他写了一副对联贴于床头,那是一副我钟爱的周总理的名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实际上,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学里提倡的做法。在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系主任就要求回乡做社会调查,我于是回到县广播电视局实习,并在省报发表了第一篇新闻作品;暑假里,我又去临县调查当地的眼镜市场情况;之后,与在省城上访的矿工们打得火热,还就他们与当地管理部门发生冲突的事件,写过一个长篇调查报道,很遗憾没有媒体愿意刊登。
当然,“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都有必要读好,而且要放在一起来读。不读“有字之書”,则难以“知书达理”;不重视社会实践,则容易成为“掉书袋”的书呆子。在这方面,李白为天下读书人做出了榜样。他“十五观奇书”“读书破万卷”;十年后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万卷书”加“万里路”,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肆
21世纪初,我从记者转行做了一名学者,算是半路出家。所谓“学者”,原始的意思是“学习的人”。读书,是学者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刚参加工作时,我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一日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日不用功,跟不上毛泽东。”在古人论读书的诗句中,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叫作:“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这是清代学者萧抡谓在《读书有所见作》中的两句诗。
与普通读者“读闲书”不同,学者读书是一件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一方面,备课、讲课、做学术演讲都需要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撰写论文、著书立说也需要博览群书,写好文献综述,也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尽天涯路”。与求学时纯粹的读书、做笔记、增广见闻不同;如今读书,荐书、写书评是读书生活的常态。曾有一家著名期刊希望我为其荐书,我直言勉为其难:“因为过于专业类的书籍,往往只是著书立说的参考;过于生活类的书,似乎又无学术研究的价值。只有那些既有生活哲理,而又不乏学术思维的书,才有推荐的必要。”
那么,应该向莘莘学子推荐哪些书呢?我推荐的保留书目基本上都是大学时代的至爱——《三国演义》(会评本)、《鲁迅全集》、瓦西列夫《情爱论》的第一个中文版、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苏联的译著《趣味心理学》、卢梭的《忏悔录》、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以及范长江的《塞上行》、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等。我的理由是:“这些书之所以至今仍然具有推荐价值,或意境优美,或烛照灵魂,或预言前路,或释疑解惑。”很可惜,现在的莘莘学子,熟读以上书单的并不多。
近几年,我曾给研究生推荐过以下几本书:一是山下英子的《断舍离》,二是李欧纳·科仁《侘寂之美》,三是弗格斯·奥康奈尔的《极简主义》。这几本书,虽然算不上学术著作,但是其功用又超出了同类书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传达的是一种生活哲理和美学原则,而这些哲理与原则又可以运用到各门各类的学术研究上。比如,电子产品、平面设计、影视批评。我认为,“高大上”的书正如历千年而不衰的《道德经》,一定不是与具体的专业紧紧绑在一起的“形而下”者,让你写完论文就想扔掉;而是“授之以鱼”,让人触类旁通。
如果说“好读书,不求甚解”适合一般的泛读;那么,“爬罗剔抉”式的阅读才更适合专业性的精读。在给研究生做读书方法的报告时,我提倡“要联系同类书籍,交流心得、比较各家之论,方能在某一方面‘超越作者”;更进一步的学术阅读,则要求必须带着批判性思维去读。有道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学有专精的博士生来说,读书方法还要汲取阿尔都塞提倡的《资本论》的“第二种读法”——“症候式阅读”;以及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倡的“对位阅读法”。学会前者,将使我们超越在字里行间解码的局限,跨越文本缺失、断裂的障碍,联系整体的社会背景,向作者提出质疑、与作者对话;后者则提倡对文本中矛盾双方同等重视,并互为参照,以避免本质主义掩盖“他者”的呼声。
多年前,我曾建议实施“真人图书馆”项目,变“读死书”为“读活书”,以推进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书”的概念早已出圈、跨界,纸本为书、真人为书,影像亦为书。我也要求自己团队的学生,在深耕纸本之外,也要去读几本趣味盎然的“影像书”——比如电影《大鱼》《楚门的世界》《肖申克的救赎》和《了凡四训》。我的用意是,青年一代要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摒弃成见、学会沟通;辨别真伪、透视假象;培养逆商,自强不息;把握自己、改变命运。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