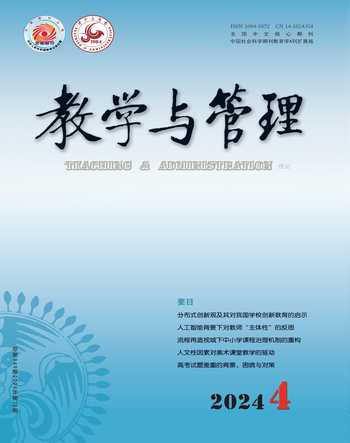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教师“主体性”的反思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机协同”教学活动成为可能,智能机器辅助下的教学也被称为“双师课堂”。但是,机器人真的能成为教师吗?这既是一个技术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教学哲学问题。已有研究对机器人教师角色的阐释和分析走入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穷巷,隐藏着对“教师主体性”和“教学不确定性”的忽视。在教学认识论中,学生是教学认识的主体,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与教师都不仅仅是抽象的角色,还是“具体的人”。教学活动也不能被简化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简单的因果反应,而应是复杂多样的实践活动。
关 键 词 教师角色;教师主体性;人工智能
引用格式 张鸿儒.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教师“主体性”的反思[J].教学与管理,2024(12):10-15.
技术手段的发展丰富了教学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教学问题。“教学手段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发展到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地步,而且由一般的提供音像手段,储存、呈现信息,实现自动化控制,发展到真正的‘教学——‘人—机对话的地步,这样就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它对教学认识过程会带来什么影响?”[1]無论是“计算机辅助教学”还是“机器人辅助教学”,都不曾改变教学活动内部的基本要素结构,而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深度参与的“人机协同教学活动”却是技术对教学活动内部要素的结构化革新。有学者提出,智能时代的教师,是“人师—机师”构成的“双师并存”的时代[2]。这引出了本研究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机器人能否成为教师?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只要技术足够进步,机器人最终将能够实现所有教师的角色功能。然而,从教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答案是否定的。学生是教学认识的主体,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与教师都不仅仅是抽象的角色,不能被肢解为功能的合集。将教师误解为“教师角色”,隐藏着对“教师主体性”和“教学不确定性”的忽视。
一、“双师”的概念隐忧
概念是思维形式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构成命题、推理的要素。因此,在研究命题、推理之前必须首先研究概念。概念是通过揭示对象的特性或本质来反映对象的一种思维形式[3]。“双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目前被广泛运用于职业教育研究和电化研究领域,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指代着不同的语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的相关研究中,“双师”这一概念给予了机器人默认的“教师”角色前提,从而导致了“机器人究竟能否成为教师”这一问题被遮蔽。对“双师”概念的语用分析,目的在于厘清此概念在研究中使用的多重语境,反思其动态的表意结构。
“双师”在中文教育研究语境最初出现在职业教育领域。教师个体层面的“双师型”教师是指既有教学能力,又有社会实际能力;既有理论教学能力,又有实践操作能力的教师。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层面的“双师”是指整个师资队伍由校本师资和校外聘请的兼职教师构成,即二元化的“双师型”师资队伍[4]。在职业教育研讨的语境中,“双师”在指代个体教师时是作为形容词的词性出现和使用的,形容教师在能力、资格方面的双重性。“双师”在指代师资队伍时是作为名词出现和使用的,形容师资队伍由两个类别的教师共同组成。“双师型教师”目前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专有名词,与其他研究领域有着相对清晰的逻辑界限。
而同属于电化研究领域的“双师教学”和“双师课堂”之中的“双师”则有着较大的语义差别,容易混淆其内涵而带来逻辑混乱。“双师教学”的起源依然是职业教育领域,指代两位教师同时进行一门学科的教育教学活动,起初在职业教育中应用得比较多,多数课程由学校导师+企业导师组成的“双师”进行教学,后续也扩展到高等教育等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教学中[5]。后续在基础教育领域,尤其是农村教育中,“双师教学”指的是一节课的课堂教学是由两位教师,即城市学校学科优秀教师和乡村薄弱试点学校本地教师共同配合完成的,乡村教师通过对平台上优质教师的资源进行分析学习后,利用互联网设备选择合适的授课方式完成最终的教学过程[6]。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双师教学”逐步过渡成为促进城乡优质资源共享的代名词,通过“线上名师+线下教师”的协同教学,将城市教育优质资源下沉至乡村学校,达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目的[7]。“双师教学”成为一种通过互联网技术来整合和再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教学模式。此时,“双师”不仅指“线上教师+线下教师”,也可能是指“线上教师团队+线下教师团队”。但无论如何,此时的教师都依然是默认设定的“人类教师”,“机器人教师”还未显现。
“双师课堂”是指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和教师共同在课堂中承担教学工作, 是一种由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承担教师的部分教学任务, 并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的新型课堂模式[8]。此后,“双师”的语义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巨大变化。其根本在于,颠覆了以往“双师”这一概念中“教师”的默认语义,挑战了只有“主体人”才能成为“教师”的前提限定。国外学者将“双师教学”这种远程教学类型中的线上教师称为“由教师充当的机器人”(Teacher as Robot),与之对应的是“机器人作为教师”(Robot as Teacher)。在调查了学生对这两种教师的态度和行为差别后指出,学生认为“由教师充当的机器人”更加可以信赖,并且会带来更多高效的学习行为[9]。机器人教师(Robot Teacher)和教师机器人(Teacher Robot)也同样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前者的本质是教师,而后者的本质是机器人。当我们不区分这两个概念时,也跳过了“机器人能否成为教师”这一理论问题。
本研究采用教师机器人的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教师机器人不能成为或替代真正的人类教师的理论缘由。教师机器人(Teacher Robot,TR)既可以是物理实体机器人,也可以是网络空间中的虚拟人物,是一种广义机器人,可以在各种应用场景中履行教师的功能职责。从理论上讲,教师机器人是一种模拟现实生活中教师的智能行为以实现其教学功能的人工物。在应用中,教师机器人可以直接参与教学实践,也可以间接促进教学过程,从而提高教育绩效[10]。已有研究中存在概念混用的情况,这与教师角色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具有密切关系。
二、“教师角色”的视角局限
何以为师?“教师”不能完全用“教师角色”来解释。教师角色是指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为实现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所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期望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总和[11]。已有研究中,对智能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转变进行了许多讨论[12,13]。但这些讨论更为准确地说是在讨论“教师角色期待”,是对教师应该具有哪些行为的理论预设。然而完整的教师角色,是由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去进行“角色扮演”,完成“角色期待”的行为过程。
“角色”最初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又被称作功能主义或功能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将社会看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组织化手段的系统,各社会组织有序地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有效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角色构成的,角色是“在个人个性与社会系统的结构之间的基本连接点”[14]。“教师角色”是教师个体将自己嵌入学校教育功能系统的立足点,我们通过对“教师角色应该是什么”的回答来指引我们成为教师的行为策略。戈夫曼对这种社会现象解释为“一旦进入某一位置,他便有义务去履行相应角色所包含的一整套行为,因此,角色意味着一种社会决定论和一套有关社会化的学说……角色因此是社会化的最基本单元。正是通过各种角色,社会中的任务得到了配置,执行这些任务的表演得以安排”[15]。这种角色理论使得角色这一概念在使用时,假设了对角色行为期待和角色行为规范统一性的期待,也即用对“教师角色期待”的讨论替代对“教师角色”的讨论,以此消除和遮蔽教师行动者具体的“教师角色扮演过程”。
将角色与规范性共识联系在一起,是帕森斯社会学的重要特色,但这一点在其他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那里引起争论。吉登斯认为,大部分角色理论都过于强调角色的既定性质。重要的是个体在角色“表演”中能够有所影响或者掌控,而不是角色本身。相对于帕森斯的“角色是个人个性与社会系统的结构之间的基本连接点”的观点,吉登斯提出:社会系统不是由角色而是由实践(再生产)构成的,正是实践而不是角色必须被看作是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连接点”(通过结构二重性)[16]。吉登斯的角色理论是关于人类能动者(主体)的理论,目的在于将人类行动的概念与结构性解释联系在一起。而传统的角色理论过于强调角色的规范性,未能关注到角色是抽象的,而角色扮演的过程是由个体展开的能动的探索过程。
回到“何以为师”这个问题,“教师”不等同于“教师角色”这个功能性意味的概念,而是哲学层面的“人类能动者”。教师的本质是主体,而教师机器人的本质则是人工物。教师机器人是人类教师的“代具”而非“代替”,教师机器人是机器人,而不是具有独立主体地位的教师。
“人工物”是指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创造出来的客观实物[17]。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在解釋“技术作为人类器官的投影”时第一次提出“技术哲学”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哲学就是对技术的哲学分析,这种分析考虑到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系统,给相关问题提供一个内在逻辑自洽的哲学总观点”[18]。而“人工物”作为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人造器官”,是一切技术哲学的分析起点。工具和机器都是人工物,机器是多个工具组成的复杂系统工具。
人工物具有二重性。人工物的实然判断是物性的,是客观对象的可测性;其应然判断是人性的,是意识主体的目的性。人类正是依靠这些人造的器官——工具、机器,极大地增强了本身所具备的实践水平。恩格斯曾言:动物对于自然界的创造力主要依赖于本身的存在;但人是利用人带来的变化让自然界为自己服务,从而来控制自然界;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便在于此,导致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劳动[19]。动物是以本能适应自然界,但人是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从而适应自己的需求。人类活动的根本特点是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说:“工具的不断创新,主要依托于原始工具无法满足生产需要或制约生产需要,人类进行改进而产生的。”[20]机器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是目的性、能动性的。教育机器人也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发展出的人工物,是人类目的性行为的产物。
因此,把教师剖解为各种各样“功能”的集合体,并以此证明机器人可以成为教师的论证过程忽视了“何以为师”的本质问题。一架机器是用它所满足的功能来标志其结构的,因而我们可以从指出一架机器的特征来研究这种对应的关系[21]。但教师身份不能完全用其社会角色功能辨认和确证。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更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穿上各种各样的“花衣裳”,但小姑娘是小姑娘,花衣裳是花衣裳。只要技术足够发达,在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机器人将最终都能够完成所有“教师角色”的“花衣裳”,这只是攻克技术难题的时间问题。但我们能否用一个足够漂亮的“花衣裳”去替代“小姑娘”本身?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关涉教学认识论的价值选择问题。
三、从“主体”到“具体的人”
在教学认识论中,学生是教学认识的主体,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与教师都不仅仅是抽象的角色,而且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是“具体的人”。教师机器人能否获得“人工主体”地位的关键在于意识,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尚不可能出现。即使教师机器人获得了“人工主体”的地位,也很难处理教学实践的复杂性,不具备“具体的人”的哲学特质。
1.“人工主体”的可能性省思
人类的活动之所以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具有自我意识。意识的本体论研究可以分为“数字本体论”和“结构本体论”两大派别。简单而言,数字本体论认为意识的本质是数字化的,而结构本体论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多种要素交互过程中的“涌现”。
在数字本体论者看来,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对离散的数字进行拟合与算法计算的过程。“所有的物质世界在本源上是信息化的,而整个世界都可以被还原为各种类型的表征,这些表征又都可以还原为数字。”[22]然而数字本体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并不能全部都被表征化或者数字化。例如,维果斯基就曾提出儿童认知发展中存在前智力阶段和前语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儿童就无法使用符号表征,可见表征能力并不是必然的特征,而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23]。虽然机器人可以模拟人工神经网络,却无法同时模拟人类认识过程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机器人可模拟与可解决的必然是小范围的问题,而不是人类全部意识活动。
结构本体论则认为,意识是一种集体涌现。“自然的认知系统是某种动力系统,与其说认知过程是无表征的,不如说是在某类非计算的动力系统中的存在状态空间演化的。”[24]人的意识活动是嵌入环境的智能体的实时适应性活动。这种系统理论把主体意识活动与环境耦合在一起,论证了大脑、身体与环境的统一性,使得意识与其所处的环境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我们将意识理解为一种弱涌现,那么机器也许会迎来一个“质变”的时刻,从此获得意识。然而我们也可以设想,在未来技术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提取意识,然后上传至计算机。后一种路径将挑战现有的“人”的定义,带领我们步入后人类主义的视野。
人工智能的强弱是从主体角度出发去考虑的,强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识,但其人工主体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自我意识可以使强人工智能的教师机器人获得“人工主体”的哲学地位,但更加具体的主体类别则需要更加具体的讨论。例如法学领域的学者认为,强人工智能是特殊物,即使被拟制为法律主体,也是在特殊物基础上的拟制,必须从强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上的特殊物出发进行研讨[25]。同样地,智能和自我意识也不是成为教育主体的充分条件。
2.教育主体是“具体的人”
教育学家顾明远曾提出:“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抽象地论述人的全面发展,而是第一次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而且预见未来发展的必然。”学者将这种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论述人的人学立场称为“具体人”的人学立场。与近代西方“抽象人”不同,“具体人”以马克思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对人的现实本质的一种全面、深刻的认识。“具体人”是社会人、历史人、文化人和实践人[26]。具备这样特征的人才能够成为教育主体,实现教学活动的真正价值。
教学活动需要由“具体的人”来培育“具体的人”。“如果把人类认识的轮廓线索比作人的骨骼,那么这些骨骼相互沟通联结靠的却是神经递质、关节筋膜——教学。教学虽然并不发现和创造新知识,却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是人类发展阶梯的踏板。其功能与价值有二:保存和传递已有知识,培养能够继承以往、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人。”[2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指出:“教师就是承担着教师责任的专业人才,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也是民族精神与素质传承的载体。”教师不仅仅是向学生传递人类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社会化,使其能够成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成为继承、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教育主体。
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文化是过去的人类历史所凝结生成的精神宝库,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与本质力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把已有的人类精神文化传递给学生,而且还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更新人类精神宝库的文化新人。学生在进入教学活动时在文化意义上是一个“未完成的存在”,对于“人是什么”并没有预先的设定,也没有人之外的力量来决定,只能通过学生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活动来确证。“人的发展始终处于变化中,也是成长与学习的过程;人与生物最大的区别是因为人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28]而教学“成人”的过程在终极意义上是教学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澄明。不仅关注学生可以通过教学获得多少知识,更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彰显与扩展,将学生塑造为社会历史实践的“时代新人”。
教师机器人不具有人类主体的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和实践性。“人工智能驱动模型由于数据资源是一定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工程性,因此在人文精神资源方面较为欠缺,人类的高级性无法被取代。”[29]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机器人教师可以通过识别道德标准、做出行为决策和执行任务等来展现出一定的“主体性”,成为一种介于人类主体与一般事物之间的实体。但是这种“主体性”是功能性的模仿而非有意识的能动性、自我意识以及自由意志的体现,是“拟主体性”,而非真正的主体性。人工智能仅以计算角度而言才具备道德,而当伦理道德被还原为一系列准则时,教学就会变得僵化和死板。教师机器人与学生的交互只是功能意义上的,而人类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才可能是伦理意义上的。
学校教育原本是儿童生活的精神家园,但是技术社会对效率与控制的偏执使人异化为“工具人”“技术人”“知识人”,丧失了人本源性的生命意蕴与灵性特征,因而也就远离了自己的家园。海德格尔指出,在技术社会,人丧失了自由的本质,变得无家可归,并由本源性的“诗意栖居”异化为“技术栖居”,这是现代社会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困境[30]。教育主体的研究要从广义的“主体”走向“具体的人”,将人性的生命活力注入教学活动中,不能因为技术手段的介入将“培养人”的活动异化为“培养工具人”的活动。
四、教学中的“美丽风险”
人类对确定性的寻求和对不确定的恐惧由来已久。“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人寻求安全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开始时试图同他四周决定着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这种和解的方式有祈祷、献祭、礼仪和巫祀等……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明许多技艺,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人就从威胁着他的那些条件和力量本身中构成了一座堡垒。”[31]人工智能技术给教学提供了“确定性”的安全堡垒,然而教学却是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艺术,甚至需要一些“美丽风险”。
1.教学实践的“非线性”
抽象的理论概念具有韦伯所说的“理想型”的特质。“理性典型”这种思想图像并非历史实在,甚至根本就不算什么“固有的”实在,我们建构这种思想图像的目的更不是要将它当作某种模型而将实在当作例子纳入其中,而是它具有某种“纯理想性的界限概念”的意义,当我们想要阐明实在之经验性内容的某些特定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时,我们便可以用它去策略实在,将实在和它进行比较[32]。理论是流畅的,而现实是曲折的。
教学理论就像是地图,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真实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却并不会被包括在地图中。“实践的艺术的难题在于去看见具体。我们通常只能看见理论指引着我们去看的东西。因此我们把蒂娜只是看作学生,我们只能看见认知发展理论或者学生人格分析理论让我们去看见的东西。”[33]角色是抽象的,而教学中遇到的学生是具体的。真正有效的教学交往,需要具体的师生之间的心灵碰触。教师的教学行为存在著一种“理论确定性”与“实践不确定性”的张力,需要教师在“即兴教学”中灵活应对,现场转化,彰显教师的实践智慧。
算法的应用使得教育成为确定性的事件,它企图将一切教育事件改造并且置于物化的世界之中。与此同时,算法将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处理成精确化、自动化的可算度的数据。强人工智能时代似乎将教育世界变成一个完全由算法操控的数据世界,而传统教育所关注的好奇心、爱、创造性与同情心等则荡然无存。然而,教育的功能在于让人们知道如何更好地生活、应该去做哪些更加正确的事情[34]。计算机系统本质上是一些可数的东西,符合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条件。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说,在这样一个封闭系统中,总有一些语句是这个系统本身所无法判断对错的[35]。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数字宇宙,如果我们的大脑都是计算机,那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对这个系统我们能想明白的东西都已经想明白了,剩下的都是永远都不可能想明白的。但如果真实世界是实数的,人脑不是计算机,那我们就有可能随时跳出任何能写成文字的认知系统。我们永远都有一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思路。教师机器人被限制在一个可数的、算法式的世界里,而教师和学生则生活在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之中。
2.教学主体的“显现性”
教学是培养人的活动,教学理论的前提性问题往往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哲学层面上是“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主体”的理论问题。哲学家格特·比斯塔则认为,我们应该跳过这些哲学问题,通过直接致力于教育活动来面对和理解哲学问题,而不是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之前就把它们看成是定论的问题。他主张,与其关注“人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不如关注“人的主体在哪里出现”这一问题。“人如何回应他者、如何回应与自己的不同,会反映出人的主体性。在这种伦理关系中,人的独一无二的主体性会出现于世界。”[36]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实现资格化和社会化,还要使其“主体化”。
“主体性”是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被激发和培育的。人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社会性的制约,但是人的发展又必须追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7]。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对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认知,认为规律处于统治地位,所有一切都要以规律为基准;自由王国是对客观规律有个明确的认知,不但能深刻理解什么是客观规律,同时还可以很好地利用客观规律进行世界的改造。从社会层面看,必然王国以必然性为主导,社会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人类的行为要以此为遵循;而自由王国不再受这种想法的束缚,人们在很自由的状态下去创造历史,学生真正成为了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人。
学校教育曾长久以来背负着“流水线一般生產学生”的骂名,然而这种千人一面的教育现象与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机制密切相关——逃避自由。虽然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赞美自由意志,渴求人的自由状态。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由,自由是人的天性,却也同样是一种需要被激发、被引导的能力。伴随自由的是“任何自我的选择都需要完全自我归责”的责任。于是,便产生了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逃避自由不是病态个体的心理倾向,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指向一种千人一面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境遇。“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 [38]
但是,只有人内心唤醒了自由,才会为全面发展的艰难历程提供源源不竭的内心动力。教学不是一个精准严格的控制过程,教学需要“美丽的风险”来唤醒人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来激发学生的主体性。智能技术的发展会替代如机器般的教师,但是会促进优秀教师回归育人的教育本心。
参考文献
[1] 王策三.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9-60.
[2] 李政涛.智能时代是“双师”协同育人的新时代[J].当代教师教育,2021,14(01):1-4+29.
[3]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形式逻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0.
[4] 曹晔.重视兼职教师的发展 构建二元化“双师型”师资队伍[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06):27-29.
[5] 金煜良,柯清超,姚永安,等.“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双师教学”模式探索[J].中小学电教,2017(Z1):38-39.
[6] 尚凯.“互联网+”乡村教育“双师教学”模式构建[J].现代教育,2019(06):39-41.
[7] 乜勇,高红英,王鑫.“双师教学”共同体模式构建:要素与结构关系分析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12):65-70+78.
[8] 汪时冲,方海光,张鸽,等.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支持下的新型“双师课堂”研究——兼论“人机协同”教学设计与未来展望[J].远程教育杂志,2019,37(02):25-32.
[9] EDWARDS A, EDWARDS C, SPENCE P R, et al.Robots in the classroom:differences in students'perceptions of credibility and learning between teacher as robot and robot as teacher [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6,65(12):627-634.
[10] Zhang,A.H.,Yu,Z.D..Teacher robot,a new concept of modern teaching[A].2011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 Education [C],2011:691-696.
[11]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教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363.
[12] 赵磊磊,马玉菲,代蕊华.教育人工智能场域下教师角色与行动取向[J].中国远程教育,2021(07):58-66.
[13] 秦丹,张立新.人机协同教学中的教师角色重构[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11):13-19.
[14] Parsons.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M].New York:Free Press,1967:11.
[15] Erving Goffman.Where the Action Is[M].London:Allen Lane,1969:41.
[16]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28.
[17] 王德伟.试论人工物的基本概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05):44-48+94.
[18] 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50.
[19][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0-561,378.
[21][31]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11,5.
[22] Wheeler,J,A. Information,Physics,Quantum:The Search for Links [A]. In W.H.Zureck(Ed.) Complexity, Entropy, and the Physics of Information[C]. Redwood City, CA;Addison Weslsy. 2008.56.
[23] 罗伯特,奥托,金伯利.认知心理学[M].8版.邵志芳,李林,徐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641.
[24] Gelder, T. Van.What Might Cognition Be If Not Compution?[J].Journal of Phiosophy,1995,91:347.
[25][26] 李育球.“具体人”教育哲学及其展开——顾明远先生教育思想新解[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6):122-128.
[27] 郭华.知识是个百宝箱——论现代学校的知识教学[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19(04):65-84+186.
[2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14.
[29] 潘军.AI理性价值智能的隐忧与消解[J].自然辨证法通讯,2018,(04):20-25.
[30] 苏鸿.教育研究中“具体的人”——现象学的视域[J].教育发展研究,2007(02):19-22.
[32] 韦伯. 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C].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台北: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219-220.
[33] Schwab J.J.The Practical: Arts of Eclectic[J].The School Review,1971,79(04):493-542.
[34] 赵旺来,闫旭蕾,冯璇坤.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算法”风险及其规避[J].现代大学教育,2020(03):28-34+112.
[35] 阿什福德·李.柏拉图与技术呆子:人类与技术的创造性伙伴关系[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226.
[36] 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5.
[37] 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4.
[38] 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97.
[作者:张鸿儒(1997-),女,陕西安康人,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郑雪凌】
*该文为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的教研传统及其现代化转型”(2024-ZZJH-06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