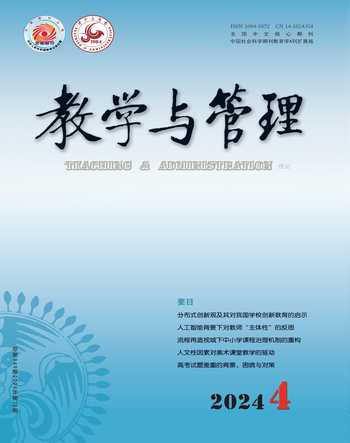分布式创新观及其对我国学校创新教育的启示
摘 要 在现代社会,创新逐渐成为需要高度社会协作的活动,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分布式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心理学都开始关注社会、文化与物质因素在创新中的作用。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分布式创新观认为创新不仅是个体的内部心理过程,更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基于近距离和远距离两种涵义的分布式创新观,我国学校应关注拔尖人才的团队创造力,发展全体学生的创新鉴赏力,提升教育环境的创新承载力,注重课堂教学的即兴创作性。
关 键 词 分布式创新;分布式创造力;创新教育;拔尖创新人才
引用格式 黄睿.分布式创新观及其对我国学校创新教育的启示[J].教学与管理,2024(12):1-4.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对科学家或发明家个人作用的宣传,个体的“创造性思维”被视为创新的核心,创新的社会协作性和文化历史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1]。分布式创造力(distributed creativity)的概念则认为创新不止发生在头脑“里”,也分布在头脑“外”,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是人们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共同建构的产物。分布式创新观突破了过去单纯关注个体创造力的研究视角,对创新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
一、分布式创新观的产生背景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曾指出:“任何发明创造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是属于个人的,其背后总是包含了许多默默无闻者的协同工作。”[2]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创新的社会协作性不断强化,这为分布式创新观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20世纪之前,许多广为人知的创新虽然被归为个人发明,但背后往往也有他人的功劳。例如,电灯的发明是美国的爱迪生和英国的斯万在竞争中相互启发借鉴的结果[3],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则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迪[4]。被誉为某一技术“发明人”的,往往只是该项技术的一个重要改进者。例如,在瓦特之前,英国人纽可门发明的蒸汽机已经在生产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当1763年一台纽可门蒸汽机模型被送到瓦特那里修理时,瓦特才对其进行了重要的改进,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性能[5]。
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复杂化,科学创新的主体进一步呈现出由个人转变为团体的趋势。一百年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98%的论文由单一作者完成,而今则不到5%[6]。对10份美国心理学会期刊的研究显示:从1960年到1980年,平均每篇学术论文的作者数量从1.57人逐渐增长到2.32人,后十年的增长速度快于前十年[7]。近四十年里,在健康、体育与休闲、护理学、物理学、家禽学、放射肿瘤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中都发现了篇均作者数的增长[8]。可见,今天的科学创新很难由个人单枪匹马完成,团队协同创新逐渐成为主流。
随着科学创新由个体行为转变为团体行为,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根据林崇德对34位院士的研究,发现对科学创新人才成长影响最大的10项因素中“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排名第一,且10项中至少7项(交流与合作、导师或研究指导者的作用、中小学教师的作用、父母的作用、大学教师的作用、科研环境氛围、成长环境氛围)与交流合作有密切关系[9]。
二、分布式创新观的基本内涵
分布式创新观的提出者索耶是一位有着特殊个人经历的心理学家。他1982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在电子游戏厂从事了两年的游戏设计工作,之后在另一家企业担任创新技术管理顾问。1990~1994年,他在创造力研究的权威学者奇克森特米哈伊指导下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从事创造力研究。他还是一位有着30多年乐龄的爵士乐钢琴家,长期在芝加哥的一家即兴剧团担任钢琴手[10]。在电子游戏设计团队和即兴剧团与他人共同创新的经历,促使索耶提出了分布式创新观。索耶的著作主要关注创新在人际之间的近距离分布,在此基础上丹麦学者格拉韦亚努进一步分析了创新在人与物之间的远距离分布,以下分别阐述两者的基本观点。
1.近距離的分布式创新
索耶把分布式创新定义为:“人们在密切合作的集体中共同生成一个共享的创造性产物的情境。”[11]有的分布式创新具有高度的限定性和可预测性,如交响乐团的成员在指挥家的指挥下看着乐谱共同演奏,其中可供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少;也有些分布式创新具有很高的开放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可能产生出人意料的创新成果。这种高度开放的、不可预测的分布式创新过程被称为集体涌现(colla-
borative emergence)。
从本质上说,集体涌现是一种即兴的社会交往,其最终结果无法预料。相反,礼节性的交往(如营业员和顾客的寒暄)和被某一个体高度掌控的交往(如单纯下达任务、布置工作的会议)则较不具备集体涌现的特点。索耶等人对学生编演课本剧和即兴剧团的表演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集体涌现具有非预设性、衍生性、交互性、协作性等特征。非预设性是指活动具有无法预测的结果,不可能预先设计;衍生性指的是每个人此刻的行动都和他人前一时刻的行动相关;交互性是指每一行动在交互中能起到何种效果要取决于他人的反应;协作性指的是每一个成员对创新过程都做出了平等的贡献。
举例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对子”就是一种典型的分布式创新。对对子是我国古代文学教育的重要方式,它指的是一个人出上联,另一个人对下联的文学活动,实质上是两个人共同创作一副对联的创新过程。出上联的人无法预料下联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非预设性),对下联的人需要根据上联的结构来设计下联(衍生性)。在下联还没对出来之前,上联的意义始终是不完整的,因此不同的下联会使同一上联产生不同的意义(交互性)。最后,历史上许多出上联者自己苦思冥想无法对出下联,通过广泛传播或征集,才找到了最好的下联,这说明对联是上下联作者共同创新的成果(协作性)。
2.远距离的分布式创新
索耶对分布式创新的研究主要关注“实时的”的集体涌现活动,在这种情境中创新近距离地分布在同一时间地点的几个个体之间。但以对对子为例,有时上下联的作者并不在见面过程中共同创作,而是上联被写出后,下联作者在另一时间地点创作出了下联,两者之间的间隔可以达到上千年。考虑到具有如此遥远距离的创造活动,分布式创新的定义就有必要加以扩展。对此,社会建构主义有深层次的表述。
人类这一物种的独有特点就在于,人类需要在一个被前人的活动所改造过的环境中生活,并且也有能力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人之所以能改造环境,并把改造的成果传递给下一代,是由于人有能力制造和使用人造物,而人造物是被纳入人类活动范围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人类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协作的模式[12]。
现代人从一出生就处于无数创新产品的包围中,并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创新的世界中。正是由于已有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人造物”,如物质工具(机械)、信息工具(计算机、互联网)和心理工具(语言文字、符号、概念),使人们今天从事创新活动更加便捷。正如朱光潜所说:“发明和创造都不免有所因袭。第一个拾树叶遮蔽身体的人,第一个制布帛为衣裳的人,以及第一个发明电气的人都要有若干天才。但是同样天才在原始时代只能拾树叶遮蔽身体,在科学进步时代才能发明电气。从此可知‘社会的遗产对于天才的影响也很大了。”[13]
在当代世界,创新分布于整个世界的物质、能源、信息网络中,也分布于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科研人员和产业技术人员的脑中。在全人类共同创新的庞大系统中,创新成果的原始提出者与改进者、启发者与被启发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的时空间隔。如果把一个集体在同一时空中协作完成的创新称为近距离的分布式创新,那么远距离分布式创新指的就是由跨越时空的多个个体在相互启发、相互借鉴中建构的创新。
远距离的分布式创新要求共同创新者之间能实现跨越遥远时空的交流,而文字和符号信息的记录就成为了实现该种交流的心理工具。对子的上联,作诗时的韵脚、节律,作词时的词谱,都可以看作是辅助人们进行文学创新的心理工具。正如维果茨基所说,文学作品的既有结构(如格律),在每一首新作品中既被遵循又被突破,恰恰是两者之间的这种矛盾构成了诗歌韵律美的基础[14]。由于有了《渔家傲》《水调歌头》等词牌,作词就避免了从一片空白开始创新的困难。作词人只要根据具体的审美需要,选定了要用的词牌,就不必再去考虑每一句的字数、平仄等,而只需要往已有的结构里填入新的词句,从而降低了创新的难度。另一方面,后人所作的新词又以各种不同方式突破和丰富这一词牌,使其艺术承载力得以扩展。
类似地,从个体创造力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道理。分布式创新观则带来一种不同的视角:再古老的诗歌,在其被创作出来的时候,都是那一时代的重要创新。“熟读”作为对已有创新成果的一种传承和模仿,帮助学习者掌握了文学创作中可资利用的一些现成结构,而“唐诗三百首”中提供的大量创新范例,又使学习者内隐地习得了诗歌语言创新的技巧。没有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掌握和利用,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创新。
三、分布式创新观的教育启示
在当代的创新实践中,近距离与远距离分布式创新已经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一方面,创新者频繁利用各个时代的已有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在团队中密切协作共同研究的。过去,人们常把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想象成性情孤僻、独自苦思冥想的怪人。但今天的创新者往往是优秀的组织者和协作者,他们通过互联网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合作者保持联系,在各种交流中互相启发和激发灵感,并通过团队把灵感转化为创新成果。创新者形象的变化相应地对创新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未来的创新人才应该同时具备近距离和远距离分布式创新的能力。近距离分布式创新要求创新者具有在团队中协作和相互启发的能力,而远距离的分布式创新者生活在分布着大量已有创新的文化网络之中,能随时利用已有的创新成果和结构,并且以一种能够和整个共同体的成员对话的形式来表达其创意。上述能力需要通过分布式创新观指导下的创新教育实践才能有效地培养。
1.关注拔尖人才的团队创造力
“钱学森之问”是我国公众对钱學森先生逝世前一直关心的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简称,这一问题常被表述为“我国学校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细读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可以发现:钱老虽然提到要培养“顶尖帅才”,但通篇谈话更强调的是学习共同体的创新氛围,对已有创新思想的借鉴和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启发等因素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例如,他着重介绍了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这所学校“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他的导师冯·卡门一有好的想法马上与人分享,使人听了“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15]。基于分布式创新观,创造力在一个成员组成多样、管理制度合理、氛围友好轻松、相互欣赏信任的团队中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因此,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不能仅关注知识和思维,更要提供机会让学生自发组成团队、协商合作规则、解决人际冲突,找到每个人在创新团队中的角色定位。为此,我国学校可引入教育戏剧、儿童哲学、社会情感学习等促进团队创造力的课程,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2.发展全体学生的创新鉴赏力
任何创新的产生都有赖于多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合作和把关(goalkeeping)。即使有一批具有很强创造力的个体提出了大量创意,但那些负责评价或管理的个体不欣赏这种创新,那些负责协助或执行的个体不具备理解创新和合作创新的能力,则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变为现实。历史上,俄国人波波夫比马可尼早一年取得了无线电表演的成功,但波波夫的发明没有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当波波夫第一次向有关当局申请实验经费时,竟得到了这样的批示:“对于这种幻想,不准拨款。”结果,波波夫的研究很快就落在了马可尼后面,发明无线电的殊荣被马可尼夺得[16]。这说明分布式创造力的培养不能仅面向拔尖创新人才,还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创新型国家建设要求每一个岗位上的公民都能理解和欣赏他人的创新,鼓励和帮助他人创新,管好用好创新团队,充分利用已有创新成果,对创新提供合理回报等。我国学校可通过合作学习、项目化学习和生生互评机制,让全体学生参与到对创新成果的共同创作和评价中,不断发展全体学生的创新鉴赏力。
3.提升学习环境的创新承载力
创造性扎根于物质世界和信息网络中,总是要以一定的物体作为表现载体,并且要借助各种各样的物质与文化资源[17]。研究表明,当教育者为儿童提供了与创新过程相关且具有启发性的工具、资源和方法,儿童对创新过程的参与和投入会大大提高[18]。因此,学习环境建设对于促进分布式创新有重要作用。我国学校可从三方面提升学习环境的创新承载力:第一,大力加强学校图书馆、实验室、艺术馆、博物馆等的建设,建立校内开放实验室和校外合作实验室制度,加强科学仪器、创作工具、电脑软件、人工智能工具的配备,使师生能便捷地获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文化的物质载体;第二,打破个体化、隔离化、封闭化的校園空间设计,通过团队工作室、露天活动场地、小型会议室、咖啡吧等校园公共空间来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非正式人际交流,为近距离分布式创新提供充裕的物理空间;第三,通过校园互联网环境、终端及信息平台的建设,帮助师生迅速掌握世界各地创新动态和成果,与校内外创新者交流合作,为远距离分布式创新铺设广阔的信息渠道。
4.注重课堂教学的即兴创作性
分布式创新观认为,真正有利于创新的教学不是照着剧本进行的表演,而是师生协作进行的“有章法的即兴创作”。一方面,创作要基于一定的结构、框架与限制条件,这就是“章法”;另一方面,创作的最终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是每一个参与者共同创新的产物。有章法的即兴创作体现在三方面的关系中。一是备课与上课的关系,教师不必把课堂的每一细节都规定下来,备课重在备“章法”,为课堂上的即兴发挥准备好基本结构。二是学习任务与学习成果的关系,教师不必把学习结果的形式和内容都规定下来,应给学生提供一定的章法供其创作,可以“旧瓶装新酒”(内容创新而形式不创新,如要求学生写一首古体诗来描写校园生活),也可以“新瓶装旧酒”(形式创新而内容不创新,如要求学生将一首古诗的内容用英文诗表达出来)。三是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教师不必要求每个学生都完成完整的创造过程,而是将学生分为启发者(负责提出大量创意)、限制者(负责选用合适的章法)、整合者(弥合创意和章法之间的冲突)等角色,使学生在互动中生成无法预料的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1] Sawyer R K. Educating for innovation[J].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2006, 1(01):41-48.
[2] Vygotsky L 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n childhood[J]. Journal of Russian &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2004, 42(01):7-97.
[3] 宋牧襄. 斯万对爱迪生——电灯发明的竞争及思想的交互[J]. 中国工程师,1996(03):35-36.
[4] 庞海波. 论创造性思维的自组织机制[J]. 心理科学,2000 (02): 250-251.
[5] 冯剑. 蒸汽机的发明[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8(10):23-24.
[6] Shapiro D W, Wenger N S, Shapiro M F. The contributions of authors to multiauthored biomedical research papers[J]. JaMa, 1994, 271(06):438-442.
[7] Sacco, W P, Milana S. Increase in Number of Authors per Article in Ten APA Journals:1960-1980[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984, 8(01):77-84.
[8] Bird, J. Authorship Patterns in Marine Mammal Science, 1985-1993[J]. Scientometrics, 1997, 39(01):99-105.
[9] 林崇德. 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85.
[10] Sawyer, R K. Creativity,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Keith Sawyer[EB/OL]. [2022-09-31]. http://keithsawyer.com/bio/.
[11] Sawyer, R K, Dezutter S. Distributed Creativity:How Collective Creations Emerge From Collaboration[J].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2009, 3(02):81-92.
[12] Cole, M. Socio-cultural historic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H-
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0.
[13]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5.
[14] 维果茨基. 艺术心理学[M]. 周新,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288.
[15] 钱学森.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N]. 人民日报,2009-11-05(011).
[16] 王欣,司德平. 到底是谁发明了无线电[J].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 2000(06):61-63.
[17] Gl veanu V P. Distributed creativity: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of the creative individual[M]. Cham/Heidelberger: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49.
[18] Boysen M S W. Embracing the network: A study of distributed creativity in a school setting[J].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017, 26(04):102-112.
[作者:黄睿(1989-),男,福建安溪人,厦门大学哲学系,特任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孙晓雯】
*该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哲学视野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FJ2023BF07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