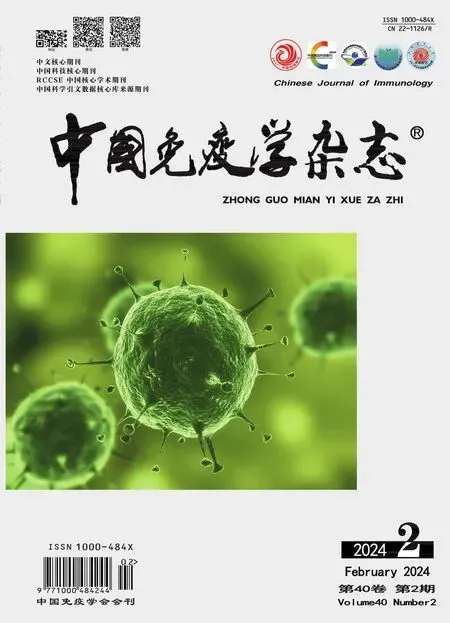肿瘤标志物对免疫细胞的调控效应及其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亓茉言 郭振红 (海军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暨免疫与炎症全国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由肿瘤细胞基因表达的或者是机体对肿瘤反应而异常产生或升高的蛋白质、糖类等物质,这些物质反映了肿瘤发生、发展及预后等情况,被称为肿瘤标志物。血清肿瘤标志物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效果、预后、复发的判断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监测肿瘤发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随着肿瘤免疫学的发展,关于肿瘤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2002年,DUNN等[1]提出了“3E免疫编辑”学说,即:免疫系统清除肿瘤、免疫系统与肿瘤之间实现力量平衡和肿瘤逃逸免疫系统的清除作用,提示在肿瘤的发生过程中,免疫系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肿瘤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肿瘤的发展走向。目前,肿瘤标志物作为肿瘤发生的重要指标,对于其研究也由原来的主要集中于监测肿瘤的发生和发展,逐步转向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临床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主要有CEA、AFP、CA125、CA15-3、CA19-9等,当下,针对肿瘤标志物AFP、CEA和CA125的免疫效应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对其免疫学效应进行综述。
1 甲胎蛋白
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是一种糖蛋白,属于白蛋白家族,最初是由胎儿的肝脏和卵黄囊产生。胎儿血清中AFP含量高,出生约2周后逐渐下降到成人水平,因此正常成年人血清中AFP含量不到20 μg/L。成人血清中AFP含量低的原因主要是肝细胞成熟后合成AFP的能力丧失,当肝细胞突变成肝癌细胞后可以重新获得合成AFP的能力。目前临床上AFP可以作为多种肿瘤的阳性筛查指标并且主要用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和疗效检测。AFP不仅可以作为肿瘤标志物,还具有许多生物学功能,例如白蛋白家族的转运功能、生长调控因子的作用、作为信号分子的作用以及免疫抑制功能,AFP的免疫抑制功能最初是在研究妊娠期免疫调节机制的过程中发现的,当向受孕妊娠期兔动物模型中注射抗AFP抗体后,引起了兔子胎儿的排斥反应[2-7]。进一步研究表明AFP是胚胎正常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因素,AFP能够限制母体免疫系统以抑制抗胎儿的免疫排斥反应以及促进胎儿红细胞的生成[8-9]。目前对免疫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和T细胞方面。
1.1 AFP抑制DC的成熟、分化并诱导其免疫代谢失调 DC作为专职抗原提呈细胞,在免疫应答包括抗肿瘤免疫的启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肿瘤产生的AFP会从多方面影响DC的功能,首先,AFP能够有效地抑制DC的成熟。在脐带血来源AFP(nAFP)和肿瘤来源AFP(tumor source AFP,tAFP)处理后的DC中单核细胞和未成熟DC的标志物CD14表达水平更高,人组织相容性Ⅰ类抗原(human histocompatibility classⅠantigen,HLA-ABC)、甘露糖受体(CD206)、共刺激分子CD80和DC成熟标志物CD83在nAFP和tAFP处理后的DC中表达均下调。LPS和IFN-γ诱导后也未能改变AFP的影响[6]。研究表明, tAFP比nAFP能够更有效抑制CD14+的单核细胞分化成为DC,这可能取决于与tAFP协同作用的低分子量分子的存在,例如脂肪酸、胆红素等[6,10]。分泌蛋白AFP可以结合多种代谢物并进入活化的淋巴细胞、肝细胞、NK细胞和单核细胞。结合脂肪酸的tAFP被DC摄取后会增强DC的糖酵解过程从而分泌更多的乳酸,形成一种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DC的表型随之向免疫抑制的表型转变[11]。此外,有研究者发现AFP能够诱导DC功能障碍和凋亡。AFP处理的单核细胞来源的DC产生IL-12和TNF-α的能力显著降低,并且AFP的处理明显诱导了DC凋亡,从而为肝细胞癌的免疫逃逸提供了条件[12]。而且,AFP处理后的人外周血来源的DC表达caspase-3和p38-MARK的水平升高,这些分子表达的升高会诱导细胞凋亡并抑制DC的成熟,并且AFP能够与肝细胞癌细胞中的caspase-3形成复合体从而影响细胞凋亡信号的传导[10,13-14]。综上所述,AFP能够抑制体内的先天性反应以限制抗肿瘤免疫反应。AFP会通过与代谢物结合进入免疫细胞内发挥作用,但AFP是否还存在其他的配体还未可知,另外摄入胞内的AFP如何影响胞内信号通路还需继续研究。
1.2 肿瘤来源的AFP抑制NK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NK细胞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抵御感染和肿瘤的第一道防线。NK细胞可以表达多种表面受体,包括激活受体(NKG2D、NKp30、NKp44、NKp46)和抑制性受体(KIR2DL3/CD158b)。AFP对NK细胞的影响最初认为AFP可以通过阻止DC产生IL-12(IL-12能够刺激NK细胞表面NKG-2D激活受体的表达)以及增加骨髓来源的天然抑制细胞间接影响全身NK细胞的活化[15],后来,研究者深入研究了tAFP和nAFP对NK细胞的直接作用,但结果显示tAFP和nAFP均能显著增强由IL-2介导的NK细胞活化,并以AFP剂量依赖的方式促进NK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并且nAFP的效果更好,同时表明tAFP和nAFP在短期内没有免疫抑制作用,在小鼠体内实验和人体外实验验证了IL-2疗法与nAFP联用能够发挥更好的疗效,但临床上的数据并非如此,还有其他因素限制了肿瘤内NK细胞的活性[16-17]。静息的NK细胞能够内吞AFP,这一结果提示细胞内的AFP受体可能在恶性肿瘤内发挥作用,长期来看肿瘤来源的tAFP会明显损害NK细胞的活性,并且直接诱导了NK细胞凋亡,而nAFP诱导NK细胞转向促炎表型,通过上调CD69的表达,提高IL-1β、IL-6和TNF-α的分泌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16]。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tAFP与nAFP在糖基化修饰、结合的分子伴侣、等电点等方面的差异,并且确定tAFP损害免疫功能的关键性因素,这对改善肝细胞癌患者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3 AFP改变肿瘤微环境中CD4+T/CD8+T细胞的比例 早期研究发现,AFP能够在体外抑制T细胞免疫应答,这一发现认为AFP可能会促CD4+T细胞分化为抑制性调节性T细胞[18]。最新单细胞测序结果联合体内外实验已证明,AFP阳性的肝细胞癌中抑制性T细胞更多,而细胞毒性T细胞数量减少。肿瘤浸润巨噬细胞上的SPP1与其T细胞上的CD44配体结合促使T细胞转向耗竭的状态,提示在AFP阳性的肝细胞癌患者中,可以通过抑制T细胞上游信号传导从而改变免疫抑制的状态以到达控制肿瘤的目的[19]。此外,有研究者用表达AFP的DC与人外周血T细胞共培养,发现AFP-DC诱导了AFP特异性T细胞反应,AFP特异性T细胞可以显著抑制荷瘤裸鼠的肝细胞癌的形成,并且AFP特异性T细胞的IL-2、IFN-γ、TNF-α、穿孔素和颗粒酶B表达上调,AFP-DC激活的特异性CD8+T细胞IL-10的产生显著减少,该研究者在这一共培养系统中发现AFP特异性的CD4+T、CD8+T细胞主要是通过颗粒酶和穿孔素来杀死癌细胞,但是不依赖Fas/FasL途径,并且AFP特异性的CD8+T比起未经AFP-DC刺激的CD8+T显示出更强的杀伤活性,AFP特异性CD4+T细胞IL-2的产生增加,在抗肿瘤过程中起辅助作用[20-21]。因此AFP-DC可能是一种较好的诱导针对AFP免疫应答的疫苗[20]。
1.4 AFP在临床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以上研究提示,AFP在肝细胞癌对抗免疫系统的效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抑制DC和NK的效应以及T细胞免疫应答实现免疫逃逸。由于AFP的免疫原性较弱,改善免疫系统对AFP的低反应性,是建立有效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关键[22]。因此,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常被作为AFP的“免疫佐剂”被应用。大多数肝癌细胞同时高表达AFP和HSP,HSP可以将细胞质AFP转运到细胞膜并将AFP释放到血清中,所以目前,新型治疗性疫苗HSP70-P/AFP-P就是通过肽合成将AFP表位肽与HSP70功能肽偶联,以增强AFP的免疫原性[23]。另外,2017年启动的一项1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为15例肝癌患者皮下注射AFP衍生肽,没有观察到任何严重不良反应,并且15例患者中有1例完全缓解,8例患者病情稳定。而且在4例患者中检测到AFP特异性的CD8+T细胞,在达到完全缓解两年的患者中观察到亲和力最强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结果表明AFP衍生肽可以诱导强大的特异性抗肿瘤免疫反应,为肝细胞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24]。在肝细胞癌的免疫治疗中,DC疫苗因可以诱导体内特异性免疫应答而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强DC疫苗的抗原提呈能力从而诱导T细胞活化发挥强大的肿瘤杀伤力[25-26]。随着对AFP免疫学效应的进一步研究,有望以AFP为切入点,规避AFP对免疫细胞的负向调控效应,激发针对AFP的免疫应答,为肝细胞癌的免疫治疗带来希望。
2 癌胚抗原
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属于细胞糖蛋白家族,最初发现于结肠癌和胚胎组织中。在人体中,CEA家族可被细分为癌胚抗原相关的黏附分子(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associated adhesion molecules,CEACAMs)和妊娠特异性糖蛋白(pregnancy specific glycoprotein,PSG)。CEACAMs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mmunogiobulin superfamily,IgSF)的成员,一般表现出1个或2个与免疫球蛋白类似的胞外可变结构域,被称为N结构域,CEACAMs在许多类型的细胞表面表达,例如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淋巴细胞等均有表达,在不同细胞表面表达会表现出不同的效应,通常与各种细胞间黏附和细胞内信号传导的作用有关[27-28]。CEACAM家族的各成员在血管形成、细胞凋亡、胰岛素代谢、肿瘤抑制和对免疫细胞的调节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29-31]。在CEACAM家族成员中主要是CEACAM5、CEACAM6和CEACAM1与免疫相关疾病以及肿瘤的进展、转移有关。
2.1 CEACAM5介导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的机制CEACAM5(通常称为CEA)在临床上常作为肿瘤标志物检测。CEACAM5通过糖基磷脂酰肌醇(glycosyl phosphatidyl inositol,GPI)分子的共价键与细胞膜相连,磷脂酰肌醇特异性磷脂酶C(phosphatidylinositol specific phospholipase C,PI-PLC)能够使CEACAM5从肿瘤细胞表面脱落释放到外周循环中[32]。分泌型的CEACAM5常在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胰腺癌和结肠癌等疾病患者的血清中被检测到。研究表明,表达在肠上皮细胞上的CEACAM5通过其B3结构域与同样表达在肠上皮细胞上的非经典的MHCⅠ类分子CD1d相互作用,促进CD1d向T细胞的抗原呈递,同时CEACAM5还能通过其N结构域与CD8+T细胞上的CD8α结合,从而使下游Lck分子磷酸化增加,进而驱动CD8+T细胞分化成CD8+Treg细胞发挥免疫抑制功能[33-34]。通常在正常生理条件下,肠上皮细胞可以通过向T细胞呈递可溶性抗原来促进CD8+T细胞分化成CD8+Treg细胞,从而抑制炎症反应。而在炎症性肠病中,肠上皮细胞则无法有效的呈递抗原,从而导致CD4+Th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失调形成促炎的状态[35]。另外,CEACAM5不仅能单独发挥作用,还能与CEACAM1的免疫抑制功能协同发挥作用,肿瘤细胞上表达的CEACAM5的N结构域可以与NK细胞上表达的CEACAM1的N结构域结合,导致CEACAM1向NK细胞内传递抑制性信号,从而保护肿瘤细胞免受NK细胞的杀伤,进而允许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36]。还有研究表明,与正常结肠上皮细胞表达的CEACAM5相比,转移到肝脏的结肠癌细胞上表达的CEACAM5有更多的Lewis X、Lewis Y糖蛋白修饰,即有更高的岩藻糖基化。众所周知,C型凝集素受体中的树突状细胞特异性ICAM3抓取非整合素1(dendritic cell-specific ICAM3-grabbing non-integrin 1,DC-SIGN)能够特异性地识别N连接的甘露糖以及支链岩藻糖基化结构[37]。因此,表达在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上的DC-SIGN可以通过Lewis X、Lewis Y部分来识别表达在结肠癌细胞表达的CEACAM5,但是不与正常细胞上的CEACAM5结合,并且当DC成熟后这种结合显著降低。所以普遍存在于肿瘤内部未成熟的DC通过其DC-SIGN受体来识别肿瘤细胞释放的CEACAM5,并且呈递给T细胞,这一研究很好地说明了CEACAM5介导的肿瘤免疫耐受微环境的形成机制[37]。
2.2 CEACAM6抑制T细胞受体信号传导 与CEACAM5类似,恶性肿瘤中CEACAM6的表达也显著增加,CEACAM6作为预后标志物和治疗靶点已有许多研究[38-39]。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上表达的CEACAM6能够显著抑制T细胞的反应性,并且抑制TCR信号通路中重要分子的磷酸化,由于CEACAM6无法向胞内传递信号,所以CEACAM6的免疫抑制功能可能是与T细胞上的配体结合所介导的[40]。肿瘤细胞上表达的CEACAM6可与活化的肿瘤反应性T细胞上表达的CEACAM1相互作用来抑制T细胞抗肿瘤反应,这一相互作用独立于PD-1/PD-L1轴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并且PD-1和CEACAM1都是将非受体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募集到T细胞受体复合物上,导致下游激酶去磷酸化,因此它们两者任意一个被招募到免疫突触上就会充分抑制T细胞受体信号传导。因此,可以使用CEACAM1/CEACAM6轴的阻断抗体来改善肿瘤对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41]。
2.3 活化的T细胞表面表达CEACAM1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这一方面CEACAM1的研究和报道最多。CEACAM1又称分化簇66a(CD66a)和胆汁糖蛋白(biliary glycoprotein,BGP)。其胞质结构域的尾部包含两个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immune receptor tyrosine-based inhibitory motif,ITIM)。幼稚T细胞表面不表达CEACAM1分子,但在TCR、IL-2或有丝分裂原刺激后CEACAM1的表达显著上调。CEACAM1是唯一在活化的T细胞上表达的CEACAM家族的分子[42]。CEACAM1的不同亚型可以发挥相反的作用,含有免疫受体酪氨酸基序的长胞质段尾部的CEACAM1-L亚型主要对TCR介导的信号传递发挥负调控的作用,而具有短胞质尾部的CEACAM1-S亚型主要在此过程中抵消CEACAM1-L的功能[43]。CEACAM1-L和CEACAM1-S在不同细胞类型中以不同的比例表达,有研究表明在外周血中大多数活化的T细胞上,抑制性CEACAM1-L的表达水平相较于CEACAM1-S更高,这有助于机体维持免疫稳态,而在肠道和肠道相关淋巴组织中驻留的T细胞中,CEACAM1-S这一亚型表达水平更高,体现了T细胞上CEACAM1的不同剪切类型在不同组织和细胞中的特异性免疫调节[44]。
CEACAM1-L亚型已被证实在许多类型的细胞中发挥抑制性的作用,包括肠上皮细胞、B细胞、NK细胞、T细胞[36,45-47]。原癌基因Src酪氨酸激酶家族的蛋白酪氨酸激酶LCK诱导T细胞中的CEACAM1-L的ITIM基序磷酸化,同时CEACAM1-L与Src同源区 2(src-homology domain 2,SH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1(SH2-containing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1,SHP-1)结合,导致CD3-ζ和ZAP-70的磷酸化减少,从而抑制TCR的信号传导途径[43]。研究表明,CEACAM1-S能够诱导IgA的分泌以及促进T细胞活化,特别是与共生微生物群的控制和对肠道病原的抵抗有关的T细胞亚群,表明CEACAM1-S在肠道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44]。CEACAM1也在固有免疫中发挥作用,CEACAM1能够抑制NK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在MHCⅠ类分子缺陷的黑色素瘤中NK细胞被抑制的强度与CEACAM1的表达量呈正相关,所以,CEACAM1可能是一种新的MHCⅠ类分子非依赖性的NK细胞抑制性受体[48]。除了直接抑制NK细胞的细胞毒作用,CEACAM1还通过下调肿瘤细胞上NKG2D的配体(NKG2DL)的表达进一步抑制NK介导的细胞毒作用[49]。此外,早期的研究已经认为CEACAM1是中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物,并且参与中性粒细胞的凋亡过程[50-51]。CEACAM1可以通过ITIMs磷酸化来招募SHP-1,SHP-1的募集使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receptor, G-CSFR)磷酸化被抑制,减弱了下游STAT3的活化以及促有丝分裂蛋白Cyclin D1和C-Myc的表达,从而抑制了中性粒细胞祖细胞的增殖。而当小鼠CEACAM1缺失后感染革兰氏阳性菌,小鼠出现明显的组织损伤和肝脏坏死,血清中产生IL-1β显著增高,CEACAM1缺失后导致中性粒细胞前体异常产生大量的中性粒细胞,从而引起过度的免疫反应[52]。而当中性粒细胞经革兰氏阴性菌表达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后,诱导Syk磷酸化形成TLR-4、p-Syk和p-CEACAM1的复合物,进而招募SHP-1,SHP-1又反过来使p-Syk去磷酸化,减少了中性粒细胞产生ROS和溶酶体酶,从而抑制炎症小体的活性降低IL-1β的产生。这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CEACAM1在先天性免疫应答中的负调节作用[53]。
2.4 CEACAM1、CEACAM5和CEACAM6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CEACAM1、CEACAM5和CEACAM6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前景广阔,有研究表明在黑色素瘤和结肠癌的小鼠模型中诱导CEACAM1高表达能很好地抑制肿瘤生长[54]。而CEACAM5和CEACAM6常被用于黑色素瘤、结直肠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相关癌肿的治疗干预措施中[55-57]。CEACAM5和CEACAM6的单克隆抗体NEO-201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比较好的疗效。NEO-201是一种IgG1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可以与CEACAM5和CEACAM6的肿瘤相关变构体相结合,NEO-201对结肠癌、卵巢癌、胰腺癌等恶性肿瘤有反应,但对大多数正常组织没有反应,NEO-201不仅可以通过诱导NK细胞介导的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ADCC)和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complement dependent cytotoxicity,CDC)来发挥抗肿瘤活性,还可以阻断肿瘤细胞上的CEACAM-5和NK细胞上的CEACAM-1之间的结合,以逆转CEACAM-1对NK细胞毒性的抑制作用[58-60]。此外,靶向CEA的CAR-T细胞疗法治疗实体瘤已经成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一个备受瞩目的研究方向,2022年国内首个在实体瘤中靶向CEA的CAR-T细胞疗法临床试验获批(受理号:CXSL2200478),临床前小鼠体内研究结果显示出明显的疗效,早期也有研究者针对CEA转移性结直肠癌的CAR-T细胞疗法开展1期临床试验,在10例CEA阳性的结直肠癌转移患者中,有7例患者在CAR-T治疗后病情稳定,有2例患者病情稳定超过30周,并且观察到肿瘤明显缩小,大多数患者在CAR-T治疗后血清CEA水平明显下降[61]。近期临床研究使用压力给药技术通过肝动脉输注将抗CEA的CAR-T直接注入肝脏的区域给药,在1例低分化胰腺癌合并肝脏转移的患者中显示出明显的疗效[62]。综上所述,CEA被认为是在实体瘤中极具治疗潜力的靶点。因此,CEACAM家族成员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靶点有着广阔的前景,希望更多研究发现它们更多的功能和机制,使之成为更好的治疗工具。
3 糖类抗原125
黏蛋白16(mucin 16,MUC16)又称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是1981年美国科学家BAST等[63]从卵巢上皮癌抗原中检测出且能被单克隆抗体OC125识别的一种糖蛋白抗原。CA125是常用于检测卵巢癌进展的常规临床生物标志物,CA125是MUC16上的重复肽表位。全长的MUC16蛋白核心是由短胞内结构域、跨膜结构域和长的糖基化细胞外结构组成。该糖基化细胞外结构是由含156个氨基酸的重复结构域所构成的,这些重复单元包含许多表位结合位点,该分子还包括富含丝氨酸/苏氨酸的氨基末端结构域,该结构域容易发生MUC16的O-糖基化。MUC16在其跨膜片段上游大约50个氨基酸的位点上可以被蛋白酶水解切割,使MUC16的胞外段从细胞表面释放形成分泌型的CA125[64-65]。MUC16的糖基化位点在促进肿瘤转移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糖基化位点是否还影响着抗肿瘤免疫反应还需要继续深入地研究[66]。
3.1 MUC16抑制先天性免疫反应 许多研究表明NK细胞、单核细胞等天然免疫细胞无法攻击表达高水平MUC16的肿瘤细胞。异常糖基化的MUC16会与NK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结合,发挥抑制肿瘤免疫的作用。例如,PATANKAR等[67]的研究小组首次证明MUC16敲除的卵巢癌细胞更容易被NK细胞裂解,这表明MUC16对NK细胞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肿瘤来源的MUC16能够下调NK细胞上的CD16和VD92/NKG2A表达,使NK细胞无法通过这些受体发挥作用来杀死肿瘤细胞。此外,该小组继续研究发现与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的NK细胞相比,在同一患者的腹腔积液中的NK细胞的表型会发生改变,最明显的差异在于CD16-CD56brNK细胞,MUC16能够选择性地结合30%~40%的具有细胞毒效应的CD16+CD56dimNK细胞,同时诱导NK细胞上CD16的表达下调,进而选择性地增殖CD16-CD56brNK细胞这一亚群,CD16-CD56brNK细胞毒性明显降低从而促进了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68]。抑制NK细胞和癌细胞之间的免疫突触形成则是另一种MUC16介导的免疫抑制机制,同样研究小组研究发现在NK细胞白血病细胞系(NK cell leukemia cell line,NKL)的刺激下,能够存活下来的肿瘤细胞表达更高水平的MUC16,小鼠的MUC16敲低后在NK细胞和肿瘤细胞间更容易形成免疫突触,从而增强NK细胞介导的细胞溶解反应,这表明NKL细胞可能选择性裂解低表达MUC16的肿瘤细胞[69]。后来,该作者又发表研究表明,MUC16不仅能与NK细胞结合,还可以与从外周血和腹腔液中分离出来的B细胞和单核细胞结合,MUC16可以通过结合表达在B细胞、单核细胞及NK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Siglec-9,促进肿瘤免疫逃逸[70]。而当干扰角膜上皮细胞表面MUC1和MUC16的表达后,加以Toll样受体(TLR2、TLR5)激动剂刺激后促炎细胞因子IL-6,IL-8和TNF-α表达和分泌水平增加,并且在MUC1-/-和MUC16-/-的小鼠模型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泪膜黏膜层的电镜结果进一步证实,MUC1或MUC16能够在角膜上皮细胞膜表面形成致密的糖保护屏障,阻止病原体与抗原提呈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结合,从而抑制先天性免疫反应维持眼表的免疫稳态[71-72]。综上所述,肿瘤细胞上高表达MUC16后,能够显著抑制免疫反应,促进肿瘤逃逸,而正常组织中的MUC16的表达能够防止不必要的TLR激活维持正常组织的免疫稳态。以上研究已经明确MUC16免疫抑制的作用,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继续研究。
3.2 MUC16突变产生新肿瘤抗原 MUC16突变产生的新生抗原在肿瘤免疫中也有着重要作用,这代表MUC16可以作为基于肿瘤新抗原的个体化疫苗的潜在靶点。MUC16在大多数恶性肿瘤中频繁突变,是突变频率位居前三的基因之一[73]。2017年在Nature上报道的一项针对少数胰腺导管癌的长期存活者的研究中,分析这一队列中的T细胞抗原发现MUC16突变产生的新抗原是这些胰腺导管癌患者长期存活的原因,同时还与肿瘤CD8+T细胞高度浸润有关,他们发现这些突变而来的新抗原具有富集并且激活CD8+T细胞的能力[74]。在此之后,MUC16的高突变与肿瘤免疫的相关性在黑色素瘤、胃癌、肝癌、结肠癌等多种肿瘤的研究中均有报道[75-78]。在一项包含30个实体肿瘤、9 850个样本的mRNA序列的泛癌分析中发现,MUC16突变的肿瘤微环境中有更多的免疫细胞浸润,GSEA富集分析也证明了MUC16突变主要富集在免疫相关信号通路上,因此MUC16有望成为一种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79]。
3.3 MUC16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MUC16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是一个极具治疗潜力的肿瘤相关抗原。在一项针对卵巢癌的研究中表明,在人类卵巢癌细胞系和卵巢癌组织中观察到MUC16显著的高表达,MUC16的过度表达通过PI3K/AKT通路促进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入侵,将MUC16过表达到DC上时能有效地激活CD8+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为卵巢癌的免疫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80]。此外,MUC16应用于CAR-T疗法也有许多研究。2010年,研究者设计了靶向MUC16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表达在肿瘤细胞表面的MUC16大部分胞外段被蛋白酶水解释放到细胞外,可以在血清中作为肿瘤标志物CA125检测到,然而MUC16分泌出去后在肿瘤细胞表面仍存在一小段残留的细胞外部分,称为MUC16-CD,MUC16-CD可以作为肿瘤免疫治疗中有力的靶标,因此研究者设计了针对MIC16-CD抗原的CAR-T,在体外能够特异性地裂解卵巢癌细胞,在小鼠原位异种移植的肿瘤模型中也显示出有效的抗肿瘤的功效,但仍存在CAR-T细胞被肿瘤微环境抑制的问题,仅卵巢特异性的CAR不足以消除肿瘤[81]。之后,研究者继续开发了一种能共同表达IL-12受体激动剂和靶向MUC16表位的CAR-T细胞疗法,IL-12和MUC16双靶点的联用能够很好地改善CAR-T细胞被肿瘤微环境抑制的问题[82-84]。此外,MUC16是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之一,许多研究证实MUC16高突变率与实体瘤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反应性相关[79,85],MUC16突变的患者显著上调PD-L1、PD-1和CTLA-4等免疫检查点的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队列和黑色素瘤队列的分析表明,MUC16的突变与免疫检查点治疗反应性高度正相关[79],这一结果提示MUC16有望成为指导免疫治疗的标志物。
4 结语
尽管目前对于肿瘤标志物的效用存在许多争议,许多科学家也在寻找新的特异性更高的肿瘤生物标志,但无可争议的是AFP、CEA、CA125等分子仍是临床上最普遍使用的生物标志。许多肿瘤标志物不仅仅在肿瘤的诊断、发展及预后等方面提供指示作用,更在肿瘤的免疫调节以及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有助于初步了解肿瘤标志物是如何影响免疫细胞从而形成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对于肿瘤抗原的研究仍存在许多难点,例如:寻找肿瘤组织特有的并且可以被适应性免疫系统特异性识别的新抗原;探究肿瘤新抗原介导的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的机制;开发针对肿瘤新抗原的免疫疗法。随着技术方法的进步和研究模式的创新,结合多学科交叉,从更宏观或深入的角度探究更多肿瘤标志物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有望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思路。肿瘤的免疫治疗为肿瘤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对肿瘤标志物的深入研究将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