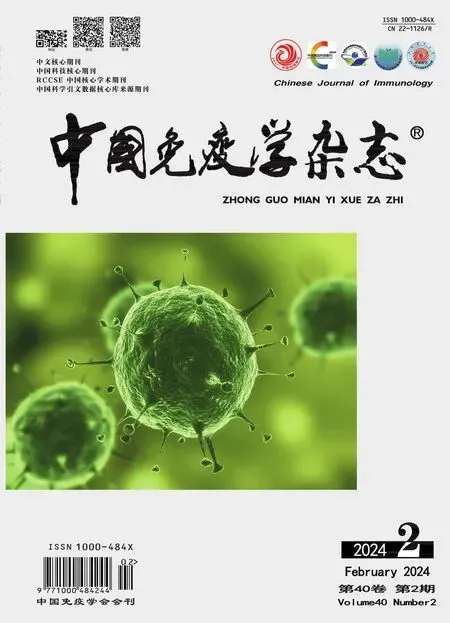重组人分泌型磷蛋白1与呼吸系统疾病相关性研究进展
薛婷 杜伟勤 (.国家卫健委尘肺病重点实验室,煤炭环境致病与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防治与基础研究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太原 03000;.吕梁市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吕梁 033000)
重组人分泌型磷蛋白1(secreted phosphoprotein 1,SPP-1),又称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是一种多功能分泌型细胞外基质糖基化磷蛋白,广泛分布于骨、肾、肝、肺等多种组织以及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等细胞中,参与机体的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如在骨组织中促进破骨细胞分化、骨形成和骨重建;在机体炎症反应中发挥促进或抑制炎症的重要生物学功能;SPP-1可作为一种趋化因子招募炎症细胞并诱导其分泌细胞因子参与机体免疫调节机制;此外,SPP-1在多种癌症中高表达,与肿瘤生长和转移密切相关;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SPP-1在呼吸系统疾病中表达丰富,可通过调节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在该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就SPP-1与呼吸系统疾病相关性进行综述,以提高和加深人们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及其治疗的认识。
1 SPP-1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持续存在且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的、可预防和治疗的慢性炎症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多种环境因素与机体自身因素长期相互作用有关,病情呈进行性发展,其病理特征是肺部炎症、气道及血管重塑、肺纤维化(pulmonary fibrosis,PF)和肺组织损伤,COPD病因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SPP-1可诱导气道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NEUT)性炎症和气道重塑,在COPD患者中表达增加[1]。腺苷是细胞受刺激或缺氧时产生的信号分子,腺苷通过激活A2BR信号通路引起多种炎症因子释放,诱导机体募集炎症细胞如NEUT、巨噬细胞等,上调SPP-1、MMP-9、MMP-12、TIMP-1因子的表达,促进COPD的发生与发展[2]。SCHNEIDER等[2]和SUN等[3]对腺苷脱氨酶(adenylate deaminase,ADA)基因敲除Ada-/-COPD小鼠模型的实验研究发现,肺组织SPP-1表达增加,进而趋化SPP1依赖的NEUT,诱导MMP9等介导气道重塑相关基因的表达,出现与肺气肿患者肺组织病理学变化特征类似的肺泡腔扩大等表现,而双基因敲除Ada/Spp1-/-COPD小鼠模型中SPP-1的表达及其依赖的NEUT的趋化作用和MMP9表达及肺部炎症反应均较Ada-/-模型显著减少,且肺泡腔较窄,提示SPP-1是腺苷及其A2BR通路下游引起肺泡腔结构破坏和肺组织损伤的重要因子,是导致肺气肿的主要介质,且与气道阻塞的严重程度相关,参与调节促进COPD发病机制的多个过程,因此SPP-1可作为评估COPD进展的生物标志物及其治疗的潜在靶点。辛伐他汀在COPD发生发展中可抑制促炎和诱导抗炎因子的表达,MANEECHOTESUWAN等[4-5]和SCHENK等[6]通过随机双盲安慰剂交叉试验的临床研究发现服用辛伐他汀的COPD患者痰液上清液中IL-13、SPP-1、CD73、IL-17表达下降,IL-10、ADA表达升高,且上述因子变化与患者有无吸烟史及激素治疗史无关,随后用香烟烟雾提取物(cigarette smoke extract,CSE)和辛伐他汀干预分别源于COPD患者和健康受试者的单核-巨噬细胞(monocyte-derived macrophage,MDM)探索相关信号通路,结果显示CSE通过激活STAT6显著促进IL-13的表达并诱导SPP-1的产生,而辛伐他汀在此过程中发挥反向作用,即抑制STAT6/IL-13通路,使STAT6磷酸化降低,进而影响SPP-1表达,导致COPD患者MDM中ADA表达增强,逆转ADA与SPP1的失衡,提示IL-13/STAT6-SPP-1轴可能是辛伐他汀治疗COPD的作用靶点,但该方案对COPD患者肺功能恢复、减少PF和黏液分泌的机制有待阐明。此外,SPP-1与COPD急性加重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其表达水平随COPD严重程度而显著增高,感染是COPD急性加重患者的常见诱因[7]。抗菌蛋白(antimicrobial proteins,AMPs)是呼吸道固有免疫反应中的重要抗菌效应分子,研究表明SPP-1可与AMPs或某些细菌表面成分相结合,削弱AMPs的抗菌活性,增加COPD患者感染的风险,进而导致病情加重和恶化[8]。
2 SPP-1与哮喘
哮喘是一种以气道慢性炎症和高反应性为特征的异质性疾病,SPP-1是诱导Th1细胞介导免疫应答的促炎细胞因子,T-box家族转录因子T-bet是Th1特异性转录因子,可诱导产生IFN-γ,进而调控SPP-1在活性T细胞中的依赖性表达,促使Th0细胞向Th1细胞极化,在Th1相关免疫应答过敏性哮喘等气道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9-10]。SPP-1在哮喘等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过程中对Th1/Th2/Th17平衡及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s)、肥大细胞、嗜酸粒细胞等不同类型免疫细胞具有潜在的调节作用,SPP-1作为一种双向调节细胞因子,在哮喘发病不同阶段具有多向性,在致敏阶段是促炎细胞因子,在激发阶段可抑制Th2细胞免疫应答发挥抗炎作用[11]。ALISSAFI等[12]研究表明SPP-1的SLAYGLR基序可与细胞表面整合素a9b1特异性结合,差异性调节浆细胞样DCs(pDCs)/经典DCs(cDCs)平衡倾向于pDCs的抗炎免疫调控作用,促使pDCs分泌Ⅰ型干扰素,进而上调pDCs表面归巢分子趋化因子受体CCR7表达,致使pDCs归巢至引流淋巴结,诱导机体对变应原产生免疫耐受,提示SPP-1可作为针对变应原有效预防和治疗过敏性气道炎症的机体免疫耐受性增强剂。动物研究发现SPP-1-/-小鼠体内特异性IgE和Th2细胞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增高,经重组SPP-1干预后减少了特异性IgE的产生,表明SPP-1可抑制机体抗原特异性IgE的产生并发挥抗炎作用[13];XANTHOU等[11]经SPP-1-/-小鼠证实了与上述一致的结果,然而运用SPP-1特异性抗体作用于SPP-1-/-小鼠,机体炎症反应增强。此外,SPP-1与哮喘相关性的临床研究显示:吸烟哮喘患者痰液SPP-1高于不吸烟哮喘患者,严重难治性哮喘患者痰液中SPP-1较病情轻者低,提示SPP-1与哮喘严重程度、肺功能受损以及气流受限有关[14-16];而XU等[17]发现哮喘患者中SPP-1蛋白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增高,但在过敏性与非过敏性哮喘患者中无显著差异,并证实SPP-1表达水平与哮喘严重程度无显著相关性;当哮喘患者年龄增长或感染呼吸道病毒时,诱导机体释放SPP-1,激活TGF-β1/Smad3信号通路,进而加重迟发性哮喘(late-onset asthma,LOA)患者的气道炎症和PF,因此血清SPP-1可作为LOA早期诊断的潜在无创性生物标志物[18];SPP-1多态性临床研究表明,哮喘患者SPP-1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是哮喘发生发展的遗传风险因素,且与哮喘临床表型有关[19]。由此可见,SPP-1在哮喘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重塑等致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部分研究结果存在矛盾,可能与SPP-1功能和结构域识别、过敏性哮喘发病、致敏与激发不同阶段机体的免疫反应以及SPP-1与哮喘发病过程中机体炎症细胞之间免疫调控的复杂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尚需进一步阐明。
3 SPP1与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是一种以肺血管结构和功能改变致肺血管阻力增加和平均肺动脉压进行性升高为特征,可最终导致患者右心室功能障碍甚至衰竭,且预后较差的复杂性渐进性恶化性疾病,该病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是肺血管重塑。SPP-1在肺血管性疾病的发展和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Tenascin-C是整合素αvβ3配体,与αvβ3相互作用可加速血管重塑,尤其是促进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s)的增殖,其表达量与肺动脉压力呈正相关,Tenascin-C沉积可加速肺血管重塑,而SPP-1与αvβ3为配受体关系,二者结合可抑制因Tenascin-C下调而引起PA-SMCs凋亡[20]。MENG等[21]通过PAH动物实验证实SPP-1可通过部分激活αvβ3-AKT和αvβ3-ERK1/2级联信号增强PAH大鼠PA-SMCs增殖和迁移,加速PAH进展与恶化;对体肺分流建立PAH大鼠模型给予整合素αvβ3中和抗体XJ735,可改善SPP-1诱导PASMCs增殖和迁移效应导致的肺血管重塑,有助于减轻PAH引起的肺血管损伤,显著缓解机体PAH状态,逆转肺血管重塑,提示该方案可作为PAH潜在治疗新策略。鞘氨醇激酶-1(Sphk1)是鞘脂代谢过程中关键限速酶与细胞内信号转导酶,Sphk1激活使鞘氨醇代谢产生鞘氨醇-1-磷酸酯(S1P),S1P是一种参与细胞增殖、迁移及细胞信号间传导等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磷脂,CHEN等[22]研究显示Sphk1和S1P mRNA和蛋白水平在PAH患者肺组织与低氧诱导PA-SMCs中显著上调,SphkK1/S1P信号促进PA-SMCs增殖和肺血管重塑,提示改变SphK1/S1P代谢途径可能是改善PAH进展的有效靶向治疗方案[23-24];此外,活化T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 cells,NFATs)是钙调磷酸酶(CaN)的重要底物,Ca2+升高激活CaN,活化型CaN与NFATs结合,使NFATs氨基酸末端调节结构域去磷酸化,NFATs核定位信号被暴露发生核转位而移入细胞核内,同时与其他相关转录因子协同作用,调节目的基因的特定转录与表达,SPP-1启动子的多个位点与NFATc3结合,激活NFATc3上调SPP-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而S1P可激活磷脂酶C(PLC)和CaN/NFAT/SPP-1信号通路,进而诱导PA-SMCs增殖,YAN等[25]运用U73122和CaN抑制剂环孢菌素A(CsA)或siRNA靶向沉默NFATc3分别抑制PLC和CaN,阻断CaN/NFAT信号通路,影响NFAT活化和S1P诱导SPP-1表达;由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γ)的激活可抑制SPP-1表达,进而抑制PA-SMCs增殖,随后运用PPARγ的激动剂吡格列酮干预PA-SMCs,结果发现S1P诱导的NFATc3激活受到抑制,阻断CaN的活性,PA-SMCs中SPP-1的表达降低,表明PPARγ通过抑制S1P诱导的CaN/NFATc3通路使PA-SMCs中SPP-1表达下调,进一步多角度证实S1P通过激活CaN/NFAT/SPP-1信号通路诱导PA-SMCs增殖[25]。相关临床研究显示,SPP-1在重度PAH患者的肺组织中表达水平显著增高,表明SPP-1与PAH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评估和监测PAH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及右心室功能障碍和衰竭的生物标志物[26-27]。上述研究均提示SPP-1可促进PA-SMC增殖进而引起PAH的发生发展,且SphK1/S1P代谢途径与CaN/NFAT/SPP-1通路可作为PAH潜在的治疗靶点,进而有效改善PAH患者的风险分层。
4 SPP-1与PF
PF是一大类以成纤维细胞增殖、胶原沉积、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大量聚集、肺组织结构破坏、肺功能受损为主要病理特征呈进行性发展的各种间质性肺疾病终末期病变,致死率较高。SPP-1与PF发病机制密切相关,其可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表达,促进成纤维细胞的迁移、黏附和增殖,研究显示SPP-1-/-小鼠肺组织MMP-1、MMP-2、MMP-9与胶原蛋白的沉积、肺部炎症以及PF程度较对照组减少[28]。IL-17主要由CD4+T细胞亚群Th17细胞分泌,在宿主适应性免疫和固有免疫之间起关键调节作用,Th17细胞及其所分泌细胞因子如IL-17的高表达与PF进展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在博来霉素(Bleomycin,BLM)诱导PF动物模型中,SPP-1的表达促进Th17细胞的分化,ECM和成纤维细胞增多、分化和增殖,OH等[29]学者研究发现SPP-1-/-小鼠Th17细胞分化和IL-17的产生较野生型小鼠明显降低,表明SPP-1通过影响致病性IL-17/保护性IFN-γ的比例参与BLM诱导的肺部炎症和PF。TGF-β1是PF进程中最强的致纤维化细胞因子,相关信号通路TGF-β1/SMADs/SMOC2以及MAPK/ERK参与PF发生发展[30-31]。DONG等[32]研究显示SPP-1通过激活TGF-β1信号通路引起成纤维细胞的分化以及肌成纤维细胞的活化进而促进多壁碳纳米管(MWCNTs)诱导的PF,推测抑制SPP-1可阻止TGF-β1/SMADs/SMOC2通路,进而减弱PF进程及肺损伤,但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33];DONG及其团队随后证实MWCNTs诱导肺成纤维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核中NF-κB的主要活性亚单位NF-κB p65磷酸化,调控相关基因MMPs组织抑制因子1和SPP-1的表达,提示NF-κB信号通路在PF致病机制的基因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34]。此外,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弥漫性间质性PF,是最常见的PF表现类型,MerTK是表达于巨噬细胞表面具有促吞噬作用的蛋白质,可吞噬受损或衰老的肺泡上皮细胞,MORSE等[35]对IPF患者肺细胞转录组测序研究显示,IPF患者肺组织尤其是肺下叶中表达MerTK巨噬细胞亚型的增殖及其所分泌SPP-1的表达水平较健康人群显著增加,而表达FABP4的巨噬细胞亚型出现死亡或者向其他巨噬细胞亚型转变,表达FCN1巨噬细胞亚型在IPF与健康人群中较为稳定并无显著增殖,提示表达MerTK巨噬细胞亚型的增殖以及SPP-1高表达与IPF患者肺损伤程度密切相关,经对测序数据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与ECM相关的基因在IPF患者中显著上调,表明ECM过度沉积及其微环境改变促进IPF的进展;临床相关寡核苷酸阵列研究显示SPP-1可以区分正常人群与IPF患者,且与IPF严重程度密切相关[36-38]。PRASSE等[39]研究显示吸烟引起慢性尼古丁刺激肺泡巨噬细胞产生SPP-1,进而诱导巨噬细胞和朗格汉斯细胞在肺内积聚,促进吸烟相关间质性肺病及PF的进展,提示SPP-1可成为治疗吸烟相关肺疾病的新靶点。上述结果表明SPP-1可作为监测PF的生物标志物,以期作为PF治疗的药物靶点。
5 SPP-1与肺癌
肺癌(lung cancer,LC)是我国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实体恶性肿瘤,已成为人类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SPP-1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生物学功能,可促进肿瘤细胞的浸润、增殖、侵袭和迁移等,可作为肿瘤诊断和治疗提供新靶标[40]。SPP-1在LC中显著上调,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被认为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转移的重要因素,FU等[41]研究发现SPP-1通过上调αvβ3表达,激活下游FAK/AKT和ERK信号通路,促进NSCLC细胞增殖、迁移和EMT,从而导致获得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耐药的发生。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4(Oct4)是一种肿瘤干细胞标志物,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发挥致癌作用[42]。Oct4通过上调参与调控细胞的生长、分化和凋亡的早期生长反应基因-1(Egr1)促进肺癌转移,而Egr1与SPP-1启动子结合,上调SPP-1,通过ERK信号通路途径使Egr1的表达增加,FENG等[43]研究证实Oct4通过调控Egr1/SPP-1/ERK通路促进肺癌进展,提示Egr1、Oct4和SPP-1呈正相关,且与人类肺癌预后不良相关,针对Oct4/Egr1/SPP-1轴的治疗策略有望成为改善肺癌严重病程的潜在靶向选择。XU等[44]通过检测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血浆中SPP-1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SPP-1的表达与SCLC患者肿瘤大小、VALSG分期、淋巴结转移等具有显著相关性,且SPP-1可作为预测SCLC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疗效及预后的新的生物标志物。SUN等[45]对临床患者血清检测研究发现NSCLC患者组血清癌胚抗原(CEA)、SPP-1、Dickkopf-1(DKK1)的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和良性肺疾病组(P<0.05),与NSCLC患者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病理分化程度及临床分期存在相关性,推测CEA、SPP-1和DKK1可能参与了NSCLC的发生发展,由于三者联合检测在NSCLC诊断中敏感度高、特异度强,提示其可成为诊断NSCLC新的生物标志物。脂类代谢异常与肺癌发生与进展密切相关,胆固醇水平升高可诱导脂筏聚集,角鲨烯合成酶(SQS)是在胆固醇生物合成及调节脂筏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的酶,YANG等[46]研究发现SPP-1高表达的肺癌患者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较短,并阐明SQS可通过SPP-1诱导脂筏相关信号通路中Src和ERK1/2磷酸化,致使机体MMP1表达增加,增强胆固醇依赖性调节和脂筏的形成,进而促进LC细胞侵袭、迁移,提示以SQS/SPP-1/Src-ERK通路为靶点可作为一种潜在的肺癌治疗策略。KRAS基因是一种原癌基因,编码KRAS蛋白,具有固有GTPase活性,而KRAS基因突变影响GTPase活性,激活PI3K-AKT-mTOR、RAFMEK-ERK等多条信号通路,使细胞具有恶性潜能的癌前病变最终发生癌变,更重要的是该基因突变与NSCLC现有抑制剂原发性耐药有关,此类NSCLC患者疗效欠佳且预后较差,GIOPANOU等[47]研究者发现SPP-1可介导吸烟所致的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LUAD)KRAS突变肿瘤细胞的存活与持久性,驱动LC早期发生与进展,通过建立LSLKRASG12D肺癌小鼠模型,分别进行SPP-1+/+,SPP-1+/-和SPP-1-/-处理,结果显示SPP-1基因缺陷和过表达对KRASG12D驱动LUAD分别发挥保护和促进作用,提示SPP-1可作为治疗吸烟所致LADC患者KRAS突变的重要靶点。此外,CHO等[48]采用si-SPP-1靶向新型PSOT转运递送系统制备细胞毒性低、转染效率高且稳定性好的si-SPP-1/PSOT复合物,经静脉注入NSCLC异种细胞移植裸鼠模型,结果显示si-SPP-1处理组SPP-1表达在mRNA和蛋白水平上显著降低,且瘤体体积和重量减少,表明特异性下调SPP-1明显抑制了肿瘤生长发展,且抑制效果优于顺铂治疗组,提示SPP-1可作为有效治疗LC的潜在靶标。
6 SPP-1与COVID-19
2019 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一种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以免疫细胞过度激活和细胞因子风暴为特征的全身过度炎症反应的高传染性呼吸道感染综合征,通常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衰竭,可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导致患病和病死人数急剧增加。C反应蛋白(CRP)、IL-6和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等指标对于评估COVID-19患者病情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SPP-1是一种调节多种细胞因子分泌的免疫促炎因子,一项小队列研究表明SPP-1发挥COVID-19病情预测作用[49],循环OPN水平与COVID-19患者机械通气频率呈正相关,且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50-51];MACDONALD等[52]学者研究发现非SARS-CoV-2感染的其他急性社区获得性肺炎病情严重患者血浆SPP-1浓度较COVID-19患者低,且SPP-1浓度的增高与COVID-19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表明SPP-1参与了COVID-19的发病机制,并通过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数据的聚类和降维分析,证实COVID-19重症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出现了与调节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的滑膜组织中CD48hiS100A12和CD48+SPP-1+巨噬细胞亚群功能类似的巨噬细胞亚群即纤维胶凝蛋白1(FCN1)阳性巨噬细胞亚群(FCN1+),FCN1+细胞的聚集及其分泌的大量标志性促炎细胞因子IL-6、IL-8、IL-1β和TNF-α、S100A12以及独特致病因子SPP-1与COVID-19细胞因子风暴、病情进展以及肺部损伤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此外SPP-1可驱动CD14+促炎性单核细胞的激活和上调NEUT表面分子PD-L1(CD274)表达,提示FCN1+巨噬细胞亚群、SPP-1以及PD-L1+NEUT多样性病变特征参与了COVID-19发生发展的相关致病机制,且是预测重症COVID-19患者转入ICU治疗紧迫性及预后监测的最优临床参数。因此,SPP-1可作为辅助诊断COVID-19的临床指标以及进行风险评估和预后分层的新型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也可作为潜在临床治疗靶点,对于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防止医疗保健系统超负荷运转以及疫情防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3-55]。
7 SPP-1与其他肺部疾病
吸烟是引发多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诱因,可导致呼吸道功能受损,影响肺部结构和功能。香烟烟雾可诱导小鼠肺组织CD4+T细胞和γδ T细胞分泌IFN-γ和IL-17A,Th17/IL-17A通过上调MMPs促进香烟烟雾诱导肺气肿的发生发展,SHAN等[56]对肺气肿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肺DCs中基因差异表达分析显示:SPP-1是最高表达量差异基因,且与肺损伤和肺功能严重程度呈正相关,通过动物实验揭示了SPP-1是肺气肿宿主肺组织中CD1a+抗原提呈细胞(APCs)髓样DCs(myeloid DCs,mDCs)通过细胞间依赖的方式诱导Th1和Th17细胞驱动免疫反应所必需的细胞因子,构建暴露于香烟烟雾中的SPP-1-/-小鼠模型,结果显示SPP-1-/-组较野生型小鼠肺损伤和肺气肿程度均明显减轻,Th1和Th17细胞数减少,表明SPP-1对于香烟烟雾诱导的肺部疾病发挥保护性作用,可作为治疗该类疾病的靶标;进一步对SPP-1-/-小鼠和野生型小鼠肺组织中APCs进行全转录组基因差异表达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多种免疫功能的诱导转录因子IFN调节因子7(Irf7)基因的表达显著增高,且其表达量随香烟烟雾暴露的持续而增强,而IL-6、IL-1β和MMP-12的mRNA表达显著降低,TGF-β1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SPP-1对不同促炎因子的调控存在差异,随后该研究团队采用si-Irf7作用于香烟烟雾暴露的SPP-1-/-小鼠探讨肺气肿中Irf7的生物学功能,结果发现IL-1β、IL-6、IL-17A和IFN-γ的表达上调,阐明了香烟烟雾通过SPP-1/Irf7轴诱导Th17免疫反应促进肺气肿发生发展的机制。GANGULY等[57]研究证实SPP-1-/-小鼠较SPP-1+/+小鼠的肺活量体重指数降低,而比顺应性较高,提示SPP-1是肺发育的功能性候选基因,可能与肺泡形成受损与肺功能病理改变等密切相关,通过对两组小鼠中与肺发育成熟相关基因转录组学分析发现,SPP-1-/-组小鼠中肺发育相关基因转录本表达模式的异常改变,这些肺发育异常或与肺部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可致肺结构和功能缺陷,增加发生肺部疾病的风险,且SPP-1与HHIP/Hedgehog、WNT5A/Hedgehog/FGF、NOTCH1等信号通路的调控及通路间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表明SPP-1在调控肺发育过程中的信号通路网络具有关键作用[57]。此外,感染及其所致的恶性循环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加重的高危因素,SPP-1在革兰阴性菌及流感病毒所致肺部感染性疾病中表达上调,并调节其他炎症相关因子进一步加剧肺损伤[58];在肺结核患者血浆中SPP-1水平增高,且可将其作为判断肺结核活动性的依据以及改善结核预后的评价指标[59];HANSAKON等[60]研究阐明新型隐球菌感染可致肺巨噬细胞SPP-1的表达,进而放大炎症反应效应,诱导巨噬细胞由M1型转向M2型,促进真菌在巨噬细胞内的生存和增殖,揭示该感染过程中SPP-1调控巨噬细胞极化的确切机制需进一步探究;由此可见,血清SPP-1可作为感染性肺部疾病评价肺损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然而,巨噬细胞表达的SPP-1可抑制某些肺部感染病原微生物的负荷量,KASETTY等[61]通过变应性哮喘SPP-1+/+与SPP-1-/-小鼠感染肺炎链球菌模型的实验研究显示SPP-1-/-小鼠肺组织免疫细胞招募和促炎细胞因子分泌更多,肺损伤更加严重,SPP-1+/+小鼠BALF以及肺组织中肺炎链球菌负荷量减少,表明SPP-1影响了变应性哮喘机体对肺炎链球菌的易感性。
综上所述,SPP-1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在多种肺部疾病中表达丰富,可诱导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且与患者病程进展和预后密切相关,已有多数研究证实并提示其可作为该类疾病辅助诊断和病程监测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的潜在靶点,然而SPP-1具有促炎和抗炎双重特性,其相关呼吸系统疾病不同信号通路的致病机制尚未阐明,因此,进一步探索和揭示SPP-1的功能异质性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发挥的作用,在精准医学迅速发展的现阶段,SPP-1分子靶向治疗肺部疾病具有非常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