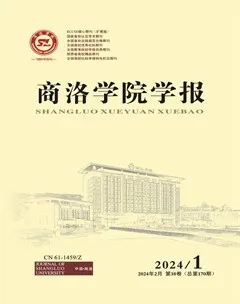况周颐词学深静说探微
刘钰晴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清朝四大词人之一况周颐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文献研究、词作文本分析研究、词学思想研究等几类。总的来说,对况周颐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研究层面,主要涉及创作构思角度、景象和情感内涵、理论发展脉络等方面,于美学、哲学层面关注较少。在况周颐词学思想研究中,学者们多聚焦于“重拙大”“词心”“词境”等审美范畴,“重拙大”是其中的热点命题。王鸳[1]指出,相对王国维的研究而言,况周颐的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况周颐词学词境理论以“深静”为最高审美理想,而“深静说”之内涵交叉于意境和境界的范畴,似周济唯美主义词境论的延伸。
对于意境与境界的内涵,学界亦多有对比探讨。王文生[2]指出,王国维对“意境”和“境界”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908 年他写作《人间词话》时,他显然是想在传统的‘意境’之外,另立新说,因而提出‘境界’。然而,在他的心目中还不能把‘境界’和‘意境’明确地分别开来。”近人研究将两者概念进行辨析并指出,意境是人脑海中的精神性现象①,而境界则是有生活意味的生活性场域②。阐析况周颐“深静说”之内涵、成因与渊源,有助于理解其词学的独到之处。
一、深静说的基本内涵
况周颐论词时多次提到了静、穆境与深静。况周颐赞赏描写外部环境之静的词句,如他评元好问“草际露垂虫响遍”,赞其能“写出目前幽静之境。”[3]181再如陆仲永的“回首千波寂”,他评曰:“能于惊心骇目中忽呈静悟之一境。”[4]况周颐以直观神悟的方式于一瞬完成对审美对象的整体把握,称道主体的情感能悟静之妙境从而写下此句。何谓境?意境自中唐以来在唯识学唯识宗三境说的影响下,“把审美带入了关于实相的直觉。”[5]182玄奘说世界境分为三种: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只有影像没有真实的独影境;既有实境因素也有虚境因素的带质境;还有在玄奘看来最真实的,“刹那生灭的主体与刹那生灭的客体照面的性境”[5]186。而意境的形成便需要“现量所认识的对象超越了独影境和带质境的性境”[5]182,物与创作主体的刹那生灭都是无间隔且超越时间的,而在这两相独有一次的刹那照面中,创作主体于无有暂住性中达成了对生命的顿悟。从况周颐对陆仲永的评价中能看出陆仲永的感觉对建构词境的重要性,他在恒常与开放中直观体悟到了静境。而词境的形成同样需要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元好问受现实环境的感召写出幽静之境,再通过创作主体识与境冥合,其幽静之境即是心识显现之幻相。再如其评吴乐庵词、袁静春词。
吴乐庵《水龙吟·咏雪次韵》云:“兴来欲唤,羸童瘦马,寻梅陇首。 有客遮留,左援苏二,右招欧九。问聚星堂上,当年白战,还更许追踪否。”此词略仿……而吴词意境较静。(《蕙风词话》卷二)[3]46
袁静春《烛影摇红》云:“凤钗频误踏青期,寂寞墙阴冷。 ”下句略不刷色,却境静而有韵。 (《蕙风词话》卷三)[3]96
况周颐在评两词时,直接点出“静”境。词境细美幽约,在词中更适合表现静的意绪。吴词将少年意气与老来沉稳心境对比,将不同时间的生命体验放于同一空间,颇有低回婉转之意。况周颐虽说吴词“意境”较静,但吴词中已有生命体味,且是具象的有空间结构的存有,所以称为“境界”更为恰当。袁词也是如此。袁词的静境写物境却有情,情景交融,有着心灵对于时间性场域的体悟,韵味溢于楮墨之表。除了直接提到“静”境,况周颐也时常间接推崇“静”境,如评价朱彝尊“桂树深村狭巷通”句“颇能模写村居幽邃之趣。若换用它树,意境便逊。”[3]32评潘紫岩词歇拍尤意境幽瑟等。“幽,隐也。”[6]此后引申为幽静之意,朱彝尊和潘紫岩之词符合况周颐评介词境的审美取向,有静的意境。“意境”偏于诗学概念,但从上述论述也能看出,况周颐的某些词论已有哲学意味,况周颐所说之境虽然往往自称是意境的简称,但有些词境已有现代所言境界之意。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尚没有明确对“意境”和“境界”的辨析意识。而深静说的核心在于点出“静”这一生命本质,又恰是“深静”的建构彰显了词作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在此基础上,况周颐进一步提出了词境的“穆”与“深静”说。“穆”本身有温和、恭敬、肃静、深微之意。“深”有深度、深奥、深刻的意思。况周颐明确指出了这两种词境:
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 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 知此,可以读《花间集》。 (《蕙风词话》卷二)[3]23
词境以深静为至。韩持国《胡捣练令》过拍云:“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 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持国此二句,尤妙在一“渐”字。 (《蕙风词话》卷一)[3]25
前人多将“深静”统属于“穆境”之下进行讨论,但在某种意义上,两境的美学品格是不同的。夏敬观认为:“《花间》词全在静穆,词境之最高者也,况氏说此最深。”[7]穆境除了“静”这一层级的要求外,还要与“厚”“重”“大”结合。何谓“重”“拙”“大”?“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超乎緻密之上,别有沉著之一境也。”[3]52一方面,“重”“超乎緻密之上”,所以内容緻密详实。另一方面,“重”强调“沉著”的“气格”,南宋遭逢靖康之变,章甫缝掖之士、尺板斗食者流无不有宗周嫠纬之思,其词的措意、题材在陆沈之痛的浸润濡染下,自是得“重”,所以穆境往往内容深厚别有寄托。如“耶律文正《鹧鸪天》歇拍云:‘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况周颐评曰:“高浑之至,淡而近于穆矣。”[3]79耶律楚材身处元朝思念故国,其词述出了山河破碎泣血诉恨的悲苦与无数失意恨人之心尚。而“沉著”是“厚”的外现,况周颐曾在词话中评赞周邦彦“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3]29,语言愈朴愈厚是由于有真情自肺腑流出,悃款入情,为文方“厚”。至于“拙”,况氏在《餐樱庑词话》中称“尚近质拙可不失尖纤”,所以“拙”偏重于强调语言文字质朴的艺术风貌。由上文分析可知,词“拙”更易“厚”,再外化便是“重”。最后,“大”与“纤”相对,指词杼轴、旨意等方面有风骨格局,整体气象宏大。所以,“穆境”的词境受儒学影响更大,侧重于追求儒家的温和中正之境。
对深静的描述,况周颐举例的韩持国词清丽婉转,芋绵温雅,与穆境偏重的品格不同。况氏特言句中“渐”字写得好,是因为“渐”字方使此词有了深远貌,境至幽夐清灵,此外也强调了情对深静之境的必要性。况氏在论述词学程序时也提到了“深”与“重”的概念,“词学程序,先求妥贴、停匀,再求和雅、深秀,乃至精稳、沉著。”[8]这里提到的沉著即“重”,要比深秀高一个层次,此处“深”的含义与深静的词境中深的内涵也不相同,但可以看出况周颐或许有意将深和重分开论述。那么怎样才算达到深静的境界呢?况周颐认为首先要求外部环境、物象、字句营造出的整体氛围是静的,同时,还需句中不提人却无形中有人,这用帘幕“隔”着的人恰是破题的关键。“隔”对物象造成距离的同时,在意向开放下心灵随之清净空寂,物象与如隔蓬山之人的情交相辉映,心灵之空寂转为情感之充实。穆境与深静有着不同的美学特征。
穆境与深静两词境的共同点是同受寄托说影响,有寂寞深远之味。穆静内涵中的“重、拙、大是建立在常州派特别是周济“寄托说”这一学术基础上的,所以强调词人在学养、人品、经历等方面的锤炼,强调词作思想内容方面的充实深刻。”[9]而常州派的寄托说之于深静,更多体现在对词“意内言外”的倡导,深静的深本身便有向内沉潜之意。所以穆境的旨趣在“格”,是人高尚格调之美。深静的旨趣在“深”与“情”,更超脱于俗世。比较而言,深静的佛道内涵重于穆静,其主体一刹与客体的照面更深邃与空寂忘我。
二、进入深静之境的途径
词人若进入一个特殊的精神境界——“物化”之境,“词境”会更易创造形成。对于如何进入深静之境、体悟深静之境,况周颐从创作论和鉴赏论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都应胸次无尘。
一方面,“净”的心识下,才能创造出静的境界。
“落日水亭静,藕叶胜花香。 ”……藕叶之香,非静中不能领略。净而后能静,无尘则不嚣矣。 (《蕙风词话》卷二)[3]48
杨用修席芬名阀……“一树藤花”,确是人家庭院景物。曰“独自看”,其殆《白华》之诗,无营无欲之旨乎?扉无风而自掩,境至清寂,无一点尘,如此云云。 (《蕙风词话》卷五)[3]131-132
韩致尧诗“树头蜂抱花颚落,池面鱼吹柳絮行”……非胸次无一点尘,此景未易会得。 静深中生明妙矣。 (《蕙风词话》卷三)[3]94
藕叶之香,于静中方能领略其中之美。这需要“净”来生静,净的内涵受佛学影响大,唯识学中有净色根,唯识学的最终目标是清净。世界存在净心,具有净性。“扉无风而自掩”,字面无尘、画面无尘,而境界已出,这首先需要创作主体胸次无尘,至静忘言,这有助于心识于虚静中以物观物,摄取物之神理。除了“净”的心态,入深静还需要“情”的支撑。此中之理与传统意境(境界)说一以贯之。“段诚之《菊轩乐府·江城子》……前调云:‘颓然醉卧,印苍苔半袖。’于情中入深静,于疏处运追琢,尤能得词家三昧。”[3]72三昧是佛教术语,是“禅定”中“定”的基础词“三摩地”所译。“禅”的意译便是“静虑”,是各种“定”中的一种[10]。称深静之词得词家三昧,比之以三昧评其他理论,可谓更切中肯綮,造化天成。此词化景物为情思,情在境中,于实中体悟到虚,达成主客统一,妙境得悟,得词家之真谛——美的真谛。
另一方面,对深静词境的创造也需要鉴赏主体的参与,其与创作者和文本共同完成对深静意境的创建。“……《扫花游落红》云:‘一帘昼永。绿阴阴尚有、绛趺痕凝。’并是真实情景,寓于忘言之顷、至静之中。非胸中无一点尘,未易领会得到。”[3]95至静之境,鉴赏主体需要有一定的经验阅历,并且做到胸次无尘。可见,深静之境的创建对读者也是有要求的。
《俱舍论颂疏论本》云:“功能所托,名为‘境界’,如眼能见色,识能了色,唤色为‘境界’。”[11]词境的形成一方面需要自然界,另一方面需要创作主体“六根为缘,六识各各的触心所,乃与六入即六种工具同时俱起”[12],与外物交互作用,触心所开动牵引六心及六心各有之诸心所,互相应合,感知境域,从而达成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创作者再将此难言之境付之笔端,鉴赏者在鉴赏过程刹那观照到此境界,感受到难言的美感。
除了要求创作者鉴赏者胸次无尘外,况周颐在“构建”深静的词境时,还注意到创作灵感与“词心”之关系。他将创作过程及创作主体的状态进行了详细描述:
人静垂帘,灯昏香直。 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鼎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 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於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 此词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焉。今不可复得矣。(《蕙风词话》卷一)[3]9
创作主体在静谧的外部环境下冥坐,念起排遣之,这一过程类似于修行实践中的禅定,偶然间直至某种境界,突然心思洞明,灵感迸发,身心同得一境。而此境界很难再得。主体心灵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如入神境,便有了艺术发现,此便是况周颐亟称的词境。此外,况周颐对于灵感来袭的过程也有详细描述:
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洎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 (《蕙风词话》卷一)[3]10两段描述如入玄冥之境,颇有佛家寂静止息之境界与道家自然无为之风神。况氏在此糅合了古典文学理论思想脉络及佛道儒等文化内涵,除了对灵感说的补充阐释,还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词心”说,倡导“吾言写吾心”,从中可见禅宗、心学对其文艺理论的影响,他指出: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书卷多,吾言易出耳。(《蕙风词话》卷一)[3]9-10
况周颐指出万不得已者即是“词心”。所以词心即是指不得不说之语,是由作者的心中酝酿出的,本心是能词心的关键。创作主体秉“心斋”“虚静”之法门,心下无尘,书卷辅之,偶有灵感袭来,于是“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13]81,刹那观照到空静之词境。鉴赏主体和词人同能领悟蕴藉含蓄、韵味无穷,具有静观之美的深静之境。
三、深静的理论渊源
(一)对意境与静传统范畴体系的继承
“意境”是“静”等范畴,在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境论诗者古往今来一直不乏其人,况周颐的静境说继承了传统意境说的理论内涵,又基于现实的背景下,力求反拨日趋轻纤脱易的词风,所以况周颐利用“静”活跃的衍生能力导出“深静”之境,将词引向内潜与深厚的境地,昭显了词体时代的面目。
从王昌龄《诗格》始,意境说便与唯识宗有关。“心之境者,性也;性之智者,心也。”[14]佛学中的境不是范围,而是性。意境自此时起,便于传统美学领域以其极强的适应性活跃在理论批评中,到今天现代美学建设中仍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况周颐对境的主体思想来源于古代传统文论,境生于象外,意境具有情景浑融、物我统一、虚实相生的特征。“静”的范畴亦与传统文学理论一脉相承。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篇便提出了“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15],要求作家心无杂念地进行艺术创作。中唐皎然阐释了禅境对诗境的影响,宋代苏轼、明代金圣叹都提出作家在构思时要内心清静,近代宗白华把老庄的虚静得道观点称为美学的静照[13]77。静安和而美善,存在于深静之境的创造、沟通与鉴赏中,况周颐为词体专设深静之境,他在读前人词时,于开放性视野中与古人之心“照面”而恍有所感,在缘起境域中品悟当下真实的美感。
除了对意境和境传统范畴体系的继承,深静说的内涵不可避免地受学术思想的影响。虚静的理论最早导源于道家,佛家对此也有影响。
(二)静的文化理论溯源与况周颐的学术背景
从老子开始,便主张清净之学,提倡无视无听的玄冥之境。“虚静”的提出最先见于《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16],在心外无物,摒弃是非善恶、功名利禄的情况下,方能达到一种天地并生万物齐一之境,而进入“虚静”的方法便是“心斋”和“坐忘”。同样,佛家也提倡类似于虚静、玄览的审美观照,禅宗亦重视“空”“静”“顿悟”,“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13]86同时,得词境时的冥思状态与佛家修行颇为相似,况周颐所云词境得悟过程与禅境得悟过程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中国儒学亦有缄默维度之说,“指语言关闭时,心意向深静敞开,传统的表述有平旦之息、亥子之间、贞下起元、天根、冬关、密冒、隐均等。功夫论表现为主静与持敬功夫的更迭互润,动态平衡:主静是凝聚收敛深静之气,持敬是修饬庄严生命的流行。儒学与道家的缄默维度同根,二者均重视深静中‘气’的生发。”[17]所以,传统文学理论关于“深静”的建构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此外,况周颐本人也是有着深厚的儒释道学术背景的。
况周颐直言其有志学佛:“余于学佛,有志未逮,愧且怅矣。然每一妄念起,辄自警日:‘余固有志学佛者,乌乎可?’”[18]况周颐亲近佛道,为文用语也有佛道的痕迹,如“影事”等,注意到了子平家言入词的现象,他特意将之记载于词话,并推崇词中用释典道书之语。论词之时,佛家语亦信手拈来,“末七字余极喜之,其妙处难以言说,但觉芥子须弥,犹涉执象。”[3]42况周颐尤其喜欢在极尽推崇之处用佛家语称赞之,此前如“词中三昧”便是一例。“芥子须弥”出自《维摩经·不可思议品》:“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19]以喻诸相皆非真,在此为推崇之语,此句只惋其“犹涉执象”,未完全超然物外,此憾矣。其佛道的思想背景使他自然而然地提倡融合佛道的深静说词境。
在清以前佛义禅理论诗的现象比较普遍,用“三昧”之类的佛家语评点诗、画比较多见。而以佛禅论词,在唐宋时期比较少见,到清代以佛义禅理论词的现象方增多,这是由于词在发展之初仅是花间樽前的遣兴工具,用以言志都少,更遑论以佛禅义理加以评释。相反,当时会有佛家对词体进行批评的现象。北宋中期以后,自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现象增多,词学地位逐渐提高。元明词学一度沉寂,自清代再度兴盛,清词尊体之风盛行,况周颐以佛禅义理入词体现了作家无意识地将诗性的观念赋予词,客观上借诗学范畴提高了词的地位。清人以佛禅论词进行破体,不排除有故弄玄虚的可能,但不可否认佛语反过来促进了词尊体的发展,促进了词的独立、辨体及词本位理念的发展。
至于对儒学的接受方面,况周颐本身熟通经义,也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祥麟是嘉庆庚申恩科举人,善启迪后进。祖母朱镇亦能诗能词,是名门闺秀。二姊月芬曾手钞《尔雅》授其读。其词话中亦有“扫叶之喻”[3]21,“丁一确二”[3]21,“甘受和,白受釆”[3]144等儒家经典的内容,可见儒学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况周颐吟诵之句如“雪声清似美人琴”,即《尔雅》所云霄雪也。况周颐文论行文亦符合儒家中庸之道,正如他称赞的王鹏运论词之言“恰到好处,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过”[3]232,是儒家文艺思想在词学领域延伸的体现,很难见其偏激之论。此外,况氏云:“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3]21这也显然是传承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可看做接继了南宋以来的复雅词派。而《离骚》便因其不合“和雅温文”之道,而被况周颐所不满。
(三)况周颐的深静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之比较
况周颐融合儒释道并继承了传统文论思想,提出了以深静为至的论词主张。晚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有类似的词境说,再之后便是王国维的境界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王国维没有直接对“境界”下定义,但是《人间词话》核心讨论的便是“美在境界”。“深静说”和“境界说”都在包括自然山水的生活中汲取养料,都注意到了词境的内涵与审美,都提到了“隔与不隔”,可见两者的相似性。但两者又有区别。“深静说”侧重于将照面一刹心灵的空寂放大付之笔端,突出静的审美内涵,而对于境本身的概念,况周颐尚没有清楚的辨析意识。从这个层面看,王国维“以超功利泯利害的文学观为本位”[20],有意地架构新的话语体系,境界说的内涵更倾向于精神性生活场域。将两者进行对比可知:
第一,王国维有意识地归纳词学的审美共通性规律并试图建构,境界美感的获得需要在审美关系的状态中实现对人生与宇宙境界的体察,其生活哲学不但取之于人,甚至可用之于人。而况周颐侧重于一霎间直观感受到静的美感,无论是否带有生活的体悟,只要是有静的感受,都属于其深静说的范畴。比较而言,境界说场域的内涵更丰富和深刻。第二,境界说从创作论的角度可分为造境与写境,从鉴赏论的角度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此种境界内容同上文分析的况周颐深静说相似,来源却不尽相同。众所周知,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尼采影响极大。叔本华说:“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也即是说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知觉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和直观分开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21]249-250这与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内蕴一致。其“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相通于叔本华所谓的“主观的心境,意志的感受把自己的色彩反映在直观看到的环境上”[21]288。而“深静说”更倾向于一种无执无涉的超脱境界,核心是“‘我’与性境的照面”[5]181,有丰富的佛学审美内涵。虽说境界说或同深静说一样不可避免地受我国古籍、佛典、道家影响,但可与西方典籍互相印证则是深静说所没有的——况周颐不谙西学。最后,王国维还具体建构了景境与情境,大境和小境,优美与宏壮等概念范畴,比较而言,王国维的境界说更成体系。
四、结语
意境的境与佛学中的境含义不同,但这不影响佛学唯识宗将超越性的审美方式带入文人的世界,使意境在不同时代的复杂语境中塑造它模式的语序。普遍而言,意境是文人内心超越性的想象,而境界是语境,是每个人的生活。而文人们同时也在生活中无意识地不断扩大意境的外延,恰如况周颐的深静说。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况周颐所谓的“境”或属于意象或属于意境或属于境界。但在当时来看,况周颐的深静说是在传统文学范畴内,对词境进行的一次梳理和提升。
具体而言,“深静”与“穆境”有着不同的美学品格。深静说的统一着眼处是“静”,这是况周颐在其文化背景下感知与提炼而出的核心概念。而王国维则在新旧转捩之际,在词学研究的背后传递出了他新时期的探索意识,他的境界说将词学由旧式吉光片羽式的感悟转向了新型体系的话语建构。境界说这一重要范畴的架构,促进了词学美学价值的独立。客观来看,况周颐在对境的整理细化方面是不如王国维的,这有思想、情势、际遇等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况周颐以文艺家敏锐的感受捕捉到了静——艺术的最高精神形式之一,这是他不可抹杀的文学理论贡献。
注释:
① 关于意境的来源和概念,争议颇多。宗白华、李泽厚、罗钢、张文勋、蓝华增、卜松山、肖鹰等都就意境的来源和概念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本文关于意境的来源与内涵以王耘说为准。
② 彭锋将意境说的来源论争概括为“正统说”“西来说”和“演化说”,又将“演化说”分为两种情形——“渐变说”与“突变说”。(见彭锋:《现代意境说辨析》,《北京大学学报》2018 年第1 期,第133 页。)本文将意境与境界概念区分辨析,刘锋杰、李长之、顾随、张文勋、宗白华、任访秋等都认为境界有生活内蕴,是生命的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