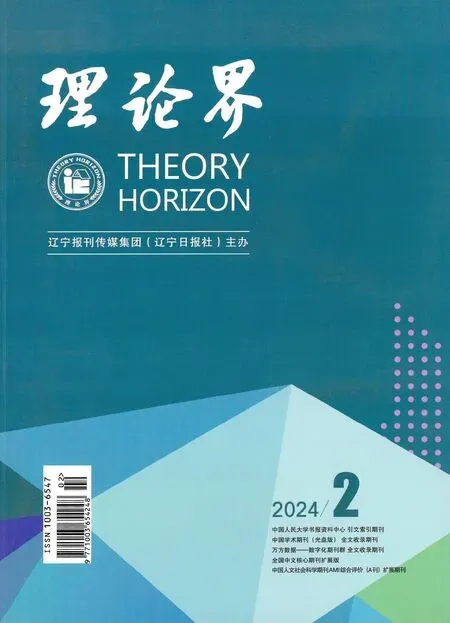何谓尽善:《论语》“子谓《韶》”章析义
汪刚迪
《论语·八佾》“子谓《韶》”章记载了孔子对《韶》乐与《武》乐的评价。因其事关孔子对舜与武王两位圣王的看法,深受后世注家的重视。分析历代注家对此章的训释,可以发现三个特点:第一,诸家皆以“未尽善”为焦点,着重疏解武王之乐何以未尽善;第二,此章是孔子以乐论史,实质上是探讨禅让与革命的关系;第三,着重发挥“乐”与“德”的关系,诉诸音乐形式的差异解释“未尽善”,从而为武王之德提供辩护。近些年,学界涌现不少相关研究。刘涛对历代注家的训释进行总结,将其区分为“褒武派”和“贬武派”,指出争论的实质是对于禅让和革命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1〕王海成在西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框架下讨论“美”和“善”的内涵,分析此章的思想史意义。〔2〕肖琦在统一“美”与“真”的基础上分析“尽善”的含义,指出由于《武》乐夸饰伐纣的正义性,所以未尽善。〔3〕何益鑫从艺术对道德的呈现入手,强调要在音乐和艺术的脉络中理解此章。〔4〕这些研究虽各有创见,但其解释的焦点仍然集中于“未尽善”的问题。实际上,过分局限于对“未尽善”的解释,正是历代注家意见难以统一的症结所在。如果把解释的重心转移到“尽美”,结合《八佾》的基本主题来解释此章,便能化解这一症结。本文即试图详细梳理历代《论语》注家对本章之注,揭明各注家的解释特色及其相应的视野,厘清其注解与原文本义存在偏差的原因,进而从“论仁”的维度对“子谓《韶》”章重新展开考察,作出更为贴切的理解。
一、禅让与征伐
《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相传,《韶》是舜时的乐曲,《武》是周武王时的乐曲。孔子评价《韶》乐,曲调优美,内容也极其美好;评价《武》乐,虽然曲调一样优美,内容却不够完美。对于《韶》“尽善”而《武》“未尽善”的原因,由汉代至唐代的经学家主要从舜与武王得天下的差别处着手进行解释。孔安国和孔颖达强调舜的禅让与武王的征伐,体现出舜与武王的德性存在高低差异,《韶》“尽善”的根源在于舜的德性完满,《武》“未尽善”则意味着武王的德性明显逊于舜,故孔子其实是对二者德性的高低进行评价。相比之下,董仲舒和郑玄则试图调和舜与武王之间德性的差异,强调二者在圣王谱系中的一贯性。
《韶》《武》本是乐章,汉代经学家孔安国却指出“子谓《韶》”章并非孔子论乐,而是论史。其解释的目的在于引入禅让与征伐的议题,以禅让与征伐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未尽善”的含义。孔安国注云:“《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之故,曰未尽善也。”〔6〕孔安国的看法割裂了《韶》《武》与具体音乐的关系,《武》和《韶》只是武王和舜的象征而已,这样便把诠释的焦点转移到了舜和武王自身的德性。进而,舜与武王又是禅让和征伐的代表,故此章的主题又变成了对禅让与征伐这一行为的评价。围绕禅让与征伐展开的论辩与汉代的立国问题密切相关。孔安国实际上将汉代关于禅让与征伐的讨论引入了对《论语》的解释中。
针对孔安国的认识,董仲舒则提出舜之禅让与武王征伐只是所遇之时不同,由于二者所处的历史处境不同,舜以禅让得天下,而武王不得不行征伐之事。禅让与征伐皆是当时政治环境使然,并不意味着有德性上的区别。董仲舒云:“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7〕董仲舒以“时”释《韶》与《武》的差异,旨在申说舜和武王皆是遵循了“帝王之条贯”的圣王,缩小了“尽善”与“未尽善”的差异。董仲舒的阐释亦针对汉代的政治情境而发。汉武帝曾问策董仲舒:“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8〕汉武帝的观点说明汉人普遍在“圣人改制作乐”的语境中理解《韶》,尤其将舜作为历代帝王之典范。这便可以理解孔安国为彰显舜的圣德,极力贬低武王的做法。然而,董仲舒则强调历代帝王所遵循的王道是相通的,自舜至武王,圣王之道一以贯之。即便存在禅让与征伐的差异,也只是取天下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心志都在于化育万民。因此,禅让也好,征伐也好,都不关系德性问题,以战争夺取天下并不能作为贬低武王的理由。董仲舒弥合禅让与征伐之间的差异,其目的在于将阐释的重心从“得天下”转移到“治天下”,从而劝谏汉武帝重视文教。
在此影响下,郑玄以另一种方式避免了从德性的视角比较舜和武王。郑玄曰:“《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又曰:《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9〕郑玄认为舜之美与武王之美不同,舜之美在于以德受禅,武王之美在于能定天下。而“尽善”的含义是“致太平”,武王“未尽善”的原因是未能“致太平”。换言之,郑玄将对舜之德的解释放在“美”的解释中,使得“尽善”的内涵与德性相分离,“未尽善”的原因不在于德性有亏,而是未致太平。如此,郑玄也化解了舜和武王之德的对比。
郑玄、董仲舒与孔安国都忽略了“美”与“善”的定义问题。直至南朝儒学家皇侃在《论语义疏》中,才对“美”与“善”作出界定:“美者,堪合当时之称也;善者,理事不恶之名也。夫理事不恶,亦未必会合当时;会合当时,亦未必事理不恶,故美、善有殊也。”〔10〕皇侃释“美”为“堪合当时之称”,这是对董仲舒“时异”说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还从“天下之民乐舜揖让绍继尧德”以及“天下乐《武》”两个维度说明舜和武王皆合其时,所以他们都是正当的,是美的。另一方面,皇侃释善为“理事不恶之名”,这又是对孔安国“揖让与征伐”之说的继承。由于武王以臣伐君,违背了君臣之义,于事理有亏,因而“未尽善”。要之,皇侃对美与善的界定既继承了孔安国对禅让与征伐的区分,也吸收了董仲舒的“时异”之说,实现了对董仲舒和孔安国之说的折中。皇侃作为南朝时人,已经脱离了汉代普遍推崇舜德,辨明禅让与征伐之义的思想语境,故能吸收二家之说,既不刻意强调差异,极力突出舜的圣德,又能区分“堪合当时”与“理事无恶”两个层次来解释此章。
皇侃之后,孔颖达却通过重新解释“尽美”,再次把舜与武王置于德性问题的讨论之中。孔颖达疏谓:“乐备,谓文德备具。不备,谓干戚之舞矣……干戚之舞非备乐也者,言周乐干戚之舞,非如舜时文德之备乐也。”〔11〕“舜以文德为备,故云《韶》尽美也,谓乐音美也。又尽善也,谓文德具也……谓《武》尽美矣者,《大武》之乐,其体美矣,下文说大武之乐是也。未尽善者,文德犹少,未致太平。”〔12〕与孔安国以来的解释传统不同,孔颖达将“尽美”解释为孔子对声音和舞蹈的评价,从而又将德性问题纳入了对“尽善”的解释之中。武王未能致太平,故其乐仅为“干戚之舞”,舜乐却“杂舞干戚于两阶,而文多于武”。相较于郑玄,孔颖达看似继承了郑玄“致太平”之说,实则通过重新解释“尽美”,将舜帝与武王又重新置于德性问题的讨论之中。另一方面,孔颖达以前没有儒者从音乐与舞蹈的内容入手讨论“未尽善”的问题,这是孔颖解释的特色。
总之,汉唐经学家关注禅让与征伐的善恶之分,其实是始终围绕德性的议题来阐发“尽善”与“未尽善”之义。无论是孔安国、孔颖达表彰舜,刻意拉大舜和武王的德性差异,还是董仲舒、郑玄为武王辩驳,说明以战争夺天下并无损于武王之德,其实都是以德性作为评价君主的标准。因此,在经学传统中,君主如何为“善”的问题,实质上是君主应该具备何种德性的问题。
二、帝王之德
相较于汉唐经学把禅让与征伐的讨论带入对“子谓《韶》”章的注释中,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对帝王之德的讨论,宋代理学家则紧扣心性问题,以成德进路为中心展开对帝王之德的解释。胡宏、陈祥道看似回应汉唐注疏中禅让与征伐的性质问题,实际上试图借此探讨圣人之心。朱子则集中分析舜与武王的德性之异,以成德进路为中心展开诠释。
针对孔颖达以“声音节奏”释“尽美”,以“功治”不足释“未尽善”,胡宏调换这一解释,以“未尽善”仅仅是声音节奏存在差异,而把“尽美”解释为帝王之德相同,又《韶》与《武》皆“尽美”,便回避了武王之德是否有亏的问题。胡宏云:“《韶》之乐德,尽美矣,其声音节奏,又尽善也。《武》之乐德,尽美矣,其声音节奏,未尽善也。观圣人者,盍亦审诸?”〔13〕胡宏将“未尽善”解释为声音节奏存在差异,其意在于指出假禅让而行篡窃,比正义的征伐更有损于德性。因此,圣王之德应该视其心志而定,而不是外在的行为。
同样从圣人心志出发,陈祥道为武王辩护,也是为了维护圣王之道与圣人之心。陈祥道云:“天下无异道有异时,圣人无异心有异迹。故《礼》以尧舜授受,汤武征伐为时,《春秋传》以揖逊征诛,其义一也。然则《韶》尽美而《武》独未尽善,岂非美者在心与道,未尽善者在时与迹欤?”〔14〕陈祥道通过区分“心”与“道”,把“尽善”解释为“心”,武王是为“时”所迫,不得不行征伐之事,非其有心如此。这种解释与董仲舒“时异”说的思路相近,但陈祥道要突出的不是圣王谱系一脉相承,而是强调圣人论心不论迹。武王和舜虽行异而心同,都当得圣人。
与胡、陈相比,朱熹把对圣王德性的讨论进一步引向了工夫论。朱熹援引《孟子》“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云:“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15〕“性之”指生而有之的德,“反之”指修养而成的德。朱熹认为,舜与武王的真正差异在于舜之德是生来如此,不假修为,又以禅让的方式得天下,所以“尽善”;武王之德乃是通过后天的修养而得,又以战争的方式得天下,所以“未尽善”。
然而,朱熹强调“性之”与“反之”的区分,反而使得他对此章的解释颇为支离。首先,“性之”与“反之”的区分必然会放大舜与武王的德性差异。这种差异在汉代经学家那里已经出现,经朱熹对先天性情和后天工夫的划分,这种差异更为明显。实际上,朱熹自己隐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其云:“今若要强说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贬武,也不得。”〔16〕若坚持性之、反之的区分,最终会造成同孔安国一样褒舜而贬武王的情况,故朱熹又说:“《韶》《武》之乐正是圣人一个影子,要得因此以观其心。”〔17〕这显然又回到了对圣人之心的关注,唯有在舜与武王兼具圣人之德的意义上才能同时成圣。不过,朱熹虽然在立场上不愿过分批评武王,却因在事实上主张天生之德高于修养工夫所成之德,而贬低《武》乐和武王的地位,甚至以为武王的工夫修养不如商汤。“汤自放桀归来,犹做工夫。……武王自伐纣归来,建国封土,散财发粟之后,便只垂拱了。……此见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汤甚远。”〔18〕要之,朱熹的解释由音乐而兼及史事,其实都是聚焦于成德进路的问题。朱熹虽然摆脱了汉唐以来的问题意识,却由于强调德性进路的差异,仍然产生了汉唐注疏中褒舜而贬武王的老问题。
其次,朱子一方面认为武王凭借修养工夫,方能成德,其德薄于舜,故“未尽善”,另一方面又引用史实,以揖逊、征伐解释“未尽善”,这导致德之厚薄与得天下的方式之间被勾连起来,“未尽善”的含义反而不够明晰。朱熹云:“据《书》中说《韶》乐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木土榖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乐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乐,所谓:‘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复缀以崇,与夫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其意思与《韶》自是不同。”〔19〕朱熹引史解经,在工夫进路之外,还指出了舜与武王取天下的路径差异。因此,有门人问朱熹:“未尽善,亦是征伐处未满意否?”朱子既坚持认为善只与武王自身的德性有关,与取天下的方式无关,又不得不承认“亦在其中,然不专就此说”。〔20〕显然,朱熹对是否通过取天下的方式来解释“未尽善”也犹豫不决。故门人发问,“尽善、尽美,说揖逊、征诛足矣,何以说性之、反之处?”〔21〕朱熹的本意是要强调“未尽善”的差异在于舜和武王之德,而非具体的行为。门人却认为用揖让与征伐足以解释“未尽善”,无需引入性之、反之的工夫问题。
要之,朱熹所坚持的乃是先有内圣,然后才能外王的宗旨。在此一立场之下,内圣必然先于外王,即便是圣王也会因成德进路上的差异而产生事功上的高低之别。然而,朱熹试图兼顾德性与事功,却导致这两个向度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朱熹本是从“心性”的角度理解舜与武王的不同,反复强调德性的差异,最终却在理论上从德性的探讨转入了对事功的比较。
宋代理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汉唐经学的解释焦点,不过,汉宋儒者都没有绕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舜与武王之间是否存在高低之分。刘涛将历代注家分为批评武王与同情武王两派,并指出贯穿汉宋注疏的是禅让与革命的关系问题。〔22〕就解释史而言,揖让与征伐的问题是孔安国带入的,后世反复争论舜与武王的高低之别时,也始终纠缠于对揖让与征伐的辨析。自董仲舒开始,帝王之德成为此章的主旨。在圣王之德的视角上,武王不能德行有失,否则“帝王之条贯”不能自圆其说,这在客观上把诠释的思路引向了帝王之德的问题,宋代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发挥。然而,平等肯定武王与舜之德,却又无法解释孔子“未尽善”的评价。因此,朱熹试图调和这一矛盾,在承认武王与舜均具有圣王之德的基础上,指出武王后天修养而来的德,不如舜生而有之的德那样完美,故“未尽善”。然而,朱熹的解释却在逻辑上依旧造成了贬低武王的结果。他力图用历史记载的事功来佐证其说的做法,也由于重内圣而轻事功的特性加深了这一结果。由汉至宋,历代注家对此章众说纷纭,却仍未能融洽地解释。
三、尽善的含义
历代注家或从禅让与征伐的差异,或从成德的角度进行阐释,但其焦点均落在“未尽善”的含义上。这忽视了此章所处的《八佾》篇论“仁”的基本主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关于“尽善”和“未尽善”的理解。唯有把此章置于“论仁”的文本脉络中,把诠释重心从“未尽善”转移至“尽善”,分析“尽善”与“仁”的关系,方能作出更为贴切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未尽善”虽未达到最为理想的境界,但仍然是“善”,只是不够圆满。孔子以乐论德的说法渊源有自,古人本就时常借乐论治。《史记》载吴季札观乐,“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23〕《韶濩》是商汤时的乐舞,季札闻之,评价是商汤有“惭德”。季札表达的是对“圣人之难也”的同情,并没有非难商汤。可见,古人论圣人之乐,往往是以一种同情的思想来解读其义。相应的,很难想象孔子在比较舜之乐与武王之乐时,其云《武》“未尽善”是旨在刻意贬武王。根据《论语》原文所在的语境,进行朴素的理解,则汉唐注疏中通过贬低武王,来表彰舜德的思路是值得质疑的。就此而言,朱熹显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作出调和。他在修德成圣的意义上肯定武王,同时表彰武王和舜的德性,就是为了摆脱褒舜而贬武王的巢窠。要言之,“未尽善”虽然不是最为理想的境界,但仍然是善。并且,从“尽善”一语看,“未尽善”应该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善。正因如此,董仲舒那种将舜与武王拉到同一高度的立场是不严谨的,毕竟孔子对“未尽善”与“尽善”作出了程度上的区分;但是,过分贬抑武王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未尽善”与“尽善”之间的差距不应该被刻意放大。
“未尽善”处于“善”与“尽善”之间。解释“未尽善”的含义,必须厘清“善”的内涵。这需要回到《论语·八佾》篇的文本脉络和基本语境中,分析孔子关于“善”的理解。细绎此章与《八佾》其他章节的关系,就会发现此章其实是“论仁”。《韶》为舜乐,舜以禅让得天下,孔子最为推崇的正是其“让”德。《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24〕孔子谈论贤臣的重要性,把舜与武王并举,其意在赞扬周文王的“至德”。在《泰伯》篇中,除文王外,还有一人也被赞为“至德”,此人便是吴太伯。《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25〕按周代继法,吴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理应继承王位,但他却反复推辞,以身“让天下”。吴太伯这种“让”的精神在周文王身上也有体现。孔子赞美文王的原因在于,周文王在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实力远超于商纣王的前提下,仍然服从纣王,没有争夺天下。合而观之,面对天下和王位,吴太伯是当取而不取,周文王是可取而不取,皆是因有“让”德与“不争”的行为,被孔子表彰为“至德”。
根据孔子极其重视“让”德的思想,再来比较舜与武王。武王以武力征伐纣王,方得天下,自是差文王一等,无所谓“让天下”。但是,舜却是“让天下”的代表。孔子明确指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26〕显然,孔子称赞舜和禹,正是因其“有天下而不与”。舜在已经得到天下的情况下,还能够禅让于他人,把“让”德推到极致。因此,舜之德与武王之德的差异,应该在“让”德的意义上得到理解。
进言之,具备“让”德也就是求“仁”。《论语·述而》记冉有请子贡问孔子是否准备帮助卫出公父子争夺王位,子贡则通过问询孔子对于伯夷、叔齐的态度来窥探答案。子贡问孔子对于伯夷、叔齐的评价,孔子赞二者为“贤人”,称其“求仁而得仁”。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之子。按礼法,长子伯夷应该即位,但孤竹君有意改立幼子叔齐。在孤竹君死后,伯夷为遵父命,独自出逃。而叔齐也因自己按礼法本不应即位,放弃王位,逃出国土。伯夷、叔齐是以国相让的代表。孔子面对卫出公的父子之争,表彰让国之德。并且,伯夷、叔齐因有“让”德被孔子赞为“仁”。遍观《论语》,尧、舜、禹、泰伯、文王、伯夷、叔齐等人,或被孔子赞以“仁”,或称“至德”,其原因都是因其有“让”行。可见,孔子对于“让”德的极力推崇。
回到“子谓《韶》”章,此章之旨看似与“仁”无关,其实“尽善”与“未尽善”的差异正在于“让”德。武王虽是圣王,却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代表着“争”。对此,孔子并没有加以贬词,而是以赞美《韶》的“尽善”来肯定舜所代表的“让”德。重要的是,“未尽善”并不与“未善”相对,它仍然是善的,只是不够理想化。所以,“未尽善”与“尽善”也非对立关系,“未尽善”处于“尽善”与“善”之间。在这里,存在一个“未善—善—未尽善—尽善”的阶梯。其中,“尽善”是最高等级的善,它与“至德”一样,是最为理想化的德性。因此,“子谓《韶》”章并不是要表达孔子对于武王征伐的贬斥,而是许《韶》乐以“尽善”,从而凸显对“让”德的推崇。有“让”德亦是得“仁”,故孔子赞舜乐“尽善”亦是以舜为仁君,“未尽善”则可以理解为孔子不许武王以仁。
四、小结
孔子赞《韶》和《武》皆尽美,又赞《韶》尽善,但历来注家所留意的却是《武》何以未尽善的问题。随着孔安国将汉代有关禅让与征伐的讨论带入文本中,关于此章的阐释便难以绕开对舜与武王德性优劣的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解的视野,导致对“尽善”与“未尽善”的解读无法深入孔子的思想世界。
实际上,当解释的中心从“未尽善”转换到“尽善”,并从《论语》自身脉络中推敲“尽善”的含义时,舜所代表的至善的“让”德,便能够提供诠释的新线索。孔子认为武王之乐未尽善,并不是为了贬武王伐纣为不义,正如董仲舒以“时”释之,武王之“争”有客观的原因。不过,武王毕竟未体现最高的“让”德,故不予以赞扬,即“未尽善”。舜有天下,仍禅让于人,其所代表的“让”德乃至高的善。■
——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