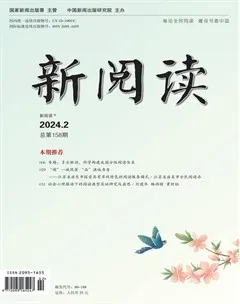宋朝的文化遗产及其反思
虞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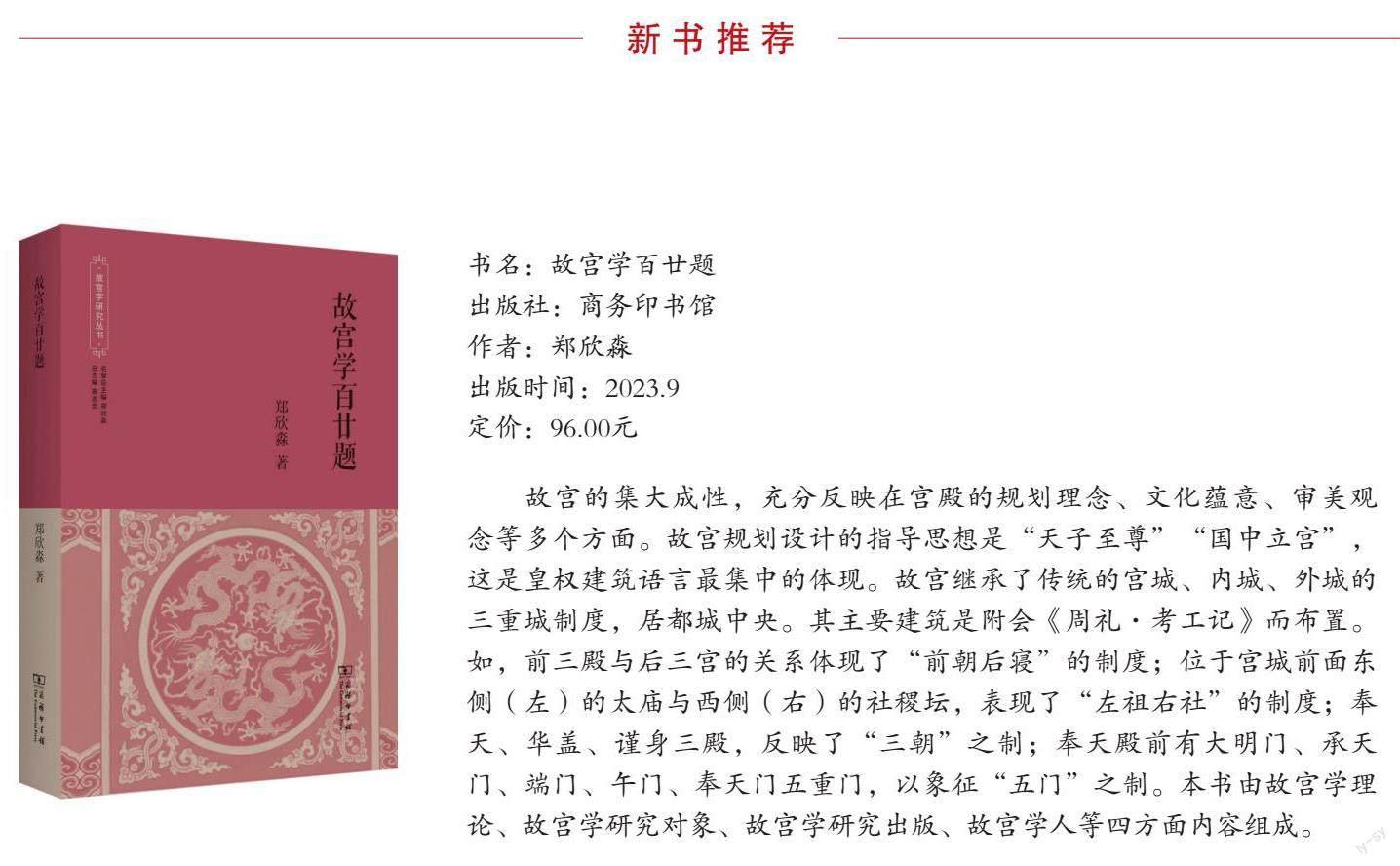
严复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如果究心于宋代的历史和文化,在笔者看来,主要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个层面。宋朝的政治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二是统治思想。
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政治制度设计。宋朝确立了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为了维护君权,防范相权独大,宋朝把军权从最高行政机构里分割出去,划归于枢密院;而在中书门下,增设了参知政事,又分割了相权;这样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与宰相并称为宰执,形成一个集体领导班子,防止相权独断。另外,再把财权分出去,成立三司来总理财政。这样一来,就能够成功地维护君权独尊,稳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对地方行政也作了全盘的政治设计。由皇帝直接任命州县长官,又设立通判,掣肘知州。在路一级层面,设立了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四大机构,各司专职,相互督察,监督州县。漕司主要负责财政,宪司主要负责刑法,仓司负责救济,而安抚使司则负责军事。这样看上去叠床架屋的权力结构,就能够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不可能再出现尾大不掉的割据祸患。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政治制度的高明设计,成功地防范了宋代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再次出现地方割据和中央混乱的局面,大一统的政权一直维持到帝制的灭亡。
军事制度优势。宋朝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三衙是三衙鼎立,互相牵制,三衙的主帅只有统兵权,没有发兵权;枢密院一般由文臣担任,只有发兵权,没有统兵权。这样一来,每到临战的时候,皇帝临时命将,能很好地对武将势力进行制约。宋朝的军事思想,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所谓强干弱枝,就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京师的禁军都比地方禁军要来得雄厚,这样就能够很好地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如果某地发生叛乱,也能迅速平息突发的事变。所谓的内外相制,是指在禁军布防上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军足以对付外地一处的禁军叛变,集结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完全可以对付京师的动乱。这样,就能有效地防范军权过大,防止以前出现的武将割据的局面。
统治思想集中。前面提到的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是有高明的统治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可以看到,宋朝人都有一种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大公始立。”在这种“天下大公”的积极思想的主导下,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太祖立了誓碑“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也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官僚士大夫的言论自由。在宋代,尤其对台谏监察制度有高度维护,所谓“崇奖台谏”“不罪言者”,“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宋代从太祖、太宗以来,基本上都能保护官僚士大夫相对的言论自由权,养成他们敢于说话、敢于论政的刚劲之气。因此,宋朝人有这么一种总结:“上之所以待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
宋朝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读书人关注的是:代表性的文学品牌是宋词。宋朝出现的市民文化的新代表——话本和南戏,《清明上河图》和文人画。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尚意书法,以及以宋瓷为极致的工艺美术,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上乘之品。
在笔者看来,宋代文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具有决定力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过几代思想家的创造性转换,宋学作为新儒学流派纷呈,大师迭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先秦诸子学之后又一座新的思想高峰。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作为宋朝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当时及其后的思想、伦理、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宋朝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平竞争。有人把宋朝称为科举社会,宋朝的士大夫官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走上仕途。而在宋朝士大夫官僚中间,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理念:盡管职位有高低,但都是“比肩事主”,在行政事务上,大家都是相对平等的。而从宋朝的地主阶级结构来看,已经没有前代所谓士族门阀地主的存在,而是士庶不分;宋代的土地流转是以经济方式实施的;这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士大夫思想家,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在宋朝社会中,士、农、工、商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到普通百姓中间。这种平等思想,在宋朝下层民众中间,也有深刻的反映。在宋朝三大农民起义过程中,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是这种平等意识的反应。当然,宋朝的平等意识与现代的平等意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我们还要区别对待。
兼容精神。兼容主要表现在宋学的多元开放、兼收并蓄上。宋学流派纷呈,尽管各派的思想主张、政治主张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在它的上升期能够互相赏识,互相宽容,这样就促成了宋学的创造性贡献。在宋朝的宗教层面,儒学、佛教和道教三教融通,并行不悖。宋朝统治者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在宋朝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儒、佛、道三种思想也是同时在生活日常中各有体现的。在宋朝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雅俗文化的共融共存。传统的诗文和长短句、小说、话本、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百花齐放。在艺术领域里,画院画、文人画和民间画齐头并进。雅化的禅宗和俗化的净土宗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共同地被加以接受。
经世理念。这个理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尤其明显。我们看到,宋代的士大夫官僚以范仲淹为代表,提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情怀;文彦博在和宋神宗的对话中提出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诉求。而理学“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实际也是主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宋代的士大夫官僚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行动实践。在这方面,南宋的浙东事功学派就是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政治行动的方针。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宋代经世理念的经典表述。
名节操守。宋学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名节操守。到北宋中期,一般士大夫已经对晚唐五代以来那种随波逐流的行为严加批判,“知以名节为高”,“不枉道以求进”。他们认为,“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君主可以实行你的刑和赏;但是“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后世人对你的评价,将是万世的声名所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可以看到,宋朝传给我们的名节操守有这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面对权位名利的非分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二是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分的层面;三是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多的亮点;而第二、第三层面,在宋朝历史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经成为当时上至将相、下到黎民百姓共同尊崇的价值观念。从杨家将的抗辽、岳飞的抗金,文天祥的抗蒙气节等,都可以看到这种价值观念在宋代的具体体现。
宋朝遗产的历史反思
宋朝的遺产也具有消极的影响。在政治遗产上,除了前面所肯定的积极因素以外,也可以看到,它的总方针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样,宋朝在军事上是各自为政、动辄掣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外敌入侵时,就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行政上尽管有互相制约、维护君权的优点。但是,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造成政治上缺少活力和短于应对。
在精神遗产上,随着南宋中后期理学官学化的进展,精神遗产也付出了负面的代价。进一步说,就是“外王”之道逐渐淡出,而“内圣”之学充分凸显。宋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在南宋后期也日渐泯灭,而个别教条也开始“理学杀人”:“二十四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过后代专制主义的扶植和发酵,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防止某些对宋朝文化和宋朝历史的误读。在笔者看来,误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宋代社会经济的误读。有的书籍里提出,宋朝是“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时代。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统治的相对完善,农民生活质量比前一代有所提高,但是在很多宋词里,也可以看到宋朝的下层民众生活艰难困苦。因此,宋朝绝对不是广大民众的所谓黄金时代。
二是对宋代言论环境的误读。虽然宋代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但是并不是没有思想禁区的,也不是没有文字狱的时代。从邓小南教授的研究里可以知道,南宋绍兴时期,由于高宗的默许,秦桧兴起大量的文字狱,到了南宋中期,韩侂胄掀起庆元党禁,树立在桂林的元祐党籍碑就是对异见思想加以禁止的标志。所以说宋朝没有思想禁区,没有文字狱,那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读。
三是对宋朝士风名节的误读。宋朝对士大夫的言论有所宽容,但是随着宋朝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变化。笔者认为,士风从来是随着政治风气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政治生态良好的仁宗庆历、嘉祐年间,出现了像范仲淹、包拯那样具有高风亮节的士大夫典范,但是随着南宋政治的内向,也可以看到,从秦桧到史弥远、到贾似道等等,在他们专政的时期,整个政治是相当污浊的,整个士风也相当腐败。从秦桧到史弥远、到贾似道也都是士大夫,追随他们的也都是士人,这时候的士风名节就不能和北宋上升期的士风名节相提并论。因此,我们也要全面地、分时段、分具体人物来对宋朝的士风名节做出正确的解读。
作者系宋史专家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