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笺
潘玉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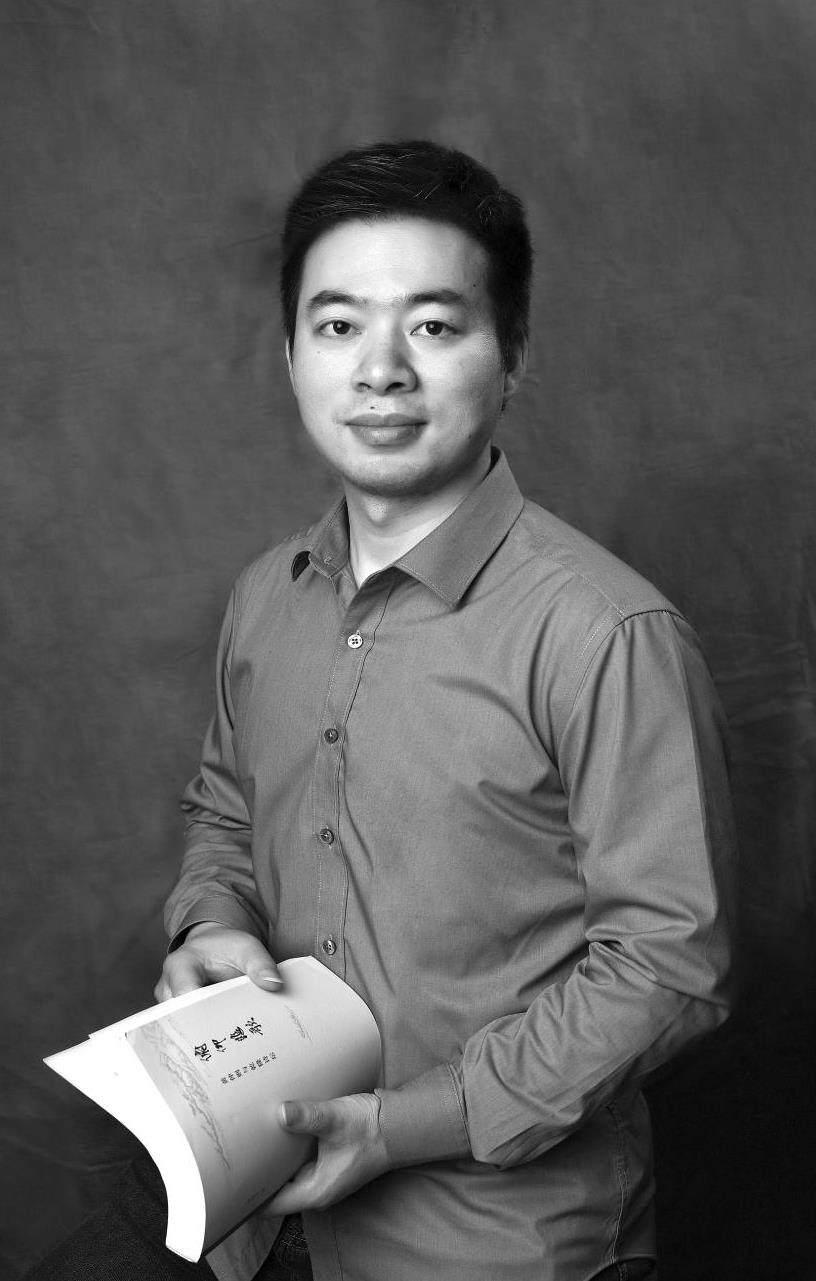
如风有信
如风有信,在一身枯黄中,柳树枝头冒出了点点绿芽。像是女孩儿新得了一支用来别头发的碧玉簪,怯怯地、满心欢喜地戴了起来。那妆容真是好看,衬以一弯柳叶眉,完全不输出塞的昭君、浣纱的西子,顷刻间,惹得边上的树啊草啊争相效仿。
庭院里,河岸边,田埂间,不知不觉,多出许多颜色来。单只梅花就有好几种:宫粉梅是淡红色的;朱砂梅是深红色的;绿萼梅是米黄色的;洒金梅的花色以白色为主,但每朵花上有浅浅的红条或红斑,料想是出自百花仙子的杰作。于是,便有那多情的诗人借物寄寓,折梅赋诗送与友人:“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梅花之外,还有迎春,有梨花,有山茶,有冬青,有桃、李、杏……且每一种草木,都有辨识度极高的色彩。这些颜色都是好颜色,它们如同一幅美丽的油画,生动地晕染着大地。
如风有信,当此时节,江南的雨水开始由凉转酥,它们脚步轻盈,翻越山川,跨过河流,时而站在枝头处,时而伏在藤蔓上,时而又钻入地底下。它们款款而行,所过之地,润物于无声,让草木的长势变得愈发葱茏,颜色变得愈发娇艳,万物生灵的心经过它的洗濯,也跟着变得柔软起来。就连空气也是如此,虽然气温并没有提升多少,有时倒春寒一来,凉冷之意依旧直袭心头,但空气里好似多了几分淡淡的不易察觉的祥和。
若是适逢一个晴天,四野里万象更新,会有一股极大的诱惑力“拉”着人们走出房门。至于出了房门干什么,泛舟游湖也好,朋友小聚也好,随便走走也好,都不会影响人们对于无限春光的喜爱。而且这种游春的兴致不独年轻人有,老年人也不例外。宋代的陆游就曾为此写下八句诗:“儿童莫笑是陈人,湖海春回发兴新。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鳞鳞江色涨石黛,嫋嫋柳丝摇麴尘。欲上兰亭却回棹,笑谈终觉愧清真。”读着,读着,让人不由得喜欢起这个率真的老头来。是啊,游兴忽起的老人能有什么错呢?要怪,只怪这春天太过迷人。
当然,音有变徵之调,春日的天气也不只有晴和雨。间或,也会下几场春雪,响几声春雷。如果说雪是丰年的预兆,那么雷声则是把这种预兆变为现实的呼喊和吁请。
如风有信,草木苏醒之后,沉眠了一冬的小动物们闻着雷声,也从各自的居所里跑了出来。蜘蛛忙着织网,蚂蚁忙着搬家,小蝌蚪忙着长大,大到蛙声十里可出山泉。
汉语里有个词组叫“草木虫鱼”,泛指所有的植物和动物。想来,对于春天的降临,欢喜早已形成一种共鸣——“草木虫鱼随物化,山川海岳亦欢呼”。但同样是欢喜,表现卻各有不同。如果说草木的特征是颜色,红的、黄的、粉的、白的;是生机,旺盛的、欣欣向荣的——俱为形容词,那么,动物的特征更像是动词。鸟儿在空中振翅翱翔,鱼儿在水里吐着泡泡,猫儿在爬架上打了个哈欠,大黄狗伸了一个懒腰走出自己的窝,虎、鹿、熊、猿、鹤耍起了“五禽戏”,鸡和鸭互相问好,却被大鹅追得满院乱跑……
春天到了,这个世界热闹极了。牛在“哞哞”叫,鹊在“喳喳”响……这一刻,纵然你我都没有公冶长的本领,也能知晓它们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心情亦是一般愉悦。
如风有信,游子们辞别家人,陆续返程。上班族们开始了一年中最初的忙碌,为梦想,为生计,埋头苦干,用智慧和汗水换取希望的果实。勤劳的农人们则纷纷背上锄头、铲子,在料峭的春寒中,在迷蒙的细雨中,或是在融融的暖阳下、春风里,种下时令菜蔬。一锄头,一锄头,一铲子,一铲子,他们在菜畦、稻田和山地里播下种子,又看着它们发芽、生长。他们施肥、除虫,用心呵护,一如当初守护儿女成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计”不总是为自己,有时也为别人。在我生活的城市,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慈善楷模”钱海军、“献血达人”周丰权、“救人英雄”王军浩、“知心姐姐”唐洁……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岗位,却因为同一个目的有了同一重身份。那个“目的”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以春天般的温暖,而那重“身份”则是志愿者。
一日路过文化礼堂,我听到里面传来阵阵应答声和笑闹声,透过门缝瞧去,原来是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工会主办的新一期的“复兴少年宫”又开课了。谈到长大后的理想,孩子们畅所欲言,有的想当一名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有的想当一名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有的想跟谷爱凌一样驰骋奥运赛场为国争光。许是在志愿者身上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做志愿者”也成了他们的其中一个选择。
“我长大了也要像钱海军叔叔一样,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是春风播下的种子,又在春天萌了芽。
树知道
树虽然没有眼睛,却有比长着眼睛的人更开阔的视野、更灵敏的预知能力。春天来了,草木萌发。人还躲在被窝里睡懒觉,它们却已先人一步感知到了春天到来的信息。
于人而言,若是一个好朋友九个月不见,重逢时自是满心欢喜,少不得要梳洗打扮一番,见面,说话,互相聊聊别后的琐事。树也一样,得知春天已经在来的路上,它仿佛迎接一个重要的远客,一去先前的慵懒姿态,眉眼间变得分外精神,将准备工作做了起来:枝干光秃秃的,未免有些不雅,意念所及,嫩芽儿争先恐后地长了出来,就像是爱美的女子往脸上抹了腮红、口红,涂了霜和粉底,还加了个漂亮的眼影。
待到脸上的妆画完了,抬头往树梢间看去,发现去年的叶子也已经有些老旧,树将风招来,吹落松散枯朽的枝叶,换了一个新的造型。又将雨唤来,洗去身上的“碎头发”和泥垢,旋即,覆之以苍翠欲滴的颜色,远远望去,整棵树神采焕发。鸟雀看见了,同它打招呼,问候着“早安”“午安”和“晚安”。每年春天,第一只鸟儿到来的时候,必先飞到树梢头。它们沿着旧一年的行迹在枝头眺望,寻找去年的伙伴,寻找今年的安身之所。
树下有时有花坛,有时有小溪。故而那些树知道的消息,花坛里的蚂蚁都知道,河里的鱼儿也知道,再算上那空中的鸟儿,可说是水陆空全都知道了。它们在水里游着,在地上爬着,在空中飞着,不断将消息扩散。于是,要不了多久,整个世界都会跟着雀跃起来。不过仔细说来,最欢喜的还是树。
树知道春天的美好,也愿意把这份美好分享给别人。春天不是落叶的季节。但是我们走在大街上,时常能看到从树上掉落下来的叶子和果实,有时落于车上,有时落于人的脚边。它们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在提醒人们,不要总是低着头,春天到了,不妨偶尔抬头看看外面的风景。
树知道很多大自然的小秘密。你若肯停下脚步,走到树前,常常能在树根处看到各种颜色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小草。若是在山间,或许还有许多时蔬。野生的荠菜和马兰头悄悄地在树底下说着话,蜜蜂和蝴蝶假装不经意靠近,实际上侧着耳朵在一边偷听。
树知道小孩子最喜欢什么,因为它也有一颗童心,不然何以四五月间会有那么多风筝挂在树梢?“江北江南低鹞齐,线长线短回高低”“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些画面,树都瞧在眼里。风知它的心意,于是便有了“何处风筝吹断线?吹来落在杏花枝”。
树知道那些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人有多么不容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它们拼命吸收阳光和雨水,努力让自己长得茁壮一些,只为夏天到来时,农民辛劳之余,可以在树荫下避避日头,于无尽的汗水里添几许惬意。
这就是树,它虽然不会说话,却常常带给人希望和温暖。
风从荷间过
怡荷园的荷花开了。为这,我等待了许久。原想趁着周末得闲,前去观赏一番,未曾想临时遇到些事情,规划好的行程泡了汤,只在朋友圈里赏了半天荷花。
事后,好几位朋友都与我说起:这两天,怡荷园里,风清冽,水清冽,碗口大的荷花随处可见,大人、小孩或坐在水榭长廊里,或穿行在阔大的荷叶之间,体会到的尽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悠远意境。人迹所至,笑语声和欢闹声不断。寥寥数语,再次激起了我心中的向往。
人世间的风景,一旦进入神识和眼帘,总有一种哪哪都是的感觉。荷花便是如此。
荷花本是夏日里的常物。六七月间,荷花开了,东向西向,南边北边,随处可见它们的踪影。它们开在景区,也开在旷野,开在“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也开在“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半亩方塘。与其不择地而生的习性相对应,不唯学富五车、标榜格调的文人喜欢看它们,乡间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人也喜欢看它们。
荷花开时,初时是一个个花骨朵,它们从一片片翠绿色的叶子中间探出尖尖的脑袋,有红色的,粉色的,也有白色的,继而“蓬”的一下,花就开了。其实这声音是很幽微的,幽微到哪怕我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都听不到花开的动静,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又极为响亮,宛如一道霹雳,在人的意识里炸响,让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夏日已至,荷花已开。
荷花开时,传递消息的有时是人,有时是风。从荷塘里的叶子吐露新芽到荷花含苞待放、将开未开,总有人在关注着它们,关注的同时不忘将消息传到外边,说与几十甚至几百里外的人们知晓,以至于荷花一开,很多游人从远处蜂拥而来。如果说人传递消息的对象只是人,那么从风这里接收消息的群体则要广泛得多了。当风掠过水面,与一朵又一朵的荷花相邀共舞,舞姿翩跹,惊艳了池水。很快,蜻蜓、蝴蝶纷纷跑来围观,青蛙和蟾蜍全都游到了荷叶下面,就连水下的游鱼也都探出了脑袋,荡开的一圈圈圆晕,与风吹起的涟漪相撞在一起。寂静的荷塘瞬间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李乐薇先生在《我的空中楼阁》一文中写有一个精妙的句子:“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如果说荷花是那“已经很美”的事物,那么风便是这“点缀”。
风从荷间过,可以将一幅静态的图画变成一段动态的视频。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等发现时,已经挤挤挨挨,到處都是。要知道,即便没有风,塘里的荷花就已十分美丽,亭亭静植,不蔓不枝,白的像玉,红的像霞,它们以绿叶为衬,俨然是画上景致。有了风,更是如花解语,无论微微颔首,还是重重点头,都显得别样灵动,一如徐志摩诗中所写——“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尤其当风吹动荷叶,露出枕着叶子而眠的露珠,以及叶下藏身的小动物,荷塘就变得愈发有趣了。等到一轮明月升上中天,乳白色的月光盈盈洒下,将整片荷塘笼罩其中,更是让它美得不可方物。
塘里的荷花不仅美,还是一个远游者。它虽然没有脚,亦不知晓舟楫飞行之法,平生足迹却遍布天南海北。浙江、陕西、江苏、江西、海南、重庆、北京,好像只要是我去过的地方,就没有它不曾到过的——不知还有多少我未曾游览的地方,亦留有它的足迹。人们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许不是没有,而是未曾发现,或者发现了也未曾留心罢了。至少荷花的“行路”之远,就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谈及“画家六法”时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或许,论读书之多,荷不如我,但论行路之远,显然,我大不如它。
荷花还常常走进书本,走进古人的诗里。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便有多首诗歌为其画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等句子,便是最好的例证。到了秦汉以后,文人作文,诗人作诗,更是到了“无荷不欢”的地步。而且,在诗人的吟咏里,荷花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芙蕖,菡萏,藕花,泽芝,溪客,水芙蓉,等等。
如果说荷花是诗人们笔下常见的意象,那么风则是把这个意象与其他景物聚拢在诗中的黏合剂,是一种捉摸不定、玄之又玄的思绪。看见荷花在动,诗人们就仿佛看见了灵感。
从荷间飘拂而过的每一缕风都是一首诗,一阕词,一支曲子。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数不清有多少经过荷花池的文人墨客,被那池中之花迷人的容颜吸引了去,纷纷为它驻足停留,留下诗句,留下画作,留下千古的传唱。这其中,有白居易的“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有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石涛的“相到熏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但要说到最得“风荷”神韵的佳作,还是得属周邦彦的《苏幕遮》,词之上阕云:“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国学大师王国维给它的评语是:“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荷的神理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上来,思来想去,大概就是周邦彦所说的这个样子吧。
有风从荷间穿过,就连难熬的溽暑似乎也多了几分凉意。此时最宜雇一艘小船,最好是带船篷的那一种。将身子藏在篷中,书卷在手,冷饮在口,不啻美妙;看得乏了,喝得累了,就靠着船舷小憩片刻,任由小舟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地飘荡在水面上,随它东南去或者西北游,人间自在,莫过于此。有这样惬意的所在,哪怕从黎明曙光初露待到深夜月上柳梢,想来很多人也是乐意的。
若是觅不到小舟,那就寻一处桥洞,最好桥下也有小荷数茎。然后在桥下寻一块方石,与荷对面而坐,凉意也会由心而生。虽然桥洞外边,水面经过阳光的照射,温温热热的,可桥洞里边,因为桥身和荷叶的遮挡,因为有风徐徐吹过,则给人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不远处的柳树和梧桐树上,知了正在拼命地嘶吼,像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暴躁汉子不知又在哪里受了气,对着空气宣泄情绪。也只有在此时,你才会发现“蝉噪林逾静”这句诗的真正含义。可不是吗?有如此聒噪的参照物,洞下、荷边的安静也就被衬托得愈发鲜明。静而生凉,这样的地方无疑是夏日纳凉的好去处。对此,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可谓深有体会。
秦观曾经写过一首《纳凉》诗:“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短短二十八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古人夏日里消暑纳凉的生动画面来。也许是天太热了,日头太猛了,诗人手执一根竹杖朝着树荫急急而奔,在画桥南畔觅得一处阴凉之地,支起胡床,高枕而卧,这一睡就是一整日。待一觉醒来,明月东升,船笛参差,池里的莲花暗香杳杳,已将夏日的暑意消减得差不多了。
细说起来,晚于秦观500多年出生的李渔算得上是他的同好。李渔曾经这般说道:“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他常常跟随那叶之清香、花之异馥,在三伏天里问流水和清风借凉意。这一点,一直为后人所效仿,而且一效仿就是数百年。
如果花和人一样也有知己,最懂梅花的自然是雪,最懂荷花的或许便是风了。特别是当风与雨联袂而来的时候,常给人一种与天晴时大不相同的美感。细雨纷纷,在风的护送下落入湖面,也落入了荷叶之上。叶面与花朵沾了雨水,娇艳欲滴,像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像初醒的婴儿刚刚啼了一场。无论远观或是近看,都是别有一番滋味。
朦胧中,我的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两个人在荷塘边相遇,一人问:“为何而来?”一人答:“为荷而来。”明明只是再恬淡不过的对话,映射在心中,竟是那样的妙趣横生。
冬青可爱,宛如故人
朋友送了我两枝冬青,灰枝红果,甚是清雅,宛如山中隐士,尘外孤标,远观近赏,不觉俗艳。我与妻子欢喜莫名,围着它们打量许久,心中丝毫未有“厌”“烦”之意。
说来也巧,约在朋友送来冬青之前的三五天,我与妻子闲翻朋友圈,见一花圃售卖的花花草草中,唯有冬青最是入眼。花圃离住处不远,就在马路对面,欲待买一枝来,却因家中无闲置花瓶,不得不打消念头。我们略一商量,打算先去网上购置一个瓶子,等瓶子到货,再将冬青从花圃移入瓶里来。不承想,朋友抢先了我们一步。
朋友送来的冬青由一张素雅的画纸包着,画纸的素雅将红色的果子衬托得愈发娇艳。娇艳欲滴的红果中间还夹了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顺”字,另有“心想事成,好事发生”八个小字。前段时间,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心情起起伏伏,好像坐过山车一般,逆行偌久,也确实需要顺一顺了。仅此一点,足可见得朋友是个“有心人”。
因是心里欢喜得緊,吃过晚饭,我连锅碗都顾不得洗,便由妻子拉着去了马路对面的花圃。我们问花圃老板娘可有合适的花瓶,老板娘左寻右寻,却始终不曾寻得一只。得知我们想要盛放的是冬青,老板娘说,花瓶是没有了,不如送你们一张便签吧,挂在冬青上,为新年讨个好彩头。妻子点点头,挑来拣去,最终从一堆便签中选了一张“一夜暴富”。老板娘用红绳将便签串好,递与妻子,妻子望着我粲然一笑,我也跟着笑了。
“一夜暴富”四字让我想起了旧时的一则典故:绍圣四年,苏轼贬官海南,因抄得《汉书》而倍感欣喜:“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与东坡居士相似,于赏花人而言,得冬青一枝,心情的明媚已如冬日暖阳一般,何况还得了两枝?
回到家中,我们思前想后,找了一个半米来高的爆米花瓶,拧开盖子,倒出爆米花封存于收纳袋,注入清水,将冬青置于其中,再将“一夜暴富”挂于冬青枝头。时值隆冬,窗外冷风如刀,屋里细枝瘦腰——但见冬青立于瓶中,如人栏杆半倚,虽是初次相遇,却如旧友重逢,两两相望,倍感亲切。
显而易见,在诸多的植物之中,冬青不是最娇贵的,也不是最好看的,它没有竹的苍翠,没有花的妖娆,甚至没有草的茂密,但它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给人以清新之感。这就好像一桌珍馐,如果尽是鸡鸭鱼肉、海味山珍,未免腻味,如果当中摆有一盘时新小蔬,则会让人觉得“刚刚好”;又譬如长篇赋文读得多了,偶尔品上一首绝句或小令,也是别有一番味道。
“冬青树上挂凌霄,岁晏花凋树不凋。”就视觉而言,冬青呈现给人的更多的是红色。那它因何以青为名,而不是红呢?显然,冬青的青非指色之翠碧,而有常青之意。花圃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只要浇灌得当,冬青可以活上两三个月,两三个月岂非就是一整个冬季?冬青,冬青,或许便是冬日常青的缩写吧。我忽然想起自己旧时曾读李渔的书,笠翁先生在《闲情偶寄》里将冬青称为“不求人知树”,他说:“冬青一树,有松柏之实而不居其名,有梅竹之风而不矜其节。”于是,赏心悦目之余,我不由得对眼前的这盆植株又添了几许敬意。
痴看良久,不觉夜深。翌日清晨,我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窗帘拉开,让阳光踏着窗棂缓缓而入,落于冬青之上,光影斑驳,愈添冬青的生机和日光的明媚。
野果芬芳候人来
从春天过渡到夏天,有很多种物候,比如蛙鸣响,比如桐花落,比如蔬果熟。蔬果有人们刻意栽培的,也有山野间自己生长出来的。
在南方,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有两味野果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是空心藨,一种是覆盆子。空心藨长在地上,有的地方也叫蓬蘽;覆盆子长在树上,树莓是它的另一种称呼。
人们在品评蔬果的时候,除了味道,也会论及它们的颜色。成熟的空心藨俱是红色的,这种红仿佛经过了雨水的润洗,来得特别的鲜艳。相比起来,覆盆子的颜色则要淡上一些,像落着一层薄薄的绒须。在乡间,空心藨和覆盆子各有别名。
空心藨的别名是果果翁。当然这果果翁只是方言的音译,到底是果果还是蝈蝈未得确切,毕竟这时节蝈蝈开始出现,人们以小动物言称同一时间出现的野果也可以说得过去。而翁字则相对容易解释,农村里的老翁在田间劳作时常常头戴斗笠,用来遮阳或者避雨,空心藨内部中空,看起来形似一頂小圆帽。除了果果翁,旧时田里还有一种杂草名为茅草头翁。
覆盆子的别名则是“甜酒”。如果说甜是指味道而言,那么酒当是指它带给味蕾的感觉了。美酒醉人,让嗜酒者欲罢不能,“甜酒”若是吃多几颗,也极易使人上瘾。它的个头比空心藨略小,味道却要较空心藨更加复杂多变:未熟时无味,半熟时微酸,待得熟到十分,则变得无比甘甜,远比街市上热卖的桑葚好吃。
每当空心藨和覆盆子成熟时,溪水边,空地上,于无垠的绿色丛中生出一种诱人的红色。与此同时,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提着篮子、拿着塑料袋悄悄走近,将果实采摘来吃,就像在大棚里摘草莓一样。果实下有许多的小刺,稍不留神就会被划伤,但这些伤口跟馋嘴的诱惑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通常,我们在采摘空心藨的时候只取果肉部分,而摘覆盆子的时候则会连底部的蒂头一并摘下。这与两者的果实属性密不可分。覆盆子的果肉比较结实,放学路上偶然得见,未曾带篮子也未曾带袋子,可以将覆盆子摘来置于衬衣的口袋里,而空心藨用同样的方式储存的话,容易挤成碎渣,惯会就地取材的孩子们大多会于近处取一株野草,散去叶子保留枝干,将空心藨一个个地往上串,像糖葫芦似的,别有一番趣味。
除了空心藨、覆盆子,与它们同一时期长出来的,颜色、味道相近的野果还有许多,但并不是每一种果子都可以食用。也正因此,每年到了四五月,大人们常常叮嘱自家的孩子,空心藨、覆盆子上若是有蛇、有洋辣子(一种毛毛虫)爬过,会留下一个个白色的斑点,这样的果子千万不能去吃。那时不明所以,后来见得多了,也就懂了,这是为了与蛇莓进行区分。因为蛇莓是吃不得的。当然,更多的野果是可以摘来吃的,而且十分美味。如空心藨、如覆盆子、如茅莓,这些野果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虽然秋天的野火曾经覆灭它们,冬天的白雪曾经盖住它们,但当春夏之交,阳光普照大地,雨水浇沃人间,它们重新捧出沉甸甸的果实,以此回馈给每一个行至山间的人。
如果说以前人们跑去摘野果是因为可吃的东西太少,那么如今,空心藨、覆盆子一经露面,大人小孩便提着篮子,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到山里,固然有尝鲜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了怀念吧,怀念曾经的岁月,就像怀念我们再也回不去的过往。
(责任编辑 王仙芳 349572849@qq.com)
如果花和人一样也有知己,最懂梅花的自然是雪,最懂荷花的或许便是风了。特别是当风与雨联袂而来的时候,常给人一种与天晴时大不相同的美感。细雨纷纷,在风的护送下落入湖面,也落入了荷叶之上。叶面与花朵沾了雨水,娇艳欲滴,像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像初醒的婴儿刚刚啼了一场。无论远观或是近看,都是别有一番滋味。
——致坚守奋斗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