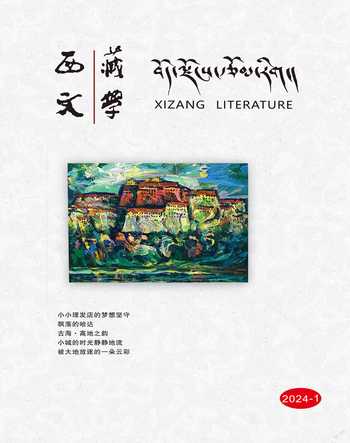飘落的哈达
旺珍,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就职于西藏广播电视台。热爱生活和大自然,用影像纪录生活,用文字探索人间。
哈达是一条河!
自古,哈达流经的地方,多处形成了自然村落。哈达河的源头起于一面不知名的小湖泊。这面小湖泊嵌在海拔七千多米的诺拉神山上,像是敬供给天神的一杯供水。诺拉神山脚下有一座诺拉寺,香火很旺。从空中俯瞰,哈达河在山间流淌的足迹,像一条飘落在人间的洁白哈达。
溜村,位于哈达河下流区域。它与拉萨市区接壤。出了溜村哈达河就汇入主河,也就是拉萨河。
溜村的清晨充斥着各种声音。
远处,机器轰鸣。近处,鸟鸣啁啾。
几只麻雀落在次多卧室的窗边,蹦来蹦去,时不时叫喊一声。它们叫得越清脆,次多觉得越刺耳,仿佛在催他起床。他起身关掉窗子,再次倒在床上,把被子一拉整个人蒙在了里面。“咚咚”一阵敲门声后央金喊道:“快起床,不是说好今天要去寺庙嘛。”紧接着央金下楼忙去了。次多并没有理会,继续蒙头躺平。
厨房煤气灶上的平锅里,酥油融化好了,央金把么古(融化的酥油)倒进五磅暖瓶里。没见次多下楼,她又“噔噔噔”地上楼,再次敲门,大声喊道:“寺庙要趁早拜。你再不起来,我可要拿凉水泼你了。”
“知道了。”次多甩开被子起身。
“叮叮”微信的铃声响起。
“早!”丹增问候道。
次多点了两个表示拥抱的小人表情发过去,就去洗漱了。
央金一手拎着敬贡主殿金灯的么古,一手拎着装有哈达和听装青稞酒的袋子。她的肩上还挎着煨桑时用的手工布兜,一面装着糌粑,一面装着小麦粒。
“快把车门打开。”央金站在家门口往里喊。
“开了开了!”次多一边按下车钥匙一边跑出来说道。
就在这时,往家赶的多吉看到了这一幕,他说:“哦滋啦,怎么所有东西让你妈妈提着!”多吉赶紧走到央金跟前,从央金手上接过暖瓶,让她坐进车里,再把暖瓶递给了央金。
“有活吗?”央金问道。
“还是没有。”多吉回答。
央金瞪了一眼家门口的“铁牛”说:“没用的东西!”
“别耷拉着脑袋,提起精神,不就差了三分嘛!这次肯定没问题。好好拜一拜,这次公务员考试如果能得到佛祖的护佑,就有希望了。”多吉拍了拍次多的后背说。
“嗯嗯!”次多没多说什么,弓身进到车里,发动起车子,出发了。
载着妻儿的白色“逍客”瞬间驶出了他的视线。
多吉回过头来好好瞧了一眼家门口的这头“铁牛”,他发现“铁牛”的眼睛上蒙了一层灰。不知是邻里的小孩还是路过的人,在它上面画了一朵云。多吉自言自语道:“一朵闲云多好,自由自在!想飄到哪里就飘到哪里。哪里像我,还得守着这个小卖部。”随即,他拿出钥匙,把家门口一旁的卷帘门闸一拉,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多吉是入赘到溜村的。他的老家是酷久村,在哈达河的上游。他家三个孩子,他是老大,下面两个妹妹。大妹妹梅朵嫁到了邻近的姹朵村,也是个农民。多吉作为长子,在溜村的日子里,他时常挂念着酷久村。因为,在酷久村老家有他年迈的母亲格桑和哑巴妹妹卓玛。
以前,多吉房前屋后都是农田,忙完农活,他习惯盘腿坐在哈达河边的草地上,抽根烟,哈达河潺潺流淌的声音在多吉听来,就像母亲喃喃的诵经声,能抚慰他一天的疲劳。
现在,农田没有了,溜村的村民都住进了长相大小一模一样的安置房,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藏式三楼小院。多吉的家就是其中的一间。从多吉家隔着几十亩地的距离是拉萨火车站。周边耸立的一栋栋高楼大厦,像大山一样包围着溜村。
说起这头“铁牛”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的运输车。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已经成了他们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年溜村的土地在拉萨市城市扩建中被征用,村民不得不告别锄头,多吉跟着多数村民一样,用国家发放的土地补偿金购买了“铁牛”。别看现在村民们对闲置在家门口的“铁牛”称之为加锅(废铁),但是曾经,溜村的村民们驾着“铁牛”驰骋于家门口的工地上,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身份的转换。邻村的人看到溜村车队驶过,觉得那阵势远超过望果节上赛马骑手们,发出羡慕的“啧啧”声。
邻村的村民们也像溜村的村民,拿到可观的土地补偿金时,也跟着购买了一辆辆“铁牛”。这样一来,周边村子几乎是每家都拥有了“铁牛”。记得当年修建拉萨火车站时,周边几个村的“铁牛”都跑来啃食这块“草地”,溜村的村民,有种自己草地里闯入了别家牦牛的感觉,很不是滋味。于是他们以村为单位开会商量,最后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民间规矩:各村“铁牛”只准吃自己村的“草”。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周而复始。但“铁牛”需要的“草”,不会持续生长,它是一次性的。看着坑坑洼洼的施工现场变成一栋栋大楼,当年为了维护本村眼前利益的规矩,竟成了“铁牛”蹄子上的枷锁。
麻雀,藏语叫康秋,意思是家鸟。大概就是因为它喜欢在屋檐下筑巢而得此名吧。在西藏,一年四季,最常见的鸟类就是麻雀。不管是牧区、农村,还是城里,有人家的地方就有麻雀。
一早,小麻雀们最勤快,扑腾着小翅膀,飞到这儿飞到那儿找食。有两只落在转经道上的廊檐上,叽叽喳喳说着话。这条转经道是酷久村诺拉寺的转经道。酷久村是哈达最上游的村子。在这条转经道上,当晨曦中村子里升起袅袅炊烟时,老人们转经的身影陆续出现,其中就有格桑。
高原初秋的晨风,习习吹来,透着寒意。格桑转完三圈,缓缓走下石阶。她一身黑色氆氇,侧着身每迈步下一个台阶,都要喘着粗气,休息一下,再迈下另一个台阶。黑色氆氇藏装的裙尾拖在石阶上,掀起一阵灰尘。这一幕被她的邻居卓嘎看到后,卓嘎立马“嘶嘶”两下把剩下的鼻烟吸掉,撩开邦典一角,把左手大拇指上残留的鼻烟灰在上面擦了擦,起身去搀格桑。
“您喘得那么厉害,还是不要大意了。”卓嘎搀扶着格桑来到长凳旁坐下。
“人老了毛病就是多!”格桑坐在长凳上,攥拳敲敲膝盖说。
“以后恐怕得让卓玛来陪您转经,您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
“老毛病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现在指望不上喽!”
“嗯?”
“她要去出家了!”
“出家?”卓嘎惊讶地看着格桑。
“嗡嘛呢叭咪吽!世间的一切聚散离合都是有定数的,我只能接受。”格桑双手合十感叹道。
“卓玛她话也不能说,怎么出家呢?”
“她的师傅找上门来了,缘分到了。”
格桑给卓嘎详细描述起当时的场景。
有天傍晚有一對尼姑师徒来到她家门口,就在家门口田地边沿除草的卓玛看见了。卓玛高兴地发出“啊啊”的声音,把她们请到客厅,恭敬地请她们喝酥油茶。两位师傅说她们是邻村米日寺的,寺院年久失修,来化缘筹资。知道她们的来意之后,格桑捐了五百元。
那位师傅看着卓玛,眼里流露出喜悦,她说:“一见这个姑娘就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
卓玛恭敬地站在一旁,双手合十频频点头。
“她三岁那年发高烧,没能及时退烧,结果烧坏了,说不了话了,但格桑听得到。”她向那位师傅说。
“您有几个孩子?”
“三个,她最小。”
临走时,尼姑师傅望着卓玛说:“如果愿意出家可以来找我。”并且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她。
“她念不了经!”
“不影响,学佛修的是心。”
从那天起,卓玛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脸上挂着微笑,等着格桑选个吉日把她送到米日寺。
“卓玛走了,那您怎么办?”听到这里,卓嘎问道。
“打电话给老大老二说了。他们说轮流养我。”
“那您要离开这里?”
格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酷久村,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她对陌生环境本能地有一种抗拒,越老越依赖熟悉的一切。
“没有办法呀!”
卓嘎见格桑叹气,马上握住格桑的手说:“您多有福气啊,每个孩子都那么孝顺,是您前世修来的福啊!”
格桑什么也没有说,她从藏装前兜里摸出黄色的小绸布,擦了擦眼屎,轻声诵着六字真言,没有任何表情,好像卓嘎说的这番话,是她耳旁吹过的一阵风一样。她的眼神,就跟她那被黄斑覆盖着的眼珠一样,黑白不再分明,透着浑浊。
有一年溜村的一个村民冒充邻村的“铁牛”,去吃邻村的“草”。发现后,被邻村村民收拾,把他“铁牛”的眼睛打瞎双腿打折,以示警告。看到这一幕,溜村的车队队长号召队员们,拧成一股绳,维护本村的利益。车队队长起意,进行集体起誓。
藏历朗嘎,天蒙蒙亮。溜村车队的队员们穿戴好节日的盛装,驾着各自的“铁牛”往诺拉寺出发了。位于酷久村的诺拉寺,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宁玛派寺庙。传说诺拉寺里供养的赞巴拉财神,得到过莲花生大师的加持。
到了寺院,他们首先进行煨桑,每个队员手里抓点糌粑、小麦粒,向着煨桑炉里抛洒,松柏枝燃起火焰,队员们又拿起青稞酒进行浇洒,瞬间升起烟雾。桑烟缭绕中,每个队员合十祈福!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诺拉寺的时候,车队几十位壮汉已经完成了煨桑和祈福仪式。接着,他们在寺院僧人的带领下,在主殿主供佛莲花生大师和赞巴拉前进行了膜拜、祈福。最后在诺拉寺的护法神殿,向着玛哈嘎拉,每个队员挨个发誓:“我将信守队里的规矩,有活时只派自家“铁牛”,绝不将邻村亲戚家的“铁牛”混进来。
从诺拉寺出来,多吉带路驾着各自的“铁牛”下了山,拐进酷久村,回了趟家。
家里的客厅和院子一下子坐满了人,格桑让卓玛打酥油茶。很快卓玛给每一位客人都倒上了酥油茶。
格桑问多吉:“盛装来朝拜寺庙,有什么喜事吗?”
“我们是来寺院集体起誓的。”
“为了什么事?”
“为了维护本村车队的经济利益。”
“立字据签协议不是时下最提倡的吗?”
“我在火车站附近大商场买的商品房,按照合同早该给我们交房,可到现在还没着落!”队长说。
“婚约也是,红本变蓝本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位蓄着络腮胡子的队员摇头感叹道。
“说白了你们是为了个人利益呀!”格桑望着这群壮汉说。
没人回答,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了。
格桑从前胸藏装兜里拿出鼻烟,倒了一点鼻烟在左手大拇指指甲和食指的凹陷处,咝咝吸着鼻烟说道:“我这辈子只经历过一次集体起誓。”
大家都看着格桑。
“那是五十年前,诺拉寺进行修缮,本村劳力都聚集在寺院。有一天寺院住持集结所有僧众,宣布寺院外墙内要埋进伏藏,现场的每一位知道伏藏具体位置的人要求起誓,保守秘密。”
“这么说诺拉寺的伏藏应该还在。”其中一位壮汉说。
格桑没有回答,她继续吸着鼻咽。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集体起誓是一件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
最后大家纷纷起身告辞。多吉离开时,看着母亲的眼神,他似乎读出了母亲内心对他的失望。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
秋叶飘落的季节,次多从溜村出发沿哈达河逆流而上去接奶奶。
与他同行的还有丹增。丹增坐在副驾驶座上,他上身穿着一件宝蓝色冲锋衣,黑色户外裤,戴着遮阳帽、墨镜,防晒口罩,手上还套了防晒手套。他精瘦细长的身段,瘫软在一旁,猛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女孩儿。比起丹增,次多的穿戴可是简单多了,一身黑色的休闲运动装。头发、五官、双手都暴露在外面,任凭阳光抚摸、蹂躏。
丹增用手机连上车载蓝牙,不管次多喜不喜欢,他任意调换着各种 歌曲。
次多不爱说话,专注地开着车。
汽车驶离溜村,背后的高楼大厦变得模糊后,进入乡村土路,道路两旁的青稞地里一派秋收的景象。丹增看到车窗外,几位村妇弓身在割青稞,他拿起手机就拍,兴奋地说:“这不就是米勒的《拾穗者》吗!”
“农民和土地是纠缠不息的。”次多挤了一下眼,打趣地说。
“我跟你也是。”丹增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扑向次多,双手搂着次多的脖子,摘掉口罩亲了一下次多的脸颊,次多瞬间觉得一股热流涌来,他迅速将车停靠在路边,把丹增搂入怀中。
丹增是学画的,三年前从中央美院毕业。在不同流派不同国籍的绘画大师中,他最爱十九世纪法国现实派画家米勒。他对米勒的作品,何止是热爱,近乎一种虔诚,恨不得把米勒的代表作进行临摹后像唐卡一样挂在佛堂里。
十年前,次多和丹增考上了同一所内地西藏班高中,之后又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关系越走越近了。
白色“逍客”继续奔驰在路上。
“我看到土地抑制不住地兴奋,真想一头扎进地里,好好体验春耕秋收,感受四季更迭。”丹增看着车窗外的田野说。
“那就捡起锄头当个农民!”次多笑着说。
“我怕我真当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就没有那么纯粹了!我还是通过画笔,描绘出我心中的农民和土地就好了。”
“银行的工作呢?”
“饭碗要,兴趣爱好也要。”
“有了坐的想着伸的,有了伸的想着躺的。“次多踩下油门加快车速说。
“一条道没必要走到黑,干吗一定要考公务员!”丹增不解地说。
“别忘了我是农民的孩子,一切得靠自己,不像你!”怼完这句话,次多脑海里瞬间想起高中时,丹增的父母每年借休假时间会来看丹增,而他的父母一次都没来过。
其实次多不是不想尝试创业,他也有他的兴趣和追求。但是,在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落榜后,他在拉薩一家教育机构打工,结果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机构没了,他也失业了。
汽车行驶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垭口,远远看到大山深处有一座村子,村里有十几户人家。有的嵌在山坡上,有的挨在山脚,也有人家临河而居。
“这才是我心中的村庄,有山有水,房屋分布错落有致。”丹增兴奋地说。
拐弯时,路边竖着一个牌子,上面用汉藏双语写着酷久村。
进了村,山体岩石上写着标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深山里的酷久村很安静,连哈达河潺潺的水声都能听得见。
进入村子,乡间小道上有牛羊自由走动。
车子停好后,他俩三步并两步来到了格桑在半山腰的家。
“嫫啦!”次多喊道。
推开门,格桑正在家中院子里捻着佛珠晒太阳。
看到他俩进来,格桑说:“累了吧,那么远,赶紧喝杯茶休息。”
“不累,现在路况好,也没那么远。我今天把您送到大姑家,我还要赶回拉萨。”
“那么着急?”
“我要从明天开始参加公务员考试培训课。考完后,我就来接您回溜村的家。”
正聊着,大门“刺啦”一声,邻居卓嘎和白珍笑呵呵地进来,手里提着装有酥油茶的暖瓶。白珍说:“路上辛苦啦,请喝杯热茶。”
次多赶紧请两位长辈坐下,自己接过白珍手中的暖瓶:“我来倒茶,您二位请坐。”
两位并排坐在格桑旁边,卓嘎看着次多说道:“啊默默,完全是大小伙子啦!”然后又笑着冲格桑说:“该娶媳妇了!”
“工作都没着落,不急不急!”格桑说道。
次多低头斟茶,随后冲她们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能当上国家干部,这书就没白读啦!”卓嘎咝咝地吸着鼻咽说。
听到这儿,次多心里嘀咕道:“怎么可能,这世上没有白读的书没有白走的路,都是算数的。”
“国家干部好啊,旱涝保收!”旁边的白珍补充道。
“普次多啦那么帅,多大了?”白珍问道。
“二十七岁。”次多回道。
“在农村早就是几个孩子的爸爸啦。”卓嘎附和道。
“不急不急,只要不带个公的回家就行。”白珍笑着说。
次多本能地看了一下丹增,丹增正忙着换各种角度拍三位老奶奶,好像没听见似的。
“要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次多走到格桑跟前问道。
“你小姑走前都收拾好了,那就出发吧,赶夜路可不好。”
卓嘎和白珍执意要送格桑到车子跟前,三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走下坡路,临上车前卓嘎握着格桑的手说:“有空常回来!”
“要回来,我不在期间,那几亩地就拜托你了。”
“放心。”
出发前,格桑发现车窗外,来了好多老邻居,她频频说道:“谢谢,请回吧!”
次多一一握手谢过邻居们之后,上车发动汽车,一溜烟跑远,身后的邻居们,还在向着他们挥手告别!
溜村村委会第一书记郭亦飞,除了开展党建工作,近期他最上心的就是统计村里孩子在公务员考试中落榜人员的情况。他想着在溜村搞果园、开养鸡场几个项目,可以给备考公务员的学子们安排一些临时的就业岗位。今天他登门挨个统计,来到多吉家门口时已是傍晚:“多吉啦,期初德勒(晚上吉祥)!”
“书记啦,请进请进。”多吉立马从小卖部里走出来,握着郭亦飞书记的手说道。
郭书记扫视了一下小卖部问:“生意好吗?”
“一般般。”
“几个孩子?”
“一个。”
“有工作吗?”
“在拉萨市里找了个临时的活。”
“考公务员了吗?”
“今年又报名了。”
“让你儿子填一下这个表,村委会可以安排个岗位。如果他愿意的话。”
“谢谢书记!”多吉拿过表格说。
格桑住在大女儿梅朵家有段时间了,但因为膝盖疼的老毛病犯了,一直窝在家。
今天她感觉好多了。她吃完最后一坨糌粑,喝完杯中的酥油茶,扶着床沿吃力地站起来,喊了一声大女儿梅朵,梅朵掀开厨房门帘说道:“您腿脚不好,要好好休息!”
“我想出去走一走。”
梅朵解开身上的围裙,扶着母亲下楼。
楼下一侧是一间小商铺,大女婿正在从他的小货车里卸东西。
“带我去田里转转。”格桑瞥了一眼小商店说。
“好好。”梅朵搀扶着母亲慢慢走着,旁边邻居家一楼开的是甜茶馆,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母女俩顺着家门口的这条柏油路走了八百米左右,然后拐到一条大马路上,梅朵指着大路两旁的塑料大棚说:“到了。”
“阿滋滋,这是什么呀?”
“我们村的地都租给汉族菜农了,不种地了。”
看着一大片灰茫茫塑料大棚,格桑感慨道:“怪不得一大早那么多人聚在甜茶馆。”
“现在城郊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啦。”梅朵得意地说。
格桑看着眼前租出去的地,回想起自己第一次拥有土地的情景。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往事了。
国家结束农村公社,实行土地分包到户。在公社劳动时大家都是集体合作,一起出工一起吃大锅饭,因此,干多干少,干好干差,没有区别。而土地分包到户,对于勤劳、能干的农民意味着是一次脱贫的机遇。
记得那一晚的月亮很圆,三个孩子都睡着了。格桑在院子里,就着月光捻着毛线等孩子们的爸爸次仁。等呀等呀,月亮都去睡觉了,次仁还没有回来。格桑起身准备回屋,这时大门外突然有了响动:“我回来啦!”格桑一听到次仁打着结的这句话就知道他又喝醉了。他被几个村民扶着,进到院里继续说道:“村里抓阄分土地,我们分到五亩地啦!”平常格桑最讨厌次仁喝酒,但那晚酸酸的青稞酒闻起来,格桑觉得甜甜的。
想到当年分到土地的喜悦,格桑本能地怀念起因病已经去世很久的丈夫,心头升起一丝凉意。在格桑心里,次仁除了爱喝酒,还真没有别的大毛病。他俩的感情,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自从有了自己的土地后,次仁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除了秋收最忙的几天之外,次仁不让格桑下地。每次去炒青稞磨糌粑的路上,次仁牵着毛驴,身边少不了格桑。来到附近的水磨坊,次仁卸下青稞之后,接下来的事,格桑就不让他插手了。他也会习惯性地席地而坐,与其他来此磨糌粑的村民玩儿骰子。
磨糌粑前先要炒青稞。炒青稞是一件很苦、很累的工作,勞动强度大,技巧性很高。首先,在烟熏火燎的炉灶旁和滚烫的沙子、烧红的铁锅、飞溅的青稞爆花打交道,稍一疏忽,不是烧焦了头发,便是烫伤了皮肉;还有青稞既要黄熟,又不能烧焦,火候最为重要。炒生了,糌粑吃起来粘牙,吃坏肚子;炒焦了,糌粑吃起来味苦。
可对于格桑来说,炒青稞就是一次娱乐,她哼着歌,整个身姿富有节奏,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上一下,整个劳动场景透着丰收的喜悦。
青稞不能炒成黑乌鸦
青稞要炒成小白鸽
小白鸽呀四处飞
带来丰收和快乐
……
午餐梅朵做了一盘青椒炒牦牛肉、西红柿肉末酱、咖喱土豆、素炒青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梅朵站起来首先给母亲碗里夹了一点青菜说:“这些菜都是在自家后院种的,没有农药,很健康的,您多吃点。”
“菜农为了产量一个劲地打农药。”大女婿说。
“你们不愿吃的蔬菜卖给城里人,你们也是有罪过的。”格桑面无表情地说道。
有一天,正午睡的格桑被叮叮咚咚的嘈杂声搅得无法休息。她缓缓下楼,发现大女儿女婿和几个汉族工人正忙着拆小商铺,看到格桑,梅朵说道:“您下来干吗,这里灰尘多,还是上去好好休息。”
“你们这是要干吗?好好的商铺怎么拆了?”
“这个商铺太小了,这几年攒了一些钱,准备再投资把整个一楼弄成一个大超市。”
“我们对面那家,原来他们家的地只有我们家的一半不到,但这些年他们家做生意赚了不少。您看他们家的三层楼房比我们家气派多了。这次弄成超市赚了钱,我们准备把二三楼重新再好好装修一下。”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怎么还想着装修?”格桑摇晃着脑袋慢慢上楼去了。
可能是年纪大了的缘故,格桑有时晚上睡不着,每当这个时候,她总喜欢跟她已故的丈夫说说心里话:“我们的小女儿卓玛,已经有了她自己的归宿,出家了。她出发去米日寺的那一天早上,脖子上挂满了邻居们献的哈达。天空飘起了雪花,真是祥瑞啊!
“我知道你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卓玛。在你弥留之际,我们都以为你走了,就请来诺拉寺的喇嘛为你超度,结果喇嘛说你内气未断,就给你服用了‘津丹,没多久你就真的走了。后来算出来,你就是因为放心不下咱们的哑巴女儿卓玛,心里有牵挂,灵魂才迟迟不肯离去。
“现在你应该转世投胎很久了吧?如果你转世投胎为人了,那么我希望自己投胎成一只小麻雀,在你屋檐下筑巢,经常能看到你就好!”
自从郭书记给了多吉那个表之后,次多一直就没回溜村家里。多吉今天又看到放在小卖部桌角的表就给次多打了电话:“村里郭书记发了一张表让你填,说是会在村里安排暂时的一个工作岗位。”
“我还是想继续在拉萨市里打工,不填了。”
“村委会那么关心,怎么好拒绝呢?”
“我想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不过您放心,公务员我会继续考。”
“什么兴趣,跟饭碗比起来兴趣算个屁!”
“跟您说了也不懂。”次多正准备挂电话。
“哼,乞丐棍棒也有头尾,怎么跟你爸啦说话的!”
“对不起爸啦,我刚才说话不礼貌的地方您原谅。但,也请您尊重我的选择。”
“什么尊重,说了等于白说吗!跟畜生一样。”
“正因为我不是畜生,所以,我不会听您的话。”
“什么?”
“您一直以来,干什么都是跟着别人屁股后头,没有自己的主见。”
“我小心翼翼辛辛苦苦,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
“我知道您为了这个家很辛苦,但没有自己的主见,就会付出代价,家门口的‘铁牛就是例子。”
家门口的“铁牛”是他心头的刺。本来就在家里没有地位的他,因为“铁牛”更是常常被老婆数落。现在儿子也这么说他,他把电话挂断,从货架上拿起一瓶白酒灌了下去。
冬日午后,格桑正坐在大女儿梅朵家中二楼客厅的卡垫上,倚着靠背捻着佛珠,翕动着嘴巴诵着经。渐渐地,她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
她走在山路上,眼前有一处山崖,崖壁上建有一座小小的寺庙。
通往这座寺庙的山路上,有一个挪动的红点,它缓缓向前移动着。她继续靠近,那点红变成了一位背着水桶的尼姑。她兴奋地喘着粗气追那位尼姑的背影,这时尼姑转身一笑,她惊喜地喊道:“卓玛!”
“我现在不是卓玛,我的法名叫阿旺曲珍。”
她扑上去拥抱卓玛,结果卓玛不见了,消失了。
弯弯的山路上只有她一个人。
她继续往上,来到寺院门口。
她看到了卓玛的师傅。
师傅正站在寺院大门一侧的壁画前,旁边围着好多信徒。
她缓缓走过去,听到师傅指着《轮回图》中央绘的一头黑猪、一只小红鸽子和一条绿蛇,说:“它们互相咬着尾巴,象征着痴、贪、嗔三毒,人的痛苦都来自这三毒。”
听到这里,她正想问,怎么祛这三毒,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当她移开双手睁开眼睛时,寺庙也消失了。
风止了。
她发现她回到了酷久村。家门口的地里盛开着油菜花,她俯下身子去触摸,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嫫啦!”
她看到她的孙子次多挥动着双手向她奔来,她揉了揉眼睛,再看,他已经来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回来了!”
编辑导语:小说写拉萨郊区的农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历程,其间既有文化的冲突、观念的较劲、思想的固守与开放,富有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也是直面现实生活,对当下西藏变化的真实反映。小说的结构上作者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读起来给人新颖又活泼的印象。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