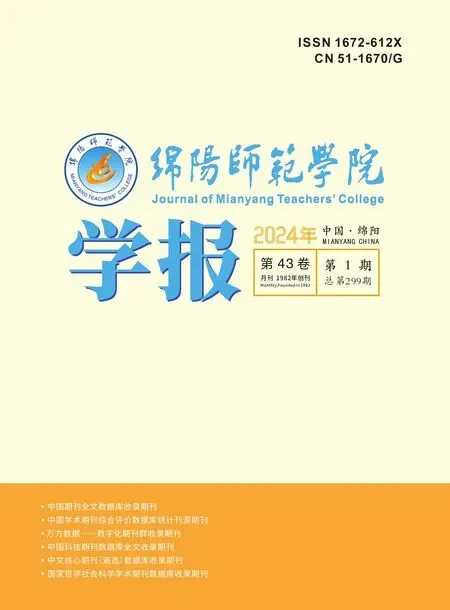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题篇数定自何人之探讨
杨栩生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关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题和篇数的确定出自何人何时,参与讨论者颇多,大抵持两类见解:其一,认为是后人(包括李阳冰)编集时的命题。《唐宋诗醇》评李白《古风》其一云:“阳冰纂《草堂集》,以《古风》列于卷首,又以此弁之,可谓有卓见者。”[1]265赵翼《瓯北诗话》云:“《古风五十九首》非一时之作,年代先后亦无伦次,盖后人取其无题者,汇为一卷耳。”[1]264詹锳①、郁贤皓②等先生从其说。其二,认为是李白自己命题、选择、编排,后世逐步增扩成五十九首。此一识见,先后出自乔象钟③、贾晋华④、周勋初⑤、阎琦⑥、薛天纬⑦等诸家。
诸家之论,虽然对揭开《古风五十九首》诗题和篇数确定的真相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似亦言犹未尽。
李白文集命名为《草堂集》。“草堂”“草庐”这类言词,大抵皆居者对自己居所的称说,多为谦言其居室之简陋,或者以此自标风操之高雅,如“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孔稚珪《北山移文》)、“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诸葛亮《出师表》)。即使是以“草堂”命名诗文集,也是编撰者自命,谦言其出自陋室,如《草堂诗话》(南宋蔡梦弼撰)、《草堂诗余》(一说为无名氏编,一说为南宋何士信编,一说为杨万里编)。如果称他人之居处为“草堂”“草庐”,命他人之文集为“草堂”集,应是很不得体也是很不尊重他人的做法。以“杰出圣代英”“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贤彦多逢迎”(李白《献从叔当塗宰阳冰》),而且“善词章”“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阳冰独步”[1]1867的李阳冰,学识修养如此之高,定不会将李白文集命名为《草堂集》。
李白曾前后三次将自己的诗文托付他人为其编集。第一次是天宝十三年(754),李白的狂热追求者魏万(后更名颢)“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得见李白于扬州,偕游金陵,临别之时,李白赠诗并“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颢《李翰林集序》)。第二次是肃宗乾元二年(758),李白长流夜郎赦还至江夏时遇倩公(按,即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有乡僧倩,雅仗才气,请予为铭”之贞倩),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第三次是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因病由金陵往依当塗李阳冰,“又疾殛”,临终之前“枕上授简”,将“草稿万卷”托付李阳冰“俾予为序”(李阳冰《草堂集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是“尽出其文,命颢为集”;第二次是“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第三次是“草稿万卷……俾予为序”,“草稿万卷”之“万卷”,虽然是夸饰之词,但却表明也是“尽出其文”“平生述作”。很显然,前两次托付,其文稿都是留有复本的。这个复本的缮写,不管是请人代劳还是李白自为,都说明李白对自己的文稿会有所整理,其中对自己文集的命名定会有所斟酌。尤其是第三次向李阳冰托付,是“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这告诉我们,虽然是“草稿”,却已成“万卷”“手集”(手抄之集),可见文稿已经李白自己作过整理、编排,只是尚未修订(“未修”),嘱托李阳冰为之作序——话里或有请其刊印的意思。
如此看来,《草堂集》应是李白自己编成并命名。
为什么以“草堂”名集?李白的家乡蜀地虽然有草堂寺——孔稚珪《北山移文》李善注谓“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2]612,据清人仇兆鳌所说,杜甫在蜀锦城之“草堂”正是“近草堂寺,因以命名耳”[3]743。但李白并无如杜甫有“近草堂寺”的居所,其经历也与草堂寺无涉,当然不会以“草堂”名其集,他人则更不会也不能用“草堂”为其名集。其所以名之为《草堂集》,或者如阎琦先生所言,“一是表明自己暂时栖居于此(当涂),二是感激李阳冰在自己走投无路之际安置自己于‘草堂’,有‘风雨茅庐’之义”[4];或者,也还有自己一生的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却“兼济”(仕)不成“独善”(隐)不就,但从出峡之初的“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望庐山五老峰》),到中年的“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再到暮年的“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李白《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李白《避地司空原言怀》),隐士情怀愈老弥剧,因而将自己的文集以“草堂”命名,以标其风操;或者,还有自己漂泊一生,穷困潦倒,居无定所且简陋有如“草堂”生活真实的苦辛。当然,以“草堂”命名其文集,究竟包含了李白怎样的情感只有李白自己最清楚,这里不过是想要说明《草堂集》之命名是出自李白自己,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出自他人。
既然《草堂集》之命名是出自李白自己,而李白在将“草稿万卷”托付李阳冰俾其作序之前对文稿又经过一番整理、编排,则组诗《古风》诗题的拟定也应该是李白自己。
所谓“古风”,正如朱谏《李诗选注》之论,“古风者,效古风人之体而为之辞也”,“美刺褒贬,感发惩创,得古风人之意”,“所言者世道之治乱,文辞之纯驳,……讽刺当乎理,而可规戒者,得风人之体”[5]221。这就是说,李白的这组《古风》,是继承汉魏五言古诗体制,以古朴的语言和“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比兴寄托,保留并发扬着风骚汉魏传统风格和精神,讽谕针砭、感发规戒而指言时事、世道。虽然《古风》中还有不少“感伤己遭”和“抒写抱负”的篇章,但这些篇章,却多是以自身的不遇于时、抱负难成抒写世道不平的愤慨。所以,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说的那样,“‘世道之治乱’是《古风》组诗的总纲……所谓‘世道之治乱’,是指三代以下,春秋战国以来的治乱之情,兼及李白当代的政道舆情,侧重于刺乱。这是《古风》五十九首的基本主题”[6]。因此可以说,《古风》组诗,形式、风格、内容,无论哪方面,都体现了李白自己自觉的拟古、复古和指言时事世道创作的自觉意识。如果《古风》之命题是出自他人之手,则体现不了或削减了李白主观上拟古、复古和创作的自觉性。换言之,是诗歌的客观体现,而非李白的主观意识的自觉性。
《古风》“五十九首”之数,并非出自后人之手,也不是历代增扩所成,而是李白自己所编定。
首先说“五十九”首之数是一个传统的传承定数。
《古风》这组诗,在流传过程中,其篇数多有出入。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谓“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7]242,宋咸淳本为六十一首。詹锳先生在《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集说》中还记录了《道山清话》所载的一条传闻:“秦少游一日写李太白古风三十四首于所居一隐壁间。”[8]15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3《诗话前集》说太白《古风》“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7]574,而在卷174《诗话后集》中说法又有不同:“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李白《古风》六十六首,真可以扫齐梁之弊而追还黄初建安矣。”[7]576明人胡震亨《李诗通》说“《古风》六十篇中,言仙者十有二……虽言游仙,未尝不与讥求仙者合也”[5]440。陆时雍《诗镜总论》则说太白《古风》“八十二首,发源于汉魏,而托体于阮公”[5]465云云。虽然李白《古风》篇数在流传中有这样的出入(后村前言六十八首,后言六十六首,何以有差,不得而知),但宋蜀本、萧注本、王注本都是五十九首。王琦在《李太白集辑注序》中说:“余所见杨子见、萧粹斋、胡孝辕三家……爰合三家之注订之,芟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第思粹斋之作补注,所以补子见之阙也,而未能尽补其阙。孝辕作《李诗通》,力正杨、萧之讹,而亦未能尽正其讹。余承三子之后,捃摭其残膏剩馥,广为综辑。”[9]1685又在其《跋》中说李诗全集之有注自杨齐贤始,后萧氏士赟作《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而注合刊[9]1688。萧士赟《补注李太白集序例》之谓“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择其善者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10]4564,其“左绵刊本”正是宋蜀本。这就是说,《古风》“五十九”首之数,从宋蜀本、杨注本、萧注本、王注本是一个传统的传承定数。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宋本‘宝剑双蛟龙’‘咸阳二三月’编入二十二卷,题作《感寓二首》,‘昔我游齐都’‘泣与亲友别’‘在世复几时’分为三首;萧本、郭本、王本则将此三首合为一首,《感寓二首》插入《古风》,凑成五十九首”[11]2。不管是一首分为三首,或者是三首合为一首,都要成就“五十九首”,可见“五十九”之数是不能突破、不能变更的。
为什么不能突破、不能变更?因为“五十九”之数是李白自己所定。
如前所言,从宋蜀本到杨、萧注本到王琦注本,“五十九”首之数是一个传统的传承定数,而“宋蜀本所根据的晏处善刻本是经过宋敏求从各种传抄本收集而刻成的”[10]4567。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载:“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合为三十卷。”[9]1477
于是,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古风》“五十九”首的这样一个传承线索:《草堂集》—乐史《李翰林集》—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宋蜀本—杨、萧注本—王琦注本。《草堂集》为李白自己所命,其“草稿万卷”在托付李阳冰前是经过他自己的一番整理、编排的,《古风》题目的拟定也是出自他自己,而“五十九”首之数又是自《草堂集》以来的传统的传承定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五十九”的篇数正是他自己所定。
再说为什么要定“五十九”这个数。
要确凿地认定“五十九”之数是李白自己所定,还得追寻为什么是“五十九”这个数,而不是任何其它的数。
《黄帝内经·灵枢·热病》载有“五十九刺”针灸疗病之方,其文云: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内、外各二,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二痏;耳前后、口下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聪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12]
又,《黄帝内经·素问·水热穴论》同样载有“五十九俞”(按,“俞”通“腧”,人体穴位)针灸疗病之方: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歧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泻五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皆热之左右也。”[12]
清人永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黄帝素问》二十四卷”条云:“唐王冰注。晁氏《读书志》作王砯,盖欲附会杜甫诗而改之。原本残阙,冰採阴阳大论以补之。”[13]378又,“《灵枢经》十二卷”条云:“是书论针灸之道,与《素问》通号《内经》,然至南宋史崧,始传于世。”[13]378虽然至南宋始传于世,但在晋人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中已有其内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甲乙经》八卷”条云:“晋皇甫谧撰。据其自序,盖合《针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撮其精要,以成是经。言针灸之法最悉。或曰王冰所撰《灵枢经》即割裂此书之文,伪为古书也。”[13]379这就是说,《灵枢经》是《针灸甲乙经》中的一部分。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百家”当然包括医家),就算读不到《灵枢经》,但能读到《黄帝内经·素问》和《针灸甲乙经》(按,其书多处提到治伤寒热病以“五十九刺”)是肯定的。李白《古风》定篇“五十九”之数的暗寓性由此而来,昭示其要以疗治人体病疾之“五十九刺”“五十九俞”的针刺疗法,针砭时弊、刺乱救世。其命意之深,创作的自觉意识之强,舍李白其谁!
注释:
①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载《李白古风五十九首集说》:“……意者,太白古风本是咏怀或感寓诗,其易为今题乃出于后人之手。” 《李太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意者太白古风本是咏怀、感遇或感遇诗,其易为今题或出于后人之手,未可知也。”
② 郁贤皓《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国李白研究》1990 年集上):“考《才调集》卷六录李白‘泣与亲友别’‘秋露白如玉’‘燕赵有秀色’三首,已题名《古风》……可能是李阳冰在编集时把有关咏怀内容的短篇五言古诗集中在一起,题名为《古风若干首》。” 《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 年版):“此五十九首诗中,李白原来有取名为《咏怀》《感遇》之类题目,也有《古风》的题目,在流传过程中有些题目失落,至李阳冰编集时,将这些诗集合在一起,题名为《古风若干首》,至宋人乐史、宋敏求编集,增成《五十九首》。”
③ 乔象钟《李白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载《李白〈古风〉考析》:《古风五十九首》的编排“并非出自曾巩,也不是出自李阳冰”,“《古风》是李白晚年自己选择、组合的大型组诗”。
④ 贾晋华《李白〈古风〉新论》(《中国李白研究》1991 年集):“这一组诗的最后命题,可能是李白有意识、总结性的构思。”
⑤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绝大多数诗应当原来就题为‘古风’,李阳冰不可能为了添一新类而将原诗题目大批去掉,一一改为《古风》。”
⑥ 阎琦《关于李白〈草堂集〉的编辑及其“古风”命名的断想》(《中国李白研究》2013 年集):“宝应元年第三次将文稿交付李阳冰,则仅仅是‘俾予为序’(李阳冰《序》)。既托付阳冰为序,则李白对自己的文稿先须有一番整理,不可能因自己病体缠绵将一沓无头绪的文稿交给李阳冰”,“59 首诗,多数无具体的人、事和时间,诗句之得,在题目之先;诗篇既已完成,题目仍然暂阙,有待后再补之意……久而久之,似此之类无题之五古渐积渐多,用何题目来处理这一大组五古……。《感兴》或《感遇》是安顿59 无题五古较为合适的题目……然而李白皆弃而不用,自创‘古风’二字,是有他的深意的”。
⑦ 薛天纬《关于〈古风五十九首〉研究的三个问题》(《中国李白研究》2013年集)认为,《古风》最初的命题和编集当是李白自为之,但李白当时未必就编好了“五十九首”,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增以及个别篇章有些出入变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