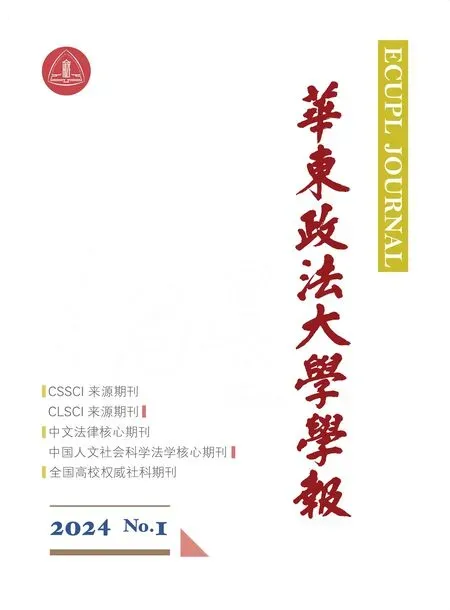被误解和误用的家事代理
——《民法典》家事代理规范体系基点再阐释
刘征峰
目 次
一、家事代理与夫妻共同债务的体系关联
二、家事代理、代理与默示同意处分
三、信赖保护问题
四、结论
遍阅民法,很难找到像家事代理这样奇特的规范构造,它突破了意思自治原则,将法律行为的效力当然及于第三人,将其称为民法上的怪胎亦不为过。《民法典》第1060 条明确规定了家事代理权及其限制规则。〔1〕本文所称家事代理仅指夫妻间的家事代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亦有承认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家事代理。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 民终3480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申136 号民事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申4736 号民事裁定书。在《民法典》颁布之前,一般将《婚姻法》第17 条第2 款以及对此进行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 条作为我国肯认家事代理权的规范基础。〔2〕参见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第2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97 页;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房绍坤等编著:《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但这两条规范均只涉及共同财产处分领域的家事代理权问题,并未扩展至其他领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家事代理权概念的使用已经远超共同财产处理范畴。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将家事代理权作为第二种类型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基础。〔3〕参见罗书臻:《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载《人民法院报》2018 年1 月18 日,第3 版。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开始,立法者就采纳了主流意见,增设了家事代理规范。按照立法工作者的解读,该规范之目的在于“方便经济交往和婚姻家庭生活,保护夫妻双方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交易安全”。〔4〕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985 页。然而,这些规范目的之间究竟应为何种关系,在规范解释和漏洞填补中又应如何具体融入这些规范目标殊值研究。我国现有文献对于家事代理权的研究呈现出同质化倾向。相关研究或集中于对家事代理权的历史演变、性质、要件及效果进行文献综述式介绍,或在讨论夫妻债务问题时附带讨论家事代理权,未能从司法实践出发把握其中最为重要的规范协调问题。本文试图从体系角度出发,澄清司法实践对家事代理权的误用,通过归纳实践中的案型,将家事代理权规范与其他相关规范进行合理的区隔,厘清我国法中家事代理权规范的体系位置。
一、家事代理与夫妻共同债务的体系关联
(一)家事代理的功能澄清:扶养义务外化
在法制史上,家事代理制度出于给予妻子操持家务便利的考虑。〔5〕Vgl.Stephan Meder, Familienrecht: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2013, S.93 f..现代家庭法奉行男女平等原则,家事代理权并非为妻子独有。比较法上,仍有相当立法例维持家事代理规定,这主要还是基于家庭团结的考虑。家庭团结是通过强化家庭共同生活义务来实现的。而家庭共同生活义务可以分解为家庭成员之间在扶养法上的义务。家事代理从本质来说是家庭扶养义务的外化。〔6〕参见刘征峰:《夫妻债务规范的层次互动体系——以连带债务方案为中心》,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92 页。
家事代理权涉及积极的家庭扶养。易言之,通过家事代理权这一规范机制,夫妻另外一方参与到了家庭扶养中。在债务负担层面,通过将扶养义务外化,让负有扶养义务的一方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至少简化了法律关系。夫妻一方无须对外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后,再向另外一方主张扶养费。这种外化为负责家务的夫妻一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自由,〔7〕Vgl.Christine Budzikiewicz, in: Jauernig Kommentar BGB, 19.Aufl.2023, § 1357 Rn.1.其在实施有关家庭日常生活的行为时无须征得另外一方的同意。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 条的规定,扶养费给付请求权属于《民法典》第535 条第1 款但书所称“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其行使与否完全基于权利人本人的身份地位”,〔8〕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2 页。不能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如果不存在外化规则,外部的债权人无法向受益的夫妻另外一方主张权利,明显不公。在权利归属层面,另外一方直接取得连带债权人地位是其扶养权利人地位外化的结果,他可以直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夫妻间的实际扶养需求在确定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时具有决定性。〔9〕Vgl.Reinhard Voppel, in: Staudinger BGB, 17.Aufl.2018, § 1357 Rn.18.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扶养不局限于《民法典》第1060 条所规定的夫妻间扶养,还包括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祖、孙之间的抚养和赡养;兄姐与弟妹之间的扶养。此外,夫妻之间扶养义务亦决定了夫妻双方依据家事代理权承担连带责任后内部的追偿。〔10〕Vgl.Andreas Roth,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9.Aufl.2022, § 1357 Rn.40.
将家事代理权理解为扶养义务的外化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夫妻双方不能通过协议排除扶养义务,但是可以通过协议排除家事代理权。实际上,无论夫妻一方依据《民法典》第1060 条第1 款与相对人约定限制或者排除家事代理权,还是夫妻之间依据《民法典》第1060 条第2 款限制或者排除家事代理权,均不影响夫妻双方的扶养义务本身,只是限制或者排除扶养义务的外化。如家事代理权被完全排除,非行为方在其受扶养权不能实现时,只能根据《民法典》第535 条第1 款向行为方的相对人主张权利,而不能直接取得连带债权人地位。如上所述,由于扶养权本身不能被代位,此时相对人无权向非行为方主张权利。
作为扶养义务外化的结果,家事代理权属于婚姻的法定效果。在性质上,有观点将其定性为夫妻人身关系的组成部分,〔11〕参见房绍坤等编著:《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第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64 页;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4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83 页。亦有观点将其定性为夫妻财产关系的组成部分。〔12〕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245 页。从家事代理权规范的适用范围来看,所谓日常家庭生活并不包括身份的相关内容,《民法典》第1060 条所称民事法律行为指向财产法上的行为。夫妻一方不能通过家事代理权代另外一方行使涉及身份性质的法律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家事代理权虽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但是其在性质上为夫妻财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夫妻财产关系不等于夫妻财产制,前者包含后者。由于扶养义务并非夫妻财产制的组成部分,作为扶养义务外化结果的家事代理亦非夫妻财产制的组成部分。即使夫妻双方根据《民法典》第1065 条的规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家事代理权仍然存在。
(二)作为体系关联基础的连带债务
《民法典》第1064 条吸收了《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规定,将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认为,这一债务类型认定背后的法理依据系家事代理权。〔13〕参见缪宇:《走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误区——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 条为分析对象》,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1 期,第262 页;汪洋:《夫妻债务的基本类型、责任基础与责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夫妻债务解释〉实体法评析》,载《当代法学》2019年第3 期,第52 页;冉克平:《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 号》,载《法学》2018 年第6 期,第71 页。相较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 条,《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明显进步在于,不再将家事代理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统一的法理依据,而是从其产生原因区分了不同的形态。不同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依据并不相同。
从《民法典》第1065 条第3 款的规定来看,如果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且相对人知道该约定,则夫或者妻应以其个人财产清偿。值得讨论的是,是否能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同时排除了所有类型夫妻共同债务的适用。在此,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一种解释路径是将《民法典》第1064 条所规定的所有共同债务类型均作为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构成内容。如果夫妻双方通过约定排除了法定财产制的适用,则该条规定并无适用空间。另外一种解释路径是将《民法典》第1064 条所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类型根据其法理类型进行划分,约定分别财产制只能排除与共同财产制相关的夫妻共同债务类型,而无法排除与其无关的类型。前一种解释方案在体系上似乎具有形式合理性。《民法典》第1062 条和第1063 条是对婚后所得共同制积极财产部分的规定,而《民法典》第1064 条是对婚后所得共同制消极财产部分的规定。紧随其后,《民法典》第1065 条涉及约定财产制,第1066 条涉及对婚内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过这种形式上的体系解释,忽略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特殊性。无论夫妻双方是否采纳法定的所得共同制,都应当共同承担家庭日常生活费用,由此形成的债务亦属于连带债务。
在比较法上,此项观点可由诸多立法例予以印证。以《法国民法典》为例,第220 条规定了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所缔结的合同对另外一方的连带拘束力。易言之,夫妻双方应当对由此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4〕参见[法]科琳·雷诺-布拉尹思吉:《法国家庭法精要》(第17 版),石雷译,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65 页。该法典第226 条规定,夫妻间相互权利义务的约定,除非有特殊规定可以适用夫妻财产制契约,否则无论实行何种夫妻财产制,均应作为婚姻的效力予以适用。与此相对,该法典在夫妻共同财产制部分对因家庭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债务亦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法典第1409 条的规定,依据第220 条所形成的债务属于共同财产的债务。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家庭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负债在性质上属于连带债务,其责任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共同财产。
在我国,并不存在共同财产的债务这样的概念,从《民法典》第1064 条、第1089 条的表述来看,立法者没有根据共同债务的类型区分其责任财产范围,共同债务亦未作为一种多数人之债的形态在合同编中规定。学界呼吁较为强烈的“有限责任论”在立法文本上未得到体现,司法解释所反映的共同债务即连带债务的规则仍应继续适用。参照法国法的前述立法逻辑,《民法典》第1064 条规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过是为了自身规定的周延性即婚后所得共同制中的共同债务当然包括家事代理所形成的连带债务。当然,《民法典》第1064 条本身的周延性是存疑的。在我国,夫妻双方结婚后,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称谓。《民法典》第1064 条第1 款只规定了共同意思表示形成连带债务这种典型情形,并未规定其他类型的连带债务。事实上,只有除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外的其他共益型债务才与婚后所得共同制密切相关。由此,如果夫妻双方通过夫妻财产约定排除婚后所得共同制,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其他类型的连带债务承担,包括通过家事代理权所形成的连带债务。需要注意的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形成的连带债务不局限于以个人名义,亦包括双方以共同名义这种形态。〔15〕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et al., “Principles of European Family Law Regarding Property Relations between Spouses”,Intersentia, 251(2013).当然,如果夫妻双方与相对方明确约定债务为按份债务,则应从其约定,不应将其视为连带债务。
能否将夫妻双方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约定视为《民法典》第1060 条第2 款所规定的双方对一方可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限制的约定呢?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1065 条第3 款所称“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应当包括为家庭日常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16〕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010 页。依此观点,排除法定财产制即排除了家事代理权。这种观点混淆了法定财产制与夫妻连带债务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实际上只排除了与婚后所得共同制相关的那一部分债务。在分别财产制下,双方仍应就一方依据家事代理权所实施的法律行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家事代理权系婚姻的重要法律效果,双方对其进行限制应以明示方式进行,不能从夫妻财产制约定行为中进行推定。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如果夫妻双方并未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只是约定排除一方的家事代理权,被排除家事代理权的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担的债务能否认定为共同债务呢?如承认此种情形下形成的债务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会导致《民法典》第1060 条第2 款的规定成为具文。此时,实施法律行为的一方承担责任后,可根据《民法典》第1059 条的规定要求另外一方给付相应的扶养费。不难发现,夫妻双方对家事代理权的限制之重要功能在于避免扶养义务外化。
(三)连带债务之外:家事代理的其他法律效果
在形成连带债务之外,家事代理亦会产生其他法律效果。而夫妻共同债务规范处理债务本身的问题,如共同债务性质的认定、责任财产范围、清偿顺序及内部追偿问题。《民法典》第1060 条所称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亦应包括权利归属效力。无疑问的是,家事代理规范所产生的债法上的效力不仅局限于连带债务,亦会形成《民法典》第518 条意义上的连带债权。据此,在对外关系上应适用《民法典》第521 条的规定。有疑问的是,家事代理之效果是否应扩展至物及其他财产的归属。在德国,行为方的配偶能否直接依据家事代理规范取得物权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非行为方并不能根据家事代理规范取得所有权。〔17〕Vgl.BGHZ 114, 74 (76 f.).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承认家事代理规范也适用于处分行为,除非处分人有相反的表示,夫妻双方形成共同共有,只承认债权效力实际上是将家事代理规范降格为纯粹的债权人保护规范。〔18〕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3 页。确定家事代理在权利归属上的效果时,不仅应当考虑财产变动的一般性规则,〔19〕Vgl.Andreas Roth,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9.Aufl.2022, § 1357 Rn.42.还应考虑夫妻双方所实行的财产制。
在德国,有观点认为,承认家事代理的物权变动效力将会对夫妻财产制的规范体系造成破坏。〔20〕Vgl.Joachim Gernhuber/Dagmar Coester-Waltjen, Familienrecht, 7.Aufl.2020, S.167.在我国语境下,是否存在这种体系破坏效应须结合我国所采纳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构造来具体分析。就法定财产制而言,与德国所采增益共同制下夫妻双方财产分别所有的思路不同,我国所采婚后所得共同制之根本系财产之共有。但是这种共有之判断,应处于财产法规则判断之后。如夫妻双方已经根据财产法规则形成了共同共有,无须再适用家庭法上的规则。故而需要同时考虑承认权利归属效果是否会对财产法规则以及法定夫妻财产制产生冲击。就最典型的物权而言,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变动除债权行为外,原则上仍需交付或者登记,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其他财产的取得多需满足一定的形式要件。而在婚后所得共同制下,财产的共有及准共有是经历“逻辑上的一秒”之结果,〔21〕参见贺剑:《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财产制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6 期,第1506 页。财产法上的权利归属状态进行了自动转换,无须满足相应的形式要件。如果承认家事代理的财产变动效力,则面临其与婚后所得共同制的适用顺序问题。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而实施法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2 条和第1063 条的规定,既可能是共同财产,也可能是个人财产。这一问题在我国更具现实性,因为目前通说并未严格将家事代理局限于家务,而是扩展至家庭日常生活中。据此,夫妻一方购买诸如个人生活用品的行为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由此取得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3 条第4 款在性质上属于个人财产。如果婚后所得共同制下财产性质划分规则是最终规则,家事代理层面的权利归属毫无实益可言,只会人为增加教义上的复杂性。
更特殊的一种情况是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在此种财产制下,家事代理仍有适用的空间。由于并不存在财产性质的自动转换,家事代理在财产归属上的意义凸显。此时,需要权衡承认家事代理权财产归属效力的利弊。就外部关系而言,即使第三人已经知道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由于权利变动欠缺形式要件,亦可能对其产生不利。由此形成第二个“逻辑上的一秒”,进一步破坏现有的财产变动体系,妨碍交易安全。就夫妻内部关系而言,虽然在分别财产制下,双方仍可能未排除家事代理,但相比于债法上的效果,财产共有或者准共有明显与双方分别所有的意愿背道而驰。不能因为家事代理的适用范围有限,就否定这种背离。〔22〕相反观点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3 页。此外,虽然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与家事代理密切相关,但据此确定家事代理财产归属效果同样存在问题,会在不同情形下分别形成对料理家务的一方或者外出工作一方的不公平。〔23〕Vgl.Andreas Roth,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9.Aufl.2022, § 1357 Rn.43.基于以上理由,不应承认家事代理的财产归属效果。
在财产归属之外,家事代理之效果是否及于形成权存在一定的争议。在此,主要涉及两项问题:“配偶双方中的一方行使权利是否已经足够了以及之后的法律后果是否对配偶双方都产生效力”。〔24〕[德]玛丽娜·韦伦霍菲尔:《德国家庭法》(第6 版),雷巍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68 页。后一问题以前一问题为基础。对前一问题回答的关键在于,是否将非行为方视为合同的当事人。对前一问题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非行为方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其只不过是依据法律的规定向相对人清偿债务并主张行为方所享有的权利,非行为方只具有类似于保证人在债务人享有撤销权而不行使时的地位,此时因行为方享有形成权,法律行为实际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25〕Marie Berger, Gestaltungsrechte und Prozessführung bei Schlüsselgewaltgeschäften nach § 1357 BGB, FamRZ 2005,S.1129 あ.根据《民法典》第702 条的规定,保证人在此时可以拒绝履行保证责任。排除非行为方的当事人地位实际上并不合理,将其置于合同当事人地位并未对交易相对人造成不利。非行为方行使的形成权本身就是行为方原本享有的形成权。然而,在内部关系上,承认非行为方可以行使形成权带来这样的问题,其可能通过行使形成权来完全否定另外一方的家事代理权,导致家事代理规范被架空。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情形是,其能否主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 条所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货。一种妥当的解释路径是将形成权行使之效力局限于本人,而非扩展至另外一方,这样可以避免行为方承担因其配偶成为合同当事人行使形成权带来的风险。〔26〕Vgl.Marie Herberger, Von der, Schlüsselgewalt zur reziproken Solidarhaftung: Zugleich ein Beitrag zum Rechtsprinzip dernachwirkenden ehelichen Solidarität, 2019, S.38.
归纳起来,即使是在家事代理与夫妻共同债务重叠适用的家庭日常生活领域,家事代理之效果也并非局限于债务之连带,还包括债权之连带以及形成权之行使等其他效果。
二、家事代理、代理与默示同意处分
(一)名不符实的家事代理
家事代理虽然冠以“代理”称谓,但其并不是直接代理或者间接代理。无论是从构成要件还是从法律效果上来看,家事代理与二者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有观点认为家事代理系法定代理。〔27〕参见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三民书局2011 年版,第149 页。此种立场只注意到了家事代理权系基于身份产生,〔28〕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5 页。不需要进行个别授权,但存在逻辑倒置之嫌。家事代理与直接代理中的法定代理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要件上来看,法定代理同样需要满足显名规则,即法定代理人需要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行为,否则无法确定行为归属。有观点将家事代理视为法定代理之重要理由在于法定代理不一定需要满足显名原则,〔29〕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0 页。此种理解明显与《民法典》第162 条(《民法通则》第62 条)的规定矛盾。
在家事代理中,从《民法典》第1060 条的规定来看,并不要求夫妻一方在实施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行为时以夫妻另外一方或者以家庭的名义。这与《民法典》第970 条规定的合伙事务执行存在明显的区分。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时,需要公开合伙名义。无论是代理还是合伙,之所以需要公开名义,是因为“第三人应受到保护,他应当知道谁是其行为相对方”。〔30〕[德]汉斯·布洛克斯、[德]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41 版),张艳译,杨大可校,冯楚奇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34 页。除了最为典型的公开被代理人名义情形外,尚存其他例外类型。对例外类型的判断亦需从第三人是否存在可值得保护的利益出发。〔31〕参见朱虎:《代理公开的例外类型和效果》,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100 页。而在家事代理中,夫妻一方并不需要公开家事代理的事实,也不需要公开其配偶,甚至不需要公开其是否结婚。如后文所述,家事代理权规范在总体上为第三人带来了事实上的利益。尤其是在第三人是债权人的情形,他不仅可以要求直接与其交易的夫妻一方清偿债务,而且可以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妻另外一方清偿债务。与代理行为相对人不同,家事代理行为的相对人此时并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利益。他所期待的债务人并没有因家事代理而受到影响。〔32〕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680 页。如果相对人系债务人,因家事代理之效果而增加了其履行费用,可归为债权人原因导致的履行费用增加,应由夫妻双方作为连带债权人共同承担履行费用。他的利益并没有因不公开而受到影响。职是之故,家事代理又被称为“加演节目”。〔3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680 页。第三人在与自然人发生交易时,该行为是否属于家事代理范畴通常并不构成双方的交易基础。这些交易通常建立在抽象人的假设之上,即使将其扩展至特定的身份,如消费者、劳动者,也并不能够涵盖自然人在家庭法上的地位。并且,如果将自然人在家庭法上的地位纳入第三人的合理预期范畴,则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并导致交易事实上无法进行。
此外,自然人在家庭法上的状态通常并不属于交易所应披露的范畴,即信息义务的范畴。值得讨论的是,如果家庭法会影响自然人的履约能力,尤其是会一般性地影响其责任财产,此时是否应当进行披露呢?这种情况主要是指夫妻法定财产制所形成的财产共有对自然人的责任财产形成的影响。在自然人未结婚的情况下,自然人的所有财产都属于责任财产;在自然人结婚的情况下,其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责任财产可能相应地减少或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人同样没有披露义务。家庭法已经通过相应的规则,比如适度扩张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来调整这种利益失衡,而不是通过强制婚姻信息披露来分配这种风险。第三人在与自然人交易时应当预见到对方可能已婚,也可能未婚。《民法典》第1065 条第3 款虽然规定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时,交易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但并不能从该款规定中解释出自然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具有强制信息披露义务。该款规定的真正意义在于明确约定财产制对外发生效力的条件。在家事代理情形中,由于其与夫妻双方选择适用何种财产制无关,举重以明轻,行为人自然更无此项信息义务。
同样,在家事代理场合,行为人的代理意思,准确来说是涉他意思,并不是家事代理发生效力的要件。而在代理中,对于代理意思是否是代理的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通常而言,代理公开包含了代理人的涉他行为意思。由于家事代理本身并不需要满足公开要件,行为人的涉他意思在此并不重要。行为人不能以不存在涉他意思为由否认行为对其配偶的效力。
从法律效果来看,家事代理与直接代理存在明显的差别,《民法典》第1060 条所称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系指法律效果归属于夫妻双方,在夫妻双方之间形成连带关系。对于直接代理而言,根据《民法典》第162 条的规定,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二者确实存在这样的相似性,即一人行为的效果归属于他人,但二者归属的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直接代理中,代理人并不是法律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在家事代理中,行为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从《民法典》对直接代理法律效果的规定中不难看出,家事代理并不属于直接代理的范畴。
综上,家事代理与直接代理虽然均属于涉他性法律构造,但二者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存在上述明显的差异,家事代理只能被认定为代理之外的特殊法律构造。因此,《民法典》关于代理之规定不能适用于家事代理。
(二)代理、默示同意处分与家事代理的识别
1.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内家事代理的识别
由于代理和家事代理存在上述法律效果上的巨大差异,在确定夫妻一方所实施的行为效力时,有必要先对其性质进行识别。在日常家庭生活范畴内,需要明确代理是否仍然有适用的空间。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家事代理权理解为法定代理权还是特殊类型(sui generis)的权力。如前所述,家事代理无法在既有的代理规范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宜采后一种观点。既然其是特殊类型的权力,自然不能因家事代理权的存在而当然排除代理的适用。因此,重点在于根据情形进行区分。
在日常家庭生活范畴内,代理发生效果的要件要多于家事代理。如果未满足代理的要件,自然不存在代理的适用空间。在夫妻一方的行为同时满足代理和家事代理要件的情况下,需要明确究竟应发生何种效力。在夫妻一方直接以另外一方的名义行为时,这一问题更为凸显。如前所述,家事代理的要件中并不包含类似于代理的公开性要件,一般认为行为人以自己名义、配偶名义或者双方名义,乃至于家庭名义均无不可。实践中行为人常不表示名义或者以自己名义。有法院认为,以本人名义或者配偶名义不影响家事代理效果的发生,即使行为人明确以其配偶的名义行为,也应当认定为家事代理。〔34〕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9 民初81 号民事判决书。这种理解实际上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在家庭日常生活范畴,家事代理绝对排斥代理的适用。易言之,家事代理不能因此被排除。根据《民法典》第1060 条的规定,家事代理可在两种意义上被排除,即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以及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存在排除的约定。在夫妻一方明确以另外一方名义行为时,不能从中当然解释出其具有排除家事代理的效果。
夫妻一方以另外一方的名义行为又可以细分为夫妻一方披露被代理人为其配偶和夫妻一方未披露被代理人为其配偶两种情况。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既然夫妻一方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已经披露被代理人为其配偶,第三人此时仍愿与其实施法律行为,可以将其解释为行为方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了《民法典》第1060 条第1 款所称的“另有约定”。据此,此处所谓“另有约定”既包括双方约定该行为仅对自己发生效力,亦包括该行为仅对其配偶发生效力。有意见认为,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即使存在夫妻另外一方授权并以其名义行为也不能排除家事代理规则,行为方应当明确表明限制家事代理权的意思。〔35〕Vgl.NJW 1985, 1395.这一要求明显过于严苛,在行为方已经披露被代理人为其配偶时,其排除家事代理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不应据此否认其效力。就后一种情形而言,因客观上从其代理公开中无法探知其具有排除家事代理权的意思,不应承认其效力。
当然,代理要发生效力仍需其配偶已经事前赋予其代理权或者嗣后进行了追认,不能从家事代理中解释出一种仅对其配偶发生效力的法定代理权。〔36〕比较法上,多数规定家事代理的立法例采双方效力立场,亦有例外。例如,根据《奥地利民法典》第96 条的规定,家事代理仅对非行为方产生效力,除非第三人非因过失而不知行为人符合家事代理的要件(即行为人为已婚、无稳定收入且操持家务的一方)。在后一种情况下,夫妻双方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Vgl.Hinteregger in Fenyves/Kerschner/Vonkilch, Klang3 § 96 Rz 5.值得讨论的是,在此种情形下,夫妻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委托代理授权对家事代理权的影响。合理的立场是并不能从这一行为中当然解释出夫妻双方存在《民法典》第1060 条第2 款所称限制家事代理权的约定。
事实上,将出具授权委托书解释为限制家事代理权需要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法律容许当事人通过单方行为限制家事代理权。《民法典》第1060 条第2 款未规定单方通知限制家事代理权的情形。是否允许单方限制必须考虑家事代理之规范目的。家事代理权是否应当允许夫妻一方以单方通知的形式排除不无疑问。立法例亦呈现出一定的分歧。持限制态度者如《瑞士民法典》。依《瑞士民法典》第174 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对另外一方婚姻共同体之代表权之限制需满足逾越代表权或者无行使代表权之能力两项实质要件之一,且需要向法院申请。《德国民法典》则采用了相反的逻辑。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57 条第2 款的规定,夫妻一方可以通知的形式限制或者排除另外一方的家事代理权,但是如果这种限制或者排除显无理由,另外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废止这种限制或者排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03 条第2 款则规定对家事代理权的限制仅限于滥用家事代理权的情形。与之相对,《奥地利民法典》第96 条则规定夫妻一方可直接向第三人表示排除家事代理权。在承认是否应当允许单方通知排除的问题上,直接通知第三人或者通知配偶应作同等评价,不能仅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故而,《奥地利民法典》实际上是认为夫妻一方排除家事代理权不受限制。
是否允许任意排除,涉及两方面的利益考量。如前所述,家事代理之本质系扶养义务之外化。如允许单方任意排除,对夫妻另外一方而言并无实际损害,因为其仍可依据《民法典》第1059 条之规定主张扶养费给付。参照《民法典》第59 条第2 款的规定,对于第三人而言,这种单方限制要发生效力需要其在通知向其作出的情况下受领通知或者知道夫妻一方向另外一方作出了这种限制,故而其利益不会受到影响。是故,应当承认单方限制的效力。
在承认夫妻一方可以通知方式限制另外一方家事代理权的前提下,仍不宜将出具授权委托书的行为解释为限制的通知。夫妻一方实施代理授权行为可能是基于第三人之要求,或者为了其配偶行为之便利,并不能当然从中推定出具有排除家事代理权的意思。延伸的问题是能否从其撤回代理权之行为中解释其具有限制家事代理权之意思。与作出代理授权不同,撤回代理授权行为通常应解释为具有相应限制其家事代理权之意思,否则这样的撤回毫无意义。
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即家事代理权已经被限制时,行为人当然可以作出个别的代理授权。〔37〕Vgl.Andreas Roth,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9.Aufl.2022, § 1357 Rn.46.行为人的此种代理授权亦不宜解释为对限制家事代理权通知的撤回,即使授权的范围与之前限制的范围一致,对家事代理权限制的撤回仍应当以明示方式进行。
同样,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内,对共有或者准共有财产的处分并非基于默示同意处分。这里并不需要对处分的事前同意或者嗣后追认进行推定解释,有权处分的效果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夫妻另外一方的意思表示。
2.超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行为的效果归属
对于超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行为,无家事代理的适用空间。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超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行为的归属时,时常将家事代理与代理混合使用,模糊了二者的界限,颇为不当。〔38〕参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6 民初2821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1502 民初1700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 民初6613 号民事判决书。在涉及法律行为效果是否归属于行为人的配偶时,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先考虑是否满足家事代理的要件,再考虑家事代理权是否被排除或者限制,最后考虑是否可以适用直接代理的规定。即使不符合家事代理的要件,亦有可能满足直接代理之要件,但直接代理并不包含连带效果。〔39〕Vgl.BSK ZGB I-Isenring/A.Kessler, Art.166 N 3b (20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双方不可能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双方实行的是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此项债务仍然可能依据《民法典》第1064 条的规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而行为人本人也成为连带债务人。例如,夫妻一方协助另外一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受另外一方的委托以其配偶的名义对外签订了合同。虽然这一行为不属于家事代理之范畴,不能据此对本人发生效力,但是因其属于共同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债务,双方仍应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便如此,仍有必要对二者按照上述顺序厘清,不应本末倒置,将夫妻一方实施的而应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行为均置于家事代理规则下处理。〔40〕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 民终7148 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适用顺序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判断行为是否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相关。日常家庭生活需要并不是一个确定性概念。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家庭日常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开支。〔41〕参见罗书臻:《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载《人民法院报》2018 年1 月18 日,第3 版。需要注意的是,抽象描述无法在个案中准确界定夫妻一方的行为是否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相关,仍需结合个案情形予以考量。按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判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考量因素主要包括债务金额、举债次数、债务用途、家庭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当地经济水平和一般社会生活习惯。〔4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年发布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 )》第47 条。按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判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可以结合负债金额大小、家庭富裕程度、夫妻关系是否安宁、当地经济水平及交易习惯、借贷双方的熟识程度、借款名义、资金流向等因素。〔43〕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第二部分。归纳这些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扶养义务的确定与家庭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据此,似乎应当以实际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基准进行判断。但相反的意见认为,应以家庭对外所展现的消费水平为标准,从客观第三者的角度来确定。〔44〕Vgl.Nina Dethloあ, Familienrecht, 32.Aufl., 2018, S.77.这种客观理解实际上是将交易安全和第三人信赖凌驾于通过家事代理实现家庭团结这一根本性的规范目的之上。后文在讨论第三人信赖问题时将对此进行详述。
夫妻一方的行为可能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直接相关,例如赊购日常生活用品,也可能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间接相关,如实施小额借贷。后者的判断原则上应当严于前者。从《民法典》第1060 条第1款的表述来看,法律并没有将家事代理局限于负担行为。结合《民法典》第1062 条第2 款的规定,家事代理亦可适用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但是否包含对另外一方个人财产的处分不无疑问。例如,夫妻一方变卖在性质上属于另外一方个人财产的首饰用以购买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否认家事代理可以适用于此种行为的理由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家事代理仅限于直接的负担行为。此种观点明显与我国通说相悖,民间借贷在我国是家事代理的重要适用场域。其二是家事代理源于家庭扶养,而家庭扶养仅能以请求权的方式行使,不能径直处分配偶财产实现私力救济。〔45〕参见刘昭辰:《夫妻间的日常家务授权(代理权)——家事律师必备的亲属法观点》,载《月旦法学教室》2012 年总第111 期,第57 页。然而,此种理解与我国法允许夫妻一方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的立场相悖。故而,此两项理由在我国法下均无立足之地。实际上,家事代理是夫妻双方应就涉及双方共同生活的事项形成一致意见的一项例外,作为例外应采限缩解释之立场。〔46〕Vgl.Marie Herberger, Von der Schlüsselgewalt zur reziproken Solidarhaftung: Zugleich ein Beitrag zum Rechtsprinzip dernachwirkenden ehelichen Solidarität, 2019, S.20.如承认家事代理适用于夫妻一方对另外一方个人财产的处分,则可能导致例外被放大,过度干涉另外一方的决定自由。并且,承认家事代理适用于夫妻一方对另外一方个人财产的处分也与《民法典》第1060 条所称“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的文义相悖。〔47〕参见贺剑:《〈民法典〉第1060 条(日常家事代理)评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 年第4 期,第108 页。
在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另外一方个人财产或者超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其使用的名义分别适用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规则。例如,在夫妻一方未经另外一方的委托授权,以双方名义处分双方共有的房屋时,有法院以另外一方知情却不表示反对,夫妻双方有家事代理权为由,判决买卖合同对其发生效力。〔48〕参见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2 民终114 号民事判决书。默示意思表示的解释需要事实基础,家事代理权本身并非事实基础。在夫妻一方将其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交由另外一方在交易时出示时,有法院从中推定出代理权授予之意思,并以家事代理作为认定基础。〔49〕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 民申31 号民事裁定书。这种推定本身并无问题,但是其基础并非家事代理权,而是非签字方的行为。此处法院不过是想表达夫妻之间作为紧密的生活共同体,在交易习惯中的这些行为应被作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处理。对于不具有夫妻身份的普通人而言,并不能从中一般性地推断出代理权授予之意思。对于夫妻而言,在一方知道交易存在,且将上述证件交给另外一方时,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产生了这种高度的盖然性。
在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义对共同财产进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处分或者处分另外一方的个人财产时,部分法院对处分效力的理解存在偏差。有法院将此种情形非行为方配偶的知情沉默之效果确定为代理之发生,混淆了无权代理的追认和嗣后同意处分的问题。〔50〕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 民终3691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2 民初5265号民事判决书。亦有法院认为,在一方对另外一方无权处分行为知情沉默时,不构成无权处分,其立论基础在于家事代理和民法上的诚信原则。〔51〕参见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2010)禹民一初字第1047 号民事判决书。以诚信原则作为立论基础不存在疑义,但将家事代理权作为立论基础却存在重大问题。正确的解释路径是,如果一方知情却不作异议,应作为默示同意处分处理,〔52〕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申字第00977 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甘民申字第236 民事裁定书;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 民终2468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民一终字第00100 号民事判决书。这种默示同意处分既可能发生在行为之前也可能发生在行为之后。
因此,在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场合,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可能会对默示意思表示的认定产生影响。不能将这种夫妻特殊身份所产生的影响归入家事代理,它与家事代理完全无关。
三、信赖保护问题
(一)信赖保护的一般性否定
前述家事代理误用现象多与误解家事代理之规范目的相关。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家事代理之规范目的是否包含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持支持观点的一方认为,家事代理具有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因为夫妻之间存在最紧密的联系,财产关系具有很大的隐秘性和模糊性,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值得保护。〔5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9-140 页。其合理性需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予以讨论。
在负担行为场合,由于家事代理之适用范围有限,第三人通常不关注具体交易对象的履约能力。尤其是在现金交易中,家事代理几乎无存在的意义。如果第三人关注与其交易的对象的履约能力,其与家事代理亦无关系,因为其有权知道的是与其进行交易的相对人。至于夫妻身份对用以承担责任的财产关系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系夫妻财产制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家事代理亦无关系。这也是家事代理不将配偶公开或者婚姻状态公开作为其要件的重要原因。第三人不能因为家事代理效果之发生,根据《民法典》第147 条的规定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如前文所述,相对人的婚姻状态并不构成交易之基础,亦非合同之内容。因此,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依据家事代理所获得的额外保护并不建立在信赖原理之上。相应地,在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第三人不能主张所谓表见家事代理。〔54〕参见林秀雄:《亲属法讲义》,元照出版公司2018 年版,第118 页。同理,在双方婚姻关系已经终止(一方死亡或者离婚)的情况下,即使第三人不知道该情况,也不能主张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4 条的规定。〔55〕Vgl.Joachim Gernhuber/Dagmar Coester-Waltjen, Familienrecht, 7.Aufl.2020, S.170;林秀雄:《婚姻之普通效力》,载《月旦法学教室》2009 年总第76 期,第55 页;贺剑:《〈民法典〉第1060 条(日常家事代理)评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 年第4 期,第110 页。
同样地,在第三人作为债务人时,不能根据其信赖相对人为唯一债权人而排除家事代理之效果。在债权让与场合,债务人尚不能以债权让与为由拒绝履行,只能根据《民法典》第550 条之规定主张由让与人负担增加的费用。同理,此处作为债务人的第三人同样不能以债权人变动为由而主张拒绝履行。值得探讨的是,如果该债权根据《民法典》第1062 条的规定,属于不得让与的债权,作为债务人的第三人能否据此要求排斥家事代理效果的发生。与债权转让不同的是,家事代理形成的是连带债权关系。虽然依据《民法典》第518 条第1 款前半句之规定,无论是行为方还是非行为方均可要求债务人履行。但债务人仍有选择的权利,〔56〕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400 页。选择向缔约方配偶履行,其利益并没有受此影响。其中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如果债权人与相对人约定债权不得让与,亦不应将其解释为双方存在排除家事代理的约定,理由有二。其一,此种情况下债务人仍有继续选择债权人履行的自由。其二,排除家事代理效果的约定需以债务人明知存在家事代理为前提,双方排除债权让与并不等同于债务人知道家事代理的存在。并且,债权让与和连带债权的形成亦非同一事物。
在处分行为场合,家事代理主要适用于动产。然而,此时并不需要家事代理发挥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作用,善意取得制度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功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14 条的规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为善意。不难看出,此处的可信赖事实指向处分人之处分权。在动产处分中,这种信赖建立在占有的表征功能之上。〔57〕参见叶金强:《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要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4 年第5 期,第81 页。然而,占有的表征功能较弱,不能仅凭占有事实就对其具有处分权产生合理信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58〕参见王利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草案第111 条为分析对象》,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4 期,第82 页。相对人的婚姻状况无疑是影响合理信赖认定的重要因素。但婚姻状况的信赖与家事代理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在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与其交易的相对人已婚的情况下,从相对人占有中推定其有权处分的合理性被大大降低。
当然,这一问题讨论的前提是相对人对该动产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只有无权处分的情况下,才有进一步讨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如前文所述,家事代理仅可能适用于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行为方属于有权处分,自然无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对于超越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动产处分,应根据名义的差异分别考虑表见代理和默示同意处分,均与家事代理无关。唯一值得讨论的情形是,第三人信赖相对人所进行的处分属于家庭日常生活范围。这实际上涉及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应如何判断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纳客观第三人标准,〔59〕Vgl.Christian Breuers, in: jurisPK-BGB, 10.Aufl.2023,§1357 Rn.17.从理性的交易相对人角度出发进行判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考虑交易相对人的看法,而应根据实际情况个别考察行为是否确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60〕Vgl.Reinhard Voppel, in: Staudinger BGB, 17.Aufl.2018, § 1357 Rn.41.如前文所述,家事代理系扶养义务外化之结果,如果将第三人之信赖作为确定家事代理范围之基础,就会与这一目的发生严重的冲突,也与家事代理无须以公开作为要件的构造相违背。既然家事代理的公开并非其要件,也就无所谓担心“第三人不免受不测之损害”的必要。〔61〕参见戴炎辉、戴东雄、戴瑀如:《亲属法》,2010 年自版发行,第132 页。故而,应当以家庭的实际生活状况而非第三人可信赖的外观作为确定标准。
家事代理之规范目的不应包含信赖保护亦可从相反的情形中推知。即使第三人合理信赖与其交易的相对人未婚,亦不影响家事代理效果的发生。第三人欲将合同之效力局限于与其交易的相对人时,则应根据《民法典》第1060 条的规定进行明确的约定。这种约定并不会对其产生过多的负担。
(二)例外情形下的善意保护
作为一种例外情况,《民法典》第1060 条第2 款规定夫妻双方对家事代理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这一规定之目的在于避免非行为方通过与其配偶倒签限制行为方家事代理权的协议来摆脱责任。并且,在承认非行为方可以单方限制行为方家事代理权的情况下,如果不设定信赖保护来限制这种行为,将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并导致家事代理规范成为具文。法律为相对人提供的此种保护是针对行为已经实施的情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人即使在行为时不知道与其交易的自然人已婚,亦不影响本款的适用。此处可信赖的事实指向不存在家事代理权被限制的情况,存在相对人知道行为人已婚却不知道家事代理权被限制以及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已婚这两种情况。有观点认为,第三人的善意应当局限于明知,而不包括因重大过失而不知。〔62〕Vgl.Andreas Roth,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9.Aufl.2022, § 1357 Rn.44.举重以明轻,相对人因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亦应被排除。这种理解对作为交易相对人的第三人明显有利。由于在善意认定中,过失要件扮演了重要的衡平作用,如将其排除在外,利益平衡将无法展开。〔63〕参见石一峰:《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136-137 页。并且,在证明责任分配上,主张家事代理限制对第三人发生效果的非行为方应承担举证责任。〔64〕Vgl.Reinhard Voppel, in: Staudinger BGB, 17.Aufl.2018, § 1357 Rn.123.易言之,非行为方应当证明第三人明知。然而,明知之事实往往难以证明。这实际上会加剧利益失衡状态,导致对第三人的过度保护。此处善意的判断至少应当与《民法典》第1065 条第3 款保持一致,将因过失而不知的情况纳入。之所以应纳入此种类型,实乃因为家事代理本就属于对第三人的额外保护,理应对其科以一定的注意义务。
四、结论
在实定法已经明确规定家事代理的情况下,应当将研究的重心从是否引入家事代理转向规范的解释和续造之上。解释和续造之关键在于厘清与其他相关规范的关系。学界以及司法实践对家事代理之所以出现大量的误解和误用,正是对家事代理规范目的及其特殊构造缺乏清晰的认识。就家事代理的规范目的而言,无法从“钥匙权”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答案,而应考虑当今家庭生活之新面貌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典型交易情况。在此种涉他性法律构造的解释和续造中,极易产生误解的是交易安全保护问题。不能将交易安全保护当然作为支持引入家事代理的理由,〔65〕参见张学军:《锁匙权研究》,载《金陵法律评论》2004 年春季卷,第161 页;马忆南、杨朝:《日常家事代理权研究》,载《法学家》2000 年第4 期,第30 页。同样也不能将其作为规范解释和续造的价值指引。家事代理作为婚姻的效果,是扶养义务外化之结果,并实际上产生了有利于第三人之结果。此外,由于家事代理之构成要件亦不包括公开,亦可反面印证家事代理规范目的并不包括交易安全保护。不能本末倒置,将交易安全作为解释和续造的出发点。
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要厘清家事代理之体系基点,需要进一步明晰家事代理规范与夫妻共同债务规范以及家事代理规范与表见代理规范、默示意思表示规范之间的关系。就前两者的关系而言,在负担行为层面,家事代理之效果并不局限于连带债务之形成,而是直接将非行为方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形成权之行使亦应包括在内。但不宜将债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共有或者准共有之形成作为其效果,后者应在夫妻财产制的框架内解决。此外,家事代理之效果还包含处分权之拟制。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并不意味着排除家事代理,限制家事代理亦不意味着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就家事代理与表见代理、默示意思表示的关系而言,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代理仍然有适用的空间,在判断顺序上处于劣后顺位。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法律行为,家事代理不具有任何适用的空间,不能将其与表见代理或者默示同意处分混为一谈。
总之,考虑到家事代理的体系违和效应,在解释和续造上应保持谦抑性,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避免其沦为纯粹的债权人保护工具,从而背离其规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