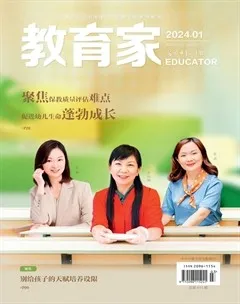天赋,机遇而非“神话”
亦心
2022年,我有幸参与到《光明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负责策划与小读者和家长交流的亲子板块。在读者来信中,一个初中女孩的倾吐击中了我的内心:这是个热爱写作的姑娘,在期待的比赛中失利,反而是相熟的朋友获了奖,于是姑娘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并不如他人般有写作天赋。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期,面临同样的困惑彷徨着……
初中时,偶然的契机,我开始发现用文字构架一个故事的乐趣,于是一边大量阅读“大部头”世界名著,一边踏上了尝试创作的路。积累了两年,满怀期待地给喜欢的杂志投稿,得到的却是遗憾的拒绝。那一刻,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根本就没有写作的天赋。庆幸的是,高中语文老师把我的作品推荐到校刊上,而一些阅读我的拙作的同龄人,用文字积极地回应我,让我有了未谋面却可彼此倾诉的笔友。这些都化作鼓励我继续坚持的莫大动力,直到后来,我成为记者,用文字装点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实现了最初的梦想。
今天回头看,如果你问我是个有写作天赋的人吗,我并不认为自己在写作领域具有比他人多么巨大的优势,但的确和我个人其他的智能相比较,写作是我的天赋优长。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天赋:一是和同龄人甚至比自己大一个年龄阶段(一般是两岁)的人相比,在某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是超越同龄人平均值的绝对优势,那么可能就是具有某方面的天赋;二是和自己相比,花费同样的时间,在A方面比B方面能取得更长足的进步。绝大部分人的天赋不可能达到顶级水准,比如艺术才艺超过毕加索,跑步速度赶超博尔特。如果只能是有绝对天赋的人才能进行,那么恐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必学艺和运动了。但如果纵向考量自身情况,寻找最突出的特长加以培养,或许就可以成就相对的天赋。
还是以我为例,尝试写作的最初三年,我也同步在练习绘画。几年并行下来,面对高中学业时间加长的情况,我审慎思考了两项能力未来的发展可能,判断写作比绘画更适合自己——因为在绘画方面,模仿是我的强项,而创造性却不明显。对个人而言,写作更能称之为我的天赋。
天赋是一种神奇的馈赠,但并非什么“魔法”或“神话”。提到“天赋”,总难免出现和“努力”的争论。不少声音强调,没有天赋,努力也没有用。这种论调回避了它的反面:即便有天赋,不努力仍然无法取得成就。美国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斯在《坚毅》里提到的两个重要的方程式:天赋×努力=技能,技能×努力=成就。也就是说,当你缺乏坚毅的品质,天赋只是未实现的潜能;唯有通過持之以恒的努力,天赋才能转化成技能,而技能才有机会结出甘美的成果。“天才少女”谷爱凌,为了每天8小时投入热爱的运动事业,学会了在车上写作业、睡觉、吃饭;《只此青绿》的领舞孟庆旸,用大量的训练突破了“奔三”后骨骼不再似年轻时柔软的生理限制,跳出了为人称道的“青绿腰”。与生俱来的优势,让他们比常人拥有更多机会,但是为了发挥天赋,他们也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而“伤仲永”的故事,也道出了天赋缺少后天训练与良好环境的遗憾收场。
我们往往太高估天赋的作用,以至于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因素。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大脑结构的可塑性极强,具有终身发展性,影响最终结果的,除了智力因素,还有沟通合作、情商等社会情感能力。沉浸在热爱的事情中,往往能让人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求学时期哪怕学至凌晨,我也要每天拿出平均半小时到1小时来写作。创作的美妙感包围着我,让我完全不觉疲惫。在《发现天赋的15个训练方法》一书中,作者肯·罗宾逊罗列了诸多帮助人们发现天赋苗头的策略,包括“描述自己”“你喜欢什么”“什么会吸引你”等。与其说是在开掘潜能,不如说是通过体系化的思考来重新认知自己,找到热衷的领域,并持续地投入其中。保持对兴趣的热忱,而非和他人简单比较,去不断追寻,享受过程的欣喜,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肯·罗宾逊提到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天赋是你来到这世上的使命,你的天赋便是兴趣与热情的交汇处。我以为,这也是我们所有普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