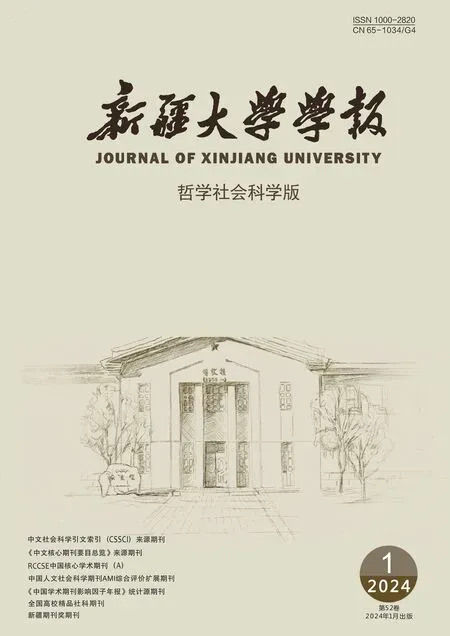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郭 明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赵园曾指出:“关于士风的论说,通常赖有化约,无以避免‘印象’式的判断的模糊影响,似是而非。”[1]士风描述大抵均建立在对历史细节的化约、提炼的基础上,既可能放大某些特质,同时也不免刊落其余。士风印象形成后又常在反复的品题申说中固化,作为一种仿佛不证自明的常识融入后人的知识结构。范仲淹作为北宋士风振起的标志性人物,在后人的反复赞颂中逐渐成为崇尚节义、奋力敢为的士风象征。这固然是对范仲淹人格与地位的合理评价,却也是士风叙事化约的结果。与这种士风印象深入人心的程度相比,学界对范仲淹本人士风观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关注还很不足。本文便拟根据范仲淹的著述行履厘清其士风观念,进而考察其文学创作中常被忽视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士风叙事中范仲淹形象的形塑过程及其历史意蕴。
一、范仲淹士风观分析
朱熹曾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2]范仲淹不仅以其立身行事为北宋士人树立了典范,而且积极参与到提振士风的过程中,历来被视作北宋士风振起的标志性人物。不仅如此,范仲淹对士风话题的关注也超过其他庆历名臣,在其著述中有大量对士风问题的深刻思考,表现出内涵丰富的士风观,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阐发。
(一)士风与世风:建立在“四民”说基础上的士人身份意识
范仲淹的士风观建立在儒家“四民说”基础上,在北宋士人中有一定特殊性。宋学精神注重内在人格的完善,评价士风也多诉诸道德评判,如欧阳修谓冯道“无廉耻”[3]、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4]1787皆是其例。范仲淹则更强调“士”在四民社会的角色定位,认识到士农工商皆生活在一共同的“世风”之中,而“士风”不过其中一端。其《四民诗》便集中体现了此认识,这一组诗由四首诗作组成,其《士》篇云: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5]26与之相应,《农》《工》《商》诸篇批判骄奢游惰、轻视商业等风气对农民、工匠、商贾的伤害,推崇勤俭淳厚之风,反映了范仲淹对“世风”的准确把握。
范仲淹将士风视作世风中最具能动性的一环,寄托了扭转世风的希望。其《上张右丞书》中便写道:“其大幸者,生四民之中,识书学文,为衣冠礼乐之士,研精覃思,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以存不朽,文章可以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5]181其中“忠孝”“仁义”“功名”等字面亦与《四民诗·士》篇桴鼓相应,可见立足四民意识以士风革新世风的内在理路。
(二)敦教育与慎选举:侧重制度设计的士风转变途径
由于以士为四民之首的身份自觉考虑士风问题,范仲淹注重士人在君臣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对士风的形塑作用。如其《上资政晏侍郎书》即云:“天生蒸民,各食其力。唯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圣人率民以养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无德,何食之有?”[5]203换言之,范仲淹固也强调士风中的道德因素,但更关注涵育士德的外部制度环境,具体而言则分士人的培养与选拔两个方面。
范仲淹重视通过兴学来培育士风,尤其注重学校制度,他在《上执政书》中指出:
复当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5]190-191
兴复庠序常被视为范仲淹之于宋学兴起的功绩,而究其用意首先在于追求“士风丕变”。范仲淹反复致意的“古道”,并不仅如韩愈及宋代理学家们强调的儒家道统,而更侧重《周官》的古制,他相信学校之制度若得恢复,则士风转变自然水到渠成。随之而来的还有科举制度的完善,《奏上时务书》云:“徒于礼闱之内,增其艰难。壮士惜年,数岁一举,乃相奔竞,至有讼争。……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5]176批评记诵、辞章之学取士的弊端,尚属宋人议论科举的老生常谈。但范仲淹指出礼闱艰难、壮士惜年与奔竞之风的关联,却是出自政治家务实的考量,值得注意。范仲淹认为士风是包括中下层士人在内的整个士阶层的总体风尚,即《上执政书》所谓“有出类者,岂易得哉?中人之流,沉浮必矣”[5]190,并非对士人道德状态的第一义的要求。因此,范仲淹较少强调从个人修身角度寻找转变士风的途径,而是诉诸制度层面。
(三)狂斐与中道:范仲淹对理想士风状态的思考
“狂斐”[5]198是范仲淹《上执政书》中的自谦之辞,语出《论语》“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一句,朱熹集注云“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6],因此这谦辞也暗寓自傲之意。《上执政书》作于天圣五年,范仲淹时守母制,上书言事有居丧越礼之嫌,但他“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5]182,这种不恤讥议、忧以天下的精神正是庆历士风的典型特征。但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在《与省主叶内翰书》中反思道:“汉李膺之徒,黑白太清,而禁锢戮辱。虽一身洁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祸,汉室亦从而亡之。……前者数君子感遇激发,而高议直指,不恤怨谤;及群毁交作,一一斥去。”[5]230其中“感遇激发”“高议直指”“不恤怨谤”道出庆历士人气质,而“黑白太清”“邪正相激”等语也正中庆历士人的短处,由此观之,范仲淹此番反思与朱熹“志大而略于事”注文不无契合。
范仲淹的上述反思本身表明,后人津津乐道的庆历士人不避怨谤的气质并不完全符合范仲淹理想中的士风样貌。这种狂斐气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正邪相激”,实有孟子“吾不得已也”的意味,且常有过甚之虞。因此,范仲淹很重视不同士风倾向的限度问题,主张不离中道。如《与唐处士书》中说:“清厉而弗静,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5]215这里借论琴理,表达了对君子之风的看法。清厉意指士人奋发敢为的意气,超过限度则表现为躁;和润对应士人谨重敦厚的涵养,超过限度则表现为佞。因此,这种清厉而能静、和润而能远的中道状态方是范仲淹心目中的理想士风。在前辈士人中,范仲淹认为谢涛堪为表率,在《祭谢宾客文》中写道:
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静之。[5]234
这不仅是表彰谢涛的持重恬退,更关注盛德懿范对士风的感召作用。范仲淹又以“循良廉让”正面概括这种德行,在为谢涛所撰神道碑中便写道:“某于公有家世之旧,又与舍人为同年交,爱公治有循良之状,退得廉让之体,足以佑风化而厚礼俗。”[5]266
范仲淹的这种观念并非浮泛之谈,而是根植于对士风现状的深刻把握。北宋前期士风未能彻底扭转唐末、五代以来的衰靡局面,士风的弊端主要表现为苟且与躁竞两个方面。此两者之间关系颇为微妙,因为奋起革除苟且之弊的努力本身便可能被指为奔竞,范仲淹曾被目为近名、躁进就是明证。在此背景下,范仲淹对士风倾向的限度问题极为敏感,主张不离中道的循良廉让之风。
二、士风视角下的范仲淹文学作品接受
由上可知,范仲淹有着内涵丰富的士风观,但其中有些侧面与传统士风叙事中庆历士人的性格气质并不完全吻合,例如他认为理想的士风状态应该合乎“中道”,这对于一位庆历士大夫来说似乎总显得过于“保守”。这并不难理解,士风观是对士风问题的全面看法,但在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士风主张则需要针对现实的士风弊病,两者存在差异是很自然的。但在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容易从对庆历士大夫的一般印象出发来考虑范仲淹的作品,因此不免忽略其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范仲淹的士风观也有着帮助全面认识范仲淹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有必要加以考察。
首先,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与其“不离中道”的士风观有紧密的联系。范仲淹认为士风与文学既能相互映鉴又可彼此影响,他在《奏上时务书》中写道:“国之文章,应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5]172-173风化见乎文章,因此观文章盛衰便可见士风厚薄;而文章应乎风化,则提供了通过振革士风来影响文学的思想依据。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正面提出了“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与时消息,不失其正”的主张,其文曰:
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观乎处士之作也,……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5]160-161
五代乱世之诗“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在当时不失为情感的真实反映,虽有失雅正却未为大病,但宋兴之后士人依然争相模拟,便有失其“真”。在“真”的基础上还须“不失其正”,即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因此范仲淹对唐异“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大为赞赏。这种“意必以淳,语必以真”的文学标准,也正是宽而不懈、直而不讦的中道士风观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
其次,有别于同侪诗歌中常见的言官视角,范仲淹的淑世情怀更多表现为精英化的制度关怀,因此其作品蕴含一种自信从容的气质。正如其《奏灾异后合行四事》所云“天下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5]526,范仲淹倾向于以自上而下的精英立场,从统摄全局的规划者视角考察士风问题。①谢琰对范仲淹政治思想中的精英意识有精到深刻的论述,指出:“他(范仲淹)没有在心性层面设立本体,也没有认识到应该有‘识仁’‘定性’的工夫,而是希望精英阶层在‘治人’过程中锻炼意志、发展智识,这是一种简朴的经验主义态度。”参见谢琰《制度之学的新开展:范仲淹思想重估》,《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3期,第121页。相应地,范仲淹看待庶众也主要采取抚育教化的精英视角。这表现在创作上,便是一种廊庑广大、堂堂正正的从容气象。如《依韵和孙之翰对雪》云:
江干往往腊不雪,今喜纷纷才孟冬。乃知王泽寝及远,益明天意先在农。有年预可慰四海,大瑞且当闻九重。况此湖山满清思,与君交唱若为慵。[5]114
此种将淑世情怀与官员的从容乐逸融合起来的作品,自非范仲淹独有,但在其他诗人通常不过是表达淑世精神的模式之一,而在范而言却是主要面向,放下精英意识通过正面刻画民生疾苦的方式相比之下要少得多。这正是范仲淹以精英化视角与制度关怀看待士人职能与士风性质的思维特点在诗歌创作上的体现。
最后,“先忧后乐”是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的核心印象,某种程度上掩蔽了他对隐逸意趣的文学阐释。其《岳阳楼记》向士人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则何时而乐耶”[5]168的问题,体现了庆历士大夫无时或已的责任感。的确,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似乎囊括了士人所有可能的境遇,于是便自然地逼出了“先忧后乐”的结论。但联系创作背景可知,所谓“江湖”并不指远离官场的布衣处境,而是指去国怀乡的迁谪生涯。如此,庙堂与江湖之间固然笼罩着无可或避的责任之网,但庙堂与江湖之外却尚有为“先忧后乐”的士风印象所化约的另一维度,即隐逸之乐。通观范集不难发现,隐逸之趣是其文学世界中的重要主题,至少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面向。
其一,以摹写隐者高士寄寓其振革士风的主张。范集径以题赠处士隐者为主题的诗歌便有《赠都下隐者》《访陕郊魏疏处士》《寄赠林逋处士》《赠余杭唐异处士》《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寄西湖林处士》《送邢昂处士南游》《寄林处士》《留题方干处士旧居》《寄安素高处士》等11 首。其中较重要的是赠给林逋的5首,大多述隐居之乐而又不失士风关怀,如《寄赠林逋处士》云:“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频。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几侄簪裾盛,诸生礼乐循。朝廷唯荐鹗,乡党不伤麟。”[5]72林逋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隐者,“几侄簪裾盛,诸生礼乐循”亦非典型的隐居景象,此类隐逸书写与《严先生祠堂记》相类,以表彰高士来提倡淡薄荣利之风,与范仲淹追求循良谦退士风的思想相符。
其二,范仲淹也不排斥吏隐之趣,并在其中隐然融入谪居的牢骚感慨。如《桐庐郡斋书事》云:
千峰秀处白云骄,吏隐云边岂待招。数仞堂高谁富贵,一枝巢隐自逍遥。杯中好物闲宜进,林下幽人静可邀。莫道官清无岁计,满山芝术长灵苗。[5]87
此诗作于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因力谏废郭后为非,被贬为睦州知州,同年四月又移守苏州,总体处于贬谪阶段。诗中“数仞堂高谁富贵,一枝巢隐自逍遥”一联将耿介不屈与隐逸逍遥完美融合,道出范仲淹隐逸书写的另一重背景,即对无端遭贬的愤懑不平,以及笑傲林下不待招引的不屈姿态。范仲淹这一年偏爱隐逸主题,尤其反复写到子陵钓台,如《依韵酬周骙太博同年》云“不称内朝裨耳目,多惭外补救皮肤。子陵滩畔观渔钓,无限残阳媚绿浦”[5]87,又如《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十)云“风尘日已远,郡枕子陵溪。始见灵龟乐,悠悠尾在泥”[5]83等等。这些作品与《严先生祠堂记》作于同年,联系创作背景当不难体会到,范仲淹对山高水长的隐者之风的歌颂中,实蕴含着“云边岂待招”式的精神自足,寄寓了傲岸不屈的抗争姿态。历代评《严先生祠堂记》者多就笔力与结构着眼,①宋人楼昉评曰:“字少词严,笔力老健。”见楼昉《崇古文诀》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125页。清人吴楚材、吴调侯评曰:“题严先生.却将光武两两相形,竟作一篇对偶文字。至朱乃归到先生,最有体格。且以歌作结,能使通篇生动,不失之板。妙甚。”见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1页。而较少在其中寻索范仲淹的心态隐曲,或许也是范仲淹士风形象对其丰富鲜活的文学世界的遮蔽化约现象的一个例证。
其三,范仲淹也偶有主动放下“先忧后乐”的士人身份,追怀庙堂、江湖之外的隐君子之乐的作品。《鄠郊友人王君墓表》即是其例。范仲淹与王镐交游早在祥符初年,尚属布衣之交。文中写道:
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迭,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凡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5]328
对于性质2,冀教版和青岛版在第二学段均是通过度量发现对角相等.在第三学段均是通过几何变换发现性质,并对其进行了演绎证明,其中青岛版不仅提供了一种详细的证明过程,还呈现了另一种证明思路,体现了证明思路的多样化.
此文作于庆历五年(1045),亦即作《岳阳楼记》前一年。其时范仲淹五十七岁,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正是士风叙事中出将入相、白发忧边的典型形象。而恰在此时,范公深情追忆入仕之前与知己游乐的经历,“当圭峰以下”数句空明动人,意境高绝,审美价值比之《岳阳楼记》不遑多让,却鲜获世人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通过今昔对比表达出十分真挚的怅惘之感:“……噫!予与君别三十七载,风波南北,区区百状。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廷,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5]328这种恍如隔世的迷惘源自身份、遭际、心态的巨大反差。前已论及范仲淹士风观中有着建立在“四民”观念上的角色意识,本文的回忆之箭却已触及其士人身份完全形成之前的畛域,这种时间、身份上的双重张力使得文章部分地脱去了作为士风表率的范仲淹形象,获得发自个人化生命体验的感染力。
总之,范仲淹本着士风与文学相互反映、影响的基本立场,将其关于理想士风状态、提振士风途径等思考融入文学创作之中。但是范仲淹文学创作的这些侧面常常受到忽视,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范仲淹虽总体成就不及北宋诸家,但其少数名篇的地位却不逊于任何大家作品,这些名篇在范集中宛如平原里拔起入云的孤峰,构成对范仲淹文学世界的印象,但也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全貌。换言之,随着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范仲淹的文学世界也在读者视野中被相应地拣择,最终形成经典作品与士风形象相互印证的局面。
三、士风叙事与范仲淹形象的演变
由上文可知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及其文学作品的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士风叙事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总体趋势上的化约与局部的补完常常并存,其中的关键节点颇值得玩味。历时地看,早期针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是与对庆历士风的刻画结合在一起的。蔡襄《四贤一不肖诗》、石介《庆历圣德诗》、范仲淹《百官图》等都有明显的士风叙事意味。此类文本多在斩截的忠奸对立的视野下刻画士风面貌,不免有失偏颇。如《八朝名臣言行录》即载范仲淹并不赞同石介所作《庆历圣德诗》,认为“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坏”[7]。可见范仲淹立身处事尚有敦厚持重的一面,而为以揄扬士风为旨归的文本所忽视。此后从欧阳修为范仲淹撰祭文、神道碑文,直至宋后的士大夫对范仲淹的题咏,也多不出士风叙事范畴,值得关注。
(一)外和内刚:欧阳修对范仲淹形象的补完
仁宗朝前后期的士风面貌并不一致,以谏诤与革新为表征的士风主要出现在仁宗朝中前期,后期则更多呈现谨厚持重之风。在庆历名臣中,韩琦、富弼、欧阳修的政治生涯均延续到仁宗朝后期,亲身经历了这一转变过程。随着新旧党争的兴起,旧党虽推隆仁宗朝的士风,但欧阳修等人已更多地以反对新法的持重、保守姿态而被记忆。换言之,“嘉祐”逐渐取代“庆历”成为仁宗朝士风的标志。但是范仲淹由于去世较早,并未经历这一转变过程。①范仲淹去世于皇祐四年(1052),其时欧阳修、韩琦、富弼仍处于新政失败后辗转州郡的失意境遇,两年之后方陆续得到起复: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入朝任翰林学士,至和二年(1055)富弼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和三年(1056)韩琦检校太傅,充枢密使。因此,欧阳修晚年的士风叙事便面临着记述、评价这一转变的问题,而如何刻画侪辈中声望最隆而又未进入嘉祐时期的范仲淹的士风样貌,更是关键所在。
欧阳修的策略是补充了庆历士风叙事中化约掉的忠厚持重的因素。这突出表现在“朋党”与“范吕和解”两个典型事件的记述上。
《朋党论》是欧阳修论述朋党问题的名文,也是体现庆历士人奋厉敢为之风的重要材料。但其中“君子有党”之说,须置于回击政敌的语境加以认识,留意其中往来相激的意味。欧阳修后来于此不无转变,如《祭资政范公文》云:“公曰彼恶,谓公好讦;公曰彼善,谓公树朋……谗人之言,其何可听?……呜呼公乎!欲坏其栋,先摧桷榱;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损百,人谁不罹?谁为党论,是不仁哉。”[4]1231-1232《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亦云:“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4]590两者皆为辩“党论”之诬,与“君子有党”说显然不同。
与“党论”相关,还有所谓“范吕和解”问题。正如上引神道碑文所言,欧阳修力主双方“欢然相约,勠力平贼”。范、吕二人表示和解的文字具在,本不成问题。②范仲淹《上吕相公书》云:“昔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言;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夙夜尽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负泰山,未知所释之地。”见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03页。然此类话题的特殊性在于,谅解姿态是否等同于尽弃前嫌,并不容易判别。在范纯仁以人子身份提出“我父至死未尝解仇”[8]的情况下,欧阳修寸步不让的严正姿态说明这并非对一段往事的单纯争议。正如王水照所说,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是“欧阳修亲历激烈党争后的新思考的结果,是对他《朋党论》思想的新调整,甚至标志着范仲淹一派人士‘跳出自身反观自身’的集体反思,意味深长”[9]。如何记述范仲淹对昔日政敌吕夷简的态度,关系到如何看待与评价庆历士人风尚的问题,是对庆历时代的士风叙事。因此欧阳修不再持“君子有党”之论,同时强调范仲淹的宽宏气度,并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作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4]591的最终评价,补充了在庆历士风叙事中常被忽略的“外和”的一面。
(二)一定之见:苏轼对范仲淹形象的概括
苏轼对范仲淹极为景慕,但当他崭露头角时范已去世,不及亲见其面。苏轼对此甚抱憾恨,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写道:
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10]961-962
苏轼着重提到欧阳修、韩琦、富弼皆以国士相待,并引述欧阳修“恨子不识范文正公”之语,不无有推测范仲淹也会以国士相待之意。苏轼素来积极结交庆历士大夫,也表现出成为其继承者的愿望。①朱刚曾指出:“我们通读二苏的贤良进卷,就可见他们对‘庆历士大夫’的肯定与理解,以及成为其继承者的真诚愿望,而此种愿望也获得了长辈的接受。”参见朱刚《苏轼十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47页。当熙宁变法开始后,苏轼与欧阳修等前辈多持反对变法的态度,因此苏轼与“庆历士大夫”之间的认同关系某种程度上便等于表明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谨厚持重之风的渊源有自。但不应忽视,范仲淹却始终以一位被政敌阻挠而不得尽展抱负的革新者而被铭记,苏轼也面临如何在其士风叙事中刻画范仲淹形象的难题。
苏轼对欧、范皆有总结性的评价文字,即《六一居士集叙》与《范文正公文集叙》。清人谓此两文各有侧重,前者专主道德文章,后者则侧重事功,②沈德潜:“为欧阳公作序,应从道德立论;为范文正公作序,因从道德事功立论。各有专属。不似近人文字,将道德文章事功一齐称赞,漫无归著也。”原文见《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三,转引自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67页。所评固是,但也不应忽略两文写法上的虚实之别。苏轼在序文中正面论述了欧阳修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对范仲淹的事功则未展开论说。《范文正公文集叙》云: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公在天圣中,……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10]962
苏轼对被群起阻挠的“新政”略而不谈,而使全文围绕范仲淹“终身不改易其言”这一核心论点展开,在引证伊尹等先贤莫不如此后,随即从反面提问:“此岂口传耳受皆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如此便敉平了主要作为新政主持者的范仲淹与晚年反对新法的欧阳修等人之间的微妙裂隙,归结于他们均具备“终身不易其言”的政治识见与操守,并隐然将矛头指向盲目迎合变法之辈,从而将范仲淹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之内。
(三)经典化与标签化:宋后题咏中的范仲淹形象
翻检历代与范仲淹相关的题咏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后人对范仲淹的关注并未因时代久远而稍衰。以《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诗颂》[5]1232-1271为例,内中收录自宋迄清题咏范仲淹事迹的诗作共104 首,其中宋代34 首,元代5 首,明代42 首,清代23 首。宋代34 首中又有14 首为宋祁、石介、张方平、韩琦等同时人的交游题赠之作,若不计这14首,则明、清两代数量均超过宋代。
但与此同时,这些文字中反映的范仲淹形象却渐趋固化,大多围绕“先忧后乐”等几个主题反复咏叹。《诗颂》所录诗作中多次提及的事迹主题可分为“画粥苦学”“才兼文武”“抵御西夏”“倡导新政”“先忧后乐”“兴建义庄”等六项。其中宋、元人题咏之作主要围绕“抵御西夏”“先忧后乐”二事,其余几项则几乎没有提及,但到明清时期的题咏之作中这六个事迹主题出现次数则变得平均起来,不少诗更几乎全以这些事迹连缀成篇。如明人徐琅《谒范文正公庙留题》云:“种学长山惜寸阴,宋家有待作甘霖。自知画粥谋吾道,谁谓调羹惬帝心?泽满义田传百世,惠存药井重千金。先忧后乐如公少,留得芳名照古今。”[5]1257相比之下,宋人虽也不免提到这些事迹,但通常不追求胪列的完备性。而宋人咏范的某些常见话题,在明清同类作品中却少见嗣响。比如范仲淹因言被黜,宋人多为他鸣不平,王十朋《范文正公祠堂诗》云:“正色朝端批逆鳞,三黜愈光名愈闻。”[5]1244孙觉《题范公堂诗》亦云:“三黜作正谏,流离成老翁。”[5]1243明清人同类作品中则较少涉及,孙觉“流离成老翁”一句流露范仲淹失意落寞之态,后人更少有着笔,亦可见范仲淹形象的经典化中的选择与化约。
《诗颂》所录虽非历代范仲淹事迹题咏的全部,但已足可见出后世熟稔的范仲淹形象在明清两代逐渐定形的趋势。相应地,范仲淹文学世界中很多景观便也随之隐没在云层之下,只有《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等寥寥数峰进入后人眺望的视野。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士风”并非某种仅待认知的现成之物,而是在士风叙事中不断形塑衍变的公共记忆,不同的记述者会根据其现实环境和价值诉求凸显士风样貌的不同侧面。与他者基于士风叙事得出的士风印象相对应,被记述者自身也有对士风问题的观点,后者即本文所谓“士风观”。士风印象与士风观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任何士人对士风的观点都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而付诸实践的部分也可能在他人的记述和接受之中变形或遗忘。具体到文学领域,士风印象往往是读者赖以“知人论世”地解读作品的依据,而士风观则是指导作者写作的价值根源,两者的歧异龃龉势必影响作品的解读与接受。范仲淹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对文学不甚措意,其总体成就也稍逊于北宋诸大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对其文学领域的研究却有受士风印象支配的特点,士风叙事特有的印象式、概括式的化约机制妨碍了对其文学世界之丰富性的全面认识。从士风视角切入,不仅有助于认识到这种化约现象的存在,也可在士风印象与士风观的罅隙中觅得被忽视的线索,表现出值得关注的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