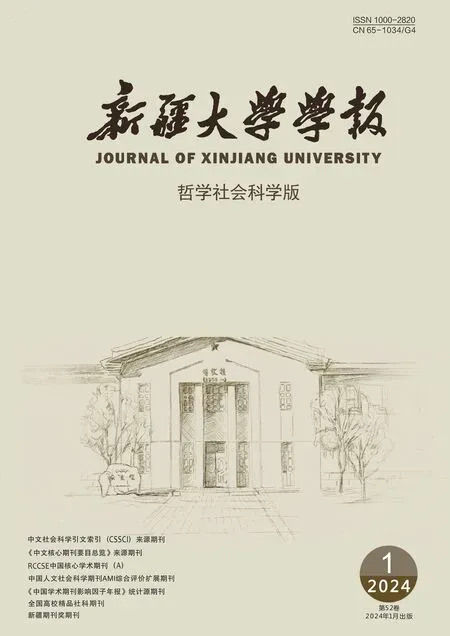边缘活力与“西游故事”的多民族叙述*
赵毓龙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21 世纪初,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重大命题,①参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5页。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中华文学“内聚外活”的文化动力系统。具体言之,“也就是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几千年发展下来都没有中断”[1]。而所谓“边缘的活力”(简称“边缘活力”),强调的是“边缘文化不是只会被动地接受,它充满活性,在有选择地接受中原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中原文化”[1]。作为一个新兴学术概念,“边缘活力”抓住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本体特征,充分肯定其在中华文学版图中的能动作用和主体地位,无论对于“中华文学史”书写,还是少数民族文学专题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中,任何一个学术概念都必然面临有关其“适用性”的核验。尤其个案研究,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契合度”是言说者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而“边缘活力”在“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研究中的适用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环绕中原的各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流中,在多民族既保有鲜明本族特色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叙述实践中,尤其在边缘地带一面吸收并反馈于中原文化,一面接纳异域文化并向中原输送的“两重滤器”作用下,庞大、丰盈、活泼的“西游故事”才得以形成。可以说,没有“边缘活力”就没有今天所看到的“西游故事”。反过来说,“西游故事”是生动反映中华文学版图内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关系的典型。
需要强调的是,“西游故事”的多民族叙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差别化的经验系统,不同板块内各民族表现出的边缘活力,在量级、时段、范围,以及对中原板块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就现有文献资料看,活力最强的是西北、西南、东南三大板块,这与北方丝路、南方丝路、海上丝路交流会通的历史空间背景相吻合,而“西游故事”正是古代“一带一路”文明碰撞、交融的产物。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为“西游故事”注入新的活力,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西北板块:故事早期演化传播的主动力
纵观“西游故事”于中华文学版图内演化传播的动态进程,“力的分布”其实一直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既是区域性的,也是时段性的。不可否认,中原板块长期充任凝聚、辐射的主动力,但从现存文献资料看,在故事早期演化传播(即由“本事”向“故事”转化)阶段,中原板块的动能并不强劲。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国,这在当时的长安士庶中引起不小轰动,但此后玄奘将全部心血倾注于译经事业,更刻意远离世俗社会。中原民众对玄奘取经事迹充满好奇,却长期缺乏“一手素材”,世俗的浪漫想象也就无所附丽。
率先将本事编译成故事的是佛教徒撰写的传记,代表性文本有释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等,但这些文本主要在佛教徒集团内部流通,形成“互文”叙事,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很有限。玄奘口述、辩机记录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倒是在中原世俗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为文士集体“征异话奇”提供了丰富材料,①参见何红艳《〈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39页。但文士们的兴趣点在于转述、再造书中的异域“知识”,而非以之为事件群,串联起一个以玄奘为主人公的“取经故事”。
从现存资料看,直到晚唐,中原世俗社会流传的玄奘故事基本停留于《独异志》中入维摩诘方丈室、摩顶松、观音授《心经》等条目的形态——本身是粗陈梗概的,彼此间也无关联。可以说,有唐一代中原地区始终未能产出一个以玄奘为主人公、以降妖伏魔为主体事件的通俗化“取经故事”。
及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取经诗话》),通俗化的“取经故事”才出现,而这部关键文本也将学界视点直接拉向西北多民族地区。
有关《取经诗话》的成书时地与文本性质,李时人、蔡镜浩、蔡铁鹰等人已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证,并得出趋同的结论:该书应是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敦煌一带)的俗讲底本。②参见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22-30 页;蔡铁鹰《〈取经诗话〉的成书及故事系统——孙悟空形象探源》,《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67页。尽管近年有学者指出现存版本所呈现的“历史时代的多层性”,③参见陈引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时代性再议:以韵文体制的考察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71页。但这些应该是文本传播、刊刻过程中的时代“沉淀物”,不影响我们对其所据故事主体形态“历史断层”的判断。《取经诗话》足以证明在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已然存在一个以唐僧(未必是玄奘)为主人公,以降妖伏魔为主体事件的通俗化“取经故事”。
以此为支点,在整合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蔡铁鹰提出《西游记》研究“视点西移”的主张,引导学界将目光投向“由‘西域’这个概念扭结起来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领域”[2]。笔者支持“视点西移”,但不主张泛用“西域”这一概念,而是更倾向将聚焦范围集中于中华文学版图,将聚焦点落在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多民族地区,考察其构造、传播早期“取经故事”的活力。
吴刚在讨论中华多民族文学交融现象时,提出其局部交融的三个层次:一是以中原汉文学为中心的内层交融点,二是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的中层交融点,三是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的外层交融点。④参见吴刚《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范畴》,《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0页。所谓“边疆”,当然是从中华地理版图角度界定的,而将其置于文化、文学交融的宏阔视野下观照,边疆多民族地区正是“外部交融”和“内部交融”的中间带。它一方面容受中原文化,又反馈于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吸纳异域文化,又在内部多民族交流、整合后向中原输送,仿佛“两重滤器”。而边缘活力正是该“滤器”功能的生动表现。
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带,历史上汉、藏、回鹘、蒙古、回、氐、羌、鲜卑、羯、党项、裕固、保安、东乡等民族长期生活于此。这里也是由河西走廊至中亚的北方丝路的重要中转地,中西文明、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此碰撞、交融、流溢、沉淀,孕育出丰富且带有文化融合特征的神话传说。同时,这里是玄奘以及众多中原僧侣和西来僧侣的驻脚地,在构造、传播“唐僧取经故事”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早有学者指出:《取经诗话》中的“唐三藏”未必是玄奘。太田辰夫、中野美代子等人认为其原型是善无畏三藏,张乘健、蔡铁鹰、杜治伟等人则认为其原型为不空三藏。⑤参见杜治伟《试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事为不空取经》,《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十四辑,第34页。这些假说有合理性。与玄奘相比,不空、善无畏更贴合《取经诗话》的密宗倾向(尤其毗沙门崇拜),而其诵咒、驱神、禳灾、祈雨等神异事迹在民间流传得也更广。这些事迹与后来的“西游故事”直接相关,玄奘事迹中却很难找到类似素材。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的密宗在晚唐五代进入“衰落而逐渐消歇”的阶段,①参见胡小伟《藏传密教与〈西游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527页。同时期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崇拜却依旧流行。②参见党燕妮《毗沙门天王信仰在敦煌的流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4页。也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西北多民族地区保持了密宗信仰的活力,而正是这股活力催生了《取经诗话》。
当然,无论不空、善无畏,还是玄奘,可能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途经敦煌的“行脚僧”形象的集合体。西北地区现存众多“唐僧取经”图像,据统计仅甘肃就有12 处,其中8 幅“携虎行脚僧图”可判定为晚唐作品。③参见霍志军《甘肃地区“唐僧取经图”与〈西游记〉》,《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2期,第153页。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行脚僧”就是玄奘(尽管后世的“玄奘取经图”确实受到这类图像影响),仅从意象看,它们可能与伏虎罗汉的关系更为密切。但这些图像可以作为实物证据,说明西北多民族地区才是“取经故事”的发源地。正如柳田国男所说:“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丘陵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3]大量“唐僧取经”图像的存在说明作为中西文明交流会通的过滤带,西北多民族地区是神异化“唐僧”形象生成、传播的核心区域。众多中外行脚僧往来、驻留于此,其事迹被不断传奇化、神异化,又经过融合、提炼,形成刻板的“唐僧”形象,相关事迹也逐渐聚合、串联成《取经诗话》的主体故事,进而在向中原回流的过程中与玄奘求法事迹相结合。
这可能是更符合历史真实的,否则无法解释在早期中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取经诗话》何以形成。我们当然仍可以假设:中原地区率先形成一个通俗化的“取经故事”,进而通过河西走廊影响西北多民族地区,但目前尚无证据支持该假设。正相反,愈来愈多文献资料证明:早期故事的演化传播得益于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边缘活力。换句话说,西北多民族地区才是故事早期演化传播的主动力。
二、西南板块:故事多民族形态的容贮器
当然,作为内、外交融中间带的多民族地区不止西北一隅,与之毗连的西南板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马旷源曾在蔡铁鹰“西移”说的基础上提出故事自“西南移来”一说,马氏自称该主张更近“戏说”,④参见马旷源《也谈西游故事研究的“视点西移”》,《西游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48页。其实颇具启发意义。
杨义在讨论边缘活力时,特别重视西南多民族地区,指出:“包括贵州、云南、川西、湘西、广西在内的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后方、后花园”,“是民族文化、语言、审美方式的仓库”[4]420。这里“仓库”的形容尤为贴切。从文化板块结构来看,西南多民族地区隶属“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⑤参见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和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6-7页。这里山高谷深,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带。各民族语言、文化保存完好,且留有明显的原始痕迹。在文学艺术方面,异域和中原文化因子在此融会,并与这里浓重的原始宗教气息和发达的神话思维结合,进而沉淀、贮存下来,形成中华文学艺术史的活化石。当我们试图发掘某个故事的多民族形态时,打开这座“仓库”的大门,总能发现不止一枚全须全尾、栩栩如生的标本。具体到“西游故事”,古彝文《西游记》就是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标本。
古彝文《西游记》于20 世纪80 年代在云南楚雄被发现,包括两部文本:《唐王书》与《唐僧取经记》,皆用古代彝族通行的音节文字书写在羊皮卷子上。从文本性质看,古彝文《西游记》属于毕摩经典。毕摩是彝族从事原始宗教活动的祭司,毕摩唱诵的经文称“毕摩特依”,汉译为毕摩经(或毕摩书),今天统称作毕摩经典。毕摩经典中有不少富于文学色彩的叙事长诗,古彝文《西游记》就是其中之一。《唐王书》讲述“魏征斩龙——唐王游地府——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的完整故事,《唐僧取经记》则从唐僧出世讲起,以之为取经缘起,继而叙述取经路上遭遇和最终成果,以“吴查卖查经”的传世收束全书。
有学者认为古彝文《西游记》是对明以后某部汉文祖本的改译,而这部汉文祖本是由汉族移民带入云南地区的。①参见张菊玲、伍佳《新近发现的古彝文〈西游记〉》,《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第72页。该结论与传统文学史中汉族文学辐射影响的刻板印象相适应,也符合近古时期彝族毕摩吸收汉族故事的一般规律。明中叶以后,朝廷加大对“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彝族传统社会“兹—毕—莫”三位一体的上层建筑随之瓦解,毕摩的文化地位下移,更多地参与到日常生产、生活中去,在与彝族儒学知识分子的交流中,“学识较高又有心的一部分毕摩,将从彝族儒学知识分子那里听到的一些用彝语表述的汉民族故事、传说等用彝文翻译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批译著”[5]。而彝族知识分子所据汉族故事,很可能是由汉族移民带入川、滇、黔、桂地区的。像毕摩经典中的“包公故事”“董永故事”“张四姐故事”等汉族故事,应该就是由此路径流入并沉淀下来的。
然而,“西游故事”从来不是纯粹的汉族故事,多地域、多民族宗教仪式引入“西游故事”的动机,也并非“嵌入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是承担重要的“释源”功能。侯冲在研究广泛流布于湘、鄂、桂、贵、陇、闽、鲁等地的佛教科仪宝卷《佛门请经科》时指出:“《佛门请经科》及与之相关的唐僧取经故事,它们出现在斋供仪式中的原因,是为了说明道场所用经是唐僧从西天请来的。”[6]这为斋供文本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提供了保障。古彝文《西游记》里的取经故事也承担该功能,只不过取来的不是佛经,而是毕摩所用“吴查十二部,卖查十二部,共一百二十查”[7]。既然涉及毕摩经典的来源问题,应该不会是很晚才发生的。
更重要的是,古彝文《西游记》所据故事的形态与明以后中原地区定型的故事有明显不同。首先,从取经团队构成看。明以后“五圣”的构成已经确立,如王进驹所言:“此一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以三藏、孙行者、朱八戒、沙和尚、火龙马为主的取经队伍开始确立下来。”[8]而古彝文《西游记》的取经团队只有唐僧、孙行者和猪八戒,龙马形象完全隐去,沙和尚虽出场,却是唐僧的抚养者,并告知其西天有经,之后再未出现。其次,从主人公名号看。齐裕焜指出孙悟空名号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宋代猴行者阶段、元明之际齐天大圣与通天大圣混用阶段、明中叶后齐天大圣专属于孙悟空阶段。②参见齐裕焜《〈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从福建顺昌宝山的“双圣神位”谈起》,《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62页。古彝文《西游记》通篇只称“孙行者”,找不到“大圣”“悟空”的痕迹。由此看来,古彝文《西游记》应该不是对明以后某部汉文祖本的改编和翻译,其所据故事的“历史断层”可能更早。
从通篇称呼“孙行者”的这一方向思考,古彝文《西游记》可能受到西北板块《取经诗话》的影响,但还有一条更便捷的路线:通过川滇缅印通道,由南亚传入。尽管关于孙悟空原型的“本土说”与“外来说”至今仍争讼不止,但不可否认“猴行者”身上有《罗摩衍那》中哈奴曼的影子。而《罗摩衍那》传入中国不止北方丝路一条途径,季羡林早已指出:“在八、九世纪以后,《罗摩衍那》已逐渐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从这一带再传入中国,是比较方便的。”[9]之所以方便,就因为川滇缅印通道的存在。
该通道向北可经由巴蜀连接陇、陕、青等地,向东可连接桂、粤等地。更重要的是,该通道是“藏彝走廊”南出口,可通过“走廊”与北丝绸之路沟通。
“猴行者”形象由该通道传入,又可与当地原始信仰中的“猴祖记忆”相结合。石硕曾指出:“藏缅语民族的祖源记忆中普遍存在着以猴为始祖或以猴为图腾崇拜的记忆、神话传说与文化痕迹”,“几乎覆盖了藏缅语所包括的各个语支的民族”[10]48。其他民族不论,仅就彝族而言。彝文典籍《勒俄特依》解释彝族起源于雪,而在雪的十二种子孙中,“猴”是最接近“人”的一种。楚雄地区流传的彝族创世史诗《门咪间扎节》中更明确有《猴子变成人》一章。此外,在彝族各类文献典籍、口传故事、传统艺术和民俗仪式中,保留着大量有关“猴子变人”的内容。③参见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3页。“猴祖记忆”无疑有利于“猴行者”形象在西南多民族地区的接受与传播,而这种原始信仰正是西南板块边缘活力的体现。
同时,西南板块的边缘活力也突出地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叙述实践。如古彝文《西游记》交代泾河龙王结局,由唐王提议,令其化作彩虹,而这一带有神话思维的情节也可在其他少数民族叙述中见到,白族打歌《洪荒时代》同样叙述了“斩龙故事”,盘古盘生兄弟斩杀恶龙后,叙述者唱道:“龙王死后变什么?龙王死后变成虹。”①参见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第一辑,1981年,第245页。再如古彝文《西游记》通天河一段,有红鱼吞没经书的情节,这可能是将“老白鼋”与“鲤鱼精”捏合为一了,而壮族师公经《西游记》有类似桥段:“鲤鱼变化下里海,连经(文)连教次又湿,连人连马次又沉(下去)。”[11]又如古彝文《西游记》里唐僧师徒遭遇的妖魔主要是牛魔王(占全书绝大篇幅),足见其形象之突出,而彝族毕摩与藏彝走廊民族原始宗教“苯”存在渊源关系,②参见朱文旭《论彝族和藏彝走廊民族“毕”原始宗教关系》,《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第23-28页。藏地至今有“打牛魔王”的仪式剧,③参见康保成《藏族仪式剧〈打牛魔王〉考略》,《学术研究》,2013年第12期,第136-143页。其中或有因缘联系。
总之,西南多民族地区是“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另一股边缘活力,由于该地区的故事长期以口承形态在各民族流传,今日所见纸质(尤其汉译)文献又基本是近古以来的文本,目前尚难确定西南板块在故事早期发育演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叙事中,西南板块保存了故事早期形态的活化石。
三、东南板块:海陆文明交融中的边缘活力
讨论“西游故事”在中华文学版图内的演化传播,东南地区是不可阙略的一块拼图。尤其福建地区的“大圣”信仰,它是推动元明时期孙悟空形象完善、定型的一股重要的边缘活力。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福州地区生成于百回本之前的文献,主要是汉族叙事实践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将其视作一股边缘活力,它与西北板块一样发挥了“两重滤器”的功能,一方面容受中原文化,一方面吸收域外文化,又与当地信仰相结合,进而向中原输送。所不同的是,闽地的域外文化主要是乘海风而来的。
就孙悟空形象的域外因子而言,哈奴曼形象传入中国本就有西北、西南、东南三条途径。前两条是陆路,后一条是海路。中野美代子曾结合泉州开元寺西塔第四层壁面上的猴形神将浮雕,推测通过海上丝路传入泉州的《罗摩衍那》“在以福建为中心进行渗透时,给予既存的‘求法的猴’形象以刺激”[12]。考虑到宋元时期泉州在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地位,《罗摩衍那》由海路传入福建地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此说并不否认闽地当时可能已存在“求法猴”形象,毕竟相较于河西走廊与川滇缅印通道,海路开通较晚,《罗摩衍那》由南海传入福建以前,当地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容受了北方的“求法猴”形象。
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时代之早晚,而是经由不同路线传入的域外神猴形象,在通过不同板块边缘活力的“滤器”时,经历了不同的“滤网”,即地域信仰。
由西北、西南陆路传入的神猴形象,在进入西部多民族地区时,与当地普遍存在的“猴祖记忆”相结合,进而形成“善相”的“求法猴”形象。王小盾曾指出:汉藏语族(包括羌、藏、景颇、缅、彝等语支和语组)各民族中普遍存在具有原始信仰涵义的猴祖神话,按其主题可分为猴祖创造人类、婚配育人、物种进化、灵猴等四类。④参见王小盾《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52页。这些神话主体上属于起源神话,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则是更为原始的图腾崇拜。而进入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时代后,“猴祖记忆”依旧生动鲜活地保存在西部各民族叙事中,“猴祖”或直接或间接地创作了人类,孕育了人类,庇护了人类,为部族繁衍和生产生活做出重要贡献,甚至牺牲生命。这类具有“英雄”色彩的猿猴形象普遍存在于西部各民族的口头故事中,成为域外神猴传入并向中原渗透的“滤网”。蔡铁鹰在探讨“猴行者”形象时指出:“古羌人的猿猴故事可以看作是《取经诗话》产生于西北地区的重要文化背景。”[13]是极有见地的,但今天看来似乎可以将视阈进一步扩大,由西北延及西南,即由“藏彝走廊”联结起来的南、北丝路所覆盖的多民族地带,无论域外神猴形象从哪一路传入,都需要与西部多民族口承叙事中的“猴祖”形象融合。
由海路传入的神猴形象则与福建地区的“大圣”信仰相结合,形成以“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为代表的猿猴家族,进而定型为“齐天大圣孙悟空”。清人笔记中已提及闽地“大圣”信仰之盛,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即称:“闽楚多齐天大圣庙。”[1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更是以闽地齐天大圣信仰为背景敷演故事。⑤参见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59-1463页。早期,学界基于“中原汉族文学辐射影响”的刻板印象,多将其视作百回本小说影响下的产物。20 世纪90 年代,福建地区发现一系列与“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相关的文物,不少文物的历史断代在元明时期,基本都在金陵世德堂刊本《西游记》问世之前。①参见王益民《孙悟空的原籍可能在福建宝山》,《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30-34页;王枝忠、苗健青、王益民《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68-71页。这与中野美代子的推测形成呼应,孙悟空“祖籍”在福建之说成为一时热点。
其实,中古时期福建地区就已存在猴王崇拜,与西北多民族地带的“猴祖记忆”不同,闽地猴王崇拜更多出于民众的畏惧心理。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六记载福州永福县能仁寺中猴王作祟,波及“福泉南剑兴化四郡界”,以致“祠者益众,祭血未尝一日干”[15]。与西北地区基于原始信仰的猿猴崇拜形成对比。这种猴王崇拜心理又与当时民间流行的瑜伽教相结合,形成善于福祸人的“通天大圣”“齐天大圣”形象。
瑜伽教源于佛教密宗,北宋时已在福建流行。南宋以后,该派法师以云游形式活跃于乡土社会,成为提供禳灾、超度等宗教服务的民间仪式专家。②参见李志鸿《宋元新道法与福建的“瑜伽教”》,《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8页。两宋之际福州永福县的张圣者就是瑜伽教重要信仰人物之一。张世南《宦游纪闻》记录张圣者所作赞语,有“苦海波中猴行复;沉毛江上马驰前”一句。学界多以之为《取经诗话》南传的证据,但考虑到张圣者的地域和宗教背景,这里的“猴行者”可能由海路而来,且与瑜伽教各种号称“大圣”的通俗化神祇有关。③参见徐晓望《论瑜珈教与〈西游记〉的众神世界》,《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第39-40页。
按瑜伽教神谱中有不少“大圣”,如猪头大圣、象山大圣等。这些“大圣”(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造神程式)通过民间宗教仪式广泛传播,又与闽地固有的猿猴崇拜相结合,形成“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等猴形神祇,最终定型为“齐天大圣孙悟空”,完善了主人公“妖仙”“凶顽”“叛逆”等形象侧面。北方的“猴行者”本无“大圣”名号,是虔诚的求法扈从,而元明时期的故事里已可见以“大圣”为核心的妖猴家族,如拟话本《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称申阳公“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16],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齐天大圣有兄长,号“通天大圣”[17]12,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则自称“通天大圣”,兄长号“齐天大圣”[17]70。这应该是闽地“大圣”信仰发挥边缘活力的产物。
尽管这股边缘活力一度引起学界注意,但一直缺少足以证明宋元时期闽地流传自成系统之“西游故事”的可靠文本,直至胡胜将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纳入考察视野,判断其所据故事的“历史断层”在《取经诗话》之后,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同时或更早,是宋元间《西游记》的标志性作品之一。④参见胡胜《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第65页。补足了证据链的缺口,福建地区的边缘活力又得以被重估。
四、北方少数民族为故事注入的新活力
在沿“乚”形空间线索考察过西北、西南、东南板块的边缘活力后,我们可将视点移至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的东北隅,讨论北方少数民族对“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影响。
由于尚未发现可靠的文本证据,目前还难以确定百回本成书前该地区是否存在独立稳定的故事系统,现存文本基本是对明以后某部汉文祖本的改译,如阿日那蒙古文《西游记》、无名氏回鹘体蒙古文《孙悟空故事第一回》、康熙间满文《西游记》等,但这不代表北方少数民族只是被动接受中原故事系统。正相反,在军事征伐、政权变更的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故事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其有别于中原汉族文化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为中原故事系统注入了新活力,使其朝着世俗化、世情化、戏谑化、游戏化方向发展。
杨义指出:“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而且深刻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4]273“西游故事”正可作为典型,尤其在金、元、清三代的代表性戏曲样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世情戏谑成分向“神魔”内涵的渗透。
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金代院本有《唐三藏》一种(另有《蟠桃会》一种,未必演述“闹天宫故事”,可能是“王母瑶池故事”)。⑤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3页。该剧归在“和尚家门”。这是按角色职业分类,相同类目有“秀才家门”“大夫家门”“卒子家门”等。仅就类目来看,难以判断其搬演内容与体制,但从金院本的一般体制来看,应以滑稽戏谑为主。如刘晓明所说:“金代的院本,与宋杂剧相同,是一种包含多种表演形态、以笑乐滑稽为主的戏剧形式。”[18]存元明杂剧中的院本也以滑稽戏谑为主。①参见胡忌《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5-106页。再看与本剧同归在“和尚家门”的《秃丑生》《窗下僧》等,由剧名即可知其中含有谐谑成分,这些成分可能伴随金院本的艺术传统和表演成规渗透进“西游故事”,对故事内质产生影响。
“西游故事”本是宗教故事、历史故事,尽管晚唐五代已实现通俗化、神魔化,世情戏谑成分却极少。故事的“吸睛”之处在于神魔赌斗变化,而非世情(甚至风情)点染、滑稽调笑。西北、西南、东南的边缘活力在此方面贡献尤少:在大宗宗教、民间宗教和原始信仰的综合作用下,“乚”形空间的多民族叙事较中原更加严肃。而相对保守的中原汉族文化圈反倒在故事的宗教、历史底色之上抹出别样的油彩,主要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带来的新活力。金院本《唐三藏》内容已难考证,元代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却留有残折,其中《回回迎僧》一折以滑稽笑乐为主,曲文诙谐,老回僧、小回僧插科打诨,颇有“院本”遗风。元末明初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更是完整保存下来。该剧市井气格外重,尤其不吝于渲染情色。从人物形象看,孙行者一身“流氓”习气,动辄以污词秽语自我标榜。唐三藏形象也被解构,第六出《村姑演说》中胖姑儿唱【一緺儿麻】,以旁观者身份形容道:“官人每簇捧着个大擂椎,擂椎上天生得有眼共眉。”[17]64带有明显的性暗示。从情节看,第十七出《女王逼配》成为重要“戏点”,女儿国王之淫态被细致刻画,孙行者之唱白更是猥亵露骨。而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作者也极不严肃,如第二十二出《参佛取经》,孙行者念佛经名目,在《金刚经》《心经》《莲花经》《楞伽经》后,突然冒出一个“馒头粉汤经”,取经仪式的庄重严肃顿时消解殆尽。这些内容不应被简单视作杨氏“好戏谑”的个人趣味。作为元代“西游故事”的集大成者,《西游记杂剧》反映的是故事在多民族“互嵌”的市民文化圈里的“公共形象”,而该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无疑得益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相对宽松的文艺氛围、灵活变通的伦理观和实用主义的宗教观。
这是明代汉族集大成文本生成的基础。并不是说百回本小说直接借鉴了杨本杂剧,而是明代汉族作家不仅继承了元代故事的系统,也要扬弃接受其审美风格——世俗化、世情化、戏谑化、游戏化。“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并非百回本小说作者的原创,而是在继承“游戏”态度的基础上,涤滤或淡化情色成分,以更具艺术力度的“幻笔”构造戏谑笑乐的结果。
这种“故事的变身”并未因百回本小说刊行而终止。入清后,在新的少数民族政权背景下,舞台上的“西游故事”进一步向“世情”轨道偏移。如康熙、乾隆朝编成的清宫连台本大戏《昇平宝筏》,整合前代戏本,成为舞台搬演之集大成者。从编创动机看,满族皇室和御用文人看重的仍是故事的“神魔”属性,正所谓“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19]在借文艺作品藻饰太平、炫耀国力方面,“神魔”题材作品确有天然优势。但在具体操作中,世情段落经常是重要“戏点”,如在全剧伏线最长、牵连最广的“牛魔王家族故事”中,原著幽微单薄的“摩云洞玉面狐”一段被放大、渲染,形成了以“狐狸思春”为中心的戏点。这段情节颇受满族皇室喜爱。康熙、乾隆朝以后,《昇平宝筏》结束搬演高潮,但在嘉庆、道光朝,《玉面怀春》依旧深得皇室偏爱。据《昇平署档案》载,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初一,于圆明园同乐园搬演第11 段《昇平宝筏》,期间外臣求见,道光帝下旨:“《玉面怀春》毕,站住戏。”[20]料理政务后返回同乐园,接唱《牛魔招亲》。当时正值多事之秋,道光帝仍坚持看完《玉面怀春》才处理国事,足见对此剧之偏爱。不唯皇室,民间亦爱此戏,《红楼幻梦》第14 回写到贾府搬演《火云洞》,特地提到:“接着借扇,因有《玉面狐思春》一出,又搭起花园来。”[21]清人“花谱”中也不乏因擅演玉面狐而走红者,如《燕兰小谱》记贾四儿演《狐狸思春》“如花解语,似柳传情”[22]。“西游故事”在清代的世情化(甚至风情化)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我们综合考察、分析了中华文学版图内“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边缘活力。需要强调的是,突出边缘活力并非回避、架空或解构中原板块的凝聚、辐射作用。正相反,中原动力始终是故事得以聚合成形并进一步丰盈、膨胀的核心能源,而汉族“终极文本”也确实经常作为“祖本”,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多民族地区,对当地的口承叙事产生影响,但不能由此形成边疆多民族地区简单容受汉文祖本的刻板印象。无论汉族“终极文本”形成前后,边缘板块始终发挥着能动作用,一面吸收并反馈于中原文化,一面接纳异域文化并向中原输送,推动故事在中华文学版图内的整体性交融。这种边缘活力是持久而旺盛的,其与中原凝聚力、辐射力构成的“内聚外活”的文化动力系统,是中华民族叙事原创力、包容力和生命力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