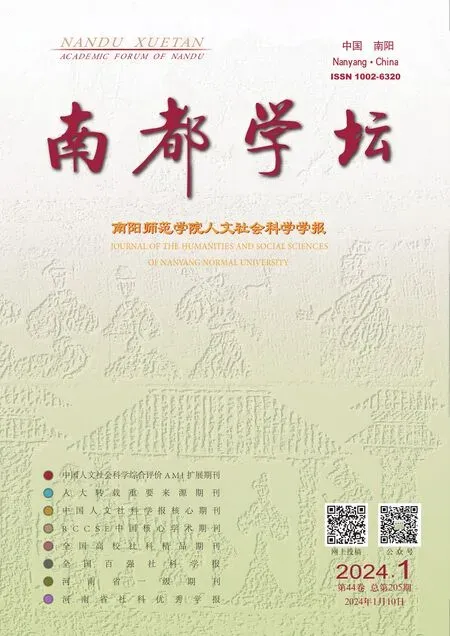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赵豫云,郭发喜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2488; 2.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梅尧臣生于宋初文风交替之际,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推动者,是中国古代诗歌由唐音转宋调的关键人物。刘克庄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1]梅尧臣一生大多时间沉于下僚、四处辗转,为官于今安徽、河南、浙江、陕西等地,有长时间的运河行旅,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和诗歌风貌。
一、运河行旅对梅诗创作的影响
近代机械化以前的中国,水路交通通常是最优选择。大运河是通联宋代京都和各路、府、州、军的一个最重要的路径或换乘路线。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四处为官是常态。漫长的运河行旅,对爱好诗艺的士人来说,作诗就成为必然。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人中并不多见。而宋代运河很多河段非自然水道,通航情况复杂,这些都影响了梅诗的创作。
(一)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
汴水是北宋大运河的核心河段。梅尧臣“一生七次进京并在京居住多年”[2],“汴河是梅尧臣主要的行踪路线,其仕途生涯也主要围绕运河展开”[3]。
汴河水源多引自黄河水(按:北宋元丰年间亦有引洛水),而黄河水有涨、枯。因此,汴河的最佳航行期只有半年左右,即在其水源丰盛期的三四月至十月。梅尧臣《送朱表臣职方提举运盐》诗云:“汴水桃花时,犀舟顺流发。”[4]1000《醉中留别永叔子履》中也有说:“新霜未落汴水浅,轻舸惟恐东下迟。”[4]186很明显地反映出汴河水的荣枯。汴河航运的顺水、阻风、阻冻、泊舟等情况增加了梅尧臣诗歌的创作量。
唐宋时期官员的运河行旅中,月余时间的长途行程较为常见。在现存梅尧臣3千首左右的诗歌(皆为其30岁后所作)里, 纪行诗就“有四五百首之多, 占全部诗作的六分之一左右,而且时间跨度非常之大, 除了最后的三四年没有纪行之作外, 几乎贯穿了诗人的一生”[5]。梅尧臣的纪行诗特别是其中的运河纪行诗,不仅增加了梅诗的总量,而且开创了宋代纪行诗的先河,对梅尧臣诗歌的风格形成也具重要意义。
(二)运河行旅对梅诗题材的影响
首先,运河行旅扩大了梅诗的题材。“顺风”行船令人心情开朗,洋溢在梅尧臣诗作之中。“汴中春絮乱,淮上鲚鱼时。顺水疾奔马,出都犹脱羁”[4]610是梅尧臣想象友人从京城到淮河的汴河行旅。“与君同川途,舟发偶后先。顺风吹我帆,已过飞鸟前”[4]849则是描写他从扬州至淮安的江淮运河行程。
但往来运河的船只也时常受到风浪影响,速度变慢,耗时增多,行船异常艰难,甚至需要临时祭祀水神(1)参见张聪著,李文锋译《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4页:“宋代旅行者相信,他们的安全旅行不能简单地依赖运气。在旅途开始前和旅途中,他们和船员们经常要祈求法力或大或小的神灵的保佑。”。如《庙子湾辞》:
我之东来兮过彼雍丘,舟师奏功兮浊水湍流。……潜伏怪物兮深幽幽,发作暴涨兮为潮头。土人立祠兮在彼沙洲,老木苍苍兮蝉噪啾啾。……胸荡肩挨同轭牛,足进复退不得休。[4]123
叙述的是梅尧臣于景祐五年(1038)解建德县(今安徽东至县)令任,入汴京途中的一段见闻。庙子湾在今河南杞县西,位于北宋汴河沿岸。汴河湍急,水位暴涨,漕运队伍为求早些通航不得不举办祭祀活动。
许多宋代文人因畏惧鞍马劳顿之苦,本可陆行的往往也舍陆路取水路。但运河行役中常遇风波之险,行船困难,这令诗人们十分倦怠、烦闷,乃至形诸笔墨。梅诗:“晓出淮口时,夜来风已止。半路逢怒号,客心愁欲死。”[4]852该诗作于泗州(今江苏盱眙)。汴河沿线的《雍丘遇雨》(雍丘即今河南杞县):“日暮风雨急,逆水舟难牵。波波入杞国,悄悄谁忧天。”[4]876亦是如此。
汴河航线历来繁忙,但“汴河处在秦岭——淮河零度等温线北侧,所以每值冬季就有凌汛”[6]144。唐人杜牧早有著名的《汴河阻冻》诗。梅尧臣亦有《答再和》:“舟行才及二三里,已复浅流如冻河。”[4]862反映的也是这种情况。
另外,逢汴河的枯水期,河水变浅,舟行速度变慢甚至需要停船靠岸,同样使得运河行旅极不愉快,梅诗有:“暮春溯汴汴流涩,自假轻航去如走。千忧万阻经灵壁,留书津吏情何厚。”[4]873亦有《依韵和表臣闻与挺之宣叔平甫饮》云:“舟浅不能进,反羡车马驰。”[4]857又有:“泛淮忌水大,我行浩以漫。溯汴忌水浅,我行几以干。”[4]855这些皆是对当时逆流汴河行舟的运河水文状况的绝佳概括。唐宋时期,“水上行舟,顺水比陆路快,逆流则慢多了”[6]139。据严耕望考证,隋唐大运河中汴河顺流日航约70里,逆水约40-50里(2)此观点参见严耕望著《隋唐通济渠在交通上之功能》,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1卷,1990年。。
一般来说运河航线较为舒适,但遇到极端情况如天气和水文的异常,时常要在中途停泊,从事各种活动,延长了旅行时间,有的甚至长达数月。运河航行中的遇阻、遇风等特殊情况,带来大量无聊时光,也让诗人们以诗遣兴,增加了诗材,如《宿州河亭书事》:
远泛千里舟,暂向郊亭泊。观物趣无穷,适情吟有托。林中鸦舅狞,席上蝇虎攫。雨久草苗盛,田芜瓜蔓弱。……少年都下来,聊问时所作。[4]121
此诗叙述的是梅尧臣在景祐五年,离建德县任,舟行于去汴京的路上,因故泊船于宿州郊野外的一段岸行见闻。运河远行令人疲倦,此刻的逗留郊亭显然助推了他的诗兴,满怀兴致和好奇下船观察宿州汴河沿岸的景物,甚至“乌鸦”“苍蝇”等凡俗之物。梅尧臣泊舟时有时候还趁机会友,如《泊姑熟江口邀刁景纯相见》诗等,这些都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
其次,运河行旅及“伤悼诗”的创作对梅诗的选材影响深远。梅尧臣“伤悼诗”不仅有古典诗歌中专指悼念亡妻的“悼亡诗”,还包括悼念亲人、朋友的诗作。梅尧臣的原配谢氏和次子(小名十十)在同年同月先后离世。庆历四年(1044)四月,梅尧臣结束吴兴(今湖州)监税官的两年任期,解任暂归宣城。五月,取运河携家北上。七月七日,舟次高邮三沟(今属扬州市江都区),其妻谢氏逝于船中并临时葬于润州(今镇江)(3)宣城《梅氏宗谱》载,其子梅增后奉母柩归葬宣城双羊山,与尧臣同穴。谢氏为望族之后,与梅尧臣共生二子一女,梅增小名秀叔为长子,次子小名十十因早夭而无大名。。他著名的《悼亡》(三首其一)诗云:“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4]245感情真挚、措辞坦率。谢氏刚病故,次子尚在(或已染重疾)。官命在身,梅尧臣不得不行船驶往汴京,再作《秋日舟中有感》白描亡妻音容笑貌,褒扬谢氏重在其贤德品性。他反对西昆体,摒弃华丽辞藻,其伤悼诗中的平白陈述可谓本色作诗,更有至真的情感注入。而且从梅尧臣伤悼诗的数量和情感的持久度上看,较之以往的大诗人而言也是空前的。
庆历四年七月,梅尧臣继续溯运河行至符离(按:宋时县名,今安徽宿州符离集)时,不幸接踵而至,其次子十十夭折,亦死于运河行程中。他作《书哀》诗悼念亡子,朴实无华,令人动容。庆历五年(1045),又有纪念次子的《悼子》:
舟行次符离,我子死阿十。临之但惊迷,至伤反无泣。……前时丧尔母,追恨尚无及。[4]286
生活状态暂时安定后,梅尧臣开始追忆庆历四年的丧子之痛。那年沿汴河北行停靠符离,失去谢氏已使他肝肠寸断,年幼的次子又紧随母亲而逝,真是祸不单行。
庆历六年(1046),梅尧臣在许昌任签书判官。这年秋天曾至汴京,续娶刁氏。这一年他的悼亡诗实皆为追忆运河行旅之作,如追忆庆历四年自湖州归汴京之行的《忆吴松江晚泊》《忆将渡扬子江》。还有回想他和谢氏数年前经运河赴湖州任的《元日》诗:“昔遇风雪时,孤舟泊吴埭。……何当往京口,竹里剪荒秽。”[4]326直述往日生活情景,自然、深沉。
庆历八年(1048),梅尧臣被授国子博士、绯衣银鱼后,衣锦还乡,率刁氏归宣城。他依旧走的是汴河和江淮运河,在宝应和高邮三沟作诗3首悼念谢氏。这年夏天作于南下回乡行程中的《杂诗绝句十七首》(其十二)云:“前时双鸳鸯,失雌鸣不已。今更作双来,还悲旧流水。”[4]456并自注乃作于高邮北的宝应道中。不久,再过三沟,回忆起四年前妻子的亡故,又作《五月二十四日过高邮三沟》。省亲完回汴京的船上,梅尧臣又一次路过高邮,再作《八月二十二日回过三沟》,时值晚秋,再过伤心地,惆怅满怀。庆历八年的梅尧臣因省亲,两次经行运河、往返汴京,是其诗歌创作最多的一年,存诗达277首,途中写有大量纪行诗,“几乎可以构成完密的旅行日记”[7]136。 重回故地以及长时间的运河旅行增强了梅尧臣对亡妻的思念,因运河行旅而产生并持续创作的伤悼诗也是其最成功的一部分作品。
除前述“悼亡诗”和“悼子诗”外,梅尧臣运河行旅诗中还有一些是悼念友人和嫡母的。庆历五年六月,梅尧臣从汴京赴许州签书判官任,由运河水道“惠民河”(4)许州即今河南许昌,北宋元丰年间升颍昌府,其地在开封西南,汴京至许州治所最近水路为“惠民河”,可直通。赴许州,作《开封古城阻浅闻永叔丧女》:
去年我丧子与妻,君闻我悲尝俛眉。今年我闻君丧女,野岸孤坐还增思。……自古寿夭不可诘,天高杳杳谁主之。[4]302
适逢运河水浅,舟行受阻,不得不停留而无趣的“野岸孤坐”。此时欧阳修在滁州,梅尧臣收到了他丧女的噩耗,想起自己前一年的妻亡子殇,表达了生命无常的同哀之情。
皇祐五年(1053),梅尧臣监永济仓。这年秋天,其嫡母束氏卒于汴京。他解官居忧,并沿汴河扶榇归宣城。当行至宁陵时,因遇风雨,舟行受阻,有《宁陵阻风雨寄都下亲旧》:
独扶慈母丧,泪与河水流。……母当临终时,嘱我贫莫羞。……三日违大梁,两宿此迟留。[4]703
宋时宁陵县在今商丘西,临近开封,写诗以代书信。舟行至盱眙汴口时,又作《过淮》:“侍亲数数来浮汴,护榇迢迢复渡淮。”[4]704叙述护榇回乡的心绪。
运河行旅及“伤悼诗”的创作对梅尧臣的诗歌选材影响深远。庆历四年在高邮、宿州发生的妻死子丧之痛,对梅尧臣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是终生性的。“在这一年之前,他几乎没有说过家人的事情。妻子、子女、父母兄弟的事情几乎都没有在诗里写过。”[8]在庆历四年写作伤悼诗以前,其写家庭和生活琐事的仅有庆历二年(1042)经汴河赴湖州监税任上,泊于润州度岁而作的《岁日旅泊家人相与为寿》。他之前的诗歌取材大多为官吏生活、周围友人、讥讽时事,家族、家庭题材尚无积极摄入。然而,亲人于运河行程中不幸离世后,亡妻的过往、死去的儿子以及健在子女的琐事,开始频繁、大量地在其诗中被追忆、歌咏。
原配谢氏更不时进入梦中。如庆历五年他在许昌签书判官任上作的《梦感》、庆历六年作的《梦睹》《梦觉》诗。梅尧臣在汴京的元夜佳节又有《正月十五夜出回》,将丧妻之痛转化为对“孤稚”的关爱。自此以后,他更加频繁地吟咏子女,乃至事无巨细,特别是庆历六年所作《秀叔头虱》等对日常生活琐屑不雅情事的描绘,乃是宋诗史上在诗歌选材上的“细大不捐,美丑不遗,雅俗不弃”[9],是追求创新的尝试。
经历决定气质,影响文学创作。已有研究者论及梅尧臣打破北宋诗坛陶渊明(陶诗的真率自然之风)接受的微澜偶泛,开启了陶诗接受的新局面也与他的运河经历、伤悼诗的创作相关:“在人到中年之时经历了丧妻丧子又丧友的巨大人生悲剧,为克服悲痛,他决定以冷静理性为应对策略。这一经历直接影响了梅尧臣的创作,不但增加了其诗的理性气息,亦引他将目光投向寓于陶渊明诗作中的平淡之风,并在与欧阳修的互动中于理论层面对‘平淡’风格进行总结与拔高,目‘平淡’为诗歌创作的最高最难之极境。……一方面大力学习陶诗的风格,一方面吸取韩孟诗派的奇险特点,熔铸出了平淡而老健的独特风格。”[10]
梅尧臣伤悼诗选材几乎皆属日常家庭生活,于平凡中见真感情,“常能在朴质的笔调中见出深挚的效果”[7]146,平淡而深邃。他“选择家庭生活题材,并把这些日常琐屑小事写得饶有兴味,为宋诗开辟了贴近日常生活的走向”[11]。从梅尧臣伤悼诗中可见运河行旅对其情感影响之深远,运河使梅诗吟咏的对象更趋向了家庭、日常等细微题材。
(三)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
北宋胡瑗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12]“宋代士大夫除了从他们的旅行经历中获得道德情操上的历练,他们也把观光活动视为拓宽视野和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13]224
因此,宋代士人的运河羁旅行役,动辄数日、数十日乃至月余,劳累奔波,路上遇到的种种变故,一方面深刻影响到了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创作、增加了各色题材;另一方面,他们吟咏唱和的同时,甚至不少也在刻意地锻炼诗艺。“覃思精微”(见欧阳修《六一诗话》)、视诗为人生功业的梅尧臣在运河行旅中刻苦作诗,有颇类唐人李贺“诗囊”的“诗袋”传说。刘延世编《孙公谈圃》载有北宋人孙升曾亲见梅尧臣北行汴河途中日作一诗的情形:
公昔与杜挺之、梅圣俞同舟溯汴,见圣俞吟诗,日成一篇,众莫能和。因密伺圣俞如何作诗,盖寝食游观,未尝不吟讽思索也。时时于坐上,忽引去,奋笔书一小纸,纳算袋中。同舟窃取而观,皆诗句也。或半联,或一字,他日作诗,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乃算袋中所书也。[14]
这典型地说明了运河长途航行使诗材变得凡近多样,人的感官始终处于新鲜感状态,才有可能做到日作一诗。这不仅有利于梅尧臣打发无聊时光,也在闲暇期间的锻炼词句、反复推敲之中提高了诗艺,甚至对他“平淡邃美”诗风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运河对梅诗风格的影响
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等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平淡邃美”(见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是指以平实质朴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社会现实内容,是一种外枯而内美的艺术风格。梅尧臣开启了北宋以“平淡”论诗的先河,是宋诗“平淡美”开始成熟发展的发端人物。作为诗学概念的“平淡”其涵义非常复杂,“‘平淡’是宋人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15]。梅尧臣的“平淡”,大体可认为是“通过古淡朴素的语言表达诗人平和雅正的性情”[16],是谢绝夸饰、大巧若拙,是融西湖之韶秀与夔州之险峻为一体的“平淡”,是宋人最强的时代审美理想。
另外,梅尧臣作诗在创作方法上又“转益多师”,其早年学贾岛、孟郊,中期效法陶渊明、韩愈,终在晚期自成一体。这是他在艺术上受中唐以迄宋初“清奇僻苦诗风长期流行,深刻影响”[7]144的结果,也与他长期作为下层官员的仕宦漂泊和运河行旅之苦有关。
(一)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风格
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游记、以诗评论诗书画等诗歌散文化的表现形式,并非梅尧臣首创,但他却是北宋前期将之贯彻最为彻底的一位大诗人,扩大了诗歌的功能并使诗的内容和题材日趋宽广。“在宋代早期的诗歌中,梅尧臣‘以诗代文’现象较为突出,给后世诗坛以较大的影响。”[17]
梅诗开启宋诗新貌的一个表征是其写日常生活题材的那些散文化、日记体的诗作。他用散文句法入诗,加大诗的叙述成分,改变了当时诗歌的一些传统功能,开宋诗一代之新面目,被刘克庄誉为宋诗之“开山祖师”。而运河行旅则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和口语化。
首先,运河行旅与梅尧臣的“以诗代书信”。梅尧臣作于庆历元年(1041)的《汴水斗减舟不能进因寄彦国舍人》:
朝落几寸水,暮长几寸沙。深滩鳌背出,浅浪龙鳞斜。秋风忽又恶,越舫嗟初阁。坐想掖垣人,犹如在寥廓。[4]187
诗题已点明“寄彦国舍人”,此时他在秋后离开汴京,经汴河赴湖州监税任的途中,由于入秋水文情况骤变(按:汴河主要水源为黄河,在十月后丰水期结束),水浅后水的流速变慢,便有诗中“暮长几寸沙”、舟行受阻的情况。类似现代生活中“堵车”一样,焦急的等待让梅尧臣“以诗代信”寄语友人。又有《代书寄王道粹学士》:
写于嘉祐元年(1056),是梅氏在居丧(丁嫡母忧)期满、返程回汴京补国子监直讲,于泗州逗留时,寄给王道粹而作。诗题直接点明“代书”,叙述因下雨不能行舟、不能如约拜访,以及期待下次赴约。虽谈不上有什么诗境,但也确实达到了书信的功用。
庆历八年(1048)梅尧臣所写的《宿邵埭闻雨因买藕芡人回呈永叔》:
秋雨雁来急,夜舟人未眠。乱风灯不定,暝色树相连。寒屋猛添响,湿窗愁打穿。明朝持藕使,书此寄公前。[4]469
作于他被授国子博士、绯衣银鱼后,率刁氏归宣城,夜晚时舟行邵埭(即扬州邵伯埭),失眠而作。此外,还有《发丹阳后寄徐元舆》等皆为作诗而将其功能局限于书信,仅起汇报自己行踪的作用,诗风皆淡而无华。
其次,运河与梅尧臣诗中的“日记体”。在宋代,“日记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裁”[13]214。不同文体之间又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日记体诗在北宋迅速发展。“梅尧臣在日记体诗的写作上,亦可谓是宋人的先行者。”[18]除了以诗代书信外,梅尧臣运河诗中的“日记”体,散文化风格浓厚,重视日常,语言平淡,有些甚至近于口语。
胡适说宋人真正实现了用口语作诗,是为的论,由宋型诗歌的主要开创者梅尧臣的一些“日记体”运河诗即可管窥。如梅尧臣作于嘉祐元年(1056)扬州至汴京归途舟中的《倡妪叹》:“万钱买尔身,千钱买尔笑。老笑空媚人,笑死人不要。”[4]866庆历六年又作《孙曼叔暮行汴上见鹘击蝙蝠以去语于予》云:“小鸟不入眼,拳发强弩机”“休笑老鸱饱,衔得腐鼠归。”[4]357较典型者另有《设脍示坐客》云:
汴河西引黄河枝,黄流未冻鲤鱼肥。……我家少妇磨宝刀,破鳞奋鬐如欲飞。萧萧云叶落盘面,粟粟霜卜为缕衣。[4]577
皇祐三年(1051),梅尧臣丁父忧结束,自宣城出发抵汴京,被赐同进士出身和太常博士,该诗写于回汴京后。诗中用口语白描了加工汴河鲤鱼的过程和步骤,叙述完整,接近散文和日记。此外还有《宿洪泽》《金明池游》《瓜洲对雪欲再游金山寺家人以风波相止》等,这种以诗代日记、代散文的写法,是梅尧臣于运河沿途大量写诗、随处写诗带来的必然结果,对梅诗爱写平淡题材的取向有一定影响,进一步促成了宋诗生活化、日常化、琐细化的重要特点。
(二)运河行旅对梅诗的议论化、讽刺化风格的影响
宋诗新貌的另一个表征是诗歌的议论化,与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参与议政的时代特色有关。运河行旅对梅诗的议论化风格也有较大影响,在他的汴河政论诗中有明显表现。梅尧臣在湖州有任两年(1042—1044)的监税官,监管盐税,亦曾在汴京监永济仓一年(1052—1053),因此熟知北宋的漕运运营。梅尧臣政论诗中有10余首涉及漕运、汴渠,其中有4首主要是谈汴河,在诗中他将议论、吟咏汴河的诗歌称之为“汴渠诗”。
首先,梅尧臣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宋代已有了“漕河”“漕渠”的同义语——“运河”的称谓,但并不常用,而多分段谓之。在整个北宋时期,“诸运河的漕运中,惟汴河的地位最重要,漕运量最大”[19]762,利用率最高。故汴河在宋人的文学作品中通常可指代整个大运河。
皇祐五年(1053),梅尧臣在监永济仓任上有《永济仓书事》:
输粮来万国,积庾下千艘。貔虎肥于豢,麒麟老向槽。中州无殍饿,南土竭脂膏。黄鼠群何畏,青鸠啄且嚎。[4]691
诗中的永济仓在汴京,是汴河上的漕运仓库。北宋与西夏和辽长期军事对峙,依赖南方漕运。同时,治理运河也加重了百姓负担。此诗怒斥了统治者的奢侈和掠民。肥于豢的“貔虎”和群而不畏的“黄鼠”,乃借喻漕运使“中州无殍饿”的同时滋生了贪官污吏,也暗自表达了自己誓将不与之同流合污的气节。
其次,梅尧臣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汴河主要引黄河水,黄河的泥沙和涨落、水量的丰枯直接影响运河,使之河床抬高、时常淤积。梅尧臣《送王正仲长官》诗就说汴渠“黄流半泥沙,势浅见蹙澳”[4]574。所以,为确保运河航运畅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疏浚和日常维护,劳民的同时甚至一些官吏借机贪污,因此有利弊之议。尽管如前文所述,梅尧臣在官场生涯中看到了漕运带来的腐败,但和其他诗人毕竟不同,他了解漕运,还客观、全面地对汴河的利弊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如他在送别诗《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三首其二)中说:
汴之水,入于泗,黄流清淮为一致。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兮万人利。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实所寄。[4]279
此诗作于庆历五年(1045)春夏间在汴京候任时。宋时汴河自今河南荥阳市境受黄河水,流经郑州、开封至江苏入泗水。漕运满足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但也便利了商贸往来,有益民生。因此,梅尧臣认为汴河整体来看属利河,其《力漕篇呈发运王司封宝臣》诗是嘉祐元年(1056)在汴京补国子监直讲时所作,亦认为运河、汴河是利河,支持运河漕运。
梅尧臣能辩证地看问题,既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同时也呼吁统治者要厉行节俭,他在至和二年(1055)所作的《吴仲庶殿院寄示与吕冲之马仲涂唱和诗六篇,邀予次韵焉》其四《汴渠》中说:“闻歌汴渠劳,谩缀汴渠诗。……譬竭两川赋,岂由此水施。……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4]796梅尧臣认为运河只是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其好坏完全在于主政者的使用,他支持汴水通航,并劝其他人“非渠取膏脂”,要理性评价运河。
复次,梅尧臣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 汴河的通航,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统治者的奢侈靡费,也榨取了南方尤其是东南百姓的民脂民膏。梅尧臣很早就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如他在作于庆历七年(1047)的《送京西转运李刑部移京东转运》诗中说:“乃令山东粟,饷馈岁可保。”[4]396这年梅尧臣解许州签书判官任后至汴京。诗中就提出就近采用“山东粟”(5)北宋人所说的“山东”包括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以及河北北路的一部分,大部分在京东东路。以替代汴渠的主张。又有《送润州通判李屯田》云:“定挈传家旧图籍,漕河应莫费吴艘。”[4]967该诗作于嘉祐二年,梅尧臣在汴京任殿试参详官。其中的“漕河应莫费吴艘”也是主张就近开辟新的粮食来源以代东南漕运说,尽管不切实际,但其提出则不是偶然的。同时代的郑獬《汴河曲》也说:“秦汉都关中,厥田号衍沃。二渠如肥膏,凶年亦生谷。”“或能寻旧源,鸠工凿其陆。少缓东南民,俾之具粥。”[20]提出通过疏浚秦汉时代的关中旧渠,从西南调运粮食以缓解或替代汴河漕运,从而减轻东南百姓负担的观点。石介的《汴渠》诗甚至说:“王畿方千里,邦国用足周。尽省转运使,重封富民侯。天下无移粟,一州食一州。”[21]11主张尽量停掉运河“转运”,最好各州自给自足。这些显然皆为书生意气,因为五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逐步往东南移动了。
梅尧臣做过漕运官,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当时的诗坛领袖。梅尧臣汴河政论诗的创作丰富了他的社会现实题材诗歌,也促进了宋初诗歌议论化的发展。
此外,运河行旅对梅诗讽刺化风格的形成亦有显见的影响。为矫正宋初诗坛的糜丽之习,梅尧臣作诗强调继承《诗经》《楚辞》传统,包括对社会不平、黑暗的怨刺。他虽然是“官场上的边缘人”,具有科举时代不少士人耿直而近乎迂腐的毛病,也被当时人公认没有多少政治才能(6)这点从他虽支持庆历新政但在范仲淹主政时期并不被举荐上可以看出。参见马茂军《庆历党议与梅尧臣诗风的嬗变》评论梅尧臣:“不具备多大政治才能”“没有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是当时朋友的一致看法,不只范仲淹一人。”见《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因而长期沉于下僚。但他受教于儒家传统,关心政治与民瘼,诗才很高,常常把一些具有深意的故事带入诗歌,以此旁及政治议题或公共话题,如《晚泊观斗鸡》:
舟子抱鸡来,雄雄跱高岸。……勇颈毛逆张,怒目眦裂盰。血流何所争,死斗欲充玩。……群雄自苦战,九锡邀平乱。宝玉归大奸,干戈托奇算。[4]122
此诗歌作于景祐五年,梅尧臣解建德县任、入汴京的长途运河行程中。唐代以后斗鸡之戏已从王公贵族普及到民间。为打发时间和消遣娱乐,运河船家设立斗鸡项目于泊船时供游人观赏、赌钱。时值景祐党争,此诗托物起兴,以斗鸡隐喻党争,由斗鸡的血腥场面,归结到全国纷争,生民涂炭,徒然给野心家制造盗窃斗争果实的机会。
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运河行程中他“喜欢捕捉途中奇特之物。一方面,梅尧臣会留意行旅中看到的新奇的景物,以动物为主,如《牛背双鸲鹆》《原有禽倏鸣升遽默下》《孙曼叔暮行汴上见鹘击蝙蝠以去语于予》《鹤》《蛟》等,以及罕见的植物‘桫椤树’‘荇’等。对于常年浸润在官场的诗人来讲,山野间的一些动植物是十分罕见的,会引起诗人强烈的好奇心”[22]118。讽刺时政或流露一时之意绪的梅诗,常用“动物”题材中以往诗人罕有关注的奇崛题材,如《灵乌赋》《猛虎行》《庙子湾下作》《依韵和许待制偶书》《蝇》等诗,涉及乌鸦、虎、老蜃、斗鸡、蚂蚁、蚊、蝇等,这类诗歌在庆历党议之中和前后也皆有创作。这时期的“梅尧臣的运河文学作品反映了他‘平淡’与‘奇巧’相结合的一面”[22]115。一方面,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在选材上平淡、朴实;另一方面他的运河诗在用语上时有奇崛险怪,亦有巧妙的构思方式,选用新奇罕见的动植物题材或是瞬间的镜头。这应该是他作诗学韩、柳以及刻意求新的一个表现,但又不免流于质朴古硬、缺乏文采,有过分议论化、讽刺化的倾向,对宋初诗风的转变影响很大。
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云:“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23]日本学者前野直彬也说:“梅尧臣可称之为日常的诗人……在翻不了身的生涯中, 他不断地观察着生活的种种细节。”[24]而长期写作且跨越梅尧臣一生各个阶段的运河行旅诗或运河议题诗可谓他整个文学生涯的一个典型样本。运河行旅使梅尧臣“大力践行日课一诗法,将创作诗歌作为穷士的精神追求,使其诗题材、风格、手法等方面出现诸多新变,直接开启宋诗面貌”[25]。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三、结语
梅尧臣除晚年为官汴京和为父母守制外,一生大多在四处辗转中度过。年少时随叔父奔走四方,入仕后则为仕宦奔波,旅途所见成为梅诗重要的主题。梅尧臣一生大半时间沉沦下僚,运河见证他的喜怒哀乐,相伴他的成长。科场的失意、仕途的不遇以及妻亡子殇的苦痛,中年衣锦还乡的荣耀,皆化为作诗的动力,使他偶然中又必然地成为新一代宋诗之风的开创者。
梅尧臣的运河诗具有典型意义。梅尧臣这样的北宋官员其运河行程动辄数月,漫长的旅途使他们时常即兴吟咏,送别、酬答、纪行、怀古等不同形式的吟唱不绝如缕,锻炼诗艺的同时,使得本就大多出身下层的士人更加吟咏日常生活,也使得平民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日趋上升。不仅诗歌,包括绘画等宋代其他艺术也呈现出家庭化、生活化的倾向,这是唐宋文化之间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处于唐宋诗转型之际的梅尧臣诗,尤其是他的运河伤悼诗、纪行诗,已现出由唐入宋,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的端倪。总之,运河增加了梅尧臣的诗歌存量,影响了他的观察和体验,锻炼和发展了他的诗艺,也影响了他的诗歌题材和诗歌风格,在中国古代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