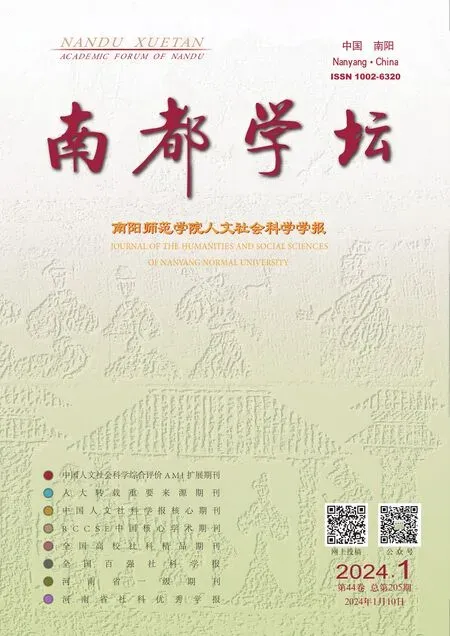启蒙与回响:鲁迅与日本的文学因缘
陈 岸 峰
(澳门城市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 澳门 999078)
青年鲁迅“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1]315寻求救民的道路。然而,幻灯片事件与日本学生对其考试成绩的质疑所造成的思想刺激,终于促使他弃医从文。显然,留日期间是鲁迅开阔眼界与吸收各国文化的黄金时光,而种种不愉快的经历却益坚定其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与探索。自从《狂人日记》发表以后,日本学界第一时间予以热情地推介,对其小说与学术的译介从不间断。由此,日本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其文坛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可谓有莫大的功劳。同样,鲁迅亦译介了日本小说,传播了当时日本的启蒙思想,并糅合日本小说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元素至其小说创作之中。
一、留日期间对革命的渴望
要了解鲁迅的启蒙思想,必须了解几段他在日本期间对革命渴望与参与的记载。
1903年3月31日,邹容、陈独秀等因江南班监督姚文甫有奸私,便“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子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2]。邹容在1903年便敢于撰写《革命军》,后来死于监狱。而陈独秀当时竟也有此激烈行动,其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就顺理成章了。鲁迅后来曾把自己剪辫和姚文甫的事综合进小说里:“我……剪掉了辫子……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3]463辫子之去留,在当时乃一件大事,关乎民族立场,亦关乎思想之进步与否。鲁迅对辫子自有其亲身经历与愤慨,在小说或杂文中亦花了不少的文字进行描写与讨论,可见此事对其刺激之巨大。三百年前留辫子是为汉奸,三百年后剪辫子一般人又以为是汉奸。由此可见,其时民智之低落。
1905年3月13日,仙台医专因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而召开祝捷会。在这前后,学校于坡形教室放映幻灯片。当中有一幅画是日本人杀中国人,据说被杀者是因为给俄国做侦探,而围观的则是一群愚昧麻木的中国人[3]416。这给鲁迅很大的刺激,此乃其产生要以文艺改变国人精神,并开始考虑中止学医等问题的直接原因。学医自是鲁迅的成长创伤,其父亲的病亦成为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一个隐喻,“救父”如救国,痛恨中医,激烈反传统,肇始于此。
1905年3月31日,第二学期结束,鲁迅动身返东京度假,半途下车,前往瞻仰朱舜水(朱之瑜,1600—1682)墓。朱氏反抗清廷,百折不挠,最后死于日本,当时应该是一批在日本怀有革命思想者的精神偶像,对于充满革命激情的鲁迅更不在话下。
由以上数则关于鲁迅在日本的活动资料可见,其革命思想正在此际萌芽,从行动而至思想上的求索,以至于其未来的事业方向,也渐露端倪。
1905年9月,鲁迅从东京回到仙台。这时,学年的成绩已经公布,鲁迅在142人中名列第68,平均分数为65.5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为59.3分。大约9月间,鲁迅收到一封很厚的信,一开头就是“你改悔罢”,“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4]。“你改悔罢”,这本是《新约》中的话,托尔斯泰在写给俄国和日本天皇的信里把这句话引了进去。该信发表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日本《平民新闻》约在8月间译载。日本的一些学生以这来讥讽鲁迅考试前已知道题目,必须“改悔”[5]。这使鲁迅感到沉痛而悲愤,因为民族的昏昧与国家的衰弱,他才招此蔑视。
二、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将“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的原因归咎于“精神沦亡”[3]99。此时,鲁迅撰写了一生中最长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全面地介绍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英国的拜伦、雪莱、彭斯,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兹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诗人,阐扬了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革命精神。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是试图以文艺作为疗救国民痼疾的手段。直到1925年他还明确指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6]因此,他自己的创作“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7]512。他明确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他说:“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8]244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的日记中都对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作了评论,他从“博观和内省”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9]326,333。鲁迅认为,以改造国民性作为救国之道,这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关键的。毫无疑问,鲁迅此举乃1644的“甲申之变”以来,当时中国思想界在扫除革命重大思想障碍上史无前例的巨大创举。
鲁迅认为,欲立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即《破恶声论》中论及的“内曜”与“心声”: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10]
“内曜”,即人之内心光亮明彻,通明洞悉。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417这一认识促使他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的观点[3]46。他甚至主张牺牲群众以发扬少数“英哲”“超人”“天才”的个性,“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3]52;“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其首在立人”[3]56-57。他盛赞拜伦等摩罗诗人,也是为了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唤起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3]99。
许寿裳回忆了他们研讨“国民性”的最初情景:
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11]59-60
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的鲁迅就认为,对于中国,“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11]60。此时,日本的几位思想家无疑成为鲁迅最直接的精神导师。例如,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有名言曰:“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植木枝盛(1858—1892)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这一著名纲领,进一步提出:“国家必须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如果人民各有自主独立的气质,发挥智慧,修养德义,专心业务,破除自卑之心,精神焕发,全心爱国,相亲相爱,团结一致,国家就不会不强,不会不盛。”[12]
在文艺方面,影响鲁迅更深的是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鲁迅在《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中说厨川白村“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8]231。收载在《鲁迅译文集》中的《出了象牙之塔》是厨川白村原著的前三篇(第一篇是《出了象牙之塔》,第二篇是《观照享乐的生活》,第三篇是《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以第一篇而论,其中第七至十四节以及十六节都是对日本国民缺陷的攻击。鲁迅认为,这是厨川白村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禁不住称快[8]242。他特别钦佩厨川白村“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8]242,以为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不容易存在,还说“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为什么旁观他人“鞭责自己”,而“痛楚”却又仿佛“到了我的身上了”呢[8]243?因为“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中国”[8]242。厨川白村对于日本的爱,多数时候是以批判与讥讽的声音来表达的,这也很投合鲁迅的习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爱,也多半是以批判与讽刺来表达的[13]126。
除却厨川白村之外,鹤见祐辅(1885—1972)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也因其对“国民性的观察”多有“明快切中的地方”[8]272,而受到鲁迅的推崇。鲁迅译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与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目的正在于促使中国的读者反省,或“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8]251,以攻中国国民的痼疾。例如,在面对西方威胁引起的民族危机时,鲁迅对中、日两国的反应进行了审视与比较:“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8]243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讲到了他的孩子因为健康和活泼而被同胞误认作是日本孩子的例子:由于照相师的不同,同一孩子在日本照相馆照的相满脸顽皮,像日本孩子,在中国照相馆照的相,便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1]81。由此鲁迅悟出:“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1]82再比如,他在《禁用和自造》中针对中日对待铅笔和墨水笔的不同态度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14]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民渐醒,国力渐强,然而直至1925年,即戊戌变法失败后27年的中国,烈士牺牲了,国民性依然没改变:“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9]26鲁迅慨叹说:“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9]21然而,直至1925年,鲁迅还是在强调:“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9]22他在1925年2月12日感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1925年2月16日甚至感叹“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9]16-17。这足见其对国家的爱之深、恨之切。
三、日本学界对鲁迅著作的译介
1909年5月的《日本和日本人》“文艺杂事”栏目就已记载了关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世界文学选集《域外小说集》第1卷的刊行,可谓世界上最早介绍鲁迅的文章,也是鲁迅作品在世界上传播的开端,但这只停留在介绍的层面。
最先在日本介绍鲁迅的是后来的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1887—1964)发表于《支那学》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浪潮》(载《支那学》1卷1-3号,1921年9-11月)。从文章的题目看,这是一篇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的文章,在该文的最后却写道:“在小说戏曲方面,没有比得上胡适的人。在翻译方面,周作人作为近代大陆文学的介绍者,成绩是很大的。他的译笔不是囿于旧文明的直译体,而是更能体现原著的神韵。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在《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一个有恐怖幻觉的迫害狂者,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尚未达到的境地了。”刊载青木正儿文章的《支那学》到了胡适手中后(1)1919年青木正儿与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小岛佑马、本田成之等组成“丽泽社”,创办《支那学》杂志,在该杂志上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此乃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人物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多次向胡适提供在日本搜索到的中国文学史资料。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提及此事。见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62-163页。,胡适附上信寄给鲁迅。鲁迅给青木正儿的回信中有以下文字:“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15]以上引文的意义在于,当时鲁迅的自谦或忧虑证明是错误的,其作品与影响在中、日两国,随着此际的萌芽,自此迸发,在两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的日译作品始于1922年5月4日发行的日文杂志《北京周报》,上面刊登了《孔乙己》的日译版,译者是仲密,即鲁迅的弟弟周作人。1932年1月《北京周报》又刊载了鲁迅本人翻译的《兔和猫》和《中国小说史略》的前半部分。日本人最初的译介,是从1924年1月到11月在《北京周报》第97-137期上连载的丸山幸一郎(丸山昏迷,1895—1924)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丸山昏迷是日译鲁迅著作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的第一人;在12月21号那一期上,《北京周报》刊出了东方生翻译的鲁迅的《我的头发》。同年,该杂志连载了清水安三(1891—1988)的《现代支那文学》一文,有关鲁迅的条目刊登在三月二号上(2)清水安三曾将自己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对清水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然后对日本古今的汉诗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认为日本人做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此事让清水安三久久难以忘怀。一般史料认为,日本译介鲁迅始于山上正义的《论鲁迅》,其实清水安三的研究要比这早上7年,在时间上堪称向日本译介鲁迅的第一人。。1926年,在大连日中文化协会出版的日文杂志《满蒙》刊登了由井上红梅翻译的《狂人日记》。井上红梅是日本第一位积极译介鲁迅作品的翻译家。他很早就发现了鲁迅作品的价值,因此不只局限于某几篇小说,而是几乎对鲁迅所有作品都很感兴趣。1927年12月,他在《上海持论》发表了翻译的《在酒楼上》;1928年,又发表了翻译的《风波》《药》《社戏》《阿Q正传》。《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8年《上海日日新闻》上,1929年又更名为《支那革命畸人传》载于日本国内一本以猎奇为主旨的月刊《奇谭》上。但鲁迅对这位“中国风俗史研究家”的翻译并没有好评,1932年11月7日在给增田涉的信中,就表露出对井上红梅的不满。他说:“井上红梅氏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译,也是无可如何。”[15]501在1932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16]
在日本方面,1927年,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大调和》十月号上译载了《故乡》,这是日本国内对鲁迅作品的最初翻译出版。1928年,山上正义(林守仁)翻译的《鸭的喜剧》,镰田正国翻译的《白光》和《孔乙己》也相继在日本问世了。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译作主要集中在对鲁迅单部作品小规模的翻译介绍上,水平参差不齐,对鲁迅原文的理解还可能存在偏差,并没有在日本社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日本学界由此开始关注鲁迅及其作品。从形式上看,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多家杂志社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客观上带动了日本国内对鲁迅作品翻译的热情,为接下来鲁迅在日本译介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初谈到有关《阿Q正传》的文章是山口慎一的《支那的新小说二三》。《满蒙》在12卷1号(1931年1月)上刊出了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阿Q正传》于同年5月连载完),同时刊载了大内隆雄的《鲁迅的时代》。鲁迅在1933年11月5日寄给翻译家姚克的回信中,对自己作品的外文翻译情况做了如下说明:“《小说全集》,日本有井上红梅(K.Inoue)译。《阿Q正传》,日本有三种译本:(一)松浦珪三(K.Matsuura)译,(二)林守仁(S.J.Ling,其实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国者)译,(三)增田涉(W.Masuda,在《中国幽默全集》中)译。”[17]在致外国友人的书信中,鲁迅致增田涉的书信占了大约七成,可见他对增田涉的信任。1936年10月19日鲁迅猝然离世,日本文化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因此决定马上出版鲁迅全集。1936年至1937年,东京改造社集合了当时鲁迅作品翻译的代表人物,如井上红梅、松枝茂夫、佐藤春夫、山上正义、增田涉、鹿地亘等人,合力完成了7卷《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出版。这部译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情况,乃20世纪30年代鲁迅著作外文译本中收录最为详尽的著作。上述译著的出版,迅速提高了鲁迅在日本的知名度。
战后日本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的文化圈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曾经长期遭受西方列强殖民统治、同为东方语境中的中国,他们体验到了“被压迫民族”的悲哀,并且对鲁迅作品中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充满了共鸣。戒能通孝所说的话,颇能传达当时的氛围:“最近我读鲁迅小说,感到非常之有趣,这实在是令人为难的事……鲁迅写的是中国,那中国是在与我们社会不同的地方……但现在却完全相同了……评论的语言从前是他人的语言,现在却正变成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日本完全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18]很多日本人惊奇地发现,美军占领下的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与鲁迅笔下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如此地相像,他们再次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以此希冀能找到解脱之路。正是这种切身的需求令战后日本再次出现了译介鲁迅作品的热潮,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更促进了日本学界对鲁迅的热烈研习:
1952年是特殊的年份,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结束,战后日本非常畸形地恢复了独立国状态。这一年,美军刚退到幕后不久发生了“五·一”事件。这是战后首次的五·一活动,并对不完全讲和的独立表示抗议。据说全国有一百万人参加,东京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尤其在东京,因为警察不许在皇宫前广场开会,群情激愤,会后很多人闯进皇宫前广场,跟警察发生冲突,最后受到镇压,死了两个人(其中一名被击毙),受伤者达到一千五百多名。公安部门宣布此事件为“骚乱罪”,逮捕了一千二百多人。左派人士为了表示抗议并宣泄愤怒,事后援用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词语,用北京的“三一八”事件来比附,表示抗议。但是东大中文系的一部分左派学生的看法,跟社会上的左派不一样。他们认为摘引鲁迅的句子来宣泄自己政治性的愤怒,是不科学的、不应该直接套用到1952年的日本,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所以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式来研究鲁迅,不能跟着社会上政治运动的路子走。就这样他们组织“鲁迅研究会”,展开了认真的阅读。每周,后来是每个月开会,精读鲁迅。一篇文章,一句话一句话阅读。不明白的词语,不清楚的社会背景,一个一个査清楚。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刊物《鲁迅研究》(1952—1966年)。[18]
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没有令日本人排斥鲁迅,反而将鲁迅视作日本当时危机的启蒙导师。根据藤井省三先生《鲁迅在日文世界》记载,1946—1949年期间“鲁迅译本等”有两部,1950—1959年期间则上升至35部,包括“鲁迅评论、传记等”[19]222-229。此阶段翻译鲁迅作品的学者包括: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鹿地亘、小田岳夫、冈崎俊夫、小野忍、武田泰淳、中泽信三、佐藤春夫、斋藤秋男、丸山升、太田良夫、香阪顺一、近藤春雄、田中清一郎、金子二郎、本隆三、尾阪德司等。1970—1989年期间,鲁迅作品的“译本”共计61部,“评论传记”共计64部,杂志文章共计298篇,数量惊人[19]222-229。而这一时期的“译本”在形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各有特色的。像1970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第1卷中便收入了竹内好翻译的鲁迅主要作品;筑摩文库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竹内好个人翻译的《鲁迅文集》全6卷;多个出版社全新出版了鲁迅小说文库本,包括1970年旺文社文库出版的松枝茂夫翻译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1971年中央公论社出版的由高田淳翻译、注解的《鲁迅诗画》,1972年潮文库出版的田中清一郎翻译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1973年中公文库出版的高桥和已翻译的《呐喊》,1975年新日本文库出版的丸山升翻译的《阿Q正传》,1979年讲谈社文库出版的驹田信二翻译的《鲁迅作品集》,1977年而立书房出版的由霜川远志编著的《戏曲·鲁迅传》。此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乃是由学习研究社1984年至198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共20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岩波书店、平凡社、讲谈社等大规模的出版社不仅刊载日译的鲁迅作品,而且引进中国的原作。《阿Q正传》《药》《藤野先生》等代表作也不断地被翻译和出版,但是相较于“评论传记”“杂志文章”呈现出的活跃状态,译本已经趋于稳定。而1990—2010年期间,有关鲁迅的“译本”共计21部,“评论传记”共计78部,“杂志文章”共计687篇[19]222-229。
鲁迅留学于日本,弃医从文亦在日本,他前期的思想、创作同日本文学具有密切联系,而译介并推崇鲁迅的文学作品及其领导地位的亦是日本。此处只是指出日本在鲁迅逝世后的翻译成果,这阶段的日本翻译对鲁迅奠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与国际文学界的地位,功莫大焉。日本的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历史悠久,数量与种类繁多,足见鲁迅思想之魅力,历久不衰。
四、鲁迅译介的日本文学与思想
鲁迅愤世嫉俗,对于国家更是爱之深而恨之切,然而对于令其百味交集的日本却颇多推崇,他如此赞美日本:“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20]178
日本对鲁迅的文学及学术有翻译与推介之功,而同样鲁迅亦很有目的性地翻译并传播了当时日本先进的启蒙思想与小说作品。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思想及作品中的启蒙思想的主要源头,便是当时的日本思想家与小说家。1919年他着手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1923年他与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包括15人共30篇作品。其中,鲁迅所译的有夏目漱石的《挂幅》《克莱喀先生》、森鸥外的《游戏》《沉默之塔》、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阿末之死》、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菊池宽的《复仇》《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江口涣的《峡谷之夜》等6家计11篇作品。此书由胡适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芥川龙之介亦在《日本小说的汉译》中对此书作了介绍。有论者指出:“这个翻译小说集……其中有些作品,如芥川龙之介、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不惟是这些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早期介绍,而且更重要者,是这些作品展示出当时中国新文学从未见过的文学品格与文学追求,那是非常个人化的文学趣味。这种个人化,其实亦透出一种现代品格。”[13]66-67
鲁迅曾谈到他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传播被虐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3]224。他颇为赞赏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原作对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亵渎的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尽情嘲讽。鲁迅在《译后记》里指出,“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菊池宽敢于揶揄和揭露,“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8]229。鲁迅所译介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此乃尼采《察拉图斯特拉》(或有时作《扎拉图斯特拉》)日译本的“代序”(3)森鸥外撰写此文不单为了介绍尼采的思想,他是针对1910年日本残酷迫害无政府主义党人的“幸德事件”而发的,带有对日本军阀政府的抗议之意。。他认为“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却仍推崇他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3]325,333。他在翻译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的后记中说:“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8]195他认为“永久的和平”“非从民众觉醒不可”[8]192,其翻译无疑又是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紧密联系的。
五、日本文学与鲁迅小说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对封建的“吃人”社会提出异议、进行反抗、有觉悟的人,这个狂人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近代的自我”的觉醒。在日本相当于《狂人日记》的作品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年)。与“狂人”相反,《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却是一位“既缺乏生活能力也缺乏果断”的懦夫。但是他不顺从明治社会(他是某部的小官吏,后被免职),这点可以说与“狂人”一样对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二叶亭四迷是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家(翻译家),爱读19世纪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这可以使人想到,也许他想在日本塑造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不满现实却无能为力的“多余者”形象。
此外,《浮云》问世后三年(1890),森欧外发表了用拟古文撰写的小说《舞姬》。这篇小说用笔记的形式写了一个主人公在德国留学期间与名叫爱莉斯的“舞姬”(舞女)相恋直至同居,但是为了在故国能飞黄腾达最后抛下爱莉斯回国的故事。他在无穷的烦恼中,写下了这个笔记。鲁迅的《伤逝》或便受《舞姬》的启发而创作。江口涣的《峡谷的夜》描述一个被丈夫遗弃后发疯的妇女,颇近《祝福》中被伦理纲常与迷信逼疯的祥林嫂。菊池宽《复仇的话》的主角八弥是一位武士的遗腹子,为报杀父之仇,仗剑寻敌,远游异乡。《复仇的话》中的某些情节和鲁迅的《铸剑》有不少类似之处。
鲁迅翻译芥川龙之介的《鼻子》,此小说以日本民间传说为题材,运用典雅诙谐的笔调尖锐讽刺了现实中那些安于现状、保守成性的人:明知弊端,却习以为常,一旦破除旧习,反而不习惯,宁可因循守旧,复归故道。显然,这也是中国国民的弱点。鲁迅曾痛心地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7]223-224对此,他沉痛地慨叹:“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对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9]143可见,他翻译《鼻子》的用意亦在于期望改造中国国民的痼疾,打败因循守旧的落后现状,启发国人的自觉。这种创作意图,大体出现在《头发的风波》中,有关国民对剪辫子的不习惯的描写。
鲁迅所翻译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末之死》对其小说创作亦有一定影响。有岛武郎是个虔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以博爱为宗旨,从生物进化发展观点出发,提出解放下一代,大力鼓吹长者对幼小者的爱,主张长辈要不惜牺牲自己,以爱和温暖抚慰幼者。“五四”时期,鲁迅多次阐发人性进化和解放,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不满于国民性的痼疾,故将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他深信“青年必胜于老人”,新的一代必然超越过旧的一代。1919年10月,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要“完全解放我们的孩子”,尖锐地批判了以封建纲常为伦理的父权。鲁迅认为父辈应该乐于牺牲自己,为青年一代开路。他大声呼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3]140鲁迅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天,读到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便挥笔写下《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称赞有岛武郎是“觉醒者”[3]363。于是乎,《故乡》中便有了寄希望于侄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狂人日记》中便有了“救救孩子”之呼吁。
综上,鲁迅揭露“吃人”的中国历史,发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和“救救孩子”的呼声,其途径唯在于“别求新声于异邦”,“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3]56;“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7]209。昔日,鲁迅离家去国,远渡日本,其在日本所受的刺激及启蒙,令他立志走上文学家与思想家的道路,而料想不到的是其作品及思想又反馈于战后的日本,以促其自新、自强。在日本,鲁迅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蒙,同样日本亦曾接受鲁迅思想的启蒙。可以说,中日两国共同孕育并成就了大写的“鲁迅先生”,亦为现代中国小说开启了一条启蒙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