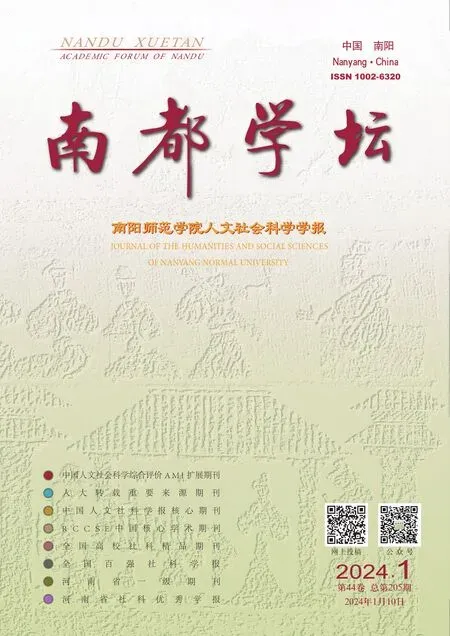“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宣 扬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秦朝二世而亡,新莽及身而灭,两个大一统皇朝的短祚命运引起了两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深切反思(1)关于西汉时期过秦思潮的研究,参见吴怀祺主编、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汪高鑫《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孙家洲《汉人“土崩瓦解”论秦亡的内涵解析》,载《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关于新汉之际士人对新朝兴亡的历史见解,可参见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曲利丽《两汉之际文化精神的演变》,中华书局2017年版;臧知非《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载《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李振宏《桓谭的学术立场与政治个性》,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新汉之际的士人已注意到秦政和新政的共通之处,如桓谭认为王莽贪功专断的行为“甚类暴秦”[1]18,第五伦直言秦朝和新朝皆亡于苛政(2)第五伦讽谏章帝说:“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参见范晔《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00页。。而将秦朝和新朝的历史联系起来全面考察的,首推班固《汉书》。
《汉书》不仅断汉为史,还贯通古今,“告往知来”[2]4243。一方面,《汉书》表、志详述从先秦至新朝各方面制度的兴废沿革,其中秦、新两代政治制度上承历世制作兴治之意,下启后王拨乱反正之功,尤其受到班固的重视;另一方面,以武、昭之际为界,《汉书》所述武帝以前史事,大体因袭《史记》原文,通过载录贾谊、贾山、徐乐、严安等人的政论,揭示了西汉前中期的“过秦”思潮。统治者转变治国方针,“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2]2021,正是过秦思潮普遍性的反映。《汉书》所述昭帝以后史事,主要沿着外戚干政这条线索展开。班固借刘向、鲍宣、杜业等朝臣言论点明西汉后期外戚权力扩大的趋势,而这一趋势最终指向王莽篡汉和新朝的速亡。班固比较秦朝、新朝政治得失,总结道:“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途),俱用灭亡。”[2]4194
本文主要考察班固关于秦朝和新朝的历史定位、兴亡原因和政治遗产等方面的论述,进而审视班固的历史兴亡观及其与东汉政治的互动关系。
一、对秦朝和新朝的历史定位
班固对秦朝和新朝的历史定位,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社会演进视角衡量两个皇朝的历史地位;二是依据五德终始学说安排两个皇朝的德运归属,以明确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班固将三代以下的社会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周朝“监于二代”[2]1029,损益礼乐,制三典五刑,因地制宜分土井田,形成了完备的礼法制度,是时尊卑有序,庶事俱济,“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2]1029,是班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至周之衰世,教化不行,刑罚错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至于战国”[2]1096,社会风气大坏,人们普遍推崇诈伪暴力,轻视礼义教化。社会风气之败坏,民众生活之困苦,至秦朝而达于极点。西汉之世,统治阶层整顿制度,与民休息,使社会发展步入正常的轨道,然而元、成以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陵夷坏于王莽”[2]1074。东汉统治者体察民情,施行德政,使社会再次迈入治世。在班固的叙述中,历史呈现出波动式的演进脉络。秦朝和新朝延续并强化了前代末世的社会弊端,背弃人伦正道,统治内外交困,都是社会经济全面崩溃的极乱之世,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两个“波谷”(3)阎步克用“波峰”和“波谷”描述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演变轨迹,以此表现出中古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周期性。参见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班固站在东汉统治者的立场,竭力贬低秦、新两朝,进而将其排除出历史正统序列。班固列出从唐尧到刘邦的刘氏家族世系,论证汉绍尧运,同属火德,为遵循周木、汉火五行相生的顺序,强行黜落大一统的秦朝,宣称汉“伐秦继周”[2]1023。在汉家“受命中兴”[2]1024的话语体系中,刘汉当永享天命,王莽因汉德衰微“窃位南面”[2]4194,违背天意,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班固立《王莽传》记新朝史事,言“莽”不言“新”,彻底剥夺新朝的历史合法性。正如《王莽传赞》所说,秦朝和新朝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为汉家“圣王之驱除”[2]4194。
值得注意的是,秦朝、新朝“余分闰位”的内涵有本质区别。《汉书·律历志》所引《世经》体现了班固的历史正统观,现将其中构建的历代帝王五德相生次序排列如下(4)帝王五德相生次序据顾颉刚所作“全史五德终始表”排列。:
太昊炮羲氏(木)→共工(闰水)→炎帝神农氏(火)→黄帝轩辕氏(土)→少昊金天氏(金)→颛顼高阳氏(水)
帝喾高辛氏(木)→帝挚(闰水)→帝尧陶唐氏(火)→帝舜有虞氏(土)→伯禹夏后氏(金)→殷(水)
周(木) → 秦伯(闰水)→汉(火)[3]
《世经》称秦为“伯”,“凡秦伯五世,四十九岁”[2]1022,以贯通周亡汉兴之间的历史统绪。对于秦朝的“闰位”,班固作出两点解释。其一,班固真正将帝王之“德”作为衡量政权正统性的标准。秦朝和共工氏一样,都有水德之运,但他们依靠谋略和刑杀称霸九州,德不配位,故“伯而不王”[2]1012,降居闰统。其二,《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典引》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4]291谓周得木德,汉得火德,木生火,故周于汉有母子仁恩之情,汉不应当直接取代周之德运。因此,上天安排秦朝“在木火之间”[4]291,令秦灭周,避免了汉朝以子代母的道义问题,而且汉伐秦继周,为母复仇,更凸显了汉朝继统的正当性。秦朝作为过渡性质的皇朝,“非其次序”[2]1271,自然享国不永。可是五德相生说以太昊伏羲氏为百王先,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2]1271,并不存在“仁不代母”的情况,班固显然是为了强调汉家正统而曲为之说。
反观新朝,班固排出的五德次序中并没有新朝的存在。“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2]1024王莽悖逆天命,盗袭帝位,其权力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因而班固径将新朝历史统摄于汉朝历史发展脉络中,明天命始终在汉,呈现出历史发展的“应然”而非“实然”。光武帝“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2]1024受命中兴,主张两汉政权一脉相承,从西汉皇朝到新朝的历史延续性被否定了,新朝的土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此看来,新朝既不正,也无统,成为游离于历史统绪之外的非法政权。易言之,秦朝行伯道,德位不够,降为与“正统”相对应的“闰统”,“闰统”意味着秦朝的存在顺承天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新朝则得国不正,德位阙失,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皇朝,新朝的存在违背天意,不具有任何历史合理性。
班固依据五德相生原理构建的政权更替统系,并不符合现实中的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历史定位嵌入了班固对不同朝代的价值判断,是我们探讨班固如何认知秦朝和新朝兴亡得失的基点。
二、论秦朝和新朝兴起的历史过程
班固有慨于秦国积德累功数百年,方从一个西陲戎狄之国逐步发展成大一统皇朝,“用力如此其艰难也”[2]363,而王莽竟玩天下人于股掌之上,未动一兵一卒就轻易夺取了汉朝江山,于是着力探讨秦朝和新朝兴起的历史过程。
班固引申发挥贾谊《过秦论》中的见解(5)班固摘录贾谊《过秦论》以为《汉书·陈胜项籍传》赞语;汉明帝诏问班固《史记·秦始皇本纪》赞语中的不当之处,该篇论赞全引贾谊《过秦论》,班固指出:“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可见班固认同《过秦论》中大多数观点。参见班固《汉书》卷31《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1-1825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8《典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8页。,对秦国逐步崛起的原因做出如下解释。一是“据势胜之地”[2]393。秦地被山带河,四塞险固,易守难攻,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秦国统治者善于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一旦有事则以逸待劳,“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4]277,六国之军顿兵坚城之下,往往不战自溃。二是秦孝公重用商君,变法图强。班固认为商君变法有两方面意义:对内废井田,开阡陌封疆,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使秦国得以“务本”[2]1126,为秦国逐鹿中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外用“攻守之法”[2]1469,连横诸侯,使其相互争斗,秦国趁机整治兵备,开拓疆土,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三是“因四世之胜”[2]1089,亦即贾谊所言“蒙故业,因遗策”[2]1821。商君虽死,“秦法未败”[5]398。秦始皇能“奋六世之余烈”[2]1823,不独在于君王“世世贤”[4]277,更因秦国统治者始终坚守商君的政治遗产,维持着治国策略的延续性。秦国政治运作稳定,整体实力雄厚,方能持续“蚕食山东,壹切取胜”[2]393,维持对山东六国的巨大优势。
对于秦始皇统一六国、成就帝业的进程,班固尤为注意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汉书·沟洫志》载秦王令水工郑国主持兴修引泾灌渠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建成后,粮食产量大增,“关中为沃野,无凶年”[2]1678,秦国国力更加强盛。班固将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秦并六国联系起来,并借郑国之口指出:“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6)此句《史记·河渠书》未载,为班固所补录。参见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8页。其次,秦始皇善用人,妥善处理君臣关系,使王翦这样的豺狼之徒“奋其爪牙”[2]1089,尽其才用。在具体的战术层面,秦将伺隙出兵,以诈取胜,在短短十年内就“禽猎六国,以并天下”[2]1089。最后,班固惊叹于秦始皇“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4]291的赫赫功业,认为秦始皇可能得到上天的指授,并用星宿分野学说曲为作解,表现出浓厚的天命观念。
关于王莽代汉建新的历史过程,班固从王莽的权臣身份入手,考察西汉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中的弊端,指出权臣篡汉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势。一方面,西汉统治者削藩矫枉过正,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基础。武帝以后,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2]395,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不受士民尊崇。当国家遇到政治变故,“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扞国难”[2]3426。另一方面,历代朝廷政治运作中必然会有外戚预政的现象,而西汉外戚之盛远迈前代。西汉外戚凭借“推亲亲以显尊尊”[2]339的汉家制度,恃恩泽获封列侯,“穷富贵而不以功”[2]4011,遂致骄奢僭盛,专权自恣,甚至多次出现外家谋反作乱的事件。宣、元以降,外戚轮流辅政逐渐制度化。外戚以“甥舅之亲”[2]1960持国柄政,排摈宗室,嫉害忠良,势力遍布朝廷内外,造成了臣强君弱的政治局面。有政治野心的“奸臣”[2]3741在人心不稳之际专擅朝政,攀至权力顶峰,欲逞其私欲,就有可能做出危害汉家社稷的政治行为。
王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台。首先,王莽因“四父历世之权”[2]4194,在元后庇荫下两度接任大司马之职,正延续了西汉后期外戚辅政的政治格局。其次,西汉后期“国嗣三绝”[2]4207,幼主即立,为朝臣擅权提供了条件。第三,王莽有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把自己伪装成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贤人君子,以邀取人心;为求仕途晋升,他侍奉诸父和元后,极尽谄媚之能事;执政后每以公义挟制、逼迫元后和孔光等老臣,残酷打击异己势力。于是王莽决断庶务,“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2]4045,已然权侔人主了。最后,王莽虚饰功德,上言“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2]4076,营造出天下风俗齐同、四夷率服的太平景象,遂理所当然地接受安汉公、宰衡和假皇帝等尊号,在官民一致拥戴下接受汉朝禅让,建立新朝。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并未客观看待王莽作为儒生的身份背景,忽略了西汉中后期儒家思想变迁对汉新嬗代的影响,这和东汉统治者吸收和扬弃汉新之际的儒家思想、彻底否定王莽之天命不无关联。
秦之兴盛在“并天下”,新之建立在权臣窃柄。故班固对秦则全面分析其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方面之优势,肯定了秦朝顺应时势统一六国的功业;对新则聚焦于统治阶层内部权力转移的政治背景,极力贬斥外戚专权之乱政和王莽得天下之不正。班固以长时段视角考察秦朝和新朝兴起的远因和近因,正可谓“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6]。
三、论秦朝和新朝速亡的经验教训
秦、新、两汉迭兴迭衰,制度或因或革,因而秦朝和新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对东汉统治者最具鉴戒意义。
班固论秦之过,以汉人过秦之论为重要思想资源,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分析取舍倾向。西汉前期的思想家集中批判“秦失其政”[4]2697,即秦朝的政治方向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班固基本赞同这一批判视角。一是刑罚深刻,“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2]2253;二是赋敛无度,百姓疲弊,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三是穷奢极欲,“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2]2296;四是穷武极诈,“北构于胡,南挂于越”[2]2811,百姓苦不聊生;五是吏治苛刻,“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2]2296,以致内外怨愤,相继流移逋逃;六是秦俗败坏,灭弃四维,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2]2246;七是太子教育失策,“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道之者非其理”[2]2251;八是多设禁忌,诛戮贤士,于是臣民谄媚事君,“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2]2011。
班固过秦的另一思想资源,是西汉中期以降儒生对秦制的进一步反思。这些反思主要集中于秦朝废除分封制和井田制两个方面。在复古改制思潮影响下,儒生以理想中的先王之制衡量汉家制度,进而溯及作为源头的秦朝制度,对之大加鞭挞,如王莽即位后颁布的限田禁奴婢诏书全面总结了秦汉“废井田”后“兼并起,贪鄙生”[2]4110的社会问题。儒生从制度层面批判秦朝,其视野更加开阔,但他们过秦是要论证汉家制度之疏阔,容易出现以今度古、将汉代社会矛盾及其起因倒栽于秦朝的问题。班固批判继承了这些儒生的见解。一方面,班固直斥秦国“坏井田,开仟伯”[2]1126,灭弃先王之道,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又指出秦朝废除分封制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2]393,随着反秦战争的爆发,秦朝因孤立无援而亡不旋踵;另一方面,班固借区博之言指出,秦朝“灭庐井而置阡陌”有利于农业生产,是“顺民之心”[2]4129的举措,可见班固意在批判秦骤废井田后未能处理好土地兼并的问题,并非主张恢复井田制。
贾谊过秦的中心思想是秦朝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攻守之势”[4]282的转化,不知道适时改变统治政策。班固据此总结出秦朝两位皇帝在秦朝灭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4]293即秦始皇继续用战时体制治理国家,“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即位后不仅没有“正先帝之过”,反而“暴虐以重祸”,加速了秦朝的灭亡[4]278、283、284。应指出的是,班固说“起罪恶”,是谨慎地将秦朝灭亡原因的考察范围限定在秦始皇至秦二世时期,意谓秦国各项政制虽有弊端,但它毕竟推动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秦朝败亡是后来统治者没有及时转变统治模式的结果,不能随意溯因于既往。
在王命论的思想框架下,新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其未能得到上天的佑命,新朝统治措施之不当是王莽逆天而行的必然结果。班固长期在朝廷监控下从事著述活动,所撰《汉书》和诸篇赋颂都贯彻了天命兴汉的历史思想,不过官方意识形态并未遮蔽他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班固仍从人事角度探讨了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
班固将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制度失中”[2]1186。“中”谓帝王“为之有数”[2]1186,令行法立。王莽推行激进的王田私属政策,罔顾土地高度集中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结果遭到富豪权贵和自耕农民等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反对。诏令对于如何计口授田的规定又不明确,豪强贵族和贪官污吏朋比为奸,从中渔利,“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2]1144。王莽推行的货币品类繁多,难以兑换,又骤行骤废,令“百姓愦乱”[2]1179,根本无法流通使用。六筦依《周官》收税,税目竟有一二十种,征收对象遍及各行各业的居民。主持五均六筦的官员都是各地的富商大贾,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2]1183,与郡县官吏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给身为商人时囤积居奇、投机敛财的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2]1183。王莽的经济改革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土地兼并、吏治混乱和农民破产的现象愈演愈烈,新朝迅即陷入崩溃的边缘。
班固追溯王莽改制的思想根源,指出王莽“动欲慕古,不度时宜”[2]1143,过于迷信儒家经典,以为其中包含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遂“专念稽古之事”[2]4131,每有改制,必寻绎附会经文,强行削社会现实之足,以适儒家典籍所载制度之履。易言之,“制度失中”不仅是王莽规划执行不力等操作层面的问题,根本在于新朝制度本身过于整齐划一、过于理想化,完全脱离了汉新之际的社会土壤,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班固对新朝政治的批判,都是紧紧围绕王莽个人的政治行为展开的。王莽通过权臣秉政的方式逐步登上帝位,唯恐后人复效己所为,遂抑夺下权,自揽政事。可是王莽好谋无断,但崇空语,征召官员讨论治河方略却不施行,坐视河决为害;耽于制礼作乐,虚饰太平,致令政事荒废;又好大喜功,妄开边衅,百姓愁苦不堪,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2]4125,新朝倾覆固已兆端于此。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不知改弦易辙,反而拒谏饰非,矫托天命,幻想着用各种厌胜之术消弭灾祸。这些荒唐的政治举措加速了新朝统治的崩溃。
纵观班固所论,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速亡的原因竟如此相似。秦朝和新朝都实行严刑峻法,赋敛无度,虚耗民力,最终积失民心而亡。秦、新统治者政治性格趋同,如秦始皇奋其私智,“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2]1096,王莽威服自专,轻贱朝臣,甚至让宦官代尚书受理吏民封事,对于王莽分封诸侯之举,班固以为有名无实,掩盖不了他和秦始皇一样专权独断的本质。班固尤为重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汉书·匈奴传》载严尤论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以此劝谏王莽不可“大用民力”,否则兵连祸结,中土疲耗,社稷有倾覆之虞[2]3824-3825。班固称赞严尤“论之当矣”[2]3833,表明秦始皇和王莽皆以穷兵致祸的共通之处。
吏治败坏加剧官民对立,是酿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不过秦、新两朝吏治败坏的政治背景却不尽同。秦朝以法治吏,“治吏不治民”[5]332,因而对官吏督责极严,二世甚至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4]2557,官吏在高压下“争以亟疾苛察相高”[2]2308。新朝统治者则忙于改定制度,官吏行事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而且新朝吏禄制度烦碎,各级官吏长期领不到俸禄,他们为谋生计,被迫利用手中的职权贪污贿赂,“并为奸利”[2]4152,让本已滥朽腐败的吏治更趋颓坏。
秦朝“荡灭古法”[2]393,王莽“专念稽古之事”,政治理想迥异的两个皇朝为何会有相同的命运?在班固看来,帝王治国应以礼为本,以法为辅,“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7]。秦朝自不必论。王莽不知顺时施宜删定律令,以礼义教化民众,一味照搬儒家典籍中的制度,并未践行先王制度中蕴含的思想内涵。为了顺利推行各项制度,王莽设立严格的科条禁令,冀图通过严刑峻法实现理想中的仁圣之治,这本身就违背了帝王动缘民情、“仁爱德让”[2]1079的王道原则,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换言之,王莽借复古之名,行逆古之实,和秦朝“同归殊涂(途),俱用灭亡”。
在王命论的背景下,班固对秦朝重其亡而轻其兴,对新朝则重其兴而轻其亡。后人因循其意,暴秦、伪新不仅指代两个大一统皇朝,也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
四、论秦朝和新朝的政治遗产
秦朝虽亡,其留下的政治遗产却深深影响着后世。班彪分析比较周汉形势,指出:“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4207“汉家承秦之制”一词被范晔凝括为“汉承秦制”[8]1323,为后世史家习用。班彪所论揭示了秦制的重要特征,即尊君卑臣,保证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班固受其父影响,认识到秦始皇“制作政令,施于后王”[4]291的开创性贡献,并多次论及汉制对秦制的因袭。一是“建皇帝之号”[2]722,皇帝制度和帝王观念是秦制的核心内容;二是“立百官之职”[2]722,基本继承了秦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和郡县制度;三是“袭秦正朔”[2]974,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四是袭秦礼乐,叔孙通制礼“大抵皆袭秦故”[4]1159,用乐“大氐皆因秦旧事”[2]1044;五是袭秦法律,萧何删述秦律“宜于时者”[2]1096,编成《九章律》。《汉书·高帝纪》叙目大肆铺陈高帝功业,然而论及高帝“革命创制”[2]4236,却仅仅举出与民约法三章的例子。这正表明汉朝建立之初全盘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社会文化体系。
《高帝纪》叙目的表述暗含了班固对秦朝制度的态度:高帝“承秦之制”并非值得称颂的功业(7)班固《高祖沛泗水亭碑铭》对汉高祖歌功颂德,论高祖伐秦灭项,封赏朝臣,光耀火德,亦不言高祖创制规摹。参见《古文苑》卷13《高祖沛泗水亭碑铭》,《四部丛刊·集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事实上,《汉书》中反复言及“汉承百王之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汉受亡秦之敝”[2]212、1112、1332,“百王”“衰周”最终都指向秦朝之“极敝”。如贾谊依据儒家伦理道德,激烈批判秦朝家庭风俗之败坏,“汉承秦之败俗”,民众追求奢靡,“弃礼谊,捐廉耻”的程度尤过于前代[2]1030、2244。董仲舒痛陈秦“除井田”后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批判秦朝赋敛繁重、与民争利,“汉兴,循而未改”[2]1137。“亡秦之敝”都是关乎国计民生、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班固解释秦汉制度之间的联系说:“汉迪于秦,有革有因。”[2]4241“革”谓“反秦之敝”,如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2]3623。对于“因”秦制,班固认为是汉初君臣迫于时势不得已的选择。理由是汉家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秦制简易适时,便于施行。这里蕴含的思路是:班固以儒家王道政治为最高理想,认为继承唐尧统绪的汉高帝“伐秦继周”,理当肩负践行周代王道政治的使命。汉高帝自不会依据后来的政治观念行事,班固却不得不曲为之说,将汉高帝“承秦之制”理解为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8)《汉书》屡屡以此解释汉初统治者“承秦之制”的政治举措。如叔孙通制礼,《史记·礼书》说:“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汉书·礼乐志》不直言“袭秦”,而是说:“(叔孙通)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让人认为叔孙通本意是制定更完备的礼制而非“皆袭秦故”,只是还没来得及做就去世了。参见司马迁《史记》卷23《礼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59页;班固《汉书》卷22《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0页。。
新制的历史命运与秦制不同。光武帝以汉家后受命中兴,视新朝为不入历史统绪的伪政权。刘秀即位后“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2]1185,全面废除新朝制度,重建汉家制度。新朝的一切制度和文化似乎都被历史抛弃了,究其实则不然。
前后衔接的两个皇朝之间的制度文化不可能没有联系。从历史的眼光看,东汉皇朝在不少方面都继承了新朝的政治遗产。首先,光武帝为避免重蹈西汉末年权臣篡汉的覆辙,削夺三公职权,事归台阁,亲总吏职,可这些加强皇权专制的举措,实质上延续了王莽不信大臣、专权独断的政治倾向,时人对此已有讥议(9)陈元谏阻司隶校尉督察三公时指出,刘秀采取各种手段“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和王莽防备臣下、专权独断没什么两样。参见范晔《后汉书》卷36《陈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3页。。其次,王莽扩大太学规模,提倡古文经学,同时灵活采取今、古文经中的学术资源,将经术和政治结合起来,为篡汉建新、复古改制的政治行为提供理论根据,王莽尊崇儒学、以经治国的政治思想在东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10)关于刘秀崇儒重教的具体举措,参见黄留珠《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286页。。再者,东汉统治者完全服膺谶纬之学,甚至将谶纬神学作为东汉皇朝的统治思想,正如叶适所说:“如符命、图谶之类,人心皆转易而不自觉,虽东汉有节义之俗,然内而朝廷,外而邑里,千载相师,莽习故在,不复能自还,可哀也!”[9]332最后,新朝部分制度仍为东汉皇朝所继承。一是制定更精确的度量衡制;二是确立南郊郊祀制度;三是下诏“中国不得有二名”[2]3819,自此社会上普遍流行单名;四是厘定上书制度,群臣上书“去昧死,曰稽首”[10];五是践行禅让制度,开启了汉晋权臣禅让的格局;六是拟将新朝统治重心移至东都,光武帝最终践行了这一政治规划。王莽通过长期的经学教育和政治宣传,让新朝的各种制度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因而新朝和东汉皇朝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是相当显著的。
班固称颂光武帝“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8]1360,他自然不会认可新汉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过班固重视先王之制的精神内涵而非外在形式,若以这一标准反观新制和汉制,我们可以认为东汉皇朝虽废除新朝的具体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新制背后依托的思想内涵。
五、“宣汉”与“戒汉”:论班固的历史兴亡观
班固论暴秦与伪新,既为宣汉家创制垂统之功德,也要戒汉家改制更化以免重蹈覆辙的必要性,其落脚点在于东汉皇朝的王道政治建设。
关于秦朝和新朝统治者的优劣比较,班固认为王莽造成的历史灾难远过于秦朝统治者。《汉书·古今人表》评秦始皇为中下,这未必公允,却符合班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2]861的品评标准。秦二世为下中,盖以赵高为祸首。《王莽传》称隗嚣移檄“数莽罪恶万于桀纣”[2]4187。檄文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类大罪,并未将王莽与桀纣相比较,可见王莽罪恶“万于桀纣”是班固个人的评断。《古今人表》以纣为下下愚人,王莽的品位自不待言。班固描述王莽暴政下民不聊生的惨状:“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11]29(11)《汉书·天文志》引述《史记·天官书》关于秦朝末年长期战乱的记载,删去“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数语。
班固以秦朝、新朝之“过”反衬西汉、东汉之“德”,赋予汉家政权以正当性。这里涉及西汉和东汉皇朝的历史定位问题。汉初统治者“承秦之制”,在制度建设上缺少开创性的贡献。终西汉一代,统治者“稽古礼文”[2]212,在礼乐、正朔、服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却没有真正革除秦制,“伐秦继周”仍旧是理论层面的构想。元帝诏书说:“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礼谊,阴阳不调。”[2]3045刘向认为汉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2]1034。汉承“周秦之弊”成为西汉后期统治阶层的共识。
与之相较,班固借王莽之祸反衬东汉初年“天地革命”的巨变。光武帝“体元立制”,重新肇建社会人伦秩序,“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得到的评价高于汉高帝[11]30-32。冯衍曾称颂更始帝诛灭王莽之功业“德冠往初,功无与二”[8]966,这一功业后来被移到刘秀身上,可见时人对灭莽功业的高度评价是一贯的。在班固看来,光武帝“改定京师于土中”[2]1035,象征着东汉皇朝要继承周制而非秦制。因此,东汉伐新、革秦、继周,正循着王道政治的轨道演进,其历史地位自然高于西汉。易言之,班固颂述汉德,实质上是宣受命中兴之东汉。
由于东汉统治阶层有意忽略新朝的政治遗产,班固循着秦—西汉—东汉的历史脉络讨论汉家制度建设问题。东汉皇朝恢复西汉制度,实际上也就继承了“暴秦之敝”。秦—西汉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正成为东汉统治者革除的对象。班固认为王道政治的建设应循序渐进,“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2]1117。东汉历经光武帝和明帝两代帝王的统治,“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2]1075,已经到了大兴庠序、制礼作乐的历史阶段。班固对暴秦和伪新的批判,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