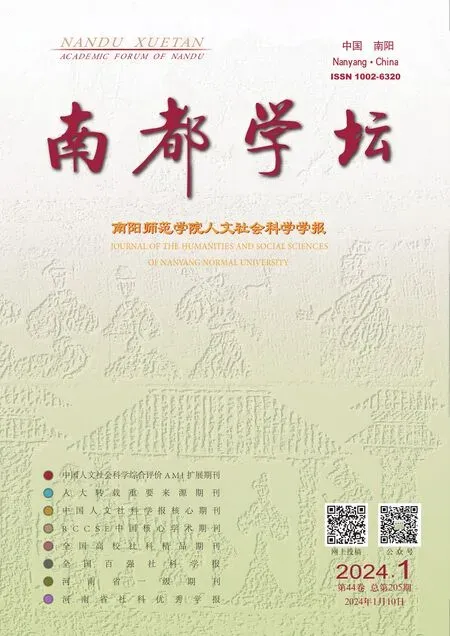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王春阳,王 璇
(1.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61; 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6)
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时说“伟大也要有人懂”。“伟大”概指《儒林外史》作为文学经典的价值与地位,而“懂”字体现了创作者寓意于作品文本之内的主体表达及其刻意构建的思想世界。“作为一个思想家,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无论是结构、人物, 还是细节和语言, 都清晰地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结果。”[1]《儒林外史》体现的思想是多维度的,对士人群体治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亦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
一、士人治生问题的产生
(一)士的产生与士阶层的形成
在礼乐制度形成的周代,士原为贵族的最低一级。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诸侯蜂起,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逐渐式微,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为了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并形成优势,各诸侯国竞相招纳贤才,整个社会形成的尊士崇士风尚,为处于贵族底层的士群体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掌控更多的话语权,谋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他们争相投奔到那些拥有权势的诸侯和达官贵人门下,士人风头,一时无两,仅齐国孟尝君一人就供养了三千门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士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群体并成为“民”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
(二)士的界定
士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汉武帝时期,由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那些以孔子后学自居,研习六艺经学的儒生成为士的主体。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因考试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更加强化了士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工具书一般把“士”解释为“读书人”或“封建时代称读书人”,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是士。明代推行“科举必由学校”,增加了童生试,“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2]1687。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童生的资格也必须通过考试获得,只有那些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作童生。童生方有资格参加院试,通过者谓之生员。生员或者相当生员资格者才能参加乡试,通过者为举人。举人才具有参加会试、殿试的资格,通过者谓之进士。“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至若乡间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烂熟之士。”[3]394可见,士并不是指所有读书人,而是指那些从农、工、商或其他群体中通过考试获得童生及以上资格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相当资格的读书人。
(三)士的社会地位
在传统社会,士作为智识阶层,由周代贵族最底层那部分人演化而来,其地位本就高于平民。而传统社会的士人群体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强化这种身份标签。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到张载的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涵阐释,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思呐喊,无一不是在强化着士之为士的群体特征。“中国圣贤立教,对‘士’自身的要求,常常远严格过对一般社会的要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势时,应当坚守自己的权利,限定自己的义务。在面对社会时,则应当忘记自己的权利,扩大自己的义务。”[4]36“士不可以不弘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人格操守和价值追求成为士人群体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精神特征。因此,与农、工、商等群体相比,士拥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具有超越自我的家国情怀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以此为起点,中国传统士人群体,以孔子思想为旨归,以儒家元典为依据,或口耳相传,或绍述典籍,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自觉承担起文化建设、文化传播传承的使命,把建设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大一统国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封建时代家天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士人群体作为文化典籍的掌握者和解释者、文化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自觉承担对社会的教化责任并努力成为道德典范,能够帮助统治者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宋仁宗说“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5]3658。明太祖朱元璋所论更具典型性。他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6]372。因此统治者有意识把士培养成为封建政府各级衙门成员的后备力量,鼓励士人参与社会管理,并通过科举制度得以实现。最具代表性的是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7]28封建最高统治者鼓励士人读书并给予通过科举考试者以极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这种人生际遇的巨大反差,使士人由衷发出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感慨,并逐步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尚。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统治者通过实行四民恒业的政策,在制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士人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天下人之利。”[8]1825公元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诏:“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9]33其目的也非常明确:“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10]209儒家知识分子的群体努力和统治者的政策干预,使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为四民之首并拥有高于农、工、商等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吾儒明德亲民之学,止于至善,乃尊于农工商,而为士之职也。[11]740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农礼乐,士所独也,何者,士固储其学,以待为民上,而任经世之责者,非若农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12]92
(四)士人的治生问题
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财用足”[13]171。农、工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商人从事物资流通,士从事文化生产。职业属性的不同也决定了谋生手段的差异,“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14]30。 “士食于官,农军授之田,商工食其力”[11]740。士作为专职读书人,读书学习就成为其卫身谋生的主要凭借:“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14]30而“士食于官”的社会认同进一步强化了读书人把通过科举制度获取生存所需物质资料作为唯一正途的认识。“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是这种认识的最通俗概括。“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14]30由于科举制度定期选拔人才,士人一旦通过考试立即获取超越常规的巨大回报,这种定期选拔和超常回报,使士人群体普遍认为只要认真读书“精其业”就能获取“科名”,最终达到“食于官”的目的。但是,制度设计和运行与社会实际是否契合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如果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不能较好解决士人的生计,就必然导致矛盾并形成社会问题,不但影响着制度效能的发挥,而且还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由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转化为阻碍力量。
二、《儒林外史》对士人治生问题的深刻揭示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推行时间长达1300年之久。作为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古代最有效的选官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的规范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均受到了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在实践中虽不断改进却因自身创新不足而未能完全与时俱进,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士人治生就是其一。到明清时期,士人能否通过读书解决个人及家庭的生计问题,与士人个体的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士人群体的努力呈负相关关系。因为国家治理对士人需求在数量上是有限度的,士人群体数量越大,竞争就越激烈,通过科举之途解决生计问题就越困难。因此,除个别特殊时期外,正常情况是士人群体无论如何努力,其大多数人还是无法通过读书来解决个人及家庭的生计问题。但是科举制度定期定额选拔一批士人充实到官僚队伍并使其享受到远超于一般人的政治经济待遇,这种表象的浮华掩盖了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对于士人遭遇的生计困顿,论者皆从士人自身找原因,或归结于个体努力程度不够,或归结于虚渺的天意,“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14]30。基于此,《儒林外史》作为“真正的士子写士子的小说”[15]5,通过全景式展示士人群体的生存困境而表达了士人治生这一深刻思想主题。
(一)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
在我国传统社会,统治者推行的“四民恒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士人必须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来获得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作为自己谋生的主要途径。“其才质之美, 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 次可以开门授徒, 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书札,代签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16]153“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14]30此外,传统士人群体把自己视为文脉和道统的化身,强调精神价值而淡泊物质享受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风尚,则进一步弱化了对获取物质财富的内在意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7]40可见,在交换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士人依靠“本业”治生的范围本来就相当有限,而整个社会对士人治生认识的狭隘化,使士人的治生观念逐渐扭曲。
一生在科举上失意的马纯上苦口婆心地奉劝匡超人: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这便是曾子的“养志”。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的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18]200-201
蘧公孙和鲁小姐门户相称,才貌相当,在外人眼里是极为般配的“才子佳人,一双两好”。但鲁小姐在了解蘧公孙无志举业后即愁眉泪眼,长吁短叹:“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虽然在其母亲眼中这位女婿称得上是名士,但在鲁小姐眼中却一钱不值:“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个名士的?”而当母亲以“现在两家鼎盛,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对其进行劝慰时,鲁小姐固执地认为“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18]142-143。而鲁小姐的父亲鲁编修,也因为女婿不事举业而气得差点丢了性命。
《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全面展现出当时社会对士人治生的认识完全固化到“科举”一途的社会现实。对士人而言只有进学、中举、考进士才是治生的正途,而其他手段都是邪路,与读书人不相干。这种扭曲的治生观念和社会风尚使出身贫寒的士人处境更为艰难,生存状况更加恶化,也使矛盾更加突出。
(二)通过典型人物深刻揭示社会现实
“艺术创作的功用不外是抒情、状物、叙事和说理四大项。”[19]106而叙事性文艺作品创作的中心问题就是典型人物的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不但反映某一社会类型的共同本质特征,而且能够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一些方面的规律,反映某一时代的社会风貌,也即这一典型人物产生的典型环境。作为我国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巨著,《儒林外史》艺术地创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周进出场的时候已经60多岁,“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因还不曾进学,仍是童生身份。当时规矩,童生进了学,即便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是到了80岁也还称“小友”。而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因此周进走进堂屋时,十几岁年纪的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而周进也不肯僭梅玖作揖。原因就是梅玖已经进学入庠成为生员,而周进还是童生。周进陪王举人闲聊半天,“掌上灯烛,官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下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次日,王举人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18]27。周进坐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即便这样的生计也安身不牢,由于不知道常来承谢夏总甲,被人所辞,“失了馆,在家日食艰难”。生活的艰辛和地位的低下跃然纸上。
而周进高中之后,放差广东学政,“绯袍金带,何等辉煌”,那些与他毫无关系的人也想尽千方百计依傍他,严贡生为了到部里告状,竟冒认是他的亲戚,“大着胆,竟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门上去投”[18]91。以前极端轻视他的梅玖为了逃脱责罚硬说周进是自己的业师,当荀玫问他:“你几时从过我们周先生读书?”梅玖竟厚着脸皮说:“你后生家那里知道!想着我从先生时,你还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里教书,教的都是县门口房科家的馆;后来下乡来,你们上学,我已是进过了。所以你不晓得。先生最喜欢我的。”[18]94那些辞退他、让他失却生计的“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竟然为他立了金字长生牌位日夜供奉。
范进54岁以童生身份出场,“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很是狼狈。中举前,因没有盘费参加乡试,去找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乡试回家,家里已饿了两三天。出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他母亲“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中举以后,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丈人胡屠户也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贺喜。从无交情的张乡绅一出手贺仪就是五十两并白白奉送临街三进三间空房一所。此后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仅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18]45。为范进母亲做佛事的和尚被人拴了,范进拿帖子向知县说了,知县就“差班头将和尚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领了家去”,而将拴了和尚的一班光棍“带着明日早堂发落”[18]52。
周进、范进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通过二人考取功名前后遭遇的鲜明对比,深刻揭示出士人之所以将“科举”看作治生的唯一“正途”,是与中举、中进士后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密切相关的,这种综合性利益是其他途径所获利益难以比拟的。正是这种超常回报和高收益,使士人的治生观念不断扭曲,也使每个士人存在侥幸的赌徒心态,如飞蛾扑火,身不死志不灭。
(三)用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
在帝制时代,读书、治学与做官并无冲突。传统社会通过科举选拔官员,不仅生产了大量读书人,同时也成为消化读书人的最好场所。但是读书人的增量与通过科举制度选官消化读书人的能力并未同步。因此,与周进、范进二人相比,倪老爹和杨执中就没那么幸运了。倪老爹21岁进学,已经做了37年的秀才,因为没有吃用,6个儿子死了1个,卖了4个。仅留的1个最后也不得不卖掉,因为“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18]313。而杨执中“只为当初无意中补得一个廪,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18]149。落得“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除夕晚上因没有柴米,“和老妻两个,点了一支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18]146。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科举制度能够获取做官资格的士人数量相当有限,录取名额有着严格的限制。以清制为例:
会试无定额。……历科大率三百数十名,少或百数十名,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为最多,乾隆己酉九十六名为最少。[20]3158-3159
乡试解额,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定额不同,到乾隆九年,“定顺天南、北皿各三十六,中皿改二十取一,贝字百二,夹、旦各四,江南上江四十五,下江六十九,浙江、江西皆九十四,福建八十五,广东七十二,河南七十一,山东六十九,陕西六十一,山西、四川皆六十,云南五十四,湖北四十八,湖南、广西皆四十五,贵州三十六”[20]3158。
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巡抚白潢上奏称该省乡试入场士子多至12000余人,举人名额却只有90人,应试与录取比例为134∶1[21]149。由于名额太少,应试与录取的比例太过悬殊,因此士子能够通过乡试考中举人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参加会试进而通过殿试考取进士了。
而未能通过乡试考中举人的大量士子,能否从政府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为了鼓励士人读书,从唐代开始,历代朝廷都为进学的专职读书人提供廪粮以保证其能够专心读书。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承平日久,士人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吸引了更多农、工、商阶层成员向士阶层流动,而制度设计和社会风气又限制了士人向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因此这种流动从多维双向逐渐固化为多维单向流动。社会阶层固化与多维单向流动的结果是读书人越来越多,群体日益庞大。为了缓解矛盾,朝廷只有扩增生员的名额,在廪生之外有大量增生,在增生之外有大量附生。但是,在所有生员中,只有廪生有资格获取朝廷提供的廪粮,而增生和附生却没有来自朝廷的任何资助和补贴。既然进学的增生和附生都未能“食于官”,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进学的童生了。增生、附生以及未进学的童生作为士人的主体,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那些能够“食于官”的士人。而且在明清时期,以六等黜陟法对入学士人学习情况进行考核,那些入廪士人必须不停地参加考试,才能保持自己“食于官”的资格。“学生的唯一任务就是学习和考试,尤其是考试,而这又是和整个朝廷的选官制度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可以这样说,考试是学生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22]405但是不断考试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士人无暇治生,进一步降低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和谋生本领,“人生当务之急以治生为最要,亦不独儒者为然,但儒者每迂缓不解事,不善治生”[23]309。
未能通过读书解决生计问题的他们,又是怎样获得生活资料的呢?
倪老爹只好依靠修补乐器为生,最后发出了“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18]312的感慨。而杨执中受盐商委托照料生意,因不善料理账目,被人称为“老阿呆”,没处开销却亏空了七百多银子。最后被拿到监里,坐着追比。荀玫家庭本来很富裕,“像这荀老爹,田地广,粮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分子派”[18]20。但等荀玫进学后,他母亲欢喜道:“自你爹去世,年岁不好,家里田地渐渐也花费了。而今得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18]95本来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反而因为醉心科举之途而把家产败光造成生计困难。这些现实深刻揭示出,就大部分士人而言,醉心科举不仅不能治生,反而妨碍治生。因此,即便统治者为了求得社会的相对稳定,“将科举制度笼络读书人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24],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士人通过本业治生的需求。因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即借王冕之口,对科举入仕的制度进行了批评。“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8]13从而造成“一代文人有厄”。
三、《儒林外史》治生问题的思想渊源
士人治生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早在唐代,杜甫就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元代许衡指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25]211清初学者全祖望、陆桴亭、张杨园也都对士人治生问题多有探讨。因此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无疑受到这些先贤的思想滋养。除此之外,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与其自身经历分不开,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一)吴敬梓的自身经历
吴敬梓出身缙绅之家,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其父亲去世后,为其留下丰厚的家产,“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26]127,根本不用为生计操心。因为这种生活环境,吴敬梓对生活之艰辛缺乏足够的体验,对物质财富在生存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更因性格原因,仗义疏财,放浪形骸,以致最后家产散尽,衣食无着,有时竟至断炊。“乃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26]127-128论者多过分夸大他不慕物质,甘于穷困的正面意义,而很少注意其“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的无奈。就在他移家南京一年之后,他还曾懊悔“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谷贻孙子”[26]55-57。发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26]14的无限感慨。并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放浪生活进行了深刻反思:“失计辞乡土,论文乐有朋”“回思年少日,流浪太无凭。”[26]19
再加上亲友在科举之途上的不如意而导致的生活贫困,也给吴敬梓以极大的刺激,其从母之子因生活贫困被迫遁入空门:
穷途久奔驰,携家复转徙,吁嗟骨肉亲,音问疏桑梓。……坐久道姓名,知为从母子。家贫遭飘荡,爷娘相继死;伯兄去东粤,存殁不堪拟;仲兄远佣书,遥遥隔江水;弱妹适异县,寡宿无依倚;兄弟余两人,流落江之涘。髡缁入空门,此生长已矣。哽咽语夜阑,寒风裂窗纸。[26]43-44
自己的舅父因为屡试不第郁郁而终:
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迍邅。……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巅。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26]46
因此,吴敬梓在扬州重逢昔日好友程晋芳,得知晋芳亦贫甚时,紧握这位昔日好友的手潸然泪下,发出了“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26]128的揪心之叹。
(二)颜李学派治生思想的影响
颜李学派是儒学发展到清初形成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以颜元、李塨师徒为领军,以“实学”为宗旨,旨在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利,在清初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颜元和李塨都出生于富裕家庭,但由于社会动荡以及清政府在京畿地区的圈地等原因,颜、李的家庭都沦为赤贫,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如务农、行医、坐馆、相地等职事。颜元还曾因“讼后家落”,不得已从城市返乡居住,“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薥秫如蒺藜,后甘之”[27]711。虽“见者不以为贫”,但不能改变其“贫穷”到无以为食的困境。“以贫为养老计,学医。”[27]712因为贫穷,“断自新岁礼节再减,虚门面再落,身价勤苦事再加”,并以此即“素贫贱行乎贫贱”自慰。他在登厕时,所见“皆粱之秕糠也”,发出了“焉知贫之苦乎”的感慨[27]782。从而认为“自古无袖手书斋,不谋身家以听天命之圣贤也”[27]733。因此他对物质基于生活的重要性认识较为深刻,对知识分子的治生问题尤为关切。颜元认为“若古之谋道者,自有礼、乐、射、御、书、数等业,可以了生”。而“今世之儒,非兼农圃,则必风鉴、医、卜;否则无以为生。盖由汉宋诸儒,误人于章句,复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业之术尽亡矣”[27]675。他不但批评时文取士消磨了士人的精力,“古者弟子为学,先教之事父、事兄,服劳奉养;今世为学,惟教之读书、作文,逸惰其身,而奴隶其父兄,此时文取士之害,读作为学之弊也”[27]676。也批评时文取士降低了士人治生的能力,“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自八九岁便咿唔,十余岁便习训诂,套袭构篇,终身不晓习礼、义之事,至老不讲致君、泽民之道,且无一人不弱不病”[27]678。因此颜元批评“若宋儒之学,不谋食能无饥乎?”[27]671作为颜元的学生,李塨对生计颇为关注。李塨家庭因为多种原因也导致贫困,“孝悫先生于兄让多分少,故致饥寒 ”[28]9。“一日绝午炊,而与友人商学古入官之事,不知饥也。”[28]14因此李塨说“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并失其二 ”[28]8。当学生冯辰“语以老亲在堂时”,李塨告诉他“治生即学”[28]118。
吴敬梓与颜李学派有着多方联系。其曾祖父吴国对与李塨为师生关系,“学院吴公国对岁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吴公深喜先生文,开雕行世”[28]4。吴敬梓的儿子吴烺、好朋友程廷祚在学缘上与颜李学派联系密切,程廷祚是李塨的学生、吴烺是李塨的再传弟子。因此“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29]190。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很推崇迟衡山和庄绍光,“前者喜欢考据学,后者是清代很有名的经学家,并且是特别着重实践的颜李学派的信徒。吴敬梓和他们做朋友,又十分推崇他们,是因为他同他们的思想一致,吴敬梓和他们都是顾炎武和颜习斋的后辈,又是乾嘉经学的前驱”[29]57-58。胡适通过考证,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宣扬颜李学派思想的小说”[30]910。亦有学者认为“吴敬梓传承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颜李学派的思想观念”,并通过文本考证得出《儒林外史》中“泰伯祠祀典仪注本于颜元的祭孔仪注”[31]的结论,认为《儒林外史》是在与颜李学派对话[32]74,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儒林外史》创作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的直接关联。因此可以看出颜李学派诸人的治生思想亦是《儒林外史》创作的重要思想来源。
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艺术形象塑造,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群体生存状况的不堪而导致人才质量下降的现实。士人群体作为传统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生存困境累积而成的精神风貌势必削弱其在文化创造和思想引领等方面的能力,进而导致整体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和治理水平的下降。因此,充分肯定传统士人群体作为自然人对物质需求并给予系统性制度保障,亦是《儒林外史》治生思想主题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