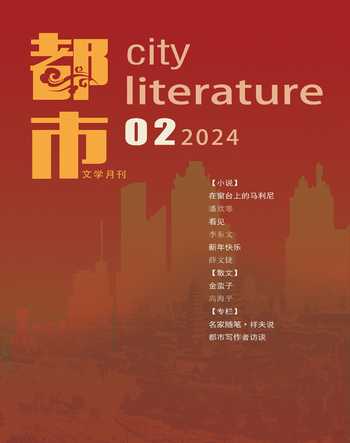一记耳光(外二篇)
“啪”,一记清脆的耳光落在我脸上,我一阵愕然。母亲是第一次对我动粗,我倔强地昂着头。看见母亲大而圆的眼眶里,瞬间噙满了泪水,我读懂了她的心疼,却无法选择原谅。
母亲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
那天,我和王阿二、华老三一道玩斗鸡,不小心撞到了班里的小霸王高浩兴。这家伙长得比同龄人高出一截,平日里仗着自己块头大,经常欺负同学,有时连女同学也不放过。我向来看不惯他,所以也不屑跟他道歉。
下午,上课铃还没响,高浩兴来到我面前,用挑衅的眼光盯着我,我回瞪他一眼,谁知,他手一扬,粉笔灰洒了我满鼻子满脸,呛得我连连咳嗽。我气不过,便冲上去和他扭打起来,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高浩兴人高马大,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他压在地上。王阿二就坐在我前排,瘦得像个猴子,平时与我很要好,关键时刻却被吓得蹲在地上,不敢施以援手。倒是我的女同桌秦霞,突然冲上来帮我,一只脚猛踩高浩兴撑在地上的手掌,另一只脚把他踢得翻了个个儿。高浩兴痛得哇哇直叫,爬起来一把揪住了秦霞的头发,死命地推搡。我又岂能善罢甘休,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抡起拳头砸向高浩兴的脑袋。一时间三个人扭打在一起,场面很是混乱。
母亲闻讯而来,一见到鼻青脸肿的我们仨,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扭过我的脖颈,不由分说,“啪”的一记耳光抽在了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痛感顿时钻到了心里,刹那间我愣住了,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安静得连喘息的声音都听得很是清楚,大家都怔住了。等回过神来,我夺门而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硬忍住没哭。母亲也瞬间呆住了,她想解释些什么,终究是什么都没有说。
我几分钟时间就冲回了家,抽泣着一头扎进奶奶的怀里。我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呀,平日里哪受过如此大的委屈。奶奶看见我脸上五个紫红的手指印,不由分说,从柴仓角落里找了根拐杖,一颠一翘地向学校走去。
事情闹大了。母亲是城里下嫁到北七房的“洋小姐”,从没和奶奶红过脸。奶奶此去兴师问罪,估计婆媳之间难以收场,到最后追根溯源,我肯定要被大哥再揍一顿。
我赶紧跑出去,把奶奶从街上拽回来,说是和同学打架,脸上是不小心被同学刮到的。奶奶半信半疑,却又万分心疼。她摸索着从床头蚊帐杆子上高高挂着的圆竹箩头里,掏出几块她一直舍不得吃的上海饼干,塞给了我。我无数次梦想得到的美味,就这样轻易地进了我的嘴巴,脸上火辣辣的痛,似乎也感觉不到了。
母亲没回家揪我,我便躲在被窝里拿本连环画有滋有味地读起来。《西游记》里猪八戒来到了高老庄,背媳妇的情节太有趣了,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傍晚,母亲回来了,她一声不吭,我也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我迅速瞥了一眼母亲,母亲的表情不是很自然,显得有点尴尬和无奈。
第二天早上,我照样拿了两毛早飯钱,在街上老虎灶转角处买了一只焖山芋,灵机一动,又挑了一只大个子的黄心山芋,准备送给昨天见义勇为的女同桌秦霞。至于那个拉胯的王阿二,从此再也享受不到我的美味早餐了。
走进教室,我旁若无人地把山芋塞到秦霞的手里,女同桌的脸涨得红彤彤的。华老三赶紧凑过来,悄悄对我说:“高浩兴被秦霞抓破了脸,他父亲来学堂里了,马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他父亲赔礼道歉,并到街上买了三个鸡蛋送给他的父亲。”又神秘兮兮地说:“秦霞扎头发的橡皮筋被高浩兴扯断了,马老师去店里帮她买了一只漂亮的花夹子……”
听着华老三的这些话,我再也忍不住了,鼻子一酸,眼泪像断线的珠子砸在了课桌上。我犯的错误,竟要母亲来偿还,想起昨天母亲那饱含热泪的眼,那一个巴掌分明是打在她自己脸上啊!此刻的我,对母亲的那一丝怨恨烟消云散,剩下的是深深的自责。
一个耳光,让我记了将近五十年。
第一次牵手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我们班换了个班主任,叫袁小萍。
袁老师高中毕业,来学校做代课教师,她负责教我们数学。她是北七房街上出了名的美女,大眼睛,长辫子,唱起歌来像只百灵鸟,婉转动听,过年时村里排演样板戏《白毛女》,女主角喜儿这个角色,一般是没人敢和她抢的。她除了人长得漂亮,演技也是杠杠的,那是我妈妈马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呢。袁老师不仅能唱会跳,上课时还会给我们讲故事,比如,小兔子的嘴怎么会豁成三瓣的?龟兔赛跑时慢吞吞的乌龟怎么能赢得了小兔子?这些秘密,都是她告诉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个新来的老师。
小学里,老师怕同桌关系太好,上课时串通一气,不专心,做小动作,一般都是男女生搭配坐。开学后第一堂课,便是重新排座位。男女生根据身高在教室外分别排成一行,矮的排在前面,高的排在后面,一边走一个,两两组合,轮到哪个是哪个。男女生是天敌,女生还容易被老师“收买”,会成天盯着男同桌的一举一动,稍有不对,就要立即汇报。因此,同桌之间一般都不理不睬,还要在课桌上用小刀划出一道明显的痕迹,谁越过“楚河汉界”,等待你的,可能是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头,或者头上磨薄有了刃口的钢皮尺,甚至还有在界线旁涂口水、鼻涕、鼻屎和万能胶的呢。
我小时候很另类,情商比较高,和女同桌关系都不错。老师一般靠口头表扬去收买女学生的举报,我直接用实物来收买女同桌的包庇,铅笔、橡皮、卷笔刀、花纸头,都是有力的“武器”,反正礼多人不怪,而且屡试不爽。所以,我的女同桌是不做“伪保长”的,还肯为我打掩护,轮到做值日生,要擦黑板、扫地什么的,我都不需要亲自干。
袁老师成天蹦蹦跳跳,很活跃,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各年级都要排练文艺节目,袁老师肯定会别出心裁,出一下风头。那时候,唱的歌,跳的舞,仍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班里挑选了五名男同学和五名女同学,根据身高排成两行,结对跳舞。我最矮,排在第一个,后面的男生们只要摆出手握红缨枪的架势就行,我却要和旁边排在第一个的女生手拉手,一只手互相牵牢放下面,另一只手攥在一起在上面作势住前冲。乖乖里个咚,那时候小孩子也封建,哪里见过男生女生跳舞手牵手的?试了一下,旁边的同学们都在笑,我更不乐意了,赶紧对袁老师说:“我手臂短,够不着,不好看,换一个人来吧!”
“蛮好的呀,不用换,”袁老师笑着说,“你俩身高差不多,看上去很般配,台型非常好呢。”
同学们听了,一片哄笑,旁边的女同学倒没说啥,我却再也受不了,转身就逃进了教室。
袁老师虽然是班主任,但毕竟是新老师,有点下不来台。她立即跑到办公室搬救兵,把教我们语文的马老师请来了。
马老师是我的母亲,而且是小学部的负责人。听到袁老师告状,她二话不说,立马闯进教室,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拎了出来。我又痛又委屈,无赖地往地上一躺:“救命啊,救命啊,老师打人啦……”顿时,校园里热闹了,师生们涌出了教室,连后面初中部的老师也跑出来看究竟。一看是马老师训儿子,都捂着嘴,散掉了。
想到上学期,我和同学打架,母亲竟当众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便更委屈了,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我知道,我的哭声肯定能招来住得不远的奶奶,光天化日之下马老师也不敢再次动手。这样,也许袁老师就不会再让我牵着女同学的手跳舞了。马老师见我大哭,扭头就走,挥挥手,让袁老师带着学生进教室,把我一个人晾在了操场上。
我也识相,停止了哭泣。哭了也没人听,白白地浪费眼泪,不划算。我仰天躺在草皮上,呆呆地望着天空,没有云朵,没有飞鸟,虽然日暮西山,也不会有星星和月亮。我变成了一个无趣的傻子,迷迷糊糊,居然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一只脚在轻轻踢我。我睁开眼睛一看,竟是刚刚和我牵手跳舞的那个小女孩。她倒背着双手,柔柔地笑道:“起来了,起来吧,我都不害羞,你为啥要难为情呢?袁老师让我来告诉你,动作改了,下次我们跳舞,动作和后面的同学一样,不必再牵着手了。”
“真的吗?你不会是袁老师派来骗我的吧?”我故意凶巴巴地盯着她说,直到看见她的脸,和晚霞一般,变得红彤彤的。
我一骨碌爬起身来,顿时心情大好……
多年以后,忽然想起,那个我第一次牵手的女孩,那张红红的小脸,在我心里闪了一下。
摸 蚌
小时候,我和阿明喜欢看连环画,也就是通常说的“小人书”。这种书有半本课本那么大,页面上,上边是图案,下边配文字,通俗易懂,特别适合小学生看。
小人书是成套的,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每套三十本左右,一本两角钱,那么整套就要六元钱,超过一年的学费了,农村里的孩子根本买不起。我父母是老师,每月有工资,所以条件稍微好一点,可以把零花钱省下来去买几本,但也买不全。我想了个好办法,整套连环画,发动班级里有兴趣的同学,大家一起分别购买,内容不重复,这样,很快就能凑齐一套,参与的同学可以轮流看。
阿明是我的好朋友,他家里的条件特别差,就是二角钱,也拿不出来。他妈妈省吃俭用,负担他和妹妹的学费,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阿明实在开不了口要钱。怎么办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和阿明苦思冥想,终于有了一个好办法:摸蚌!换钱!买书!
我们的家乡,三万六千亩白荡圩连着十万八千亩芙蓉圩,河网密布,水产丰富。除了鱼虾,河底里还有无数的蚌和螺蛳,如果能摸到那种可以用来人工嫁接培育珍珠的三角蚌和鸡冠蚌,那就更值钱啦。
星期天的下午,我來到阿明家里。打开水缸盖子,舀起满满一瓢凉水喝了个痛快,阿明从墙角落里翻出一只蛇皮袋,我俩光着脚,沿着村后的石驳岸向北塘河的通济桥跑去。
以前听大人们说过,通济桥下面的河道里有许多巨大乌黑的三角蚌,一只就能卖几块钱。但是,通济桥下水流湍急,几乎年年都有游泳的人被淹死,所以敢去的人不多。小人书的诱惑,像无数条章鱼的爪子,揪住了我们的心,要是真能找到这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定把桥下翻个底朝天。
我俩像一阵风似的卷到了北塘河边。通济桥的南北桥堍以巨大的金山石砌成,桥面用五块十几米长的厚石铺就。长方形的桥洞下暗流涌动,常年盘踞着几个水缸大的漩涡。一路奔腾而至的河水,到了桥下突然收窄,河水就如耀武扬威的巨蟒突然被塞进了铁笼,在此处显得分外暴躁。翻滚的巨浪不时撞击着桥墩,粉身碎骨之后悻悻地向东而去。
阿明顾不上安不安全,从堤岸上扯着一把藤蔓就下到河里去了。俗话说,“六月六,猫狗淴冷浴”。可现在还没到农历六月,河水的上半段和下半段,犹如剃头担子一头热一头冷。我也慢慢地爬下河堤,入水的刹那间,腿肚子上传来一阵刺骨的寒凉,我一哆嗦,差点抽筋。好在阳光火辣,加上运动时人体会产生热量,我俩在水里游了一会儿就不冷了。整个下午,我们轮流下潜,为了安全,腰里拴了根绳子,一个人潜下去,另一个人留在岸边攥紧绳子确保安全。就这样,我俩在通济桥下的深水里反复折腾,直到累得精疲力竭。阿明的潜水功夫了得,一口气能憋很久,从河底的淤泥或乱石缝里,抠出不少河蚌。我主要负责配合,把阿明摸到的蚌,小的扔在岸上,大的装在河边的蛇皮袋里。漩涡和暗流不时地把我们冲到下游,但我们又很快游回桥下,像两条拼命去上游产籽的大马哈鱼。
傍晚,彩霞满天。我俩爬上岸,单腿跳跃,抖掉耳朵里的积水,开心地瞅着那大半袋子的收获。倒出来,清点一番,有一只比我的头还大的三角形老蚌,边缘锋利,漆黑发亮,阿明说:“这个家伙最难搞了,我换了三次气,才把它从黑铁木托的河底里抠出来,上了岸感觉整个人一点力气也没了。”
我俩懒洋洋地躺在北塘河的岸堤上,一动也不想动。平时声嘶力竭的知了,此刻竟然叫得很欢快,大运河里波涛汹涌的流水,一时也变得风平浪静。体力恢复了一些,我俩便抬着装了半蛇皮袋的蚌,喜气洋洋地回去。我们知道,菜市场西南角有人收购河蚌,于是跌跌撞撞地向那边走去。
20世纪70年代末,前洲的珍珠养殖业如火如荼。所以,除了那个最大的三角蚌,其余的很快被一个叔叔花三块钱包了去。阿明虽然是个孩子,也知道奇货可居,光着膀子捧着它在菜场里走来走去。不少人被这只罕见的大蚌所吸引,不由自主停下来看稀奇,有的人还拿起来掂掂重量,但是三块钱的开价,让他们频频摇头。
天色渐暗,菜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三角蚌还没有找到买家,我们又饿又累,恨不得把这个大家伙扔回河里。终于,有一个阿姨过来问:“两块五卖不卖?”我抢着说:“卖卖卖!”
阿明攥着五元五角钱,脸上笑得像朵花。第一次赚钱,不仅体现了自身价值,而且还做成了人生的第一笔生意。阿明把钱递给我,让我保管,他怕带回家里没处藏,万一被他母亲搜去,就白忙一场了。
扳着指头过了一周,我俩步行八公里,来到前洲街上的新华书店,买了全套的连环画《三国演义》,整整三十一本小人书呀,我俩开心地跳了起来。
责任编辑 阎 畅
作者简介:
周宏伟,1967年生,江苏无锡人。散文、小小说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工人日报》《北方文学》《广西民族报》《作家文摘》《海外文摘》《青春》《红豆》等报刊。曾获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