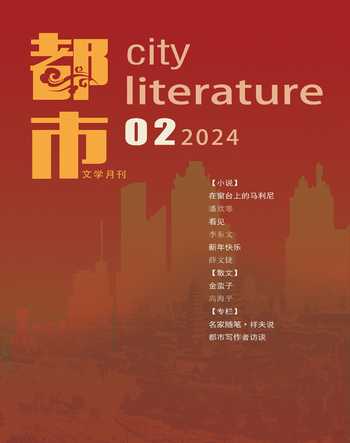随笔六章
大雪帖
“大雪”这个节气很富有诗意,试想早上一起来从屋里推门推不开,从窗子里朝外望望,原来是一夜大雪封了门,人需要从窗里跳出去扫雪,把封门的大雪扫开人才能从屋子里一个接一个地出来,这样的早上,随便望空一喊,或者是哪怕咳嗽一声声音也会显得格外的清亮。大雪之后的清早,不知为什么总是能听到喜鹊的叫声,也真是格外的清亮好听,“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喜鹊不开口不说,一开口就是连叫四声,叫两声的没听过,叫三声的好像更没听过,它落在树的最高枝上,在大雪过后的清晨,尾巴一点一点:“喳喳喳喳,喳喳喳喳。”什么意思呢,没人知道,但总是喜庆的,好听的,没人不喜欢喜鹊叫。而老鸹的叫声却往往是一声,成群的老鸹从空中掠过,它们是你一声我一声地对答交谈,好像是在高空中讨论着什么,但它们的叫声总是一声或者两声,“哇——”“哇哇——”,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叫着飞着叫着飞着就那么飞远了,也不管人们在下边有多少想法有多少疑惑,它们才不管呢,它们说完就完事了。人们看着越飞越远的老鸹都会在心里想,它们这一天一天地飞来飞去,它们到底是去了什么地方?这简直是没人知道,到了晚上,它们又飞着叫着飞着叫着地飞回来了,它们晚上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它们的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医院附近,医院附近的那些个树上一到了晚上就会落满了老鸹,几百只,或者比几百只还多,有人到那些个树下去扫老鸹粪,一扫就扫半筐。据说这些个老鸹粪能治眼疾,但怎么个治,谁也说不清,弄些个老鸹粪直接抹眼睛上吗?我问过几个中医大夫,但他们都说不知道,这种事问西医可能也不行,西医不懂这个,西医懂X光,你到医院去看病,西医大夫一准儿会让你先去照X光,他们哪会知道这种事。有人说这事得去问大仙,但现在去哪儿找大仙?鄙人东北老家的萨满也许会知道,但买张票回去就为了问问这事也不值得,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老鸹粪被拿去做了什么。现在的许多事都问不清,越问越乱,还是别问的好,比如说你找个鸟类专家问问这些个老鸹在高空中都“哇哇”地说些个什么,他们肯定也回答不来,谁也不知道它们整天在高处胡说些个什么。
下大雪好,鄙人从小就比较喜欢下大雪,一下大雪就可以出去堆个雪人,找根胡萝卜当鼻子,找两个小煤球做眼睛。大雪这节气有一点不好,就是到处都能听到猪叫,这个节气是杀猪的正经节气,在鄙人老家的东北,要吃杀猪菜,但那锅酸菜炖猪肉是能吃不能看,那么老大的一个锅,里边“咕嘟咕嘟”满满炖的都是酸菜和猪肉——平时那大锅里煮的可是猪食,里边烂白菜叶子的什么都会有。酸菜炖猪肉据说是越炖越好吃,但我可不喜欢。还有就是大雪一过就可以蒸粘豆包了,豆包师傅这几天是最忙的时候,他是被请到各处去给人家和面,他只负责和面,头天和好面,隔一晚上第二天再来看看面发好没有,“发好了,蒸吧。”他一声令下这一家人就得忙一整天。多少粘高粱配多少白面居然也是学问,关于这一点,你去问大学的教授他们也会说不出来。做粘豆包在东北是件大事,一冬天吃的粘豆包要一下子全被蒸出来,然后全放到院子里去冻。豆包师傅也不收什么工钱,顶多是拿些个粘豆包回去给他老婆交差。
今天是“大雪”,外面照例是听到了喜鹊在叫,一连四声,一连四声,可真是清脆好听,太阳现在也出来了,说是“大雪”,但老天爷连一点下雪的意思也没有,老天爷现在真是太不解人意了,你想让它做什么它偏不做什么,这就是现在的老天爷,我日它祖宗的。
春之色
关于春天的颜色,王安石曾经说过: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七个字来得真是好浩荡,自从他写过这样的一句,别的人再也作不出像样的句子可与他相比。想他当年坐一只小船浮在江上,除了看看两岸山色,想必还会喝喝酒,或再吃点什么。我是没有学问的人,至今都不知道宋朝那里都有些什么吃的,尤其是拿什么东西来下酒,因为这个问题我最近还特意查了一下花生的历史,因为花生是下酒的好东西。花生传入中国要比胡豆晚,大约在1530年,先是传到了中国的沿海一带,然后才大举进入内地,所以说王安石并没有吃到过花生。日本的花道家田中昭光说迎接春天到来的花大多是黄色,他这话说得极有道理,是观察过的,而不是信口胡说。别的不说,一年四季先开的蜡梅首先就是黄颜色的,从没听谁说见过红色的蜡梅,这是没有的事。蜡梅之后的迎春花照例也是黄的,迎春开花是泼泼洒洒,是左泼一下,右泼一下,这么泼一下,那么泼一下,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那么多颜色,到处泼来泼去,到处泼来泼去。于是,春天就给它们这一泼两泼地泼来了。
我这个人,是看到花也会想到吃,但我不知道迎春花可以不可以吃,我想如果它也能够像藤萝那样可以用来蒸藤萝饼就好了。还有田头那些俗称“婆婆丁”的蒲公英,自然也是黄的。蒲公英的花可以吃,一小朵一小朵拖了面糊炸出来——起码是不难吃。日本人不管什么都会用来做天妇罗,这个叶子那个叶子或者是一大段亮紫的茄子照样也会被放在面糊里拖拖放油里去炸,还有黄瓜花,居然也可以做天妇罗。用什么做天妇罗完全取决于早上起来天妇罗师傅在菜地里碰到了什么。
黄颜色鲜明爽利,让人眼睛舒服。日本作家田山花袋在他的一篇小说中这么写道:“主人公躺在那里,两眼望着外边,对他的女朋友说:‘等到油菜花开过后我再死吧,我要再看一次油菜花。”什么是诗意的人生,这才是诗意的人生,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还记着花。
油菜开花,动辄是一大片一大片,黄得让人心亮,所以各地都好像有油菜花节。油菜花的最终作用当然是结籽榨油,我吃的油里边以菜籽油居多,从小就吃这个,说它好,它好像又太普遍了,让人想不出它的好;说它不好呢,老不吃还让人想得慌。至于已经在中国贵族化了的橄榄油,吃不吃也就那样,你要是对别人说我有多么多么想念橄榄油,别人肯定会笑你。
夏日冰
那年在承德,看到人们开着大解放车从冰窖里往外一车一车拉冰,忽然才知道冰原来也可以放到窖里储藏,据说可以放一年,冬天储存好,到了夏天人们再把它们从窖里取出来做刨冰。用那么个小碗,里边放点葡萄干什么的,很好吃,到了夏天谁不爱吃点凉东西?只是不知道承德的那些冰窖现在还在不在,但我还记得那个冰窖,在去外八庙的一个高土坡上,车可以直接开进去,想必里边很阔大很深,而且还凉飕飕的,但冰在里边怎么放我就不清楚了。在日本,到了冬天也要储存冰,在选好的河里取冰,用锯把冰锯成长方形冰砖然后拉走,据说他们藏冰要用土,一层冰一层土地码起来,也是到了夏天再把这些储存好的冰卖出去给人们做刨冰。日本跟中国一样,到了夏天街头有不少卖刨冰的,刨冰的小贩使一个很锋利的铲,一下一下从整块的冰上往下削冰沫儿,用一个纸碗在下边接着,也是往里边掺一些甜甜酸酸的东西,或在冰上浇一层红豆泥。红豆泥当然是甜的,起码鄙人是没吃过咸的红豆泥。鄙人的爱人很会做红豆泥,锅里放很少的水,但那豆子居然很快就被煮熟了,但说“煮”像是不对,是“烀”。我们这地方把煮豆子叫作“烀”,东北那边也叫“烀”。东北和山西最北部的古平城有许多语言都相通,因为什么?因为一千六百多年前鲜卑人在这地方建过都,而且为时不短,整整九十六年——差不多一个世纪。那年这地方搞城建在城北离四中不远的地方挖出了不少东西,我记着有很多的鹿角,但人们都不清楚古时候的人们搞那么多鹿角做什么,一时说什么的都有,但有两种说法像是比较靠谱,一种说法是御厨在这里,但御厨用鹿角做什么菜?人们又说不上来了。另一种说法是估计北魏的医药局在这里,所以留下这么多鹿角。平城以西,在接近西山的地方有个叫“鹿野苑”的地方,曾经是北魏皇家的狩猎场,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是既没有鹿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比如野猪、狍子什么的,只是野鸡还是很多。在野外草地上行走,忽然,吓你一跳,就从你的脚边扑棱棱棱飞起一只野鸡来,或是一群,你根本就看不到它们,你想不到它们居然就从你的脚边飞起来。我的二位兄长都喜欢打猎,我认为这是遗传,因为我的父亲就喜欢打猎。但我的父亲比我的两位兄长走得远,我的父亲去内蒙古草原去打,走两三天。有一次他扛着一只黄羊回来,血淋淋的一只,用麻袋包着,父亲直把它扛到屋里来,扑通一声把它撂到火炉子边上。黄羊肉不好吃,不知道怎么有点酸。我记得那会儿是冬天。我的兄长他们都有很好的猎枪,但有一年政府下令要人們把枪都上缴,那就上缴呗。我的两位兄长可真都是守法的老实人,他们连架都没打过,要打,也只会和自己老婆打,我们这地方把跟老婆打架叫“干仗”,有点夸张是不是?虽然滑稽,但想想这种举轻若重的说法对男性可以起到某种安慰作用,所以我表示理解。
有人告诉我承德那些藏冰的冰窖过去都是专供皇帝用的,跟老百姓无关,北京据说也有好多处冰窖,不过人们也许并不知道。
说到夏日的冰,一般人都不会整块整块买来咯嘣咯嘣放嘴里咬着吃。在印度,街边到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摊儿,差不多隔几个摊位就会有一个卖刨冰的,他们用的是木匠的刨子,只不过是把它们倒过来放着,固定在那里,让它们老老实实别动,小贩儿一只手拿起冰块在上边反复推拉,另一只手里拿个杯子把刨出来的冰沫子接住,然后再往冰杯里加点这个再加点那个,然后递给旁边等着吃它的人。我站在旁边往往会看良久,往往被小贩的飞快动作搞得眼花缭乱。我也想试试来一杯,但再一想那个“万人杯”你用了我用我用了他用,他用了他他他再用,终于不敢上前一试。
卫鸦在印度待了好长时间,居然说那边的东西很好吃,这简直把我吓了一大跳。想必他除了吃印度的稀糊饭还用了不少次那种万人杯,这得需要有多么雄壮的胃口。
向卫鸦致敬。
日常帖
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天天早上一起来就去写字,写字的时候往往还没洗脸,每天都会写几张几乎是正方的那种元素纸,然后才去洗脸,而且习惯是一边洗脸一边看看已经张贴在墙上的字,自己给自己找找毛病。然后才是画画,有一阵子,几乎不用想,天天早上一起来就画工笔草虫,蜻蜓、螳螂、蜜蜂、蚂蚱……我很少画蝴蝶,蝴蝶看上去好看但画不好很难看,色彩越是漂亮的东西画出来往往越不好看,比如锦鸡,可真是漂亮,但画出来就很不好看。孔雀也一样,费劲巴拉画老半天,费不少颜料,挂出来一定是很像大花被面。牡丹画一枝两枝、两朵三朵可以,如果六尺整张画一大幅,张挂起来可不就又像是乡下人喜欢的那种大花被面。我有一阵子是天天画梅花,每天画一幅,画完才去吃早饭,我画梅花从不用胭脂,只用赭石:点花朵也用赭石,染老干也用赭石。趁老干上的赭石还没干,赶紧再往上加一点点三绿,赭石加三绿可真是好看,梅枝转绿的那种气息一下子就出来了。画梅花所用的时间会短一点,如果画工虫就比较费时间。我画工虫,一般是用三平尺或兩平尺纸,而且只喜欢用生宣,一张纸上只画一只虫子,现在已经积攒了不少在那里。画虫子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我一旦死掉,我的女儿会把它们慢慢卖掉以做家用,所以画得十分工细。
我的日常,天天一起来就这样,先写字、画画儿,画完画儿会去阳台给阳台上的花浇浇水。有一阵子,我决定从此不再种花了,我决定种菜,想了想,决定种西红柿、青椒、豆角、茄子,从花市那边买了菜秧子,还买了不少那种用羊粪做的农家肥,还有各种搭架子用的材料——豆角、西红柿,包括茄子和青椒都需要搭架子。在阳台上种菜的时候,天天早上一起来的功课就是给菜浇水,但阳台上种菜实在是不行,首先是生虫子,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虫子。翻开黄瓜的叶子看看叶子的背面,有密集恐惧症的我被吓了一大跳,叶子背后已经布满了虫子。各种的菜里边我特别喜欢茄子,喜欢它的那种颜色和那种特有形状。前不久我去重庆的大渡口,那边有个地名居然叫“茄子溪”,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最近就用这个“茄子溪”为题写了一篇小说。好的题目或地名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一下子就让人记住,比如我在云南,具体是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居然有个地方的地名叫“养龙所”,我想这个名字是不是太特殊了,如果在封建时代,这个名字一定不会被允许存在。
在我们北方,秋已去而冬将至的时候屋里最难让人将息,真是十分的冷。我一直住着的那套老房子的暖气年久失修,即使是来了暖气也不暖和,今年冬天快要来的时候,我就和我爱人商量着搬到另一处房子里去住,那边暖和些。就这样,冬天不觉就已经来了,冬天和春天不一样,春天来的脚步要慢一些,慢慢慢慢地往过走,而冬天却是要不来就不来,要来一下子就大步大步地走过来了。虽然我已经搬到了另一边,但我还是经常会回老房子取东西。有一阵子我去了外地,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下过了一场雪,那场雪不小,地上都结了冰,我忽然想到了老房子大露台上边的那些花草。我在露台上种了不少花花草草,薄荷就有十多盆,春天来的时候我会用它来炒鸡蛋,味道不错,我还试着用薄荷包过饺子吃,是完全的不行——我这饺子是“清凉油”牌的——但下面条的时候在面里放点薄荷还真不错。到了云南,几乎什么菜里边都要放点薄荷,这可让人受不了,但比起放折耳根我还可以接受。
从去年开始我就不再在阳台上种菜,只种各种花,我喜欢那种蓝色的和黄色的野菊花,居然从网上买到了种子。这两种菊花开花真迟,深秋才想起开花,一小朵一小朵的花真是碎叨叨的,但不难看,也好闻。忽然间,不知从哪里一下子飞来了那么多的蜜蜂,一夏天它们都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它们出现了,小菊花加上小蜜蜂可真是热闹。下过了一场雪,地上到处结冰,我忽然想起了它们,忙赶回去看。我发现露台上的花不是冻死而是早已全部干死掉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里很难过的事,我对那些枯死的花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在心里想,它们明年还会不会重新长出新苖?菊花应该会,我希望它会,也希望其他的花也会。
“对不起,明年见。”我听见我自己说。
人和花是有爱情的。
冬日初
立冬之后按说照例就已经是冬天了,随着朋友去郊外看了一次红叶,说红叶似乎不太准确,应该是黄叶。鄙乡以北的左云与右玉一带道路两边种的都是杨树,现在叶子都已经黄了,因为杨树,鄙乡还有一个“杨树局”,每次我从那个院子门口走过看到那个牌子都会感到奇怪,如果杨树也可以成立个局的话,那么可以成立局的树一下子就可以列出许多,像什么苹果树、梨树、枣树,这个树那个树可真是太多了,比树重要的还有麦子,还有玉米,还有棉花,还有大豆,还有高粱,那可也真是太多了,但那个局现在还在,而我每次从它的门口经过照例还会在心里感到纳闷,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院子的门口倒是种了两棵很高很粗的杨树。
杨树叶子的黄,我认为要比银杏叶子的黄重一些,但没银杏的叶子黄得那么透亮。如果不看银杏的叶子,杨树的叶子一旦被秋风吹黄,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黄色的杨树叶子被西斜的阳光一照可真是好看。红叶在鄙乡好像不太容易看到,可能是与树种有关,我都想不出来在我们那地方秋天有什么红叶,但黄叶衬着高蓝的天着实要比红叶好看些。虽然我们那地方只有黄叶可看,但一旦说起去郊外的事,朋友们照例是说“走,去郊外看红叶”,好像不会说“走,去郊外看黄叶”,好像人们已经习惯把秋天或红或黄的叶子统统称之为红叶了。
去左云和右玉看完黄叶,不久便下了一场小雨,天突然冷了下来。这天早上起来去外边吃早点,手就有点伸不出来了,只好把手放在豆腐脑的碗上取暖。我早上起来照例是要来一碗热乎乎的白豆腐脑外加两根刚出锅的油条,豆腐脑里我会放许多韭菜花和油泼辣子,我喜欢这种刺激,白豆腐脑上浇韭菜花和油泼辣子也好看,碧绿的韭菜花、红的油泼辣子、白色的豆腐脑放在一起可真好看。我的口味比较重,比如在北京吃早点我就特别喜欢在炒肝儿里边放大量的蒜泥,北京的炒肝儿放蒜泥是一个味儿,不放蒜泥又是一个味儿。因为天一下子就变冷了,我一边吃着豆腐脑和油条,一边就想着回去把母亲给我做的那件坎肩找出来。那件坎肩是用我穿过的一件旧衣服改成的,去掉了领子和袖子,上边钉着五个黑色的四眼圆扣子,是母亲给改的,里边还絮了一点絲棉,穿在身上很是暖和。我每年都会把它找出来穿穿,也只是穿几天,我不舍得整天穿着它。母亲离开我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如果经常穿着它,它一旦被穿坏了可怎么办?这么一想我心里往往就会发慌,就会赶紧把它脱下来。但我想最近应该把它拿出来穿穿,尤其是这几天,虽说过了立冬就可以说是冬天来了,但好像它还没有正式来,所以屋子里的暖气还没开始送,一早一晚可真冷。
坐在那里吃着豆腐脑和油条,我突然想起母亲给我做的坎肩了,那上边从里到外都是母亲一针一针缝下的针脚。关于这件坎肩,我是既不洗又不让别人碰它,我个人坚决地认为母亲的气息还在上边,如果一拆一洗,如果一拆一洗,如果真得一拆一洗,这样的坎肩怎么可以拆洗呢?
是为记。
松竹梅
马上老弟,你说你最近要从南面过来,问我可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带给我。
现在已经是年底了,虽然没有下过太像样的大雪,但天气却突然大冷起来,昨天和前天的晚上居然冷到零下三十二摄氏度,这可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今天是冬至,按照老天爷的习惯,北方要在正式数九之后才会大冷,所以,一下子冷到这样,真是让人想象不到。我已经把皮衣找了出来,是一件去年爱人给置办的貂皮大衣,我想也不是什么好貂,但穿在身上着实是可以抵挡外边的风寒。这么早早地就穿起貂皮在北方也是不多见。所以,你要是真想绕道过来看我,最好有所准备,起码要穿厚一点才好,才不至于冻到,在半道上作筛糠状。
这次你回来,因为你问我想要什么东西,你还特地说到了“八宝印泥”,八宝的印泥我已经有几盒,但平时都不用,因为八宝印泥太夺色,一幅画挂在那里它那个红显得特别的扎眼,所以我一般只用朱膘,颜色更优雅一些。
这次你回来,我忽然想让你带两件东西给我。一是梅花,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正经梅花开放的季节,但蜡梅想必差不多快要开了。我那年在昆明,是深秋季节,秋雨绵绵的,居然看到了蜡梅在雨中开着;还有一次是在泉州,居然也是在秋雨中看到了它,花朵不大,小小的,但很香。而且我还记着那次是在著名的“草庵寺”。
你这次回来,我只要一两枝蜡梅,你用个大一些的纸盒子把它带回来就行,因为是坐飞机,就不要特殊的处理,你放心,它不会在半道上干死掉。现在说到梅花,当然只能是蜡梅,正经的梅花现在都还在梦乡之中,所以想都不必去想。还有,除了梅花之外你再给我折一两枝竹子来,就道边的那种小细竹就可以。
这是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想到的事情,我要在这个岁尾插一个松竹梅“岁寒三友”出来。花瓶已经准备好了,是用一个大号的日本备前烧的花瓶,备前烧的特点我也跟你说过,是朴素之中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备前烧一般是不上釉的,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泥土和火的杰作。我这只备前烧花瓶上有许多蟹目,也就是连着烧十多天才能出现的那种非常美丽的结晶体,就跟螃蟹的小眼睛一样,白白的一小粒一小粒,特别的好看。
今年马上就要过完了,今年是一个让人特别不如意的年份,所以我要在岁尾的这个时候插它一个松竹梅的“岁寒三友”出来。这原本是一个极为传统的题材,无论是插花或画画都是常见的,但常见的东西未必就不好。还有就是松枝,这个好说,我院子里就有,我去折一枝白皮松的细枝就好,这你也知道,我对白皮松是情有独钟的。这几天我院子里的那株白皮松的叶子已经绿到发黑,愈发显出它于西北风中的凛然,你冷你的,我依然绿着!这我是喜欢的。
听说你马上就要回来,酒我已经准备好了,你问我都想要些什么,我也想不起别的什么想要的东西,其实有你在一切都就有了。但你看你看——我还是想到了梅花与竹子,因为这两样东西北方没有,起码是我这里都没有。
好了,就到这里。
责任编辑 刘照华
作者简介:
王祥夫,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作品见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山西文学》《黄河》《新华文摘》《芙蓉》《江南》等刊物。文学作品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赵树理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