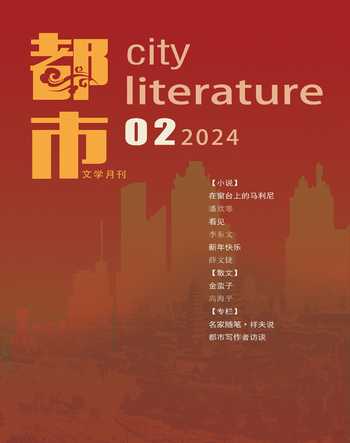曾剑:源于个人体验的表达
曾剑,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等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及中国军事文学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向阳生长》《山河望》,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玉龙湖》《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等。曾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及短篇小说奖、方志敏文学奖等若干文学奖项。
曾剑是实力派军旅作家,近年来长、中、短篇小说数箭齐发,引起文坛关注。他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获得方志敏文学奖,中篇小说《比远方更远》获得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哨兵北舞》入选“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十年选”,这些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盈荡着细腻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作为人的个体生命的身份困境。作家曾剑是真正把兵当作人在写,而且這样写非但没有减损他笔下这些战士的尊严,反而让这些军人更有灵魂的活力,更具挺立的精神力量。
主持人:曾剑老师是凭借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登上文坛的,比如你前期的短篇小说《今夜有雪》《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饭堂哨兵》等,带给文坛一股清风,你能对你这些初期的军事文学作品做个简要概述吗?较之当下的军旅题材文学作品,它们有着怎样的个性与共性?
曾剑:我初期的这些军事文学作品,与前辈军旅作家们的作品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农家军歌”式的叙事,但与那些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进入军营的军旅作家不一样,我是属于90年代入伍并在部队成长起来的作家,有着对部队、对军营新的感悟,有着我们这一代军人在军营的独特体验。我作品里的主人公,与莫言、阎连科、陈怀国们笔下将当兵等同于“吃公家饭”的身份设定不同,比如《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里的“我”,除了想走出农村,更多的是出于对军装和军营本身的渴望,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支撑他走向了军营;再比如《哨兵北舞》里的韩泽中,他本身就是城里人,而且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他当兵,纯粹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男子汉——多年跳舞的他,行为举止有些阴柔,他想让自己变得阳刚。通过在军营里接受锻造,他达成了愿望。他做到的,不仅是言行举止更加刚劲有力,更主要的是,军营生活经历在他心灵上、精神上烙下了印痕,他呈现给战友的形象从而变得孔武有力起来。
军营崇尚的是令行禁止,讲究的是整齐划一,但作品中的人物,要走出共性,写出其个性。比如我的短篇小说《穿军装的牧马人》,就是“个人化写作”的一种尝试。我努力写出其个性,写出这位军营“牧马人”不同于其他拿枪操炮的战士的地方。有读者说这篇小说读起来语言轻盈,其实我创作时写得很艰难,一直找不到开头的那个句子。先是用第三人称,后来怎么写都觉得很“隔”,很飘,沉不下去,不真实。大约三四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像是突然来了灵感,我选择了第一人称,就当我面前坐着几个地方的朋友,我向他们讲述一个发生在边防军营里的故事,小说由此展开叙述。
我借第一人称,将“个人化写作”运用在这篇军旅文学作品中,其实是借个人化写作的幌子,写出军人的“独特性”;但我同时也意识到,不能失掉作品的普遍意义,也就是“我是谁”这样的人类普遍的问题。士兵也是人,唯有逐渐解除这种生命的大困惑,解决了身份体认的模糊性问题,才可能成为一个坚如钢铁的士兵,成为一个坚如钢铁的人。我以“个人化写作”的方式展开,用个体生命感受和情感力量推动人物转变,容纳哲学命题,解决人生疑难,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刚入伍战士的内心困惑。
主持人:请谈谈你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吧,关于长篇小说创作,你有哪些创作理念?你认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才是好小说?
曾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讲述了湖北红安大别山南麓这片被革命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杨氏家族四代人从军卫国的故事。杨向阳的二爷(小说中的“二爹”)十三岁时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此后音信全无。二奶每天到后山坡盼着丈夫回来,这成为竹林湾一道永远不变的风景。二爷成为杨家后人的精神导师,也成为作品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灵魂的指导下,二爷往后的三代人,前赴后继,踏入军营。因杨向阳家弟兄多,杨向阳便被过继给聋二当儿子,并得到了聋二浓浓的父爱。在聋二的教导和影响下,杨向阳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官,以文学的形式传递大别山的红色精神。聋二去世后,杨向阳发现聋二身上因战争留下的伤痕,才知道养父的退伍军人身份。杨向阳回想起养父的教导,终于明白养父红色精神的来处。杨向阳感念养父的恩情,以亲生儿子的身份为他送葬,将养父埋葬在金色的油菜花丛中。
《向阳生长》出版后,好评不断,先后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以及凤凰网等数十家媒体报道,获得著名作家苏童、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老师等的赞许。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是有一个企图的,我想努力地把家族史放置于中华民族史中,最后是否达成了这个目的,不由我说了算,得看读者评价,但我的确做了这样一种努力。
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要调动作家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我认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它故事要好、语言要好。要把长篇写好,作家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去书写、去打磨。
主持人:我读过你很多小说,对你的小说语言印象深刻。你喜欢用短句,语言简洁、凝练、有韵味。你在小说创作中,对语言有什么要求?
曾剑:我对语言是有要求的,甚至可以说是追求。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也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好的语言来铺陈,单纯依靠故事内核、情节的反转,这样的作品算不上好小说,那只能是停留在故事层面。
我一直注重语言的打磨。语言好,并不是用华丽的辞藻来堆砌,相反,用词要准确、要朴实,要用独特的语言写出细节,在细节描写中体现语言的力量。我在《饭堂哨兵》中写那个哨兵:“哨兵这两个字,从哨兵自己的嘴里喊出来,传进耳朵,哨兵心为之一震,如同听到自己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让他恢复成哨兵,于是,哨兵挺胸、抬头、收腹、提臀,两腿绷直,两眼平视前方,把自己站成一个标准的哨兵。夜的黑漫过来,路灯的光,像夜幕里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一个哨兵站立的姿态,其实是留在他脑子里的,那个画家笔下的哨兵,阳刚、帅气、有质感,像一尊青铜雕像。”我认为我的描写是准确的,我对这个哨兵的原型太熟悉了,我每天去饭堂都能看到他。
但我知道我的语言功力其实还很欠缺。看看莫言老师在《红高粱》中关于红高粱的描写:“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些句子时,被震撼到了,我甚至没有刻意背诵,就能复述出这些语句来。莫言老师的语言有音乐节奏感,有颜色,有气味,有一种拉紧了弦的弓一样的张力。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军旅作家”这个标签?你觉得这样的标签是否有利于宣传你和你的作品?
曾剑:“军旅作家”这个标签,给了我光环,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羁绊,我正努力地在创作军旅题材小说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近年我在《当代》等杂志发表了《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慈悲引》《太平桥》《后现代的花枝》等乡土题材小说,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有的作品还进入年度小说选本。
我其实很热衷于书写乡土题材小说,这些小说,既是我对故乡的灵魂依托,更是我内心的精神指向。我写故乡,比之于军旅题材,更依赖于现实,作品里的主人公,现实中大都确有其人。乡村女性在我笔下的样子都很纯美,如槐花、秀清、春光嫂及部队驻地的女理发师、房东儿媳等,她们都是那么善良温婉。这些人物,现实中确有其人其影,但她们与现实中也有差别,并非我作品中描写的那么完美。她们其实是我内心希望她们成为的那个样子。乡土题材的作品,是我在军旅小说题材之外的突破与突围。
主持人:曾剑老师刚才谈到“军旅”与“乡土”,您如何看待“都市文学”或者说“城市文学”?我印象中你也写过一些让我感到难忘的“都市文学”作品,但数量不多,能说说原因吗?
曾剑:我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从大山里走进军营,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农民成为军官,从放牛娃成为作家,我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其实都在城市中,可以说,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城市度过的,但我始终对城市不是那么熟悉。我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活经验为支撑的,所以,这就是我写都市题材小说比较少的原因。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城市是辽宁阜新,这是一个因煤炭而兴,又因煤的枯竭而面临发展难题的城市。我对阜新有着特别的感情。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军校毕业,来到东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阜新留住了我,让我在辽西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我是阜新的女婿,东北话叫“姑爷子”。我与阜新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近几年,“回望”成为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途径。我“回望”的目光,主要朝向两个方向,一是故乡,一是军营。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我的老家湖北红安,那个出了223个将军的革命老区,一个是第二故乡辽宁阜新。
中篇小说《玉龙湖》书写的背景即辽宁阜新,我写东北这座煤炭枯竭的城市里,人的生存状况——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很忧伤。短篇小说《岳父的桃林》,则以我岳父岳母等阜新老一代文艺工作者为人物原型,写他们一代人在那个年代的爱与温暖。他们的故事曾经感动过我。在我的笔下,阜新化名为“煤城”,因为阜新是煤电之城,另外,也是避免小说过于写实,毕竟小说是虚构的艺术。
主持人:你调入沈阳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时,部队的驻地在沈阳,后来你又定居沈阳。请谈谈你对沈阳的印象,以及你近年的创作与沈阳的关系。
曾剑:我非常喜欢沈阳,我住在沈阳地铁一号线二号线的交汇处。随着沈阳地铁线路的增加,我家到哪儿都很方便。我们小区附近,有沈阳最高楼恒隆商业中心,有市府广场。几年前,沈阳市委、市政府还都在这里。我曾说过,我们居住的小区,是沈阳的中心,而沈阳又是东北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我们小区也是东北的中心。这当然是调侃,可也表明我对这片地域的喜爱。
我的作品,与沈阳有直接关系的不多,作品与沈阳间接的关系则无处不在。
先说直接关系,我的短篇小说《荆芥的香味》《黎明》写的就是沈阳的人和事。我不想太具像化,所以我在作品里,把沈阳称为“沈城”。我以后會更多地写到沈阳,但是我笔下的沈阳,与“铁西三剑客”笔下的沈阳是不一样的。他们从小在铁西那片重工业区长大,沈阳工人及工人子弟的生活,是刻进他们骨子里、融入他们血脉里的。他们写沈阳,可谓信手拈来,而我不能,我不太熟悉沈阳,我没有沈阳工人阶层的生活体验,我仍然像沈阳城里的一个客居者,我写不出沈阳工人或工人子弟的生活。我只能写我自己的生活,写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对沈阳的体验和感悟。
再说间接关系。我在部队做专业作家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在沈阳,期间发表的作品都是在沈阳创作的。我已经习惯了沈阳的气候:四季分明,冬天很冷,但室内很温暖,当我披霜带雪走进家门时,对家的温暖体验是那么深刻。
我的叔伯舅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我七八岁的时候,他说我将来适宜往东北方向发展,长大后我果然来到东北当兵,后来成为专业作家。我曾有两次进京的机会,但都没成,我心里很郁闷。后来想起我舅舅的话,心里豁然开朗,原来这是命中注定。
这或许是迷信,但也有心理作用,至少可以开导我,让我放下某些东西。
我在沈阳已生活了十多年,但与那些土生土长的沈阳人比,沈阳于我,还是相对陌生的。但沈阳一定是我下一步书写都市文学要拓展的一块疆土。
主持人:常常有人说,作家要多体验生活,你觉得一个作家为了写一部某方面的作品,而去体验生活的做法是否可行?这种体验与人的长期生活经验差异其实很大的,你认为这样体验来的生活,能否进入你的文学作品?
曾剑:一个作家为了写某个领域的题材,是可以去体验生活的,但这种体验,必须是沉浸式的,不能走马观花,飘浮在生活表面。前段时间,我在一则短视频中看到徐则臣先生讲写作课,他对于生活的感知说得非常形象,他以小时候在河里游泳为例,说获得写作经验如同游泳,要钻入水底,憋住气,努力向前潜游,努力地成为最后一个钻出水面的那个人,这样,他对“水底”的体验就是最深刻的,当他钻出水面的那一刻,他必定也最有成就感。
我的中篇小说《整个世界都在下雪》就是缘于一次沉浸式体验。当时,我一个朋友告诉我有这样一个“扶贫”的故事,他说我可以写。我说,我怎么写?那个女子长得什么样?她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那个山村是依山而建还是傍水而立?那里的山是什么形状?那里的水是什么走向?然后,我就到他那里,住在那儿沉浸式体验了十一天,回来后创作出《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我想说的是,体验生活,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比如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其中要写到煤矿那几章,他不熟悉煤矿工人的生活,他就住到一个煤矿招待所,与矿工交谈,甚至数次下井体验一线矿工的劳动。陈忠实写《白鹿原》,住到原上的乡村。柳青为了写《创业史》,干脆当起了农民。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生活经验,比如我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和《山河望》。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沉浸式体验,其实是生活本身。这也是我写都市文学比较少的原因——我对于都市生活的体验,更多的还是漂浮式的,未能达到所谓“沉浸”的状态。对我来说,想要创作出更多都市题材小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时间的恩赐。
主持人:现代小说源于个人体验的表达。曾剑老师是忠实于个人体验的写作者,塑造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当然,个体自然就是社会的一员,个人中有整体性,他也是整体中的个体。现代小说的魅力也在于此,找到那些尚可以称之为“个体”的文学形象。作为一个执着于书写个人体验的作家,曾剑老师对体验过的、沉浸过的生活具有书写的动力,这让他的写作工作变得诚实。感谢曾剑老师的写作经验分享!
曾剑:谢谢主持人!
责任编辑 高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