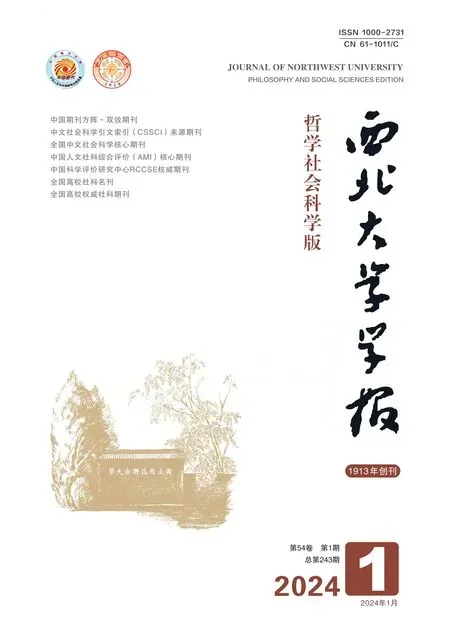谈谈周原考古的意义
——1979年4月22日在西北大学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
【编者按】本文根据苏秉琦先生家藏未刊文稿整理。文稿未署年月,据《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所收叶迈致苏秉琦先生书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册225-226页),及《安志敏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册539页),苏秉琦先生在1979年4月22日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邀请,于西北大学做了“周原考古收获”和“考古学为历史时期任务出贡献”的学术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整理录音稿,拟发表于《人文杂志》创刊号,后虽经苏秉琦先生多次修改,终未能定稿刊发。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大顺先生完成文稿录文,2021年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先生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校核文稿,并据出版规范与郭大顺先生一起对文稿再做核理。
最近在扶风、岐山的发掘现场召开了周原考古工作会议。会议刚刚结束,张院长(1)张堃生(1915—2005),陕西澄城人。1936年前参加革命,长期在辽宁工作,任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顾问。曾于1969—1977年任辽宁省博物馆领导小组组长,1979—1982年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就约我来谈谈周原工作。可是从何谈起呢?如果谈我在那里看到的具体东西,显然不一定适合今天的场合,因为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可能多半已经看过了。如果我没有把张院长的意思理解错的话,那我就谈谈周原考古工作的成果有什么意义?它在学术上有哪些价值?今后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方面?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在这里谈谈,算是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吧。
一、斗鸡台发掘与周原考古
谈起周原,不禁使我回想起三十年代在这里的工作。我参加的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工作,是从1932年准备、1933年开始的。工作一直继续到1937年,最后发现的那个大墓陪葬的车马坑,已是“七七事变”前后的事了。发掘完毕,恰遇战争爆发,一部分同志就没能直接回京,几经辗转才到了北京。我当时在北京,也没法出来。1938年从北京绕道越南,才到了云南昆明。我讲这些,说明当时要做点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呀!
就发掘的目的性来说,当时是比较明确的。就这个学术课题而言,至少还应追溯到20世纪初王国维的一些看法。
王国维在研究商周史料之后,提出了一个论点——“殷周不同说”(《观堂集林》卷十)。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后来一些同志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追本溯源,都与王国维的这一看法有关。王国维当时提出这个论点时,尚未获得实物证明,但在今天看来,它依然是具有启发性的。商与周的文化传统确有不同之处。但是,把它引申一番,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理论联在一起就未必妥当了。为了支持这一说法,强调当时已有冶铁、铁器,农民、地主作为两大对立阶级也已出现,甚至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等作为奴隶制转化为封建制的标志等等,恐怕就更不妥当了。
王国维还有一个论点是讲“周和秦”的关系。在他看来,周和秦在文化上具有某种特殊联系,这就是他的《战国时秦国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东方各国用的文字是一个传统,而关西的秦却跟周的文字关系密切。他说:“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观堂集林》)这又是一个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周人与秦人关系问题很有启发性的论点。他的文章发表到现在已经七八十年了,但在这一点上似并未引起后来学者们的充分重视。
三十年代我们在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工作,正是从这样一些角度出发,试图从地下实物资料对周人与秦人文化及其渊源关系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的。
武王克商以后的周,社会文化面貌确实不同于商。周人应有其自己的文化传统。周人灭殷以后,也不可能是把殷人的一套制度全部继承而发展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五百年左右的秦,它和关东各国有所不同,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在某些方面同殷周之际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颇有相似之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换句话说,和商同时的周是怎么个样子?比商更早的周又是怎样的呢?就秦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是怎样的,春秋以前的秦又是怎样的呢?殷周之际在我国古代史上是一大转折,周秦之际在我国古代史上又是一大转折。
而先周与先秦的发展道路又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却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一、两者都是起于泾渭上游、陕甘之间,尔后在周原一带建立都城,再后迁到西安附近,以关中为基地,入主中原;二、两者在入主中原之前,都是在我国西部相当大的范围内先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三、显然,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这种地位,都和他们最初发迹本来就是在所谓“戎狄之间”并和他们具有密切关系有关。
因此,我们对于他们在我国历史上,或者说在我整个中华民族史起的作用,应该如何给以正确的认识呢?这正是三十年代初我跟随徐旭生先生等前往斗鸡台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在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整个过程中所经常思考谈论的问题。
现在追述一下当时我们的思想活动似乎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我们编写报告的时候(2)整理注:“报告”,指苏秉琦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完全没有谈这个问题。所以那么做,是考虑到发掘报告应是专谈工作及其成果,而不是发表“一家之言”的适当形式。有关这方面的想法,应该换一个形式去讲才好。本着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在报告中没有谈这些问题。例如,在斗鸡台挖的那批墓葬使用了“瓦鬲墓”“屈肢葬墓”这样一些古怪名词,完全避开了“周”或“先周”、“秦”或“先秦”等字样。其实,不提者正是想说也。可是说又说不清楚,于是就采用这个办法把它避开了。
当时对这批瓦鬲墓同周人的关系是怎么想的呢?第一,从年代讲,有的估计要早于武王克商以后的周代,有的估计相当西周,但分界线拿不准;第二,从文化性质讲,周与非周的分别更拿不准。根据史书记载,周人是从邠迁到周原来的。“周原”的名称似乎是在周人迁来之前就有了。周人同周原的关系似乎是人因地得名而不是相反。果真如此,周人应说是“客家”。
史书记载,周人到此地后“贬戎狄之俗”,说“戎狄”就含有“贬”的意思。有所舍必有所取。既然说“贬(去)戎狄之俗”,就含有吸取了“土著”文明的意思。西周末平王东迁是受戎人侵扰的结果,平王东迁时担任护送任务的恰恰是与戎狄较接近的秦人(襄公),而不是周人早期分封的诸侯。平王东迁后秦人(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说明这时候周人已成为周原土著,而秦人则沿着当年周人的足迹,开展了自己与土著融合的过程。关系相当复杂。
首先,周人初到周原的时候还带着“戎狄之俗”。就是说,他们的文化面貌和戎狄有区别,又有共同点。当时周人自己就含有周与非周(戎狄)文化因素(俗),所以说贬戎狄。其次,周人的文化面貌和周原土著之间也是既有区别,又有共同点,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周人来到周原就能够“贬戎狄之俗”与建立都邑,成为统治者。显然,周人所贬的“戎狄之俗”,实际上也就是周人文化因素中某些与戎狄相同或相似的那一部分而已。再次,周人来到周原之前的关中一带,所谓“八百里秦川”(指渭河盆地)土著小国很多,其文化面貌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我们根据史书提供的这些线索,来初步观察分析这批瓦鬲墓的发展变化,考虑它们所反映的史实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种把它叫作“锥脚袋足鬲”以及和它共生的一些器物,它们出现在此地和它们的突然消失。另一种具有较明显的形制发展变化的鬲,我们当时把它叫作“折足鬲”,近年大家常把它叫作“瘪裆鬲”,我意把它称作“折足瘪裆鬲”似乎更贴切一些。这种鬲和西周时期的常见铜鬲显然具互相模仿的关系。还有一种我们当时把它叫作“矮脚鬲”,实际上它是“殷式鬲”的发展形式,我意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定名为“浅空足分裆鬲”比较准确。这种鬲在周原一带也像“锥脚袋足鬲”,出现的突然,消失的也突然。但我们对它们在这里发现的历史背景是比较清楚的。总之,它已是周人强大以后殷周文化交流的结果。
那么, “锥脚袋足鬲”在斗鸡台的出现和它们的突然消失,是否同周人早期活动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呢? 同样, 晚于“瓦鬲墓”的“屈肢葬墓”出一种“铲脚袋足鬲”, 这类鬲在这里的出现和消失也很突然, 它同秦人早期的历史关系如何呢? 作为考古学问题, 这两种袋足鬲的关系又如何呢? 还有这两种袋足鬲同发现在甘肃青海境内诸原始文化当中形制类似的袋足鬲的关系又如何呢? 无疑, 问题是错综复杂的。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铜鬲常常就是模仿这种陶器鬲(瘪裆鬲)的形制,同时我们又知道在关中西部这种鬲使用时间很长,变化也很大。那么,在斗鸡台这种“锥脚袋足鬲”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自然使我们会联想到它可能同周人早期活动的历史有关系。用它作封面插图,我曾有这样想法,把它比作钓鱼的钩饵,期待以后从它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联系,说不定能对周人早期活动历史以及他们和其他人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找到突破口。
继“瓦鬲墓”之后的“屈肢葬墓”,根据我们对它们的排序顺序,有一种我们称之为“铲脚袋足鬲”的墓是其中较早的,而在这一组墓中的这种鬲的出现和消失也很突然,正同前述(瓦鬲墓中的“锥脚袋足鬲”)情况相似,这类屈肢葬墓使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可能同秦人有关。
前后两项在这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两种同类不同型的“袋足鬲”之间的关系,加上它们二者都同甘肃境内诸原始文化中普遍存在含有这种鬲的人们同它们(指先后两次出现在周原一带的含有两种类型的鬲的人们)之间具有的联系,是很清楚的。但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整个历史事实又是曲折复杂的,对于这些我们当时只能是期待光复后的工作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当时我使用了这样一个鬲作封面的想法就是这样。
正是在如上所说的思想考虑下,我们选择一件“锥脚袋足鬲”作为报告封面插图,曾把它戏称作:好比钓鱼的钩饵,抱着期待的心情,希望在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会得到解答。
从那时算起,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考古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这期间的工作和发现的材料,对于我们原先提出的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线索。这几年周原考古工作揭露面积是很大的,收获是很丰富的,这次能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无比的高兴。结合近若干年来和它有关的其他材料、线索,使我们对当年心目中存在的那些问题,还不能说已得到解决,宁说还远远没得到解决,但使我们的眼界已经大大地开阔了。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这条线索——“锥脚袋足鬲”, 简单谈一谈周原考古工作中新发现材料的学术意义。
二、周原考古的学术意义
近年周原考古新揭露出两组建筑,我只看了其中的一组,扶风的凤雏村西周甲组宫殿(宗庙)基址。看了工作站陈列的标本,已揭露出的建筑物是重要的,出土的实物是相当丰富的,但考虑到周原考古工作所涉及的这一整个学术课题范围之广泛,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应有足够的估计。现在已揭露的材料比起它后面隐藏的复杂史实,不过是犹如刚刚拉开了帷幕的一角,现在设置的工作站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根据对发现的一批甲骨文字资料的初步判断,是周人早期活动的记录,对凤雏建筑群周围文化堆积层出土器物的初步分析,判断这组建筑物跨越的年代,早期部分要早于武王灭商一段时间,晚期部分包括整个西周时期。有同志猜想它的早期部分大致同史书记载古公亶父迁岐之后的一段时间相当,我看这可能与史实相去不远。就是说,这组建筑群跨越的时间,大致相当从太王(古公亶父)到平王东迁。
我们说,周原发现的两组建筑群是重要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它们是我们迄今为止第一次发现的相当西周或周人的重要的成组建筑遗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第一,这里从古公亶父一直到平王东迁始终是周人的一个都邑,它并没有因为后来建设了丰京、镐京、洛邑作为新都而被废弃,相反,它在西周二百多年中,继续起着同其他两地新营建都邑有所不同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自宋朝以来出土具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出在周原一带这一事实得到旁证(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这说明周人虽然自从在周原营建都邑以后步步东进,营建新都并分封诸侯,但它在周原的旧都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纪念地而保留下来,恐怕还是一个起着它最初曾经起过的特殊作用——大后方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它的规模可能是相当大的。
第二,现在揭露出的两组建筑群离地表不深,但建筑基础基本完整,没有被后来人们的活动破坏,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因为西安的丰、镐和洛阳的王城、成周,都被后来营建都邑破坏严重,恐怕难得还有像样的建筑遗迹保存下来。近年山东曲阜鲁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鲁是周初周公儿子的封地,非同一般,在分封诸侯国中占有特殊地位,但到汉代又在原地封国建都。多年以来,使我们对这项工作感到特别棘手。我们根据地表勘查材料判断,不论是灵光殿的基础,还是城墙遗迹,都是汉代的或者是战国—汉代的。那么西周的鲁城在哪里,是什么样子呢?近几年曲阜鲁城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从对城墙遗迹进行了大量的解剖,证明它虽经过多次修筑,一次比一次加厚,但它的最初夯筑还部分地保留在墙的内芯,它的时代可以早到西周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沿袭使用到西汉,“外壳”基本上保存了原状,“内容”也可能保存了西周的布局。
我们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建设工程中动土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对原来建筑物遗址的破坏力也很惊人,所以很难指望西汉的“鲁灵光殿”还能保存下多少西周春秋时代的痕迹。周原现在发现的属于西周(先周的周人都城)两组建筑群到目前还是第一次,是否会有城墙遗迹被保存下来,根据鲁城情况来看,也是可能的。
两组建筑群附近的北吕墓地,根据已经挖掘的部分,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来了解周人迁到周原前后的历史。从这处墓地埋葬秩序看,应是一个氏族的,但早晚葬制却有明显的不同。整个墓地的埋葬顺序是由东而西,同一时期的墓南北成行,从东起:
第一排,分三组,各组的埋葬顺序是从南而北,三组跨越的时间大致相同,墓坑是东西长方竖穴,其中两组从头到尾都用一种“瘪裆鬲”(我曾把它叫作“折足鬲”),我看把它叫作“折足瘪裆鬲”更确切些。有趣的是,其中一组的末尾一个,使用的已是一种我曾把它叫作“锥脚袋足鬲”,为了更确切起见,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叫作“锥脚袋足隔裆鬲”。由此可见,它的出现说明:(一)对周原而言,它是外来的,(二)它在当地出现的时间,是同当地原来流行的“折足瘪裆鬲”形制发展序列中的某一个环节相当;
第二排,埋葬顺序是从北向南,墓坑方向是东西向,随葬“折足瘪裆鬲”;
第三、四排,是大致时间平行的两组,埋葬顺序均从北向南,墓坑是南北向,随葬“折足瘪裆鬲”;
第五排,埋葬顺序、墓坑方向、随葬陶鬲同上(三、四排)。
北吕墓地与凤雏建筑群遗址的关系。凤雏建筑群所在地点文化堆积的开始时间,根据它们所含“折足瘪裆鬲”互相对照比较,约与北吕墓葬第一排第一、三这两组墓的末尾相当,而北吕第一排第三组的末尾墓随葬的鬲,则是所谓“锥脚袋足隔裆鬲”。两者的下限大致相同,到西周末。
把北吕墓和凤雏建筑群结合起来,可以列出如下的年表:
一期,以北吕墓第一排为代表,约相当殷商后期;
二期,以北吕墓第二排为代表,(对照凤雏早期)约相当殷末;
三期,以北吕墓第三、四排为代表,(对照凤雏中期)约相当西周前期;
四期,以北吕墓第五排为代表,(对照凤雏晚期)约相当西周后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种“锥脚袋足鬲”在此地出现时间在年表一期之末;第二,它同“折足瘪裆鬲”的发展序列中的一个特定环节共生;第三,再从这一墓地的排列顺序与墓坑方向的早晚变化来看:一期排列顺序是由南而北,墓坑是东西向、长方形;三、四期排列顺序是由北而南,墓坑是南北向、长方形,只二期排列顺序变为自北而南,而墓坑形制也未变,仍与一期相同;第四,这种“锥脚袋足鬲”的出现时间是在一期之末,而二期的转折变化则是紧随在它的出现之后而发生的,它们这种关系似乎不是偶然的。就是说,以这种似外来形制的鬲的出现为契机(以对当地文化传统而言),使这里社会发生了——结合凤雏建筑群的年代上限大致与二期相当——大的变化,由村落变为都城,人们的风俗习惯变了。
这些既保存着当地传统的一面(如随葬陶器),也有违反当地传统的一面(埋葬顺序与墓坑方向)。这一大的社会变化的发生、发展,既来得突然,但从过程看来却又是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的,发人深思。
我们的工作并非为了给《周本纪》作注解,做考证。但这一看来很不寻常,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现象,却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周人在古公迁岐后与姜姓的联姻,既有很古的渊源,也有其新的社会、政治意义。《周本纪》说古公迁岐之后“贬戎狄之俗”,不言而喻,有破就有立,同时也就意味着和当地土著结合。反过来,从当地土著一方来说,则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就是说,当地土著是在更大程度上被融合于周人了。就周人和当地社会历史发展而言,则更应该说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那么,在这次的大变化发生之前,夏商时期的关中地区(包括周原)社会文化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虽然不多,但已远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一团漆黑了。
关中、晋南、豫西北,也就是汾渭伊洛流域地区,自远古以来文化关系就比较密切接近,到夏商时期依然如此,但在这三部分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说明三者在此时期文化发展道路上的不同。
例如,这一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原是鬲类陶器从它最原始形态的“高袋足隔裆”类型,发展到“带鋬高袋足联裆”类型的分布中心。到夏商时期,即约距今三四千年间,三个部分鬲类的发展分道扬镳,各自经历过一段不同的发展道路。豫西北部的特征,先是鬲类在炊器中少见了,鼎类流行,随后是“高低脚浅空足分裆鬲”类流行,而鼎则在陶器中变为罕见的器类。晋南的特征,先是甗、斝流行,真正鬲类罕见,随后是从腹足分节的“高袋足隔裆”类鬲,发展为腹足分节的“浅器足分裆”类鬲。关中的特征,是从前一时期的“带鋬高袋足联裆”类鬲,直接发展而来的“折足瘪裆”类鬲,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西周春秋时期包括受周人影响所及的大部分地区鬲(包括陶器和铜器)的主要型式。
我们从这一时期这三个部分鬲类陶器发展变化的差异,可以对当时这三部分人们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得到启发:
豫西北部在这时期较前半段所发生的社会文化面貌上的变化,明显地同来自淮河水系人们的影响有关,在它的后半段所发生的变化,则是同洛河囗邻近大部地区具有密切关系。晋南部分的整个变化和同它邻近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包括燕山南北)具有密切关系。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腹足分节矮空足分裆”类鬲的出现,时间都可以上溯到夏代,而它在后者范围内延续使用的时间则长得多,属于战国时期的易县燕下都还可以看到它的后裔。
关中部分在这期间,西安以东的华县南沙村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同偃师二里头很接近,在西安以西范围内,则直到这种“锥脚袋足隔裆鬲”在早于西周初不太远的时候,在这里出现之前同其所处邻近地区之间,似乎没有发生过类似以上两个部分那样大的相互影响、作用过程,以致使它们的本来文化面貌产生过很大的变化,而周原一带在相当殷商晚期所发生的变化则是很明显的。
这种“锥脚袋足隔裆”类鬲的分布范围,根据近年材料,大致包括陕西的凤翔、宝鸡和甘肃的平凉等地区。对这些材料的初步分析,它们所跨越的时间不很长,但同它形态接近的“袋足隔裆”类鬲在甘肃平凉一带则似乎跨越时间很长。因此,联系到史书记载春秋战国之际秦人从陕甘之间由西而东的发展史实,同考古材料中“锥脚隔裆”类鬲与屈肢葬墓恰于此时突然出现于关中西部一带,我们似乎可做如下设想:这种在周原一带突然出现的“锥脚袋足瘪裆”类鬲的原生地是陇东一带,而它们产生的背景则大致可以说包括甘肃的东部和中部更为广大的地区。
周人除了步步东进,还向西发展,否则,《穆天子传》又是怎么回事呢?何况周人的老根是在关陇之间。就政治上讲,周人是向东发展,但从它的队伍本身来看,其核心、骨干力量应是关陇一带出生的人呀!既然如此,那他们就不可能只往东不往西。秦人也是如此。他们从西往东,也是以宝鸡、凤翔作根据地。但他们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宝鸡、凤翔人,而更是关陇之间的人。
天水曾叫秦州、秦安,陕西却没有一个县名带“秦”字的。《编年表》《大事记》上写的秦,只是它灭六国以后短短的一小段,好像是昙花一现。其实,它的根子还深着呢。既有跟周同时的秦,难道跟商同时甚至跟夏同时的秦就没影响?不一定。和周并存的那个秦就没有它自己的渊源吗?我们看到的秦也是步步东进。同样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它东进之前就不考虑到后方该怎么办?把倾国之兵拉出关外打仗,就不怕别人抄后路?无后顾之忧正说明秦在西、南、北三面有一定的基础,否则怎敢以倾国之师出兵关东,这说明在秦的背后还有一大段时间和一大块空间。可这些情况,文献上根本没有记载,我们已有的若干考古材料的线索可以说明这些问题。事实上,在秦并六国之前,秦人的力量主要用在经营西半部的中国,到了后期,才把主要力量用在东半部的中国。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们的发展壮大是有个过程的。只有在它强大之后才能制定东进的战略,而为了壮大起来,它必须苦苦经营本族起源的关陇之间。
由此可见,目前正在进行的周原考古工作,对断代史上西周这一段有它特定的意义。由于东、西两京保存不好,周原的发现正可以有所补救。它本身又是周的政治中心,起着重要作用。但它的意义决不限于西周,还应包括西周以前很长一段历史。当然,它不仅限于扶风、岐山两地,也包括武功、扶风、岐山、宝鸡等一大块。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从这里犹如打开一孔历史的窗户,看到周、秦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对西半部中国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周原的考古工作,可以探索周、秦时期西半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等等问题。甚至我们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去探索“丝绸之路”从何而来的问题。
难道“丝绸之路”仅仅是一个交通路线问题吗?仅仅是东西文化的交流问题吗?仅是汉族的问题吗?由于我国多数兄弟民族生活在西半部,所以在研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关系问题上,难道不也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吗?
近几年周原发掘成果的意义,两处建筑群遗址的揭露,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工作自身的划时代意义。就是说,它将意味着我们将会以此为出发点,长期深入地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探索周人和秦人早期的历史,并通过他们和同他们同期的其他的人们共同体的关系,来了解这一历史时期(包括夏商周),我国西北部处于这一地区(陕甘间)的诸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
这是个大课题,是有待于我们长期工作、探索的课题。现在,周原考古工作站的选定和这几年的新发现,仅仅是揭开了帷幕的一角。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也是我们几十年来的宿愿,从心里感到高兴。
如前所述,周原新揭露出来的两组建筑自身和从中发现的遗物,特别是甲骨文字资料,明显证明它们是周人早期活动的真实资料。它们所跨越的年代,据我们对遗址文化堆积物的初步观察判断,下限可到两周末期,这一点同西安附近的沣河两岸所谓丰镐遗址一致。它的上限要早于武王灭殷一段时间,确切地讲,是否可以说恰与史书记载古公亶父的建岐时间相符合?有同志这样猜想,我看这猜想可能与事实相去不远。
就是说,他们跨越的时间约太王迁岐到平王东迁,周人政治上最为活跃的相当殷商晚期和西周时期。结合历代到最近从这一带出土的大量带铭文的青铜器,进一步说明周人尽管随后在丰、镐、洛阳建立都城,有大量分封诸侯国之后,直到平王东迁之前,一直把这里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可以猜想,它的地面建筑规模可能不小,不亚于丰、镐、洛阳。
在周原期间,我和宝鸡的同志一起讨论过这件事。我说:姜太公钓鱼的那个钩,我们当时就准备了的,看什么时候把鱼钓上来。三四十年,你们总算把鱼钓上来了。这是想说,现在进行的周原工作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要仅仅看到这两个宫殿遗址,而是一片开阔地带。它的西边不超过平凉、天水一带,东边也不一定能到武功(最多到武功),而是扶风、岐山、宝鸡,连西边的天水、平凉,这是一大片。
我在周原住了三天,看了些材料,感到三四十年前考虑的问题,到现在,若从一个角度看,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就是说,当周人到岐山的时候,如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说,是包括陕甘之间这一块的。至于这种文化和创造这种文化的人,是否非要去和历史文献上的什么记载结合起来,那倒不一定。
三、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文化
根据考古材料提出来的考古学文化,这本就是一项科学研究。但要把某一个文化跟历史文献中某一个民族、国家或别的什么名字简单地联系在一起,我是不赞成的。去年在庐山召开的印纹陶文化讨论会上,有人提交了一篇文章叫《荆蛮考》。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具有这种特征的陶器是一大片,包括东南十几个省,能说这都是荆蛮吗?
文献是文献,文献上的名词,常常是张三可以叫这个,李四也可以叫这个,往往“名同实异”,名字是一样的,实际却是两回事。有时也可能是“实同名异”,同样的东西,却叫不同的名词。总之是名实不相符,这是常有的事。拿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某一名字,跟我们发掘的考古资料随便一对就说对上了。我看这不是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
以往,每当发现一座大墓,人们就纷纷考证说这是史籍上所记的某人的墓。如果说墓中的资料比较齐全,这样做自然是对的,问题是有些墓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却非要去做这样的考证。则人们不仅要问:书上就那么几个名字,等把这些名字用完了,再发现些墓怎么办呢?你上哪里去找名字?好像挖出一个大墓,想必是有名的人物。辉县出一个大墓,就说是信陵君的。咸阳杨家湾挖出一个大墓,也说是某某人的墓。其实不一定。所谓“百夷”,究竟是一百还是九十九,谁知道呢?“百越”者就是说不清也。所谓“万国”者,也是数不清也。古人写书时就数不清,你现在怎么数得清呢?
我不是说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这二者之间就绝无关系,我也不是“不可知论者”。问题是随便地用文献上的名词和考古上的材料,这样做是很不妥当的。不管是一种文化或一个大墓,往往都不是轻易地就能做出结论的。
如前所述,从地下材料看,西周时期最主要的“都”——大城市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两处。一处是曲阜的鲁城。鲁是周的封国,但它非同一般,它是周公儿子的封地。在周代分封的诸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鲁城发掘的情况看,这个城保存得比较完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好的前身,在西周以前就有相当的规模,西周基本上利用了这个基础。直到汉代它的平面布局也还没有多大的变化。它可以代表西周时代都城的布局。
另一处就是在周原看到的这两组建筑群,不管是属于宗庙,还是属于宫殿,都可说明从古公亶父到文王这一阶段至整个西周(平王东迁以前),周原这个地方始终是周人的一个都城。它并没有因为建设了长安的丰、镐两京和洛阳的王城而被废弃。相反,在西周这两百多年中,周人始终把周原这里作为实质上的旧都。要不然为什么周代有长篇铭文的铜器,大多出在周原而不出在长安、洛阳或别的地方呢?从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一书看,宋朝以来具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就出土于周原一带,这就非同小可。说明周人虽然步步东进,从周原到长安,又到洛阳,虽分封诸侯,但它的老根据地周原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纪念地而保留下来,恐怕是一个起实际作用的政治中心。
因此,从周原目前发现的这两组建筑遗迹来看,可以断言这里还可能发现更多的建筑遗迹。而今后的进一步工作,必将使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到从古公亶父迁来岐山,直到西周末年这段时间内周原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期 望
正由于此,在周原考古工作会议期间,大家倡议筹备成立周原研究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时顾名未必就能思义,对周原研究会就不能理解得太狭隘。一粒种子刚发芽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将来能长到多高多大。难道周原的这粒种子将来就不能变成一株参天大树吗?周原这个地方是打开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地方,应该打开这扇窗户,去看看这个宝库里边藏的是些什么。去研究这些复杂的历史问题,这绝非凭空想象。对周原工作的意义做这样的估计也决非毫无道理。这虽是我个人的意见,但它是我几十年来的心愿。
对周原的工作,我们并不是第一代,比我们更老的学者,他们也想过这类问题。现在的工作是老一辈人工作的发展,这项工作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有同志问:“你们这项工作几年完成呀?”这话不对。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完成的,它往往需要几代人连续地做下去。说“三年完成”“五年完成”,对具体的工作、具体的任务可以这么说,但对一个重大的课题,能说哪一年完成、交卷吗?要是我们这一代人交卷了,那么是把真理穷尽了吗?这一点也带有普遍性。
这个问题,我可能说得远了一些,这倒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我工作不多,但考虑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了。结论无非是自己年老,但我并没有“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的伤感情绪,反倒有叶剑英元帅讲“满目青山夕照明”的乐观情绪。因为我们的课题是一代接一代地接着做了,而且我深信,我们的工作是“一浪胜似一浪”,我们的同志也是“一代胜似一代”。
愿有志于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能意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踏踏实实地向着课题的纵深方向前进!
(根据苏秉琦先生讲话录音整理稿整理,原稿未分节,个别字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