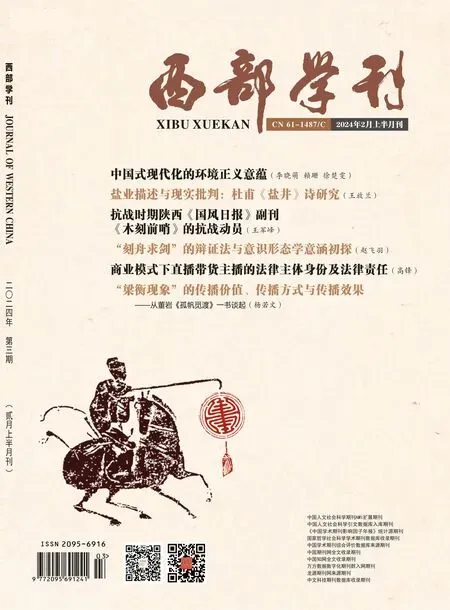“刻舟求剑”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学意涵初探
赵飞羽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州 215123)
“刻舟求剑”是《吕氏春秋·察今》(以下简称《察今》)中的一则寓言:“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1]517作者作为即将大一统的秦王朝的新兴贵族,借此故事说明了“守法弗变”的谬误与“因时变法”的必要性。尽管这个故事本身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显然无法与作者的阶级身份、意识形态立场和所处时代背景割裂开,它本身的简单主旨会由于这些历史性因素的介入而异化、折射出不同层面的含义。本文就从辩证法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刻舟求剑”的故事结构及其背后的历史性含义,并试图从理论上探究其所面临政治困境的出路。
一、对立、调和与同一:“刻舟求剑”的基本辩证结构
在“刻舟求剑”的朴素隐喻中,舟的行进代表现实情境的变动,求剑方法代表政治策略,“守法弗变”的主张就如同楚人荒谬的行为一样不可能实现“治”的政治理想。通常的解读会认为,“刻舟求剑”所表达的是对于守法派单方面的揶揄与讽刺,动态变通的“因时变法”超越了静态僵死的“守法弗变”。然而,“刻舟求剑”带有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就目的而言,故事的作者与被叙述的“楚人”保持一致(求剑)。基于这一前提,变法派对守法派的否定实际上只是一种“内在越界(immanent transgression)”[2],只是特殊性内容在普遍性框架之内的互相否定,就像《察今》开篇所说的,“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1]518。各种政治策略最终总是殊途同归的,作者与楚人、变法派与守法派之间的差异只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一点在“舟已行矣,而剑不行”的表述中也有所体现:实际的剑沉入水并非不会再改变位置,而故事中有意去用已失落之剑象征某种超然的同一性。
归根结底,这种同一性的调和作用是更为根本的,是上述对立关系的本体论基础。作者和楚人共享同一个行舟失剑的线性模型,而变法派与守法派也都默认通过“法”与“时”的某种契合可以达到“治”的理想模式。然而,高度中心化的封建秩序回溯性地定义了那个令双方都认同的“治”,“刻舟求剑”的争辩也就不是一种认识论或价值论上的对立,而是政治立场上的同一——作为贵族官僚,维持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凌驾于派系斗争之上的。于是,变法派对守法派的否定只能沦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3]:经由封建统治秩序的扬弃,双方在“时”与“法”的层面上的势不两立的根本差异,变成了在普遍的封建统治秩序中被设定的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变法派的论证最终实现的效果是,将自身与守法派的差异建立在了统治权力的同一性基础之上,双方的政治斗争在第三方(高度中心化的封建政权)的调和之下失去了激进的对抗性。
因此“刻舟求剑”的想象模式之根基并不是“因时变法”,而是“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它代表的是落水之剑在这个线性时空序列中的确定性:楚人认为剑与舟大致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因此按照坠剑时的刻痕就能在对应位置找到它;作者则认为需要引入“时”(即行舟)这一线性变量,通过思考其与剑的相对位置来制定取剑之法。然而应当被注意到的是,剑的确定性并不是一个实证的依据,而是为了规避理论上的诸多任意性才去设置的前提。同样地,喜怒无常、变幻莫测的君主主导着对“治”的政治图景的解释,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着“治”的现实化进展,变法派只能在现有的政治实践场域之中为“治”设定一个临时性的位置。这些预设活动并不代表着谬误,但是它们必须至少经过从假定到实践才有可能被证明,变法派的所作所为却是借用封建统治秩序的强力保证抹消了本应被纳入考虑范畴的不确定性。这种操作不仅把一个空想的状况确立为观念上的实在,它还会使得那个足以压抑一切不确定的干扰因素的封建统治秩序神秘化、永恒化,成为这种观念上的实在背后的本体论依据。于是,一切观点都唯有建立在这种依据上才是合理的,变法派的理论思考反过来被这种预设所支配,剩下的只是在这个预设好的界限内完善认识和优化决策。变法派看似比守法派思考得更全面、更变通,却忽略了他们依靠的那个对于剑的定位、时的动态与法的应变拥有绝对解释权和决策权的封建政权本身是个更为庞大的形而上学机器。仰息于封建政权这个绝对的“一”,无论在变量上思考的怎样“多”,由此而提出的变法始终局限于针对旧法的变法而不是真正普遍的变法。以不变的形而上学框架作为基础,变法就不再代表某种变革的新生力量,而是实现了与守法的形而上学式的同一。
二、虚假的反思与狗智主义意识形态景观
除了有关政治阵营与封建权力的争执,“刻舟求剑”之中还有着一套简易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变法派借此故事指出了蒙蔽守法派的“虚假意识”,试图纠正其对社会现实的扭曲与误认,引导整个政治实践场域趋同于变法派主导的“正确”叙事。然而守法派并未因此改变,在这里如果不将守法派简单地视为无法接受真理的愚人,那么似乎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守法派早已清楚现实的动荡以及变法与守法的利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仍然选择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4]。这种使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程序无能为力的正是所谓“狗智主义”(1)狗智主义:与代表平民大众对官方文化拒斥的“犬儒主义”(Kynicism)不同的是,齐泽克所谓的“狗智主义”(cynicism)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立场,它说明人们能够反思到普遍性秩序背后的特定利益关系,但实际上不去做出颠覆这些特定关系的行动。的意识形态,它的出现表明被批判者并非毫无反思或反思不到意识形态幻象的虚假性,而是他们坐享旧秩序带来的利益、不愿冒险去行动。不仅如此,变法派的立场表达——停留在封建统治秩序框架下与守法派进行相互否定——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其狗智主义的意识形态底色,无论变法派的结论多么义正辞严地指出了守法派的谬误,最终仍然同样实现了向封建政权的皈依。
“刻舟求剑”展现出的意识形态景观是对其隐喻框架的一种印证。作者自以为比楚人高明,但却同样深陷舟与剑的线性模型之中而没有意识到这个看待问题的视角本身是应当被颠覆的;变法派自认为站在真理的一方而守法派是盲从旧法的庸人,但最终还是选择退缩回封建政权的舒适圈中、扮演好为封建大他者之主人话语辩护的大学话语这一角色。从整个贵族政治的运作模式的角度去看,政治家们尽可能激烈地互相批判,而他们的否定性都未能超出封建政权维系的实践场域。狗智主义意识形态或许留下了自由反思的余地,但在允诺了阶级利益并代表着超意识形态暴力的大他者——封建政权的中介之下,一切否定性的因素都没有落实到政治实践的立场表达上,随之所有反思与批判就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意识形态(仅就其针对贵族官僚政治家而言)生效的方式并不止于在“知”的层面宣称自己拥有真理并强迫人们相信,它已经渗入了整个“行—知”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行”的层面消解了主体的否定性,也就使得主体在“知”的层面上的智性努力化为泡影,最终呈现出的就是所有人都相信“虚假意识”的效果。只是看到这种效果而不能意识到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是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批判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不仅无意真正阻止主体通过反思生产出否定性的理论,反而将这种反思活动当作收买和支配主体的手段。受这种意识形态支配的人们并不表现出反思的匮乏,对于行动上无能为力、唯有屈从于封建政权的贵族政治家而言,反思是他们仅有的可以完成自我认同的方式,他们恰恰会生产出过剩的理论成果并自认为可以凭此超越意识形态幻想。这些贵族政治家越反思批判,就越沉溺于意识形态陷阱,越无法严肃看待自身与论敌的辩证关系、无法真正进行突破框架的行动,这就是他们被意识形态俘获的方式。就如前文所说的,变法派之变法不是普遍的变法,那么他们的意识形态反思也不是普遍的反思:变法派作为新秩序的先行者,并没有意识到其使命除了对守法派的反思还应当有对自身的批判。作为内在于守法派之中的否定性因素,变法派批判了守法派却没有将这种否定性重新运用于自身,陷入了超越“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幻想而不能真正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些否定性的成果。
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刻舟求剑”最关键的故事元素仍然是楚人之“剑”,它所隐喻的“治”对应的正是守法派欲望的、已遗失的过去与变法派企盼的、未实现的将来。这个被欲望之物必须是被崇高化为不可能触及的,唯有如此才它能作为一种对象成因,驱动着贵族政治家不停地去进行破除“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游戏。因此,仅仅通过对比现实而美化那种传说中的合理的政治生态模式,只不过是一边将其永远隔绝在过去、一边享受否定当下的不合理现状带来的智性快感;不去尽可能推动一切有效的激进变革以迎接理想政治愿景,却以理论水平胜过论敌而自矜,则正是将那种理想的政治愿景无限推迟于将来。这就是在现有封建统治秩序之下摇尾乞怜的贵族政治家们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够彻底的表现,他们或许能够拥有超出普通民众的较高智性思辨水平,但并不具有成规模的行动力,也更加不可能使封建统治跳出兴亡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最终,变法派颇有些歇斯底里的理论生产活动,与守法派面对现实的变动仍然梦呓般去呼唤某个完满旧秩序的回归一样,都是被意识形态幻想俘获后的绝望的重复。
三、视差辩证法对贵族政治模式的突破
同为变法之士所著的《商君书》有过如此论断:“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5]它指出的是借助封建统治权力实现变法必定面临的问题,即诞生于封建贵族阶级的理想秩序反过来会被此阶级的保守本质所掣肘,很快就会丧失其进步性而重新沦为反动的统治工具。这种根本上的矛盾是无法在封建统治的模式之中被彻底解决的,因为这种模式总要设定一个天然不受法支配的崇高地位。如果要抵达某种真正能够超越守法与变法双方的、对于整个封建秩序代表的普遍性框架具有颠覆性的结论,那么首先要去设想如何不通过超越性第三方的中介去理解二元对立。对此,齐泽克的一个见解值得深思:“辩证的综合”(即通过引入同一性中介的方式调和对立)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更为重要的是对立双方从根本上的“不可化约”[6]。这种理解首先导向的是对变法理论本身的反思:在原本的形而上学想象图式中,变法派与守法派是一种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关系,就类似被一个更大的集合囊括在内的两个不同的理论子集。然而,变法与守法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就法作为观念体系集合而言,一系列的法代表一种特殊性的统治秩序,而这一特殊性秩序的普遍化必定形成对任何其他可能的特殊性秩序的压抑,变法与守法同样需要完成这种压抑的过程;既然不存在一个预先被定义的、最理想的政治,那么任何普遍化的法就都意味着激进的、无根据的政治实践活动,因此守法早已是一种变法。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视差关系”(2)视差关系:齐泽克重新解释了辩证同一的规律,他认为不仅要看到对立两面是同一事物不同视角下的存在样态,而且要清楚认识到这个事物的自身的同一性必定以其内在差异为中介,而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或绝对的保障。,变法与守法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是同一种政治实践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必然分裂导致的结果。
在这种“视差关系”中,双方的同一性不由超越性的第三者来中介,也不是对矛盾的彻底消解,而是以双方根本上“不可化约”的差异为前提。所谓视差意味着看待问题的方式的扭转,这个结论是对狗智主义意识形态陷阱的颠倒:并不是先有一种绝对理想的政治,政治家才能通过它来建立自我认同并党同伐异,最终被封建统治权力所调和;真相恰恰是封建统治秩序本就是不完满的、内在具有不一致性的,其从属的政治家的意见分野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的体现,而这种矛盾使得政治家总是处在应然—实然的两极——封建秩序严密运转的完美表象和理想之“治”的完满图景——中间。如果这种矛盾不是根本上“不可化约”的,那么应然—实然的两极就应该是完全同一的,结果就是“本体论的闭合”,即任何政治意见的对立根本就不会出现并且既定的统治秩序会永恒运行下去。同样地,不是这种实然—应然的想象模式作为意识形态幻想的一部分驱动着政治家重复其理论活动,而是政治家的理论活动早已深刻介入这个实然—应然想象模式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实然的表象和应然的图景离不开他们的理论活动的支撑。
变法派错误地认为自身是外在于守法派的否定者,而实际上变法是内嵌在守法之中的否定性因素,因为旧法或原有的普遍性秩序对于特殊性的压抑与整合总是不完善的,它形成的只是一个临时的政治架构,其中的矛盾或不一致性终将绽出、呼唤着新秩序的降临。并且,如果说谬误也是真理实现的诸环节之一,那么变法派所做的恰恰是借助封建大他者的绝对权威省略了在谬误之中探索的必经之路,这种做法是其没有魄力和决心去面对政治实践根本上的不确定性的体现。如果说对于自身和自身与论敌的辩证关系进行反思是变法派不愿为之的,由于这种软弱性,对于封建统治秩序本身的批判就是变法派完全无力为之的。就像作者会无视楚人“刻舟求剑”的行动也有成功的可能一样,变法派只能认识到旧法需要翻新,令他们无法想象的是在某些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反而应当依循旧法才能够取得治理成效。贵族政治家们总有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余裕和政治投机的契机,无法拒绝绝对的利益与神秘的权力,不敢于承认“关于历史的秘密知识并不会给出其道路的知识”[7]。只有认识到封建统治秩序不仅无法给出绝对的真理反而还将会成为变法的最终阻力,想象到何为“治”的问题只能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可能仅仅从理论上解决,变法才有可能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将封建统治秩序悬置起来的精神,就如梅洛-庞蒂所说,伟大的革命家“不用航海图,基于当前的视景而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