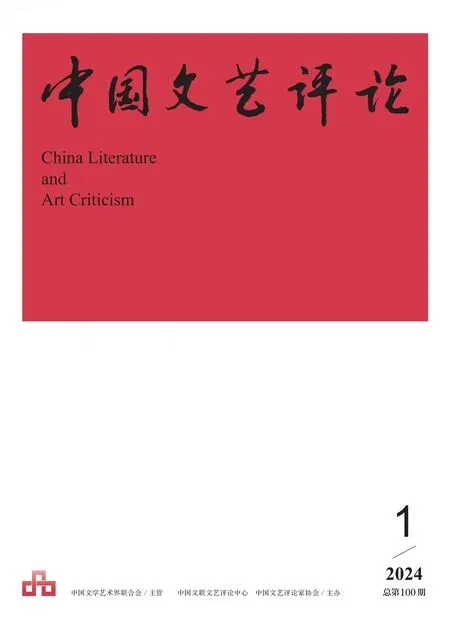“时间”的生成
——神话叙事在艺术中的三种表达形态
■ 马 硕
引言
在艺术的世界中,神话是当之无愧的源头,包括对“何为艺术”与“艺术何为”的理解也都暗藏着神话对人类精神的指引,而最为显著的标识便是出现于艺术中的各种符号。符号的“连续性”与“象征性”帮助人类建立起了早期的思维方式,并为艺术呈现的多重方式提供了可能。维克多•特纳直接将象征符号与物等同起来,他认为象征符号“通过与另一些事物有类似的品质或在事实或思维上有联系,被人们普遍认作另一些事物理所当然的典型或代表物体,或使人们联想起另一些物体”[1][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页。。在符号的助推作用下,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幻在不同场域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进而产生了神话。神话思维作为艺术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它存在一种原逻辑的性质,即主客体的混融与交流,以及形象与情感的相互转换,使神话思维实现了向叙事形态的转化,并以一种相对更为具象的方式留存于艺术创作中。
应该说,相对于“艺术”这一概念而言,神话是一种“先验”的形态,因此,在面对神话这种艺术并进行阐释时,就需要一个恰当的角度。其中,时间与空间在人类的经验中构成了最初的直觉,这种关于时空的直觉便是美学家韦尔施所言的“美学的规定”[1][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6页。。相较于空间的具体性,时间则因其抽象性,更多地触及了人类的感知与想象能力,白天与黑夜的交替、春夏与秋冬的轮转,帮助人类形成了最初的时间观念,这些表现在神话中,便使得神话叙事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味。
人类的神话记忆从来不曾只停留于久远的故事中,而总是尝试着在不同的媒介之中复现神话的诸多“时刻”。从古至今,神话中的时间总是流转于不同的艺术媒介中,诚如龙迪勇所说:“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试图模仿另一种媒介的表达优势或美学效果”[2]龙迪勇:《“出位之思”与跨媒介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第184页。,此所谓“出位之思”,也表现为跨媒介叙事。在诉诸于人类的视觉、听觉、知觉等艺术媒介中,神话的时间有着不同的表达形态,它或是在凝滞中蕴含着张力,或是在延宕中凝练出永恒,或是在循环中透露出变迁,艺术的传达既表现出神话时间的多元内涵,同时也间接地描摹出人类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变动。
一、凝滞:神话叙事中的永恒艺术
出于对死亡的天然恐惧,可以想象人类在初期阶段就已经开始追求长生不老,虽然这一类的努力最终都成为了神话的一部分,但人类仍然还是从艺术中找到了永恒,即通过某种物体的承载,使不同时空下的人产生联系的可能,进而达成与时间的对抗。
从西班牙阿塔米拉(Altamira)与法国拉斯科(Lascaux)洞穴发现的壁画中可以推测,当早期的人类在尝试用一些线条去勾勒猎物时,就在无意识中推开了艺术的大门。那些集合着现实与想象的描绘,开辟了人类的现实视角,而线条的成型又意味着对猎物生命的把控。绘画者通过表现猎手反复猎取猎物的场面,期待获得某种神奇的能力,于是,墙壁上那些线条简单的图画便具有了永恒的意味,而其中的思维方式又在盛行的交感巫术中得到了强化。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考察艺术的起源时,把动物绘画作为人类早期艺术的代表作品,那些创作于公元前15000年至公元前10000年的壁画,被贡布里希认为是“对图画威力的普遍信仰所留下的最悠久的古迹,换句话说,就是原始狩猎者认为,只要他们画个猎物——大概再用他们的长矛或石斧痛打一番——真正的野兽也就俯首就擒了”[1][英]E.H.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杨成凯校,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42页。。尽管早期的人类未必会将自己的画作当作一种艺术,但在当下的讨论中,他们的行为仍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些原始艺术中,已隐隐透露出神话思维制约下的视觉艺术,对于凝滞时间形态存在特殊认知。早期的人类对时间未必有更抽象或更具体的感受,但却有意识地通过一些工具将时间的某些细节刻录下来,进而通过这种方式去构成人类某一部分的文化记忆。
如果说人类的早期艺术更多的是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一种朴实的愿望,那么人类后世所创造诸多作用于视觉的仪式或形式则极大地拓展了时间的表现空间,这在神话题材的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莱辛在评价古希腊雕塑《拉奥孔》时,认为其美感“源于杂多部分的和谐效果,而这些部分是可以一眼就看遍的”[2][德]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拉奥孔及其儿子们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的组合构成了莱辛所说的“美感”,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即雕塑整体的“凝滞”。时间并不会因此而真的完全静止,只是通过不同时空的人的观照,产生一种看似一致的相对性,这才使时间获得了某种张力。虽然莱辛从中看到了动态性的成分,可是若没有时间凝滞所造成的动作、事态的紧张感,动力也会随之消失殆尽。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中的神话叙事,都要求创造者在神话与现实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时间”正是这样一座桥梁,除此之外,就连观看者在艺术品中获得某种永恒的意义,也同样需要时间的介入。
文艺复兴以降,表现时间的凝滞成为西方艺术家们的普遍选择。米开朗琪罗在他的名作《创造亚当》(CreationofMan)中,创造了一种将时间进行空间化表现的艺术手法,即“间距”的使用。他把神话中上帝将生命灵气吹向亚当的表述,转化为上帝将手伸向亚当,且造成两人手指的“间距”,也就是说,米开朗琪罗将生命创造的瞬间转化为视觉中的间距,从而使创世蕴含的“创造”(Creation)与“全知全能”(Omnipotence)的观念在这种间距中凸显出来。另外,在油画作品拉斐尔的《圣米迦勒和魔鬼》、卡拉奇的《圣母哀悼基督》、卡拉瓦乔的《多疑的多马》,以及雕塑作品让•古戎的《怜悯圣母》、洛朗•奥诺雷•马凯斯特的《半人马涅索斯举起戴亚尼尔》中,观者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表现对象的动作“一直保持其发生的状态,并在目光‘面对’它的每一个当下重新来临,用敞开的无限性淹没观者的有限意识,形成一种时间上的崇高体验”[3]尉光吉:《死亡即此时:绘画的瞬间与间距》,《文艺研究》2020年第9期,第31页。。在这些刹那成就永恒的表现瞬间中,时间凝滞在生死之交,既对抗着过去,也展望着未来。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当代绘画也尝试着从传统的神话题材中找寻时间凝滞的可能。比如当代画家朱新昌所作的《山海经》、《聊斋志异》系列等当代工笔画即是典型例证。朱新昌的创作虽受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但更加注重中国民间艺术的传统特性。在其代表作《聊斋•公孙九娘》和《山海经•精卫填海》中,朱新昌特别注重描绘云彩或水花的升腾之势,而人物在其中若隐若现,画家以极强的造型能力,“能赋予简至而流畅的线条以抽象凝蓄的力量,使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笔下适度变形的人物在呈现出有说服力的真实感、体量感的同时,无不显现出一种谜一样的神性。加以构思时精于从初始文本中择取动作性最强、最富有表达张力的瞬间片刻,原作的大本大宗被完整地表现了出来”[1]汪涌豪:《从朱新昌的创作看中国画的探索》,《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第55页。。这里的“瞬间片刻”其实正是时间凝滞的证明,只不过与西方绘画不同的是,这里的时间镌刻的是中国人对于神话传统的记忆,因此自然地具有了一种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相较于绘画、雕塑、建筑等传统的视觉艺术,舞蹈、电影等艺术形式因其综合性而超越了一般的视觉感官,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到时间凝滞的魅力。舞蹈其实最早可追溯至人类早期的仪式行为,神话与仪式相伴而生,因此神话在主题、场域、角色、审美等方面均影响着仪式实践,这自然延伸到了舞蹈艺术之中。如在保留着浓厚原始文化特征的萨满仪式中,舞蹈便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萨满的舞步绝不只是肢体动作的组合,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神话与宗教气息。萨满一般被认为是贯通天地、能够通神的人物,在其舞蹈进程中的“出神”状态,象征着他和神灵之间的交流,而在这种时间凝滞的时刻,舞蹈的观看者似乎也和萨满一样,进入到一种神秘的环境之中。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类的神话哲学思维影响着舞蹈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在一些与图腾信仰、萨满文化相关的舞蹈中,神话的在场往往是非常醒目的。伍彦谚认为:“按照神话哲学思维,可以说每一个神话舞蹈化的动作都有与神话情节或内容相对应的内涵。原始先民将信仰幻化为图腾,把自己装扮成图腾,并作为一种集体的标志,模仿图腾的形态而舞,将对图腾的崇拜与祖先的崇拜融为一体,形成仪式的原生形态,形象生动的舞蹈形象与动作便赋予了仪式动感与生机。”[2]伍彦谚:《论神话哲学思维对民族舞蹈的影响》,《江淮论坛》2022年第4期,第179页。舞蹈虽然是动作的连续,但在动作的间歇或静止形态中,神话的时间得以在缝隙中显身,它虽然是凝滞的,但给予观者的却是丰富的动感与生机。
又如电影,其所提供的时间景观不同于传统艺术,如巴迪欧所说:“在本质上电影提供了两种时间思想:一种是建构的和蒙太奇的时间,另一种是静态拉伸的时间。”[3][法]阿兰•巴迪欧:《电影作为哲学实验》,李洋等译,[法]米歇尔•福柯等著、李洋选编:《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想要表现出“具象”的电影,首先就需要通过对时间的掌控获得一种能力,使无论宇宙或是生命,都能在胶片中定格,然后将“每个真理都变成一种手法、修辞和谎言”[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学机器》,魏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可以说这种能够随意操控时间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成为了神话叙事的一部分。尤其在新神话类型电影中,比如中国的动画神话宇宙系列、美国的复仇者联盟系列等,创作者固然用迅速切换的运动时间表现英雄们的神迹,但他们更乐于使观众看到英雄们在善恶身份转换的那一刹那所表现出的灵魂挣扎。这种在时间凝滞时刻所表现出的英雄,在人性与神性之间转换的复杂性,构成了这些神话英雄的意义。在这种时刻,“这些形象其实已经使自己充满了时间,且到了近乎迸裂的临界点。正是这种契机性时间的饱含使这些形象具有了某种震撼力,而这种震撼力反过来又构成了它们特殊的灵晕(aura)”[2]Giorgio Agamben, Nymphs, London and New York:Seagull Books, 2013, p.4.。也就是说,当下神话题材电影早已脱离了讲述传统神话故事的阶段,而是利用时间的灵活姿态,表现英雄们在凝滞时间中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复归,这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积极意义。
二、延宕:神话叙事中的流动艺术
人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不仅通过眼睛所见的诸多神话形象发现神话的意蕴,而且也通过另一种感官形式认识神话,即听觉。神话的最初讲述者以语言描绘神话的场景和想象中的英雄,使听众从大家共同了解的语言中了解神话的样貌。讲故事的行为塑造了人类早期的听觉艺术,恰如叙事学家傅修延所说:“讲故事从一开始便是一种生产听觉空间的行为——一人发声而众人侧耳,这种‘点对面’的沟通已在对人类社会架构进行最初的塑形。”[3]傅修延:《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89页。在讲述神话的过程中,一个新的与现实空间相区别的神话空间逐渐浮现。
听觉之所以能够帮助人类形塑神话,是因为讲述者口中声音的传输不同于视觉与触觉,也不同于人在阅读时在心中唤起的感觉,而是借助于似断实连的声乐与人的听觉器官发生作用,从而在人的感觉层面产生暂留效果,这与时间的绵延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脑海里时常萦绕的某段声音或旋律,常常会经由人的发声器官显现出来,这便是声乐暂留的证明。尤其是声音由形象的语言描绘出来的时候,这种声乐就会在人的脑海中幻化成具体的形象,从而对人的想象产生长久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神话直至当下仍经久不衰的原因。早期的口传神话不仅通过声音的传输塑造了初期的共同体社会形态,而且通过声音在人类大脑中的暂留使人们获得神话记忆,这造成了时间在听觉艺术的神话叙事中呈现“延宕”形态。随着人类语言的不断成熟,神话逐渐摆脱了早期的粗糙描绘阶段,而被赋予了越发成熟的叙事外观,这促成了早期英雄史诗的诞生。《格萨尔王传》《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等经典史诗,最初都是由讲述者口头传播的。在一次次的传唱中,英雄们在听众的脑海中有了逐渐清晰的形象,英雄们的事迹也经过听众的口耳相传,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聆听史诗,是试图在繁琐的日常时间中保留一种神话时间,这种时间能够在人的头脑中不断延宕下去,因此能够给人以强烈的神秘、崇高的感受。传承千年的史诗虽然之后有了凝固的文本化形式,但像《格萨尔王传》这样的作品,仍然在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地流传,“雄狮大王格萨尔”“九头魔怪鲁赞”的故事,在反复的传唱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这构成了中国广袤的西北地域上不同民族所享有的共同神话记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依靠讲述者传播神话的实践,神话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容,这可称之为“新口传神话”,比如借助新的技术条件实现的音频分享平台,即是典型的案例。这些音频分享平台保留了传统口传神话的“点对面”的传播方式,但却不再是围绕篝火,而是利用“单向度的自媒体形式”[1]张多:《当代中国神话的大众化重构——基于新兴自媒体对神话资源转化的分析》,《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第116页。,使听众利用手机、耳机等现代通讯科技实现更大范围且有效的传播。在喜马拉雅、蜻蜓FM、荔枝FM等音频分享平台,踊跃着“爱讲神话的小志”“震震君”“小亚神叨叨”“钱丢丢”等新型神话讲述者,他们将神话移入电子媒介的语境之中,赋予了包括神话在内的民俗“第二次生命”(Second life)。它与“第一次生命”(First life)相对,指神话从之前隐蔽的环境中挣脱出来,并“将在通常都远离其最初环境的一个新的语境和环境中被表演”[2][芬兰]劳里•杭柯:《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户晓辉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第103页。。简要来说,自媒体平台上的声音主播们,一方面,利用耳熟能详的神话题材(如《山海经》《封神演义》等),运用不同的讲述方式,尽可能多样地为听众提供新型的收听手段。一些主播可能利用较为传统的形式为听众作神话故事的普及,另一些则可能以较为幽默的娱乐化方式丰富现代人对神话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也发挥了“声音”在音频分享平台的优势。相对于围绕篝火讲述神话时声音的失真与模糊,通过现代科技塑造的声音更加清晰且令人舒适。在听众普遍使用耳机的时代,主播们普遍使用优美的声色,舒缓而和谐地讲述被现代改编的神话,使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片心灵得以休憩的领域。当听众戴上耳机,就会被包裹进一种神话讲述的氛围之中,这不像人在剧院或音乐厅中的感觉,而是“当声音从颅骨上直接向戴耳机的人传送,他不会再把事件当作使从声音的地平线传来,不会再觉得自己被一组可移动的事件围住。他就是这一组事件,他就是这个宇宙本身”[1]R.Murray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r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Knopf, 1977, p.119.。这种沉浸感其实正是主播们希望实现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声音的空间中,神话的时间自然地延宕着,不管是使人们安睡,还是令人们心灵放松,这已经使新口传神话表现出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神话的新生态,获得了崭新而蓬勃的生命力。
除了诉诸于人类语言的听觉艺术,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抽象的艺术形式,即音乐。与人所发出的语音不同,音乐是由音符、节奏、韵律所连接而成的声音形式,人类创造音乐起初受自然万物所发出声音的启发,在模仿中逐渐掌握声音的规律,并最终创造出感发意志、愉人性情的音乐。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较早地对神话与音乐本质的趋同性作了说明。在他看来,神话与音乐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时间上的连续性,运用着同一套语言模式。斯特劳斯之所以将音乐视为神话的替代品(就像传奇小说一样),是因为人类以神话思维感受神话,与聆听音乐时的时间感受具有一致性。斯特劳斯将音乐与神话视为“消灭时间的工具”[2][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这是因为“在声音和节奏作用下,音乐作用于听众的生理学时间,这是不可逆的,然而由于音乐作品的内部结构能够将这种历时性的片段转化为共时的总体,听众通过聆听音乐又仿佛进入一种时空停滞的永恒状态。神话同音乐作品相类似,它是对历史性与恒久性之间二律背反关系的成功克服”[3]董龙昌:《论列维-斯特劳斯的音乐人类学思想》,《美育学刊》2016年第5期,第111页。。
时间在神话和音乐中的共同表现,使得音乐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史记》中曾载卫灵公带乐师师涓为晋平公庆贺新台的事件。师涓在席间弹奏了几首纣王乐师所作的曲子,乐师师旷因此而深感不安,但却不能予以制止,这几首受到鬼神谴责的靡靡之音最终给晋平公带来了亡国之祸。隽永的音乐借助了无限延展的时间得以绵延,因为无论如何重复,一段曲目总是需要同样的时间,听众才能借助被分割的时间去感受乐曲的延宕,其中俞伯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以及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凤求凰”都可以看作是神话在音乐中延伸的艺术形式。也正因如此,《礼记•郊特牲》中才会说:“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5页。在一些神话题材的音乐中,如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作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国作曲家何占豪、陈钢所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均表现了时间的矛盾性存在。时间“没有终点,即没有穷尽,是永恒的,但这个永恒本身又是由时间所赋予的,它是流逝的”,这些乐曲表现了时间“连续不断地生成和永恒的自我存在”。[1]刘锟:《论洛谢夫的神话哲学与美学思想》,《俄罗斯文艺》2020年第1期,第47页。
三、循环:神话叙事中的重复艺术
从人类文字的发展史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人创造的汉字还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这些从图画符号延伸出来的文字,引发了人类早期丰富的视觉体验以及由之而来的心灵变动。在经验和理性的作用下,这些符号最终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固定下来,人类再通过对文字的组合、转接,创建出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文学。与直接观看的艺术不同,文学的艺术形式不是在人类视觉经验层面发生作用,而是通过读者的阅读使人在心灵中生发想象,并最终在脑海中创造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
在人类发展早期,文学作品是以神话的样式存在的。鲁迅指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创世神话、造人神话和洪水神话遍布世界各地,这不仅是对人类共同生存经验的想象性表达,同时也以故事的形式使人类的共同记忆能够传承下去。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技术时代未到来之前,人类用来表达时间的方式是类似的,那就是由初级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一种“循环”的时间认知。太阳等天体的循环式运转、自然界中的生老病死、草木荣枯和生产活动中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些不仅是自然中生发的景观,而且在人类世界里具有了叙事性。在这些“故事”中,循环的时间形态成为万物运行的助推力量。这一观念影响着人类文学作品的创作,在早期神话作品中,时间留存着其朴拙的状态,被赋予了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
神话为人类创造了开始、过程和结束的概念,而循环时间的存在,则使得人类不仅尝试在文学中还原过程性的事件,而且更为注重这一事件的可重复性。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与其说这是一场人间的战争,毋宁说是神明之间的争斗,双方的英雄们都在为了荣光而英勇奋战,但在这长达15693行的史诗中,展现的具体内容几乎都是打斗—倒下—打斗—再倒下—再打斗。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不幸死亡,也有人获得新生,变换的是姓名,不变的是双方在看不见时间边界的空间中,发生着这样一场毫无休止的战斗。而到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的十年海上之旅又呈现出了时间的循环,尤其是他们在风神的帮助下,用一口神奇的口袋装进了海上所有的逆风,结果在一路顺风中终于快要抵达目的地时,一众水手竟然鬼迷心窍地认为这个充气皮球一般的口袋里隐藏着金银珠宝,于是放出来的逆风又一次将他们吹回风神岛,可这一次却没有了风神的帮助。叙事经过一个循环又回到了原点,这种神谕式的命运主题恰恰是在一种循环时间观的引导下完成的,循环被赋予了优美的特质,成为与神话叙事密切相关的要素。以至于在吸收了史诗养料的西方小说中,也充分表现出了它们所受到的这种影响。如以批判教会著称的《巨人传》,拉伯雷以庞大固埃的奇遇为叙事脉络,到最后找到了能喝酒的神瓶,空中传来“喝吧”的声音其实与他意为“饥渴”的名字“固埃”形成了奇妙的循环。400年后的罗曼•罗兰也或多或少地承继了这种思路,在他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天才钢琴家克利斯朵夫孤零零地出生、又孤零零地死去,虽然有过对命运的抗争,到最后却仍向命运低头,也曾有过爱情,但始终孑然一身。他的一生好像做了许多事,又似乎什么都没做,时间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不规则的循环,用更为隐性的方式介入叙事,从而超越了时间在传统叙事中的表现形式。
较之于西方的海洋文明,中国的文学叙事传统对于时间的循环形态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农耕文明发达,四时节令即是先民在对循环时间的长期观察中提炼出来的。《击壤歌》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礼记•月令》则从春季的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到夏季的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再到秋季的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最后到冬季的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以四季的变换对从天子到庶民的所有应做应为作出了规定,这显然已是从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礼治”中对时间流转和循环的一种叙事展现。不管是较早由《淮南子》辑录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话,还是后出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它们的讲述主题都围绕先民更为熟悉的天地秩序的失衡与恢复。共工怒触不周山致天地失陷、十日并出致生灵涂炭和天地混沌未分等景观,皆是天地失序的一种表现,因此女娲、后羿、盘古的创举,即是以神力推动停摆的时空重回正轨,如此天地的循环往复才能得以延续。由此可见,中国的早期神话也是在循环时间观的引导下,具有了与西方神话文本相似的外观。中国古人甚至将循环视为一种游戏,如“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等诗词歌赋,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神话思维的叙事基础,并影响了后世的叙述。
从小说创作来看,唐人小说与宋代传奇,乃至明清小说,都保留了浓厚的神话叙事风格。循环的时间观念仍然是小说家普遍坚守的对象,其中《三国演义》开篇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为叙事时间的循环奠定了基础。再从神话叙事的角度看时间的循环,又会有新的发现——《红楼梦》《西游记》《隋唐演义》《醒世姻缘传》《镜花缘》等小说中都存在两种叙事,一种是现实的故事讲述,另一种则是神话叙事,而且后者对前者有极强的统摄作用。即使如《醒世姻缘传》这样的世情小说,也会以转世、消业的叙事来为夫妻姻缘、父子关系等现实状况作出解释。凌濛初借小说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1][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而这一目的正是在时间的循环下,使古典小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有了可供承托之处。把循环观念作为叙事引子的写作被杨义先生称为小说的“叙事元始”。他认为:“中国作品的叙事元始,是出入于神话和历史、现实和梦幻的。它采取动与静、顺与逆等一系列两极对立共构的原则来组建自己的时间形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叙事层面,以多姿多彩的形式显示了时间的整体性观念。”[2]杨义:《中国叙事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94页。中国古典小说与循环时间相关的神话叙事风格可见一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使一些作家试图重新从神话资源中找寻灵感。他们不再在创作中秉持一种直线式时间观念,而是重新讨论时间循环的可能。这种创作现象符合诺思洛普•弗莱对文学史发展之循环特性的发现,即“文学史的运动发展演变成在两个极端世界之间的置换更替、有规律的演进循环,表现为非移用的神话、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再转向神话”[3]高海:《神话隐喻下的文学阐释与审美乌托邦——诺思洛普•弗莱理论及其对中国文艺批评的启示》,《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5期,第104页。。在《神话的诗学》一书中,俄国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苏醒》、托马斯•曼的《魔山》《约瑟及其弟兄们》,以及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城堡》等小说创作视为20世纪文学中的“神话主义”现象,这其实即是弗莱所说的西方小说回归神话的具体创作实践。梅氏提到,20世纪神话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表现于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面,即“主人公在空间范畴永无休止地再现和复制(形同一体者),特别是在时间范畴永无休止地再现和复制(主人公周而复始地生、死、复生或以新的形体呈现)”[4][俄]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1页。。在这一视域下,布卢姆在都柏林的漫游、卡斯托普在疗养院的居留经历、土地测量员K面对近在咫尺的城堡却始终无法进入的窘境,都成为神话英雄冒险历程的现代再现。而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如莫言、贾平凹等在神话叙事方面作出的开拓使他们对循环的时间作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描述。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本就是对循环时间的再现,贾平凹的《山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小说,则开辟了一种新的神话叙事方法,即在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中表现神话时空的渗透,由自然时间的循环所引发的“互渗”现象,使他们笔下的历史既包裹着神话也反映着现实。
结语
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德国哲学家谢林说道:“如果艺术本身是永恒的和必然的,那末,在其时间范畴的显现中,则无偶然性,而存在绝对必然性。”[1][德]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25页。在谢林看来,神话是一切艺术创作的“质料”,时间范畴的引入能够使创作者借助时间形态的表现直抵艺术的本质境界。可以这样认为,时间的复杂性与抽象性,为人类实现从生命有限性到价值无限性的突破提供了可能。在艺术形式愈加多样的今天,人类仍然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养料、寻找想象的空间,这是因为在当下人类琐碎的时间体验中,永恒性已成为一种奢侈品,人们已习惯于徜徉在由技术、理性所打造的虚构世界中,却很难体验到真实的感觉。神话虽然是一种虚构,但它给予人的感觉却是真实的,时间的多种类型为这种感觉提供了依据。因此,当人们越发感觉到神话的宝贵,试图从神话中找寻一种久违的感觉时,其实是在找寻曾经多元化的时间观念。由此,传统的神话时间在艺术实践中与人类的现代心灵实现了神奇的交汇,一个将要被遗忘的、神秘而博大的神话世界开始重新回到人类的生活,人类也必然能够从中获得对神话时间的具象化认知,以及对艺术创作真正价值的深刻认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艺术形式,它们都为人类重新感受神话时间提供了重要的中介,时间以或凝滞、或循环、或延宕的形态,吸引着人们在神话艺术前驻足、观赏和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