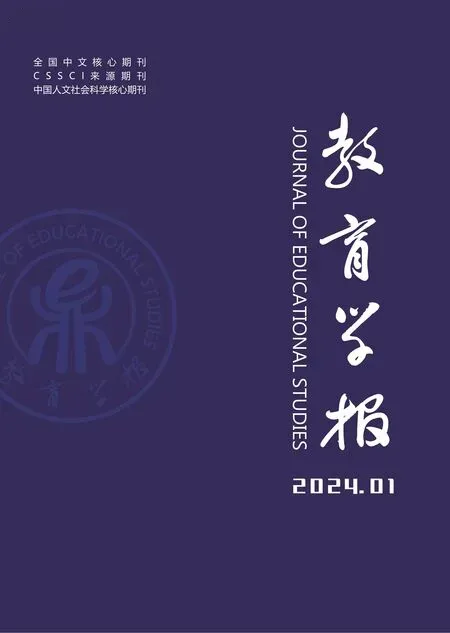印刷革命塑造教育现代性
——基于文本、图像、空间的三维透视
黄希雯 董 标
(1.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2.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在宏观历史事变的背后,往往存在一些“默默无闻”的推手,不易被注意和发现。古腾堡的印刷术自诞生起,便为西方15—19世纪的历史布置舞台(resetting the stage)。[1]303印刷革命(古腾堡革命)——“未得承认的革命”(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的最直接后果是,带来“印刷本”这一新事物并创造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print cultures,printing culture,printing cultures,printed culture,printed cultures,the culture of print,typographical culture)。“所有印刷都是‘教育的’”(all print is “educative”)。[2]3在西方现代教育史中,以印刷革命的“代言者”印刷本为切入点来探寻教育现代性,具有独特的、“未得承认”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理解印刷如何形塑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以及如何促成了教育中理性与主体性的产生。
一、问题源起与研究背景
欧洲的印刷术为印刷革命提供技术前提,印刷革命与不同的国家、地域、社会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印刷文化;印刷文化涉猎范围极广,本文将视野聚焦于印刷本之上,透过印刷本这一物质,以更为具体、清晰地阐明印刷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本文尝试达到两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目标:(1)经由揭示印刷本与教育现代性的概念所指,初步形成关于印刷本特性、教育现代性特征的认识;(2)初步分析并解释印刷本(主要是15—18世纪)与教育现代性的关联。
(一)印刷革命的前因后果
印刷革命有前因后果。7世纪中国唐朝发明的雕版印刷,以及12世纪从中国传到欧洲的纸张,皆为欧洲的印刷革命作序。1450年,德国美因茨(Mainz)的金匠约翰·古腾堡(也有翻译为古登堡、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4—1468)创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机。“1456年,欧洲人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3]在这之后,印出了更多“摇篮本”(Incunabula)。(1)“第一本书”,不等于“第一件印刷品”。“摇篮本”,指1450—1500年期间印制的早期印刷本,以宗教典籍为主,在板式样貌上与手抄本较为相似,是手抄本到印刷本的过渡阶段的典型产物。“到1500年,欧洲已有超250个地方建立了印刷所——意大利80个,德国52个,法国43个,这些印刷机生产了27 000个版次,设若每一个版次有500本,彼时1亿人口的欧洲拥有约1300万的书籍。”[4]印刷本渐渐取代手抄本,除《圣经》、布道辞、祈祷书、年历等以宗教为主的材料外,关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以及大众读物也开始出现。借助印刷,人文主义的相关思想与典籍得以从意大利传到北欧,为其带来一股新气息。
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教会教皇长期以来实施的精神控制及其自身内部的严重腐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将手写的《九十五条论纲》(拉丁文:Disputatioprovirtutisindulgentiarum),张贴在维腾堡(Witttenburg)大教堂门上。随后,他的论纲、论文,在十五天内以小册子、传单、海报的形式传遍德国。“据推算,16世纪里出版的书本总量达1.5亿到2亿册。这样的推算可能还过于保守。”[5]新教、天主教都意识到印刷所隐藏的巨大威力,通过印刷,他们不断向公众宣传、推广、解释自己的教义教条,宗教改革运动由此推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亦得益于印刷术,启蒙运动中,印刷商已成为重要力量。18世纪末19世纪初,阅读书籍、报纸、杂志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惯常。19世纪至20世纪,电力—电子时代(电报、电话、唱机、电影、广播、电视)来临,印刷与新媒介融合出新。新的电子时代建立在印刷所建构的意识与空间之上。
(二)印刷与教育现代性的相关研究
印制的世界(The Printed World)不是自洽领域,不是自主空间。书面知识的精神价值和象征价值得到认同,书面阅读与文化资本的获取建立联系,造纸和雕版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听觉信息与视觉信息在日常生活中的换位,社会流动与图书市场的系统发育,人口增长和大众教育的崛起,等等,都在印刷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某个因素,印刷文化难兴。虽说在17—18世纪之交的“古今之争”中,即有敏锐的著作家,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印刷新媒介,(2)参见: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著:《书的战争》,1704年版,译本见管欣译:《桶的故事·书的战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但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仍只有少量专门著述,在学术界产生了大小不一的影响。如《从写本到印本:中世纪文学导论》,(3)H.J.Chaytor(1945),From Script to Print: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Litera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域界自限,不如《书籍的历史》流布广远。(4)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1958),The Coming of the Book:The Impact of Printing,1450—1800,Translated by David Gerard,Edited by Geoffrey Novell-Smith and David Wootton. 参见:吕西安·费弗尔、亨利-让·马丁著,和灿欣译:《书籍的历史:从手抄本到印刷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
最近半个多世纪,印刷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谷登堡星汉璀璨》[6]、《理解媒介》[7],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1],以及沃尔特·翁(Walter J.Ong)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8],等等。
印刷革命出现后,小册子(pamphlet)、日历(calendars)、年历(almanacs)、大报(broadsheets)、海报(placard)、纸牌(playing cards)、书籍(books)等印刷品日益丰富。印刷革命与教育、教育学的联系已被部分研究者关注到,其焦点多围绕阅读、读写能力(literacy)、印刷材料等展开,但却未对印刷与教育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作明确、深入的分析。见《教育学、印刷与新教:儿童的话语》[9]、《印刷读写能力的发展:联结认知和社会实践理论》[10]、《美国现代教育与印刷文化》[2]、《在伊朗创造历史:教育、民族主义与印刷文化》[11],以及《教育的“技术”发展史》[12]、《彼得·拉米斯与印刷技术时代的教育变革——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元认知”框架》[13]等文章。
本文无法尽述“印刷研究成果浩如烟海”的当代学术景观。上面提及的这些文献,已经透露不少有价值的新知,展现某种、某类、某维度上的矛盾运动:一方面,印刷提高了个人的读写能力,促成了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印刷也使个体被标准化、统一化,并与更大的社群、民族、国家建立起联系。正是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教育现代性在不断被印刷塑造。
论及教育现代性(modernity),有诸多论说。现代性,指向从18世纪中期欧洲启蒙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特征是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个性化及科学的兴起。[14]现代性指涉人类运用理性思考,了解、解释、预测或控制各种现象。[15]中国大陆学者认为,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是理性与主体性。[16]教育现代性,则指现代性社会中教育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品格和样态,或者说是现代性精神、理念、原则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和兴起,从而使教育呈现现代性精神气质。[17]教育的现代性虽有多种指向或解释,但本文主要将其聚焦于理性与主体性的范畴,即关注人的理性与思维、主体性与意识的发展。在印刷与教育现代性之间,人为桥梁、衔接二者,教育现代性指向人在教育活动中所体现的理性与主体性。
综上,下文将从印刷本的文本、图像、空间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印刷革命如何促使读者的理性与主体意识生成,而教育现代性又如何在此过程中得以萌发。
二、印刷文本与教育现代性

(一)印刷文本的“他者”世界
1439年活字印刷面世前,抄写时代几乎没有“文本”的概念。“每一份抄写都是个人作品的艺术呈现,每一个艺术家都声称自己有权利‘演奏’抄写、展示书法、改变字词,以适应个人喜好,随个人意愿增减作品内容。”[20]抄写员总能依据自己的思考,在原有的抄写稿上有所加工,个体与其相融,合二为一,形成叠加式的抄写本。阅读的人亦难分原作,“沉浸”在手稿里,随时将“自我”代入抄写的世界。印刷则使文字得以固定和保存,停留在页面中。印刷的内容材料大多是静默、冷淡的,缺乏生动、形象的气息,“手稿尚有评注或旁注(glosses or marginal comments),仍在与世界进行对话……印刷术则强加了封闭或完结的物理感觉。”[8]130于读者而言,印刷文本是已完成的、不可改变或加工的状态,因而构成一个“他者”的世界,与“我”的世界明显区分,成为符号性、实体性的存在,亦成为主体之外的客体存在。因为印刷术,已产生的文本和过去永远被固定在一段距离之外,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世界,并且不可能被复原——这种感觉是我们现代意识的标志。[1]119在空间、时间上,印刷文本以其独有的保存功能,将当下与过去分割开来,成为培植现代性的肥沃土壤。印刷出现之初,印刷本尚不普及,但可进入到部分群体的生活中。已有教徒通过每日所读的印刷本,形成主客体的初步意识,将自我与他人分离开来。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他者”世界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自身对《圣经》的阅读和理解,凭借个人的、内部的信仰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以内在的主体性重新认识周围的世界。
阅读印刷本的人们,亦是受教者。当人们形成清晰的主体概念时,印刷文本便在教育中生发出两个不同维度的影响。
一方面,面对印刷本时,读者为主体、文本为客体。读者、受教者的身份分明,他们是有别于文本、教者的另一方,拥有自己的角色与地位,个体的意识得到极大培养与发展。“与书籍建立起来的神秘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条轨迹,阅读活动在其中呈现为一个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确立‘他者’,为主体求索立基;神交之际,无边的大欢喜;文本‘入体’,让身体产生明确的生理反应;在这一过程的终点,阅读中断,书籍舍弃,彻底解脱。”[18]89从“他者”到主体,文本逐渐进入我们阅读者的心灵与头脑中,最终,离开书籍之时,我们便产生了新的思考。这种“主体”与“个人”的出现,在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教育对象以平等乃至超越的姿态矗立于知识获取的过程中。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人是教育的核心,对人与主体性的凸显和强调,构筑现代教育的精神品质。况且,“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读者、每一个主体都在阅读印刷文本的过程中,拥有着特有的解构方式,他们的主动性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得以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面对知识时,文本是教者与主体,读者是受教者与客体。作为知识的化身、权威的载体,文本促成了客体的诞生,受教育者成为接受知识的对象,也成为教育中的客体性存在。当印刷文本愈来愈普遍和流行时,教育者便彻底占据了强力地位,受教者的主体身份随之受到压抑,个体的想法与意识也可能被忽视。比如,宗教改革虽推动了大众教育与知识普及,但是将民众当成接受识字教育的“他者”来看待,人们是在一个圈定的场域和设定的程序中接受教育的,“学校知识的传播、获得和复制形成一种程序性话语,其中,主体为知识对象,学生是话语研究与审查的客体,甚至是可证知识的体现。”[9]119印刷创造了一种“新”教育(现代教育),它使“接受”教育变成“受”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在思想与意识上的主动性。
(二)印刷文本的叙事方式
手抄本是通过个体的行为生成的,借人手诞生,与个人紧密联系,蕴含丰富的感性经验,其叙述呈发散式的结构状态。印刷本则从集体性的印刷工厂或作坊中产生,历经梳理、排版、校对、审核、印制等流程,更具系统化、组织化,也在文本叙述上遵循了明显的线性逻辑。印刷文本,在连续思维和书写的线性运动中构成,文本有其核心范畴、基本思维线索和概念关系,[21]每一份印刷文本都拥有自己的问题中心或假设前提,文本内容围绕“问题”步步展开、铺陈,或说明、论证。印刷本通过规范化的语言叙事方式造就了一种公共世界,在变化的文本中提供了一种不变的法则。
当阅读印刷本时,读者便进入到其中的文本主题与问题世界,跟随其叙事方式,层层推开,延展认识。基于此,读者的思维逐渐从经验世界转向理性世界,形成分析问题、论证事件的行为习惯,理性得以孕育,逻辑得以产生,现代性得以萌发。麦克卢汉一语中的,“印刷术不仅是消费媒介和商品,它教会人们,如何在系统化的线性基础上,组织其他活动,它向人们展示,如何建立市场和国家军队。”[22]印刷术乃至印刷术带来的印刷文本,都并非静态的技术或物品,它不仅使人们浸润到文本特有的叙事方式中,养成组织化和系统化的思维特性,更渗透至人们的教育活动。
如此一来,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观念发生着深刻转变。首先,要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这是得以阅读印刷文本、发展理性思维的前提。“以印刷技术为背景的‘读’和‘写’成为文化素养的基本标志。”[23]在口语乃至手抄本时代,能够“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重要体现,而在印刷文本兴盛时期,“说”已远远不够了,“读”“写”成为新的培养方向,教育对人的要求明显提高了。其次,要学会有条理、有逻辑地看待与分析事物,儿童被置于集体的环境中进行考量。波兹曼(Neil Postman)在讨论印刷的偏见时指出,“儿童走向成年,需获得我们心目中的好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即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的思考能力,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操纵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24]68由于印刷遵循逻各斯的法则,从文本的核心问题出发,有秩序地展开理解,严谨地表达自我,已是成“人”的必修课。
教育中理性意识的蓬勃发展,确能使人趋于现代化,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与此同时,也埋下了问题的祸根。印刷术使“书写的力量”得以普及和标准化,监狱长般的教师依据分类的标准表格,检查、评估、记录和描述要管理的人……16世纪的路德教育改革文件中,已出现关于排名与考试的论述。[9]6-7,84随着文本学习的制度化,人也被物化、制度化了,书写的力量渗透到教育中,使理性思维的发展和文本分析的能力成为评判儿童的唯一指标,更使儿童的培养如生产流水线般,趋于机械化。而且,不止是儿童,在印刷文本所建构的思维环境中,教师也被迫顺应标准化、一致化的文本材料与教学流程,他们被“钉”在规范与逻辑之中。有学者指出,“学校的读写能力以及它的教授是霸权主义的,因为它只评估学术性的读写能力”[10]66,这种专制,正是印刷文本所带来的。
三、印刷图像与教育现代性
图像是印刷本中另一不可忽视的存在,它根植于我们的感官,比文字、文本更直观、形象,甚至更具有解释力。尤其是在识字教育尚未完全普及的时候,图像为信息的获取扫清障碍,沟通了读者与印刷本,“使用图形媒介,既向外,向着读者的生活世界,又向内,向着书中的内容。”[25]164
(一)印刷图像的神像具化
公元5至15世纪的神,特指上帝,上帝是神圣教堂中的塑像,更是虔诚信仰中的虚构。若要认识上帝、了解上帝,需在布道堂聆听、祷告,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走近上帝,接受上帝的指引。虽有部分关于上帝的手工画像,但画出来的手稿何其珍贵,难以复制和还原,它们只为教会上层所拥有,凡人无可窥得。因此,心中的神是抽象、崇高的,个人是渺小、微不足道的。弥撒是一场遥远而模糊的表演,牧师背对人们,站在教堂前的圣坛上,用拉丁文低声念着圣餐祷文,他在会众看不见的地方做了系列复杂的动作……印刷的物件则增进了与神圣人物的关系,通过与印刷品的互动——圣人的故事和图像,可形成对超自然事物的直接体验。[1]92-93当印刷出现,图像的复制获得极大便利,随印刷本流入更多群体的阅读中时,“阅读变成跪在祭坛前的同义词”[26]。
上帝从圣坛走下,其形象、样貌、生活显现于印刷本的图像,成为具像化、近距离的存在。图像就在身边,圣经可以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上帝便能通过自我进行认识,而无需依赖中介。书本的普及,使人们习惯了“唯圣经”(sola scriptura),即全面象征(tout-symbolique),从圣像到画幅,图像改变了符号,从显圣变成了表象,从主体变成不过是客体而已。[27]上帝的神圣性逐渐淡化、日常性增加,完成了第一次祛魅,瞻仰式的祷告转为了书本中的对话。由此,延续千年的信仰方式发生改变,人从上帝主宰的世界剥离出来,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神的完全崇拜,从而建构了主体意识。“15世纪的祈祷者们越发频繁地使用眼睛和视觉,而这种从‘嘴’到‘心灵’的感官转换具有重要意义。”[28]
通过印刷本的图像,神成为可触摸、可对话、可讨论的了,而当更多的内容、材料被公开时,人们便得以在共同的文本和图像中穿梭、比较,产生新的思考与见解。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印刷使人们阅读同样的文本、研究相同的图像;它使同一个人得以比较对同一现象或事件互相敌对和矛盾的陈述,因而也鼓励了质疑。”[29]30这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Allegory of the Cave)有异曲同工之处,站起来、走出去,看到外面的太阳,才知道洞穴所见的光影是假象;印刷图像所带来的变革亦是如此,通过它,人们看到另一种信仰方式,看到另一种知识解释,才得以分辨虚无,把握真实,持一种审视、批判的态度。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认为,教育以解放为目的,要唤醒人们对变化世界的批判意识,鼓励人们不断反思。[30]印刷革命带来的神像具化、主体意识、反思质疑,恰恰促成了教育的解放,推动教育现代性的不断生成。质疑过后,言说、表达、辩论的欲望随之产生。路德等人代表的新教,与罗马教皇执掌的旧教,刊印论稿,相互辩论与抗衡,二者的活动虽体现不同的宗教主张,但都是以神为中心,就神而作的言说与思考。“印刷业正在创造全新的阅读社会及全新的、强大的文学形式:由印刷推动的论战写作(polemical writing)”[31],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中“主流声音”的主导地位得以被打破,更多批判性、反思性的“呐喊”被听见,更多边缘、底层的群体被看见,教育的解放与主体性也从个人扩展到群体。
(二)印刷图像的知识建构
欧洲中世纪时,流传的多是与宗教、神学相关的知识,教条教义可用文字阐明,它们构成知识的主流。与理性挂钩的科学类知识,则尚未获得充分发展。活字印刷术诞生后,情况大有不同。原本难以临摹的图像被迅速、便捷地复刻,带有插图、结构、框架的复杂性知识不断生成。在解剖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等领域,印刷术使信息传递,从模棱两可的文字转向精确的图形和数学表述。[32]
印刷图像带来了一场知识革命,塑造了具有理性特质的现代世界。理解印刷与理性,可以从理性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及一种思考能力的维度展开。一方面,基于印刷图像,以数字、符号为代表的科学知识不断充盈,人们在接触与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也在逐步掌握更多的抽象信息与经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识普遍包含图表、数据,可以通过公理、逻辑进行反复推导与验证,因此,人们也开始遵循科学法则,以分类的、分析的、结构的思维模式对客体进行认识。到16世纪末,欧几里得、解剖学、物理学的书籍,可供所有具备识字能力的人阅读,各类书籍随手可得……100年里,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起来,新环境使世界充满新信息和抽象经验……这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 man)的诞生。[24]52-53
印刷图像,为教育的现代性生长提供可能,这一点在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印刷本出现之际,正是新型大学建立的高峰期。[33]各种知识内容呈爆炸式增长,科学学科迅速发展,它们进入学校,成为课程设置。与此同时,基于这些学科自身的特性,教师也以更为科学的方式组织和展开教学过程,帮助儿童建构关于知识、学科的理性观念,形成分门别类的认知方式。印刷改革了课程,使其囊括了大量作者和多种语言,这在手抄本时代是不能想象的……从16世纪开始至今,因为印刷,科学和工业将分类(划分)的法则,拓展至所有涉及调查和实用性知识的过程中。[34]当这些学科内容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于课本与教材时,印刷本也成了无声的教师,它是杰出的教学机器,是完美的传授知识工具,学生可以依据印刷材料进行自主性学习。如此,基于印刷图像所形成的知识建构图景,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教育过程,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气息,教育逐渐步入现代社会的轨道。
然而,印刷图像的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非常普遍。图像挤占了文本的空间,与图像有关的知识不断膨胀、过载,逐渐碎片化。真实的、虚假的,有用的、无用的,皆难以确定,个体淹没在新知识、新世界所创造的混沌中。“有太多需要了解的东西,人们(尤其是阅读和接触印刷品的人)正变得心烦意乱和不知所措,这导致了对于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成为何样的人的伦理上的混乱,认识论上的混乱产生了伦理上的混乱。”[35]印刷图像建构的知识,不仅消解了人们基于这些知识所发展出的理性思维,也使得人们消弭了主体性,引发了现代性的困境。而且,由于印刷图像的便利性,知识更加精准、具体,思维也更加固化、僵化。一旦言及教育,便摆脱不了学科的分类、知识的门类、课程的组织,印刷图像最初引入的科学性思维,愈发演变成固化的教育模式,图像的功能转为单一的说明、解释,教育的功能也转为了纯粹的知识施予。
四、印刷空间与教育现代性
空间与身体、意志联系在一起,它以“有形”的形式和“无形”的场域影响着个体,塑造着教育现代性。印刷本所构成的空间,与副文本密切相关,副文本是印刷文本与读者的中间地带。法国文学评论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指出,“副文本(paratext)为世界提供进入与返回的可能。它是一个在内(面向文本)外(面向关于文本的世界性话语)之间都没有明确界限的区域。[36]2副文本分为内文本(peritext)——出版商的内文本(版式、封面、印刷等)、作者、标题、引言、前言、注释等,及外文本(epitext)——公共的外文本(公共回应等)、私人的外文本(日记、访谈等)。由于印刷本是关于印刷材料本身的,故下文主要围绕内文本展开探讨。
(一)印刷本的版式样貌
印刷商或出版商生产了内文本,使印刷在封面、格式、字体等方面拥有独特的形式。形式影响着内容,印刷成品以物化的方式构建着人们的理性思维。
虽有精美的抄写本存在,但因誊写人的字体不同等原因,它们大多并不一致,排版样貌各有千秋。手持一份印刷本,则是截然不同的体验,我们可看到整齐的文字、规范的版面、一致的区间。印刷在排版上的控制,常因其整洁性给人以深刻印象:行列规整,右边对齐,页边留出空白,无需借助手稿中常用的线和边框。[8]120印刷本带有一种“威严”,它容不得半点杂乱无章,刊印次数最多的四十二行《圣经》便是典例,它是印刷初期的优秀制品代表,字母、单词按语言次序依次排开,一段段的文本构成方方正正的板块模样。
阅读时,人们不仅看到文本和图像,更是处在印刷本所框定的空间中,久而久之,便养成了规范的认知方式——凡是零散、杂乱的东西,需得到梳理、规整、组织、分条缕析、一一陈列,才能面世,拉米斯提出的“印刷教材范式”(Ramism)即在这样的设定中诞生。(6)拉米斯教材源自法国人文主义学家、教育改革者彼得吕斯·拉米斯(Peter Ramus,1515—1572)提出的拉米斯主义(Ramism),拉米斯主张用印刷本取代手抄本,拉米斯主义强调逻辑、修辞、定义、分类等。参见:董标:《教育理论的知识基础是什么——教育认知革命“宣言”》,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92-102页。显然,印刷本建构的版面空间,将人带入理性的世界,而人又将此种思维带入更广阔的活动与实践中。读印刷本,是获取知识的过程,也是受教的过程。如果说,印刷本的文字与图像是受教育过程中的内容,那么,印刷本的空间则仿若接受教育的“场所”,它塑造了不同的教育形式。
在上述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欧洲的人们开始建立教育组织和学校制度,将孩子放入固定的教育环境中,全面、系统地培养。于是,学校教育获得社会的关注,加速了自身的发展历程。16世纪的欧洲,班级的概念与形式开始出现,年龄阶段、学生数量成为重要的划分尺度,教学被纳入计划与安排的轨道。路德的追随者斯图谟(John Sturm)根据6~15岁学生的能力,将他们分成不同班级,每班分小组,由班上年长的学生管理,使教育愈加规范化、系统化。[37]除此之外,法国、荷兰等国亦纷纷效仿,建立了学校组织与学校制度。如此,通过印刷的特有版式,教育愈发强调统一、标准与规范,理性的意识与观念不断渗透其中。
然而,在走向规范的同时,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踏入了形式的束缚与管控中。印刷出现之前,尽管没有读写教育的概念,但社会各处都是教育的场所,儿童处于松散、自由的学习状态,可从日常的生活、社会活动中习得知识、习惯。印刷出现后,教育这一活动逐渐集中于学校,产生了“狭义”上的概念,即仅指学校教育。“公立学校规范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集中选择与控制知识的大规模传播”[9]4-5,印刷的板式样貌以及印刷材料本身,正为这一观念及实践提供支撑。学校成为被监管和利用的场所,教育被看作国家统一的必由路径。16世纪中叶,公立学校系统在德国运作,1599年的《维腾堡法令》(WurttembergOrdinance)标志着现代学校组织的开始,儿童的全面管理成为大势所趋。[9]118(7)参见:菲利浦·阿里埃斯著,沈坚、朱晓罕译:《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216页。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人们也普遍认为,抵制异端的最好方式便是教育儿童,对俗世信徒的教育尤为紧迫。[38]“印刷的网络”(network of print)等同于监狱,它有力地控制着学校教育,正与我们欢呼雀跃的现代性并肩同行,“现代社会是通过空间来统治和管制的社会。”[39]只是,由于这张“网”已渗透到教育、社会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上,我们便难以自发地意识到。
(二)印刷本的空白区间
除却出版商的内文本外,印刷本自身也存在内文本。以下将印刷本的空白区间与内文本的部分要素结合起来,探讨印刷空间如何塑造教育现代性。
手稿或抄写稿通常不会有过多的空白区域,因为它们以记录或保存文本内容为主要目标。满满当当的文字填满了读者的心灵与大脑,读者无需做过多思考,只需将内容吸收与消化,他们是被动的接受者与学习者。印刷本则因刊印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留有空白区间。
就印刷本的边白而言,它既为作者提供注释的平台,也为读者提供记录感悟的空间。注释有个古老的名字“gloss”,它的使用可溯源至中世纪,文本被置于页面中间,小字母以各种方式围绕在其周围,加以解释,这种设计在15世纪的摇篮本中很常见;16世纪出现了边注(side notes)或旁注(marginal notes),它们较短,附在更具体的文本片段后面;18世纪,人们习惯把注释放在书页的底部。[36]320当越来越多的印刷书籍都出现注释时,注释便在整体上打破了文本的线性罗列方式,于文本之外创造了一种破碎感。在这种破碎感中,无论是作者或是译者——作者通过注释补充信息、译者通过注释阐明个人理解,都使文本边界得到延伸,展现了主体性。与此同时,注释集中在页面底端,印刷本的文本侧边呈规整的空白区块,读者在阅读时,便能随时在文本旁记录感悟、书写观点,或共鸣、或批判,“旁注可以是与作者的对话,也可以是与自己的对话。”[40]这一切都象征着平等的对话与互动。
就印刷本的留白而言,它是一种有意识操作,作者特意在书写过程中留出空白板块,为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在《项狄传》里,劳伦斯·斯特恩用精心设计的怪诞手法利用印刷空间,留下整页的空白以说明他不想写某一题材,而想让读者填补空白。[41]98这一做法在珍贵的手抄本中并不常见。因此,空白不代表“无”,它为“有”留出空间。当个人离开集体、喧嚣的环境,寻一僻静之处,揣摩印刷本的留白区块之时,自我的想象与思考便得以开启,如波兹曼所说,“独立的读者与他自己的眼睛……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印刷创造一种心理环境,个人主义成为正常的、可接受的心理条件……印刷给予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24]40-42
印刷本的空白区间,也在教育中孕育着主体性。读文本、接受教育时,有空白领域给予个人自由空间,那么,教育也并非将文字、图像塞入受教育者身心的简单过程,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在现代社会的萌芽阶段已难以行通了。教育当留有余地,不仅要尊重学生,聆听学生的想法,让他们与教育者、与知识形成平等的、有效的互动,更要发挥“引”(education来自educere,educere,意为“引出”)的功能,引导个体,为他们的独特思考提供平台,“空白行和印刷页面上的空白空间反映了思维和感觉主体之间的空间”[25]306。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刻着“认识你自己”(8)福柯认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中,“认识你自己”的箴言,总是与“关心你自己”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关心是人的需要。正是这一点,确保德菲尔神庙的箴言得以实行,显得实用。参见:MARTIN L H,et a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Tavistock,1988:16-49.的铭言,苏格拉底则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宣言,对自我的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正是关心自己、重视自己的体现。主体性的增长使个人将自身看作重要存在,进而认识自我;而对自我的认识,正是教育的要旨,是“成人”的关键。
与之相对,印刷的空间也带来了主体的封闭性与束缚性。印刷本构成特定的封闭场域,面对空白区间,个体的思考不断充盈,逐步占据全部的内心世界,受教育者停留在自我的想象与对话中,与外界社会隔离,造成精神世界的封闭。印刷限制了人们面对面的、真正的交流,它具有内向性、封闭性,而非外向性、开放性。《学会生存》指出,印刷出版给予人类新的巨大力量,但也产生不利影响,书本提供了制约个人的特殊工具,使人养成一种偏见,认为书面文字是一切称得上知识的知识的表示,比日常生活中学来的经验更优越。[42]这样的印记深入骨髓,即便离开印刷本,我们的思维和实践也仍然被“困”在印刷建构的知识网络中,始终以其为行动的“蓝本”。
五、结 语
文本、图像、空间,是印刷革命的“代言人”——印刷本的典型三要素,也是理解印刷革命塑造教育现代性的三维透视面。当我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触印刷,即手捧一份印刷本时,必然会进入到其已然形成的话语体系中,并将这种话语力量带到具体的实践中,进一步改造周围的社会与生活。印刷本不只是信息或内容的简单堆积,它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构建着特定类型的人与社会。印刷书籍将古代世界和中古世界熔为一炉——或者像有些人说的将二者混淆起来——并因此而创造出第三个世界,即现代世界。[7]218而教育,则尤其受到印刷革命的影响,因为印刷本是知识的载体,是教育的中介,更是教育学的场域。因此,印刷本在创造现代世界的同时,亦塑造了教育现代性,这一教育现代性,最终完成了首次全球化教育革命。
印刷本带来的理性与主体性,并非完全使教育向“好”或“善”生长,如伊芙·帕顿(Eve Patten)等人所言,“学者们只看到了印刷的激进色彩,却几乎没有意识到其保守作用”[29]8。在教育观念、思维逻辑、培养模式、学校制度等方面,印刷都催生了教育中的困境与矛盾,人也在此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消极品质,失去本真与自由。印刷是启蒙、是革命,亦是束缚与控制,理解这一点,便能对教育现代性有更透彻的认识。
概言之,印刷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它是一场“未被承认的革命”,值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追溯教育现代性源流,分析欧洲的印刷革命,乃至中国的印刷术,研究印刷本,或可帮助我们理解教育中的困境,从历史中寻找解释,进而有所启发、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