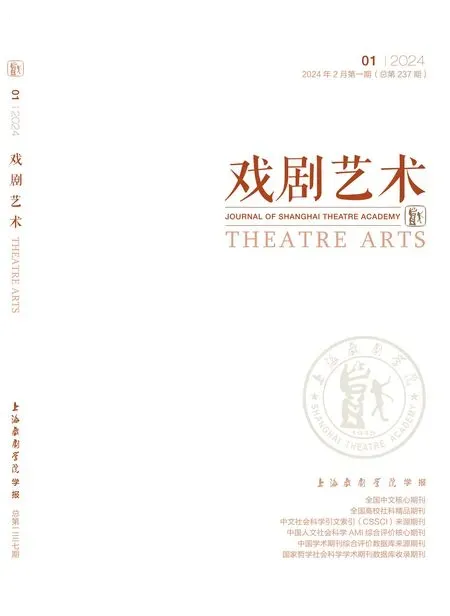歌舞伎剧场的近代转型及身份确认
方 军
作为东方传统演剧艺术之一的歌舞伎,自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形成以来,曾屡次遭受挑战并展开相应的变革。明治维新拉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帷幕,在此期间歌舞伎变革中出现了一个突出而鲜明的要素,即剧场。剧场同歌舞伎变革异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彰显出近现代歌舞伎剧场身份转型和确立的复杂性。
一、歌舞伎业者启动的歌舞伎剧场身份变革
郡司正胜认为:“纵观日本戏剧史,设备完善如同现代剧院的剧场的出现,终究始自歌舞伎。”(1)[日]郡司正胜:《歌舞伎入门》,李墨译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歌舞伎的剧场性,根本上源于其庶民化特征。歌舞伎之前产生的包括能乐在内的日本传统艺能,均从宗教祭祀仪式演化而来并长期保留着祭祀仪式的特质,因而受到特权阶层的保护,其表演空间主要在寺院和神社,在明治之前几乎没有出现大众化、商业性的剧场。歌舞伎的形成,则与此大相径庭。“歌舞伎是作为‘能’的逆反者而诞生的。在‘能’执着于王朝趣味,追求一种民众生活外的艺术境界,渐渐脱离庶民社会之际,一种舍弃先行‘艺能’的文学趣味以及象征主义,伴随着新民众的勃兴,发自于肉体的‘艺能’诞生了。”(2)[日]郡司正胜:《歌舞伎入门》,李墨译注,第37页。
河竹繁俊指出,在庆长中期,早期歌舞伎的表现形式即歌舞伎踊,也曾借用能乐舞台进行表演,但歌舞伎踊所借用的能乐舞台围起了一道“入口”,用于向进来的观众收取入场费。表演的目的不是为宗教设施募集善款,而是由表演者直接获取费用,这标志着“歌舞伎首先冲破了由特权阶级作后盾的原有的艺术生存模式,以民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演出”。(3)[日]郡司正胜:《歌舞伎入门》,李墨译注,第116页。这一特性,使歌舞伎必然越来越深地融入世俗空间中,并作为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演艺方式,形成自己独立的剧场形态。
江户时代的歌舞伎剧场以芝居小屋的形式存在,其空间规模事实上在当时已相当庞大,被称为“小屋”,本身便带有对歌舞伎贬低之意味。可见,“发自于肉体艺能”的歌舞伎,因所谓的“风化”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江户幕府政权的种种限制。对此,人们更多地关注幕府对于歌舞伎表演者的限制,然而幕府的限制性乃至歧视性政策,在歌舞伎剧场方面也有极为鲜明的映射。
幕府所承认的具有合法经营许可权的歌舞伎剧场,在江户(今东京)城内仅有三家,即被称为“江户三座”的中村座、市村座、守田座(原森田座)。至江户时代后期,剧场所处的区域位置突出地外化为歌舞伎身份的典型象征。1841年(天保十二年),根据幕府的指令,“江户三座”被强制性地从原址搬迁到江户城外偏僻的猿若町,并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形成了所谓的“剧场街”。剧场街的出现,并非为了刺激歌舞伎的繁荣发展,而是将歌舞伎演出场所同“游街”并置,从而对歌舞伎施行“风俗取缔”这一带有明显歧视的限制性举措。歌舞伎从江户城的中心被驱离,压缩于边缘地带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江户幕府统治终结。
1868年揭幕的明治时期,全面开启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对于歌舞伎而言,新的时代带来的冲击,首先是针对歌舞伎的诸多禁令的取消以及择地自由而打破的剧场区域上的限制,意味着歌舞伎获得了重返东京城内的可能。然而,此时的歌舞伎所面临的已不仅是单纯的“回迁”问题,更面对着一个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作为深深根植于大众趣味培育发展起来的民族演剧样式,歌舞伎显然能相当敏锐地感受到时代风气的异动。
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欧风尽染,在各领域几乎无所不涉的欧化风潮的猛烈冲击下,歌舞伎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场所搬迁和地理回归,未必能在已成为时代变革中心的东京站稳脚跟。歌舞伎业者中率先洞察到这一情势并作出实质性反应的,是“江户三座”之一守田座的“座元”——十二世守田勘弥。作为资深业者,守田勘弥一方面要雄心勃勃地将自己掌控的歌舞伎团体及剧场从猿若町带回东京城,实现歌舞伎的中心“复归”,另一方面又要以此为契机,使歌舞伎卷入欧化风潮中。以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歌舞伎以变革的姿态主动卷入欧化风潮无疑更有利于其“复归”,乃至实现更为宏大的抱负。为此,守田堪弥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通过建立新型的歌舞伎剧场来完成复归和变革两大历史性任务。
守田勘弥复归的据点,是位于东京京桥区的新富町,守田座也因进入新富町而更名为新富座,在此建造的歌舞伎剧场亦称为新富座。曾经被迫限制压缩于城市边缘的歌舞伎剧场,在欧化风潮中,不仅没有陷入更深的边缘化的境遇,反而奇迹般地实现“复归”,在东京中心区域建立了标志性的演剧场所,这确实得益于守田勘弥果断而高明的改革策略。
守田勘弥主导的歌舞伎剧场复归进程,是同直面欧化风潮紧密裹挟在一起的,新富座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守田勘弥在新富座的改革从三个方向上进行。首先,削弱幕府印记,特别是去除了被设置在剧场外观顶部的“橹”。橹,对于江户时代的歌舞伎剧场堪称灵魂,是歌舞伎剧场获得日本官方经营许可权的象征,这一标志物被去除,无疑宣示了歌舞伎剧场新的身份。其次,采用西洋新技术,将瓦斯照明装置引入新富座,从而使歌舞伎剧场有了全新的氛围,并开启了歌舞伎前所未有的夜场演出模式。守田勘弥剧场改革的第三个方向,则有告别芝居小屋的意味。新富座禁止观众进入后台演员休息及演出准备区域,而在传统的芝居小屋中,观众可以随意去探视自己喜爱的演员。(4)[日]永井聪子:《劇場の近代化》,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14年,第39页。守田堪弥制定这类制度,目的在于淡化芝居小屋的游乐性,把新型的歌舞伎剧场向严肃规范的艺术化演出场所推进。围绕这个目标,新富座及之后的新型歌舞伎剧场,首当其冲的变革对象便是“茶屋”体制。
茶屋,是传统芝居小屋附设的服务性设施。茶屋不仅为观剧者提供观剧期间的餐饮茶食、物品存寄等常规服务,甚至部分“粉丝”与歌舞伎艺人在演剧之余一起饮酒作乐等活动,也通过茶屋来安排。“吃东西是看剧时的乐趣之一,人们在茶屋点的吃食源源不断地送到观众席。经典的午餐是幕内便当,即戏剧幕间休息时吃的盒饭。”(5)[日]堀口茉纯:《日本歌舞伎》,杨晓钟、赵翻、赵楠婷译,杨晓钟校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茶屋是芝居小屋弥漫喧闹的市井氛围的重要来源,由于茶屋的存在,芝居小屋犹如一个供庶民娱乐、聚会、休闲的综合装置,游乐气质因茶屋而格外凸显,这同欧化风潮下的剧场范式格格不入,因此守田勘弥的新富座及后来的歌舞伎剧场都坚决地废除了芝居茶屋。茶屋在芝居小屋中还拥有一定的座位分配的权力,芝居小屋中被认为能完整欣赏到歌舞伎魅力的栈敷席,由茶屋掌控,茶屋根据客人的消费状况决定这些座位的去向。随着茶屋的废除,同茶屋消费捆绑的座席分配体制也必然瓦解,根据座位定价售票的票务体系逐渐在新型剧场中扎下根来。茶屋及其所关联的观剧方式的消失,意味着歌舞伎剧场迅速脱离了江户时代的芝居小屋,向现代剧场的身份进一步靠拢。
在新富座这座新歌舞伎剧场内,守田勘弥热衷于进行各种西洋化的尝试。1878年(明治十一年)举行的新富座新剧场落成典礼上,登台者们皆着西式燕尾服,邀请仪仗队现场演奏音乐,营造出浓厚的欧化气氛。守田堪弥还在新富座“推出了《漂流奇谈西洋剧》,剧中部分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并从一个西方剧团邀请了特约演员参加演出”。(6)[日]毛利三弥:《日本戏剧现代化早期的坎坷道路》,黄觉译,《戏剧》,2013年第3期。总之,新富座成为守田勘弥在欧化风潮下各类奇思异想的实验场,不仅是歌舞伎剧场本身,也包含了在其中进行的部分表演形式和表演内容。
守田勘弥在新富座推行的这类欧化新奇举措未免过于表象化,但也表明歌舞伎作为根植于民众趣味的大众演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时代风潮中转身的意愿和能力远比通常想象得更大。不过,守田勘弥本人后来也对猎奇式的西洋风逐渐失去了兴趣,毕竟这无法成为歌舞伎革新的持久推动力。相比之下,他对于新富座剧场所作的改革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守田勘弥以演出运营者对于演出设施的敏锐和执着,紧紧抓住了剧场这个演剧艺术中的枢纽环节,带领歌舞伎进入城市中心并开启歌舞伎剧场新的身份试验,推动了歌舞伎的时代转型,因此被认为是将日本演剧和剧场引向近代化的桥梁。然而,守田堪弥的举动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雄心和抱负。确切地说,他更是明治时期社会各个方面对于歌舞伎微妙态度的集中投射。这种投射率先在歌舞业者身上表现出来,但又远远不止于歌舞伎的圈子之内。
二、多方卷入的歌舞伎剧场身份塑造
欧化风潮极大地重塑了明治时期的戏剧观。在明治时期戏剧观的大变革大重塑中,剧场问题出人意料地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剧场俨然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象征和符号。
日本在欧化风潮下的剧场“觉醒”和剧场执着,首先源于对西洋的器物崇拜。在当时的东京,陆续出现了以鹿鸣馆为代表的一批模仿西洋样式的建筑。西式大剧场气派的构造、华丽的外观、复杂的工艺,都足以作为文明象征物,在欧化风潮下的日本引起器物层面的崇拜。大剧场在欧洲的不少地方居于城市中心位置,甚至成了地标性建筑,这也使西式大剧场得以冲击性地进入日本人的视野,以至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在日本建造西式大剧场的明确主张。
器物层面的向往和崇拜,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对西式剧场背后的活动方式进行探究。当时对于西式剧场及西方演剧有直观认识和体验的,并非歌舞伎界业内人士,而是圈外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有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的人,福地源一郎(福地樱痴)堪称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的明治政府使节团中担任翻译。该团在长达一年半的行程里,访问了欧美多个国家,以商谈修改西方列强对日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并考察欧美的治国经验。出访过程中,使团经常被所在国官方邀请去剧场观摩演出,使福地源一郎对剧场和演剧艺术产生了强烈兴趣,并积极投入到戏剧活动中。福地源一郎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对于西方演剧形态的理解,是紧密依托剧场这一载体以及其中承载的现场演出而直接获得的,而非仅仅通过文本的方式间接接受。他后来成为歌舞伎剧场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同这种接受方式可谓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意识到,剧场具有被塑造为城市新兴市民阶层社交场所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剧场甚至是国家形象的体现。为了实现这样的剧场愿景,不可避免地要对上演剧目进行改造。
早在1872年(明治五年),东京府便对三座的座元们下达命令,要求表演贵人、外国人,以及携家眷的观众看了不觉得难为情的高雅剧目,其内容应作为教化的一部分,并且要忠于史实。随后,明治政府将歌舞伎演员置于教部省的监督之下,演出脚本也要经过检查。艺能开始受新政府管制,同时这也证明其对社会的影响引起了政府的重视。(7)[日]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郭连友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275页。1878年(明治十一年),在明治政府高级官员松田道之的官邸内,政界人士和学者还曾就演剧改良问题,同歌舞伎业内人士进行了交流。
尽管歌舞伎有不少不符合文明开化的“猥亵野鄙”之处,以及以西方镜框式舞台的演剧标准衡量而表现出的“粗陋”,但明治时期的日本毕竟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了西方国家,因而对于传统民族演剧的态度,总体上并未趋于贬低和否定。日本社会主流一方面不希望歌舞伎被遗弃或走向边缘化,一方面又要求歌舞伎进行改良,以更加符合“标准”,因为“歌舞伎原本沾上了江户末年烟柳巷的臭气,就在为其‘除臭’的同时,西方戏剧被引入日本,以达到熏陶城市精英的目的”。(8)[荷]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8页。以文明教化的标准改造歌舞伎并将其装入西式剧场,展示日本新形象,这是当时从日本官方到学界乃至业界都在追求的目标。毕竟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的国力已今非昔比,因此既要显示自己已经位于文明开化之列,又要展现日本的独特性,成为日本社会近代以来一直抱有的心态。至于在展现日本新的文化形象方面,歌舞伎作为民族演剧形态确实有无可争议的独创性。不可忽略的是,与其他同样体现日本独创性的传统艺能相比,歌舞伎的特别之处在于,歌舞伎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已完全实现了剧场化生存和创造,这是其他传统艺能当时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优势。歌舞伎也因此远比日本其他传统艺能更具有市民性,如果把新型剧场作为日本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歌舞伎则最具备导入其间的可能性。
守田堪弥的剧场举措,某种意义上正是明治政府官方意志的传导。新富座当时还曾承担过日本国家层面的外事任务,接待过德国皇室成员等人,是日本首个向西方显要人士展示歌舞伎艺术的剧场,这正符合明治政府和上层知识分子对于歌舞伎的要求与期望。
各种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使歌舞伎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变革动力远远超越了歌舞伎业界。日本政界、学界主导的演剧改良运动致力于歌舞伎的雅化、高尚化,除了要求摒弃演剧中的“陋俗”之外,剧本和剧场成为演剧改良关注的两大核心要素。1886年(明治十九年)成立的以末松谦澄、依田学海、福地源一郎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演剧改良会,作为体现明治政府意志的御用机构,在《演剧改良会趣意书》中明确提出,“把剧本创作看作一项荣光的事业”,“建造构造完整的能供戏剧演出以及音乐会、歌唱会等等使用的剧场”。深受西方剧场文化熏陶的福地源一郎,甚至不再满足于只在理论上发声,而直接把歌舞伎改良的愿望付诸剧场实践,其成果便是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投入运营的由福地源一郎、千叶胜五郎共同建造的剧场——歌舞伎座。
对于福地源一郎来说,拥有自己所主导的剧场,才能更直接地把他在剧本方面的追求体现在歌舞伎上。即使在失去歌舞伎座的经营权之后,福地源一郎仍保持着“立作者”(驻院作者)的身份,以继续从事歌舞伎剧本创作。在歌舞伎座,“江户时代风格的演出法逐渐被改变,设备及其他方面也洋溢着仿佛是圈外知识分子创造的欧化气氛”。(9)[日]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郭连友译,第287页。不过,歌舞伎毕竟是典型的演员艺术,福地源一郎这样的圈外欧化日本知识分子在剧本上所达到的成就及发挥的影响力仍是相对有限的。相比之下,剧场作为他的变革支撑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歌舞伎座的出现标志着歌舞伎剧场的发起者从封闭的歌舞伎界内部脱离出来,打破了家族和业界限制,圈外力量逐步介入到歌舞伎演剧资源的配置中,歌舞伎也由此步入了社会化运营的轨道。
三、和洋之间的歌舞伎剧场身份选择
歌舞伎座是福地源一郎为实践演剧改良目标而建立的歌舞伎专用剧场,但它并不是演剧改良会理想中的西式大剧场。演剧改良会倾向的西式大剧场,是以巴黎大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作为范本的(10)[日]永井聪子:《劇場の近代化》,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14年,第54页。,并定位于综合性剧场而非专用于歌舞伎演出。歌舞伎座作为歌舞伎专用剧场的身份一度是尴尬的,它既不是欧洲歌剧院的照搬,又不得不朝着西式剧场的方向进一步靠拢。初建时的歌舞伎座,选择了完全西式的建筑外观。外观的西洋化固然相对容易,但作为歌舞伎专用剧场,其内部构造上的矛盾却是关键所在。
歌舞伎在江户时代高度的庶民化传统和娱乐性特征,使其对于满足世俗民间趣味向来乐此不疲,演出中不乏各种新奇,尤其是器物(舞台设施、布景、道具等)的各个方面充满奇思妙想。比如,“宝历八年(1758年),大阪的歌舞伎艺术家并木正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旋转舞台,就是将台板锯开,在台板下安装机关,使台板可以旋转的构造。每当剧情、场次变化,早已在背面布置好的道具、布景、演员就旋转过来”。(11)车文明:《中日传统剧场转台研究》,《文化遗产》,2012年第3期。转台(歌舞伎中称为“盆”)的运用,是歌舞伎演出重器物、重新奇、重刺激、重视觉效果、重观众反应的典型表现。类似于转台这样的大器物,即便置入逐步机械化的新型剧场也不显得违逆。
然而,歌舞伎演剧中并非所有的器物都天然地相容于西式剧场,最典型的莫过于花道。花道是从舞台延伸到观众席的演剧装置,从历史上看,花道的产生源于观众向俳优赠送“缠头”所用的通道,早期功能主要用于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后来逐渐被歌舞伎的表演所利用,成为“本舞台”之外又一个重要的表演空间。花道这样的演剧装置不仅从未在西方剧场内出现过,而且同镜框式舞台注重制造幻觉的演剧形态直接形成冲突,因此花道的存废问题便成为歌舞伎剧场“西式化”进程中的焦点。在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包括演剧改良会内部都不乏废除花道的声音,当然也有人针锋相对,包括对于西式剧场和演剧形态极为熟悉的福地源一郎,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保留日本演剧的独特性。作为歌舞伎剧场的持有者,福地源一郎的选择无疑至关重要,如果当时的歌舞伎座取消花道装置,很难想象会对后来歌舞伎的演出样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花道的存续,标志着歌舞伎专用剧场在内部构造上没有采用镜框式舞台的模式,歌舞伎专用剧场由此而保留了自己最根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使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在歌舞伎专用剧场中仍具有相当大的展开空间及独特的展开方式。极度不符合西式剧场规制的花道得以保留,反映了日本在经历了欧化风潮强势冲击后,整个社会“考虑到日本的历史、传统、习惯,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以扎实稳健的文明开化为目标修正发展轨道”。(12)[日]佐佐木克:《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孙晓宁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86页。尽管如此,歌舞伎座的内部空间还是向西式剧场的模式作出了调整,继废止芝居小屋中的茶屋体制之后,最典型的变化便是观众席的构造。在传统的芝居小屋,观众席并非一人一座的座椅席而采用枡席,即长条式的座席样式,每座可根据长短坐若干人。新富座曾在接待外国来宾时临时性地设置过座椅席,但平时仍为枡席结构。歌舞伎座最终确立了座椅席构制。设置座椅席,从根本上说是为观众观剧时的交流设置阻隔,使观众之间的交流被限制于一定的范围内。同时,座椅席事实上也“规定”了观众的观剧视角,而枡席在身体的规限上则要少得多。总而言之,日本歌舞伎专用剧场的西式化方向,是从守田勘弥便已开始追求的去游乐化,向严肃化、高雅化推进。一方面,在剧场内部减少了观众之间能够随意展开交流的媒介,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营造艺术殿堂的意味,去除之前的芝居小屋从“茶屋的运作”“观众席的设置”“演员和观众的交流”等各个方面所弥散的市井烟火气。初期的歌舞伎座完全采用西式的外观,这样的做法今天看来固然有失偏颇,但它的发起者们显然也是试图以这种欧风强化的方式营造歌舞伎剧场艺术殿堂之意味,这种殿堂图景不仅作用于演员等歌舞伎从业者,也作用于观众,从而在演剧改良中以各个维度把歌舞伎带向雅化、高尚化。
演剧改良会所主张的以巴黎大歌剧院等为摹本的大剧场,直至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才在东京真正建成,名为东京帝国剧场。这一年恰是明治时期的最后时光。东京帝国剧场是在强大的实业界、财经界背景的支撑下建造起来的,筹委会成员中便有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等产业界代表人物。这是一座从建筑外观到内部构造都完全西式的剧场,以西洋歌剧的演出为重点(为此东京帝国剧场成立了歌剧部),同时提供给各种门类的表演艺术开展演出活动,堪称日本最初的大型综合剧场。
东京帝国剧场从一开始就没有排斥歌舞伎的意图,而选择了“和洋折中”路线。把歌舞伎“装”进西式大剧场演出,仿佛是一场期待已久而终于实现的“预谋”。在完全西洋化的大歌剧院式的剧场内表演歌舞伎,营造了一种奇异的景象,犹如歌舞伎日后海外展示的“预演”,而其首要问题就是花道的设置。东京帝国剧场作为兼顾各类演出的综合剧场的做法是设置替代性的花道,且长度短于歌舞伎专用剧场中的标准花道。(13)[日]永井聪子:《劇場の近代化》,京都:思文閣出版,2014年,第58页。对于歌舞伎而言,东京帝国剧场具有双重意义。首先,这标志着日本歌舞伎在新的时期开始走出自己的专有剧场,这对于歌舞伎后来同其他类型演剧的合作交融及更大范围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它不得不作出艺术完整性上的部分让步。其次,歌舞伎进入日本建造的西洋歌剧院式的剧场内,也意味着歌舞伎已通过演剧改良获得了所谓的“日本国剧”地位,被认为足以展现日本的国家形象。东京帝国剧场在辉煌时期曾接待过世界诸多著名艺术家来日本演出,梅兰芳的首次(1919年)和第二次(1924年)访日公演,都是以东京帝国剧场为中心展开的,歌舞伎也参与了梅兰芳的访日共演。在东京帝国剧场这座日本当时最高端的剧场中,歌舞伎的国际化交流显然有了全新的土壤。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明治时期,新富座、歌舞伎座、东京帝国剧场是东京三座对歌舞伎演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剧场。除了早已不复存在的新富座之外,歌舞伎座和东京帝国剧场至今还在运营。东京帝国剧场因其主打的西洋歌剧运营失败而逐渐失去了综合性大剧场的辉煌,几经波折,目前主要用于东宝音乐剧的演出,已基本上同歌舞伎绝缘。拥有逾130年历史的歌舞伎座,则仍是日本的歌舞伎演出重镇之一,梅兰芳第三次访日公演(1956年)的主舞台也转到了歌舞伎座。歌舞伎座在建成后,又经历了数次改建与重建,其中的变迁颇值得回味。(参见表1)

时 间事 件1889年建成并开始运营1896年确立株式会社制度1911年实施第一次建筑改建1921年因火灾事故烧毁1924年重建工程完成,再度开业1945年在空袭中被炸毁1949年成立新的株式会社歌舞伎座,致力于歌舞伎座的战后复兴1950年完成战后重建工程并再次开张2002年登录为“有形文化财”2010年再次实施改建工程2013年完成改建工程后投入新的运营
明治时期最后一年(1911年),既是东京帝国剧场建成开业,也是歌舞伎座第一次“变身”之年。极具象征性的是,歌舞伎座的这次变身废除了剧场初建时的西式外观而改造为日本式的建筑风格。在后来的数次重建中,歌舞伎座均未重现西洋式的剧场外观。
结 语
明治时期是日本作为一个传统东方文明国家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歌舞伎这种从本民族民间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演剧艺术,既然不像能乐那样基本被放置于博物馆化的真空环境中,就必须直面时代提出的转型挑战。
日本明治时期演剧改良主张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西方现代演剧为主的原则和标准,推进歌舞伎的雅化,使其适应近现代城市生活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并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文化形象。其微妙之处在于它既要使歌舞伎向西方标准靠拢,又要展现日本独特性。在当时的日本,欧化风潮下对于西式器物的崇拜,使剧场问题亦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近现代的歌舞伎剧场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成为日本这一时期歌舞伎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和焦点所在。
近现代进程中的歌舞伎剧场的变迁,是日本政界、学界乃至产业界等方面的力量以空前的规模卷入,与歌舞伎业界复杂作用的结果。明治时期,歌舞伎分别出现了三类剧场,分别是以“新富座”为代表的歌舞伎业内改良派主导的剧场,以“歌舞伎座”为代表的日本新型欧化知识分子主导的剧场,以“东京帝国剧场”为代表的实业界主导的剧场(尽管不是歌舞伎专用剧场),其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在西式“标准”和日本独创性之间构建起平衡机制。
这一时期的歌舞伎剧场改革方向,总体而论是剧场的殿堂化、高雅化、严肃化,废除了茶屋这类凸显游娱氛围的附属性服务设施,使剧场变成更为纯粹的演剧容器。观众与演员的交流、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受到一定的约束,一系列新的剧场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使江户时代芝居小屋的氛围几乎完全被改变。
日本近代歌舞伎剧场的身份确立,在西式标准下遭遇过严峻挑战。花道作为歌舞伎艺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能否在新的歌舞伎专营剧场中得以留存,不仅是剧场问题,也是关系到歌舞伎演出艺术形态的问题。花道的留存,使歌舞伎专用剧场最终保留了自己的身份特征。
歌舞伎剧场变革的又一成果,是以东京帝国剧场为契机,走进了非歌舞伎专用的综合性剧场。歌舞伎在东京帝国剧场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可以想象,随着近代国家形态的形成,歌舞伎必然同诸多外来的演剧艺术发生交流与关联,同时歌舞伎也面临走向国际舞台的使命,因此歌舞伎在东京帝国剧场更像是为新的时期进行的“预演”。
歌舞伎剧场充当了日本近代剧场变革的先锋,其主动求变来源于深厚的社会基础、民众基础,以及强大的剧场化生存和创造力。近现代日本歌舞伎剧场在变革中也曾出现过舞台上的表演过度追求洋风洋味、剧场外观完全采用西式构造等极端化的做法,但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逐渐修正。以今天的歌舞伎座为例,剧场内设座椅席的同时,也设置了一部分传统的枡席,甚至江户时代作为剧场经营许可权的象征,后被守田堪弥视作旧时代标志而废除的“橹”,也作为一种装饰符号出现在当代的歌舞伎座的外观上,以恢复早期歌舞伎剧场的部分记忆。歌舞伎的饮食文化,通过剧场便当、剧场料理店等形式,亦成为歌舞伎专用剧场整体氛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历史的长期演变,日本歌舞伎剧场逐步从西洋化的思维方式中走出,完成了自身的近现代化之路,从而确立了现代社会中的歌舞伎剧场身份。深入认识这一进程,对于东方传统演剧艺术,仍是有重要意义的。
-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宋金杂剧历史分期新论
- 关于“戏剧情境”的现象学思考
- 人工智能识别中的人物性格分析
——以经典人物麦克白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