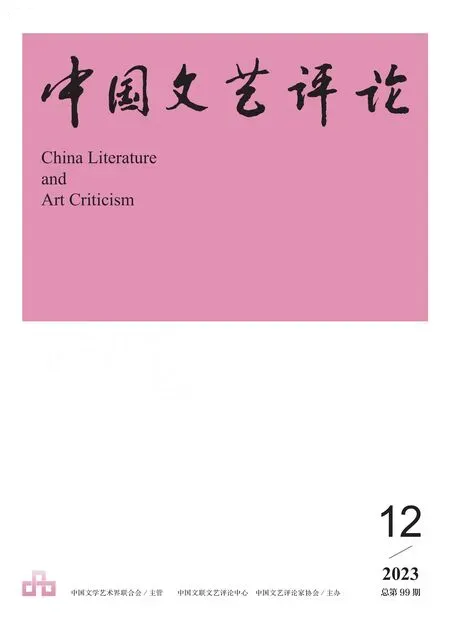伊明•艾合买提:致力汉维文学翻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采访人:白哈提古丽•尼扎克
伊明•艾合买提,1942年生,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洋大曼乡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书记、副主席,新疆艺术学院院长等。从事诗歌创作与翻译工作六十余载,译著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聊斋志异选译》《思宫街》《狼图腾》《与狼共舞》《丝绸之路》《杜甫诗歌》等。创作诗歌一千余首,出版诗集《幸福之歌》《花海》《被爱的年代》等。曾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文艺奖”。
一、从事翻译事业源于兴趣和责任感
白哈提古丽•尼扎克(以下简称“白”):老师,您好!很荣幸有这次宝贵的机会,跟您就汉维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众多翻译家的不懈努力,一大批以汉语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陆续被译介给维吾尔语读者。虽然从事汉维文学翻译的学者不在少数,但像您这样数年如一日潜心翻译的译者却不多见。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译者风格研究和翻译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这次访谈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汉维翻译领域的现状,而且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请简单谈谈您的教育经历,您是怎么与文学翻译结缘的呢?
伊明•艾合买提(以下简称“伊”):在当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文学翻译研究确实是一片“空白区”。在我心里,我的文学翻译启蒙跟我的童年教育密切相关。我出生在南疆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爱学习。1960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在喀什地区维吾尔中学读书。虽然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中学,但教学质量、管理水平都很高,师资力量也很强大,招生对象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等南疆地区的优秀学生。师资队伍也由1935年毕业于喀什师范学校、新疆学院、新疆师范学院的优秀人才组成,甚至还有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当过老师的资深教师。这些老师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他们的言传身教不仅为我打开了学习之门,还给我传授了不同的理论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接触到了还不错的图书资源,并趁课余时间阅读了很多书,其中包含大量翻译作品。从那时起,我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翻译产生了神奇的感觉。我的文学翻译生涯,是从1958年把毛主席诗词的乌兹别克文翻译成维吾尔文后正式开始的,当时我的翻译稿并没有公开发表,只能在班级、学校举行的一些大小活动上朗诵。随着接触的文学图书越多,我对文学翻译的兴趣也越发高涨。1960年我去了北京,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的两年预科学习,1961年也就是预科的第二年,我第一次试着翻译了刘坚的短篇小说集《草地晚餐》,有十多篇短篇小说。我把译稿寄给了《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编辑部。不久之后,我收到了《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编辑部的一封信。信里写道:“翻译得真不错,继续努力!”我的翻译处女作刊登于《新疆日报》1962年2月的某一期上,我还收到了八元稿费。今天,我收到这封回信已经61年了,信纸早已变黄,字迹也褪色了,但我始终珍藏着那封信。可以说,那封信给我的命运带来了一个转变,当时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从那时起,我备受鼓舞,接着翻译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等,其后该小说被编入语文教材。这是我即将进入高校求学的时刻。我原本希望读理科,并一直为此做了一些准备。虽然我喜欢文学,但我一直认为文学不是一种专业,只是业余爱好而已。结果,我在北京大学读理科的梦想没有实现,之后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跟汉族同学一起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在之后的文学翻译生涯中,首先是我对文学的热爱,其次是充实的大学生活和之前的预科学习经历,都对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您被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之前从事的工作与文学翻译并无关系,但是您从未放下或中断文学翻译,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伊:我诚恳地说,其中的原因在于我对自己的正确发现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从我的第一篇译作中我感受到了自我,并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此后我陆续有作品见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很多读者仅通过文本的语言技巧和节奏就能认出我的译作,这使我有足够的信心继续进行文学翻译。除此之外,我上大学之前,在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师们的悉心培养下,已经深深爱上了文学翻译,接着系统地学习了汉语。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能够翻译好,而且内心有一种希望、一种自信一直激励着我,除此之外,并无特殊原因。
白:您是土生土长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您能熟练运用汉维双语,又掌握了扎实的文学翻译知识,在汉维文学翻译领域,是一位具备深厚学术根基和较高翻译素养的学者。在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翻译的作品占多数,还是按照有关部门的部署来翻译的作品占多数?您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重视的事情呢?
伊: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这两种因素中,我按照有关部门的部署来做的翻译比较多。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来翻译的作品也有可能在刊物上发表、跟读者见面,但不一定会有积极的主题思想,那样的翻译我不做。因为文学翻译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第一位的。因此,我按照有关部门的部署来翻译的作品较多,其中有文学作品、各种政论和研究论文等。我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以下三点:其一,重视文学翻译对文化交融的作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论用哪种语言创作,都是在给读者讲述一个特定的故事,其中都暗含着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区的文化。文学作品的语言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所以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在理解好作品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切实地翻译出其中的文化韵味;其二,重视译作语言的通俗易懂性。我特别重视语言在交流中的中介作用,语言是文化交流交融的桥梁,译作的语言能够给读者留下第一印象。我一直认为翻译语言越通俗易懂,以简洁的方式呈现原作所具有的美感,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才会越好;其三,不能仓促地动笔。一般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条件允许,我会反复地翻阅整篇原作,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掌握作品的特色,查阅相关资料、包括作家的其他作品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前期工作非常关键。做好这些准备后,我仍然不会轻易动笔。许多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凭借自己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有价值的译作,让人越读越欣赏。他们游刃有余地运用不同的语言,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二、翻译唐诗是“我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白:谈到唐诗的翻译,您可谓成就卓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把唐诗翻译成维吾尔文呢?都说诗歌翻译很难,古诗更是如此。面对这个难题,您是以怎样的心态去迎接挑战的?
伊:唐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人们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唐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1982年中华书局再版《全唐诗》,共收录诗人3276家,作品53035首,基本反映了唐代诗歌的全貌。[1]参见张国祥编:《全注全评全唐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4页。唐诗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了解它们并发扬光大。翻译唐诗,是我生命中最好的礼物。至于我翻译唐诗的动力,首先是为了运用好自己所学的知识,让更多的维吾尔文读者接触唐诗。我在大学阶段学习了四年的古代汉语,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古诗,其中唐诗占多数,有一定的积累。我当时多接触唐诗也有原因:首先,唐代的文学遗产远远超过其他年代,这与唐代繁荣发展的经济、唐代执政者的政治思想模式和唐代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其次,我刚才也提到了唐代的诗歌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显著的地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唐诗更深层地展现出来,值得我们翻译、学习和深入研究。再次,古往今来,汉维翻译历史悠久,亚森•阿瓦孜、克里木•霍加等前辈早就认识到翻译唐诗的迫切性,在这个领域下了不少功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成果,但仍然有翻译的空间。我在这里插一句:古诗词的翻译并非每位译者想做就能做的,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辛劳,需要不断地研究、学习和深造。亚森•阿瓦孜花费了整整20年研究唐诗,再着手翻译,其他前辈也是如此。但是无论难度多高、代价多大,我们一定要做下去。
岁月不饶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精力也没那么充沛,做几个小时翻译就觉得很累,但我没有放弃,只要条件允许,我会坚持做下去。至于原因,一方面出于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期望,另一方面出于对我们前辈的尊重,也为了让新一代译者意识到此项工作的紧迫性。我最早从李白的诗歌开始翻译,大概是在2010年,我把李白的五六首诗歌翻译成维吾尔文,在《天山文艺》杂志上发表。后来,也或多或少地翻译了一些古诗,2020年翻译出版了《杜甫的诗》维吾尔文译本。我最近把自己翻译的唐宋诗词分别编订成十本书,交给了出版社,其中包括李白、李清照、苏轼等文学家的诗词,其中一些诗词被选入学校语文教材。
白:您对翻译唐诗有什么样的独特思想理念?
伊: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而且每个年代的文学也有所不同。唐诗有自身的特点,宋词与唐诗相比又有独特之处。因此,在翻译诗词之前,首先要了解诗人生活的年代背景,翻译诗词的每个词、每个句子时都要进入诗人生活的年代,全面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的事件等因素;其次要深入了解并探索诗词的创作起因,如诗人的经历、写作环境等因素对作品的影响;最后还要了解诗人或词人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技巧。因为诗词翻译不仅仅是字面的翻译,还是时代文化的翻译。我翻译诗词的时候,会努力把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时代的特点和本身的古典性翻译出来。因此,我使用的译文语言风格有独到之处。我翻译李白诗词时便尽职尽责地遵守以上规律。不少读者表示,阅读我翻译的李白诗词时完全不会感觉到自己阅读的是译文版本,好像站在李白的身边听着他的朗诵。根据读者的反馈,可以说,我的译文比较接近原文的风格特点。
白:您在翻译李白和杜甫诗词的过程中,使用了哪些翻译策略?
伊:虽然李白和杜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他们的诗歌创作风格有明显的不同,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所以在我看来,无论翻译李白、杜甫或其他人的诗词,都要了解他们的世界观,要进入他们生活的时代,要具备跟他们精神对话的能力,这样才能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文,才可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我对杜甫和李白诗词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其实翻译是没有捷径的,只有平时多看书、多积累,才能做到胸有成竹。维吾尔传统诗歌按照格律形式分为阿鲁孜格律诗和巴尔玛克格律诗两大类。我翻译李白的部分诗歌时运用阿鲁孜格律诗中的格则勒(“格则勒”是采用阿鲁孜格律的一种双行诗形式,以每两行为一联﹐每首三至十二联不等﹐多数为六至八联。首联两行同韵﹐以后隔行押韵、一韵到底,押韵形式为AA、BA、CA、DA……)、麦斯纳维(“麦斯纳维”是采用阿鲁孜格律的一种双行诗形式,以每两行为一联,每联同韵,押韵形式为AA、BB、CC、DD……)、穆勒伯 (“穆勒伯”是采用阿鲁孜格律的一种四行诗形式,押韵形式为AABA或ABCB)。比如,就拿王翰的《凉州词》来说: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第一、二、四句押韵,格律形式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即平声与仄声互相交替出现,形成了该诗的节奏和音乐感。而在阿鲁孜格律中,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化构成不同的调式、格式,以长、短音节的交错变换赋予诗句以音乐的美感,使之起伏变化、跌宕有致。可以大致认为,唐诗格律中的“平声”相当于阿鲁孜格律中的“短音节”,仄声则相当于“长音节”。我在翻译《凉州词》时,首先尊重原诗的押韵形式,采用了第一、二、四句押韵的穆勒伯形式;其次我采用的是阿鲁孜格律中的“-v--/-v--/-v--/-v-”调式(其中“-”代表短音节,“v”代表长音节),与原诗不同的是,根据维吾尔语和阿鲁孜格律的特点,我翻译的时候,把原诗的七字(七个音节)翻译成了十二个音节,尽量保留原诗的韵律和音乐感。
翻译其他诗词时,虽然我按照阿鲁孜格律诗来翻译,也体现出了阿鲁孜格律诗的拜合里的音律特点,但翻译的时候,绝不能局限于某种诗词形式。我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和诗词形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出原文的内容,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更流畅,为此我巧妙地运用了阿鲁孜格律诗的各种诗歌形式特点。翻译杜甫的一些诗歌时则摆脱了此种传统诗歌形式的固定模式,大量运用了另一种诗歌形式巴尔玛克格律诗的音律形式,这种诗歌形式的表达方式较为自由、趋于口语化,在格律方面的要求也较宽松,维吾尔民谣、口头文学中的诗歌绝大多数都采用巴尔玛克格律。如果翻译杜甫所有的诗歌都按照阿鲁孜格律形式的几个固定模式,将难以表达出原文的风格和诗人原有的情感,也很难达到原文拥有的艺术高度。因此,我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翻译形式。比如,我在翻译杜甫的《丽人行》时,运用了巴尔玛克格律,而巴尔玛克格律通过音节的交替变换赋予诗歌节奏感和音乐感。《丽人行》也是七言,我翻译时,把原诗的七字(七个音节)翻译成十三个音节,音节的组合形式为“4、4、5”,即每句由四个音节、四个音节、五个音节组合而成。这样的表达不受长、短音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发挥,把原诗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其实,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诗句表达方式比较自由,他们有时候会让形式服务于内容,相比之下是更看重内容的,此种特点在李白诗歌《战城南》和杜甫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都有体现。
三、反思不足有利于打造精品译作
白:上面我们谈论了唐诗的翻译过程,接下来,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翻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契机和过程吧。
伊:提到这部译作,我心里就充满遗憾。不过没关系,木已成舟,我就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吧。这本书我是被委托翻译的,在1982年末,新疆人民出版社组织一个工作组前往南疆开展工作,主要目的是发现有能力的翻译人员,给他们布置翻译任务,考验他们的实际能力。工作组在南疆各地组织现场会议,强调开展翻译工作的紧迫性。当时我刚好在阿克苏地区工作,虽然工作内容跟文学和文学翻译无关,但工作组的人都知道我是文学翻译的内行。会后,工作组组长将另一位译者艾沙•木沙和我叫到办公室,委托我们两个人合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并强调说时间紧迫,让我们尽快行动起来。于是我们俩把书分成两半开始工作,我负责前半部分,艾沙•木沙负责后半部分。现在回想起来,我很遗憾当时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更糟糕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每人手上只有一半文本,我们两个人又不在同一个单位,没法互换各自手中的文本,导致我们俩人都无法知道作品的完整内容。这部小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作为它的译者,没有把它翻译得尽善尽美,加上编辑方面的问题,最终仓促地出版发行,与维吾尔文读者见面。译作正式发售后,一些读者关于译本发表了评论文章,说译得不错,并指出了很多不足之处。文学领域的工作者应该多写类似的文章加以批评,这样才能让翻译者意识到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在翻译的过程中,我的致命弱点就是对作品的主题——中国农村实际状况的理解不够深刻。这部小说在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后引起文坛的关注,但是我们对这部作品知之甚少,也缺乏进一步的了解。这既是因为时间有限,也有我们个人的主观原因。由于这部作品是合译,我们缺少协商处理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机会,我和另一位译者没能形成统一的翻译观,在叙述风格、语言使用习惯上出现了差异。总之,及时翻译并出版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仓促和不完美的翻译工作,却是对原作者劳动的不尊重。这部译作在我的翻译生涯中也是个大遗憾。我把这些遗憾说出来,并不是就遗憾谈遗憾,而是说翻译工作应该有精益求精的追求,有对原作者和读者高度负责的意识,通过不断反思来提升自己的翻译水平。
白:您前面曾提到,文学翻译是一种需要很强责任感的工作。对于“责任”的理解,能否请您阐述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也许对尚处于探索中的年轻译者来说会有激励作用。
伊:文学翻译对了解该行业的人员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创造性活动,有责任感的译者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责任感与很多方面密切相关:其一,译者首先要对原作负责。原作是基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作可以或多或少地加以改动,不过要注意分寸。其二,译者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众所周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活动,凝结了译者的大量心血,所以要终生为它负责。少数民族出版业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一部作品被翻译出版后,若无特殊情况,即使另有译者进行更高质量的重译,新译本出版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虽然最近几年来,这种情况似乎有所变化,但还是少数。所以作品基本以初次译文的形式跟读者见面,如此一来,如果翻译出现严重问题,就会造成一场难以挽救的悲剧。当然,译者会遇到一些困难是很正常的,主要涉及主、客观因素,但无论如何,要尽量避免对翻译细节作出草率处理。如对某部作品的翻译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以放下,总会有人胜任。其三,译者要对原作者的劳动负责。文学创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作者长久的心血和汗水的精华。有许多作者为了写一篇作品,可以奉献一生收集资料、刻苦钻研。译者应该尽量避免盲目地改动原作的细节。其四,译者要对译作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负责,从而正确引导读者。国内外新出版的作品很多,不可能全部翻译出来。因此需要对作品精挑细选,选择那些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艺术性和思想性深刻的优秀作品去翻译。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很强的职业道德修养。
白:您认为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学翻译?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伊:文学翻译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确实不能低估。尤其是在维吾尔文学中,翻译文学所占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当然也包括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我们的不少作家通过译作学习了更先进的思想和更出色的创作风格。我从大学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文学翻译,在这个领域需要做的事情确实太多了。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地翻阅新的作品,但也无法掌握全部情况,只能在一些学术场合上了解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当然,虽然有高水准的译作陆续问世,但质量差的也不少。这和部分翻译者对翻译工作持有比较肤浅的看法有关。不少人都错误地认为精通两种语言就可以翻译文学作品,但事实绝不是这样。在实际工作中,翻译者不能忽视自己承担的责任。文学翻译比文学创作更难,正如郭沫若所言:“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还原作者的真实体验,时常要扮演双重角色甚至多重角色。每位译者首先要了解原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意图。现在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情况: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不到位,只以赚钱为目的,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会两种语言就能胜任的劳动,其实并不是,用语言来进行交流和从事翻译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以前上述情况很少见,我们前辈谦虚谨慎、勤奋刻苦、不断学习,为了翻译好一部作品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他们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现在的部分年轻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缺乏合作精神,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太愿意合力解决。文学翻译跟文学写作完全不一样,在文学写作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删掉自己不太熟悉的情节,但在文学翻译中,每一个小细节都必须处理到位。我们确实有非常经典的翻译巨作,直到现在,有责任感的译者都很尊重那些译作和翻译家,我在翻译实践中也会常常向那些翻译家、译作取经。当然,年轻的译者也一定要利用好现在的优势,现在学习的条件已经很好了,跟以前无法相比,只要有学习的意志,就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来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年轻译者要善于交流经验,不断提升自己,特别是提高专业素养。
借此访谈之机,我也回顾了自己的翻译生涯。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对话不要中断,因为你们的研究是对我们以及诸多前辈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的最好回馈。文学翻译实践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涉及文本理解、翻译方法、译者风格和文化语境等诸多视角,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出发,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选题。换言之,汉维翻译理论是一片亟待发掘的、广袤的处女地,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在访谈中提到的一些实践细节看似简单,或许对未来汉维翻译实践和理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中国文艺评论的其它文章
- 走向人文教育的美育
- 网络文艺高质量发展略论
- “空”(Leere)在中国美学 [1][2] 本文要归功于“波恩学派”如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和汉斯-格奥尔格•默勒(Hans-Georg Möller)的美学基本思想,也得益于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弗朗索瓦•程(Francois Cheng)和北京学者(宗白华、叶朗、王锦民)的相关著述。为保证思想的严谨以及能有一概览,本文没有对儒家、道家和佛教进行学术上繁琐的区分,特别是个别情况从美学意义上来看差异并不明显。(作者原注)
- 本雅明论中国艺术
——以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汉学为中心[1] 关于本雅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学术界已对本雅明《拱廊计划》的中国元素特别是中国器物进行了举证,发现其是超现实主义的碎片拼贴和辩证意象,实质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策略。参见曾军:《拱廊“星丛”中的中国》,朱立元主编:《美学与艺术评论》第13 辑,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61—371 页。本文则专论本雅明对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的取用态度。 - 中国书画理论在西方(1827–2022)
- 藏地复调的协奏、杂奏与变奏
——杨志军《雪山大地》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