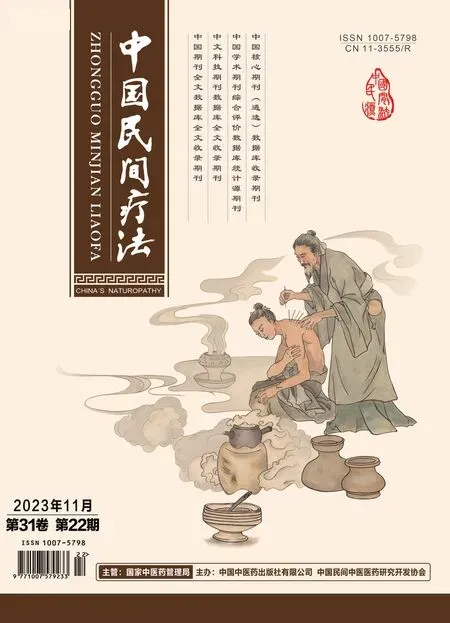针灸疗法治疗卒中后便秘的研究进展※
朱庭威,吴林纳,李桂平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卒中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及高经济负担的特征,对人们的健康生活构成严重威胁[1-2]。卒中,又称“中风”,中风后患者或因长期卧床,肠道气机升降失常,或因饮食结构改变,脾失健运,或因素体气虚,加上久卧进一步伤气,导致无力推动肠道蠕动而发便秘,研究显示,卒中后便秘发病率为30%~60%[3]。便秘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阻碍卒中的康复,还易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故合理诊治卒中后便秘尤为重要[4]。目前临床治疗本病多采用口服或外用药物,但药物不良反应较多,且疗效不稳定,易使患者产生依赖[5]。针灸具备操作简单、患者接受程度高、长期效果稳定的优势,近年来许多研究证实针灸治疗中风后便秘疗效较好。现将近年来针灸治疗卒中后便秘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 针刺疗法
1.1 毫针 毫针治疗疾病讲究“气至病所”,不同选穴、手法、角度和深度效果各不相同。针刺治疗卒中后便秘的取穴分为局部取穴和循经取穴,局部取穴以腹部诸穴为主,主要为天枢、中脘、气海等,循经取穴以胃经和任脉的选用频次较高;所有穴位中,应用频率最高的是天枢[6-8]。陆春花等[9]根据选穴不同将中风后便秘患者分为天枢组和支沟组,均采用芒针深刺手法,并另设口服乳果糖为对照组,治疗两周后天枢组临床疗效、症状积分和便秘患者临床评分量表(CCS)评分均优于支沟组和对照组,且治疗后天枢组血清P物质(SP)含量更高,血清血管活性肠肽(VIP)含量更低,说明深刺天枢治疗便秘效果更优。王志杰等[10]将采用奇穴结合辨证取穴治疗的中风后便秘患者37例设为观察组,奇穴取其门、其角、其正、通便等穴,对照组采用口服乳果糖治疗,治疗两周后观察组便秘评分和首次排便时间优于对照组,且治疗后4周随访发现奇穴组便秘评分仍低于对照组,说明奇穴疗法相对于口服乳果糖具有见效快、疗效好且持续时间长的优势。周鑫[11]认为不同行针手法治疗中风后便秘效应不同,中风患者多年老体虚,形不足应温之以气,烧山火手法长于补益,能激发气的温煦和推动作用,从而更好地改善便秘,治疗时先针刺气海和双侧天枢、足三里、支沟,并使其得气,观察组在气海、足三里两穴行烧山火手法,对照组则行平补平刺手法,两周后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6.70%,优于对照组的73.30%。袁海妮等[12]研究不同刺激量针刺天枢治疗中风后便秘的效应关系,针刺双侧天枢、足三里、上巨虚和支沟得气后,根据对天枢刺激量的不同将中风后便秘患者分为强刺激组和弱刺激组,药物组口服乳果糖治疗,两周后发现3组患者便秘症状均有改善,但相对于弱刺激组和药物组,强刺激组大便性状评分(BSFS)增幅更大,便秘患者生活质量评分(PAC-QOL)和便秘症状评分降幅更大,机制可能为强刺激天枢可对直肠产生更强的机械刺激,从而兴奋神经纤维并释放5-羟色胺等神经递质,进一步促进肠蠕动并增强排便反射。郭宝全[13]将运用眼针联合俞募穴法治疗的中风后便秘患者设为试验组,眼针取大肠穴、肺穴和下焦穴,体针取肺经、大肠经的俞穴和募穴,对照组行常规体针治疗,治疗两周后两组患者中医证候总评分、CCS评分和PAC-QOL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试验组降幅更大,说明眼针联合俞募穴疗法在改善便秘和提高卒中后生活质量方面优于常规针刺法。由此可见,毫针疗法治疗卒中后便秘疗效显著,合理的选穴、手法、刺激量能进一步提高疗效。
1.2 电针 苏美意等[14]将应用芒针深刺会阳、次髎二穴配合电针治疗的中风后排便困难患者设为电针组,对照组采用普通针刺治疗,治疗4周后发现电针组在周平均排便次数、大便性状、生活质量、排便困难度方面的改善力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机制可能为芒针深刺会阳、次髎可使针感传导至直肠,配合电针可以增强该区域血流运行,同时可以刺激骶神经和盆神经丛,激发骶髓排便中枢,从而改善便秘。邹康西等[15]将电针针刺肾俞和会阳治疗的中风后便秘患者37例设为电针组,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连续治疗30 d后发现两组患者症状均明显改善,在后续随访中发现电针组平均每日完全自主排便次数(CSBMs)高于对照组,排便困难程度低于对照组,说明电针疗法更持久稳定。龙茵等[16]观察电针天枢不同深度治疗中风后便秘的疗效,根据针刺深度分为3组,深刺组刺至突破腹膜,常规组刺至肌肉层、不突破腹膜层,浅刺组刺至皮下脂肪层,治疗4周后比较各组周平均CSBMs、CCS评分并随访3个月,发现深刺组的短、长期疗效均为最佳,其次为浅刺组,说明针刺疗效与痛觉相关,深刺突破腹膜和浅刺相较于常规针刺能产生更多的痛觉感,从而释放更多神经递质以促进排便。电针是传统针刺和电力学的结合,能对穴位产生更强、更持久的刺激,且“针刺剂量”易掌控,远期效应更好;毫针操作相对简单、灵活,患者耐受程度较高,在短期疗效方面与电针并无太大差距[17]。笔者认为,对于耐受程度较高的患者,或顽固性便秘患者,或便秘反复发作者,电针疗效更优。
1.3 火针 梁家彬[18]观察火针与毫针治疗中风后阳虚便秘的疗效,火针组穴位取“肠三针”,即上巨虚、关元、天枢,针具取0.40 mm×35 mm细火针,将针前1/3烧红后速刺相应穴位,不留针,隔日治疗1次,对照组行毫针治疗,穴位同火针组,治疗两周后发现火针组便秘症状和中医证候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且火针组缓解焦虑和提高卒中后生活质量程度优于对照组。中风患者发病后由于久卧伤气,多发虚证便秘,火针不仅能通过刺激相应穴位改善便秘,还可通过火针独特的热效应温通经脉,增强人体阳气,达到助阳补虚的效果,对中风后便秘证属阳虚的患者具有较好疗效[19]。
2 艾灸疗法
艾灸可通过热辐射和药化效应温通经络、温补阳气,中风后便秘患者多体虚,胃肠无力传导,艾灸可温经通络,促进胃肠部血液循环,增强肠蠕动功能,从而达到治疗便秘的效果[20]。艾灸治疗中风后便秘局部取穴多为腹部诸穴,以就近行温热刺激,远端取穴以足三里、上巨虚、支沟的应用频次较多[21-22]。欧小婷[23]观察“引气归元”温和灸结合针刺治疗中风后气虚便秘患者的疗效,观察组采用从上而下温和灸引气归元穴组(中脘、下脘、气海、关元)治疗,每穴灸10 min,总计40 min,同时行针刺治疗,穴位取天枢、上巨虚、支沟、照海,对照组单用针刺治疗,治疗两周后发现观察组在排便时间、排便速度、便意、粪便性状及气虚症状方面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说明“引气归元”灸法结合针刺疗效优于单用针刺疗法。冯泽慧[24]观察黄芪汤结合热敏灸治疗中风后气虚血瘀型便秘的疗效,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口服黄芪汤,药灸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热敏灸治疗,治疗14次后药灸组便秘评分量表(BM)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指数)优于对照组,且结束治疗两周后药灸组症状仍有好转,说明热敏灸结合黄芪汤治疗中风后便秘疗效确切,短期疗效和远期维持均有优势,原因可能是热敏灸疗法相对于传统灸法在施灸定位及时间定量方面更为精确,治疗时可做到“灸之要,气至而有效”。刘禹[25]探求灸法的量效关系,根据每次施灸量的不同将60例中风后便秘患者分为A组(每次1壮)、B组(每次两壮)、C组(每次3壮),穴位均取神阙,治疗20 d后发现C组便秘主症和兼症改善效果优于其他两组。刘禹[25]认为艾灸治疗存在1个阈值,超过该阈值疗效不会继续升高,甚至会抑制中枢神经兴奋,但此研究中灸量最大为每次3壮,且疗效优于其余两组,故并未确定是否达到该阈值。孙一鸣[26]基于肠道菌群探究针灸治疗中风后便秘的疗效,将80例卒中后功能性便秘患者分为两组,分别予针刺与艾灸治疗,3周后发现两组患者便秘症状均有改善,艾灸组在增加总产短链脂肪酸(SCFAs)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减少肠杆菌、肠球菌、梭菌方面优于针刺组,针刺组甲烷菌丰度降低,普雷沃氏菌丰度升高,说明针刺和艾灸虽然均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治疗便秘,但两者改善菌群的机制不完全相同,临床可结合应用。艾灸治疗卒中后便秘疗效显著,且可结合针刺治疗进一步提高疗效,但艾灸的量效关系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其他疗法
3.1 温针灸 魏一明[27]观察温针灸治疗中风后虚秘的疗效,治疗组在基础治疗后取肠三针(天枢、关元、上巨虚)温针灸治疗,对照组在基础治疗后采用常规体针治疗,14 d后发现两组患者便秘症状均改善,但治疗组在便秘频率和兼症方面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且总有效率为93.33%,高于对照组的73.33%。武娇娜[28]将82例中风后气虚便秘患者分为两组,A组采用耳穴压豆联合温针灸治疗,B组仅采用耳穴压豆治疗,治疗两个疗程后A组总有效率为95.12%,高于B组的80.49%。中风恢复期患者多气血亏虚,温针灸可增加对胃肠道的理气通阳作用,相较于火针,其作用更温和持久,治疗中风后虚证便秘疗效显著[27-28]。
3.2 穴位埋线 穴位埋线疗法不仅具备针刺疗法的短期速效作用,还可利用药线起到长期埋针效应。杜嘉等[29]应用穴位埋线法治疗中风后便秘患者210例,根据针管内是否装入药线分为埋线组和假埋线组,穴位均取天枢、中脘、下脘、关元、气海、大横及大巨,两组患者操作方法一致,1次埋线持续两周,治疗4次后埋线组周平均自主排便次数(SBMs)增加,且排便困难症状大幅好转,PAC-QOL评分降低,Bristol粪便性状评分升高,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假埋线组,且研究过程中脱落患者数较少,说明穴位埋线疗法治疗卒中后便秘疗效突出,具备治疗间期长、患者依从性好的优势。郑昊等[30]将175例卒中后便秘患者分为埋线组、电针组和药物组,埋线组在大肠经俞募穴行埋线治疗(两周1次,治疗两次),电针组在相同穴位行电针治疗(每周5次,治疗20次),药物组口服枸橼酸莫沙必利片治疗(每日3次,餐前服用,服用4周),治疗4周并随访两周,发现埋线组治疗期有效率略高于其他两组,随访期有效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说明俞募埋线具有更好的持续效应,且操作间隔为两周时效率更高。
3.3 耳穴贴压 耳穴疗法可从总体上调节人的神经活动,通过脑-肠轴改善胃肠运动,且耳穴疗法作用部位在耳部,能结合其他疗法进一步提高对卒中后便秘的疗效[31]。惠志敏等[32]将80例中风后便秘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耳穴结合穴位按摩疗法治疗,耳穴取大肠、直肠、便秘点、脾、三焦、皮质下等,配合腹部穴位按摩治疗两周,对照组采用口服麻仁丸治疗8周,治疗结束后发现观察组排便时间和间隔更短,排便速度更快,总有效率更高。耳穴贴压是将王不留行籽贴于耳郭反应点并进行按压的疗法,由于耳郭神经丰富,故贴压不同的反应点可以通过神经反射调节全身脏腑的运动,配合穴位按摩可泻实补虚,缓解便秘症状[33]。惠志敏等[32]的研究中对照组治疗时间为8周,观察组治疗时间仅两周,说明耳穴贴压联合穴位按摩疗法相比于口服麻子仁丸治疗起效更快,疗效更优,改善中风后便秘患者临床症状更具优势。
3.4 穴位贴敷 宋佳[34]观察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卒中后便秘的疗效,治疗组采用穴位贴敷(实秘取大黄、枳实、厚朴等药,虚秘取黄芪、党参、白术等药,将以上药物研碎制成药饼贴敷于神阙及双侧天枢)治疗,对照组口服通便灵胶囊治疗,7 d后发现治疗组排便速度和首次排便时间均优于对照组,说明穴位贴敷能有效改善卒中后便秘。穴位贴敷作为中医外治法,是中药理论和针灸理论的结合疗法,可使药力直接透过皮肤进入人体,既能治疗便秘,又可减轻寒凉药物对胃肠道的负担,且用法灵活多变,不同证型的便秘患者可选用不同的药物[35]。
4 小结
针灸疗法改善卒中后便秘疗效确切。相较于药物治疗,针灸疗法起效更快,远期疗效更佳,无药物依赖性及不良反应,且针灸疗法对卒中后患者的神经、运动功能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是非药物治疗卒中后便秘的有效手段之一。诸多针刺疗法中,毫针较为灵活、作用范围较广,选穴、手法和刺激量尤为重要;电针、火针是在毫针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刺激法,合理应用疗效更优,但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针刺、艾灸及其他疗法之间并无冲突,临床上多种疗法结合应用能进一步提高疗效。此外,笔者发现针灸治疗卒中后便秘的临床研究疗效评价指标偏主观,缺乏生化、影像学指标等客观评价,后续期待开展真实医疗环境中的大样本、高质量、多中心的长期研究,并设立客观指标,如肠道菌群、胃肠运动功能等,或统一主观疗效评价标准,为卒中后便秘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