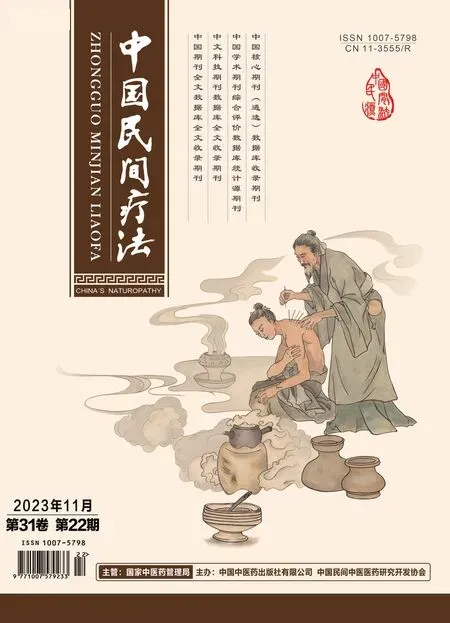急性心力衰竭的中医治疗概况※
邱逢意,许 飚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2.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江苏 南京 210006)
急性心力衰竭(acute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AHF)是由心脏泵血功能异常所致,以急性肺淤血、肺水肿及组织器官有效灌注不足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临床综合征。研究表明,AHF患者5年全因死亡率为55.4%,心力衰竭出院的患者人次数年均增速位于心血管病病种榜首[1-2]。现代医学治疗AHF以稳定血流动力学、缓解症状为目的,采用利尿、呼吸及循环支持等治疗方式,但存在药物毒副作用多、症状易反复等弊端[3]。AHF多属于张仲景提出的“心水”范畴。《金匮要略》言:“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燥,其人阴肿。”“短气,恶心不欲饮。”AHF发作时的症状与上述描述相似。该病还可归属“心痹”“心胀”“心咳”“喘证”“水肿”“心悸”等范畴[4]。近年来,中医药在认识及治疗AHF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本文就AHF中医研究概况进行阐述。
1 中医认识
中医认为,AHF起病,由禀赋薄弱、外邪六淫、内伤五劳等引起,或为本脏脏气虚弱,邪气入侵脏腑,也可因他脏久病,影响心的生理功能,最终致心体、心之气血阴阳受损。心气虚则津液难行,血不利则为水,痰饮、瘀血互生,进一步耗伤心阴、心阳。AHF多由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发作,张何璐等[5]认为该病病机可有二,一为久病伤及心、脾,正气抗邪无力,风、寒、湿邪迅速由肺及肾,肾阳亏虚,膀胱及三焦气化无权,水饮聚集,又凌心射肺;二为心气阴不足,痰、湿、血瘀或热毒侵袭,骤然痹阻心脉,导致心体失养,心气逆乱。陈伯钧教授认为岭南地区AHF患者病机主要为心阳不足、虚阳外越,脾虚湿瘀,肝郁气滞,辨治从心阴盛阳衰、脾易虚易滞、七情伤肝及心出发[6]。崔德成主任医师认为,“阳微”为心气、心阳虚衰,“阴弦”为痰浊、瘀血、水饮病理产物积聚,AHF的发病机制是阳微阴弦程度加深,三焦气化失职,水饮内停凌心[7]。AHF尚未有统一辨证分型,彭广操等[8]基于数据挖掘分析1 388例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患者的主要证型,发现阳虚水泛、气虚血瘀、心肾阳虚证较多。李彬等[9]将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期病机分为阳虚水泛、阳虚喘脱、痰浊壅肺。王铭等[10]将AHF的西医分型赋予中医内涵,以干湿对应肺气虚、水湿,以冷暖对应心肾气虚、阳虚,如心气虚为干暖型,心肾阳虚为干冷型,气不行津、水凌心肺为湿暖型,阳虚更重、水凌心肺为湿冷型。
2 治疗方法
2.1 内治法 AHF与气、血、水相关。心的生理功能正常运行基于心气充沛、心血运行畅达。肺为相傅之官,助心行血。肺主水功能正常,则津液布散有度,无碍血行。若气不行血,则血液运行缓慢,难以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故见四肢不温、少尿或无尿;若血留滞于肺脉为水、为痰,故见喘促、咳痰。总之,气虚、血瘀、水停是AHF主要病理环节。水停是AHF发作的最终及关键“标实”因素,缓急之治在于利水。以下从补气利水、活血利水两个方面总结AHF的内治思路。
(1)补气利水 ①温阳补气利水。《血证论》言:“水化于气,亦能病气。”“肾中阳气不能镇水,为饮为泻……此病气即病水矣。”气源于肾水,受心肾之火蒸化,若水不行,气亦病,故治气即治水。温阳补气法旨在补心、肾、脾之阳,可改善胸闷气喘、少尿肢冷症状。该法以真武汤为基础方,肾阳偏虚加肉桂、牛膝,心阳偏虚加桂枝、薤白,脾阳偏虚加干姜、丁香等,水饮重加猪苓、白术等药性平温之品。于江等[11]运用真武汤加味辅助西药治疗AHF伴利尿剂抵抗患者,有效率达93.33%,治疗后血浆N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尿量、低钾血症发生率均较治疗前改善,且改善程度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参附注射液由红参、黑附片提取而成,具有益气温阳的作用。张富汉等[12]研究发现参附注射液可增加心肾阳虚型AHF患者心排血指数,降低外周血管阻力指数及血清学指标。②养阴益气利水。心体为阴,心气为阳,若心体失养,则心气不充。《血证论》言:“真武汤尤以术苓利水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故并行而不悖也。”养阴亦可益气。养阴益气法旨在改善阴虚AHF患者的心功能,调节神经激素系统,减轻炎性反应,保护心肌。该法多以生脉散为基础方,偏气虚加黄芪、党参,偏气阴虚加红景天、酸枣仁、黄精等,水饮重加薏苡仁、白芍、白茅根等利水不伤阴之品。韩毅等[13]运用生脉散加减治疗AHF,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内皮素(ET)、醛固酮(ALD)、血浆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显著低于治疗前,且疗效优于贝那普利。王银燕等[14]运用益气复脉注射液(由人参、麦冬、五味子提取而成)治疗AHF气阴两虚证,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NT-proBNP水平、中医证候积分、24 h尿量均较治疗前改善。若AHF患者阳气暴脱,阴液不固,症见汗出、喘促加重、烦躁不安,甚则神昏,则运用破格救心汤温阳益气、回阳救逆,可加用麝香、苏合香醒神开窍,磁石、蛤蚧、补骨脂、胡桃肉等补肾纳气,当正气渐复,再予以治水,徐徐图之[15]。
(2)活血利水 《脉经》曰:“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血脉瘀阻则停而为痰,留而为饮,故治水需活血祛瘀。活血利水法以血府逐瘀汤为基础方,血瘀重加丹参、延胡索、五灵脂增强化瘀止痛之效;痰饮重加益母草、马鞭草、泽兰、鸡血藤等活血利水之品。陈武君等[16]在西医治疗基础上采用活血利水法治疗AHF患者,结果显示该法能降低患者NT-proBNP和血浆胃促生长素(Ghrelin)水平,改善心功能。曾健等[17]研究丹参酮ⅡA磺酸钠联合尼可地尔对老年AHF患者心室重构的影响,结果显示该法相较于尼可地尔更能提高临床总有效率,改善心功能指标及血流动力学指标。
2.2 外治法
(1)针刺法 《针灸大成》言:“胸满肢肿:内关、膈俞。”《灵枢·终始》曰:“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针刺内关可以宽胸利气、通畅气机,促进肺宣发肃降功能恢复[18]。郑婉等[19]采用西医常规疗法联合针刺双侧内关穴治疗左心室AHF患者,结果显示该法可改善患者不适症状和心功能,降低心肌损伤相关标志物、炎症细胞因子水平。腹部脏腑、经脉分布较多,腹针疗法以神阙调控系统理论为核心,通过刺激腹部穴位达到调整脏腑功能的作用[20]。钟国就等[21]采用薄氏腹针辅助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术后并发AHF患者,通过补肾元阳、温养心脉,达到改善心衰症状、降低NT-proBNP水平及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的作用。郭雪峰等[22]针刺足三里及丰隆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发现针刺能升高LVEF,降低NT-proBNP水平及明尼苏达心衰生活质量量表(MLHFQ)评分,且穴位刺激强度与疗效呈正比。
(2)穴位贴敷法 《医学源流论》言:“今所用之膏药……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里者,或驱风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膏药即指薄贴,穴位贴敷虽为外治,实则蕴含内外同治之理,用包含有辛香走窜和引经活络之效的药物外敷穴位,使药力直透皮下,刺激局部腧穴,直达病所;又可通过穴位激发经气,将药力贯通经穴所联系之脏腑,达到调节脏腑气血、阴阳的目的[23]。彭吉新等[24]研究加味苓桂术甘汤联合穴位贴敷治疗AHF的疗效,贴敷药物多为温阳、活血、利水之品如肉桂、吴茱萸、商陆、红花等,穴位取肾俞、神阙以壮阳,取内关、心俞以补心宁心,取膻中以降气平喘,取涌泉以开窍降逆,结果发现该法可改善患者中医证候评分、脑钠肽(BNP)水平。总之,穴位贴敷可改善AHF患者不适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适于长期应用,延缓病情进展。
(3)耳穴压豆法 耳穴是分布在耳部的腧穴,或称为反应点。当人体内脏受病时,耳部的一定部位可相应出现压痛、结节、变色等。根据全息理论,耳郭也为人体全身的一个缩影。耳穴压豆法通过在耳穴表面贴敷压丸刺激相应反应点,以防病、治病[25]。研究表明,采用耳穴压豆联合壮肾灵外敷治疗AHF,可缓解患者胸闷、纳差、心悸、水肿、食欲不振等症状,改善心功能[26-27]。
(4)灸法 灸法是通过对患者穴位皮肤的温热刺激,发挥温阳补虚、温经通络、活血化瘀、调理脏腑、平衡阴阳的作用。虚劳宜早灸,选穴少宜重灸,若扶阳可灸关元、命门温补脾肾[28]。《扁鹊心书》提出:“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雷火灸属火热灸,可通过热力将药力渗透入皮肤组织深部。郑晓峰等[29]发现参附注射液联合雷火灸(穴位取膻中、气海及双侧内关、足三里)可改善AHF患者血氧指标,降低1周内死亡率。灸法有补虚之效,可缓解AHF患者症状,但医者在施灸过程中要注意患者感受。
3 基础研究
AHF的基础研究主要以大鼠为研究对象,围绕中药提取物或复方相关的检测指标进行研究。杨征等[30]研究发现,瓜蒌皮提取物可增强AHF大鼠心肌收缩力,改善心室舒张,对心室率无明显影响。魏秋醉等[31]研究发现,血竭提取物可保护AHF大鼠肾功能,降低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及丙二醛含量,改善心肌缺血,降低氧化应激反应。李影雄等[32]研究发现,加味人参四逆汤可减轻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大鼠心肌组织的炎性浸润和纤维化,减少血清中各种炎症因子含量。陈海媚等[33]研究发现,不同剂量的炮天雄可以降低AHF模型大鼠血清中血管紧张素Ⅰ、ALD、内皮素-1、心房利钠肽、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陆爱民等[34]研究发现,丹参多酚酸可以缓解AHF大鼠心肌损伤,提高心功能,还能抑制含Nod样受体家族含吡啶结构域蛋白3炎性小体激活,调控免疫炎性反应。可见,中药可以通过抗氧化应激、减少炎症介质、调节神经体液因子等机制发挥抗AHF的作用。
4 小结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AHF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在病机、辨证分型、治法方药、治疗机制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本文梳理中医药治疗AHF的概况,提出以下思考。①中药静脉注射液现较广泛用于临床,但许多研究使用中药静脉注射液时未明确证型,可能影响疗效判断,且关于中药注射液联用的研究较少。②治疗AHF,某些毒性大的药物如附子可能是疗效关键所在,未来应加强对有毒中药增效减毒的研究。③研究选取的样本量偏少,缺乏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用盲法的研究较少,未来仍需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④研究中药物应用时长、疗效评估时间不统一,评价标准中缺少对于生命体征的监测数据,各研究评价标准存在较大差异,一部分研究采用新型生物标志物评估疗效,但再入院率、随访生活质量及生存率等远期指标较少纳入。⑤中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低活性的特点,可以改善AHF患者电解质紊乱、利尿剂抵抗等问题,但相关机制研究不足。⑥AHF引起的缺血、缺氧可对全身多器官造成损伤,如胃肠道缺血或淤血引起消化吸收功能下降,临床研究时应予以重视。中医内治法、外治法均可以有效缓解AHF病情,临床中利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手段减少AHF发作,有更大研究前景和运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