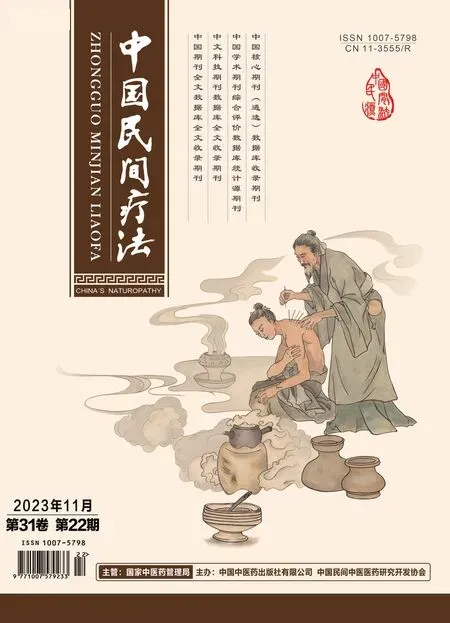孙志广运用石膏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经验撷要※
彭 雯,肖 雄,孙志广
(1.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 210017;2.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吐酸指胃中酸水上泛,又称为“泛酸”[1]。现代医学中胃食管反流病以酸反流为主要表现时可将该病归为吐酸的范畴加以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是消化内科常见病,但病情常反复,使病程迁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属难治之症[2]。
孙志广教授为第3批江苏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系统疾病30余载。笔者有幸师从孙志广教授,发现其善于治疗以吐酸为主要表现的胃食管反流病,其中石膏的应用得心应手,现将其应用石膏治疗吐酸的经验总结如下。
1 吐酸多热证,石膏除热佳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孙志广教授认为该条文基本概括了吐酸的发病机制即胃热气逆,并总结为两点:一为肝胃郁热、脾胃湿热,表现为胃灼热、反酸、口苦等症状;二为胃气上逆,表现为嗳气、呕吐、咽部不适等症状[3]。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云:“若久喜酸而不已,则不宜温之,宜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结散热去则气和也。”认为久病吐酸多为热证,宜用寒凉药散热结。因此,孙志广教授认为治疗本病当以清热降逆为大法,胃热一祛,冲逆之气可去大半,呕吐、吞酸之症可解。孙志广教授受玉女煎与清胃散加味方的启发,以及素有“张石膏”之称的张锡纯学术思想的影响,将石膏作为治疗本病的要药。玉女煎出自明·张景岳《景岳全书》“新方八阵”,由生石膏、熟地黄、麦冬、牛膝、知母组成,治疗肾水亏虚、胃火亢盛之少阴不足、阳明有余证,症状为“烦热干渴、头痛、牙疼、失血等”。该方以石膏为君药,取其清阳明有余之火而不损阴,清热生津的功效治疗胃热津伤。孙志广教授从玉女煎组方要义中汲取经验,认为胃火上逆导致胃灼热、口苦、反酸诸症,无论治本,或是治标,清热均是主要环节,并认为君药石膏在方中具有主要作用。因此,在治疗以胃热气逆为主要病机的胃食管反流病酸反流时,孙志广教授选用石膏为君药,取其入阳明经,清胃热,兼以生津之效,同时配伍川牛膝引热下行,并常将玉女煎中的熟地黄改为生地黄,增加清热凉血作用[4]。《医方集解》记载有医家将出自《脾胃论》的清胃散加石膏,并与生地黄、黄连等配伍治疗胃火上攻之牙龈肿痛,使原方清解胃热之力更强。孙志广教授认为,胃火牙痛、胃火吐酸皆因胃火上攻而致,因此治疗吐酸时也当仿清胃散之清热降逆之法,加石膏,使胃热降,火自去。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列举的135则病案中,有46则用了石膏,石膏也列于药物详述部分之首。张锡纯不仅用石膏治疗脉象“洪滑而实”的外感实热证,还用其治疗内外妇儿杂病,如瘟疹、腹痛、小儿发热、关节肿痛、手足拘挛、产后出血不止、眼病、牙痛等,认为“其性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即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孙志广教授认为张锡纯打开了应用石膏治疗内伤杂病的大门,带来诸多石膏应用的启发,结合消化科门诊患者较多为胃食管反流病,即属吐酸胃热气逆证,石膏这味“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尽可应用。
综上,孙志广教授认为胃食管反流病酸反流多由胃火上逆而致,石膏乃清胃热之圣药,多方将其列为降逆胃火之君药,该药用治胃火上逆之吐酸,当能堪任。
2 细论石膏在吐酸(胃食管反流病)中的应用
2.1 石膏非大寒,微寒正入胃 古人多言石膏为辛寒之品,虽归胃经,但用于辨病为吐酸的胃食管反流病时是否过于寒凉?石膏大寒之说并非一日而成,历代医家早有此观点。《名医别录》言:“石膏,味甘,大寒,无毒。”《开宝本草》谓:“(石膏)味辛、甘,大寒,无毒。”明·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认为石膏:“大寒而兼辛甘则能除大热。”诸医家多畏石膏寒凉,使寒从中遏,损伤脾胃,在临床应用时常有顾虑,如李杲《脾胃论》言:“如食少者,不可用石膏。”认为食欲减退之脾胃虚弱之人正气已虚,不可应用石膏。汪昂《本草备要》言石膏:“足阳明胃经大寒之药……然能寒胃,胃弱血虚及病邪未入阳明者禁用。”认为体质虚弱和血虚之人或热不盛,未入阳明,不可应用石膏。《医学启源》云:“(石膏)性寒味淡……乃阳明经大寒药,能伤胃气,令人不食,非腹有极热者,不宜轻用。”认为石膏大寒,可损伤胃气、败胃,所以非腹部有大热者,一般不要轻率选用。
然而,并非所有医家均认同石膏大寒的观点,如《神农本草经》记载石膏“味辛,微寒”。《伤寒论》第397条记载:“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此为伤寒解后尚有余热之证,即邪退正虚、脾胃虚弱之时,竹叶石膏汤重用石膏至1斤,可见石膏并非大寒。认为石膏微寒的后世医家也较多。如《本草纲目》认为:“石膏,气味辛,微寒,无毒。”叶天士《本草经解》载:“石膏气微寒。”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谓石膏:“若确有外感实热,他凉药或在所忌,而独不忌石膏,以石膏之性非大寒,乃微寒也。”石膏归肺胃经,为清泄肺胃气分实热之要药。可见,石膏微寒也得到诸多医家的认可。
孙志广教授受张锡纯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崇石膏微寒之说。张锡纯应用石膏治疗内伤诸病,孙志广教授亦不拘石膏大寒之说,认为石膏是甘寒之品,而非苦寒之品,无苦寒药久用多用则败坏脾胃之虞。在热性方面,石膏善清内蕴之实热;在病位方面,石膏善清肺胃之热;在清热方式方面,石膏“透热外出”。正如张锡纯所言:“盖诸药之退热,以寒胜热也,而石膏之退热,逐热外出也。”石膏以甘寒之性入胃经,清胃火而不至伤正,生胃津而除烦渴,虽然胃食管反流病非外感实热,但辨证多属胃热,且有冲逆之象,石膏微寒,归胃经,可透热外出、降冲逆,对胃食管反流病之胃灼热、反酸、胃脘嘈杂、口干舌燥等症均有良效[5]。
2.2 用量适中,配伍得当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认为石膏为金石之品,量少则一小撮,难以收效,不同于前人用至七八钱,常用至一两,有时甚至七八两。孙志广教授应用石膏治疗以吐酸为主要表现的胃食管反流病时,常用剂量为20~30 g,认为石膏在此处并非清外感实热证,而是清在里之胃热之证,不必猛量,中量服用即可使药效留于中焦,发挥清胃热之效,且该病多缠绵,非一日可得之功,需长期慢服,不可期其一剂中的,用量过大,会使寒凉中遏。另外,矿石之剂难以消化,量多反有损伤脾胃之弊,但遇脾胃实热之证,放胆用之,常获疗效。
正如张锡纯常仿《伤寒论》白虎加参汤之意佐人参以扶正祛邪热,治疗热实而脉有虚象之人,孙志广教授治疗以吐酸为主要表现的胃食管反流病时,若合并脾胃气虚,也常佐党参(或生晒参)、炙黄芪等益气扶正,但炙黄芪用量常不过15 g,舌苔厚腻偏实邪者需慎用,或减少剂量,虑其补益助湿温、助热,不利于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对于确有虚寒并夹湿热者,如胃食管反流病合并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辨证为上热下寒者,还需配伍砂仁、干姜、肉豆蔻及桂枝、附子等温热之品,仿半夏泻心汤黄连配干姜之意,以鼓舞中气,温运脾胃[6-7]。如为脾肾阳虚之腹泻,并无热证,则应多加注意,石膏之寒常可使腹泻难愈,甚则加重,临床应避之。
2.3 知常达变,临症加减 运用石膏治疗胃食管反流病仍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临证时患者症见反酸、胃灼热、牙龈肿痛、舌红、苔黄、脉数等胃热之证,方可用之,尤其适用于口干、口渴之证。但切不可一见胃食管反流病,便用石膏,犯以偏概全之谬。
单一味石膏不能成方,应与他药配伍应用。孙志广教授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时强调辨证及配伍,常以玉女煎为基础,石膏配生地黄、知母、黄连等清解胃热,并以半夏厚朴汤之法半夏、厚朴、紫苏梗等以降胃冲逆之气,再辅以四君子汤之党参、茯苓、麸炒白术以固护脾胃之气。孙志广教授强调上下气机的联系,下焦通畅,则中焦冲逆之气可降,若患者大便秘结,常加蒲公英、槟榔、全瓜蒌等清热理气通便,以通下焦气机[5]。胃食管反流病属于功能性胃肠病范畴,常合并神经、内分泌异常,若肝气犯胃、肝胃郁热而致吐酸反流者,孙志广教授则在以上组方基础上加左金丸方(吴茱萸3 g,黄连片6 g)以泻火疏肝和胃;如兼有情志不畅者,则加木蝴蝶、郁金等疏肝[8];如月经不调、肝肾阴亏、潮热盗汗者,则加用二至丸(女贞子12 g,墨旱莲12 g)以补肾养肝;如睡眠欠佳者,则加酸枣仁、合欢皮以养血安神。
3 验案举隅
患者,男,58岁,2016年10月25日初诊。主诉:反酸伴咽部不适间作3年余。患者3年前开始出现反酸,伴咽部有异物感,胃灼热、嗳气时作,时有口干。外院行胸部CT、心电图等排除心肺疾病,喉镜排除耳鼻疾病,查胃镜示反流性食管炎A级,幽门螺杆菌(Hp)阴性。曾服用质子泵抑制剂雷贝拉唑症状稍有好转,但停药后症状立即反复。刻下症:反酸,胃灼热,咽部有异物感,口干,大便欠成形,日行1~2次,舌红,胖大有齿痕,苔黄,脉弦滑。西医诊断: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诊断:吐酸,脾虚湿热证。治以健脾清热降逆法,方选半夏厚朴汤合四君子汤加减。方药组成:生石膏30 g(先煎),法半夏10 g,干姜6 g,紫苏梗15 g,枳壳10 g,川厚朴10 g,生地黄12 g,砂仁6 g(后下),党参片12 g,炒白芍12 g,麸炒白术12 g,茯苓15 g,仙鹤草30 g,粉葛根15 g,黄连片6 g,泽漆6 g。14剂,每日1剂,早晚温服。嘱患者忌茶水、咖啡、辛辣之品,睡前2 h 禁食禁水。2016年11月10日二诊:患者反酸及咽部不适明显减轻,无胃灼热,嗳气减轻,大便较前成形,日行1次,舌红胖大,苔薄黄,脉弦滑。处方如下:生石膏30 g(先煎),法半夏6 g,紫苏梗10 g,枳壳10 g,川朴花6 g,生地黄12 g,砂仁3 g(后下),太子参12 g,麸炒白术15 g,炒白芍15 g,茯苓15 g,仙鹤草30 g,粉葛根15 g。14剂,煎服法同前。2016年11月30日三诊:患者症状减轻,偶有反酸,无咽部不适及嗳气,食纳可,二便调,舌红已减,胖大,苔薄黄,脉弦。效不更方,予前方再服14剂,煎服法同前。患者症状几无,停药后半年复查胃镜,胃食管反流病已愈。
按语:该患者为有内镜下表现的典型胃食管反流病,辨证属脾虚湿热。初诊属本虚标实,急则治其标,治以清热、降逆、利湿为主。方中石膏、黄连、生地黄清热化湿兼凉血,党参、麸炒白术、炒白芍、茯苓、仙鹤草健脾补虚,法半夏、紫苏梗、枳壳、川厚朴、砂仁化湿降逆,泽漆清热解毒,葛根升阳止泻,干姜反佐以防诸药过于寒凉。二诊时患者胃热气逆诸症均减,故减半夏、砂仁、紫苏梗用量,改川厚朴为川朴花,去泽漆、黄连、干姜,但石膏之量不减,加大补脾益气之药,改党参为太子参,炒白芍、麸炒白术加量。三诊时患者偶有反酸,继服前方,巩固疗效。
4 小结
孙志广教授认为,吐酸的发病机制为胃热气逆,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以吐酸为主要表现时可纳入“吐酸”范畴进行治疗。孙志广教授受玉女煎、清胃散加味方和张锡纯临床应用石膏经验的启发,认为石膏直入胃经,清降胃之逆火,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恰到好处。对于石膏性“大寒”还是“微寒”之辨,自古就有。张锡纯应用石膏治疗内伤诸病,故孙志广教授认为石膏微寒,而非大寒,属甘寒之品,而非苦寒之品,可生胃津而除烦渴。因此,临床治疗以吐酸为主要表现的胃食管反流病时多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玉女煎、半夏厚朴汤为基础方,以石膏为君药,常用剂量为20~30 g,根据兼症,临床加减应用,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