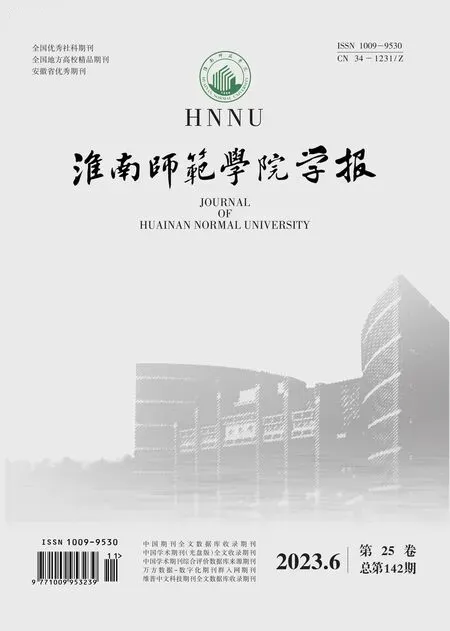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呈现
——以潘玉良绘画为中心的考察
范本勤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现代人文语境下的女性意识,包含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前者是女性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学层面的自我认知和体验;后者是女性在性别意识的前提下,作为主体,以自主的途径和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满足自己需求的意识。女性意识既是对男性权力和男性经验的积极否定,也是对自身价值的觉醒、体悟,甚至自我批判。
贾方舟将中国现代女性艺术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女性意识的萌动、女性经验的展开、女性主义的崛起,并认为,“女性意识的萌动就是从潘玉良开始”,“潘玉良的意义在于她是一个较早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艺术家,……从女性艺术这个角度看,潘玉良这个角色很符合中国女性发展的最初阶段。”[1](P12)所谓女性艺术,并不泛指“女性的艺术”,而是出自女性的视角,以女性的身体感觉、体验,呈现出的文字画面,这是女性艺术的前提。潘玉良在20世纪早期的“洋画运动”中成长起来,与当时活跃在画坛的女性画家(如方君璧、关紫兰、丘堤等人)类似,从写实性的绘画基础起步,尝试探索各种现代性画风,形成相对稳定的绘画风格。从绘画本体的造型技巧看,潘玉良并不能独占鳌头,但是,潘玉良有着其他女画家所没有的曲折传奇的人生经历,而她的绘画又与自身经历息息相关,时时透射出对自己性别身份和人生际遇的思考,彰显了其性别意识的觉醒,这是活跃在民国画坛的其他女性画家难以媲美的。也因此,潘玉良的绘画,在溯源中国美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男性图式体系的解构、女性主义的萌发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
一、镜中人:自我审视与自我认同
肖像画的功能在19世纪中期以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照相,所以肖像作品大多是由赞助人及其家族私藏的,一些画家也创作自画像,但也基本限于自藏。19世纪下半叶以来,包括自画像在内的肖像画逐渐成为公开的展品和流通的商品,在这种情形下,画家的自画像就不再只是“自我欣赏”的私密性作品了,而是兼有了与观众对话的中介功能,这样,画家在创作自画像时,必然就要考虑向观众展示什么样的自我形象。画家通过自我形象设计——包括姿态、角度、神情、服饰和道具,以及光线、背景、色彩、线条等等艺术要素——最后形成的,是带有各种象征性符号和意味的、重塑性的自我叙述,而这种自述,往往是(或期望是)直面观众的审读的。“我是谁”“我希望我是谁”“我期望你认为我是谁”——画家内心的自我形象、自我意识、自我身份的认知,都会通过自画像流露出来。换言之,自画像的这一特性使其成为研究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最好文本。
潘玉良(1895—1977)出生在扬州,本名张世秀①,未满周岁父亲去世,8岁母亡,由亲戚抚养,后流落到安徽芜湖,寄身妓院,以婢女或艺伎的身份活到18岁,直至遇见陈独秀和潘赞化,在陈独秀的撮合下,潘玉良嫁与潘赞化为妾,人生命运由此转变。 22岁时,跟随安徽籍画师洪野学西洋画,开启了艰辛而绚烂的艺术生涯。“虽然潘玉良的社会地位与个人身份随着其艺术道路的开阔而逐步提升,但是悲惨的出身、讳莫如深的经历与为妾的现实,还是成为了阻碍其得到更大发展空间、收获平等友善关系的根本性因由。”[2](P19)在遇见潘赞化之前,潘玉良的人生是卑微的,而在嫁与潘赞化后,虽然丈夫疼爱有加,物质上也有保障,但“妾”的身份仍是不愿与外人道的。这种“讳莫如深”的隐痛不仅伴随终生,且不时地被揭开伤疤,遭受冷眼甚至粗暴的对待。
潘赞化在1955年写给她的家信中所说:“你一生不解(讲)究装饰,更有男性作风。少年骑马射箭,都是好手。”[3](P23)与潘玉良交往过的友人们对潘玉良的性格特征也有一致的印象:“此人豁达大度,性格豪放,说话大嗓门,能喝酒,会划拳,爱唱京戏,女唱男,唱黑头,须生……她这个人在当时是属于思想解放的一类,爽朗的很。”[4]这种性格表现,既是天生所赋,也与其早年寄身青楼、见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关,更不容忽略的是,其间有自我保护、刻意男性化,以及积极跻身男权社会、获取身份认同的复杂心理因素。在人前的喧嚣,无法掩盖独处时的痛楚。时常面镜而观,自我审视“我是谁”,并通过自画像呈现出来,借此达成自我认同。在潘玉良的存世作品中,可以查阅到绘于不同时期的自画像至少有19幅,其中多数创作于异国他乡。容貌平平的潘玉良如此热衷于创作自画像,除了对自己容颜的自怜之外,上述心理诉求应是可以蠡测的重要诱因。

图1 《自画像 》潘玉良 1924年图2 《自画像 》潘玉良1940年
图1、图2两幅自画像分别作于1924年、1940年。潘玉良创作前者时,尚在法国跟随西蒙学画,绘画手法还较为稚嫩;而潘氏创作后者时,已是再次回到法国寓居的16年之后了,历经归国10年教学和创作生涯,艺术水准已有长足进步。共通之处是,两幅作品中,作者对自己的容貌都有一定程度的美化,尤其后者,刻意润饰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温暖柔和的光线下,浓妆艳抹,姿态优雅,娇艳盛开的瓶花更加衬托出人物的妩媚。

图3 潘玉良肖像 (摄于1920年)图4 《自画像 》潘玉良 1945年
潘玉良年轻时的照片(图3)中呈现的容貌,与影视作品中的演绎相差很远。旅美画家林蔼是潘玉良的挚友,她在回忆潘氏的容貌时说:“真正的潘玉良,外表是丑得不能再丑的女人,她的身材矮胖,她的脸庞既不白里泛红,也没有酒窝,而是黧黑,而五官的奇特,令人注目,她的声音,不是莺声呖呖,而是像虎啸猿啼,她那过厚的嘴唇,使人怀疑她的祖先好像来自非洲。”[5]林蔼的说辞并不是为了揶揄潘玉良,也不是完全客观的描述,其真正用意是提醒世人,勿以为潘的人生成就是靠美貌带来的。不过,林蔼的言语可以侧证,潘玉良的容貌即使不很丑陋,也与“漂亮”无缘。
这两件跨越16年的自画像表明,潘氏在此期间是欲以世俗美感示人的,这种心态与传统社会中的普通女子并无二致。然而,在此后若干年的几幅自画像表明,潘玉良的内心世界有很大转变,不仅在形象上从附庸男性审美观转变为真实地展示自我,而且在精神上有刻意呈现坚毅冷峻、孤独沉思的自我状态之趋势,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逐渐明晰起来。图4、图5两幅自画像作于1945年,画面构思异曲同工。人物立于窗前的自然逆光下,身体的姿态已无柔弱温婉之感,上肢与手的动势甚至有些男性化倾向,衣着朴素,肤色沉着,容貌平庸,自我美化的匠心已了无痕迹。与1940年所创作的自画像相比,瓶花、半身人像的素材组合几近一致,但画面所呈现的视觉感受判若云泥,作品已从“被观赏”(尤其是男性的观赏)的预设情境转向女性“自我诉说”的精神图式。图6是两年后(1947年)的自画像,取胸廓以上形象,躯体、动态等反映性别的特征似乎已无关紧要,去除了瓶花,背景做平面化处理,用特写的方式,对人物的面部作重点刻画。怪异的发型、宽广的额头、深陷的皱眉纹、折叠的下巴不仅真实反映了50岁出头的年龄,更着重刻画出了纷乱而凝重的情绪,尤其是直面观看者的眼神,带着凛冽的审视意味。如同赫伦·谢夫贝克、凯绥·柯勒惠支那样,用 “不美”的自我叙述,模糊了性别界限,突出了精神表达和思想张力。

图5 《自画像 》潘玉良 1945年 图6 《自画像 》潘玉良 1947年
造型果敢、用笔刚劲,潘玉良的绘画很早就呈现出男性绘画的气质,但她早年在创作自画像时,却小心的将自己包装起来,以温婉示人,这种矛盾体现了复杂的心态。一方面,生活的经历使其缺乏安全感,潜意识里处处模仿男性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另一方面,在描画自己的形象时,又把自己回置到男性观众的对面。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20世纪40年代以后,自画像中性别特征的逐渐弱化、精神面貌的着意表现,体现出潘玉良已形成不受观看者左右的主体意识。
二、女人体:叛逆与隐喻
纵观潘玉良的存世遗作,人体画占有最大篇幅。早在上海美专学习时期,潘玉良就已开始人体题材的绘画创作,虽然石楠在《潘玉良传》中关于潘氏以自己为人体模特创作油画并公开展出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撑,但刘海粟主持的美专西画教学中,注重人体模特写生的训练方法,初步培养了潘玉良对人体题材的兴趣,应是题中之义。尔后,潘氏又出洋学画,西方学院里的训练更是以人体写生为中心,长期严谨的训练使得潘氏具备了扎实的人体画写生、创作的能力。但是,这些并不是潘玉良终其一生坚守人体题材的充分理由。以人体为媒介,对自己的情思进行隐喻性表达、对男性权威进行无声的反抗,是在实践艺术技巧和表达审美观念之外,促使潘玉良专注于人体画的重要因素。
色粉画《顾影》是潘玉良早期人体画的代表作,在1929年全国美展中展出。画中描绘一女子正向而坐,手持镜而自顾,面部流露出的忧郁的神情。李寓一评曰:“女士此作,于愁苦怅惘、爱惜、郁闷等,似与惆怅相近,而亦未曾明示于观众,盖亦人间之大迷也。女士心性耿直,胸无点尘,……无一幅一笔一点之间,不为其忠诚心灵之表白。”[3](P102)显然,这是一件有隐喻意味的作品:其一,画中女子容貌普通、身材健硕、肤色沉着,与民国早期通俗绘画(如布景画、月份牌等)中体现出的流行审美观不同,而与潘氏自己,倒是十分相像;其二,顾影自怜,面露怅惘之色,与其说是精心设计的艺术构思,倒不如说是潘玉良在那个时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潘氏1928年回国,随后即受聘于上海美专,担任西画系主任,开始了10年教学生涯。上海美专是潘玉良学画经历中的重要一站,但潘氏在美专学习期间遭遇的歧视,让她对美专有着复杂的情感,加之现实之中又受到丁远(美专总务长)等人的排挤,历史的隐痛和现实的艰难叠加在一起,使得潘玉良的内心压抑苦闷,这种情思在《顾影》中可见一斑。潘玉良在此次画展中的参展作品,除《顾影》外,还有《黑女》《歌罢》《酒徒》《灯下卧男》,共五件之多。积极地公开展示自己的作品、参与社会活动,是潘玉良一贯的作风。其在归国后精心策划了大型个展,引起了文化界不小的轰动。归国后,参加的画展不计其数,各大艺术社团、组织,也常见其身影。这些社会行为,一方面是出于对艺术的酷爱,如潘氏自己所说:“生性喜欢美术的我,对于音乐、雕刻、绘画都曾经做过相当的练习,但自绘画上的色彩把我引诱成了一种嗜好之后,音乐、雕刻在事实上就只得牺牲了。”[3](P94)另一方面是要雄心勃勃地在男性社会争取成功,以绘画的成就证明自己“不让须眉”,让人们淡忘自己的出身,最终获得平等的对待和公允的评价。理想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目的纠结在一起,不易分辨,但其中“平权”的女性意识之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潘玉良作为女性,其出身和作画题材,使得那些坚守旧(道德)观念、对潘氏颇有微词的人,自以为获得“呈堂证供”,更加肆无忌惮地予以攻讦。这种广受非议的情形应是潘氏可以预料的。然而,正是这些攻讦激发了她的叛逆心理,越是困难越要坚持,将人体画当作回击旧道德、彪炳新观念的宣言;同时,她在艺术理想上不愿妥协,在现实功利和艺术理想之间,宁可牺牲前者而成就后者。人体画题材的坚守,生动体现了潘玉良作为特定女性个体的反抗意识以及坚贞不屈的品格。
“潘玉良以女体做对象的作品,似乎都有一种‘自画像’的隐喻,潘玉良不一定是一个刻意表现潜意识隐喻的画家,但是,她的隐喻却耐人寻味。”[3](P114)如《顾影》中,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有观照自身的意味。若将潘玉良的人体绘画分为写生与创作两种类型,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创作型的人体画中,人物形象的营造,包括面部形体和妆容、人体的整体性特征,甚至肤色都有以自己为蓝本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其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彩墨画中愈发明显。如果说写生中的人物形象会较多受到客体(模特)的掣肘,对于潘玉良(所能驾驭的绘画技能)来说,主观化的改造存在一定困难,那么,在离开模特进行创作(或在写生的基础上再创作)的时候,潘玉良的造型是相对自由的。恰是这种自由状态下的造型,最真实地反映了潘氏的某种艺术观:追求真实之美、健康之美,强调了女性的身体自主意识,否定了男性对女性的“物化”。这其中,也暗含了对自身——一个有着类似形象的普通女子——的积极肯定。《着上衣的女人体》(1959年)、《海边浴女》(1959年)、《坐姿双人体》(1963年)、《戴帽女人体》(1963年)等,是这类绘画的代表性作品,从中不难发现,画中人物有着几乎千篇一律的饱满脸型和五官、细长眉线、偏暗的肤色、健硕的体型。
三、多彩情节:温暖的女性世界
在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在纯粹的用于训练绘画技能的写生以外,潘玉良通常都会在画面中精心营构情节,以实现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潘氏写实的、文学性的绘画,是古典艺术传统的延续,与她所处时代的“先锋”艺术理念有较大出入。对潘氏绘画的评价,新旧各派褒贬不一。蔡元培、徐悲鸿对其赞许有加,而有现代派色彩的“决澜社”先锋庞薰琹对其却不以为然:“一九三○年,……她在上海美专时教油画,在艺苑画模特儿,属于法国学院派的画法。她似乎没有想追求什么新的创作风格,她只是规规矩矩地画,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气。”[6]无论如何认定潘玉良的艺术才能,其文学性的绘画都是作为女性画家(用以重建现实的)较有价值的选择,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天探幽其心灵世界打开方便之门。如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当她们用自己的话语重建现实时,她们才能获得表达个人经验的权力。而女性艺术家一旦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自身、转向个人经验的呈述和心灵事件的表白,这些深潜的情感领域便成为建构女性话语的理想境地。”[7](P99)家庭、母爱、思乡、闲逸等都是潘玉良情节性绘画中常见的主题,围绕这些主题展开的具体情节,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
《我的家庭》创作于1931年,自传式的描写了家庭生活:潘玉良坐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一副知识青年的模样,对镜写生,在她身后站立的是潘赞化和儿子(正妻之子),他们专注地看她作画,看起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和谐美满。张道藩称赞道:“一张很有趣很难得的画……观众们能不羡慕潘女士家庭的快乐吗?整幅画的结构和色调的分配都很好。”[8]其实,将家庭以美满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是潘玉良美好心愿的倾诉方式而已。这一时期,虽然潘玉良的公开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但在家庭中,潘氏却尴尬地在教授与侍妾的身份之间不停转换,所受屈辱是一言难尽的。将潘的正妻排除在画外,体现了潘玉良对传统婚姻关系和道德观的反抗。新旧观念相互纠缠、身份错位而无力改变,是促成潘氏再度远赴欧洲的深层原因,只有“出埃及”才能摆脱现实痛苦、维护内心的尊严。“旧女性”向“新女性”的跨越,由一次出走标志性的完成了。
潘玉良一生未育,其原因扑朔迷离,但如普通女性一样,也是期盼母亲角色的。《我的家庭》是这一心迹的真情流露,而从潘玉良的书信以及潘赞化后人的回忆录中,也可以有力地证实这一点。在此后留法岁月的画作中,真实的家庭欢聚情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虚构的母子嬉戏、哺乳等情节,彩墨画《母与子》(年代不详)、油画《哺乳》(1961年)是其中最精彩的代表作。在《母与子》中,潘玉良描写的是母子嬉戏的情节,婴儿躺在小床上,似乎刚刚从美梦中醒来,欢快地呼唤母亲,母亲匐下身来将孩子搂入怀中,母子亲昵的情境被营造得真实而感人,而母子身形的夸张对比,又有强调安全感的用意;在《哺乳》中,一位身材丰腴的母亲躺在沙滩上,婴儿满足的吮吸着乳汁,母亲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远处背景是蓝色海洋,衬托出母爱之纯净、博大。虽然潘玉良的此类作品有很多未署日期,但从时间可考的作品中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创作的高峰期,此时的潘氏已是暮年,老而无子,无法释放、无处安放的母爱只能倾注于画中。与早年不同,暮年潘玉良营构的母爱情节更加富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树荫下,花丛中、碧海蓝天,母与子在自在的天地嬉戏,专注于自身处境的“小我”已经悄然让位于观照普遍母性的“大我”了。
对亲人和故土的眷恋,是离乡万里的潘玉良无法拂去的情绪。但潘氏在画作中宣泄思乡情绪的方式是委婉的,常常借助歌舞、游戏等母题,进行隐喻性的情节设计,以实现排解离愁、抒发心灵归宿的目的。《放风筝》(1956年)描写了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女孩孤身一人放飞风筝的情节。风筝常被用来象征情思羁绊,一线牵连、漂浮不定,随时有断线飞去的危险。而此作中的情节另有所指,风筝似乎暗喻潘氏本人,风筝的主人则象征着故土,无论漂泊多远多久,那根线永远牵在故国家园。《玩扑克的女人》(1957年)中的隐喻更值得思考:1956年,潘玉良因思念家人申请回国,但被拒国门之外;而在同年稍后,张仃、吴冠中邀请她回国任教,她却婉言谢绝了。可见,对于自己在异乡的去留,潘玉良内心充满矛盾。“她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于是创作了这幅作品,借用玩扑克的女人这一图像符号来传达她对未知的迷惘、对命运的叩问,也反映了面对世事无常,画家凄惶无助的心情。”[9]此类作品很多,所借助的情节(或符号)也是多样的,如《双人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劝酒》(年代不详)、《采茶女》(1953年)等等。
探询潘玉良内心的女性世界,其绘画中的各种休闲情节的描写是不可忽略的。春游、戏水、沐浴、露营、垂钓、玩牌、聊天等各种休闲活动充斥于潘玉良的作品中,就单个作品看来,这些情节往往没有特别的意涵,但总体观之,却是能清晰地展现潘氏的生活观和价值观的。19世纪中后期,印象派的崛起不仅改变了绘画的审美范式,也极大的改变了绘画的内容,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户外休闲生活,成为印象派画家们热衷的绘画情节。这种转变的缘由,是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传统生活形态,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工作时间以外的多彩的闲暇生活,成了人们的精神居所。与同样长期寓居海外的其他画家(如常玉、唐蕴玉、赵无极)相比,潘玉良在作品中对现代性的闲暇生活投入了更多的笔墨,究其原因,除了潘氏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受现代生活文化的浸染,从而心向往之以外,其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也是不可忽略的。潘玉良自幼被拐来卖去,两次改姓,在婚姻中也是低人一等的侍妾身份,早年被命运摆布的生活,使得潘玉良对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有着刻骨铭心的向往和珍视。晚年,思乡心切的潘玉良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回国,正是这一心迹使然,就如张仃回忆,“我问潘玉良是不是也想回来,她很爽快,说:‘说实在的,国内生活我恐怕过不惯。’这可能是她没有回来的主要原因。”[4]轻松浪漫的休闲生活情节被反复吟咏,体现了潘玉良对生活的热爱,更是其自由和独立精神的映射。
四、结 语
通过对潘玉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绘画情节的简要梳理和剖析,可以发现性别认知、生命体验、权利觉醒、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多种维度的女性意识,被有意或无意、或明或暗地嵌入其中。这些女性意识是混沌初开的,并没有发展为激烈的女性主义,更不类同于当代的女权主义。但是,与苏珊娜·瓦拉东、赫伦·谢夫贝克、凯绥·珂勒惠支、弗里达·卡罗这些活跃在20世纪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女性画家一样,“她们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就在于她们意识到有她们自己的视角,有她们自己的经验领域和判断标准,有她们自己特别关注和感兴趣的事物。而且她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经验方式与思维方式也与男性不尽相同。”[10]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潘玉良以自己的方式,描画了自己,也描画了那个时代。
注 释:
①关于潘玉良的本名及出身,尚无孩童时期的原始证据可考。《上海美术志》记录其本名为陈世清,生于扬州。桐城潘家楼《木山潘氏宗谱世壁卷》记载潘玉良原姓陈,本名为世秀,字玉良。潘玉良在上海美专学籍档案中的名字为潘世秀,而在与潘玉良往来的书信中,友人们都称呼其为“潘张玉良夫人(女士)”。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潘玉良本姓张,在父亡后随母改姓陈,嫁与潘赞化后随夫姓潘,世秀是曾用名。此外,关于潘玉良在芜湖妓院中的身份问题,王玉立、董松、曹子达等研究者通过考证,均认为,其身份应为婢女或陪唱歌女,而非妓女。
——潘玉良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