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是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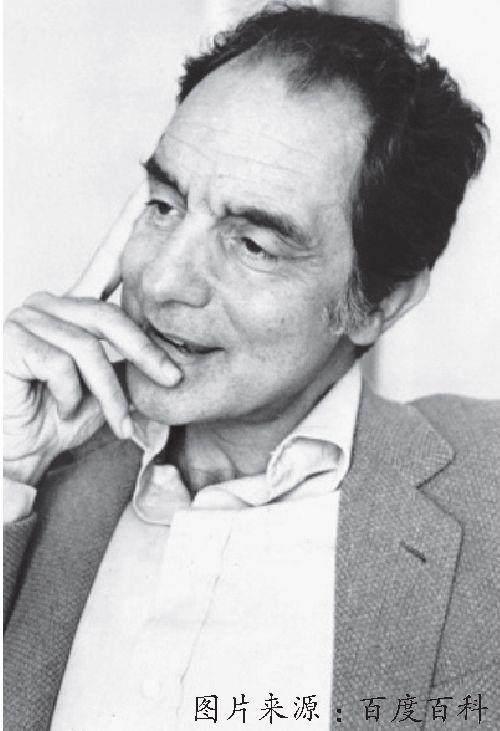
2023年10月15日,是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纪念日。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当代作家。他是和博尔赫斯齐名的大家,也曾有过“南有博尔赫斯,北有卡尔维诺”的说法,但与博尔赫斯相比,卡尔维诺更加平易近人,他的文字充满了大自然童话般的魅力。
卡尔维诺选择了寓言这样一种传统的体裁,又赋予它新的形式和内容,在延续文学传统和后现代文本实验之间,他以一种轻逸、迅捷的笔触表现现代人的异化,却避免让读者深感沉重,这样一种美学追求丝毫不会削弱他对理想的表达,即反异化的追求:呼唤完整的人格和坚实的存在,虽然不能“兼济天下”,但可以“獨善其身”,即获得个体的完善。
金句分享 |
卡尔维诺笔下清醒自知的哲学
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
——《巴黎隐士》
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不自我建设、不努力,就可以得到个人或集体的解放。
——《巴黎隐士》
我所有的自负都来自我的自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我内心的软弱,所有的振振有词都因为心中满是怀疑。
——《看不见的城市》
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以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四处游荡流亡,其实只是掩饰至今没有找到愿意驻足的地方。
——《看不见的城市》
放弃一切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些,困难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你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还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以后又有许多其他东西可以放弃。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不快乐的城市在每一秒钟都包藏着一个快乐的城市,只是它自己并不知道罢了。
——《看不见的城市》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看不见的城市》
从这面到那面,城市的各种形象在不断翻番,但是却没有厚度,只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两面都有画的纸,两幅画既不能分开,也不能对看。
——《看不见的城市》
寓言·童话·乌托邦
在对幻想的痴迷和建构这件事上,很少有人能超过卡尔维诺。他曾借用诗人但丁的一行诗句(《炼狱篇》第17章第25行)“接着下雨般掉入那高度的幻想”,断言“幻想是一个下雨的地方”。
1985年9月,卡尔维诺在哈佛大学主讲“诺顿论坛”讲座时突发脑溢血,为他开颅的主治医生宣称,从未见过像卡尔维诺这般复杂而精致的大脑结构。鉴于20世纪初神经学家已经揭示出大脑高度可塑性的秘密,卡尔维诺这颗高度智慧的大脑及其贯穿于小说创作生涯的高度幻想其实在他孩提时代就已埋下种子。
1925年卡尔维诺刚满2岁,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他们住的那幢别墅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给卡尔维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始终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而别具一格。
卡尔维诺始终坚信,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3~6岁之间——在他学会读书之前。那个时期陪伴他的是各种图书、周刊中的彩色插图,以及各式各样的玩具。当时的畅销读物《儿童邮报》开启了卡尔维诺通往幻想世界的大门,尚未识字反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优点,这使他全然沉浸在书刊中丰富多彩的插图和漫画中,并在其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变体:“我会逐期追看每个系列的漫画——我创造各种变体,把一个个单独的插曲,拼凑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故事,把每个系列中反复出现的元素细加考虑和挑选,然后把它们联系起来,把这个系列与另一个系列混合起来,重新发明新系列,把配角变成主角。”不去顾及那些文字,而是在图画及其系列范围之内悠然自得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白日梦,成了卡尔维诺无限想象力的基石。
13岁之后,卡尔维诺又迷恋上了另一种更加复杂而精致的图像——电影。他自述:“有几年我几乎天天都去看电影,有时候一天去两次,就是我们所说的1936年和战争开始前那几年,总之就是我的少年时代。”电影对于他而言是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银幕中的世界里,他感到了“饱满、必要、连贯”。现实和电影就像两个互有交集的世界,沉浸在一个世界中的卡尔维诺,总会想到与其交错的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我无法再融入那里,因为我已经回到了外面的世界;但同时又带有一种近似于怀念的感觉,就像在边境线上回头望的人。”
现实和幻想是卡尔维诺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47)到《帕洛马尔》(1983),他越发倾向于内在的思考,但卡尔维诺的内在是根植于现实之上的,无论他的幻想之翼飞得多高多远,他所有思考的基点始终是现实世界。
卡尔维诺说:“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是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我们可以说,接受世界本身状态的作家将是自然主义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状态但希望对世界进行阐释并将其改变的作家将是童话作家。”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
⊙ 沈萼梅 刘锡荣
在大众的认知中,“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是卡尔维诺的巅峰之作。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栖息在树上的男爵》(1956)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篇小说组成,有人把它称之为“纹章三部曲”。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像是想逃遁现实,或是干脆倒退到昔日古老的年代中去,以魔幻般的、寓言式的和完全超越现实社会的题材,揭示现代人变态的形象。采用了影射和暗喻的手法,极富有哲理性。
《分成两半的子爵》
《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主人公梅达尔多·特拉尔巴子爵在土奥战争爆发后,跨上了战马,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奥地利国王接见了他,并授予他中尉军衔。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土耳其军队的一颗炮弹击中胸膛,把他从头到脚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半,右半部分的躯体居然还活着,人们把他抬回了城堡。
这个只剩下右半部分躯体的子爵在城堡里过了很长一段隐居生活后,开始外出游逛。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伸手可及的物体分成两半,连苹果与蘑菇也都给掰成两半。他还放火焚烧农民的茅屋和干草堆,牲口和村民都被活活烧死,就连从小抚养他成人的奶妈也险些丧了命;次日,子爵硬说奶妈脸上的烧伤是麻风病症状,下令把她关进了麻风病院。因此人们称他为“邪恶的子爵”。
过了不久,村里出现了另一个与梅达尔多子爵一模一样的怪人,那就是他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掉的左半边身躯,当时被埋在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的尸体下面了,后来又被当地的两位隐士用油膏和香料医治救活了;梅达尔多这左半部分躯体回到故乡后,到处行善,助人为乐,劫富济贫,帮助寡妇干活,还去麻风病院看望奶妈,所以人们称他为“善良的子爵”。放牧的姑娘与他不期而遇,他们相爱了。
“邪恶的子爵”对“善良的子爵”恼恨极了,竟派遣手下的卫兵去谋杀他。但由于“邪恶的子爵”的专横暴戾早已引起手下人的不满,卫兵们不仅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反而请求“善良的子爵”率领众人起义。善良和美德感化不了邪恶,于是一场决斗终于发生了,两半子爵各持一柄利剑,厮杀拼搏,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们先后被对方的利剑沿着原来被炮弹炸开的伤口从头部直劈脚跟,立时双方鲜血直流,扭作一团,当初那两半身躯劈开时的伤口又粘在一起了。
半个小时后,村民们抬着一副担架来到城堡,见躺着的是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子爵,他伤势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在护士和大夫们的日夜精心护理下终于苏醒过来了,“子爵重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好也不坏,是一个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就是说,从外表看来,与没有被炸成两半之前的那个子爵一模一样”。
这不禁令人怀念过去的身体,也让人想到善良子爵曾讲到的一句话:“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痛苦,理解每一个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
小说采用一个骑士式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把当代社会在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当今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社会使人异化、使人失去了自身的人格存在并造成人的本性退化和衰落的写照。
目睹社会中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作者像是作出一副苦涩的怪相,露出一种讥讽的微笑;作品的格调郁闷、伤感,如小说的第一章就展现了横卧疆场剖腹开膛的战马,断肢残臂的官兵,还有因鼠疫蔓延而丧生的人们。
这篇寓言式小说的结构是几何形的,把现代人兽性的“恶”和理性的“善”对称地一分为二,后又重合在“完整的人性”之中。作品所要表现的道德宗旨是理性制服兽性,善良战胜邪恶,教诲人们要克服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各种潜在的敌人,不做一时发作的兽性的俘虏,做一个真正的有完整人格的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在人世间犯下了许多罪孽,在行善积德之后变得成熟了,从而重又理智地获得了完整的人性。
《栖息在树上的男爵》
《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的故事发生在1767年6月15日,那天主人公科西摩·比奥瓦斯科在其父母特意邀来做客的达官贵人就餐席间,竟然厌恶地把仆人端上来的一盘蜗牛推开了,他父亲当即大发雷霆。科西摩一气之下走出餐厅,只见“他爬上了冬青树,身上穿着赴宴时穿的考究的礼服,这是他父亲严格规定的,尽管他只有12岁……”。
原来科西摩早就忍受不了贵族家庭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了,他那对公爵的头衔垂涎三尺的父亲,一心考虑的是贵族家谱和继承先辈家业,热衷于同远近权贵的争斗和倾轧;他那出身将军世家的母亲,终日厮守着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以编织度日。对于笃信旧式礼仪和家教的父母亲,“如果就餐时有誰从盘子上抬起眼睛或者喝汤时发出轻微的响声,那可就不得了”。科西摩还妒恨与父亲同父异母的那位当律师的骑士叔叔,他面容丑陋,又善于弄虚作假,可他是家父唯一信赖的人,既是庄园总管,又是水利工程师。他更讨厌那一直未嫁人的姐姐巴蒂斯塔,她整天冲人高声嚷嚷,以发泄自己积郁在内心的怨恨。
“蜗牛事件”只是个导火线。有一天,那位当律师的叔叔带回家一篮子食用蜗牛,后来被放在地窖的一个木桶里,科西摩和弟弟(故事的叙述者)在桶底挖了一个洞,还为可怜的蜗牛铺了一条逃生之路。夜里,当主管全家膳食的姐姐巴蒂斯塔发现蜗牛都逃跑了时,居然鸣猎枪报警,召唤众人举着火把四处围捕起蜗牛来。父亲发现了木桶底下的窟窿,猜出是科西摩兄弟俩所为,就用马鞭抽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科西摩兄弟还在一个阴森的小屋里被囚禁了3天。当6月15日中午科西摩被第一次放出来与家人共进午餐时,姐姐却端出蜗牛当主菜,所以激怒了科西摩……
栖息在树上的科西摩经受了生活的种种严峻考验,为了求得生存和摆脱险境,他不得不与大自然展开殊死的搏斗:他用弟弟给他的猎枪捕获野味,学会了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原始烹调方法,用吃剩的野味与农民换水果蔬菜;还学会了在洗衣盆里用肥皂洗衣服,然后在树杈上晾干;他与一只母山羊交上了朋友,学会了挤羊奶喝;他还与一只母鸡达成了协议,让它隔一天在树洞里给他生一个鸡蛋;后来他还从树上往水塘里撒下钩子钓鱼吃。
他虽然离开了家庭,在树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但他仍然关注家庭成员的行踪,他爬到教堂旁的大树上聆听全家人做弥撒,还躲在梧桐树上旁观了姐姐的婚礼。他栖息在树上,居高临下,发现了骑士叔叔默默为全家人所做的一切:养蜂、指挥兴修水利等。从此他与叔叔之间产生了一种理解和默契。他还爱上了第一天爬上树时曾遇见过的姑娘维奥拉,后来她成了一位老公爵的遗孀。那位姑娘仰慕科西摩超凡的毅力,也使科西摩领略了爱情的甜蜜和失恋的痛苦。科西摩还目睹了拿破仑时代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世事沧桑……
后来,在树上栖息了长达65年的科西摩衰老了,他已向众人显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但他坚持不从树上下来;他的病情恶化了,人们把一把安乐椅和一张床抬上树,但他却骑在一个枝杈上,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一动不动地坐在树上,身子已经呈半僵硬状态了。最后,科西摩从树梢上窥见从一个英国人驾驶的热气球上抛下一个带着长长的绳索的锚,当绳索从树旁擦过时,他轻捷地攀住绳索远离而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
小说通过年幼的男爵在树上栖息的生活经历,隐喻了现代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生活,就得脱离这个可恶的现实社会。
《不存在的骑士》
《不存在的骑士》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法国查理大帝的时代。一天,查理大帝检阅集合在红色城墙下的一支庞大的部队,他一一盘问了在眼前走过的士兵的姓名。一位骑士准确地向陛下报告了自己所率部下的人数和所建树的战功:“五千名骑兵、三千五百名步兵和一千八百名侍从,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达五年之久。”查理大帝满意地听着那位骑士的禀报并加以褒奖。在队伍中有一位“穿着一身镶黑边的白色盔甲,盔甲上没有一丝碰坏弄脏的痕迹,全身潔白无瑕,各部位衔接紧密无缝,头盔上还插有一根顶翎羽饰,像公鸡的头冠一样五彩缤纷,光彩夺目”。查理大帝发现这位白盔白甲的骑士后,顿时惊愕不已,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全身装束得如此洁白严整的骑士。当查理大帝问他为何上下一身洁白时,骑士不直接回答,只报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阿杰鲁尔福·埃摩·贝尔特朗迪诺。骑士不摘头盔,也不对陛下露出自己的面容,查理大帝只听得从头盔底下传出来这样一个清晰的声音:“因为我是不存在的,陛下。”
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没有肉身的骑士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别人的身体:“使他更受刺激和更为恼火的事情是看见从帐篷边沿里伸出来一双双赤裸裸的脚丫子,脚趾冲天翘起。沉睡中的军营成了躯体的王国,古老的亚当的肉体遍野横陈,腹中的酒气和身上的汗味蒸腾向上。”当那些看似正常而规整的肉体做着淫邪烂俗的事情时,这个“空心”的人却比任何一个角色都更具有骑士的精神。
这位与身上佩戴的盔甲已合为一体的“不存在的骑士”,正是现代人“机器化”了的象征:人们与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担负的职能已融合为一体,麻木地下意识地从事着社会为自己安排好的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社会意识。
小说语言幽默含蓄,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如种菜人古尔杜鲁,就是个“实实在在地在菜园子里干活的人,他与绿色的野生的自然界融为一体,而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全身套着盔甲的阿杰鲁尔福终日机械而又准确地做着各种动作,但他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尽管他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但他总不能如愿以偿;由于他所从事的又是一场荒谬而又残酷的战争,一场基督教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所以他总是竭力从自己的过去中去寻求自己生活的意义。
“明天黄昏日落时,我将会怎么样呢?我能确认自己是个人了吗?能确认自己在行走过的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吗?”这位“不存在的骑士”向往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暗喻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焦虑不安的心态及其不稳定的地位。最后戴白盔穿白甲的骑士消失不见了,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综述
“我们的祖先”寓言三部曲从不同层次上含蓄而又幽默地揭示了现代人体现自我存在和向往自我解放的心态:《子爵》篇抒发了被现实社会截肢解体了的现代人想完善自己和使自己变成完美的整体的愿望;《男爵》篇则是表现主人公企图以逃遁现实的自我抉择来达到封闭式的自我完善,揭示了人类与其共存的社会的无法相容;《骑士》篇的主人公则力图通过实际上“不存在”的“自我存在”,来赢得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卡尔维诺作为寓言式作家的文学地位。作者似乎超脱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后退到古代社会,借助叙述先人的故事,以寓言式的魔幻般的题材,让主人公以“子爵”“男爵”和“骑士”等贵族头衔出现,却又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关系。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说道:“由于原始人跟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可以说他自身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跟任何其他有机物质的存在别无两样;而原始人进化到现代的人之后,由于他跟生产和经济发展进程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整体,所以他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人与一切都融为一体了,没有摩擦,而且他与四周围的一切(自然与历史)都不发生任何关系(与之进行斗争或通过斗争达到和谐)。”(《我们的祖先》出版前言,1960)
卡尔维诺的作品用寓言故事般的格调、寓言式的人物、寓言式的节律揭示了现代人存在价值的蜕化,阐明了处在一切都已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的现代人实际上都已沦为“一样东西”,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卡尔维诺以辛辣的笔触谆谆告诫读者,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现代人有如工厂里的机器一般,被8小时工作制或7小时的坐班制所羁勒,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窒息并捆绑着人们,却又以不断丰富的物质享受赋予他们近似于“幸福”的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