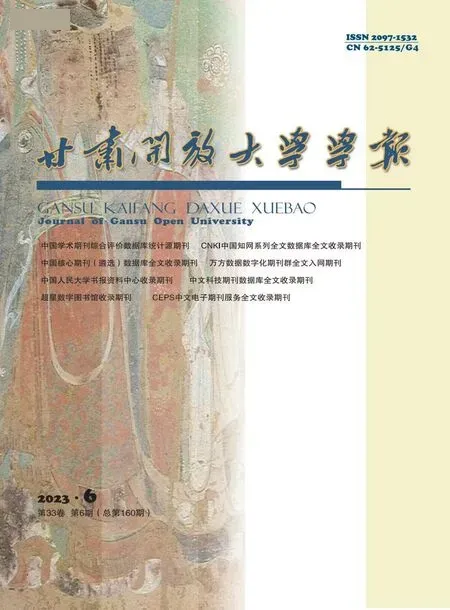“狭窄的心”与“大的宇宙”
——论冯至《山水》的艺术哲思与世界性视野
罗占婷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山水》收录了冯至的14篇散文,这些散文既是冯至人生轨迹的确证,也是他关于创作、艺术与文化看法的映射。“山水”对于冯至来说不仅是一种人生观、更是文化观与艺术观。在《山水》中,冯至将“自然化了的人”看作是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认为“它们都和山水树木一样,永不失去自己的生的形式”[1]115。如果说生命之思是冯至《山水》表现的重要一面,那么关于创作、艺术与文化的思考也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在《山水》中,冯至受西方绘画与雕塑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抽象写意式的熏陶给文本营造了雕塑般的立体感与去时间性的静默感,引发了他对于“美”的本质何为以及“美”如何呈现的艺术追问,进而又催生了他对于“中国—世界”的文化关系思考,具有独特的艺术性、丰富的思想性以及复杂的文化意蕴。但是目前学界对冯至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其诗歌创作尤其是《十四行集》上,相对忽略了《山水》的重要地位。虽然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冯至《山水》的文化价值,但他们的研究多是从“存在主义”视域出发,分析其中的生命意识,如解志熙的《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2]、陈邑华的《灵魂里的山水——论冯至散文集〈山水〉》[3]等。这些研究相对忽略了冯至作为孤独的“沉思者”,不断“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新生”的过程。基于此,本文从《山水》中的“艺术哲思”和“世界性”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冯至的艺术和文化思考,进而分析冯至的文学观以及《山水》的文化价值。
一、从“艰”的人生到“涩”的创作
回溯冯至的文学之路,大致有这样一条脉络:早期对五四浪漫抒情与感伤文学风尚的推崇,当这样的创作风尚开始滑向“感伤自恋”的趋向后,他转而推崇周作人倡导的“涩”的文学。其一,因为自身“艰”的人生经历。冯至年幼丧母,虽然继母给了他同样的母爱,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冯至内敛沉默的性格,表现在创作上则呈现为幽微与节制。北大求学时孤独的体会、哈尔滨任教时清苦的生活体验以及辗转南下到西南联大随时遭遇战争空袭的威胁又加深了他的人生体悟与生命思考。这起伏的人生经历促使冯至意识到浪漫抒情式的创作不能完全将人生与生命的全貌囊括进文章之中,从而萌生从幽微的感伤抒情转向“涩”的文学的创作想法,这是个体生命思考与现实不断交织之后纵深的心灵沉潜与超越。
其二,1928年冯至返回北京,在京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他渐渐与周作人身边的一些讲究趣味的言志派文人接近,周作人的创作思想开始成为他关注的对象。1929 至1930 年间与周作人的弟子废名合办《骆驼草》文艺刊物让他更系统地接触了周作人所提倡的“涩”的文学观点。“涩味”与“简单味”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两大审美追求,对此,钱理群总结道:“周作人人生哲学与美学的真谛就在于“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4]这与冯至1930年6月20日刊发在《朔风》第4期上的文章《涩》的文学思想不谋而合,“我不但不希望天官赐福,手持白玉如意走入我的梦中,我反而想多多地遇见几件不如意的,艰涩的事以了此一生。我的道路太贫乏了”[5]1-14。冯至深感过于“顺畅”的文章对生活与人性的体味明显不足,适当增加文章的“涩”度才能将生活、将人性往纵深处写去。
“涩”是周作人看透人生的虚妄之后如品苦茶一般地品味人生之苦因而颇给人“涩味”之美感的散文。显然,周作人关于“涩”的核心观点是在“洞察‘人间苦’、看透人生虚妄之后,既不再执迷人生却也不厌弃人生,而是折中西方的唯美—颓废主义和东方佛道的释然达观观念,着意要在“不完全的现世”里“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显示出一种以品味人生涩苦为美感的唯美——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5]1-14。周作人“涩”的文学是由反人生之“艰”所到达的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这恰恰与此时冯至的生命思考高度契合。在《涩》中他说到:“看透了人生,觉得不太好,也不太坏,将来既不光明,也不黑暗,因此而更自加警惕,黾勉地生活着,体验着,于无可奈何中为人类作点好的事情的人们,我却更爱他们。”[5]1-14冯至爱着的这些人,正是《人的高歌》中的石匠、修灯塔的渔夫,《忆平乐》中的裁缝,等等。他们的生活固然艰苦,但他们全然不把“艰”当作生命意义的全部,而是在人生的“艰”中体验生之忧患带来的“苦乐”,这样的生命哲思体现在冯至的创作中,便是“艰”的人生转向“涩”的文章的智慧。
如果说冯至由人生之“艰”转向文学之“涩”是自然而然的过渡,那么里尔克对其精神启发则是一种契机,是一种“神”(域外)的力量在召唤着他。在给杨晦的信中他就说道:“我曾经幻想我的将来的诗,要望向那方面的努力:做一首诗,像是雕刻家雕塑一座石像。”[6]119里尔克的文学思想以及他对罗丹与塞尚的推崇又让冯至在绘画与雕塑的领域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突破口,大大增加了其文章的“涩”度。
在德国留学期间,冯至开始探求中国传统抽象的写意手法如何与西方实体存在的绘画与雕塑结合是他转向“涩”的文学的具体实践。他思考如何将自己以德语文学、德语思想家和存在主义哲学为背景的知识与思想转化为具有本土性、能为普通读者和报纸刊物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也即如何把“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一颗老树》中老人静静地坐在石墩上,俨然如西方著名的雕塑思想者那般,但是,老人的神情中携带了他一生中的风雨骤变,且这样的骤变还在无声的继续着。看似静止的画面中实际暗含了历史与岁月的涌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少女、羊与鼠曲草构成了一幅恬静美好的画面,坐着的少女在周围环境的衬托下,具有一种近似乎“神”的意义。西方雕塑“凝定”式的手法与中国传统写意式手法的完美结合,不仅表现了冯至在文学创作上所做出的新尝试,也显示了冯至意在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写景抒情的创作方式与西方雕塑与绘画相结合的野心。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回望与总结,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另外,冯至在创作中特别注重“时间”在文本中的“呈现”。因为“时间本质上沉沦着,于是失落在当前化之中”[7]419,冯至将自然山水中的事物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但这样的写作策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将“时间”剥除,而是将时间手中执掌的宇宙万物生命的无上权杖拿掉,此时时间就和宇宙万物并列一起沉浮,“此刻”“当前”才会与他相遇。并且,时间在《山水》中已经没有意义,万物在他笔下都是超时间般的存在,他断然切断人与物的历史性存在,只做横向的延申而避免纵向的深入。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他写道:“在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它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其中可能发生的事迹,不外乎空中的风雨,草里的虫蛇,林中出没的走兽和树间的鸣鸟。”[1]73在这里时间似乎停滞了,自然被排除在人类历史之外,不论人类历史怎样变化无常,自然都是百年如一日,不起任何变化。自然的永恒性在去时间性的存在中得以彰显,时间的延续性在万物舒展开来的时候悄然隐身,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永恒,永恒又在人们的默然与放置中变成了一种静默。自然的演变、生命的新生和消逝以及人生形式的变化在去时间性的有限空间中达到了永恒与不朽。
冯至自我更新的思想激越促成了他由“艰”的人生向“涩”的文学的过渡,与此同时,雕塑般的立体感与去时间性的静默感更加深了他文章的“涩”度。冯至这一创作转向是他在经历了创作低迷期之后力戒相沿成习的人化自然、别有寄托的浪漫化抒情态度,这种观察和写作的姿态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山水抒情。这不仅是冯至勇于转变《昨日之歌》《北游》里惯常的浪漫抒情方式,更是他自我人生形式更新的有力印证。
二、“美”的本质追问:让“存在者成其所是”
冯至对于艺术本质的思考也是《山水》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冯至对于艺术始终有一种执着的精神,“美”的本质是什么?“美”如何存在?如何去表现“美”是他创作更新之后的持续追问。留学德国期间,他接触了歌德、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尼采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等思想,中西思想在他身上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致使青年冯至无时不陷入自恼与自我怀疑中,但同时这样的纠结也给了他艺术上的启发,使他对创作、艺术有了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他被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诗里的一句“因为美只不过是恐怖的开始”所震撼,随之产生了这样的感叹:“世界是深沉的,还有许多秘密未曾揭示。美和一切庄严的事物只是要求放心大胆地去将其把握和忍受。但是在这些面前我总是惊讶地停步不前,没有足够的勇气踏进去。”[6]152-153他深知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对艺术的本质认识还有很大欠缺,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可知冯至对艺术的思考并不局限于艺术本身,而是延伸到了人生价值,文化经验之上,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并未与其他人类事务分隔开,而是被吸收进个人的和文化的经验的整个范围中去,却并未消弭作为一种经验模式的个性。”[8]
《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写了一个青年为一名少女的微笑所吸引,将自由的少女拘禁起来,用尽各种方法想要把少女的微笑雕刻出来,结果却不尽人意的故事。青年雕刻出来的微笑不但与天使的微笑相去甚远,而且他的自我否定也将少女逼入了绝境。青年想把天使的微笑引到人间的想法遭遇了失败,这不光是青年雕刻家的失败,也是青年冯至对艺术看法的改观。青年雕刻家想当然的以为“天使”最重要的是它带着超凡微笑的面庞,冯至认识艺术的过程和这青年一样,最初认为艺术是浮于表面的外在物,即“美”的装饰,但殊不知“美”的装饰绝不是“美”本身。青年“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腻脂的石块”[1]26,用上最好的材料去从事如此这般神圣的事物,但他所雕出的面庞没有一个使他满意。于是青年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态度不够诚恳,太过于小心了,但当他放开胆子时天使的微笑也越雕越远了。他十分沮丧,“他看他是一个没有根源的人,不配从事于这个工作”[1]28。他的沮丧颓废将少女一步步逼退,最后他只得到了一副少女的“死面具”。
在这个凄美的故事中,青年雕刻家想将原始空间(修道院楼上)里的“美”呈现在一个充满现代性的空间(礼拜堂里的神身边),他机械地将少女的微笑模仿出来,把少女从存在的坏境中剥离出来,试图将神秘的想象力实体化,但却遭遇严重的失败。这个故事可以说是青年冯至在文学创作中内心的自化,物体形象与人的联结,隐藏的是转喻链条形成形体的变异,转而成为作家精神的投射。在此,冯至实质上有意借这个凄美的故事来反驳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柏拉图美学思想受知识论的制约,“力图经由或者利用一个个具体的审美活动去达到‘美本身’,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审美活动的时间性过程特性被忽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审美价值的湮灭。”[7]419青年雕刻家妄想用“雕刻”的手段将不可捉摸的神秘微笑复制在没有生命的实体上是不现实的想法,这种实践在创作上来说不是一个主体以一定的距离去描述一个客观的表象,而是将自己的一己之见加诸于物体之上,背后隐含的是冯至对主客体关系、认识论的全新理解。同时也映射了冯至对“模仿说”的质疑,“模仿说”生硬的创作过程让冯至感到反感,他决心摆脱这种复制般的创作手法,不再醉心于事物表面的装饰而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在他看来,艺术家单纯地呈现外部是无法到达“美”的,只有去探寻“美”的本质,才能够达到“美”的完整呈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悖论,即“美”本身的“美”震撼人心与“美”的本质的艺术呈现的不可能性以及“美”的本质永恒性的存在。如何抓住“美”的本质而不是“美”的装饰是冯至一直在思考的艺术问题,他不把“美”的对象从大环境中抽离出来,他只是在大环境中将“美”呈现出来,这是他一个重要的艺术观点。
冯至对艺术的看法与里尔克不谋而合,“人不应在物质的去感觉它为我们而含有的意义,却是要对象地看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9]具体来说,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也即主体放弃自己至高的位置,将自己所带有的先前之见抛诸脑后,不再把“物”当作一个“客体”来认识,而是将主体与物共同置身于同领域中,窥探“物”的变化时刻以及万物间相似的结构,以达到对“美”本质上的认识。
冯至对于艺术的思考是立于现实的基础上的,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唤醒个体生命自觉、积极承担有意义的人生的手段,是冯至在艺术之路上迷惘时候的坚定选择。他对“美”、对艺术的本质追问都是经过灵魂的燃烧或沉埋而引发的创作之思,他永无厌倦地在艺术世界里翱翔,探寻自己的人生与创作之路。
三、“狭窄的心”与“大的宇宙”
冯至对于文化的思考是建构在创作与艺术之上的,其中潜藏着他的个人经验世界。在他身上分别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子,他思想上的二重性决定了他对于文化的思考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也决定了我们研究冯至时不能不考虑他对两种文化是如何整合与更新的。考察冯至在《山水》中对文化的见解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可知《山水》的创作历时十多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地变化,五四以来宣扬的“人”的主体性开始被国家主流话语掩盖,个人追求与价值实现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难以为继。同时,随着冯至人生阅历的增加以及创作态度的改变,对于文化的看法也难免发生改变。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动,冯至对文化的看法经历了从“小同”到“大同”的转变,也即从“民族的”文化到“世界的”文化过渡。在这其中,冯至是怎样在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创造了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灵魂里的山水?何以实现这样的创造?其中隐含着作家怎样的文化心理机制?
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学者们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缺少本土性的肯定,多数将之视为是对西方的模仿和靠拢。但既然中国文学被纳入了世界格局之中,那么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世界性的因素单方面对中国文学施加影响,也完全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两者的双向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作家本身的创造力,正是中国作家本身的创造力和自觉的文化意识,让中国现代文学不至于迷失在“世界性”的漩涡中。
冯至的创作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性的生存环境中的经验表达。鲁迅很早就洞见冯至的这种思考并作出了评价:“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10]在冯至生活的时代,救亡图存是冯至外在生活的核心,在外界的纷乱侵扰下,冯至开始思考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勇敢地决断和选择,而不在于决断和选择什么。”[11]这看似与中国儒家倡导的“不舍弃”相悖,但实际上使冯至的思考超越了生活和现实的窠臼,而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两句诗》就以在林径里看到的贾岛的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树息树边身”想到欧洲诗人写到的青年在水边看到自己的倒影,进而想到中国的明心见性。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相通之处。《罗迦诺的乡村》中,作家行旅到瑞士东南的特精省罗迦诺城,虽然他认为这里的一切给了他在故乡一样的感觉,但他们一行人却对居住在这里的人极不信任,害怕邮局里的人会将自己的信件弄掉,认为送煤油的小厮没有将煤油送到等诸件事表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但最后他又说:“在这些人中间住不了几天,大家便熟识了,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把皮鞋脱去,换上家乡的布鞋,把领带抛开,换上反领的衬衫,时表也用不着,锁在箱子里,自有那日出日落给我们正确时间。”[1]55可以看出冯至不满足于抽象地讨论个体生命孤独存在问题,而是把对中外文化传统和现实人生的批判考察结合起来,这使得本来很抽象的外国的人生观念就被中国化、通俗化了。
这种转化方式是何以实现的呢?何以不会让读者觉得他的创作没有“穿着中国衣裳,脖子上系着一条西服领带”[6]139之感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冯至在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和抉择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超越了现时存在,创造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范型和新视野。在《山水》中,冯至没有刻意突显传统,但中国传统的文化根脉无意识地影响着他的写作,与西方哲学相印证、相整合,一同构成他的生命哲学与文化自觉。同样在《十四行集》中,他既歌颂了歌德、梵·高,也赞扬了杜甫与鲁迅。在这些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心在理解与领会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超越所获得的“一个大的宇宙”。中国儒家传统宣扬的“大我”与西方存在主义宣扬的“个体生命孤独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异质性,但显然,冯至对两者加以合理的扬弃,把独立的个体思考积极引入“大我”的值阈中,使两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蒙古的歌》里作家对蒙古有着刻板的印象,“蒙古是一个野兽,是无愉快的。石头是野兽,河水是野兽,就是那蝴蝶也想来咬人”[1]9。此时的作家沉浸在自我的认知当中,对于俄国人唱的蒙古歌的意义,只是觉得新鲜。但俄国人的回答让他即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那不过是片面的观察罢了。什么地方没有好的歌呢。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过我们文明人总爱用感情来感染人,像一种病似的”[1]14。一个外国人对于不同文化间的理解是可以超国界的,而作家意识到的世界反倒日渐狭窄,这里不仅有作家对自身的反思与自愧,更有对于世界性文化的思考,即文化不应该存在国界,各个民族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将之刻板化与简单化,就像作家在《十四行集》里写的“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12]便是作家此时真实的文化心理写照。
冯至对于文化的思考一方面是基于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与超越,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于歌德“决断”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舍弃”的赓续,正是在两种文化的整合下,冯至对于自身、生命意义、“中国—世界”文化的思考才形成了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又脱胎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现代新型知识分子范式,由此获得了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世界性文化视野。同时冯至不断地在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整合与超越中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颗狭窄的心”以及“一个大的宇宙”。
四、结语
冯至《山水》的创作之思、艺术之思与文化之思是建立在自我更新的生命求索之上的,对于创作的思考让冯至得以从五四以来浪漫——抒情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向着“涩”的文学深掘。同时,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影响让他的创作呈现出类似于雕塑般的立体感与去时间性的静默感。中国传统的审美体验方式让他摆脱了存在主义哲学思辨的玄奥与抽象,而存在主义的冷静与哲思让他脱离了浅层的情感缠绕而走向了生命的深度。对于艺术的沉思让他得以在平凡的世界里寻觅“美”以及“美”的本质何为,对于文化的思考让他得以超越“中国—世界”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超脱不同文化的局限。他在《山水》中的创作、艺术与文化之思迸发出了巨大的思想火花,在沉潜、探求与超越中不断走向生命的成熟与人的旷远。
——冯至《蛇》的一种读法